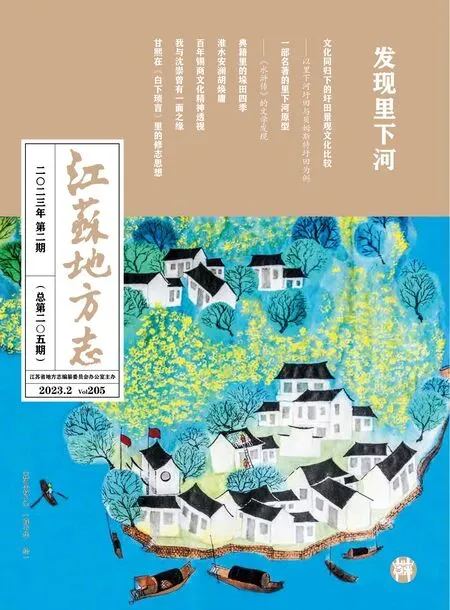民国方志学术研究综述(下)*
——基于两轮修志期相关成果的综合研究
◎潘捷军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浙江杭州310025)
三、民国方志学若干研究成果及相关人物研究选介
如果说本文前两部分“‘方志学’的创立与发展”是着眼于方志学史脉的纵向梳理,“基本体系和若干重点研究”是侧重于研究方志学科体系的横向架构,那么以下这一部分则无疑是一个个具体的微观点,从而有助于从“线”“面”“点”纵横交错的整体层面,来进一步考察新时期民国方志学研究的总体状况。除前已涉及的内容外,现再择要介绍以下几个“点”:
(一)《中国近代方志学》及许卫平的民国方志学术史研究
从方志学术史构建角度看,许卫平的近代方志学术史研究是新时期中为数不多的专以近代为主题的系列研究,当然具体又包括晚清和民国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民国研究角度看:
作者较早在《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论文中,在介绍了“编修了众多的志书”“兴起了空前的研讨热潮”等民国方志事业发展的环境背景后,还着重介绍了民国方志学的总体特征:一是通过“方志基本理论认识有所深化”(包括方志定义、性质等问题)和“方志编纂理论进一步完善”(包括义例、志例和记述内容等问题)等两个方面,“发展了方志学理论”;二是通过“方志目录学的建立”“方志整理学的发展”“方志史料学的创立”和“方志发展史学的产生”等四个方面,“完备了方志学的分支学科”。[1]
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稍晚出版的专著《中国近代方志学》中,又从方志“基本理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编纂理论研究的深化与完善”和“各分支学科的形成”等几个方面,进一步作了深化研究和阐述,并相应勾勒了民国方志学的基本框架。同时也正如书中所言:由于时逢“乱世”,因而“民国时期比起封建帝制统治下的时代,尽管进步得多,但毕竟还处于旧时代的变化延伸之下,其文化必然会受到旧时代的羁绊。”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认为,尽管它还尚不完善且具难免的时代烙印,但作为重要过渡,它既是对清代章学诚初创方志学的延续继承,同时也标志着“学科意义上的方志学开始形成,并且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二)梁启超创立“方志学”的重要贡献
如果承认民国在中国方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那么应首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大批史志学者为之所作的突出贡献。当然,学术界也认为:“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3]其原因自不待言,这在一定意义上似应更重梁启超为之所作出的贡献。
与章学诚在清代方志学史上的地位一样,作为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学术大家之一,梁启超(1873——1929)在民国方志学史上的地位同样居功至伟,其最重要的贡献可能也就在于“方志学”的首倡,因而也是新时期的研究重点。除一些方志学史著作有不同程度涉及外,刘光禄、胡巧利、廖菊楝、周生杰、曾荣、韩章训等学者,都先后作过相应的专题研究。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方面,是梁启超以所创“新史学”为其后创立方志学而产生的引领之功,这也是方志学创立的重要历史环境和学术基础,如他视“新史学”为“国民心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即为典型之例。因而“怀有新政治诉求和新史学理念的梁启超意欲超越以往修修补补的做法,实现带有根本性的整体重建,即推倒以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建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编纂体系”。[4]有研究进一步分析认为,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标志,梁启超还创立了一整套比以往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在“破”与“立”两个方面“既否定了封建史学的一统天下,又为资产阶级新史学指明了方向”。[5]
另一方面,是“方志学”的直接创立之功。由于学术界历来视方志学为史学重要分支,因而梁启超自然会由此及彼而关注传统方志学的时代变革。事实上从其上述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指向和“新史学”的建构体系,特别从其时方志事业的转型变革之风,就可直接所见其“新史学”与方志学的关系和引领所在。正如有研究所言:由于梁启超“指出了方志‘亦代有进化’,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研究方志,因而超轶了前人。这比历史上有些人一味推崇宋志,全以宋志为圭臬是前进了一大步。”[6]
以往学术界还多认为: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梁启超也明确认为“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但章学诚虽“把方志提到了与正史并等的地位,却没有把方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认识和探讨,在他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方志学’一词。”[7]而正如傅振伦所言:“正式确定方志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正是梁启超。其重大贡献就在于在历史新旧转换的关键时期,以“新史学”等新思想同样引导引领了方志学的历史转换,主要标志便是1924 年发表的《说方志》以及同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当然从方志学发展史脉看,没有章学诚就没有梁启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梁启超之所以能在前者基础上又进一步,研究多关注了其所构建的学术体系框架。例如在《新史学》中,梁启超首先把中国史学分为10 类,第7类便是地方志。在此基础上,他还对方志的性质、意义和价值,产生和发展过程,方志史料的搜集、整理和鉴别,志书的体例、篇目设计,以及修志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等,涉及方志发展史、基本理论和编纂方法等学科体系的各方面问题,均做过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
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梁启超的方志学术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提炼。例如,韩章训以多篇论文的形式曾对梁启超做过重点研究,并将其方志思想总结概括为三方面:一是“观念论”,包括方志观念说、概念说、生成说、发展说和方志学说;二是“编纂论”,包括事业说、为谁服务说、修志人才说、修志方法说;三是“文本论”,包括志属史说、志书作用说、表达体式说。同时该研究还概括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观点:如认为之前从未“有人对‘方志概念’进行过理性思考”,而梁启超“率先提出‘方志概念’的学术意义,就在于它为近代方志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支点。”又如认为自唐代始,就不断有人论及方志起源问题,但多局限于起源何时、何事或何书,这种空泛简单判断“是缺乏应有说服力的,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而梁启超“则独辟蹊径,分滥觞、成长、定型三阶段进行解说,这样就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方志生成的基本脉络,故被许多后人所肯定和继承”。同时该研究还指出了梁启超“长于方志思想观念的阐释,短于方志体例的论述”等不足,这应与他缺乏志书编纂实践有关。[8]
作为思想学术大家,梁启超一生所涉及范围很广,方志学仅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同时也难免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又有史志学者认为,在其涉及的众多学科中,应以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同时也正因史志关系的密切程度,因而即使是很小一部分,却使方志学迈开了历史性的一大步,并引领了民国方志事业的发展前行。
(三)民国其他方志人物的有关研究
由于民国在方志学史的重要地位,除梁启超外,还有一大批学者同样是新时期学术界研究所关注的重点。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有:
1.民国方志学者群体研究
例如,黄燕生在新时期第一轮修志期的相关研究中,以傅振伦为例,勾画了民国方志学家的群像。研究认为:“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一端系于传统方志学的余脉,一端开启现代方志学的诞生。”为此该研究包括其他研究也多认为,处于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直至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要变革的风口浪尖,这一代方志人“与旧学的感情既难割舍,但在如何看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其思想观念又与他们的前辈迥然不同,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批判精神”,以及刻骨铭心的民族危机意识和民生家国情怀,以此为动力,“民国学者不但把方志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分支加以研讨,而且亲身参与方志编纂,并在修志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自觉与‘旧史学’划清界限,从而使民国时期的方志学展现了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重新给方志定义,一是彻底改造方志。”[9]
姚伟则从对传统方志学的扬弃角度考察了相关问题。作者在文中指出:以往有“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如果一谈及方志学,则言必称章氏之说,实为后人汗颜。”文章进而从几个方面概述了民国志家的共同特点:一是在史志关系这一制约方志发展的前提命题上,他们既多认可章学诚“志属史体”的传统论见,同时又意识到“仅承认方志是史,未免失之偏颇”“方志的性质也就应该具有多重性”;二是注意到民国方志学家以进化史观、民生思想等先进思潮对其时方志界的影响引领,以及将新兴经济、科技等方面内容引入新志的具体运用;三是介绍了志书形式应“文不拘体”“以后方志,决不当再以文章体裁分类”,志书内容“不贵应有尽有,而贵应无尽无”等诸多辩证理念和创新方法。在介绍上述基本共识和特点的同时,文章也介绍了其时存在的各种不同争议。文章最后指出:尽管这一代方志学家也存在不少局限缺憾,但当时“能有如此的精神,取得如此的成果,亦属难能可贵”,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勇于创新和变革,也就不可能为我们留下这些值得借鉴的遗产。”[10]
在新时期第二轮修志中期,沈松平在出版的《方志发展史》专著中,同样以“民国方志诸家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扬弃”为题作了专题考察,同时相对更侧重于与章学诚传统理论比较,他们在志书新理论、新方法上的创新探索。例如认为“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一大特色是注重志书的实用价值”,民国方志诸家则既给予继承,更有所创新。恰如文章引用吴宗慈所言:章学诚“所谓实学者,乃偏重于史裁,若今日则方志所重在实学,乃为一切民族社会、经济与科学问题。”从而不仅为“经世”传统赋予了全新内涵,而且彰显了民国志家革新求变的时代特征。作者还以黄炎培所纂《川沙县志》、陈训正所纂《鄞县通志》等多位学者和多部志书为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在降低人物传记地位、独具一格编纂大事记、开创“概述”“索引”先河等从体例到内容的诸多变化。最后还指出了其志书形式仍习惯囿于旧文体、理论与实践脱节以及内容仍有诸多封建糟粕等若干弊端。[11]

部分民国方志学研究著作
2.有关人物专题研究
处于转型变革期的民国方志学术,可谓学派频现,名家辈出,除上述梁启超简介和民国方志人物综述外,以许卫平《中国近代方志学》和仓修良《方志学通论(修订本)》等方志史著作专列人物为例,新时期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还有以下几位方志名家(以人物卒年为序)。有的虽卒于新中国成立后,但其方志学成就主要在民国时期。
“兼取两家,各有所继”的缪荃孙。缪荃孙(1844——1919)系江苏江阴人,晚清民初著名学者。他曾受命创办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有“中国近代图书馆鼻祖”之誉,并曾任清史馆总纂等职,也曾参与从晚清到民国的《顺天府志》《江阴县续志》等多部志书编修,同时著有目前所见最早方志目录——《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等。新时期以来,宋云龙、杨洪升、王萍芳等学者,都对缪荃孙的方志成就及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例如,杨洪升从几个方面对缪荃孙的方志思想进行了梳理概述:首先,在传统的两个流派中,认为缪荃孙既不属于地理派,也不属于历史派,而是“学无今古,亦无中西”“兼取两家,各有所继”,即既“极重地理沿革”“也非常注意征今”。其次,认为缪荃孙十分重视遵循志书的存真求实原则,坚持倡导经世致用的功能,并善于在尊重传统规范体例基础上有所创新。第三,认为作为著名目录和金石学家,以主编的《顺天府志·艺文志》《顺天府志·金石志》等为标志,“他于这两门用力最勤,成就甚大”。作者还着重对缪荃孙的“志者也,志地、志人、志事、志物,上之自古迄今,下之由近及远,无饰辞,无私造,则谓之良志”等经典理念进行了重点分析介绍。[12]宋云龙等也以民国《江阴县续志》等为例,从五个方面概括总结了缪荃孙的方志成就与思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编辑原则,详今略古、务求实用的编辑方针,科学严谨、详略得当的编辑体例,提倡新学、开明豁达的编辑态度,招聘专家、分工协作的编辑方式。综观全文和缪荃孙的一生经历,其实这既是对其方志成就的集中概述,同时也反映了他处世治学的品格风范。[13]
积极致力于“辨抄袭、正谬误、审体例、寻因革”的王葆心。王葆心(1868——1944)系湖北罗田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京师图书馆总纂、武汉大学教授、湖北通志馆总纂等职。他精通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多种学问,尤在方志学方面“功力最深,造诣最大”。特别步入花甲之年后,他逐渐淡出其他领域,全身心投入家乡《罗田县志》等志书编纂和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还曾与甘鹏云合纂《湖北文征》等。两轮修志期以来,学术界对王葆心的关注度首先和大多聚集于方志学领域。如研究多以其《方志学发微》为例,十分推崇其“治学之要,始于条理,终于贯通;始于剖析门户,终于不分门户”的学术思想;注重其“辨抄袭、正谬误、审体例、寻因革”的方志编研理念。也有研究以其列指鄂东山川形胜和历代用兵要略,丝毫不差地研判了日军侵扰罗田的路线和时间为例,说明其十分重视编志与用志的紧密结合。恰如后人为其所作墓志铭载:“就其著述而论,实以考证为方法,以文史为旨归,而于方志学所论尤精博”。[14-16]
撰著中国方志史上第一部《方志学》的李泰棻。李泰棻(1896——1972)系河北阳原人,因年少学高,尤以所著《西洋大历史》而声名鹊起,22 岁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曾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长、北京市立师大校长等职。他也是一位横跨两个时代的史志大家,除撰有《中国史纲》《中国史学研究法》等史著外,还曾主纂《绥远省通志》《阳原县志》等志书。尤其是1935 年所著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志学》的重大影响,直接奠定了其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新时期的研究首先是在史学大框架内,关注到“李泰棻一方面充分肯定传统史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则根据新式的西方史学理论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如他曾将史料分为主料和副料,“主料”是指研治国史的主要资料,主要包括二十四史、各种杂史、笔记等;“副料”则是“因主料而生出种种目录、考证、辑补、评论等项”,其重要性虽总体上不如主料,但有时却“甚于主料”,等等。这一研究无疑对以“资料性文献”为本质特征的方志编纂和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研究还关注到李泰棻在此基础上所构建方志学的重要思想,并对其“志分多体之不必”“门目不得过多之不当”“生人不得立传之商榷”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方法进行了深入研析。[17-18]当然也有学者意识到,正因为李泰棻对史学、方志学两者的统摄程度及密切关系的认识定位,因而其反复强调的“方志者,一方之史”“一方之志,即为一方之史”等论见恰有矫枉过正之不足,即他“把方志与史等同起来”“完全是用写史的要求和方法来编写方志,就难免要出现概念混乱、界限不清的情况。”[19]这应是对李泰棻方志学尚不多见的批评意见。
客观地看,民国方志可谓学派纷立,名人辈出,因篇幅所限,本文仅能选取以上几位略作介绍。当然,有些其他方志名家贡献影响不可谓不大,但学术界关注度似还不够,相关研究成果也不多,亟待进一步加以研究。
四、余论
改革开放两轮修志期以来,学术界对民国方志事业发展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方面,黄苇较早便有民国系“乱世修志”之言,并在方志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反响与共识。付贵九较早也在相关研究中指出:“民国时期,因时局关系,修志工作时断时续,加上当时人力和物力匮乏,这项工作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20]因而学术界往往将民国方志当作“‘全盛’清代方志的一个尾巴和后缀”,等等。另一方面,除许卫平认为民国方志学“奠定了中国方志学地位”的评价之外,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化,新时期还多有学者呼吁,应给“民国方志一个合适的历史位置”[21]。如曾荣便认为:“民国虽然只有短短38年,但志书编纂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却是历代修志实践不能比拟的。”[22]邸富生也认为:民国“志书内容之丰富,体例之完备,绘图之精确,都较清代有很大进步”[23],等等。
应当说,上述两方面意见都应视为学术界对民国方志事业重要的研究视野。至于究竟如何对民国方志事业作较为准确的定位结论,相信通过上述梳理综述,读者和学界自有评价,这也是笔者基本以“述而不论”方式撰写此文的初衷所在。当然还应注意的是,一定意义上方志事业格局与其学科发展还不能等同相论,即修志覆盖面再广,志书数量再多,却未必有相应较高的学科建设水平,这与改革开放两轮修志期以来的学科建设相对滞后于志鉴编纂实践是同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