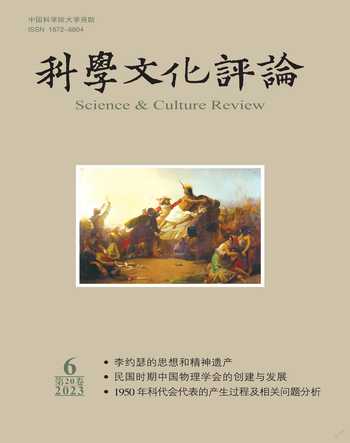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摘 要 1943—1946年李约瑟的中国之行意义重大,自此之后他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根本转移,实现了由生物化学家向中国科技史家的蜕变,奠定了李约瑟后半生著述事业的基础及其精神内涵。围绕李约瑟的战时在华活动,探讨其思想和精神遗产的内涵和意义。
关键词 李约瑟 中英科学合作馆 科学外交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3-12-05
作者简介:梅建军,英国剑橋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为《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刘晓、莫弗特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一书的序言,有删节。
李约瑟作为一名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为我们留下了皇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C,也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份极为丰富且厚重的学术遗产。作为20世纪的一名思想者,他留下的思想和精神遗产也同样丰富、独特而精彩。只不过,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通常都聚焦于其学术遗产和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上,而较少深入探究其思想和精神遗产的内涵和意义。在李约瑟一生的经历中,1943—1946年的中国之行可谓意义重大,因为自此之后他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根本转移,实现了由生物化学家向中国科技史家的蜕变。
李约瑟(Joseph Needham)于1900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英格兰著名的昂德尔(Oundle)公学上完中学后,他于1918年入剑桥大学学习生物学;1925年博士毕业后,在霍普金斯爵士(Frederick G. Hopkins, 1861—1947)的实验室中从事化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的专著《化学胚胎学》,成为该学科的创始人。1934年出版《胚胎学史》。1941年,李约瑟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可以说,在李约瑟启程赴中国之前,他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生物化学家。但鲁桂珍(1904—1991)的出现,悄然间改变了他生命的轨迹。
1937年,鲁桂珍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指导教师正是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Dorothy Needham, 1896—1987)博士,因此机缘,她与李约瑟相识而相知。通过与鲁桂珍和其他中国学生的接触和交谈,李约瑟对中国文化及其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鲁桂珍的鼓励下,开始学习中文,进而产生了去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强烈意愿。1942年,经不懈努力,他终获英国政府派遣前往中国,身份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1943年初,他抵达战时中国的首都重庆,数月后创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旨在推进中英科学合作与交流。
1942年,李约瑟在启程前往中国之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到了他中国之行的使命,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与政府部门建立密切的联系;其二是调查中国大学的学术需求;其三是探索中英之间教授交流的可能性;其四是做学术演讲,内容包括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尤其科学史与文化的关系、科学人文主义和东西方的关系。他还特别指出:“迄今尚无一部科学史叙述中国古代哲学家科学思想之起源,致使西方完全不知中国之伟大贡献。”由此可见,李约瑟中国之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官方之间的联系,此外更重要的是调研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探求学术交流的契机,推动中英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
人们一直很好奇李约瑟为什么要放下在英国剑桥相对安逸的科学研究工作,却要跑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四处奔走,忍受种种的艰难和不安定。而且,他抵达中国后,不是想着尽快完成所承担的工作,及早返回英国,而是积极运作,获得英国驻华使馆和英国政府相关部门的经费支持,创立“中英科学合作馆”。与他同期抵达中国的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希腊哲学家陶育礼教授(E.R.Dodds),在中国呆了一年,履行了计划中的讲学使命后,很快就返回英国了。李约瑟显然有自己长远的计划,因为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样一个常设机构,有了自己的运行经费和工作人员,他便能够制定详细的考察计划,在战时中国的后方东奔西走,不惧艰苦,乐此不疲。后来他还让自己的妻子李大斐博士也到了中国,担任副馆长一职,共同为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很显然,李约瑟不仅愿意前往中国,而且愿意长时间地在中国生活和体验,近距离地观察和记录战时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那么,是什么激励着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回到李约瑟的中学时代。对李约瑟一生有过长远影响的是昂德尔公学的校长桑德森先生(F. W. Sanderson)。他曾谆谆教导李约瑟及其同学们:“要以开阔的心胸思考问题”,“要找到值得一生去追求的东西。”这两句话对李约瑟的启迪和影响至为深远,以至他晚年回想起自己一生的经历时,还会想起这两句话来。可以说,李约瑟之所以要前往中国、之所以要转向研究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在他思想的深处,就是要践行桑德森校长的教诲。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就是他所怀抱的对东方和中国文化,尤其是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李约瑟在中国期间曾给鲁桂珍先生写信,谈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所带给他的感受:“从我初到这里以来,你们的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然而正因为此,我能够深入各处城乡的生活(当然东奔西走历尽辛苦);我踏着孤独的脚步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因而充分欣赏了古树丛中和荒园中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市集的生活,亲眼看到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黎明时所经受的苦难。我说‘历尽辛苦,不是夸张。有时我搭个行军床在荒庙里过夜,有时蜷缩在合作工场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虫蛇百足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鼠……那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永世感激你带我领略了这一切。”[1]
读《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个最深切的感受是,李约瑟对践行出使中国的使命是如此地尽责、尽力和尽心。自抵中国之后,他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后方各地奔走和考察,详细地记录他所走访的每一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现状,包括校舍、图书收藏、实验室设施、研究人员的数量、专长和工作内容。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人如他那样抱着深厚的同情心,不畏艰难地走访如此多的地方和机构,与如此多的人进行交谈,留下如此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包括所拍摄的大量珍贵的图片。要想认识和理解抗战时期中国后方各地知识界学人同仇敌忾、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没有比李约瑟留下的记录和评语更全面、更直接和更客观的了。李约瑟看到并感受到了中国知识精英在国难当头的境况下所焕发出来的坚韧精神,也从中领悟到,中国文明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蕴含着不可撼动的巨大的精神内涵和力量!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及时了解战时中国后方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状况,李约瑟每完成一项考察,必诉诸笔端,撰写相关的报道,及时发表在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上,1943年有5篇,1944年有2篇,1945和1946年各有1篇。抗战结束后,李约瑟和李大斐将这篇文章汇集在一起,加上他和李大斐博士一起撰写的一些工作报告、信件、日记、诗歌和演讲,合编为一本书,名为《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2]。在此之前的1945年,李约瑟还汇集了他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以及朋友赠送的有关陕北解放区科学研究状况的照片,在伦敦出版了《中国科学》(Chinese Science)的画册[3]。1947年,徐贤恭和刘建康挑选并翻译了李约瑟发表的6篇在华考察的文章和3篇演讲的文章,汇为一集,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战时中国之科学》的书名出版[4]。1952年,张仪尊将《科学前哨》编译为《战时中国的科学》(上、下册),由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出版[5]。1999年,在王钱国忠的积极推动和努力下,余廷明等人重新翻译了《科学前哨》和《中国科学》,以《李约瑟游记》之名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收入了《李约瑟研究著译书系》[6]。
2000年12月9日,为纪念李约瑟百岁诞辰,位于台湾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与李约瑟研究所合作,举办了题为“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展览,首次展出了与李约瑟生平相关的大量实物和图片资料,包括他1943—1946年在中国考察期间所使用的证件、名片、地图、笔记本,所收到的信件、聘书、奖章,以及砚台、书法和绘画礼品等。配合这一展览还出版了题为《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特展图册,其中收录了李约瑟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何丙郁教授撰写的短文,论及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所带来的变化,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评论:“一切一切的转变,实现了李博士大约五十年前的愿望,世人看中国的眼光,不再如此带着偏见,反能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大环境欣赏其文明。‘要研究人类精神及物质发展史,就不可能不研究中国科技史,这已是新一代东西方学者的共识,也是李博士终其一生最大之成就,对后世最深邃的影响。”([7],页16)
2015年9月,李约瑟研究所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合作,利用李约瑟1943—1946年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举办了题为《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图片展览,在剑桥大学开放日向社会公众开放。李约瑟研究所的莫弗特馆长和布里斯托大学的戈登·巴雷特博士 (Gordon Barrett) 精心策划和布置了这一图片展。自2016年以来,这一展览被安排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弘立书院、深圳大学等教育机构中展出,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这一展览的成功也直接促成了《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书的写作计划。
李约瑟本人十分看重他1943—1946年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这段独特的经历。1948年,在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的信件中,他这样写道:“从1942年到1946年的四年间,我在中国处于一个特别有利的位置,既不是纯粹的政府官员,也不是商业人士或传教士,而是一个科学和文化合作使团的负责人。我极其幸运,因为我的职责使我能够在战时中国后方的广大区域做深入的考察,而且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就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主题向中国学者讨教,并留下笔记。我也有幸积累了一批优秀的相关中文书籍,并安然无恙地运回剑桥,现在正为我所用。因此,我只能当仁不让,因为这是天时、地利与人和赋予我的责任。”In China during the four years from 1942 to 1946 I was in a particularly good position, neither purely governmental, commercial nor missionary, but the head of a mission of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I was exceedingly fortunate in that my duties took me through consulting with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present subject. I was also lucky enough to accumulated on excellent collection of the relevant Chinese books and to get them safely transported back to Cambridge, where I am now making use of them. I dare not, therefore, decline the responsibility which circumstances and inclinations have laid upon me([7],頁21).
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的序言中,李约瑟谈到了写作这部著作的作者必须具备的六项综合条件:其一是具备科学素养,并从事过多年的科学研究;其二是熟悉欧洲科学史,并从事过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三是了解欧洲历史上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其四是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各地做过广泛的旅行;其五是懂得中文,有能力查阅中文文献;其六是有幸得到过广泛领域的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指导[8]。可以看出,这六项综合条件中,至少有两项与他上世纪40年代在中国生活的这段经历直接相关,即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有机会与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以及与中国科学家和学者的交往如此重要呢?读完眼前这本《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书,我相信读者们自会找到答案。在我看来,李约瑟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段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经历,在于他从中找到了值得自己一生去追求的事业,那就是通过东西方文明的互鉴,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从而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条合作和共同繁荣的和平道路。
這样一本书在今天出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或者说为什么在今天还要出版这样一本书?是为了回顾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的发展吗?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李约瑟在战时中国的考察经历吗?抑或是为了让读者们更充分地分享李约瑟在战时中国所拍摄的大量图片?毕竟这些图片是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资料。在我看来,仅仅从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这本书的出版动机和价值,未免有些过于狭隘。如果我们能从李约瑟一生所从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事业,来反观他在抗战时期中国的考察经历,我们就能意识到,正是这一经历奠定了李约瑟后半生著述事业的基础及其精神内涵。因此,在今天出版这本书,其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完整而珍贵的历史资料,更在于进一步地认识、发掘和揭示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英国学者利昂·罗恰(Leon A. Rocha)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李约瑟的思想中“包含了政治远见、开放精神和道德要求,值得我们继承”[9]!因为这一思想表明,现代科学和医学远未完结,仍处在发展之中;它们对“真理”可能不具有垄断性;非西方的文化仍有可能修正我们获取真知的途径和方法;而研究非西方文化的科学和医学史也会有助于构建一个多元化的科学,不仅完全认同自然和现实的复杂性,而且包容来自不同阶级、性别、民族和文化的片面视角。罗恰的评论反映了新一代欧美学者仍在反思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并肯定其积极的长远的价值和意义。李约瑟毕其一生,始终在倡导“普世科学”的观念,相信人类的文明必经互鉴、互容与交融,最终走向“天下大同”。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和深刻的道德感召力量,是值得进一步地挖掘和阐发的。
参考文献
[1] 鲁桂珍. 李约瑟的前半生[A]. 李国豪等. 中国科技史探索[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37.
[2] Needham, J. & Needham, D. (eds). Science Outpost: Papers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British Council Scientific Office in China) 1942—1946[C]. London: The Pilot Press Ltd., 1948.
[3] Needham, J.. Chinese Science[M]. London: Pilot Press Ltd., 1945.
[4] 李约瑟. 战时中国之科学[C]. 徐贤恭, 刘健康译. 书林书局, 1947.
[5] 李约瑟, 李大斐. 战时中国的科学[C]. 张仪尊译. 台北: “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2.
[6] 李约瑟, 李大斐. 李约瑟游记[C]. 余廷明等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7] 何丙郁. 李约瑟研究所暨附设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简介[A]. 王玉丰. 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C]. 高雄: 科学工艺博物馆, 2000.
[8] Needham, J..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6.
[9] Rocha, L.. How Deep Is Love? The Engagement with India in Joseph Needhams Historiography of China[J].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6, 49(1): 13—41.
Ideological and Spiritual Legacy of Joseph Needham
MEI Jianjun
Abstract: Needhams journey to wartime China in 1943—1946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which fundamentally transferred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metamorphosed himself from a biochemist to a historian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stablishing the writing career and spiritual implication of latter half of Needham, the journey also shows the value of his ideology and spiritual heritage.
Keywords: Joseph Needham,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scientific 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