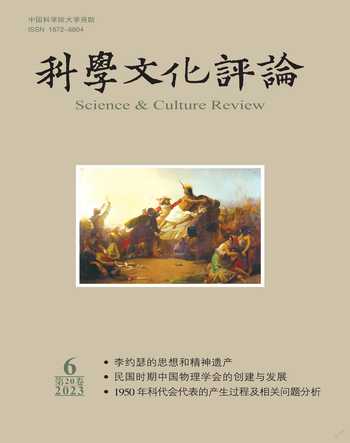李约瑟眼中的战时中国科技力量
摘 要 李约瑟战时来华期间全面考察了中国的科技力量,显示出他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现代科学事业。他不仅关注纯粹科学,更关注科学在经济和国防建设方面的应用,并提供了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通过与中国学者合作,他對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探访和理解不断深入。而他在中国开展国际科学合作的经验,直接促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奠定了战后科技外交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关键词 李约瑟 抗战 中英科学合作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3-08-01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刘晓,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教授。Email:liuxiao@ucas.ac.cn。
本文在2023年8月1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中国现代科技史”研讨会上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中英两大主要盟国的关系升温,进入了合作的新阶段。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化学家李约瑟不远万里来华,为当时艰苦卓绝的中国科学教育事业提供了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他战时来华“雪中送炭”的三年(1943年2月—1946年3月)不仅是他人生经历的转折,也为中英两国关系搭建了桥梁。李约瑟很早就认识到他战时来华期间所见所记内容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和照片,让英、美等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科学界的情况,促进科学的国际合作;同时他也希望让中国朋友知道,“我怎样叙述和赞美他们这种克服战争与流亡的种种困难的努力”[1]。
1944年冬,李约瑟返回英国述职期间,为英国读者编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中国之科学》(Chinese Science),他在前言中写道:
你将看到中国新旧科学的典型对照。你将看到中国科学家以何等的才智和精力解决迫在眉睫的困难,有效支援了盟军的作战。战争一旦结束,中国的科学一定能成长为一支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都举足轻重的力量(a force of major significance)。英国公众特别是英国科学家有必要知道,即便是现在,哪怕困难重重,在满目疮痍的中国,这支力量也焕发出磅礴的生机。[2]
李约瑟关注的战时中国科学的力量,既包括科研机构和大学,政府设立的研究部门,更包括直接服务于抗战的实用科研组织资源委员会和兵工署,以及防疫和医学机构。这些机构和组织大多经历了内迁,重新布局,并扎根大后方,除了坚持教学和科研之外,还以顽强的毅力服务于抗战和生产。随着李约瑟访问行程的明晰,他心目中的科学形象也显露出轮廓:它不仅包括教育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实验室,而且存在于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战时科学的动员与贡献、国际援助与合作的通道机制等,他甚至深入东南和西南前线了解战局发展,参观兵工厂与战地医院,现场目睹战争造成的破坏。
戈登·巴雷特(Gordon Barrett)曾参与李约瑟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他在《描绘中国科学:李约瑟科学外交中的战时照片》[3]一文中阐述了李约瑟战时外交活动中这批照片的价值。近年国外对李约瑟的战后国际科学合作贡献研究较多,《十字路口的李约瑟:战时中国的历史、政治和国际科学(1942—1946)》[4]揭示了他这段经历与他来华前后思想的连贯性。《获得一席之地:联合国体系中的科学》[5]讲述了李约瑟推动教科文组织设立科学部并主持的经历。王晓与莫弗特合著的《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6],从出版专业的角度讲述了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历程。以上这些研究提供了我们研究李约瑟和抗战科技史的新颖视角。
一 李约瑟对我国战时科技力量情报的调查
李约瑟战时受命来华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处于封锁和艰苦条件下的中国科学事业,并提供急需的物质和道义上的帮助;一方面是为了恢复纯粹科学的国际交流,一方面也在于提升与抗战有关的应用科学研究。尽管他心仪中国古代科技史,但并没有找地方潜心于自己的研究,因为他感到“道义和物质援助的需要太迫切了,不允许这样做”[7]。于是,他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先后作六次长途旅行,基本涵盖了当时中国的主要学术教育中心和重要科研机构。如果今天的科学史家想派遣一名情报人员回到战时,观察中国的科学状况,恐怕很难找到比李约瑟更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他会见科学家的名单,还是访问理科实验室、兵工厂、矿山等地,都区别于长期流行的专注人文领域学者和思想的民国学术史取向。
作为英国外交部和文化委员会选定的赴华代表,李约瑟负有文化(科技)宣传和调查情报的任务。1946年2月,李约瑟离华前夕,系统总结了几年来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的工作。首先便是建立官方的联系,中英科学合作馆发挥了两国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作用。英国方面,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中英科学合作馆与英国生产部、供应部等建立了联系,后者还专门设立中国办公室。中国方面,中英合作馆与教育部、经济部、兵工署、军医署,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关都建立了正式联系和私人友谊。而要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就必须深入实地探访。乘坐一辆卡车,李约瑟和同事们用三年的时间,奔波10个省份,完成了25000公里的公路行程,共计访问了296个机构(不计东部之旅)。
历次旅行的时机和意图显然都经过周密的设计。如东南之行就在湘桂战役进行期间,许多机构被迫再度内迁;而西南之行正值中国内地军队和远征军反攻滇缅之际。抗战结束时的北方之行,李约瑟不无接触延安方面之意,东方之行则看到复员初期的上海、北平和南京,反映了他对中国战后命运的思考。当然,这些旅行也就较少考虑季节的影响,如西南之行已近冬季,归途中多人感冒病倒,而北方之行适逢四川雨季,卡车被淹,困守绵阳数天。
李约瑟认识到科学在中国的抗战和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而且主张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并重,因此他能够突破机构和行业的界限,较为全面深入地考察涉及科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即包括李约瑟为见到的每个科学家“登记造册”,用卡片记录下中英文名字和关键信息。英国文化委员会科学部下设一般科学、工程、医药、农业,这些领域均在李约瑟收集情报的范围之内。
(1) 交通基础建设。交通是作战和经济活动的生命线,不仅反映出相关的工程、机械等技术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各类机构的战时布局。李约瑟亲自乘坐卡车出行,途经交通干道,并在有铁路的区域尽量选择乘坐铁路,无疑有考察交通基础建设的意图。如西北之行日记的封皮背面,即写有“甘肃路纪念”“公事路行”等字样,每篇旅行报告的开头便详细列出里程和路况。西北之行,李约瑟对川陕甘公路有了深刻的理解;东南之行,则乘坐黔桂铁路和湘桂铁路,还不惜冒险穿越衡阳铁路桥;西南之行,则沿着滇缅公路西行至保山;北方之行,紧密围绕陇海铁路,还对正在施工的宝天铁路充满兴趣。李约瑟记录下公路管理部门、铁路机车部门的工作和面临的困难,对相关的工程师院校格外留意。
(2) 基础科学。基础科学代表国家科学研究的实力,且与教育紧密相关,但在战时颠沛流离和与世隔绝的条件下,基础科学的生存状况最不容乐观。李约瑟来华初期,首先探访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科研机构,以及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重庆、成都的高校。每到一处,他都要参观图书馆和实验室,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李约瑟了解到许多科学家转向了应用研究,但仍有不少科学家依旧坚持,希望基础科学的传统不致中断。他提供的科学仪器和图书资料,也主要是面向这些机构。
(3) 重工业。重工业是现代国防力量的基础,李约瑟以盟国外交人员的身份,通过兵工署和资源委员会,探访了大量的兵工厂和厂矿企业。李约瑟对甘肃的油田、江西大庾的钨矿、广西八步的锡矿,以及各类化工厂、机器厂、电子厂等均有详细的记述,西南之行更是进入多家兵工厂。这些兵工厂和企业的负责人大多是具有留学背景的科学家,与李约瑟能够进行深入的交流。虽然出于保密原因,这些访问一般没有留下照片,但相关情报均以秘密报告的形式递交英方。
(4) 轻工业。轻工业关乎民生经济,也是持久抗战的保障。李约瑟考察的轻工业主要是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为代表的组织,在四川之行的成都、西北之行的双石铺和兰州、东南之行的赣县、北方之行的宝鸡,李约瑟都会见了组织的负责人,详细了解具体的合作社状况,甚至帮助培黎学校寻觅新址。工合组织受到政府的压制,以及抗战胜利后,严重通货膨胀和战时经济解体让许多合作社面临经营困难和布局调整,这些都引起了李约瑟的注意。
(5) 医药系统。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除了留意高校的医学院系,李约瑟通过与卫生署以及军政部军医署的联系,参观了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实验院、西北防疫处等。尤其西南之行,李约瑟不仅到访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中央军医学校、昆明血库,还深入前线察看远征军的野战医院。
(6) 农业科研机构。以中央农业试验所为代表,中国设有各级的农业试验站,如李约瑟东南之行参观福建省农学院和农事试验场、广西农事试验场;北方之行参观秦岭林业管理处、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西北农学院等。水利设施方面,李约瑟参观了都江堰,成都的中央水工实验室、武功水工试验所,以及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等。
二 李约瑟和科学合作馆的主要工作和贡献
李约瑟在合作馆的年度报告中,曾有过系统总结。首先最为直观的,是提供急需的科学物资。这些物资包括科技图书、期刊、缩微胶卷和科学仪器。许多散布到穷乡僻壤的大学和机构,几乎丢失了全部的藏书,李约瑟赠送的6775册图书无异于雪中送炭。1944年,一位记者曾这样描写工作中的李约瑟:“记者往访时,渠方忙于检查外文书籍,手执毛笔,以中文亲书收件人姓名地址,书法虽非银钩铁划,以一来华犹未经年之英人而克臻此,殊使中国访客为之讶异。盖书画事乃躬亲理之,其服务精神令人感佩。”[8]因运输困难,167种英国科技、医学杂志以缩微胶卷的形式输送到中国,这些胶卷被分发到100个配备阅读器的中心。而在空中运输航线建立后,合作馆可以定期收到188种杂志,这些杂志由专人分发给各个科研机构。
大后方的实验室普遍极为缺乏仪器和化学试剂,科学合作馆为他们提供紧急科学器材供应服务,收到并办理了333份订单,对于维持科研活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合作馆还放映一些英国的科学电影(如有关青霉素和麻醉剂),发表广播讲话等。
第二,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科研工作状况,以及推荐科研成果在西方发表,输出中国的科学文献。李约瑟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介绍每次旅行看到的不同地区的科学技术概况,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学通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集刊,都被送到英国和美国散发或转载。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直接推荐研究论文向国外著名刊物投稿。克服普通邮寄的困难,合作馆向西方输送了139篇手稿,接受率达到86%。当然,合作馆也为英国图书馆购买了所需的中文图书,李约瑟本人则搜寻到大量的古籍,包括一部《道藏》。
第三是向中国的科学技术机构提供咨询。李约瑟不仅是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通信研究员,还担任了教育部和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的顾问,军医署的咨询专员。萨恩德被任命为中央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卫生署的顾问,毕铿担任贵州陆军军医学校的客座教授。在重庆,李约瑟、李大斐、毕铿和萨恩德等人至少做过100次演讲,而在旅行途中,他们共计做过123次科学讲座。
最后,许多中国学者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提供的访问教授和访问研究员名额,得以前往英国进修和工作。这些对我国恢复对外科技交流,培养人才起了关键的作用。
三 对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追寻
在每次旅行中,李约瑟还注意搜购古籍,探访传统中国的科学印迹,常常触碰到中国文化的深层内容。如西北之行在敦煌对佛教的参悟,东南之行對朱熹的留意,北方之行更有对道教圣地的探访和对道教典籍的讨论。
李约瑟首先对中国历史和科学思想格外留意,《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两卷随处可见他此时发现的资料。如在历史概述中引用敦煌的壁画,1943年的西北之行因卡车故障在那里滞留长达一月。他把朱熹誉为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相当于西方的阿奎那和斯宾塞,因1944年东南之行在福建建阳访问时,看到麻沙镇一座牌楼上书“南闽阙里”,朱熹流放于此,印行自己的著作(这里也成为古代的出版中心)。1945年的中秋节,北方之行途经留坝县的著名道观留侯祠(张良庙),他与道长讨论道教:“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回忆那一次和马含真住持(鹤真监院)所作有价值的交谈。我至今仍保存着在笔记本上抄下的那一座庙宇中‘月白风清、高士炼丹的题词。”路过成都时,他与华西大学郭本道教授谈论道家哲学,曹天钦回忆中写道:“我更不会忘记在成都华西坝的钟楼上,李约瑟一连三天躲起来,同郭本道教授讨论道家的内丹。”[9]
战争阻碍了中国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反过来也激发了他们从中国古代文献中挖掘科学成就的热情。1943年李约瑟刚到昆明,访问北平研究院时得知钱临照在《墨经》中发现了不少和现代科学知识相通的记载,李约瑟在SCC致谢中第一个感谢的科学家便是他:“钱临照博士对《墨经》(公元前4世纪)中的物理学原理所作的阐释使我惊叹不已。”接下来的四川之行,李约瑟来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10]。1944年的西南之行访问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李约瑟在文庙大殿演讲“中西科学史之比较”,引发了热烈的思考,竺可桢、郑晓沧、胡明复、钱宝琮等均发表意见,正是这些思考和讨论,让李约瑟于次日下午列出了SCC大书的明确计划。
李约瑟1946年离开中国前到访北平,更是集中拜访多位科学家和科学史研究者,为中国科技史研究搜寻资料。闭门闲居的李乔苹已经完成了《中国化学史》一书的增订和英译,李约瑟见到该书如获至宝,提议将书名改为《中国古代之化学工艺》(The Chemical Arts of Old China),在英国出版,并提出代为介绍出版家,该书为他写作《化学卷》提供了许多素材和方便。李约瑟接触到中国学者所做的这些前期工作,无疑让他认识到,他要播种的地方不是荒原,而是沃土。“在整个这段工作期间,我有机会遇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有些人当然对他们自己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感兴趣,所以,我能得到无可比拟的指导。”[11]此后李约瑟每过几年就会到访一次中国,与中国科学史界的同仁进行学术交流,源源不断地获取考古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以丰富完善自己的著作。
正如后来的李约瑟研究所继任所长何丙郁先生讲:“我们不可误认李老为中国科技史的先驱者。本世纪(20世纪)20、30年代,一些中国老前辈在这方面已有相当的贡献。例如,数学史有李俨和钱宝琮……”但是,这一切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唤起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技史的注意。相反,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博得高度的评价。“中国科技史因而开始获得世界学术界的公认。这才是李老对学术和中国人民的大贡献。”[12]
四 国际科学合作事业的开创
从20世纪开始,科学越来越成为一项国际化的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类国际科学联合会纷纷成立,1931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它依靠科学界的自发力量进行组织,因此二战期间,由于各国科学家研究工作的转向,以及跨国交流的不便,许多国际科学联合会实际停止了活动。而在政府支持下,英美、英法等国建立了科学交流的机制,1941年英国科学促进会召开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会议,倡导组织反法西斯国家的科学联盟。同时,英国文化委员会组建科学委员会,进而设立科学部,负责向其他国家推荐科学书籍和期刊,派遣科学家海外讲学,介绍英国科学进展,成立办公室与苏联和中国进行科学交换。李约瑟的中英科学合作馆就是适应新的形势,不断摸索创新,成为战时国际科学合作的典范。李约瑟不无自豪地表示:“此次大战最主要的产物却是完全另外一种国际科学上有组织的联络,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合作馆。”[13]
早在赴华前夕,李约瑟访美时便有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国际科学合作的想法。来华伊始,李约瑟在昆明做的第一场学术报告便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国际科学合作》,并在许多机会反复重申。李约瑟设想,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面成立一个科学合作组织,“将作为一种工具,把一切必要的信息从西方输送到东方,建立和维持一切必要的科学和技术联系”。
李约瑟对国际科学联系的长期关注,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加深了他的观点。他开始越来越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的相互关联。随着思想和经历的增长,他将想法写成一系列的关于国际科学合作的备忘录。
第一个备忘录完成于1944年7月东南之行结束后,但注明起草于1944年春。4月10日他曾在遵义的浙江大学演讲《和平和战争中的国际科學合作》,经过一年多来的实践,李约瑟无疑更加确信“战后必须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国际科学合作”。“我们多数人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国际科学合作机构,各国的代表要具有外交官的地位(或是相当于从前国联官员的任何地位),并在通信及运输方面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便利,但他们必须从双方政府及大学实验室选拔,以避免商业方面的干扰。这种国际机构的中间目的,是把最先进的应用科学和理论科学从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介绍到工业化程度较低的东方国家。”
李约瑟接着介绍了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经验,明确提出,国际科学合作机构若要成功,主要应当在联合国同意于战后设立的世界机构之下获得保障。“毫无疑问,盟国中的‘四强将会发挥核心作用。”最后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应当由联合国设立,职能是促进全面科学合作和收集情报,在所有国家或地区设常驻代表团,应当有永久性的总部。
1944年12月,李约瑟返回英国述职期间,撰写了第二个备忘录《战后国际科学合作组织的一些措施》,继续呼吁建立国际科学合作机构(ISCS),它应当兼具和平和战时科学合作组织的优点:“科学世界在和平时期自发地形成的组织形式,以及战争压力下许多国家采取的组织方式,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从根本上尝试着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1945年初,李约瑟到达华盛顿,了解到美国国务院顾问葛孚发博士(Grayson N. Kefauver)曾写过一本备忘录,阐述拟议中的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的工作。该组织源于二战期间在伦敦召开的盟国教育部长会议,最初的计划是设立一个专为教育文化的机制(UNECO),但是许多国家的科学家都主张应将科学包含进来,否则战后的重建工作就无法进行。李约瑟得知后立即致信英国科学促进会“社会与国际联系”分会主席理查德·格雷戈里爵士(Sir Richard Gregory),建议利用UNECO实现国际科学合作机构的功能,认为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即可:名称中加入“科学”;将应用科学和纯科学一起写入组织章程。并修改具体条款加入科学的内容。格雷戈里爵士立即与参会的英国代表团联系,准备在4月的教育部长会议上通过,虽没有完全实现目标,但推动了一些具体条款的修改。
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3月,李约瑟起草了第三份备忘录《科学以及国际科学合作在战后世界组织中之地位》[14]。李约瑟针对葛孚发博士关于UNECO的24条目标,提出了融合ISCS功能的13条修改。该备忘录在纽约和伦敦被广为散发,得到了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科学委员会的全盘接受。罗忠恕、郭有守及成都教会五校的教授也向旧金山会议致函,支持成立科学国际合作组织。然而,美国方面还是希望成立一个纯粹的教育组织,而多数美国科学家则希望一个单独的国际科学组织。
1945年6月,李约瑟前往苏联参加苏联科學院成立220周年会议,他随身携带了多本备忘录,向各国代表团散发。1945年11月,UNECO筹备会议将在伦敦召开,为响应此次会议,朱利安·赫胥黎、柯如泽、贝尔纳和李约瑟一起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科学的国际合作,李约瑟的文章即重申了备忘录的内容。
而随着原子弹的爆炸,科学在人类事务中的重要性大大提升,各方对科学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会议期间,旅英科学家协会通过盟国教育部长会议最先提出了UNESCO的方案,最终美国代表团同意了这个修正案,并得到其他代表团的支持。11月6日会议最终决定,新的组织名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6年2月,“科学在UNESCO中的地位”会议召开,朱利安·赫胥黎担任主席。开幕式上,他提到自己受命担任UNESCO筹备委员会秘书。而在旅英科学家学会讨论中,赫胥黎提出UNESCO的五方面工作,其中第三条,就是贯彻李约瑟在备忘录中的提案:在地球这块面包上均匀地涂抹科学的黄油,并在全世界推广他在中国的工作。他给李约瑟写信,邀请他出任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助理,负责自然科学部(Division of Natural Science)的工作。
因此,李约瑟不得不结束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工作,返回伦敦,此后为联合国服务。李约瑟邀请了包括鲁桂珍在内的一批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共同组建该部门。不久教科文组织迁到巴黎,11月19日,第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在巴黎大学开幕,中国的李书华、竺可桢、赵元任、汪德昭、钱三强等21人参加。李约瑟开始推广他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模式,会上决议设立多处科学合作馆,并命秘书处“自距离科学工业中心辽远地域为始,于1947年先成立四处,即东亚(中国)、南亚(印度)、中东及拉丁美洲四区”([13],页23)。
然而,李约瑟的左派背景,以及与苏联和中国的特殊联系,引起了美国人的怀疑,杜鲁门政府以“共党渗透”为名,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8年4月,李约瑟决定辞职,带走一张同事签名的橡木办公桌回到剑桥。
五 结语
李约瑟从中国返回英国不久,便将战时发表于英国杂志的介绍各地科学状况的文章、中英科学合作馆的年度报告、部分日记、信件等结集为《科学前哨》(Science Outpost)。他解释说:“我们大家,英国科学家和中国科学家一起,在中国西部构成了一个前哨。”[15]李约瑟的中国经验,为他领导教科文的科学部提供了依据。
鲁桂珍说:“李约瑟的一生可以明显地分成两个半生,但是要确定转变的准确时间,并不容易。最现成的界线可以划在1948年,那是李约瑟在中国工作了三年多,又在巴黎任了两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任总干事助理之后,回到剑桥那一年。”[16]从此,李约瑟以非凡的使命感,开启了新的生命篇章。就在那张书桌上,李约瑟开始写作一部酝酿已久的巨著。1948年5月18日,李约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寄出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选题建议。
李约瑟是中国战时科学的调查者和援助者,是国际未来科学的构想者和擘画者,也是传统科学的发现者和解说者。虽身份迥异,宗旨却始终如一,那就是鲁桂珍所说的,“从1937年起,他要解决的明显课题,就是如何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科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以这种有趣的方式交汇于一身。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的李约瑟,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 战时中国之科学[C]. 徐贤恭, 刘健康译. 书林书局, 1947. 自序.
[2] Needham, J.. Chinese Science[M]. London: Pilot Press Ltd., 1945. 16.
[3] Barrett G.. Picturing Chinese science: wartime photographs in Joseph Needhams science diplomacy[J].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23, 56(2): 185—203.
[4] Mougey, T.. Needham at the crossroads: histor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cience in wartime China (1942—1946) [J].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7, 50(1): 83—109.
[5] Petitjean, P.. Finding a footing: The sciences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A]. Petitjean, P. et al(eds.). Sixty Years of Science at UNESCO 1945—2005[C]. Paris: UNESCO, 2006. 48—52.
[6] 王晓, 莫弗特. 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22.
[7] 李约瑟. 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一年的工作[A]. 李约瑟, 李大斐. 李约瑟游记[C]. 余廷明等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3.
[8] 服務中英科学合作的一位在华英国学人——尼德汉及其中英科学合作馆[N]. 大公报(重庆版), 1944-02-15.
[9] 曹天钦. 从抱朴子到马王堆[A]. 李国豪等. 中国科技史探索[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0] 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M]. 袁翰青等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9.
[11] 李约瑟. 《李约瑟文集》中文本序言[A]. 潘吉星. 李约瑟文集[C].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
[12] 何丙郁. 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6, (2): 93—98.
[13] 联教组织科学合作馆[A]. 科学联络[R]. 联教组织科学合作馆, 1948. 15.
[14] 李约瑟. 科学以及国际科学合作在战后世界组织中之地位[J]. 科学文化评论, 2018, 15(1): 21—54.
[15] Needham, J. & Needham, D.(eds). Science Outpost: Papers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British Council Scientific Office in China) 1942—1946[C]. London: The Pilot Press LTD., 1948. 13.
[16] 鲁桂珍. 李约瑟的前半生[A]. 李国豪等. 中国科技史探索[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Joseph Needhams Perspective on Chinas Wartim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LIU Xiao
Abstract: During his wartime visit to China, Joseph Needham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showcasing his broad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 scientific endeavor. He not only concentrated on pure science but also emphasized its application in national economic and defense construction. Both aspects of science received valuable material and moral support from him.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scholars and fieldwork, he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Additionally, his experience in Sino-British scientific cooper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UNESCO and laid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postwar scientific diplomacy.
Keywords: Joseph Needham, World Anti-Fascist War,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UNES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