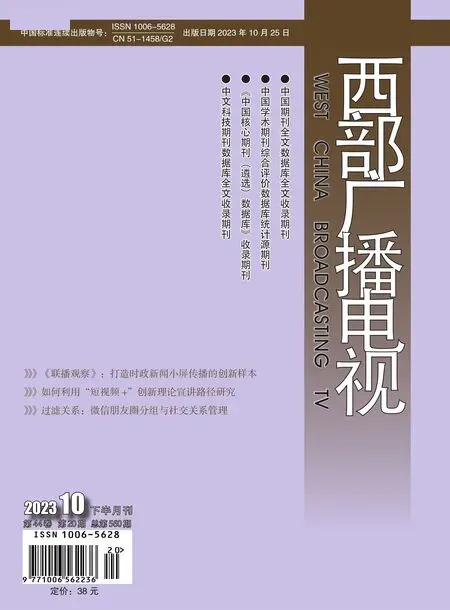国产单口喜剧幽默话语的性别身份建构
——以单口喜剧竞技节目《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为例
魏雨竹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学界对幽默的关注最早可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此后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幽默进行了研究,逐渐发展出了三大理论:优越论、释放论、乖讹论[1]。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语言学学者们结合语言学理论的新发展,在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多模态、社会语言学等学科领域从多个视角深入探究了幽默话语的语用策略、神经认知机制、社会影响等,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性别和幽默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单口喜剧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较高的欢迎度以及对现实社会问题的讨论吸引了传播学、影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语言学及其交叉学科的相关研究发现,单口喜剧不仅仅是一种喜剧节目,其对社会现实具有强大的建构作用[2],也是性别协商重构的重要场域[3]。因此,很多学者从性别视角对单口喜剧的幽默话语进行探究。如考特霍夫(Kotthoff)通过对一位德国单口喜剧演员的幽默话语研究发现幽默可以颠覆传统性别行为模式,揭示幽默有益于女权主义的可能性[4];伯纳乌(Bernabéu)对7位北美和英国的女性单口喜剧演员的幽默风格进行分析,探究了她们进行性别身份建构的方式[5]。国内学者从性别视角对单口喜剧的研究较少,主要是从影视学的视角出发关注单口喜剧对社会性别规约的影响。例如,薛静通过分析《脱口秀大会》的节目设置以及其代表演员的单口喜剧表演,探究了节目中的女性形象书写和对性别问题的探讨,认为其推进了中国性别平等的进程[6]。
总之,先前研究从不同视角出发探究了单口喜剧中的幽默话语和性别的关系以及其对性别秩序的影响。但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国外单口喜剧的幽默话语,缺少对国产单口喜剧的关注。此外,虽然有少数学者从影视学视角探究中国单口喜剧对社会性别规约的影响,但其研究多聚焦于节目设置而忽视了幽默话语这一主体。因此,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探究国产单口喜剧节目《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中单口喜剧演员通过幽默话语的使用构建了何种性别身份,并讨论其对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性别秩序的影响。
1 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
总体上,性别观经历了从“本质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发展历程。20世纪中期以前,受本质主义影响,性别普遍被认为是人与生俱来的属性,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差异也是由生物基础决定的[7]。早期性别研究的三条路径,即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都属于本质主义性别观下的性别研究范畴。这些研究认为语言差异是性别的直接标记。这使性别拘泥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从而不断强化社会现有性别秩序中男尊女卑的性别刻板印象[8]。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女权运动和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尝试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重新定义性别。他们认为,性别不完全是由生理决定的,而是一种动态的“身份”(identities),其不断变化、不断被重构[9]。在建构主义性别观下,性别差异不再是本质的属性差异,而是在社会文化中社会实践建构的结果。同时,语言使用不再被视为性别的直接标记,而是在某一语境下,实现特定交际目标的手段[10]。通过语言的使用,说话者自身及他人的性别身份得以建构,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协调重构。由此来看,社会建构主义的性别观摆脱了二元论的桎梏,认识到性别的多元性及动态性。本研究认同社会建构主义的性别观,认为性别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建构与协商的动态身份。
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等人的影响下,话语不再仅仅被视为对社会现实的被动反应,而是一种社会实践,主动地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同时也参与知识和权力关系的协调和再生产[11]。因此,话语在性别身份建构以及性别秩序的协调重构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形成了性别研究的第四条路径:话语路径。此路径下的性别研究中,话语被视为建构性别身份的主要途径和方式。Litosseliti总结了话语对性别身份进行建构的两条实现路径:“自己或他人的话语对性别身份的建构”和“产生特定话语的性别身份”[12]。换言之,性别身份在自己和他人的话语实践中得以建构。说话人一方面通过其话语意义对自身和他人的性别身份进行建构,另一方面,说话人基于某种性别身份而产生的话语方式也隐性地参与其性别身份的建构,同时也参与某种性别身份范畴的协商。这两条路径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因此,本研究对性别身份建构的分析从这两条路径展开。
2 研究设计
2.1 语料的收集和处理
本研究语料取自2021年8月10日至2021年10月13日在腾讯视频上播出的网络自制单口喜剧竞技节目——《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据统计,截至2021年11月23日,《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播放量已达26亿,平均每期播放量1.5亿,超越了先前在中国风靡的《吐槽大会》,并在2022年1月17日获得“影视榜样·2021年度总评榜”中“年度人气综艺”的奖项。由此可见,该节目是单口喜剧行业的代表作,有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确定语料来源之后,笔者通过讯飞转写软件把节目的视频资源转写成文本,并依据视频内容对其中的转写错误进行人工核对和修正。接着,笔者根据考特霍夫(Kotthoff)总结的幽默与性别有关的四个方面(地位、关系、攻击性和性)筛选语料中凸显建构性别身份的幽默话语,共筛选出21篇男性脱口喜剧演员的幽默话语和11篇女性单口喜剧演员的幽默话语。笔者采取随机抽样法从中随机选出男性单口喜剧演员和女性单口喜剧演员的幽默话语各7篇,组成一个小型语料库,共计18 089字。
2.2 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
研究总体上基于话语对性别身份建构的两条路径展开。幽默话语的幽默风格与幽默话语意义相互补充,对说话人及他人的性别身份进行建构。本研究采用质性量化相结合的方法,从国内单口喜剧演员的幽默话语的幽默风格和话语内容两方面探究中国单口喜剧演员使用幽默话语建构了何种性别身份,并讨论其对社会性别秩序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马丁(Martin)等人把幽默风格分为四类:亲和型幽默(affiliative humor)、自强型幽默(self-enhancing humor)、攻击型幽默(aggressive humor)和自贬型幽默(self-defeating humor)[13]。亲和型幽默是通过讲笑话、说有趣的事情等帮助人际互动,建立友好关系的一种幽默话语风格。自强型幽默则是在压力或逆境下发现有趣之处,是一种自我情绪管理方式,也是一种应对机制。攻击型幽默是指以他人为笑柄,对他人进行批判性嘲笑、讽刺、贬低的一类幽默话语。自贬型幽默则是通过自我贬损来娱乐他人的幽默话语。
在研究的第一阶段,本文探究国产单口喜剧演员如何有意识地使用幽默话语,通过特定的幽默风格建构自己的性别身份。笔者首先按照阿塔多(Attardo)的方法,把语料库内的幽默话语分成多个幽默片段[14];然后再采用Martin对幽默风格的划分,用Nvivo 12软件对语料中男性女性单口喜剧演员的幽默话语风格分别进行编码,得到每种幽默风格的使用频次和频率;最后,以此为基础探究单口喜剧演员通过其幽默话语风格隐性地建构何种性别身份并探讨其性别身份建构的影响。
在研究的第二阶段,本文将探究幽默话语如何用其话语构建性别秩序、性别关系,显性地构建性别身份。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霍姆斯(Holmes)和马拉(Marra)按照幽默话语对社会秩序和文化规约的“挑战”或“加强”作用,把幽默话语分为“颠覆型幽默”和“加强型幽默”[15]。第二阶段将以此分类为基本框架,分析单口喜剧演员的幽默话语建构了何种性别身份,并讨论其对性别秩序的影响。
根据高铁系统所需求的滤波器指标,先评估指标通带的实现方案,再根据指标通带远端抑制的要求考虑是否级联低通滤波器。
3 幽默话语的性别身份建构
3.1 幽默风格与性别身份建构
话语风格和性别关系密切,性别差异往往导致话语风格差异,这也使得说话人可以通过策略性地使用特定的话语风格构建目标性别身份。根据霍夫曼(Hofmann)等人对1977年至2018年间幽默的性别差异研究的总结,唯一和性别明显相关的幽默风格是攻击型幽默[16]。与女性相比,男性使用该类型的幽默话语频率更高。因此,攻击型幽默的使用和一系列男性气质密切相关。依据Martin对幽默风格的分类,笔者用Nvivo 12软件对收集的语料进行编码,并得到男性和女性单口喜剧演员每种幽默风格的使用频次和频率。
从数据统计结果来看,男性和女性单口喜剧演员都较高频率地使用亲和型幽默(男性34%,女性30%)、自强型幽默(男女性均为27%)及攻击型幽默(男性20%,女性25%)。男性和女性在亲和型幽默、自强型幽默和自贬型幽默话语风格的使用频率上差异不大,此结果基本符合Hofmann的研究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单口喜剧演员使用攻击型幽默话语的频率(25%)高于男性单口喜剧演员(20%),这与幽默风格的性别差异研究结论恰恰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文化中,温和顺从是典型的女性特质,而具有攻击性则通常是男性展现个人能力的途径和方法[4]。在国产单口喜剧幽默话语中,通过高频率使用攻击型幽默(25%),女性单口喜剧演员构建了反抗、具有攻击性的性别身份,颠覆了传统中国女性温柔、缄默的刻板印象。同时,女性单口喜剧演员使用攻击型幽默话语,从不同视角对事件或他人的行为和观点进行评价,从而建立了女性独立思考、有思想的新型性别身份。
攻击型幽默的使用还通常暗示着一种不平等关系的存在[17]。在攻击型幽默中,“笑柄”即讽刺对象的地位往往低于攻击型幽默的发出者。通过对女性单口喜剧演员使用的攻击型幽默的目标类型进行统计和分析,笔者发现其82%的攻击型幽默话语的主题与男性相关,且75%的嘲讽对象是男性群体或个人。由此可见,女性单口喜剧演员通过把男性作为笑柄,削弱男性在社会中的优势地位,构建女性强者的性别身份,从而试图颠覆社会中男性处于较高地位的社会现状。除此之外,攻击型幽默的高频使用也表明幽默话语的产出者对他人的情感遭遇的敏感度较低[16]。女性单口喜剧演员使用攻击型幽默的频率高达2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体贴他人、支持他人等传统的女性气质[4],从而构建了强硬的新型性别身份。
而男性单口喜剧演员的攻击型幽默话语使用频率较低,且低于女性单口喜剧演员的使用频率。由此可知,在国产单口喜剧中,男性单口喜剧演员较少通过嘲笑、讽刺他人或事件来娱乐观众,这使得其幽默话语中的攻击性减弱,从而构建了更为友好温和的性别身份。
笔者通过对国产单口喜剧幽默话语的幽默风格进行量化分析发现,虽然存在个体差异,整体而言,单口喜剧幽默话语颠覆着传统的性别秩序。女性单口喜剧演员通过其幽默话语构建了强硬、独立的新型性别身份,而男性单口喜剧演员则构建了更为温和友好的新型性别身份。
3.2 幽默话语与性别身份建构
模糊性是幽默话语的基本特征[18]。奥林(Oring)认为解读者无法确定幽默话语的唯一表征意义,而只能对其意义作出可能的一系列解释,这使得幽默话语可以讨论严肃话语禁止的话题[19]。另外,幽默话语放松和搞笑的特质也使“只是玩笑”成为其逃脱评论和批判的“借口”[20]。因此,幽默话语常被女性主义者使用以挑战性别秩序、打破性别刻板印象,从而协调重构新的性别秩序和性别规约。基于Holmes和Marra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对幽默话语的分类[15],以及幽默话语对现有性别秩序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笔者将国产单口喜剧的幽默话语分为颠覆型幽默和加强型幽默。
单口喜剧演员的颠覆型幽默主要有构建新型性别身份给予该性别身份非消极性评价,以及构建传统性别身份并给予该性别身份消极评价这两种策略。例(1)中,单口喜剧演员通过构建新型性别身份并给予该性别身份非消极评价,从而挑战了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秩序:
例(1):
在该片段中,该男性单口喜剧演员通过使用身份元话语“……我做了这么多年全职爸爸……”,建构了男性在婚姻关系中承担家务责任的性别身份,以及女性在外打拼事业的性别身份。同时,笔者通过分析该片段中单口喜剧演员对老婆的话语的转述,发现该话语仿拟了工作语境中上级对下级的话语方式和内容,由此也建构了在婚姻关系中,女性家庭地位较高的性别身份。在传统的性别秩序中,男性往往比女性享有更高的社会和家庭地位。因此,单口喜剧中这些性别身份的建构打破了人们对中国社会婚姻关系中男性及女性的刻板印象。
根据收集的语料,笔者还发现单口喜剧演员会通过建构传统性别身份并给予消极评价形成颠覆型幽默话语,从而挑战现有性别秩序和性别刻板印象。
例(2):
大家好,我是鸟鸟。我出生的时候我爸在产房外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肯定是个男孩儿。看到我是个女孩儿,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观众笑)。我当时就想我爸哭声这么大,肯定是个男孩儿(观众笑)。
在该片段中,单口喜剧演员通过讲述她父亲在其出生时,看到她是个女孩而大哭的趣事引发观众哄笑。这是由于“孩子出生”和“父亲大哭”这一对立脚本产生了一种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通过观众主动地寻求合理的解释而得以解决,即父亲期待的是男孩。观众在这一“乖讹—消解”过程中获得情感上的愉悦,从而使该片段产生了幽默效果。通过强调父亲对男孩的期待,该单口喜剧演员构建并强化了男性在社会文化中处于较高的地位、拥有较高的权力的性别身份。在讲述该片段时,单口喜剧演员使用其独有的冷静讽刺的语调,反讽了男性具有较高地位和权力的社会现实。通过讽刺表达了对这一性别身份的消极评价,该片段挑战了现有性别秩序。
单口喜剧中存在的第二类幽默话语为加强型幽默。该类型的幽默话语通过构建符合社会性别期待和性别规约的性别身份并给予该性别身份非消极评价,加强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秩序。
例(3):
你知道吗?跟她在一起压力很大。只要我每次瘫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她就一定会出现在我和电视之间,拖地(观众笑)。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想说我说你挡住我看电视了行不行?然后这个时候,电视里突然开始放了公益广告。那个公益广告的广告词和我女朋友的背影给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磁场压制着我(观众笑)。我当时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就是我女朋友的背影在这样,然后公益广告在放“你以为现世安好,其实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观众笑)。我还看什么电视,我干活去吧我(观众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干什么活,因为我觉得我家里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干净,最后没有办法我给自己洗了个澡(观众笑)。我一边洗我一边说原来这个家最脏的东西就是你(观众笑)。因为我是那种不爱收拾的人。就是我觉得家就是放松的地方,我越在家人面前我才应该越乱,就是乱世佳人嘛(观众笑)。
在该片段的前半部分,单口喜剧演员通过描述和吐槽其女朋友做家务的场景,构建了女性承担家庭事务的传统性别身份,加强了现有性别秩序中女性承担更多家庭事务这一性别规约。在该片段的第二部分,该男性单口喜剧演员讲述自己从想找家务做,到最后给自己洗了个澡,这一意想不到的故事发展使该话语具有幽默效果的同时也突出了男性不做家务的思想行为习惯,从而构建了较少承担家务责任这一传统性别身份。且在该幽默话语中,单口喜剧演员通过一系列解释加强了这一身份的合理性,从而加强了大众对这一性别的刻板印象。
4 结语
单口喜剧中的幽默话语不同于人际交往中的即时性会话幽默,是一种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达到某种效果的计划幽默[21]。因此,单口喜剧的幽默话语不仅具有基本的娱乐观众的功能,还具有参与协商或重构社会秩序的潜能。性别身份并非本质的固有的,而是说话人通过话语选择性呈现其性别中的某种特质而建构的[22],该理论同样适用于幽默话语实践。在《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中,女性单口喜剧演员高频率地使用攻击型幽默,总体上构建了具有反抗意识、有能力、有思想的新型女性性别身份。同时,其攻击型幽默常常把男性个人或群体作为笑柄,削弱其权力地位,从而挑战了现有性别秩序中男性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男性单口喜剧演员的部分幽默话语也在挑战性别秩序,如通过构建家庭地位较低、全职爸爸等新型性别身份,挑战了现有性别秩序中男性具有较高地位以及在外工作的性别规约。男性参与对性别规约的反思和对性别问题的探讨对社会性别平等观念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6]。这也体现了中国性别意识的进步,男性群体的加入使中国性别平等观念具有了更广大的群众基础。此外,通过对其幽默话语内容的质性分析,笔者认为国产单口喜剧的幽默话语可以按照其对现有性别秩序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分为颠覆型幽默和加强型幽默。总体来看,国产单口喜剧的幽默话语通过使用不同的话语策略构建不同的性别身份,既挑战了现有性别秩序,同时也对现有性别秩序起到了一定的加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