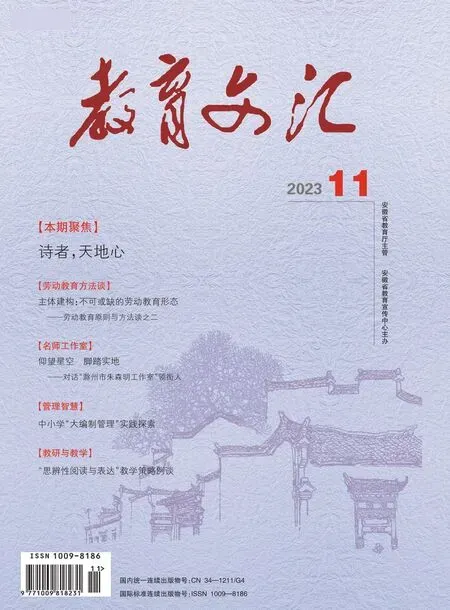主体建构:不可或缺的劳动教育形态
——劳动教育原则与方法谈之二
安徽艺术学院/柳友荣
今天,公众知识中有关劳动教育的阐释与传播还远没有达到科学、合理的水平,对劳动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理解还远没有达到足以顺利推进劳动教育教学的水平。正因为如此,劳动教育的实际效果不理想、育人功效没有落地的情况司空见惯。有些地方、有些学校还停留在“课本上读劳动教育,课堂上讲劳动教育”的“纸上谈兵”状态,劳动教育成效显得十分苍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明确指出的“一些青少年中出现了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现象依然客观存在,劳动教育现实情况不容乐观。
前不久,我遇见了这样一件有关劳动教育的尴尬之事:
一位对劳动教育有着很高热情的IT 企业负责人对我说,他招来了一批从事信息技术的研发和设计人员,希望得到我的劳动教育方面的理论支持,快速研制一种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线上解决方案,针对当下学校劳动教育的师资、教育教学能力、课程、评价等教育资源上的不足,提供线上教学、优质课件、精品课程、典型劳动教育案例、劳动教育项目、劳动教育效果评价等,借以帮助广大大中小学提升劳动教育的育人质量和工作效率。
这位负责人滔滔不绝地描述着这套“劳动教育解决方案”的完美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商机,我听了他的宏大愿景之后,忍不住告诉他: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其他四“育”不同,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教育形态,它无法全部采用虚拟世界的方式来实现,它必须“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受教育者应该,也特别有必要在真实生活的图景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劳动“经验”,虚拟平台是无法整体替代劳动教育鲜活生动的现实样态的。
一、“建构”是什么
“建构”(construction)这一概念源自20 世纪90 年代建构主义哲学,是建构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作为一种全新的学习理论,它强调面对复杂学习环境和真实的学习任务,学习者“身临其境”,积极参与,主动表征学习内容。一般情况下,学习者既要通过在真实世界的体验中“建构”一种知识,又要在“建构”的过程中“解构”(deconstruction)自己内心中已有的知识图式,具体地说:首先“建构”教学是教师通过综合分析知识体系,合理设定教学设计,采用“抛锚式教学”,又称情景教学,给学习者提供一个结构机巧、富有弹性、便于学生生成自主知识体系的真实生活场域,让学习者在沉浸式的学习中矫正自己原有的知识图式,“解构”不切合实际的“个体经验”,重新“建构”内心真实的知识图式和体系。
“抛锚式教学”本质上是教育者通过有效教学设计,把教学内容建立在富有感染力的真实生活事件上,而设计并确定这一真实事件,通常被形象地借喻为“抛锚”,一如船锚抛出后能固定船体的位置一样,“真实生活事件”也可以固化学习者的认知通道,简化认知路径,优化认知策略,提升认知成效。我们说,“建构”是最好的劳动教育学习的姿势,就是因为它能够引导教育者的“抛锚式教学”,引导学习者在“解构”不科学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在真实鲜活的世界里,“搭建”合理规范的认知体系和获得认知结果。
我们可以从“亲情劳动体验周”的劳动教育活动设计中,体悟“抛锚式教学”的真谛:
根据《意见》中“大中小学每学年设立劳动周,可在学年内或寒暑假自主安排”的要求,我们在安徽艺术学院的劳动教育课程设置中,设计了具有综合育人目的的“亲情劳动体验周”。具体要求是:每一位学生都需要利用寒暑假陪伴父母“工作”一周,全程体验父母的劳动过程,全面体悟父母的劳动付出,深度体认父母劳动价值,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对父母劳动的认同和理解,达成尊重父母劳动、珍惜父母劳动成果的目的。这一具有良好感染力的“真实生活事件”的“抛锚”,很好地锁定学生与父母的亲情互动,催生亲情共振,唤醒亲情共鸣。我们还是从下面这位学生对“亲情劳动体验周”的讲述中来感受主体“建构”的魅力。参与活动的一位女学生在“亲情劳动体验周”选择了陪自己在菜市场卖菜的母亲劳动一周。每天凌晨4点多,在浓郁的夜色中,她陪母亲蹬着三轮车去郊外菜农处选购新鲜蔬菜,然后赶回位于城区的菜市场摆摊设点,零售新鲜蔬菜。临近中午,母女二人才能收摊打烊,拖着倦乏的身躯从菜市场回家,回到家里母亲还得忙碌一家人的午餐。在菜市场这位学生不仅感受到了世态万象,通过一周的劳动,她还深刻地体验了母亲的辛苦操劳,理解了母亲的不易。在“劳动反思”中,她写道:“20 岁的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每天那么早起床,披星戴月,顶风冒雨,寒来暑往,日复一日地劳作。一分一毛积攒起来的收入原来从微信里给我打过来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不够多,每每总是感到不够花;现在每一次收到母亲转过来的钱款,内心都一阵阵收紧地难受……”这是有关劳动教育的“主体建构”过程,对于这位学生来说,这样的“亲情劳动体验周”甚至要超越许多堂劳动教育课上的获得。
我非常认同劳动教育的倡导者、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的观点,劳动教育本质上是人格教育,而不啻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真正的劳动教育是对人的内心的浸润,而不局限于对身体的训育。因此,在劳动教育中,学习者参加什么样的劳动并不重要,而在内心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去躬行劳作,才是劳动教育的本质所在。
二、为什么需要“建构”
“建构”作为一种学习者的学习状态,从其理论形成的那一刻起,就迅速风靡教育界,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诸如SC(student-center学生中心)理论、PBL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 问题教学法或者Project-Based Learning 项目教学法),它很好地激发了学习者的内心准备状态与学习潜能,激活了学习者的深度学习动机,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学习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为实现良好的学习效能做出了坚实的铺垫。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和知识时,为什么需要“建构”,为什么在“建构”的氤氲里,学习者精神状态焕发,更容易取得突破呢?
众所周知,与一般动物相比,人类幼子在降生那一刻是最没有生命力的。很多动物幼崽凭借天赋异禀,很快就能独立行走和自食其力。与此相比,人是一类要相对孱弱得多的存在。人类幼子十分脆弱地来到这个世界,需要较长时间的襁褓依偎、呵护哺育才取得了些许基本的生命能力。达尔文的“生长相关律”表明:“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息息相关。”[1]因此,人与生俱来是一种“未完成性”的存在。作为当代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兰德曼在其著作《哲学人类学》中称,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本来就是一种非确定性的、非完成性、非特定化的客观存在物。正因为这样,人与动物相比较,又相对具备了更大的可塑性。动物只是借力于本能遗传所获得的那些“完成了”的素质,便很快地适应了自然界,但穷其一生,也只能止步游离于这种生命格局的“限定性”。人类则不然,虽然在与生俱来的“完成性”上阙如,但因此也具备了极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在真实生活世界中,不断地、反复地获得应验的机会,从而使得人类有着远远超越普通动物的心智和能力。
这种“未完成性”应该就是人类能主动“建构”彰显自身适应力的基础。人在真实生活中不断的“建构”,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他思想中的“此在”(Da-sein)。“此在”是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是人在具体“时间—空间”上的“此”之在。[2]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在“家”中的我和“单位”中的我的差别;青春的“此在”和“知天命”的“此在”之不同。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人的生命在不同“时间—空间”上对世界的建构。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其实亦然,建构主义强调知识是“异质的”和“个体化的”,是个人建构的“自我理解”,所有的知识也都是“社会性建构”。[3]诚然,主动采用“主体建构”的方式对于劳动观念的形成、劳动习惯的养成、劳动价值观的确立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劳动教育中的“建构”为什么特别重要
劳动教育不能只在课堂上讲劳动、黑板上写劳动、口头上说劳动,劳动教育需要“实践”,需要在真实生活世界里的实践。《意见》中明确了劳动教育要“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以体力劳动为主,注意手脑并用”。正如马卡连柯所说,真正的劳动教育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是知识教养与熟练技术的结合。[4]陶行知先生也曾呼吁,传统教育造就了两种病:一种是“软手软脚病”,另一种是“笨头笨脑病”。因而,造成了“田呆子”(劳力者)和“书呆子”(劳心者)两个极端。他强调,要在“劳力上劳心”。[5]所谓“劳力上劳心”,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既要强调动手的劳动,也要强调动脑的劳动,倡导“积极主动”地“建构”。
学者柳夕浪认为,劳动教育既是五育中的目的又是基础,更是我们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我们五育如果是个金字塔的话,最高层是智育德育和美育,第二层是体育和健康教育,最坚实的这个基础层次就是劳动教育。劳动教育既是我们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的目的,同时又是支撑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重要手段。所以说劳动教育作为最坚实的底盘就显得最为重要。[6]既然劳动教育既是“五育”的目的,更是“五育”的手段,很显然,我们就不能在教育的方式方法上,按照普通“四育”那样刻板套用,而应比其他“四育”更加倾向于“主体建构”,更加乐见受教育者的“亲力亲为”“体悟体认”“躬行实践”。
在西方世界的公共知识里,其一直把豁免繁重劳作看成是超越普通人生活的“上层”生活,劳动与闲暇似乎一直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从词源看,“school”有“闲暇”的本意,在中世纪西方文化中,“学校”只是少数“悠闲阶层”的专利。闲暇可以达成人类的潜能开发和本真的自由。即便如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闲暇”并不是“无所事事”,不等于碌碌无为的“空闲”。“空闲”出现在劳作的间隙,用来排遣劳作带来的痛苦、恢复劳作过程中的体力消耗,“闲暇”则是在自由的精神世界里创造生命的意义。[7]这就像“闲暇”的燕妮要求马克思给她推荐书籍,“闲暇”的卢梭沉醉于编纂“植物志”一样。因此,如果我们试着从学校教育历史来看劳动教育,那么,劳动教育中的“主体建构”同样是突破学校教育时空的局限和规制,让学生贴近现实生活、尊重生活意义的重要路径。
四、劳动教育中的“建构”的实施
在劳动教育的现实中,我们似乎都已经非常重视“劳动实践”和“主体建构”了。《意见》要求:“实施劳动教育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学校要对学生每天课外校外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强化实践体验,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提升育人实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的劳动教育实践中,不少诸如“劳动月”“劳动周”“校外劳动实践”“居家劳动”等,却常常被“打卡”“摆拍”“一日游”的乱象所替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主体建构”的异化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还是集中在于教育者没能将劳动教育实践设计成基于习惯养成的锻炼、尊重学生经验世界的差异性、在师生共同体的基础上完成意义建构等。
(一)关注“劳动教育实践”
大家应该关注的是,我这里为什么不提“劳动实践”,而是“劳动教育实践”。就像我们去植树,植树本身是一个劳动实践,其本身是一个劳动体验的过程。如果我们运用得好,学生会爱上植树、愿意去植树,那就是“劳动教育实践”;如果运用不好,学生在植树过程当中会厌恶劳动,植完树以后根本没有对这个劳动过程的体悟,也不会珍惜这样一个劳动机会。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也不热爱劳动,那就不是劳动教育。换句话说,有劳动不一定有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本身是把劳动融于教育当中,通过科学的课程设计来使劳动本身充满教育元素。在植树过程中,要想把植树变得教育化,我们得有植树这门课程的科学合理设计。作为劳动课程的设计,我们要告诉学生一些劳动知识。比方说在南方植树和在北方植树不一样。在南方植树,要在树根处垒起一些土,以分散过多的雨水,否则树根会烂掉,树就活不长;在北方植树要挖一个坑蓄水,否则树会因为缺水而枯死。
劳动教育融入了知识,是不是就能培养出热爱劳动的学生呢?还不一定。知识仅仅解决了劳动认知的问题。有关劳动的“知情意行”4 个要素中,最后形成的才是劳动行为,而其间的情意元素就是爱上劳动的表征。怎么让学生热爱劳动、喜欢植树活动呢?我们可以让学生以班级、小组等名义给自己栽下的这棵树命名,把学生个人与这棵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乃至与学校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植树活动才会变得更有意义。再结合劳动方法设计,比如,在劳动竞赛中喊着号进行劳动,会使得劳动更加有意义。就是通过简单的一项课程设计,就把劳动实践转变为一种劳动教育实践了。
(二)基于习惯养成
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常常因为设计不符合学生的学段特点、内在需求,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主体性,从而难以达到“建构”的主动性,以及高质量的劳动教育情意元素的“建构”效果。
古语曰:“少若成天性,习惯成自然。”要养成青少年学生躬行实践、主动“建构”的习惯,就需要让学生认识到从来就没有什么事理是被我们在抽象的识记中热爱上的。就像海德格尔所言: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以某种操劳于周围世界上手事物的方式,并为了这种方式亮相的。海德格尔用与“锤子”这一用具打交道,来说明“上手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建构”)对于揭示“锤子”是否“称手”具有非常重要的操作价值。“对于锤子越少瞠目凝视,用它用得越起劲,对它的关系也就变得越源始,它就越发昭然若揭地作为它所是的东西来照面”,我们把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叫做“上手状态”。[8]可见,事理皆是如此,我们要了解事物的“真实面貌”,建构“照面”事物的“称手”状态,就必须要保持经常性的“上手状态”。而“上手状态”就是我们主动“建构”的过程。长此以往,我们便会因为在建构活动的“意义”世界里,建立了与事物的“称手”关系,进而乐此不疲地与此“打交道”,从而养成了躬行实践的良好习惯。
在劳动教育中,如何才能让这种与劳动教育实践“打交道”行为变成常态化呢?很明显,应将必须要做的劳动教育实践制度化,并与学习者集体一起共同订立相应制度,让每一个“主体”参与制度的订立过程是特别重要的。《礼记》有言:“鸡初鸣,咸盥漱,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说的也是用制度化的行为养成促成生活习惯。
(三)尊重学生经验世界的差异性
从劳动知识,到劳动情感和意志,再到劳动行为,“知情意行”这一认知链条是不能分隔的。我们期望在学生身上养成某种劳动“行为”,仅仅有劳动知识的传授,很显然是不够的。劳动行为的发生,一定基于“热爱劳动”这一“情意”被激发。建构主义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强调在个性化、独特的经验世界里,关注每个人的认知风格和活动兴趣,养成不同个体的劳动取向和情趣。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每一个具有不同劳动取向和职业方向的个体融汇一起形成的,如此才有了丰富多彩、相互弥补、充满张力的生活世界。
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在具体的劳动教育实践中,引导学生在自己的个性化活动和活动方式上生成新知识、新体验、新价值,而不是每每总是另起炉灶,罔顾学生的个性化现状。
(四)在师生共同体的基础上完成意义建构
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在劳动教育实践中主动“建构”,是在教师的引导、启发、支持、激励下达成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某种劳动实践直接作为任务,在没有任务教师的教学设计下,生硬地交代给学生。应该注意做到两个环节:
一是劳动教育实践的“共同愿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奋灶”为目的。譬如,预告学生在实践中可能会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可能会遇见什么样的困难,注意总结并在集体中交流等,借此激发学生“建构”的活动兴趣。
二是基于“异质、均衡、互助”的原则,组建合作小组,让学生在成长共同体中取长补短、互相激励、互为支撑,维持“建构”活动的动力。苏霍姆林斯基说过,集体是教育的工具。教师是共同体文化的建设者,在劳动教育实践中,有必要创设一些信息交流平台和载体,诸如劳动教育实践“珍宝箱”,及时沟通交流,增强集体的“增温仪”和“连心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