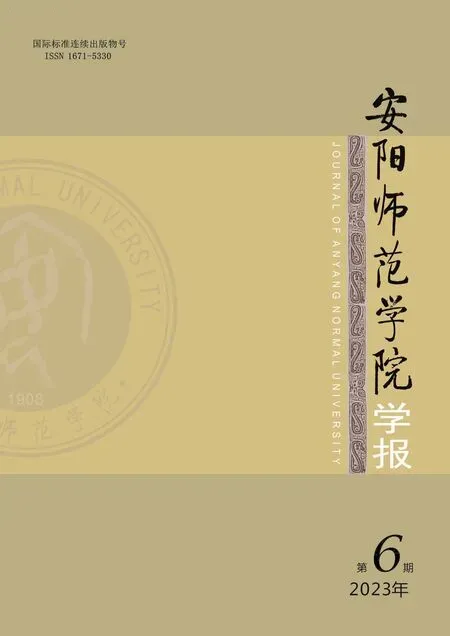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重释与回归
——评鲁枢元的生态随笔近作
彭 彤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作为一位忧思现代文明危机、心怀自然秩序与生灵万物的当代学者,鲁枢元长期坚守于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化研究的精神园地。20余年来,他先后出版了《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等多部著作,试图将人类精神活动作为一个活跃变量纳入地球生态系统、将生态作为一个诗学审美范畴引进文化艺术领域,从而建立自然—人的精神—艺术三者间的统一对应结构,重建人与自然复归原初生命关联的后现代生态观。鲁枢元的生态文化研究擅长汲取古今中外诸多观念学说的思想养分,具备“融合思维方式和文化宽容精神”[1]的开放气象。继《陶渊明的幽灵》之后,《天地之中说聊斋》是鲁枢元在生态视野下、借助生态批评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进行生态思想追溯与重新挖掘的最新力作。在这部漫谈式的随笔著作中,作者的学术目光与生活目光交错在一起,编织着他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精神谱系,追求人回归自然的生活愿景,以及崇尚道德理想的文化人格。
一、精神漫游:文化随笔写作
鲁枢元具备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这使得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构成了他写作生命的两条经络。在这两条经络中,作者始终关注着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社会、人类精神世界的损伤,并试图以亲近自然的东方古典精神文化,疗愈现代人的精神困境,重建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态观。早在《隐匿的城堡》(1995)《精神守望》(1998)《心中的旷野》(2007)等文化随笔中,鲁枢元着眼通过社会现象,去审视现代社会心态中携带的文明病症。他对奴役自然、女性、非人类物种的人性之恶,商品化社会中大众精神的媚俗化现象展开批判,传达他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的心灵异化状态的警惕与忧思。他的文化随笔根植于自身的社会经验、生命体验与阅读感悟,在“学术眼光和回忆目光的交错、学术理念与内心忆语的重叠”[2](耿占春语)之中,传达其复归自然的精神追求。
在鲁枢元的学术生命中,人的主体性创造与“生态学的人文转向”[3]是其关注的核心要素,二者构成了一个双向互动的有机整体。在生态文艺学的学科理论建树上,鲁枢元曾创造性地将自然生态研究与哲学思考、审美体验、伦理判断相结合,催生出一种具备有机整体性的自然观、世界观与宇宙观,表现出崇尚个体自由、众生和谐、恢复人与自然的血脉关联等宏观视野下的整体指向与关怀众生的人文温度。就思想脉络而言,《天地之中说聊斋》是作者一贯生态理念的延续,特殊的是,该书以文学研究为思维框架。鲁枢元从对蒲松龄其人其文的精神观念出发,体系性地传达着自身的生态理念。这一思路在《陶渊明的幽灵》(简化本,2021年)中已经体现。《陶渊明的幽灵》与《天地之中说聊斋》都是鲁枢元生态目光与学术洞见、学识积累的创造性结合。
《天地之中说聊斋》的体例分为“蒲文指要”与“名篇赏析”两部分,构成了作者关于《聊斋志异》的作家论与作品论。在篇目顺序上,作家论遵循时代背景、作家身份、生活环境、生命事件等思维线索,作品论则以个体心理、文化根源、形象分析、语言风格等部分为逻辑结构;在篇目命名上,作者围绕女性、乡土、自然、爱欲等主要维度,提炼出《聊斋》中潜在的生态思想——这些都是作者逻辑严谨的学理性思维的体现。与《陶渊明的幽灵》不同的是,《天地之中说聊斋》更多地注入了作者自身的经历、性情与感受。在具体行文中,作者以随笔形式展开自己的精神漫游。可以说,在学理性思维、灵性经验与随笔文体的张力形式中,实现了作者逻辑思维与率真性情的交融。
以作家论的《乡先生》为例:作者以时间顺序叙写蒲松龄的生平际遇,同时穿插着自身的个人感慨与对科举制度、私塾先生等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典故的介绍。作者以蒲松龄的身世际遇为叙述主轴,衍生出附近人物的家族世系,以网状结构呈现出蒲松龄生活环境乃至心境的全景细节。作者共情并悉心着墨于蒲松龄关注世情、人心、乡治、民生的生命热度,以及他独特的“乡土性”身份与性格,字里行间流溢着作者对朴实厚道人格的推崇与对蕴藉深远文风的青睐,这本身也是作者自身心性的映照。在《蒲庄与毕府》中,作者则从地理学角度描摹蒲松龄“生命活动的生态系统”[4](P23),即点明构成蒲松龄生活、创作环境的自然、乡村与毕家府邸三个不同的空间场域。通过描述蒲松龄在毕府的人际交游与所受的知遇、赏识等社会活动,作者还原了《聊斋志异》在其创作之初的素材来源、社会传播路径等真实场景。在该文中,鲁枢元以其独到的学术洞察力,揭示生活空间的流动性对蒲松龄创作心境的镜像式影响,以严密的逻辑线索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生活真实,践行着一种具有丰富细节的“微观历史学”,彰显出自身的学术眼光。
再来看属于作品论的《万物有灵》:作者先是立足于《聊斋志异》中角色塑造的幽微之处,揭示该书潜在的众生视角与非人类中心立场;而后,他结合当今社会的校园欺凌与虐猫事件,深掘人性中的残忍、暴虐因素,以此批驳“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并将其归因于人与自然界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此基础上,鲁枢元认同于“万物有灵”观点中蕴含的生命平等思想,并通过追溯人类远古神话、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图像乃至道家、佛教教义中所蕴含的人与兽的和谐共生关系,传达“众生互缘而生、万物相依相存”[4](P51)的宇宙生命共同体观念,以此点明《聊斋志异》根植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它与当代生态观念指向的契合之处。在中西互印的视野下,他倡导“世界整体性””生态伦理学”两种生态观,崇尚一种万物和谐并生的“生态世界大同主义”[5](P5)“环境世界公民理想”[5](P5)。就运思行文而言,鲁枢元的思维自由驰骋于古今中外之间,以寻求诸观念的相互佐证。他的生态观蕴含着一种原乡意识,弥漫着人文理想主义气息。可以说,在学术洞察与自由心性、发散性思维的交织中,作者的随笔写作保持着一种独特的张力与活力。
总的看来,鲁枢元的生态学视域关注作家的生命活动与作品人物关系中传达出的生态指向。作者以平视与共情的目光,看待蒲松龄的生平遭际及其所塑人物形象的性情与命运,在呈现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生存现场感的同时,传达出自身的系统生态论观点。在作者的行文中,逻辑的严谨演绎与性情的酣畅挥洒相互交织,呈现出自由、广博的精神气象。这种随笔写作以文学的率性姿态,回应着中国古代的自然写作资源与当代学术写作范式。通过“着眼于自我与世界、文化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生活之间多样的相似与互动”[5](P10),这种漫谈式的文学形式,能“把其他写作模式中彼此分离的不同生命体验、范围与视角整合在一起,重新联结自然科学中相互孤立、分离的东西,更准确地解释世界的复杂关联性”[5](P22),也能够“在体验的美化转变过程中,打破思想与沟通的僵化结构”[5](P7),以文学的经验书写与跨界姿态,成为一种“不断更新的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能量的来源”[5](P13)。这种保留个体经验的精神漫游,与作者“精神生态”学说传达的理念是一致的。
二、生态之维:《聊斋志异》思想的当代诠释
生态学视角是鲁枢元对中国古典文学典籍进行静观与再阐释的核心切口。在《陶渊明的幽灵》中,鲁枢元曾立足于陶渊明简单质朴的自然人格,倡导“物我合一”的人生体认、“忘怀”“孤往”的心灵境界与“真”的人格理想。通过挖掘“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和谐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精神”[6](P50),鲁枢元期望为‘人与自然’这一问题,找寻一份东方式解答;为陷入生态危机的当代人,提供一份关乎心灵慰藉与人生意义的参照。《天地之中说聊斋》延续了这一思路。在该书中,鲁枢元立足于现代文明的生态之思,希望通过挖掘《聊斋志异》一书中潜在的生态要素,来接续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与自然同源共生的精神谱系,同时呼应当今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环保意识。以此,矫正现代科学主义观念误导下人类对自然界的贬低与破坏,并重建当今时代的生态伦理。
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鲁枢元尝试着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里,汲取构建后现代生态型世界观、人生观的生机与活力。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朴素的现象学思想、先天的整体论与生成论思想、和谐的自然美学、自发的生态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人们再也无法拒绝的学术资源和精神能源。”[6](P131)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哲学”,鲁枢元搭建起一种有机整体的宇宙观。他将自然视为本体,视为人类的生存依据,建立起生态观的自然本位:“人类不过是地球共同体的衍生物,宇宙是一个由天、地、神、人共同组成的有机体。”[6](P4)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天人合一”的观念,并对该概念进行阐释:“天人合一”意味着“‘自然’与‘人道’的交融与和谐”[6](P22),意味着人“与天地自然的整体运作融为一体,在自然的流转循回中获得心灵的宁静与精神的永恒”[6](P70)。这一概念涉及个体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理念秩序乃至时代的精神气度与审美风范。
以天人合一观为出发点,鲁枢元抽炼出中国传统精神中“真”这一哲学概念,以阐释人内心的自然性。在鲁枢元看来,“自然”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一种本真、本源状态”[6](P13)。以此为基础,鲁枢元倡导回归自然,认为陶渊明重返田园“意味着回归自然,回归生命源头,回归到心灵的栖息地”[6](P82)。只有回归自然、回归本真,才能实现精神自由,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创造返璞归真的美学境界。鲁枢元对“中国式的宇宙论图像”[6](P104)的描摹、对陶渊明人格理想的推崇,蕴含着他对工具理性、技术统治时代的现代性反思。他试图以“中国古代视自然为大化流行、天人合一、生机充盈、自由和谐、完美至善的有机自然观”[6](P97),对抗西方现代社会中物我对立的自然观及建基其上的政治、经济与人格结构。他认为在“世界精神文化版图”[6](P136)中,作为“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精神的化身”[6](P92)的诗哲陶渊明,在通往生态时代与后现代自然哲学的旅途中,具有“为地球人类创建生态型生存模式”[6](P133)的典范意义。
遵循这条开掘中国古典文化资源,进而搭建后现代生态路标的道路,鲁枢元将目光投向了《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他试图“在大自然的视野内、运用生态文化的目光,对(《聊斋志异》)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做出再阐释”[4](P263)。在该书中,鲁枢元对《聊斋志异》进行生态观阐释的焦点在于“荒野情结”。在他看来,“荒野”不仅意指地理学意义上的原生自然生态,也意味着“人类思家的亲情,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人类与整个生态体系的联系”[7](P273),即“荒野”一词指涉着人与土地、生态系统之间归属关系的意义连接网。“荒野”概念连接着人类心理学意义上的“恋地情结”(即人类对物质生存环境的情感依恋),意味着人类的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因此,鲁枢元认为“荒野是人类之根、心灵之源,是深藏于人类精神深处的意象与情结”[4](P42)。在他看来,“荒野”是乌托邦化的人类生存家园,是人类本真心灵的怀想与寄托之地,是人类潜意识中积淀的原始意象,也是人类创造力生发的源泉。这里,“荒野”不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荒郊野外,还意指一种物我交融、恣意洒脱、无所拘束的心灵状态,意指个性与精神自由的领地。在这块心灵荒野中,自然界保留着宇宙秩序的神秘性,人拥有神话的原始思维方式与生命原初的野性状态。
鲁枢元的“乡土”概念与“荒野”具有相似的内涵。在《为乡土代言》一文中,鲁枢元曾表述道:“乡土聊斋意味着大地的精魅与秘奥。”[4](P124)“乡村,是旷野与城市之间的缓冲地带,它既是人类活动的场域,又是大自然的留守地,其中蕴含着质朴的人性与蓬勃的生机。”[4](P122)“蒲松龄对于青林黑塞、鬼狐花妖的一往情深,也可以视为站在乡土的立场上对自然的呼唤,对野性的呼唤。”[4](P124)鲁枢元对蒲松龄将荒野、乡土叙事编织成生命叙事的阐释,也构成了他自身的精神自传结构。他对“时代的复魅”的呼唤,呼应着他的“回归”诗学:主张消弭人与自然之间的裂痕,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生命与心灵的深层相通。当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呼唤“复魅”不是回到愚昧、迷信,而是回归对自然秩序的敬畏、对自然生灵的尊重,使“个人的情感世界走向容纳万物的慈爱境界”[7](P273)。
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鲁枢元曾以中西比较的视野,解读大诗人陶渊明的生平,并提炼出“低能耗、高品质生活方式”这一现代人的生态导向;在《天地之中说聊斋》之中,作者则以发散性思维向读者普及诸多的生态理念。重要的是,他将青林黑塞(也就是未受工业文明侵蚀的乡土世界)与生态生活的范式加以打通,在中国乡土文化传统绵延不绝的现实下,搭建起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生态路标。可以说,鲁枢元立足于当代生态危机的现实情境,延续着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精神谱系,又汲取了众多西方学者的思想观念。他以广博的见闻、深厚的学养重新激活了《聊斋志异》中的道德理想,阐释出了《聊斋志异》中隐含的生态伦理观,使其契合现代世界的普遍价值追寻。在《天地之中说聊斋》一书中,作者带着当代的生态意识观《聊斋志异》,以自由、随性的漫谈语调评《聊斋志异》,使得中国古典文学在”人类纪”到“生态纪”的过渡中获得新生,并重新赋格。这种随笔写作的“漫游”姿态,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态批评思维模式与文化批评的自省形式。风趣、率真、活泼的写作体式,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弥漫着人文精神气息的“心灵地图与文化风景”[7](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