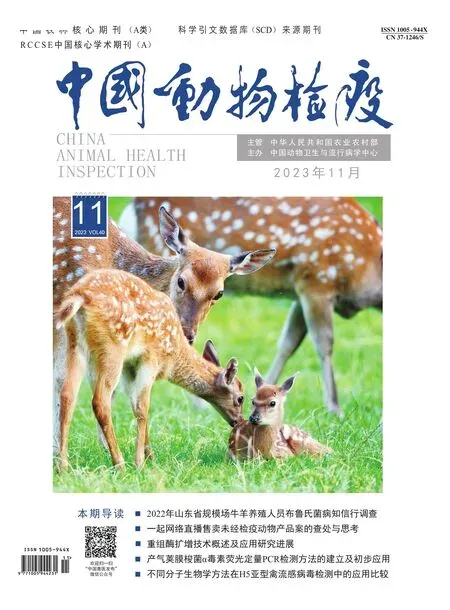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发展历程及思考
张 倩,常 凯,陈 颖,李沐洋,孙洪涛,王君玮,陶雨风,富宏坤
(1.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山东青岛 266100;2. 青岛国际旅行保健中心,山东青岛 266071;3.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北京 100062;4.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山东青岛 266032)
随着全球新发、再发病原微生物传播事件的发生,动物实验操作过程中存在的生物安全风险日益被人们重视。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以动物为载体的实验需要用到生物安全实验室。
我国生物安全验室建设和管理体系建立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比较晚。随着国家对生物安全的重视,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也越来越完善,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何通过加强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提升管理水平,减少生物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实验的准确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国内外学者一直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历程,来对比分析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的建立过程,以及现阶段管理体系运行和实验室实际发展需求产生的矛盾,以期为下一步制定科学的标准法规和适宜的技术规范提供参考,切实提高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和运行水平。
1 国外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发展历程
20 世纪50、60 年代,苏联和德国发生了多起实验室病原微生物感染人事件[1]。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引起了欧美国家监管部门的关注,并着手研究制定实验室生物安全措施。1974 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联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布了《基于危害的病原体分类》,第一次按照生物安全水平将实验室划分为4个级别[2],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肯定。
为指导各国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建设与管理,减少病原微生物感染性事件发生,世界卫生组织(WHO)于1983 年颁布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LaboratoryBiosafetyManual,以下简称《LBM》)。该版《LBM》根据设备和技术条件的不同将生物安全实验室划分为4 个级别,根据致病性和传染性危险程度将病原微生物划分为4 类风险,并规定不同类别病原微生物要在对应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中操作[3]。WHO 鼓励各国采纳生物安全的基本理念,并根据自己国内实验室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操作规范。《LBM》的出版,标志着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有了统一的标准和指导原则。与此同时,美国CDC 联合NIH 于1984 年出版了《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准则》(BiosafetyinMicrobiologicaland BiomedicalLaboratories,以下简称《BMBL》),也明确提出了将感染性病原微生物和实验室活动分为4 个级别的概念[4]。《LBM》和《BMBL》成为当时各国建立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两个重要参考标准,许多国家在其指导下制定了本国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和操作标准。
随着新型致病微生物的不断出现,生物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生物反恐形势的日益严峻,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也引起了众多国家的关注。为了适应新形势和新状况,WHO 分别在 1993、2004、2020 年对《LBM》进行了3 次修订,随后美国CDC 与NIH 也将《BMBL》进行了更新,2020 年已更新至第6 版。《LBM》和《BMBL》虽几经修订,但基本都是根据流行病的特点和当时需要,在上一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删减和扩充。而WHO 在2020 年发布的第4 版《LBM》[5]内容有了较大变化,它取消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水平分级,强调基于风险评估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策略,尤其是“安全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新理念更加灵活和贴近实际需求,是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2 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的建立
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建设起步较晚。20 世纪80 年代,我国与欧美等国家合作建立了第一批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90 年代开始自行设计与建设。但是,我国首个与生物安全实验室有关的标准是2002 年卫生部发布的《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233—2002),其对当时的实验室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SARS 疫情后,国家开始重视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2004 年,国家先后发布了《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4)、《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2004)和《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其中《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4)[6]首次提出了将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分为4 个级别的概念,并对每个级别实验室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建设与管理上开始与国际接轨。2006 年卫生部发布了《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理规定》,同时印发了《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名录》将病原微生物分为4 个风险等级,并规定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应与所需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级别一一对应,至此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比WHO《LBM》的发布已经晚了20 余年。
2006 年之后,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步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基于前期在实验室建设、运行管理、生物安全控制等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国家分别在2008 年、2011 年和2017 年对《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4)、《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2004)和《微生物和生物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WS233—2002)进行了修订。其中《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和《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2011)由于建立了系统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和实验室认可评价体系,并创新了各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分类方法,成为当时国际上领先的标准。
2016 年11 月,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颁布了《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我国将建立布局合理、网络运行良好的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国家体系。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生物安全步入了依法治理的新阶段。
随着这些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密集发布与实施,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以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管理体系,并初步实现了对生物安全实验室从立项、审核、环评到最后认可和资格批复等一整套流程的全覆盖。我国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合作建设第一批生物安全实验室,至今已完成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标准体系初步形成,实验室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各部门积极参与的跨越式发展,提升了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3 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体系运行现状
目前,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和标准体系逐步完善,尤其是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设计、建设、运行和管理能力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整体的管理与运行中不断出现新状况和新问题。
3.1 标准滞后,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
我国与实验室和生物安全有关的强制性标准《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和《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2011)距离发布日期已超过10 年。这段时间内,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标准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需求。另外,与国外先进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化管理体系相比,我国针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各项管理规定大多属于纲领性文件,具体的详细操作规范较少,没有形成针对某一行业的实验室管理规范和标准[7]。比如,近几年数量和规模都快速增长的疫苗生产车间,这种与生物安全相关的大规模试验和工业化生产活动,其暗藏的风险要比同级别普通生物安全实验室大很多,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具体操作标准。这些都是影响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的因素。
3.2 使用量极大的基础实验室存在诸多安全隐患
设在全国各地的一、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在运行和管理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国家对高级别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审批和年度审核都十分严格,具有一套完整的备案、认可和审批程序,但对分布在各地的使用广泛的基础生物安全实验室在管理上相对松懈。当前,卫生管理部门虽对生物安全基础实验室实施强制性备案制度,但未制定强制监管措施,导致管理和监督均存在缺失。尤其是医疗和疾病控制机构的生物安全基础实验室使用率非常高,检测的感染性样本来源于各类门诊患者,而制度缺失、管理松懈问题非常普遍。这些隐患还体现在实验室生物安全设施设备不足、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不健全或可执行性差、实验室专业人员比例不高、在岗培训流于形式、生物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等方面[8-9]。
3.3 实验室工作人员尤其是高校学生和科研机构中的流动人员安全意识淡薄
2010 年东北农业大学28 名师生感染布鲁氏菌,2019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65名高校学生感染布鲁氏菌。Choucrallah 等[10]和Wurtz 等[11]分别对加拿大和世界各地实验室获得性感染的原因进行调查,发现多数的获得性感染事故都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高校学生和科研机构短期进修人员普遍存在对新的实验室环境不熟悉、实验操作技能不熟练、生物安全自我防护意识薄弱等问题,且菌毒种的转移性导致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难度大,这些因素都增加了病原微生物的散播风险。
3.4 生物安全实验室维护费用大,闲置率高
生物安全3 级及以上实验室的建设和维护费用昂贵,作为国家生物安全的储备力量,其使用率并不高。COVID-19 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我国为了抗击疫情而建立的大量疫苗生产车间和病毒检测实验室,也必然会随着疫情防控的全面放开而闲置。如何提高这些生物安全实验室的使用率,使其成为抗击新疫情的储备力量,是监管和管理部门应该思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4 思考与建议
4.1 修订完善现有标准,制定新标准
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现有的国家标准体系尚有很多内容有待修订、补充和完善。比如,《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GB19489—2008)和《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GB50346—2011)是目前国内与生物安全实验室有关的主要国家标准,但距离发布时间已逾十年,其内容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需求,尤其是工业化的疫苗车间这种与生物安全密切相关的大型实验与生产活动。如何有效开展生物安全设施建设、使用与管理,亟需修订现有标准,同时针对某些行业制定操作可行的实验室管理标准或指南,以确保人员的职业健康及环境安全。
4.2 加强对基础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监督与管理
加强监督、强化管理是消除基础实验室生物安全隐患的唯一手段。通常,生物安全实验室从建设、验收、体系建立到实验活动实施,各环节的生物安全风险控制都由国家级机构负责。国家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控制审批或备案数量、监督检查、制定法律法规等强制性手段来强化对基础实验室的管理,不断将生物安全理念植入从业人员思想意识中,督促基础实验室的各种实验活动不断规范化和正规化,降低风险系数。当前,建议积极推动对动物病原微生物2 级实验室的强制性管理工作,做到不留死角,不断扩大监管范围[12]。
4.3 加强人员管理和培训
人员作为实验活动的实施主体,是开展生物安全风险控制的关键。尤其是高校实验室,人员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大,个人防护意识差,一个研究常常涉及多个实验室,导致人员感染风险增大。建议效仿美国和瑞典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将生物安全理念引进大学学堂,针对生命科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学生开设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课程,保证从业人员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意识和知识背景[13]。加强对实验室从业人员、学生和流动人员的管理与培训,做好人员资格资质审查、应急演练、监督、考核、授权、能力验证以及身心健康监测,这些都是降低实验室获得性感染和病原微生物泄露风险的有效措施。
4.4 探索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新模式
当前,多数国家现行的实验室生物安全建设和管理标准,仍然沿用病原微生物分类与生物安全实验室分级相对应的方法。但《LBM》第4 版取消了实验室生物安全水平分级,强调基于风险评估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策略,这对未来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发展方向给出了指引。所以,针对我国COVID-19 疫情后大量生物安全实验室空置的情况,探讨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势在必行。比如,针对空置率极高的2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要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基础上强化以循证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工作,使这类实验室能更加灵活经济地运作,为将来可能出现的疫病做好防控准备。
5 结语
在未来,国际合作和交流将不断加强,一些新技术和新设备将不断用于实验室生物安全领域。国家监管部门要做好生物安全实验室发展的顶层设计,为生物安全实验室创建一个健康的发展环境,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创新能力。具体可通过建立和完善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体系,扩大专业评审人员队伍,增加对基础实验室设备设施的投入,加强实验室强制性备案和明确认可范围等方式来强化管理。总之,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传染病的全球大流行,并且当今世界的变数和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生物安全实验室已经不仅仅是开展人兽传染病研究和防治的重要场所,也是国家应对重大传染病疫情及生物危害的重要基础设施,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