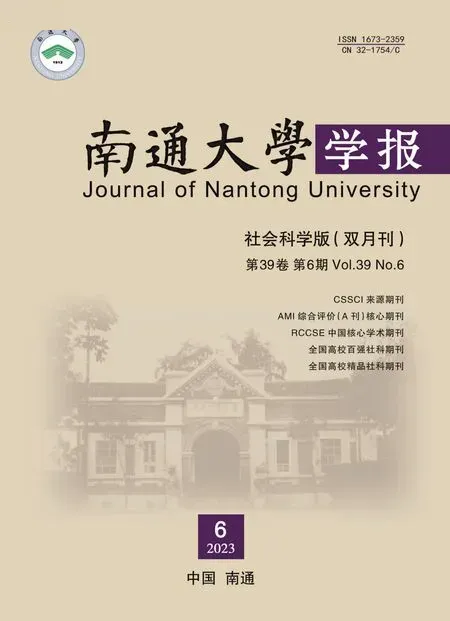新旧互望:论鸳蝴散文及其与海派散文的关系
陈 啸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海派文学是近现代都市的产物,其基本的特点是“取上海市民的眼光来打量上海这个当时的东方大都会,来写这个中国土地边缘上的‘孤岛’”[1]。这其中以20 世纪30 年代“京海论争”为起点的新文学海派是当然的主体(“京海论争”直接导致了京海派文学概念的形成),但也包括约定俗成的旧海派(主要指“鸳鸯蝴蝶派”,也称“礼拜六”派)。鲁迅、沈从文等的文章里就明确地说过,“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2]。本来,“海派”就是一个复合与流动性的概念,具有“较强较广的历史包容性”[3]27。
在全体“海派”文学创作中,散文小品数量庞杂。绝大多数海派作家都写有不少散文及旧体诗词,有的更是以散文小品的写作著称于世。在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近现代上海无疑具备某种超乎寻常的特殊观照价值。而对上海观照的诸文体形式中,由于其特别的文体特征和价值取向,散文显然具有着相当开阔的言说空间。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海派散文①虽然海派散文更多的是小品,但同样包容更多的随笔、游记、日记、书信、杂感文、政论、时评、序跋、回忆录、人物特写、笑话、谐文、寓言等,故此,本文所谓的海派散文取广义散文的概念。的源头——“鸳鸯蝴蝶派散文”(后文统称为“鸳蝴散文”)说起,钩沉爬梳,分析海派散文的发生形态、生长语境、文化症候等,并以此管窥全体海派散文文学文化史的特殊地位。
一
源于传统乡土中国文化的特点,包括散文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很久以来与中国城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内在相合的。历史上的中国也曾出现过很多诸如建康、扬州、江陵、长安、洛阳、开封等著名的城市,但封建时代中国城市质属于乡土文化的政治型城市,文人与城市的关系并非“工商性”的遇合关系,而多是其政治发展的寄托之所。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也多质属于乡土文化根性的政治型文学,由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散文也一直重视载道益世等的思想内容要求,并多限于应用性强的杂文学的特征。而且,比之小说、诗歌等文体,中国古典散文似乎更有着与传统乡土文明的亲密关系,这从其长期居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正统地位,似乎可见一斑。
宋代中期以来,资本主义与商品经济在中国东南沿海开始萌芽发展,中国的城市亦始产生了工商都会的精魂,中国的文学也渐次发生质变。就散文讲,清末民初以来形成于上海的报章体散文,最初体现了中国文学自乡村旷野、政治情怀及应用文体向都会景观及都会情感的趋近或转变。报章体散文,信笔写来不拘束,畅所欲言,通俗浅明,舒卷自如,解放了古文文体,打破了桐城派文统,开一代文风。在维新派人物梁启超手中,报章体极一时之盛,且影响深远。虽“报章体”散文较多带有“革命”与“改良”的色彩,但因报纸具有大众文化传媒之特点,其文体势必考虑大众读者的阅读与接受。报刊也正是后来海派散文借以产生的温床。
上海建城始于元朝的1292 年,明朝时期成为东南沿海棉纺手工业中心,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立上海海关。但上海真正迈入现代都会化的进程还是始于1843 年11 月17 日的开埠。开埠以后的1845 年12 月9 日出现了英租界,又相继出现了法租界、美租界。1863 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上海也成为全国最大租界面积的城市。租界初称“夷场”“洋场”,后逐渐成为华洋杂处的国际商业大都会。正是缘于沪地现代都会化的发展,单纯迎合“大众读者”的报纸杂志与鼓吹“政治”“革命”旨在“启蒙”的文化刊物日益分离,造就了一批通俗作家,也吸引了部分严肃写作者下海,如此,“海派”文人异军突起,海派散文的先声之作——鸳蝴散文也随之诞生。①鲁迅与沈从文等就曾将鸳鸯蝴蝶派视为海派,这是地域文化概念的“海派”影响下的文学现象。鸳蝴散文意指鸳鸯蝴蝶派文人的散文小品创作。同整个鸳鸯蝴蝶派文学一样,鸳蝴散文虽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但毕竟属于商业文化的产物,其显在的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体现了市民的生命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深入,工商资本的因素愈益增多,乡土中国的文化模式日趋离散。作为意识形态的散文逐渐远离精英性的“资鉴”及文人雅士人生态度的抒发等传统,开始转向现实、大众与通俗。
在其根本上,鸳鸯蝴蝶派代表着海派文学的早期形态。其共同的特性是因缘于海派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是近现代中国都市工商文化的产物。其文学的宗旨是为了满足都市市民“趣味”“消闲”等的需要,以慰劳累之余的休息。现代报刊媒体是包括鸳蝴文学在内的整个海派文学滋生的温床,也为其兴盛提供了可能。就鸳蝴文学而言,其缘起、兴盛、发展的过程似乎也一直维系于《礼拜六》《游戏杂志》《游戏新报》《星期》《快活》《消闲月刊》等创办与发展。鸳鸯蝴蝶派文学创作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以言情为主,旁及侦探、武侠、历史、宫闱、社会等众多领域,在诸如小说、诗歌(主要是旧体诗及通俗诗歌)以及翻译等方面都做了突出的历史贡献。然而,实际上,鸳蝴文人尽管主要以小说谋利以生,但却非常重视散文的书写。长短不一,率性而为,随笔、游记、通讯、感想等等项目繁多,相辅相成。鸳蝴文人的绝大多数在写小说之际,几乎都写有多少不一的散文。或者说,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之际,诗文小说文类等级的变更,以及散文功能观与小说功能观的差异、创作的背离(且又互补互动),小说创作成了鸳蝴文人谋生的职业,但作为有着浓厚传统意味的鸳蝴文人,又有着写作散文的习惯性。散文作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文体或固有文体,在鸳蝴文人的心里,地位一直很高。实际上,很多鸳蝴文人本身既是小说家,也是散文家,有的更是以散文创作闻名于世。鸳蝴派的刊物也是非常重视散文文体写作的,其所刊载的笔记、随笔、游记、通讯、感想录、轶事类等各类散文作品与小说几乎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平分秋色。对于散文小品的重视方面,有时甚至重于(短篇)小说,比如散文小品中的谐文,其稿费的标准常常高于短篇小说等,似可说明一斑。
鸳蝴派阵容强大,成分复杂,也因此意味着鸳蝴散文数量的庞杂,且异于相较统一于市场规约下的鸳蝴小说。鸳鸯蝴蝶派以“南社”文人分化而来的“星社”为中心。据范烟桥的说法,他们在一次聚会的晚上,值双星渡河之辰,故题名为“星社”。常有不定期的聚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切磋文艺。早期成员有范烟桥、郑逸梅、赵眠云、屠守拙、顾明道、孙纪于、姚赓夔(苏凤)、范菊高等人。后又有孙东吴、周瘦鹃、江红蕉、蒋吟秋、朱枫隐、顾诚安、徐卓呆、程小青、赵芝岩、陶冷月、黄醒华、黄转陶、黄南丁、尤半狂、尤次范、尤戟门、徐碧波、范佩萸、杨剑花、周克让、陈莲痕、吴闻天、程瞻庐、金芳雄、严独鹤等众多文人加入,另有未隶社籍但常为他们摄影的徐新夫,恰巧凑成了天罡之数——36 人。这些文人起先在苏州雅集、办刊、写作,后多活动于上海。时至1937 年,陆续加盟者达68 人,分别是:许月旦、包天笑、许息庵、孙筹成、张善子、陈迦庵、丁慕琴、赵苕狂、颜文梁、陆澹庵、马直山、施济群、钱诗岚、易君左、高天栖、芮鸿初、尤彭熙、谢闲鸥、黄白虹、陈听潮、张枕绿、钱释云、俞逸芬、吴吉人、沈秋雁、朱其石、周鸡晨、陆一飞、钟山隐、郭兰馨、范系千、徐沄秋、毛子佩、陈蝶衣、范叔寒、金寒英、姚民哀、方慎庵、吴莲洲、柳君然、蒋蒋山、凌敬言、应俭甫、张一敬、张碧梧、张舍我、朱大可、徐耻痕、薛逸如、唐大郎、郑过宜、金健吾、钱瘦铁、江小鹣、任乐天、刘春华、杨守仁、胡叔异、丁翔熊、丁翔华、黄觉寺、顾肖虎、陶寿伯、匡雄勋、杨清罄、朱庭筠、陈巨来、杨家乐。其中,杨家乐为唯一女性,且为殿军,是徐碧波的夫人。抗战爆发,“星社就成了星散”[4]。成分复杂,人数众多的鸳蝴文人几乎都写有种类繁多体式不一的散文,其散文的创作量有时是惊人的,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周瘦鹃、郑逸梅、范烟桥、程瞻庐、平襟亚、张慧剑、郑逸梅、胡寄尘、严独鹤、姚民哀等。
二
鸳蝴文人身上尚留有浓厚的旧文人气息,旧学根底良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较深,古代士大夫鄙视小说之影响依然是其潜在心结,故虽以小说为业(这是都市生存的需要,也是小说文类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之际兴起的结果),但骨子里仍然看重散文文体自古以来的正统地位,而鄙视小说的游戏功能,甚至以“小说家”为羞,有着对散文文体不自觉的留恋与自动性的书写。郑逸梅就如此说过,“鄙人从小就喜欢报纸上所刊的杂著小品,或是剪存下来,粘在一本簿册上,或竟为誊文公,把他抄录分编”[5]198。如果说,小说写作是一种职业,散文写作则为“遣兴抒怀”。实际上,鸳蝴文人的“习惯性”散文创作是非常认真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6]2,视其为一种生命的歌哭。在此意义上,鸳蝴散文似乎有着超功利的一面。
鸳蝴散文直接承袭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散文,“笔记”体的味道明显,且有拟古色彩。平襟亚、郑逸梅、范烟桥、周瘦鹃、张慧剑等皆擅长“笔记”体散文,为文夹以杂文气。典型的如平襟亚的代表集子《秋斋笔谈》即融合了“笔记”与“杂文”的写法,叙议夹杂,文白兼有,笔锋铦利,层出不穷,亦纪实也。郑逸梅著作的《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两本书以笔记文体琐记近现代文史掌故,文字短小精悍,叙述亲切生动,兼具史料性和趣味性。范烟桥的以历年笔记整理成的专集《茶烟歇》(民国廿三年十二月廿四初版中孚书局发行),凡十万言,总目录有193 篇,也是他四十初度的纪念。专集所收皆为笔记随笔,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有名人轶事,涉及忠臣、良将、孝子、烈妇、名士、美人、酒狂、侠客等,较有名的如翁同龢、石达开、柳亚子、苏曼殊、胡雪岩、汪笑侬、李涵秋等;谈风物吃食的如鸡头肉、鸭馄饨与喜蛋、状元糕、素火腿、豆饼、闵饼与闵糕等;游踪见闻的如“山东道上”“莫干山观日出”等齐鲁胜概、吴越山水;记录小说家言的则有《水浒之作者问题》《儒林外史之作者》《花月痕》等;其他诸如珍闻掌故、风俗闲话、述古论今、社会事实、读书心得、诗酒风流、论文谈墨、搜罗典籍、征文考献等等,皆有涉及。范烟桥本人淡泊自甘,善稗官言的一面,其文字也皆可见一斑。《茶烟歇》一编,巨细无择,风趣雅洁,不拘体裁章法,识其小而见其大。但求信而有征,或可补正史之讹、官书之阙。周瘦鹃的零话留声机片,谈欧美新发明之返老还童术,谈小说家之拿破仑,谈状元糕之艳史(与之相关的香艳故事),谈治病的方法,谈罹患残疾的世界名人,谈爱修饰的文学家,谈耶稣纪元以前三千八百年时之惧内者,说做媒,谈女子的装束,谈上海时兴的跑冰场(旱冰)与冰嬉,谈美人足,记接吻逸话等等的笔记体。古文写作是其当行,同亦开始写作白话文。诚然,中国传统资源,尤其是切近的近代文学的经世派、桐城派、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近代学术及文体革命等,特别是梁启超依凭《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等20 世纪初期的几个重要刊物所渐次掀起的,包括诗界、文界、小说界等的文体革命,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也促进着鸳蝴散文由古典而现代的变革。另外,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的报章文体更是直接影响了鸳蝴散文的体式。它们都生成于晚清以来报刊所建构的文学空间,分属于报章文体的不同阶段及不同形态。但皆“以妇孺皆知的语辞、简洁明快的逻辑,抒写胸臆,表达见解”[7],都有着报章文体的平易畅达、情感丰沛、条理明晰等的特点,只是少了些政治宣传的色彩与隽快雄放的气势。鸳蝴散文的不鹜辞藻、言之有物、敦本务实,与后期桐城派文章理论,如姚朴的文章学也有相合的地方,只是淡化了明道与经世的意旨。当然,这些散文也不再拘囿于一定的文章做法,而似一种自然与随意,也就有着灵动鲜活的一面。作为大众媒介的产物,以及西风东渐、白话文运动等的影响,后期鸳蝴文言散文已不再嗜用典故,转而追求清浅通畅,在文体、种类与艺术上已体现出都市审美的特性。
质言之,鸳蝴散文的突出特点是消闲、游戏与近情。取材宽泛随意,求新鹜奇,形式不拘。常常微言轻言,小题小作,不求宏旨,唯求轻趣。有租界阛阓景观的歆羡与礼赞,亦有世俗生活的钟情与品味,时滑稽,时幽默,嬉笑怒骂皆可成文。鸳蝴散文是日常性的散文,普通市民是其主要读者对象。家常、平易、亲切是鸳蝴文人的追求,更是鸳蝴散文的显性特点。如他们触及的某些题材“儿时顽皮史”“新年趣事”“新婚的回忆”“社会趣问题”等,写法不拘一格,摇曳多姿,品种繁多,各具风采;其艺术风格上的共同点是注重趣味,诸多世态、掌故、风物、趣闻以及人物、观感、游记等的抒写都显得生动活泼,以吸引读者为要。[6]1-7鸳蝴散文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人事、艺林、风情、世态、博闻、行旅、休闲、饮食、趣味、影评等,几乎无所不包,似生活的万象,也似一种“哈哈录”“调笑录”式的新笑林或戏谑之文。在他们的散文中,很少能够看到当时复杂的文学纷争,看到的是历史深井中的记忆的碎片。内中有着鲜活的身世经历、爱情遭际、亲情伦理、笔墨掌故、生活细碎,记录着20 世纪中国早期市民文人真实的生活境况、心路历程。他们是一批真实与纯粹的文人,没有面具,没有伪饰,磊落坦荡地呈现出种种真率与热情的一面。他们也向往“名声”,有了“名”大可获得“利”,但并不趋炎附势,而是努力展示自己的才华。其“名”其“利”,就隐含于他们的写作。鸳蝴散文常常散见于《礼拜六》《游戏杂志》《游戏新报》《快活》《消闲月刊》《红杂志》《红玫瑰》等报纸杂志,这些与“鸳鸯蝴蝶派”名字连在一起的报刊,本来就具有明显的消遣性质。生活化、消遣性与趣味性等是鸳蝴散文的标识,也是与后来新文学海派散文的共通点。不过,鸳蝴散文的市场意识并不强,其小说用白话,散文依然多用文言,远离平民。当然,部分鸳鸯蝴蝶派文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加之20 世纪20 年代中期以后,新文学作家南下带来的相互影响,其散文创作的现代市民性也在增进。他们在戏谑之中,也有对现实的关注或者微讽,不再是单纯的无厘头之趣。比如:对新价值观道德观的倾向与认可,对时局政治的讽刺与百姓疾苦的关心,对社会人物好坏两面的辩证评判,对法律不平等问题的臧否,对女性古今命运变迁的考辨,等等。仅以程瞻庐的《古今一恸歌》一文为例:“古闺女之极端派——女子要向深闺藏,朝朝夜夜莫出房。女子无才便是德,尽管一丁都不识。女子夜行必以烛,要是无烛便停足。女子与男莫授受,男子投河你袖手。女子裹就足纤纤,轻易莫到画堂前。女子笑时莫现齿,嘴唇上贴包皮纸……”“今闺女之极端派”——“今之闺女自由花,今之闺女走满街。今之闺女不向闺中坐,自命交际花一朵。今之闺女爱妆束,玻璃纱映浑身肉。今之闺女自由讲恋爱,美貌郎君由我拣……”[8]显然,这已不再仅仅是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而已经有着丰盈的现代意味的反思、批判与思考。但总体来说,鸳蝴散文的基本格局是保守的,“旧”中有“新”,“新”“旧”交融,但“旧”大于“新”,整体滞后于新文学的步伐,鸳蝴文人“士”的济世传统与“怀古”的千年母题,似乎一直或隐或显地呈现着。士子情结与士商两难也一直是很多鸳鸯蝴蝶派文人的真实写照。郑逸梅有一段话,就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士到士商的心理变迁,士之不易以及“文丐”似的生活。他说:“士农工商,士居其首,今则农也,工也,商也,均生活裕如,甚至投机取巧,夤缘而官,于是高车驷马,炫耀于市,惟士则啼饥号寒,艰困备至,大有头童齿豁,竟死何稗之慨,我固终身戴破头巾而忝为士,则绝不愿其后人再受如此之艰困,但我意不然,士之不为世重,乃干戈扰攘之际之特殊情形,终有承平之一日,及既承平,则知识分子,必能扬眉吐气,况人生于世,所以异于其他动物者,因有学问与意义也,若无学问意义,则与其他动物奚择哉!彼懵然无所知,惛然无所晓,衣文绣,食膏粱,且以骄人者,在我目光中观之,无非一狗之幸而饲于豪富之家,卧锦茵,饱肉脯而已,我愿我儿之苦之为人,我不愿我儿之乐之为狗,我儿若亦投机取巧,夤缘为官,我当为厉鬼,一击儿头。”[9]甚至到了40 年代,鸳蝴派整体上依然不属于现代性的范畴。在上海的文化圈子内,“除了鸳鸯蝴蝶派以外,其余不问左派,右派,现代派,象征派,留美派,留日派,新月派,古典派,都各显神通,舞笔弄墨,也常有聚会,毫无敌意存乎其间”[10]956,似乎也足以说明鸳鸯蝴蝶派文人与整个新文学阵营的疏离。实际上,鸳蝴文人创作的灵感与素材的来源及其文学接受的场域似乎也主要集中于当年上海的四马路以南,而不是以租界为中心的区域,这本身也就意味着新旧的区分。
不过,近代的上海虽然仍算不上是成型的现代都会,但毕竟有了刺激中国文人的现代精神与物质元素,故此,鸳蝴散文开始有了不同于乡土经验的现代都会“动”的意绪。散文的主要载体——报章,散文的接受对象——市民读者(主要是老派市民读者),散文的功能——消遣、趣味与娱乐等,已开始带有现代工商与消费性的特点。以报章为载体决定了散文的受众甚至写作者的下移,散文不再属于少数精英者的属物,散文的功能也不再集中于“载道”或寄情,而是向着通俗与趣味的一路发展。在最根本的意义上,鸳蝴散文最早也最真切地显示传统文学转型的轨迹。中国现代散文区别于传统散文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于它的轻松与随意,而非严肃与庄严。鸳蝴散文的通俗化似乎从根本上划开了与历来以严肃高雅面目出现的古典散文的界限。新文学作家在现代散文的创作中,更多倾向于西方散文的絮语体(胡梦华提出过“絮语散文”),与传统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散文有一种明显的割裂,它不是渐进的,而似突变。鸳蝴散文则不同,它直接由传统文学尤其是古典散文过渡而来。初期的鸳蝴散文即有着明显的古典意味,文言的色彩尚浓,有着模拟古代经典散文的痕迹。鸳蝴文人的古文功底往往比较深厚,而且他们也乐于保留这种古典文学的意味与传统文人的行状。不过,传统文人的读书入仕之途已经割断,他们是都市风雨中的流浪者,是中国较早一批城市中的精灵与城市中的平民知识分子。报人身份与“江湖”之远的处境使他们更多倾向于传统文人隐逸的情怀,在他们的散文写作中也随之不自觉地钟情于传统中国“小品”“笔记”的风格及韵味。似“笔记与杂文的混合体”,时夹以“春秋”笔法,这是区别于当时的新文学作家的。[6]4其散文语言也多为文言或松动的文言。显然,初期鸳蝴散文还基本属于传统文学的范畴,却也显现出转型的迹象。随着时代与文化的发展,比之新文学作家,鸳蝴文人虽步履舒缓,但同样与时跟进。其散文小品创作则随之显示出驳杂却也杂有现代性的一面。比如:常态性的文言写作到尝试性的白话写作,甚至有了欧化的色彩。在同一作家身上,常常兼擅多种笔调。这种离散的写作与视角本身即意味着鸳蝴文人前进的途程。其文言写作较之先前的文言写作,也显得更为平易晓畅、通俗易懂。在读者意识的规约下,他们非常注意散文的趣味、精短、活泼、趋时,力求大众与通俗。到了20 世纪30 年代后半期和40 年代,随着时代进展与现代性的增强,不少鸳鸯蝴蝶派文人及一些新起年轻作家如陈蝶衣、周楞伽、冯蘅、柳絮、唐大郎、龚之方、横云阁主、曾水手、慕尔、傅大可、青子等的不少散文,已然具有了现代海派的意味。
三
散文不同于小说,散文更是一种文化的文体,近距离地体现人的文化心理本质。小说在于讲故事,在于娱悦人心,鸳蝴文人更是把小说当成了“稻粱谋”的工具,充分发挥了小说之“小”说的一面。也许正因如此,鸳蝴小说作为“通俗”小说区别于包括海派小说在内的高雅小说,而“散文”之于新旧海派,似乎并没有明确的“雅”“俗”“杂”“纯”之分。或者可以这样说,鸳蝴小说遮蔽了对鸳蝴文人真实文化心理的直接显现,它是间接的,似乎仅显示了鸳蝴文人被动迁就消费市场与迎合市民读者的一面。鸳蝴小说很难真切地反映鸳蝴文人文化心理渐变的轨迹,它更多地迁就于市民。诚然,鸳蝴小说创作一开始就注重通俗与消闲,且纯然为白话。相反,鸳蝴散文的市场意识一开始并不是很强,更多地停留在心灵的宣泄,而且文白夹杂,或者干脆地说,鸳蝴文人的散文创作是不自觉的自我书写,远离平民,不以“市场”为鹄的,依然有着贵族化写作的特性。直到1930、1940 年代,鸳蝴散文方体现出市民消费与消闲的一面。这种自我书写的“自动化”无疑有着巨大的文化承载功能,真切反映出文化人的心灵本质与变迁的轨迹。而作为一种文体,最早也最真切地体现出传统文学转型的轨迹,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缓缓延续。传统中国文学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忽视鸳蝴文学尤其是其中的鸳蝴散文的深层考察,而止于新文学考辨,我们恐怕难以看清中国文学由“传统”而“现代”的演变逻辑与渐进型态。单纯地考察新文学,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割裂”与“沟堑”,而单纯地考察鸳蝴小说,我们虽能体会到消费文学的现代性与异质性,但或难以体现由传统“乡民”而现代“市民”的心灵史。单就近现代中国散文而言,缺少鸳蝴散文更是不完整的。鸳蝴散文是近现代中国都市文学的合理组成部分,甚至是别有意味的组成部分。研究鸳蝴散文对于了解近现代中国都市文学,以及了解整个都市文学与市民散文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将鸳蝴散文看作海派散文的“序幕”或先声,主要在于其由古典而现代、由乡土而都市转型的轨迹。在“源”与“流”的问题上,鸳蝴文人与新文学作家整体上分属于“新”“旧”两大文学阵营,如此,海派散文与鸳蝴散文并不是直接的源与流的关系。吴福辉先生在研究海派小说的时候,即是将鸳蝴派与新文学海派作了区分,并没有将鸳蝴派小说纳入其海派小说研究的范围之内。他强调,在中国只有海派文学,才开始了真正的都市审美,有了现代的都市意绪。海派文学脱胎于新文学,而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一直以来都是水火不容的。附属于海派文学的海派散文更多地借鉴西方都市文学,而鸳蝴散文则首先在于继承(它与传统中国古典散文的关系,前文已有论述),然后才有革新及都市化的影响。鸳蝴散文与新文学海派散文作为双线演进同域发展的特殊态势,也无疑有着复杂的关联,相互暗示与影响在所难免。首先,作为“他者”“借镜”的鸳蝴散文与海派散文一直存有着复杂的对话关系。鸳蝴散文的问世早于海派散文,又与海派散文双线演进、同域发展。①在更细微的层次上,鸳鸯蝴蝶派文学所体现的老上海的文化趣味区域,多集中于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相交的上海四马路。当年四马路的形形色色,正象征了旧文化分解前的最后一幕。而新文学海派的活动区域及其文学所呈现的文化地理区域主要集中于逐渐取代四马路地位的南京路、外滩一带,更多带有殖民洋化的色彩。但在更大范围上看,它们毕竟同属于海派文化地理区域,有着共同的海派文化背景,也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交融与交叠。在都市语境、媒介空间、文人交游、文学制度等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海派散文与鸳蝴散文在各自保持相对独立品格的同时,又难免存有着对抗衍生、借镜反思、迂回折射等对话关系。比如在认同都市、接受都市,并进而批评都市等的特点上,新文学海派与鸳鸯蝴蝶派是类同的。它们统一于“海派”文学的大旗之下,而且有着新旧海派的区分。然而,文学的“新”与“旧”哪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呢?!只是由于“‘五四’时代胡适之先生提倡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学遂有了新和旧的分别”[11]。不过,在海派文学的传统性、商业性上,新旧海派之间是有其共通点的。当然,新文学海派又确是五四新文学分化而来的作家队伍。上海的商业性,也常常造成海派报刊等的宽大或包容,像《杂志》《小说月报》(是20 世纪40 年代,顾冷观主编的,不同于同名的老牌《小说月报》)、《大众》《春秋》《万象》等杂志,更是鲜明呈现着新旧海派文人的靠拢,也由是影响着新旧海派文人的深度交融,这规约着小说,当然也影响着散文。其次,在共同的文学场域中,在大的市民化的空间里,新文学海派虽然敌视或批判鸳蝴派文人,但包括鸳蝴散文在内的鸳蝴文学及其生产机制,如创作机制、传播机制、接受机制等,也总在或显或隐地成为影响新文学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并进而影响了新散文的价值机制、美学机制及文体特性等。尤其是,新散文中的海派散文与鸳蝴散文甚至有着直接的遇合关系,它们同属于都市文化的精神造型,都有着消闲、娱乐、趣味化的倾向,以及取材广泛、疏离“宇宙之大”、关注日常生活、捕捉都市流行色等特点。实际上,新旧海派散文的游戏性(当然也不是一味地游戏,而是时有讽世。旧海派散文也曾一再强调戒除文字的“轻薄与下流”[12],同是上海文化消费市场规约的结果。1940 年代,新旧海派就有了合流的事实。这“合流”虽有“新”向“旧”的归位,但更多还是体现于“旧”不同程度的新变,如周瘦鹃、郑逸梅、平襟亚(别署秋翁、网蛛生等)、程瞻庐、秦瘦鸥,顾醉萸等此时的散文多取消闲价值取向,以消闲作为解脱压抑与自我救赎的方式,显淡然出尘之风。消闲的本质特点在于个人化,也遂之带来了文字的生活化。另外,闲雅有趣、感旧怀人、杂话生活、艺海探幽等等,虽然还是他们一贯书写的对象,但时代的因素、新文学的影响已经依稀显现在他们的散文小品的创作中。他们开始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与现代意义,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此前为文的游戏、消闲、趣味、幽默、滑稽等的风格,也非单纯的纪实、记录、轻小以及趣味与知识,而暗寓了诸多的讽世之语,“笑”中之“泪”,察世之思。正如《不惜珊瑚持与人》(发刊词)里,范烟桥如是说:“以美的文艺,发挥奋斗精神,激励爱国的情绪,以期达到文化救国的目的。或者说:既然把文化救国做幌子,应当都用硬性文艺了,为什么又是小说等等软性文艺占了大部分?这一点,我们也要附带声明,我们相信‘卑言易入’的老话,是有价值的;并且常受着刺激,未免要趋于愤懑而狂易,所以我们要把软硬两性的文艺,调节一下,总之,我们绝不使读者看了,至于颓废,这是可以请放心的。”[13]平襟亚在《秋斋笔谈》里也说“笔者终于希望太平盛世的来临,使文章不为商品,疗饥无待煮字”[14]2。标志着海派散文的别一向路。而“旧”向“新”的靠拢,“新”向“旧”的归位,在中国常常成为一种必然。作为一种直接体现作者个性与人格的艺术,新旧海派散文的合流似乎也正体现着中国文化“新”“旧”的“互望”或新变的艰难。复次,在修辞法则与语词系统上,近现代上海作家的文学语言异常复杂。上海是个移民城市,各地方言汇聚于此,杂以翻译语言,洋泾浜英语、文言、松动文言、五四白话等,而语言形式的问题,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更是一种思想、思维方式的现代革命。散文的本体即语言,对语言的要求,比之小说、戏剧等文体,相对较高,故而,鸳蝴散文与新文学海派散文的语言关系及特点必然也是互动相生丰富多彩的(这是另文专门叙述的问题了)。
必须特意指出的是,“新”“旧”海派散文虽同处于也产生于商业文化的语境里,但毕竟有着时空的区别与错位,在文学价值、文化心理、物质主题等整体的意义上,依然分属于新旧文化的不同范畴。不过,在一定的意义上,新旧时代交界处的鸳蝴散文是新文学海派散文的催生者与发脚处,也先期体现着新文学海派散文的基本特征,是海派散文的最早呈现。它们共同体现着上海都市的发生语境,以及老上海的精神记忆。
散文与都市的结合,是不同于小说等文体的。作为一种社会性、实用性的文体,散文有着其他文体无法比拟的书写广泛性,举凡社会、历史、习俗等均可纳入书写的范围,能够迅捷且直接地反映日趋丰富的日常事变。其包容的广泛性使其所反映的内容也就几乎无所不包。如此,新旧海派散文与海派文化相表里,它体现着近代上海的味道与质地,也是中国与世纪的混合体。新旧海派散文因“海”的影响,其意义已不在于散文的形式,而重在因殖民都会影响下的人生况味与特定的文化内涵。此种意味新旧海派小说当然也有,但散文似乎更是都市文化与作家心灵外化的表征形式。新旧海派散文的文化形态集中体现了作为“社会中心点”(与“政治中心点”的北京相对举)[15]50的上海所形成的非统一、非逻辑、有差异、未完成的海派文化的特点,是一种趋于民间、现实、生活的大众文化,一种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区域性都市文化,却也代表了近代整个的中国都市文化,或者直接地说,海派散文表征了特定时段的都市中国——一个有别于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物质文明的城市中国。而且,对偏于“言志”“写心”的海派散文的通观,无疑是对海派文人心态研究的深入,如此,似乎更能逼近海派文人内心深处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土、高雅与通俗等的挣扎,直接地揭示出社会心理的变化,从而,也更能直观近现代以来都市化进程中都市人精神的历史,直接体现着都市人心灵的变迁及现代都市文化的价值理念,表征了当时整个中国都市的真实。不同个性海派文人及其散文的“声色”汇总,在一定的意义上,正构成了近现代上海的文化性格,也因此营造了上海的文化世界,赋予了上海独特的品格。而近现代上海文化无疑是近百年中国文化的缩影,也由是决定了海派散文成为观照近百年中国社会与文化无可取代的形象图谱,是都市中国文化发展史无可替代的注脚,对于了解近现代都市化的中国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