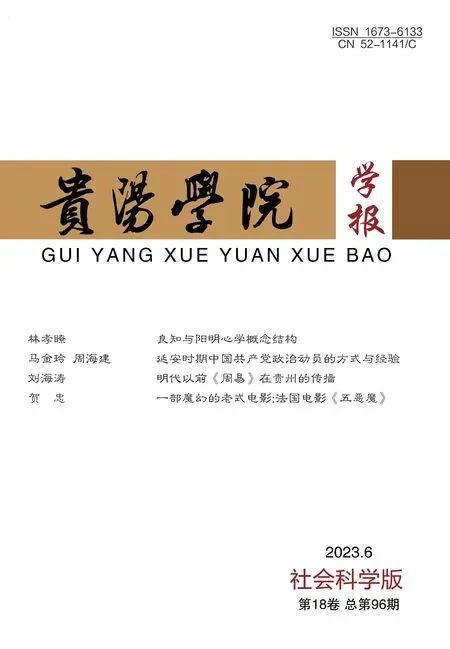阳明快乐情感的减法智慧
——从“说”“乐”“不愠”说起
马正应
(贵州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儒家十分重视快乐情感,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都以真乐、大乐暨大快活为理想境界。这种乐是从外部获得的还是内在本有的?是步步积累而来的还是无所待而然的?在其达成方法上,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和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有何不同?
一、从朱熹到王阳明
《论语》开篇即提出“说”“乐”“不愠”三种快乐情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朱熹看来,在性质和范围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对个体而言的,是一种自洽之乐,或者说在第一阶段,情感之悦在己不在物。朋来之乐与人不知之不愠则包含着己他关系,或者说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情感之乐与不愠在己更在物。这其中有一个由内而外的过程。在关系上,时习是后二者的基础,三者从前往后有一个次第的进程,又有一个易与难的区分。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朱熹严格按照《论语》中这句话的本来顺序阐释:“《学而》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后亲师友。‘有朋自远方来’,在‘时习’之后。”[1]446一者,情感之悦源于自修;二者,时习之悦是基础,而且先于朋来之乐,不愠的情感同样如此。或问:“说在己,乐有与众共之之意”,朱熹回答:“若果能悦,则乐与不愠,自可以次而进矣。”[1]452这里有一个从悦到乐与不愠的过程,其中也强调了悦是基础和前提。朱熹的阐释与程颐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颐认为“说先于乐者,乐由说而后得,然非乐则亦未足以语君子”[2],时习的愉悦之情获得于前,朋来之乐表现于后,君子应做到内与外的统一,它们是前与后、内与外的关系。
其二,在难易度上,“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3]47。乐容易得,因为有朋之来,是为顺己;不愠相较而言则难以达成,因为“人不知”是逆于己,与己相逆则容易心不甘、情不乐。“愠”虽然不是勃然大怒,只是小小的不快活,却也极难避免。只有成德之君子能够做到逆己而不愠,故第三阶段才是是否成德的判断标准。
其三,朱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3]47既学又习,有所收获,心中和顺、喜悦并意识到自己心中之悦与心中之所悦,这是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进行反思之乐,为自洽之乐。同样,在“要知只要所学者在我,故说”[1]452在这一由学到知(反思)再到悦的过程中,悦是学和知的结果。更进一步,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到熟后,自然说否?”曰:“见得渐渐分晓,行得渐渐熟,便说。”“习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愠’处,方是成德。”[1]454这里不仅强调了不愠同步于成德(与前述同义),而且认为情感之乐是逐步积累而来的,由时习的渐修过程一直修到德盛仁熟并成德,最终在情感上不愠而大快活。
可见,在方法上朱熹等理学家运用的是加法,其特征为从无至有、沿前往后、由易到难。这种方法又体现出有得与未得的结果及相应的乐与不乐的情感。朱熹说:“然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从,始为可乐。须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从者但一二,亦未能惬吾之意。至于信之从之者众,则岂不可乐!”“此段工夫专在时习上做。时习而至于说,则自不能已,后面工夫节节自有来。”[1]451所谓“得”显然也是在做加法:自己修习有得,故而可乐;以己之有得推及他人,使人有得,故而更乐;信从者越多,此乐越多。其中同样有一个从时习到朋来和人不知的渐进过程。“至于说”即为时习之得,这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作为“后面工夫”的朋来和人不知便自然展开,自然有得。概言之,乐因“得”而得。朱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同样表现出“得”的加法原则:“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3]98所谓“愤”是“心求通而未得”[3]95的情感表现,可见其中的忘忧之乐也是做加法后有得的情感表现,即有所得而有所乐。又如,朱熹引张敬夫语注“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3]89譬如五谷,“知”是知道它可以食用,“好”是在行动上食用并喜欢它,“乐”是喜欢它同时又吃饱了。所谓“未至”就是加法未能做到底。朱熹做的是未得则愤、已得则乐的加法,故而在朱熹眼中,“全体至极,纯亦不已”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只有圣人能做到。
与步步积累的加法相反,阳明认为“乐”是通过减去遮蔽而显露出来的,“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4]32所谓“只求日减,不求日增”之法即为减法,阳明称其为简易透彻、轻快脱洒的工夫。以精金为喻:圣人之心纯乎天理而不杂染人欲,如成色十足的万镒精金;人心的陷溺是由于不专务锻炼精金(即人心)成色,却投之以锡铅铜铁等乱七八糟的外物,使之“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此即加法,其结果是人心容易疑迷于外在之气与物欲,同时又泛滥多岐、支离破碎而离合不纯。人心本来无昧,但人欲的滋生遮蔽人心、天理,使之不得敞亮。做减法就是要减去人欲而使人心敞亮,如同镜子本自光亮却受尘垢之蔽,尘垢去除则镜子自然回归光亮。“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4]3,做加法是以外物来增益人欲,烦乱人心,如同将镜子放在污水中清洗,越洗越脏。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和乐之本体。恢复人心、恢复到真正的快乐所要做的不过是去除人欲,做人欲的减法,“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4]37
由此,阳明对于“说”“乐”“不愠”这三种快乐情感的阐释,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在方法上,均与程朱理学分道扬镳。需要强调的是,阳明快乐情感的减法智慧与其良知说是相呼应的。“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4]52一者,良知与物无对,为人之本有,良知之外无需再加分毫;二者,在与乐的关系上,良知本来自明,不乐是因渣滓的障蔽,以致人心与良知、与乐之本体相隔断。加以致知之功,则良知莹彻而恢复为自觉的状态,良知一觉则荡去人欲、渣滓,恒照所有情感,实现乐之本体的袒露。阳明之学的内核是致良知,不务外求而反求诸心,其快乐情感的减法原则、显现着良知的内向觉醒与外向去蔽相统一的智慧。
二、乐是心之本体
程朱理学之“乐”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仁的一种规定或其所应有的一种特性,相较而言,阳明之“乐”则是一种本原性的存在:
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来书谓“人之生理,本自和畅,本无不乐,但为客气物欲搅此和畅之气,始有间断不乐”是也。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悦则本体渐复矣。朋来则本体之欣合和畅,充周无间。本体之欣合和畅,本来如是,初未尝有所增也。就使无朋来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尝有所减也。来书云“无间断”意思亦是……良知即是乐之本体。[4]216-217
以“乐”为“心之本体”,即云人心在本质上是乐的,且此乐为真乐、大乐,为精神的超越和至高的境界。作为心之本体,“乐”在情态上是人心的本然和必然状态,为人所本有,是人生来就有的真正快乐,本来如是,与物无对;在关系上是与天人万物为一体、原无间隔的“欣合和畅”;在量上则“未尝有所增”“亦未尝有所减”,即从不因为外物顺于我心而有所增加,也从不因为外事逆于我心而有所减少。简言之,乐是心之本体,是亘古永恒的,安如磐石而无所动摇,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柏拉图所谓“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5]249的美本身相似,“一切美的事物都以它为泉源,有了它那一切美的事物才成其为美,但是那些美的事物时而生,时而灭,而它却毫不因之有所增,有所减”[5]249-250。不过,柏拉图的美本身存在于理式世界,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外在的。阳明之乐却存在于人心,是纯然内在的,所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4]1711。既然如此,作为心之本体之乐,是本来就有的而不是“得”来的。
因此,回归乐之本体是良知自觉基础上的减法智慧而非加法。具体在时习、朋来和人不知的问题上,阳明反对朱熹等先儒的意见。在阳明看来,习是习此心,理义悦我心是因为人心本来就以理义为悦。人心不悦不过是因为这种快乐被层层遮蔽,“得”之加法于事无补,反而增加无谓的累赘。时习之在于减去干扰和畅之气的“客气物欲”,使得心之本体自然恢复,继而本体之乐也得以自然恢复,其表现则是情感之悦,或者说悦是在做减法的过程中本体渐渐恢复的情感表现。在逻辑上,既然乐为心之本体,那么只需要做减法,减去所有的外在因素,即可袒露、恢复本体之乐。反之,朱熹之“学”要求“效先觉之所为”[3]47,譬如“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1]448,在阳明看来是一种舍心逐物而驰求于外的加法。退一步说,效先觉之所为是“学”的应有之义,并无不妥,但仅仅效其人是不够的,不能专求诸外而应反求诸心,在自身良知的自觉、乐的袒露上下功夫。不像减法那样只需去减,加法需要无量数的工夫,阳明以之为支离破碎的工夫①(1)①阳明有诗《月夜》其二批评朱熹与郑玄:“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参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66页。,是错看了格物之学。故而朱熹由“所学者熟”产生的快乐(时习阶段所得之悦是学和知的结果,如前所言)在阳明看来不过是做加法得来的,是与人心为二的外来之物,所谓“今且理会个‘学’,是学个甚底,然后理会‘习’字、‘时’字”[1]446的层层加法对于个人而言是不堪重负的。朋来与人不知的次第关系同样是在一步步地做加法,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快乐。更不乐观的是,按朱熹的逻辑,只有成德之人才是真正快乐的,但加法只有做到相当高的程度才能成德,普通人难以做到。如此,这种快乐是非本体的、由外而内的,甚至是与心为二的,不具备普适性。
同样,在阳明看来,在后两个阶段,既然人心本乐、本自“欣合和畅”,那么在朋来的情况下本体之乐不会增加,无朋来时也不会减少,故而不必去增;在人知我的情况下不会增加,在莫我知之时也不会减少,同样不必去增。“后世人心陷溺,祸乱相寻,皆由此学不明之故。只将此学字头脑处指掇得透彻,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畅茂条达,自有所不容已,则所谓悦乐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4]227-228相较而言,“得”的加法既不简易也不透彻,千头万绪、繁琐不堪,即便有所“得”却也支离破碎,容易导致“人心陷溺,祸乱相寻”。从正面意义来看,如果明白此学为良知之学,以致良知为“生身立命之原”,不去做外求的加法,那么时习、朋来和人不知所对应的悦、乐和不愠等快乐情感就会自然而然地袒露、呈现。
“‘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4]109阳明虽然并未指名道姓,但很明显这是对朱熹关于有得未得之说的直接批评。无论是未得还是已得都是做加法的结果,换言之,有得之后才会产生快乐情感。阳明以之为非,认为朱熹由渐修而得乐和成德的方法太过繁琐且难以达成(实际上朱熹自己也意识到“得”的难处,由此法达成真乐境界缺乏普适性,只有圣人才能做到)。既然乐为心之本体,那么人心“真无有戚时”,自然不必做“得”的加法。
孔子早就批评过“得”的加法:“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论语·阳货》)具体在忧乐的情感上,据《孔子家语·在厄》,子路向老师请教“君子亦有忧乎”的问题,子曰:“无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只要有意于“修行”之道,即使未能成就却有在途中的探求之乐,有所成就当然也很快乐,不管是哪一种都无一日之忧。反之,未能成就时忧虑于得不到,得到后又忧虑于失去,不管是哪一种都无一日之乐。“得”与“失”不过是心之所患,是外加于快乐情感上的遮蔽情绪,悖于君子的修行之乐。孔子称赞颜回“不改其乐”并连续长叹“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阳明也称赞颜回“不改其乐”,并从“得”“失”的反面角度,认为颜回“此与世之谋声利,苦心焦劳,患得患失,逐逐终其身,耗劳其神气,奚啻百倍”[4]1025。孔子、颜回已经有了明显的乐如磐石的意味,阳明则明确地把孔颜之乐提升到心之本体的地位,强调在修行过程中,君子永远是快乐的,小人本来也是快乐的,但其患得患失之心成为快乐情感的遮蔽。这也正是现代新儒家钱穆以孔颜之乐为人生本体,为“人生一最高境界最高艺术”[6]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本体之乐与七情之乐
阳明感叹道:“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4]119宇宙的一切都是由这个精灵送到的,任何事物都无法与它相比[7]。既然良知是心之本体和乐之本体,乐也是心之本体,那么良知、乐与心是三位一体的。乐是良知和人心,故而良知具有高度的情感体验性,致良知当然也是对快乐情感的追求和实现:“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4]82“慊”为满足、心安、和畅快乐之意,“自慊”为俯仰无愧的和畅快乐,可见良知在情感上的内指性,致良知在情感上就是对乐的心之本体的自觉和袒露。
在良知的情感性与外显的、感性的情感的关系上,阳明说:“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4]73良知如同日光,恒照万物,也摄照所有情感。作为本体的良知,与人人都有的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本无区别,七情也无所谓善恶,但人心有所执着而流于私欲,如同云雾遮日,故而不识良知,于是二者就区分开了。只有“认得良知明白”才能使七情回归本位,因为良知之用正在于“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4]126喜怒哀乐等都是人性的表现,在自然情况下是中和的。人心、良知受到外来之气和物欲的遮蔽,情感也就不再中和,有所过或有所不及。也就是说,日常的感性情感是自然的情感,与本体之乐本无二致,心中有了私念,才使之从真乐中脱离出来,成了负面情感。所以好色、好利、好名等一应私心须扫除荡涤,丝毫不留,让感性情感回归到中和状态,恢复真乐。周敦颐以窗前草“与自家意思一般”[2]60而不薅除之,在阳明看来就是感性的情感与心之本体的契合。薛侃去草则是着了意,忿懥、好乐不得其正,感性的情感与心之本体分离开来,成了两样。良知所照之处,因减法这一简易透彻、轻快脱洒之功,一切情感都得以净化,回归中和,“认得良知明白”就是要让感性的七情合于内在的心之本体的真乐。具体到本体之乐与感性七情之乐的关系及其实现的可能性上,阳明说: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4]79
心之本体之乐与七情之乐的关系,同作为本体的良知与作为感性情感的七情之间的关系一样,心之本体的真乐的至高境界不是感性的快乐,但又与之不无关系,不外在于喜怒哀惧爱恶欲的七情之乐。“圣贤别有”的最高境界的“真乐”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因为“常人之所同有”,可见常人的七情之乐与心之本体之乐乃一体两面,或者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也可以说这种真乐就是理性与感性相统一之乐。说二者不同,是因为真乐是内在的,七情之乐是外显的,真乐无待而七情或有滞,七情有滞则会遮蔽真乐,或者说过或不及的七情不是真乐。说真乐“不外于七情之乐”,是因为处于中和状态的七情之乐就是真乐,二者是一回事。人之所以不乐,不过是因为自寻烦恼、自求忧苦、自加迷弃,七情之乐的本真面貌被遮蔽。所以阳明才说此乐“未尝不存”,即人人皆有,圣贤有,常人也有。
同样,在方法上,作为心之本体之乐“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但七情终究是感性的、易变的,所以往往溢过中和的情感而少有不足的情况,溢过了就成了“私意”,作为“私意”的情感当然要直接减去。弟子陆澄得信闻儿子病危,心中忧闷不堪,阳明告诫云:“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4]19也就是说,在曲解了儒家真义的人眼里,儿病当忧且应忧不能已。但在阳明看来,父母因儿病而“一向忧苦”其实于事无补,而且扭曲了疼爱孩子这一美好情感,实为私意。乐为人之本有,而人之所以忧苦,全是因为庸人自扰,属骑驴觅驴,是“加”进去的。此亦如《大学》所否定的“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的情感,并不中和。忧则忧矣,但要及时止忧,调停适中,回归心之本体之乐。同样,“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4]19-20。阳明引《孝经》“毁不灭性”来推论,认为父母去世,子女哭泣到伤害自己身体,甚至死亡的地步,这样的过分情感也需要直接减去。但凡心中识得无所待而然的乐之本体,即便有哀也不失本心,不失其增减分毫不得之乐。
然从另一角度而言,哭也是乐。对于“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的疑问,阳明答曰:“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4]127大哭一番是为排解、减去心中的悲痛,显出作为心之本体的、本原性的、永恒存在的、未尝有动的乐,心归安处,所以说“不哭便不乐”。此亦见本体之乐不同于七情又不外于七情之义。“此心安处是乐也”实为“乐是心之本体”的另一种表述,但更强调心与乐的动态关系。一方面,心灵得以抚慰安顿即是乐;另一方面,心灵得以抚慰安顿之所,即乐为本体之处。孔子要求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论语·阳货》),孔子、阳明化礼制为情感之心,实际上蕴涵着乐之本体,即“不甘”“不乐”“不安”为乐之本体的外在的、感性的表现,而乐之本体安如磐石而未尝有动。这是知孝处孝、知丧处丧的安与乐,其中有一个动态的情感变化过程。就此而言,“此心安处是乐也”正好符合真哀真哭的伦理原则。阳明并未因肯定本体之乐而否定感性的哭,不过是在做减法,以良知自觉之功减至“本体未尝有动”的乐之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