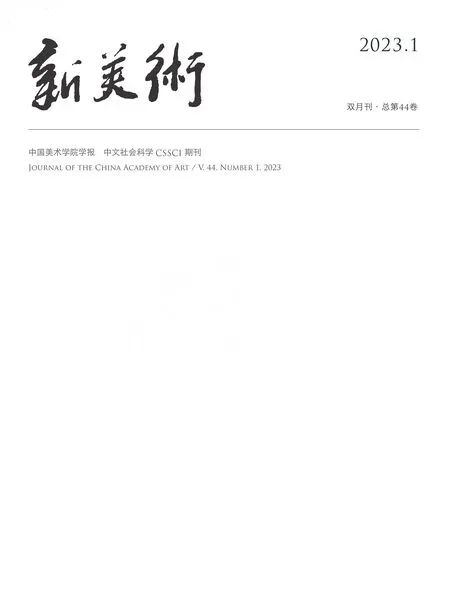陈师曾东京留学考*
王 梓
一 引言
近代以来中文语境下使用的“留学”是日语“留学(りゅうがく)”的借词[neologism],指的是晚清同治以来,中国人到日本和欧美等国接受各类教育的活动。1李雪涛,《留学史研究范式的评价与反思:以〈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为中心的讨论》,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 期,第137 页。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梳理了1870年至1926年中国留学制度的创立与设计、主要留学目的地、留学生人数、所学科目、留学生管理和思想变迁等内容,为作为学科的中国留学史奠基。2同注1,第134 页。现阶段关于中国留学史的研究相对侧重于留学制度和政策,对“留学内史”,即新知识生成的路径和载体、学术谱系的梳理,研究对象留学前后思想的差异性,被移植的新知识如何成为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则是关注不足。3同注1,第138—139 页。
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同样关注艺术家的留学问题。华天雪和曹庆晖具体阐述了“美术留学”与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和中国留学史研究的关系,提出“美术留学”是 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和内容,也是近现代中国留学史的有机组成。4华天雪、曹庆晖,《由“果”而“因”:关于“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与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载《美术观察》2019年第7 期,第35 页。以 20世纪上半叶为限,中国学生“美术留学”的目的地首先以日本为主,五四运动后由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展等原因逐渐形成了“留欧”与“留日”潮流并重的局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美术留学”随之沉寂。5同注4。考虑到时代和历史语境的特殊性,“美术留学”涉及的研究范围与广义的留学稍有不同。研究近现代中国的“美术留学”不应局限于制度意义上的留学,即在学校及其他机构接受专业教育,相反,被研究对象留学期间的游历、考察和交流都是美术留学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6同注4。
现有成果的研究对象多为留学期间学习西方美术(绘画、雕塑和图案等)的中国艺术家群体,而忽略了留学期间学习美术以外的科目、归国后从事中国传统美术创作的艺术家。研究方法方面,先行研究多将“留学”视为研究对象生平的一个特定阶段来加以简要叙述。由于对海外资料掌握的不足,研究者对艺术家具体留学经历的探讨时常不够充分,关注点多集中在留学这个结果对艺术家的个人创作、所处的艺术圈,乃至本土美术界产生的影响,例如新美术思潮与观念的引进,现代美术社团的组建、专业报刊的出版和美术展览的组织等等。此外,影响研究的部分也缺乏详细扎实的溯源。
李雪涛指出,大部分归国留学生移植的外来新知识和新思想的生成均与留学本身有关,“留学”是知识生成的“原点”。对于“留学内史”研究的不足,将无法展开对于“留学影响史”的进一步探索。7同注1,第135—136 页、第138—139 页。以本文的研究对象陈师曾(1876—1923)为例,俞剑华、龚产兴、朱万章和胡健的研究专著均对艺术家在东京的八年留学经历语焉不详,缺乏对陈师曾学习的课程、内容及师承关系的考证,也鲜少涉及陈师曾在东京的交游状况。8俞剑华,《陈师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龚产兴,《陈师曾年表》,载王明明主编,《京派绘画研究》,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39—63 页;朱万章,《陈师曾》,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胡健,《朽者不朽:论陈师曾与清末民初画坛的文化保守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留学内史”的角度入手,通过档案等一手材料的运用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还原陈师曾在东京弘文学院(1903—1904)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4—1909)的具体学习情况,以期澄清一些史实。本文还将重点关注陈师曾师从小山正太郎(1857—1916)系统学习图画科目的经历,从“知识迁移”的角度梳理陈师曾的图画相关知识生成的路径和载体,并以所撰《铅笔习画帖》(1907)和《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的意见》(1920)为例,探索陈师曾移植的美术知识如何与本土现有美术知识有效融合,从而成为中国美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最后,本文将探讨陈师曾因留学经历而引发的对于复兴文人画的思考和实践,并以陈师曾的译文《欧洲画界最近之倾向》(1912)、《文人画之价值》(1921)和此前较少为学界关注的《南畫に就いて》(《关于南画》,1922)为例梳理艺术家绘画史观形成的思想脉络。
二 陈师曾留日早期的经历:抵达东京、成城学校、弘文学院
陈师曾于1902年3月29日搭乘神户丸号邮轮赴东京,开启了长达八年的留日生涯。9[日]北冈正子,《日本异文化中的鲁迅》,王敬翔、李文卿译,麦田出版社,2018年,第55—58 页。根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公信第八二号:南京陆师学堂俞总办率留学生出发前往我国之件》(明治三十五年,即1902年3月21日,图1),陈师曾以随行“文案”的身份同行赴日。10同注9,第55—56 页;日本从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即1872年1月1日)由和历改为西历,并将当日调整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而同时期清朝仍沿用农历。

图1 日本外务省《公信第八二号:南京陆师学堂俞总办率留学生出发前往我国之件》
陈师曾得以成行应是得益于信函中提到的“俞总办”的帮助。“俞总办”即前一年(1901)接任江南陆师学堂校长的俞明震(1860—1918)。11同注9,第60 页。俞氏属维新派,戊戌变法期间积极支持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并参与陈师曾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在湖南推行的新政。此外,俞家与陈家还是姻亲,俞氏的妹妹俞明诗(1865—1923)是陈师曾的继母。12张求会,《陈寅恪家史》,东方出版社,2019年,第154—156 页。
根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1903年3月)所示,陈师曾抵日后曾短暂自费就读于成城学校武班(陆军部,图2)。13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1903年3月29日,第16 页。需要指出的是,报告中记载的陈师曾抵日时间为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即1903年1月),与《公信第八二号》所载日期“1902年3月”矛盾,陈师曾抵日时间仍应以《公信第八二号为准》。成城学校是陆军学生的预备学校,于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开始设立清朝留学生部,该部分为文武两班,教授日语,合格的武班毕业生将直升陆军士官学校,文班学生则修习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的预备课程。14同注9,第70 页。由于就读时间较短,陈师曾在成城学校学习的具体课程等信息暂不可知。

图2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第16 页
北冈正子依据保存于日本讲道馆的弘文学院相关资料——《学生异动报告书》,指出陈师曾于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5月入学弘文学院。15同注9,第73 页。在1903年11月刊发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中,陈师曾注册的学校已由成城学校改为弘文学院(图3)。16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编,《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清国留学生会馆,1903年11月21日,第29 页。

图3 《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第29 页
弘文学院由时任高等师范学校(1902年 3月,校名由“高等师范学校”更名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并致力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嘉纳治五郎(1860—1938)创立,历经近一年的筹备,于 1902年 4月 12日正式获官方认可而设立。17同注9,第78 页。学院主要教授日语和基础教育课程,为中国留学生后续升入高等专门学校或大学做准备。18同注9,第94 页。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进入弘文学院学习的黄尊三(1880—1950)在当年 6月 27日的日记中记录如下:“弘文学院是专门为教育中国留学生而设,就像普通中学一样。学科上重视日语及普通学科,是为了将来要报考高等学校与大学的预备学校。因为中国学术缺乏基础学养,若不多加补习,便无法学习高级的专门知识。”19黄尊三,《黄尊三日记(上)》,谭徐锋整理,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10 页。
弘文学院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渊源颇深,除校长嘉纳治五郎以外,学校还聘请了多位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与高师毕业生来校任教。20同注9,第312 页。北冈正子指出,正因为两校之间的紧密联系,弘文学院的毕业生中选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深造的学生相较于其他学校为多。21同注9,第312 页。这一点也多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陈师曾选择之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深造的原因。
《私立弘文学院规则》提供了陈师曾在弘文学院的具体学习情况。22同注9,第94—104 页。根据《规则》第二章第四条,弘文学院的新学年从每年的9月11日开始,第二年的7月31日结束,每个学年共分为三个学期。学院设有年限为三年的普通科和两年的速成科,除年限缩短外,速成科学习的课程与普通科不存在明显差别。以普通科为例,第一学年的必修课程包括修身、日语、地理历史、算数、理科指导、体操。第二学年的必修课程在第一学年的基础上增加了代数、几何、理化和图画,并新增英语作为选修科目。最后一年的课程设置中保留了修身、日语和体操,不再开设地理历史和理科指导,新增了三角函数、历史及世界趋势、动物、植物等课程,并将英语调整为必修课。23同注9,第96—99 页。值得注意的是,周树人(1881—1936)等多数中国学生均选择了速成科,即在两年之内完成弘文学院的学业,这样可以提早升入上一级学校继续深造。24同注9,第112 页。《陈师曾年表》中记载其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时间为 1904年秋(明治三十七年),这一观点也是学界目前公认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陈师曾在弘文学院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并于此期间学习过《学则》中列出的部分必修课程。25龚产兴,《陈师曾年表》,第39—63 页;《陈师曾年表》,载朱良志、邓锋主编,《陈师曾全集诗文卷》,江西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290 页。
关于陈师曾在弘文学院的业余生活和交游,学院明确要求中国留学生集体住宿,根据陈师曾的室友沈瓞民(1878—1969)的回忆,同住的中国留学生还包括周树人、刘乃弼(1878—?)、顾琅(1880—1940?)、张邦华(1873—1957)和伍崇学(1880—?)。26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载《文汇报》,1961年9月23日。根据日本外务省保存的《受第四五四二号》(图4),陈师曾的五位室友均为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派出的官费留学生。

图4 日本外务省《受第四五四二号》
学院还为住宿的留学生安排了较为丰富的暑假(每年8月1日至9月10日)活动,主要形式有避暑和远足两种。27同注9,第269 页。根据《弘文学院沿革资料》,1903年8月学院组织了赴伊豆的伊东进行的避暑旅行;同月,留学生们还集体前往位于埼玉县东南部的大宫公园远足,并参观了日本铁道公司大宫工厂以及王子纸场。28同注9,第270 页。陈师曾很可能参加了上述暑期活动。
三 陈师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
笔者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画派的国际形象塑造:“现代中国画”概念的一种诠释》一文中引用大村西崖(1868—1927)编纂的《禹域今画录》所刊载的陈师曾自传,已证明陈师曾“既而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学科。”29笔者认为,这份材料应是现存最早、最完备可靠的陈氏个人小传,早于其父陈三立(1853—1937)撰写的《长男衡恪状》(1923)以及陈三立的学生袁思亮(1879—1939)所书的《陈师曾墓志铭》(1926),对于学者研究陈师曾的生平和艺术谱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日]大村西崖,《禹域今畫錄》,又玄画社,1922年;陈三立,《长男衡恪状》,载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钱文忠标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96 页;袁思亮,《陈师曾墓志铭》,载《华国》1926年第1 期,第83—84 页;王梓,《20世纪20年代北京画派的国际形象塑造:“现代中国画”概念的一种诠释》,载《美术观察》2021年第11 期,第49—54 页。关于陈师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留学经历,先行研究以龚产兴的《陈师曾年表》和《陈师曾全集》所载《陈师曾年表》为准:陈师曾于1904 秋至1909年夏(明治四十二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学习。30同注25。然而,关于陈师曾在此期间的注册身份、所学科目、学习内容、师承关系等问题仍待解决。
陈师曾留学期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即为弘文学院创始人嘉纳治五郎。31《職員》,载東京高等師範学校,《東京高等師範学校一覧》,明治37年4月—明治38年3月、明治38年4月—明治39年3月、明治39年4月—明治40年3月、明治40年4月—明治41年3月、明治41年4月—明治42年3月、明治42年4月—明治43年3月。每学年由校方出版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包括学校规章制度、各学部课程安排、教职员名单、在校生名单以及历年毕业生去向等详细的信息,是研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运行状况的最权威史料。学校的办学目的是培养师范学校、中学校、高等女学校等学校的校长和教员,兼具研究普通教育的方法。32東京高等師範学校,《東京高等師範学校一覧》,明治36年4月—明治37年3月,第50 页。相应的,陈师曾学成归国之后长期担任公立师范学校的博物学教师(任教学校根据时间先后排列分别为:通州师范学校、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33龚产兴,《陈师曾年表》,第291—301 页。
关于陈师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籍信息,目前可以从1908年4月至1909年3月(明治四十一年至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3月至1910年4月(明治四十二年至明治四十三年)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中找到陈师曾“听讲生”身份的证明(图5、图6),但未注明属于哪个学部(1908年之前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尚未在“在校生”一栏中列出“听讲生”,1910年之后的听讲生名单中不再有关于陈师曾的记载)。“陈衡恪”的“恪”均误写为“格”。有记录的毕业年份为1910年,而非《陈师曾年表》中记载的1909年。34邵艶、[日]船寄俊雄,《清朝末期における留日師範生の教育実態に関する研究:宏文学院と東京高等師範学校を中心に》,载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编,《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 2003年第10卷第2号,第394页。1904年秋至1908年3月的在学信息暂不明。

图5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1908年4月至1909年3月)“听讲生”名单(左)

图6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1909年3月至1910年4月)“听讲生”名单(右)
关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招收“听讲生”的具体规定,以及“听讲生”的学习和考核要求,可参见下列几份文件。其一,根据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11月11日制定的《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第一条,“外国人于文部省直辖学校学习不受该校一般学则规程约束,学习所规定的学科中某一科或数科者,需由外务省在外公馆或本邦所在外国公馆介绍方许可。”35同注34,第394 页。其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8年6月17日制定的《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细则》(图7)第一条记载:“依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如外国人希望入学,则可作为听讲生特别许可。”36《外國人特別入學規程細則》,载東京高等師範学校,《東京高等師範学校一覧》,明治41年4月—明治42年3月,第115—116页。因此可认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依此入学,学习科目大多为某学部(例如博物学部)中的一科或数科。其三,“听讲生”在学习科目数量上与日本人有区别,属于特殊对待,但在考试上与日本学生完全相同,如1907年4月(明治四十年)制定的《听讲生学习心得》(图8)第四条:“听讲科目应与本校学生一同参加考试”;《外国人特别入学规则细则》第三条:“向学科修了,并获得相当成绩者授予毕业证书。”37《聽講生受業心得》,载《東京高等師範学校一覧》,明治41年4月—明治42年3月,第163—164 页;《外國人特別入學規程細則》,第115 页。然而,由于史料不足,“听讲生”的具体考评标准、是否颁发和如何颁发毕业证书等问题尚存疑。

图7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细则》

图8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讲生受业心得》
根据《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的记载,陈师曾以“听讲生”的身份在校的专攻科目一共有四门,分别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和农学。38同注34,第395 页。这四门课均为1904年4月开始实施的新规中规定的博物学部本科的必修课程。39同注32,第61—63 页。这是陈师曾自传和先行研究中关于陈师曾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科的判断依据。综合《陈师曾年表》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两份资料记载的陈师曾入学和毕业的大致年份可知,本文中讨论的陈师曾在校期间课程学习等一应信息均应参考上述新修版规程。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从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开始在本科的基础上新设了预科和研究科,其中预科的修习时间为一年,升入本科之前必须先修预科且成绩合格。40東京高等師範学校,《東京高等師範学校沿革略志》,明治44年, 第64—65 页。本科时限为三年,明确分为四个学部:国语汉文部、地理历史部、数物化学部和博物学部。研究科期限为一至两年,开设目的是根据学生的就业意向(例如小学、中学、专科等)进行进一步的知识和教育培训。41同注40。
以1904年的新规为准,预科课程包括:伦理(人伦道德的要旨)、国语(讲读、普通文法及作文)、汉文(讲读)、英语(讲读、文法、作文会话、书取)、数学(算数、几何学、代数学、三角法)、论理(演绎法、归纳法、方法学)、图画(临画、写生画、几何画、水彩画)、音乐(声乐练习及理论)、体操(普通体操法及游戏、兵式训练)。42同注32,第63—64 页。本科博物学部的必修课程如下:伦理(伦理学)、心理学及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学校卫生、教育法令、教授练习)、植物学(外部形态学、内部形态学、分类学、生理学、实验)、动物学(通论、各论、发生学、进化论、实验)、生理学及卫生(人身生理、卫生、实验)、矿物学及地质学(矿物学、地质学、实验)、农学(作物论、土壤及肥料论、农业经济论、养畜及养蚕论、实验)、英语(讲读)、图画(写生画、水彩画、各种画法)、体操(普通体操及游戏、兵式训练);选修课程为化学、佛语、音乐(图9)。43同注32,第61—63 页。

图9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学部本科课表(1904年4月开始使用)
根据陈师曾的专攻科目,整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记载的相关授课教师信息如下:
丘浅次郎(1868—1944),理学博士、教授,动物学、生理学及卫生;
齐田功太郎(1859—1924),理学博士、教授,植物学;
高仓卯三鹰(生卒年不详),教授,动物学、生理学;
佐佐木祐太郎(生卒年不详),教授,农学;
高橋章臣(生卒年不详),教授,植物学;
橋本章司(生卒年不详),助教授,农学;
大泽谦二(1852—1927),医学博士、讲师,生理学及卫生;
根本莞尔(1860—1936),植物学副手;
安藤孝(生卒年不详),植物学副手;
内田茂(生卒年不详),动物学副手;
赤松又次郎(生卒年不详),清国学生指导;
高桥彦一(生卒年不详),农学副手。44《職員》,载《東京高等師範学校一覧》,明治41年4月—明治42年3月、明治42年4月—明治43年3月。
除有记载的四门专攻科目之外,由预科和博物学本科的课表可知,图画是博物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图画课设置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博物学学生绘制博物图的能力,即以写生的方式精确地描绘植物、动物和矿物的形态。陈师曾归国后曾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图画教师。45陈师曾,《对于教授普通图画科意见》,载《绘学杂志》1920年第1 期,第9—12 页。所以基本可以肯定,陈师曾就读于博物学部期间曾系统学习过图画课程。依据《听讲生学习心得》第三条,此推论符合规定:“准许听讲的科目至修了为止不得变更,但具有充分理由获得特别许可时则不受此限制。”46《聽講生受業心得》,第164 页。而陈师曾的友人、学者桥川时雄也曾回忆,陈师曾在东京期间曾跟随小山正太郎(1857—1916)学习过铅笔画和水彩画。47[日]橋川時雄,《橋川時雄の詩文と追憶》,[日]今村与志雄编,汲古書院, 2006年,第24—25 页。小山正太郎正是当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画讲师,而铅笔画和水彩画在小山正太郎的图画教学体系中均占据重要的地位。48[日]金子一夫,《小山正太郎の図画教育観》,载《近代日本美術教育の研究 明治·大正時代》,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99年,第391—392 页。陈师曾学习图画的经历以及小山正太郎对其在图画知识体系生成和在社会转型时期看待东亚传统绘画等方面的影响将在本文的第三、四、五节重点探讨。
学习之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课余活动,主要包括校友会、各类学科专业社团活动以及修学旅行等。
根据《高等师范学校三十三年规则》,校友会于1901年正式成立,该会的主要目的是修养精神、锻炼身体、振作校风和会员互助。49同注40,第69—70 页。校友会吸纳本校学生为正式会员,校长、教员等为特别会员(后改称赞助会员)。校友会还设有谈话部、杂志部和各类体育运动部等,并于成立的次年(1902)开始正式发行校友会杂志。50同注40,第69—70 页。根据 1903年修订版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规则》,校友会的规模在不断扩张,基本规制保持不变。51同注40,第69—70 页。
除校友会这一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学生组织之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各个学部的学生也会组织专业性质的社团。例如,博物学部的学生从1903年开始在校组织博物学会。该社团定期开会,活动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邀请本学科的知名学者到校演讲,编辑出版杂志等社团刊物等等。52同注40,第69 页。
由陈师曾学成归国后在通州师范任教期间发表的《在通州师范校友会第二次会上的讲话》可知,陈师曾对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上述两类学生组织非常熟悉,在讲话中谈及的日本学校校友会组织方法悉数参考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会和专业学生社团的经验:
日本学校校友会组织方法,各不相同。以弟肄业所及之高等师范学校之校友会言之,其情形方法,可与本校参考。其宗旨在训练学生,所以会中办事之人,皆学生任之。以养成其自治力及公共心,故学生与校长师长合一处。会长以校长当之,副会长以教务长当之,办事者如书记交际等,皆学生为之。……所办之事分二种,一文艺部。如伦理学会、国文会、地理历史会、讲演会。……讲演会,无论何种学术,皆可言。即校外之人有声望有学术者,皆可几期来讲。……每部必有干事员,费皆由会员及校长给予。凡会事,教员帮忙而已,学生为主体。53陈衡恪,《在通州师范校友会第二次会上的讲话》,载刘经富编,《陈衡恪诗文集》,江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95 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陈师曾后来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和专业学生社团的经验直接应用于在北京组织现代美术社团,尤其是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之上。这部分内容将在《“沙龙”在民初北京画坛的兴起与发展:以陈师曾为例》一文中进行详细论证。
最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从1903年开始逐年实施修学旅行计划。各学部每年至少组织一次修学旅行,每次时间为数日至十数日不等,旅行内容包括异地考察学校以及按照学部的专业进行实地考察,旨在增强和丰富学生的实践经历。另外,各学部每年还会组织数次前往东京近郊的远足活动。54同注40,第69 页。陈师曾作有一首七言律诗《日光山采植物》,诗中所记录的便是博物学部于1908年夏季组织的一次赴关东地区栃木县以采集植物标本为目的的修学旅行。陈诗云:“十日山行雾雨中,阴林夏木凛秋容。有时鸣瀑飞晴翠,顷刻浮岚滃太空。啼鸟乍随樵径转,鲜花远傍佛龛红。采香不惜沾衣冷,未必荃兰满药笼。”55陈师曾,《日光山采植物》,载刘经富编,《陈衡恪诗文集》,第28 页。
四 小山正太郎的图画课
陈师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博物学部图画课的讲师为日本著名的洋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小山正太郎,助教为平木政次(1859—1943)。56同注32,第183 页。小山正太郎是陈师曾留学期间获取西方美术知识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对陈师曾的影响涉及多方面,例如陈师曾编写的《铅笔习画帖》、归国后的图画教学理念及内容,以及在新旧时代更迭之际对于复兴东亚传统绘画的思考和实践等等。
小山正太郎于1878年首次任教于高等师范学校,并于次年2月参与制定了学校的教学规则,奠定了以自在画(临画、写生)和用器画(几何画法、透视画法、投影画法、测绘图法等)为主体的图画课教学模式。57[日]金子一夫,《小山正太郎と洋画教育》,载《近代日本美術教育の研究 明治·大正時代》,第130 页。“自在画(自在画)”是指不借助尺子、指南针等工具就可以徒手画出的画。相反的,“用器画(用器図)”表示需要使用尺子、量角器或圆规等制图工具来绘制的几何图形。经历辞职风波之后,小山正太郎于1901年被重新任命为高等师范学校手工图画科和博物科的图画教师,1912年被任命为手工图画科的学级主任(即系主任)。58高村真夫编,《年譜》,载《小山正太郎先生》,不同舎旧友会,1934年,第309、311 页。
小山正太郎授课主要使用自编教材,核心内容汇总整理成《图画教授法讲义》(1909),后又有重新整编的《图画讲义》(1915)。59[日]小山正太郎,《図画教授法講義》,新潟県教育会,1909年;[日]小山正太郎,《図画講義》, 修学堂,1915年。《图画教授法讲义》总计七章,分为“图画科的目的”“临画教授法”“听画”“色彩画教授法”“写生画教授法”“各种辅助画”(即用器画)、“考案画教授法”(即图案画)、“复画教授法”,附录部分另有小山正太郎对图画科重要问题的回答,例如“铅笔画与毛笔画之争”,等等。60[日]小山正太郎,《目次》,载《図画教授法講義》。小山正太郎认为,图画教育的必要性在于图画具有语言文字所缺乏的直观性与普遍性的特质。图画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能力的培养,二是思想的表达。具体而言,第一项是图画相关的种种能力,例如观察、想象、记忆、理解、计划、判断、创作等,又或者是培养美感、手的灵活度等,主要针对低年级学生。高学年阶段则主要以训练第二项为目的。61[日]小山正太郎,《第一講 図画科の目的》,载《図画教授法講義》,第3—9 页。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小山正太郎将临画、听画、思考画、辅助画、写生画和复画列为“自在画”的教学范畴。62[日]金子一夫,《小山正太郎と洋画教育》,载《近代日本美術教育の研究 明治·大正時代》,第130 页。举例来说,临画的目的在于训练学生发现、捕捉原画形貌的能力。63[日]小山正太郎,《第二講 臨画教授法》,载《図画教授法講義》, 第10—11 页。听画又称听写画[dictation exercise],教师口述线条,学生下笔,使线条构成某种图形,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注意力。64[日]小山正太郎,《第三講 聴画》,载《図画教授法講義》,第25 页。写生画的要点在于照实物原样描绘,而非依靠个人美感对描绘对象进行重组。65[日]小山正太郎,《写生画教授法》,载《図画教授法講義》,第47—48 页。复画[memory exercise]又称为记忆画,即凭记忆将画过一遍的画再默写一遍。66同注62,第131 页。值得注意的是,听画和复画两项来自美国的美术教育家沃尔特·史密斯[Walter Smith,1836-1886]的著述。67Smith,Water.Teacher’s Manual for Freehand Drawing in Primary Schools,James R.Osgood and Company,1875,pp.13-15.金子一夫指出,听画和复画的教授在明治后期被废除,但小山正太郎在自编讲义和实际教学中依然重视这两项内容。68同注62,第131 页。小山正太郎同样重视用器画的教学,所用的理论课本包括《器象显真》[The Engineer and Machinist’s Drawing Book]、《运规约指》这类西洋书籍的汉译本以及威廉·埃兹拉·沃森[William Ezra Worthen,1819-1897]、埃利斯·亚布拉罕·戴维森[Ellis Abraham Davidson,1828-1878]和沃尔特·史密斯等人所著的西洋书籍。69同注62,第131 页。此外,还有学生回忆,小山正太郎的教学指导方法并非现场上手作画进行示范,而是以教鞭边指着画面边进行解说。70[日]金子一夫,《高等師範学校講師および国指定教科書編纂》,载《近代日本美術教育の研究 明治·大正時代》,第135 页。
根据《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记载的1904年版新修课程表,博物学部预科的图画课每周总计六小时,分别为临画、写生两小时;投影画法、照镜画法、黑板画练习两小时;水彩画两小时(图10)。71同注32,第64 页。本科在第一学年安排了图画课:第一学期每周学习写生画两小时;第二学期每周学习水彩画两小时;第三学期每周学习各种画法两小时(图9)。72同注32,第71 页。授课内容和模式基本上沿袭了小山正太郎1879年初次任教时制定的范式,并根据博物学部的具体培养目标有所调整。例如,黑板画训练主要是为了学生毕业后授课时在黑板上用粉笔作图做准备。写生和水彩画在预科和本科的图画课中所占课时比重均较高,这两门课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培养学生精准绘制兼具科学之真、自然之实和艺术之美的博物图的能力。户外远足采集标本并绘制博物画是博物学部学生的重要培养方式之一。

图10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课表
小山正太郎的助手平木政次回忆,小山氏为博物科学生开设的图画课通常采用集中授课的模式,一次性连上四至五天,课后会组织茶话会以增进师生之间的交流。73[日]平木政次,《高等師範に於ける小山先生》,载高村真夫编,《小山正太郎先生》,第101 页。平木政次还提到,小山正太郎还会带学生去东京郊区或更远的地方进行写生旅行,训练学生观察自然和户外写生的能力。74同注73,第103 页。旅行途中学生们也能看到小山正太郎实际作画的情形。75同注73,第103 页。
根据上述课程安排,我们可以推断,陈师曾应当熟识小山氏的授课方法和图画教学理念。陈师曾归国后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图画教授,结合留学期间所学以及实际授课的心得体会,他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做了题为《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的意见》,该文在多处阐发了小山正太郎对图画教育的理解以及具体教授方法的经验,讲稿整理后刊登于《绘学杂志》。
首先,陈师曾在开篇表明了学校开设图画课的两点必要性: 其一,“精神上美感教育,养成高尚思想之人格。惟教育可以变化气质,增进知识,养成完尚之人格。”其二,“技能上之练习。目观手摹,以练技能,不特图画可以进步,即人之观察力亦当趋于灵敏。故美感教育对于社会上应用之点甚多。”上述两点是基于小山正太郎提出的图画教育的主要目的,即能力的培养和思想的表达。
其次,陈师曾将图画教育应包括的主要画法分为三种:
(一)临画。仿范本。(二)写生。对实物。(三)记忆画。记忆画者,即作画时,目前不置一物,而将平日所曾临者、所写者、所见者,任笔挥洒写出之谓也。此种画法最为有益,一可比较前日临画时曾留意否,一可练习记忆力与理会力,补助画法进步,收效不鲜。要之皆所谓自在画也。又有器械画,即普通教育之几何画也……他如投影画、透视画,亦皆此画之一种。76同注45,第10—11 页。
由上述归纳可知,陈师曾和小山正太郎一样非常重视“自在画”的教授,临画、写生和记忆画(即小山正太郎所谓的“复画”)均是小山正太郎在自编教材《图画教授法讲义》等和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日常教学中侧重的内容。陈师曾在“器械画”(即用器画)部分列举的投影画和透视画,也均属于小山正太郎所制定的图画课教学模式的主体部分。需要注意的是,陈师曾在文中将器械画解释为“普通教育之几何画”是不正确的,几何画应和投影画、透视画等并列,属于用器画的一种。
进入20世纪,临画和记忆画在图画教学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写生所取代,日本从明治晚期开始逐渐在图画课程设置和教材编纂中取消了这两类画。77同注62,第131 页。陈师曾却和老师小山正太郎一样坚定地支持临画和记忆画的保留,认为在上述三种画法中,“临画一法尤为重要”,并以接近全文一半的篇幅对临画的要点、方法和步骤加以详细阐述。值得注意的是,陈师曾从总述的“临画之要,在先习古人如何用笔,如何位置,如何赋色,而后能知画中之气韵与夫美术之所以有价值也”,到末尾处临画的两种方式“摸法”和“分段临摹法”,其讨论对象均是国画而非西画的临摹。讲解“摸法”时,陈师曾将图画课常见的铅笔应用于国画的临摹,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范本的大致轮廓、标注主体的位置,此举是发挥了小山正太郎提倡图画教育应以铅笔画为主导时强调的铅笔易使用、画痕易修改的特性。78同注45,第12 页;[日]小山正太郎,《毛筆画と鉛筆画との得失》,载《図画教授法講義》,第88—91 页。陈师曾认为,图画的重要性在于可以代表各国国民的个性,研究图画的方法“宜应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 按照上述思路,陈师曾列举的记忆画也是国画创作的重要方法之一,例如山水画和花鸟画,画家将不同时段观察自然的体验默记于心,之后再呈现于画面之上。
陈师曾对于临画的重视与其在《南畫に就いて》一文中提出的学习和研究国画需要“法古”的观点相一致。“以古为法而不拘泥于古……盖推陈出新,若无陈亦不出新”,意思是若不以古为法则习画毫无根据,“终究不得古贤本真趣味及东洋之特长的文明精神”;而如果过于拘泥古法,则会为陈法所困,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使得时代性或个人特征埋没而终”。79陳衡恪,《南畫に就いて》,载《東洋》1922年第25 卷第10 号,第130—131 页。综上,陈师曾在阐释由日本引入的、图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方法时,仍以国画为例,将图画的新理念与国画的传统画法融会贯通,既在北京传播了小山正太郎的图画教学理念,又借助图画重申了临画和记忆画训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使得图画成了本土绘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五 陈师曾的《铅笔习画帖》
光绪二十九年(1904),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图画科第一次被引入普通学校的教育之中,教学目的、内容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明治时期的美术教育的影响。80胡知凡,《日本对我国清末时期中小学图画教育的影响》,载《美育学刊》2013年第4 期,第36 页。为满足新式学堂教科书的需求,许多出版社开始翻译和编纂日本的教科书。81同注80,第38 页。光绪三十三年(1907),尚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陈师曾绘制的《寻常小学铅笔习画帖(第四学年用)》(图11-1)由上海普及书局发行、东京博信堂印刷。82严晓星认为,发行和印刷由上海和东京两处异地完成,可能是由于当时出版界的风气,也可能是出于合作的便利。见严晓星,《陈师曾早年的〈铅笔习画帖〉》,载《舟榻编》,江西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24—28 页(《铅笔习画帖》全篇见同书第28—49 页)。上海普及书局创办于光绪年间,以出版教材见长,晚清部分由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便是由日本方面印刷、上海普及书局发行的。83严晓星,《舟榻编》,第25 页。在石鸥整理的1900年至1911年间问世的留日学生编译教材中,上海普及书局发行的有五种。84石鸥,《附录三: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载《弦诵之声: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文化使命》,湖南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21—127 页。需要注意的是,在陈师曾的《铅笔习画帖》之后,由清政府模仿日本文部省制度成立的学部编写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两套国定小学图画教科书——《初等小学图画教科书》三册(1910),《高等小学图画教科书》四册(1909)。85国立编译馆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研究小组编,《中小学教科书用书编辑制度研究》,正中书局,1988年,第16 页。
《铅笔习画帖》的“画者”一栏署名只有“陈衡恪”一人(图11-2),但本书从装订方式和内容(说明文字、插图)方面基本上完全照搬了小山正太郎的《尋常小學鉛筆畫手本 第四學年用》(《寻常小学铅笔画范本 第四学年用》,图12-1)。86[日]小山正太郎,《尋常小學鉛筆畫手本 第四學年用》,载[日]海後宗臣等編,《日本教科書大系·近代編 第26 巻 (図画)》,講談社,1966年,第160—165 页。

图11-2 陈师曾,《寻常小学铅笔习画帖 第四学年用》封底

图11-3 陈师曾,《寻常小学铅笔习画帖 第四学年用》,第一铅笔画法

图11-4 陈师曾,《寻常小学铅笔习画帖 第四学年用》,第九立方体

图11-5 陈师曾,《寻常小学铅笔习画帖 第四学年用》,第十四木叶

图11-6 陈师曾,《寻常小学铅笔习画帖 第四学年用》,第十八圆柱

图11-7 陈师曾,《寻常小学铅笔习画帖第四学年用》,第二方胜

图11.8 陈师曾,《寻常小学铅笔习画帖 第四学年用》本册之要点

图12-1 [日]小山正太郎,《小學鉛筆畫手本》封底

图12-2 [日]小山正太郎,《尋常小學鉛筆畫手本 第四學年用》凡例
小山正太郎绘制的《小學鉛筆畫手本》系列(寻常小学二至三学年,高等小学一至二学年)出版于1904年11月,该书的内容和装订方式以小山正太郎所绘、1899年12月发行的《小學習画帖》(《小学习画帖》,明治三十二年十二月)为基础,各题材下甚至有相同的画。87同注62,第135 页。
《小學鉛筆畫手本》和白浜徵(1886—1928)绘制的《小學毛筆畫手本》(寻常小学二至三学年,高等小学一至二学年)共同隶属于明治时期日本第一期国定图画教科书的范畴,其诞生的背景是关于基础教育图画科目的讨论。进入明治三十年代,针对毛笔画教育的批判渐长,图画教育界内开始将“教育性图画”作为新理念引入,即将基础教育中的图画科目从毛笔画重新整理为教育性图画。文部省于明治三十五年设置“基础教育阶段图画调查委员会”,使之审议基础教育阶段图画科目的方向,长期坚定拥护铅笔画教育的小山正太郎位列委员之席。在委员会的报告中,也可见委员们认为不应在基础教育的图画科目上区分日本画与西洋画,而应教授有用的图画,即所谓的“教育性图画”。教育性图画也可理解为倡导铅笔画教育和倡导毛笔画教育这两派达成的折中方案。88同注62,第135 页。此后,教育性图画的具体化成了图画教育界的重中之重,其中第一步是根据国家教科书制度编纂国家指定的图画教科书。89同注62,第136 页。小山正太郎在第一期的图画教科书编纂工作中发挥了绝对的主导权。90同注62,第135—136 页。
针对在小学阶段要求学生学习毛笔画还是铅笔画的问题,小山正太郎给出了如下的回答:毛笔画表现了一种轻妙的笔意,有着特殊的趣味,小学阶段想要达到这种高度太困难。小学阶段图画的目的在于正确把握形状及对其摹写,在这一点上毛笔不及铅笔。91[日]小山正太郎,《毛筆画と鉛筆画との得失》,第88—91 页。小山正太郎倡导铅笔画的理念也体现在了《小學鉛筆畫手本》的编纂和绘图之中,例如《凡例》的第三条(图12-2):“本书不用轻妙潇洒的运笔,而主要目的在于正确描绘形态,这更适合令学生掌握通常形态,获得正确描画的技能。”

图12.3 [日]小山正太郎,《尋常小學鉛筆畫手本 第四學年用》,内页1

图12.4 [日]小山正太郎,《尋常小學鉛筆畫手本 第四學年用》,内页2

图12.5 [日]小山正太郎,《尋常小學鉛筆畫手本 第四學年用》,内页5

图12-6 [日]小山正太郎,《尋常小學鉛筆畫手本 第四學年用》教法须知

图12.7 [日]小山正太郎,《尋常小學鉛筆畫手本 第四學年用》本册使用须知
陈师曾《铅笔习画帖》的图片部分和小山正太郎的《小學鉛筆畫手本》(图12-3—图12-5)一样总计二十六张,其中陈师曾版原样照搬了小山正太郎版的十五张图,依次是:第一铅笔画法(图11-3)、第五角钟、第六蝴蝶、第七茶瓶、第九立方体(图11-4)、第十扫帚、第十二地球仪、第十四木叶(图11-5)、第十六黄瓜、第十七食盒、第十八圆柱(图11-6)、第十九茶筒、第二十灯塔、第二十四杂物、第二十五杂物。另有八张图是在小山正太郎版的原图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第二方胜(图11-7),原图画的是折纸方胜的正面,陈师曾版画的是俯视的视角;第三桃花,陈师曾将原图的花瓣改为圆形;第四提灯,陈师曾将原图的灯上装饰改为蝙蝠;第八日记本,陈师曾略去了原图上“小太郎”的签名;第十三麦草扇,陈师曾将扇子的形状调整为圆形;第十五图中,陈师曾将刀的形状改为扇形;第二十三杂物,陈师曾将太阳旗改为龙旗;第二十六杂物,陈师曾将物品种类进行了微调,摆放位置不变。只有三张图未包含在小山正太郎版中:第十一望远镜、第二十一苹果、第二十二习画本。
陈师曾《铅笔习画帖》的文字部分略去了小山正太郎《小學鉛筆畫手本》的《凡例》和《教法须知》(图12-6),只逐字逐句翻译了《本册之要点》(图11-8、图12-7)。《本册之要点》结合其中的四幅图总结了小学四年级的《铅笔习画帖》要教授的主要内容。第一图(铅笔画法)的目的是使用铅笔进行斜用笔、水平运笔垂直运笔的涂画练习,实现不同的线条效果和浓淡区别。第二图(方胜)和第十四图(木叶)的目的是训练简单的实物写生。第九图(立方体)和第十八图(圆柱)是为了教授基本的透视画法而设置,第九图所示为焦点透视,第十八图所示为缩短法,即物体根据位置不同会呈现不同形状,长度相同之物随着距离渐远会显得变短。
为了充分理解《铅笔习画帖》中占主体地位的图片的选择标准和所蕴含的教学目的,我们还应参考小山正太郎《小學鉛筆畫手本》的《凡例》和《教法须知》。由《凡例》可知,图片所绘内容均为学生日常所见之物,前二十二张图表现的单一主题,细节较丰富,目的是训练学生进行精确细致的绘画;后四张“杂物”则是多主题的组合,线条较为简略,只保留了大致的轮廓线,这是为学习略画的方法而设计的。由《教法须知》可知,学习用具是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要求通过改变运笔的角度来表现浓淡差异。图画的要求是位置端正、形态正确、运笔扎实。做画时先起草稿,再由画纸左上方向右下方正式作画。草稿尽量用直线,先画大体结构再加细节,用铅笔轻画,画错时用橡皮擦除,可以反复修改。
六 小山正太郎与陈师曾的诗意毛笔画
根据小山正太郎的年谱记载,其在1912年前后创作了一批诗意毛笔画,部分作品在1912年至1913年之间在《太阳》杂志上连载。92同注58,第309 也。有趣的是,陈师曾于1912年上半年在上海的《太平洋报》上陆续发表了六十余幅后来被丰子恺誉为“中国漫画的起源”的毛笔画作品,其中约三分之一是诗意简笔画,且陈师曾开始发表的时间(4月)晚于小山正太郎的时间(1月)。二者的画稿均以毛笔、浓墨绘制,线条简练,之后再通过石印的方式呈现在报纸杂志之上。
小山正太郎的诗意毛笔画囊括了中国文人画的四绝——诗、书、画、印。例如,画家的《咏剪刀》以明代李时勉的同名诗为主题,在画面左侧以行书抄录了全诗,落款是小山正太郎的号“先乐山庄主人”,并以墨笔仿出连珠印“山”“正”的效果(图13)。根据小山正太郎本人的解释,虽然他只在画中描绘了一把剪刀,但真正意图是替诗人表达对使用这把剪刀在闺房做女红的佳人的思慕之情。93[日]小山正太郎,《畫と詩》,载《太陽》1912年第18 卷第4 号,第162—165 页。值得注意的是,画家掺以西法,用毛笔成功地呈现了刀锋的明暗变化以及剪刀不同部分在质感上的差异。

图13 [日]小山正太郎,《咏剪刀》,载《太阳》1912年第18 卷,第164 页
1912年4月4日的《太平洋报》则刊登了陈师曾以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为主题的作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图14)。整幅画用笔用墨极为简洁,却充满诗意。远景中,陈师曾以寥寥数笔勾勒出诗中听雨的小楼以及环绕小楼的风景。画面由上、下、右侧三面边框环绕,左侧一支盛开的杏花似是要探出这个诗意的场景,客观上成了边框的一部分。卢宣妃指出,杏花的布局方式是陈师曾学习日本明治、大正以来报纸杂志上流行的插图样式的表现,其构想来源主要是日本画家从欧洲引入的新艺术[Art Nouveau]风格。94卢宣妃,《陈师曾〈北京风俗图〉中的日本启示》,载《美术史研究集刊》2010年第28 期,第 213 页。
为了解释小山正太郎发表诗意毛笔画的用意,他的《诗与画》一文于1912年2月1日率先刊登在《太阳》上。该文主要探讨了中国文人画领域中画与画上题诗的关系。95同注93,第159—160 页。作者在开篇即点出文本的主旨:起初文人以绘画自娱,后来题诗在文人之间盛行。若题诗与画相配,则能相辅相成,生出无限妙味;反之,若题诗流于形式,则对画有害无益。接下来,作者从正反两方面举出中国画史中诗配画的例子,借此说明合适的题诗使画活跃,将画与题诗放在一起看更生趣味;不解深意的学者、诗人等妄加题诗,反而使画深受题诗之害。例如题诗的字写得不好会大大影响画本身的地位;诗与画中所表现的内容相同时,虽然诗确实是好诗,但题在画上只是重复而已。诗可以表达无形的深意,画却难以表现时间等无形之物。以画表达场所、形、色等擅长的方面,再添上可以表达无形的诗,即补画之短,于是相辅相成,自然生出无限妙味。96同注93,第159—160 页。最后,小山正太郎阐明了撰写此文以及在《太阳》上发表诗意毛笔画的初衷:在以文学、美术为首,各方面逐渐发达的时代,绘画领域中各流派在不同方面大放光彩,作者期望此时能有善画、善题诗之人出现,使得题诗与画能相辅相成,成就更高的趣味,并且自愿作为此项倡议的前驱,继续在《太阳》上发表作品。97同注93,第159—160 页。
小山正太郎的第二篇文章《题跋与画》于同年3月开始在《太阳》上连载。这篇文章摘录了所有小山正太郎创作的诗意毛笔画作品上的题画诗。这些诗作均为中国古体诗,作者或为中国诗人,或为包括小山正太郎本人在内的日本汉诗诗人。98[日]小山正太郎,《畫と題辭》,载《太陽》1912年第18 卷第4 号,第159—160 页;第18卷第6号,第179—181页;第18卷第10号,第179—181 页;第18 卷第11 号,第185 页。《题跋与画》中摘录的诗作表明,截至1912年8月,小山正太郎至少创作了七十幅诗意毛笔画,然而最终只有不到二十幅发表在《太阳》上。99同注98。
考虑到小山正太郎作为明治至大正时期日本知名西画家和美术教育家的身份,以及他在明治中期(19世纪80年代)的“铅笔画与毛笔画之争”中积极倡导在普通图画教育中以铅笔画替代毛笔画的经历,他晚年发表在《太阳》上的诗意毛笔画和讨论文人画的文章便格外值得玩味了。小山正太郎绘画和书法中的笔墨稳重而流畅,反映了艺术家用笔的功底;他创作的古体诗也颇为可观。事实上,小山正太郎对于中国文人艺术的兴趣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的“汉学趣味”也已经广泛地被日本学者探讨。100同注48。据平木政次回忆,小山正太郎私下常常用毛笔作画,练习书法和作中文古体诗,且格外擅长南画的创作。101同注73,第103 页。平木政次还提到,某年11月去石川县进行写生之旅时,小山氏应邀为接待家庭画了一幅诗意毛笔画作为纪念。他还提醒平木,下次写生旅行之前要准备好纸、毛笔和一本中国古体诗诗集,以便于应酬作画时参考。102同注101。
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因小山正太郎和陈师曾不约而同关注中国文人画而值得玩味,但是二者关注的原因和方式却不尽相同。当小山正太郎在《太阳》上发表他的诗意毛笔画时,代表西化和现代化的明治时代即将结束。在此背景下,小山正太郎在《诗与画》中明确表示希望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重拾被遗忘的、曾经作为日本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学。103同注98。1912年的中国刚刚见证了帝制的倾覆和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仍处在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程中,西方近现代美术思潮和史论也开始被引进。104陈池瑜,《导读》,载陈师曾,《中国绘画史 文人画之价值》,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第10 页。文人画家如陈师曾,先后接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西方教育的熏陶,又正在经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因而能敏锐地察觉到在这个破旧立新之时,诸如传统文人画等所谓的“旧”,随时可能被“新”所取代。《南畫に就いて》(《关于南画》,1922)陈述的、关于“法古”和“生新”的辩证思想,早在陈师曾留学归国之后即体现在他的绘画创作中,而发表在《太平洋报》上的诗意漫画就是对该思想的有力阐释。在笔墨、画法和思想等方面,《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诗意漫画是对传统文人画的本真趣味的重现;简化用笔、掺以插画的装饰性风格以及经由大众媒体传播的手段是为了能找到一种重塑文人画在现代社会意义和价值的方法,以确保文人画在新时代的存续。对于普通大众而言,与报纸紧密结合的诗意漫画远比代表精英阶层的文人画更容易理解。
七 留学与陈师曾绘画史观的形成
1912年,时任通州师范学校博物教师的陈师曾在《通州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上发表了《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一文。105陈衡恪,《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载《通州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2年第2 期,第24—35 页。该文直译自日本洋画家久米桂一郎(1866—1934)刊发于前一年的《歐洲畫界最近の傾向》。106[日]久米桂一郞,《歐洲畫界最近の傾向》,载《教育学術界》1911年第24 卷第2 号,第456—474 页。久米桂一郎的绘画风格源于法国印象派的外光法[plein-air],自巴黎学成归来后于1896年与同学兼好友黑田清辉(1866—1924)共同策划了白马会(1896—1911),并于次年开始任教于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科。107[日]浦崎永錫,《第十三節 白馬会の結成》,载《日本近代美術発達史 明治篇 第9》,東京大潮会出版部, 1960年,第277 页。陈师曾很可能是通过好友李叔同了解到了久米桂一郎的绘画作品和思想。李叔同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期间,曾于1909年和1910年两度参加了白马会的展览。108陸偉榮,《李叔同の在日活動について》,载《日中藝術研究》2002年3月 ,第90—91页。
陈师曾的译文基本准确地表达出了原文的意思,略有几处误译或省略个别语句,正文部分没有加入译者的个人见解。此外,译者采用文言文形式进行翻译,在语言风格方面接近近代的日语表达。文章主体部分,久米桂一郎明确了法国作为19世纪欧洲绘画中心的崇高地位,梳理了法国从18世纪的洛可可到20世纪初的后印象派等流派在绘画理念、理论和技法方面的演变脉络,清晰地呈现了在19世纪科学性精神的影响下,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绘画由极端追求写实到注重画家为自然所刺激而表达出的情感的转变。109同注106。陈师曾翻译本文的动机则在附录中揭示:
西洋画界以法兰西为中心,东洋画界以吾国为巨擘,欧亚识者类有是言。东西画界,遥遥对峙,未可轩轾,系统殊异,取法不同,要唤起美感,涵养高尚之精神则一也。西洋画输入吾国者甚少,坊间所售,多属俗笔,美术真相,鲜得而观焉。日人久米氏有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一篇,今译之以介绍于吾国学界,藉以知其风尚之变迁。且彼土艺术日新月异,而吾国则沉滞不前,于此亦可以借鉴矣。110同注105,第35 页。
附录的聊聊数百言体现了陈师曾绘画史观的初步面貌:在客观认识东西方绘画的差异的基础上,肯定中国画在东亚美术界的重要地位,并承认中国绘画在进入20世纪之后停滞不前的不利局面;充分认识到西方绘画由古典写实到表达情感的变化趋向的进步性,并以此作为改变国画困境的重要参考。
由《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的翻译和评述开始,陈师曾的绘画史观的延续性在艺术家的代表作《文人画之价值》(1920)和《南畫に就い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11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载《中国绘画史 文人画之价值》,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第153—163 页;同注79,第127—135 页。陈池瑜指出,陈师曾关于中国画的思想和研究集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完成,“但却是厚积薄发,是其长期思考积累的结果”,“对中国画史有了一种深刻洞见和宏观把握”。值得注意的是,久米桂一郎在《欧洲画界最近之状况》中表达的若干观点对陈师曾为中国文人画的理论辩护有所助益。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文人画注重画家的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专任主观”),不刻意追求形似(“文人画不重客体”),与欧洲画坛由以写实为基础到画家的情感表达的转换趋势相一致,故中国文人画具有进步性和生命力,而不是衰败倒退的。112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第153—163 页。该主张有力地反击了由陈独秀(1879—1942)、康有为和徐悲鸿(1895—1953)等美术革命的领导人提出的中国画衰落、抨击文人画,以及采用西方古典写实方法对中国画进行改良的方案。113康有为,《万木草堂藏画目》(节选),载吴晓明编,《民国画论精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3年,第6—12 页;徐悲鸿,《中国画之改良》,载《绘学杂志》1920年第1 期,第12 页。
关于文人画中形似与思想情感表达孰重孰轻的问题,陈师曾以“照相”为参照来强调文人画的价值在于表达性灵和感想:
仅拘于形似,而形式之外,别无可取,则照相之类也。人之技能,又岂可与照相器具、药水并论邪?即以照相而论,虽专任物质,而其择物配景,亦犹由意匠寓乎其中,使有合乎绘画之理想与趣味,何况纯洁高尚之艺术,而以吾人之性灵、感想所发挥者邪?114同注112,第154 页。
陈师曾对于照相和照相技术的看法来源于久米桂一郎的《歐洲畫界最近の傾向》。久米桂一郎认为,照相术的进步是欧洲画坛发生由极端追求写实到注重画家情感表达的转变的动机。“最近技术的发展甚为显著,直追绘画,于是以写实为基础的绘画,其存在价值也变得薄弱了,因此人们对绘画的要求转向照片所不具备的价值。画家观察事物,将因事物刺激而产生的情调付诸画面,这其中的趣味是照相机这样无生命的机械所无法做到的。”115同注106, 第473 页。类似的观点陈师曾在《对于普通教授图画科的意见》中再次提道:“抛弃古人之笔法,而独从事于写生,工则工矣,其如非画何?此照片之所以无价值也。何则?仅有形似而无神韵故也。”116同注45,第12 页。
《南畫に就いて》重复了《文人画之价值》中对宋元明清文人画发展的梳理,提出研究文人画应着眼于从“法古”“生新”和“去俗”三方面。关于“法古”的观点已在本文第三节中加以论述。陈师曾在《南畫に就いて》中首次提出了对“生新”中“新”的看法:“新并不一定指欧洲西方的东西,支那(中国)风格也不一定为旧。谈及新旧,欧洲西方有自己的新旧,支那(中国)也有自己的新旧。以古为法,若不拘泥于此,则可创造出新的样式。”117同注79,第131—133 页。陈师曾关于“法古”和“生新”的辩证思想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主旨“精研古法、博采新知”相通。正是基于这样的主张,陈师曾在谈到对中国画未来发展的看法时,明确表示反对采用东西融合的方法来改良和复兴中国画。陈师曾指出,东西方艺术都有自己的体系、历史和传统,二者之间既有不同点,也有类似的点。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是否能融合、未来是否会融合的议题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陈师曾不主张东西方绘画必须融合,同时也不断言二者绝对不相容。118同注79,第131—132 页。“去俗”则又是对《文人画之价值》的延续。陈师曾认为“去俗”是人品、学问、胸襟的问题而非技术上的问题。“脱俗的画是一种高尚的文人画,是文人思想的表现。有言真而不妙,妙而不真。所谓妙指精神活跃,即使不似实物也能给人以感觉。真而不妙只是技术精巧别无深意,毫无文人画的价值;妙而不真即不求形似,这在文人画中往往可见。”119同注79,第133—134 页。
八 结论
从留学史的角度来看,在东京的留学对陈师曾而言是其西方美术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生成的阶段,为他之后的翻译、教学、画学研究、绘画实践乃至艺术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师曾在创作和史论研究中兼具了对中国绘画传统的尊重与坚持、对西方艺术的理解与包容,此种态度与他的留学,尤其是师从小山正太郎的经历密不可分。正如俞剑华在1928年发表的《国画通论》中所言,能胜任国画改革任务的艺术家应具备五要素:关于国画,艺术家需要对画论有深入的了解、掌握全面的画史知识并具备熟练的绘画技能;关于西画,艺术家同样需要在绘画史、理论和实践方面受过扎实良好的训练;此外,艺术家还应该具备勤奋的探究精神,敢于做出改变的勇气,以及对国画和西画兼收并蓄的态度。120俞剑华,《国画通论》,载《真美善》1928年第3 期,第1—23 页。陈师曾正是国画复兴的不二人选。对晚清到民国的中国美术界而言,以陈师曾为代表的留学生逐步推动了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
从当时的留学制度来看,陈师曾在东京的学习属于晚清留学的范畴,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例,中国留学生按照日本文部省和学校的规定,主要以“听讲生”即旁听生的身份进行学习,课程选择方面既可以像陈师曾一样主修博物学部的必修课,也可以跨学部修课。1912年之后,中国留学生才正式开始按部就班地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预科、本科甚至研究科。
从知识迁移史的层面来看,留学生在海外的学习生活是他们知识生成的原点,也是形成他们知识谱系的重要步骤。研究陈师曾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图画的经历有助于系统考察由英国到日本再到中国的图画知识的迁移情况,并理解陈师曾引进的图画知识如何与国画创作与研究相结合,从而成为中国本土现代美术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在东京留学期间接触的西方美术的相关影响渗透在陈师曾的翻译、教学、研究和创作的成果之中,这其中既有直接借鉴小山正太郎的图画教学方法、久米桂一郎的关于欧洲画坛新趋势的观点的“显性”研究,也有体现陈师曾兼收并蓄的艺术史观的“隐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