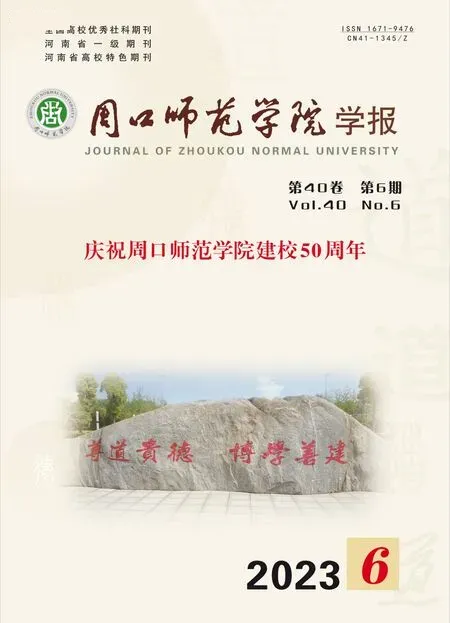从蔡邕的辞赋创作看汉魏文学的演进
袁亚铮,尹一航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030000)
汉魏之际是文学演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文学演进的趋势是:润色鸿业的作品消失,文人逐渐将目光转向现实生活;这一时期文人不再以帝王的喜好作为创作旨趣,其创作更多地体现了文人自身的趣味;这一时期经学衰微,其对文学的束缚也随之减弱,文人在作品中的情感描写更加大胆。目前,学界对于汉魏之际文学演进的这几大趋势已有不少讨论,但已有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勾勒其演进的趋势,鲜有从具体某个文学体裁的演进来探讨此问题。如以辞赋为例,汉魏之际辞赋的一大转变是由批判现实转向日常生活描写,这是汉魏之际辞赋演进的大趋势,而学界对辞赋演进这一趋势的探讨尚不充分,尤其是对辞赋演进的中间环节语焉不详,其实,在汉魏之际辞赋的演进中蔡邕是重要环节。但学界历来多侧重于其碑文研究,而忽视蔡邕在汉魏之际辞赋演进中的作用研究,基于此,本文以此为题目,以蔡邕的辞赋创作为视角管窥汉魏文学演进的问题。
一、蔡邕辞赋中女性的描写增多
东汉以前辞赋中涉及男女恋情的有宋玉的《高唐赋》和司马相如的《美人赋》。《高唐赋》描写人、神之恋却终未交接。《美人赋》对女性描写颇多,但赋中女性描写却是为了衬托男性的“不好色”。从以上两篇辞赋可以看出,东汉以前的辞赋虽偶有描写男女恋情,但相对较为遮掩,尚不能太明显、直露。东汉晚期随着经学的衰落,经学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减弱,人们开始正视一己之私欲,整个社会充斥着享乐之风,而这种放纵的风气最先是由上层统治阶层引起的。如桓帝时外戚梁冀穷奢极欲,史载:“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1]1182(《后汉书·梁统传》卷三十四)其时,不仅外戚骄奢,甚至帝王也耽于世俗的享乐。史载灵帝光和四年(181)“是岁帝作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帝著商估服,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帝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京师转相放效”[1]346。东汉晚期上层统治者骄纵享乐的风气很快流播各地,各个阶层皆纷纷效仿。
士大夫阶层的放纵享乐体现在文学中即为描写男女情感更为大胆。以蔡邕为例,蔡邕今存辞赋15篇,完整的有《述行赋》《青衣赋》《短人赋》和《释悔》4篇,蔡邕的辞赋虽然全篇不多,但描写婚恋的辞赋却不少,此类辞赋如《协和婚赋》《检逸赋》和《青衣赋》。《青衣赋》以侍女的容貌和心灵为描写对象,其辞云:“金生砂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纵横接发,叶如低葵。修长冉冉,硕人其颀。绮袖丹裳,蹑蹈丝扉。盘跚蹴蹀,坐起昂低。和畅善笑,动扬朱唇。都冶武媚,卓砾多姿。精慧小心,趋事若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2]573
本赋可以分为几层。开头“金生砂砾,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写侍女的出身,作者对其卑微的出身叹息不已;接着“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从各个角度描写婢女的美丽,作者笔下此婢不但美丽且灵动,赋中写其善笑“和畅善笑,动扬朱唇”宛在眼前;继而写其无双的才干“精慧小心,趋事若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总之,在作者笔下此婢女是“世之鲜希”“宜作夫人”。值得注意的是,赋中还写了主人公与此女的情愫“虽得嬿婉,舒写情怀”。最后写二人的思念之情。本赋是现存辞赋中首次以下层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辞赋,赋中主人公对婢女的才貌赞叹不已,对婢女的出身同情叹息,甚至与之产生了恋情,这在当时为礼法之士所不容,此赋一出就遭到批评,比如张超就撰写《诮青衣赋》讽刺本赋。
除《青衣赋》外,蔡邕描写女性的辞赋还有《检逸赋》,赋中主人公对该女子的爱慕,甚至到了魂牵梦绕的地步,其辞云:“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寫而无主,意徒倚而左倾。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思在口而为簧鸣,哀声独而不敢聆。”[2]596描写情爱如此大胆、直率,在以往的作品中甚为罕见。其篇虽不全,难以全面评价,但即使是残文亦能管窥其大略,正如有的学者所论“但从残文来看,他对爱情是写得比较大胆的,不惟‘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还‘思在口而为簧’,这是何等的刻骨!后来陶渊明的《闲情赋》即是仿效蔡邕此赋的”[3]。
再如,蔡邕的《协和婚赋》描写婚礼仪式,甚至于婚夜的全过程,笔致亦颇为大胆。赋中或赞美新娘的艳丽动人“丽女盛饰,晔如春华……其在近也,若神龙采鳞翼将举。其既远也,若披云缘汉见织女……面若明月,耀似朝日,色若莲葩,即如凝蜜”[2]589。或描写婚夜夫妇合欢“长枕横施,大被竟床;莞蒻和软,茵褥调良……粉黛弛落,发乱钗脱”[2]589。钱钟书先生评这几句云:“前此篇什见存者,刻划男女,所未涉笔也。……‘钗脱’景象,尤成后世绮艳诗词常套,兼以形容睡美人。”[4]本赋虽不甚有名,但它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本赋虽残缺不全,但由以上描写亦足以窥见作者在辞赋创作题材上的开掘上较少顾忌之一斑”[5]。
蔡邕对辞赋内容的开拓对后世影响很大,蔡邕之前辞赋中女性,或为神女,如宋玉《高唐赋》,或是想象中的绝色女性,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和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几乎不涉及现实中的女性。蔡邕《青衣赋》中的女性不但源自现实,还出身低微,其后,建安文人的《寡妇赋》《蔡伯喈女赋》系列,辞赋中所写的女子皆为普通女性,足见其受蔡邕辞赋的影响。汉魏之际蔡邕辞赋中的女性描写大增,究其原因,有学者认为,此点与儒家思想影响的削弱有关,如马积高先生云:“我在前面曾说这时儒家思想对赋的影响削弱了,蔡邕的赋就是例证。”[3]但脱离了儒家思想控制的文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色情意味的增加,马积高先生云:“不过,他(蔡邕)的《协和婚赋》又写得太放肆了,竟稍带有庸俗的色情趣味了。这在边让的《章华台赋》中也略有表现,可见不是孤立的现象。”[3]蔡邕辞赋创作中对男女恋情大胆、直接的描写,既是汉末士人世俗享乐的写照,同时也是汉魏之际辞赋创作新趋势的反映。此外,蔡邕辞赋中的女性描写对后世的美人赋题材影响深远,陶渊明的《闲情赋》就是模仿蔡邕的赋作而作,其《闲情赋》序云:“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6]此序中提到“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则可知蔡邕此类赋作在后世影响深远。
二、蔡邕辞赋中的文人趣味明显增强
文人趣味就是文人的闲情逸致,而“闲情逸致进入主流话语的前提条件是言说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获得相对的独立性,三者缺一不可”[7]。就政治而言,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期,君主集权得到加强,统治者对士大夫的控制亦较强。到了东汉中后期,政治昏暗,宦官专权,士大夫阶层在和宦官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群体自觉”意识,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次党锢之祸就是这种“群体自觉”意识演化的结果。就经济而言,光武帝刘秀能够建立东汉政权很大程度是因为有豪族的支持,这些豪族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其多拥有自己的庄园。就文化而言,东汉中后期经学自身的烦琐,再加上士大夫热衷于政治斗争,更加造成了经学的衰落。经学衰落之后,其对文化的控制逐渐松动,脱离经学的束缚后,辞赋、诗歌、书法等文艺样式迅速发展,呈现繁荣的景象。总之,东汉晚期的士人群体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而这几种因素是形成文人趣味的前提。
虽说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对文人趣味的形成皆有一定影响,但这其中政治因素尤其值得注意,东汉末年的政治因素对士大夫阶层注意力的转移有很大影响。面对东汉末年的政治黑暗,士大夫阶层一方面投入与宦官势力斗争的洪流中,另一方面,随着对政治的失望,其将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方面,加上东汉末年整个社会享乐风气的盛行,这些助长了其流连诗酒、游于艺术的风气。具体来说,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之祸”对士大夫的参政热情打击巨大,此后士大夫的精神旨趣分流为二:“一是潜心经学的,继续钻研学问,郑玄可为代表;二是游心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蔡邕堪为代表。稍后,士大夫开始突破经学藩篱,涉猎老庄,于是玄风渐炽,也正是在这期间,闲情逸致开始进入士大夫的言说范畴。”[7]
汉末文人中最富有文人趣味的当属蔡邕。蔡邕的辞赋很大部分都是描写日常生活的闲情逸致,如其《笔赋》《弹棋赋》《弹琴赋》等。古代文人多擅长琴、棋、书、画等技艺,蔡邕在其辞赋中也描写了这几种技艺,足见其身上浓厚的文人趣味。其《弹琴赋》云:“观彼椅桐,层山之陂。丹华炜炜,绿叶参差。甘露润其末,凉风扇其枝。鸾凤翔其颠,玄鹤巢其岐。考之诗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协之钟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2]581赋中作者描写琴材桐树的生长环境颇为讲究,所以,用此树制作的琴才能“通理治性”,表现了作者对古琴的制作非常考究。接着作者写道:“尔乃间关九弦,出入律吕,屈伸低昂,十指如雨。清声发兮五音举,韵宫商兮动徵羽,曲引兴兮繁弦抚。然后哀声既发,秘弄乃开。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2]581从作者对弹琴过程的细致描绘可以看出蔡邕对琴道的精通,而深谙琴道正是文人高雅趣味的体现。如果说歌咏琴、棋在辞赋中还比较常见的话,那么专门咏毛笔的辞赋则非常少见。蔡邕赋中对毛笔的歌咏源自其书法家的眼光,其云:“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慓悍,体遄迅以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丝之缠束。”[2]579赋中作者对制笔材料的选择极其精严,体现了文人对笔墨的重视;扇子亦是文人常用之物,蔡邕在《团扇赋》中描写团扇的轻便云:“轻彻妙好,其輶如羽。动角扬徵,清风逐暑。”[2]597辞赋中的雅趣其实是蔡邕日常生活的体现,蔡邕在《释悔》中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是“闲居翫古”[2]599,而在闲居中把玩琴、棋、书、扇这些文人常用之物,正是其文人趣味的体现。
蔡邕的文人趣味不但体现在其琴、棋、书、扇日常生活情趣中,也体现在由于自然外物的触动而引起内心情绪的变化上。正如李春青所指出的:“当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成为个人情趣的合法性表象形式时,当莫名的闲愁、思古的幽情、淡淡的惆怅、浓浓的思念以及‘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的感时伤怀成为诗文书画所表达的主要内容时,文人身份就被确证了,而文人趣味也就成为文学艺术的主导因素。”[8]蔡邕的文人趣味就多体现在自然外物的变化上。其描写秋蝉生命的逝去云:“白露凄其夜降,秋风肃以晨兴,声澌咽以沮败,体枯燥而冰凝。”[2]586(《蝉赋》)此赋前两句写秋日的清晨,选取了露水、秋风两种意象,再经“白”和“凄”的点染,使得赋在一开始就带上了浓浓的感伤氛围。接下来写寒蝉,把蝉在秋天即将死去的具体现象,上升到自然规律的高度加以审视,暗示生命的起始和结束带有必然性,是期运之所然。全赋以写景始,借蝉况人,曲折地表达了生逢末世文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曹道衡先生评价此赋云:“寥寥数句,但颇有抒情意味,语气虽较凄凉,但无悲观的情调。”[9]蔡邕善于抚琴,但琴声总能触动其伤感的情绪,从其《弹琴赋》“一弹三欷,凄有余哀”[2]581就能看出。不唯秋蝉的澌咽,琴声的触动,连晚秋的阴雨连绵亦足以引起蔡邕的伤感,其云:“夫何季秋之淫雨兮,既弥日而成霖。瞻玄云之晻晻兮,听长霤之淋淋。中宵夜而叹息,起饰带而抚琴。”[2]595(《霖雨赋》)文人是敏感的,蔡氏祠堂前的栗树遭人攀折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能引起其感伤。栗树无故遭到摧残让蔡邕想起了其生逢乱世,命若蝼蚁,顿生身世之感,其辞云:“形猗猗以艳茂兮,似碧玉之清明。何根茎之丰美兮,将蕃炽以悠长。适祸贼之灾人兮,嗟夭折以摧伤。”[2]584(《伤故栗赋》)生活中看到瞽师,蔡邕亦会以己度人,为其遭遇而悲叹,其辞云:“何矇眛之瞽兮,心穷忽以郁伊,目冥冥而无睹兮,嗟求烦以愁悲。抚长笛以摅愤兮,气轰锽而横飞。咏新诗之悲歌兮,舒滞积而宣郁。何此声之悲痛兮,怆然泪以憯恻,类离鹍之孤鸣,似札妇之哭泣。”[2]593(《瞽师赋》)此段描写深沉悲痛,作者对瞽师遭遇的同情充溢在字里行间。总之,蔡邕辞赋所表现的文人趣味,正如龚克昌先生云:“汉赋发展到蔡邕手里,已完全从描写帝王的皇宫帝苑中走出来,进入了一般封建文人的生活领域。它的表现范围大大扩展了。”[10]
总之,从蔡邕所咏的琴、棋、笔、蝉等赋可以看出,蔡邕的赋作多描写日常生活,其创作体现了文人辞赋题材的转移,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题材颇为广泛,由京殿苑猎的圈子脱出,而迈向自我的日常生活的见闻感受……”[5]108总之,蔡邕辞赋中对文人日常生活的描写说明汉末文人将注意力转到自身上来,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文人觉醒的体现。
三、蔡邕赋中呈现出“聊以游意”新的文学观念
东汉晚期经学的式微导致了其对文艺控制的松动,加上桓帝、灵帝尚奇好异,京城贵戚皆争相效仿,史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灵帝于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于是公卿贵戚转相放效,至乘辎軿以为骑从,互相侵夺,贾与马齐。”[1]3272东汉中后期,在整个社会尚奇娱乐风气的引导下,辞赋、书法、绘画等文艺形式的发展势如破竹,其具体表现为鸿都门学的兴起上。
鸿都门学的设置是东汉晚期文坛的大事,但鸿都门学从一开始就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史书云:“光和元年(178),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1]1998关于鸿都门生的生源,李贤注云:“时其中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1]341鸿都门生学成后,灵帝下令“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1]1998。灵帝下令选用鸿都门生任职一事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反对,光和元年(178),有虹蜺昼降于嘉德殿前,灵帝召杨赐及蔡邕等入金商门,问以祥异祸福所在,杨赐对曰:“《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又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如驩兜、共工更相荐说,旬月之间,并各拔擢,乐松处常伯,任芝居纳言……殆哉之危,莫过于今。”[1]1780时阳球拜尚书令,奏罢鸿都门学,其曰:“案松、览等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俛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1]2499
由上述所引材料可看出,杨赐和阳球皆对鸿都门学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杨赐认为,鸿都“群小”以“虫篆小技”“并各拔擢”,阻碍了以经术为业的士大夫的仕进之路,遂强烈要求灵帝“斥远佞巧之臣,速征鹤鸣之士”[1]1780。阳球甚至以出身低微为由指责鸿都门生不是靠真才实学而是“依凭世戚,附托权豪”进入仕途,于是阳球以忧伤“圣化”为名,希望“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总之,以杨赐、阳球为代表的士大夫因为鸿都门生挑战了儒生的地位,挤占了儒生阶层的政治空间而强烈反对,也反对以鸿都门学为代表的辞赋的崛起。
当时灾异频发,蔡邕上书言事亦言及鸿都门学,史书云:“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1]1996-1997蔡邕的上书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鸿都门学以书画辞赋取士破坏了正常的选举制度,应当停止;其二,书画辞赋虽为“小道小能”尚能“聊以游意”,如“当代博弈”一样亦有其自身的价值,不过,君子却不能志于此。蔡邕认为,应该区别对待经学和辞赋,治国匡政首选经学,但辞赋亦可以供人欣赏和娱乐,它们的功能不同,作用也不同,蔡邕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书画、辞赋的价值。
蔡邕的辞赋观对魏晋文人影响很大。在魏晋士人心中,儒家经典的地位很高,它关乎治国理民,而以辞赋为代表的文学则更多的是士大夫参政之余的一种娱乐消遣。蔡邕的辞赋观看似降低了文学的地位,“但比起班固、王充等人强调赋颂‘润色鸿业’、‘褒颂记载’的功能,蔡邕的文学观具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把文学从政治和经学中剥离出来”[11]。蔡邕认为,辞赋、书画,虽不能匡国理政,但可以娱乐遣兴,在“听政余日”可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其言外之意,士大夫在公事之余,应有自己的娱乐消遣生活,而辞赋正是这种娱心遣兴的产物。这里蔡邕强调辞赋的娱乐性,而对于长期以来盛行的辞赋的“讽谏”作用不予理会,反映了其辞赋观念的新变,而这种观念对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蔡邕的一些赋作即可视为是其娱心遣兴生活的体现。如蔡邕最看重的是其史学家、经学家的身份,但除此之外,蔡邕对于特殊人群亦怀着好奇的态度,比如他对侏儒和女性这两类人,就颇怀好奇的心理,这表现了蔡邕对于此前士大夫阶层所不屑的特殊群体有所关注,因而将其写入赋中,聊以游戏。如蔡邕的《短人赋》,其描写侏儒云:“雄荆鸡兮鹜鷿鹈,鹘鸠鶵兮鹑鷃雌。冠戴胜兮啄木儿,观短人兮形若斯。热地蝗兮芦即且,茧中蛹兮蚕蠕须。视短人兮形若斯。木门阃兮梁上柱……脱椎枘兮擣衣杵,视短人兮形如许。”[2]576赋中蔡邕将侏儒比喻为蠕动的蚕蛹,令人捧腹。清代的浦铣评价此赋云:“蔡中郎《短人赋》,亦俳谐体也。”[2]928可见蔡邕此赋无讽刺侏儒之意,而是将侏儒群体作为奇异之人来欣赏,从中得到奇趣,蔡邕此赋毫无严肃的意图,其目的即为娱乐,即“聊以游意”。再比如,其《检逸赋》云:“夫何姝妖之媛女,颜炜烨而含荣。普天壤其无俪,旷千载而特生。余心悦于淑丽,爱独结而未并,情罔寫而无主,意徒倚而左倾。”[2]596描写主人公对美女的爱慕,亦属于游戏之作。此类的赋作还有很多,如《笔赋》《弹琴赋》《弹棋赋》大抵可以视为其“聊以游意”之作。
总之,蔡邕认为儒家经典关乎治国理民,其地位不能动摇。然而辞赋的作用也不能完全忽视,辞赋可以作为士人参政之余的一种娱乐消遣,即蔡邕所说的“聊以游意”。汉魏之际的文人正是在这种“聊以游意”观念的指引下,才将创作视角转向女性和外物,并因此创作了较多歌咏女性和外物的辞赋,显示了汉末辞赋题材的新变。
综上,蔡邕作为汉末文坛领袖,不但在辞赋的创作上成就斐然,而且还引领了汉魏之际文学发展的趋势。汉魏之际是社会大混乱时期,同时亦是文人逐渐走向觉醒的时期,此一时期的文人需要直面社会的动荡,需要驰骋一己的兴趣爱好,需要在短暂的生命中追求享受和不朽,所以文学亦需要直面社会和人生,而这一趋势在蔡邕的辞赋中已有所体现。儒学控制力减弱,带来了文学的解放,此前文学中罕见的女性甚至是情欲描写,在蔡邕的赋作中已较为常见,尤其是其将对女性的体态美、服饰美、才德美的描写放置在日常生活中,开启了魏晋南北朝美人诗赋一类。因为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不同于一些政治家怀抱改变现实的理想,亦不同于潜心学问的经学家,以蔡邕为代表的部分文人开始沉浸于琴、棋、书、画的日常生活,并在辞赋中描写自己的情趣,抒发自己的闲情逸致,使文人趣味、闲情逸致开始进入士大夫的言说范畴,开启后来文学中的闲情书写,在后世形成了独特的文人士大夫的审美传统。最后蔡邕已不再将学问仕途作为人生的唯一追求,其希冀在学术之外、公事之余可以将生命寄托于书法、辞赋和音乐中,可以“聊以游意”,这种超越现实的闲静,引领着后世文人士大夫追求更为高雅的审美人生。在引领文人从专注经学到经学、文学双修,从此前侧重追求政治高度转向追求审美人生,从此前文学在经学的束缚下畏首畏尾,到文学可以直面人性、抒发真情,可以说在汉魏之际文学转型的潮流中,蔡邕是关键人物。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