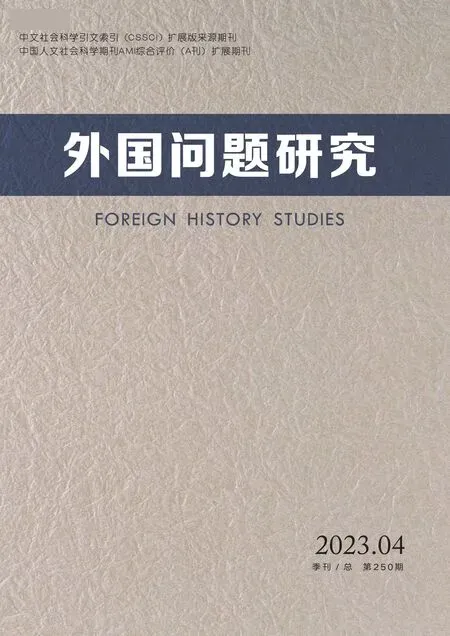大正时期铃木文治工会思想的演变
陈安楠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工会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作为当前日本工会组织源头的友爱会,其创建者铃木文治的工会思想在大正民主运动时期呈现出明显的“低—高—低”走向:由大正初期尽量避免与政府产生矛盾的生产协调主义,中经1919年前后围绕团结权的取得与政府形成对立,再到大正后期向“现实化”即保守化的转向。目前国内学界关于战前日本工会的研究多集中在片山潜等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工会,对铃木文治及其创建的友爱会着墨不多。(1)刘国瑞:《片山潜与近代日本工人运动》,《黄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伊文成:《日本近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挫折浅析》,《外国问题研究》1985年第1期;伊文成:《略论日本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日本学界从劳动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等角度(2)塩田庄兵衛:「戦前わが国の労働組合:総同盟の分裂、評議会の創立をめぐって」、『社会政策学会年報』第5巻、1957年;松尾尊兊:『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6年;三谷太一郎:「大正社会主義者の『政治観』——『政治の否定』から『政治の対抗』へ」、『年報政治学』第19巻、1968年;隅谷三喜男:『日本労働運動史』、東京:有信堂、1966年;池田信:『日本社会政策思想史論』、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1978年;吉田千代:『評伝 鈴木文治』、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1988年;金子良事:「1920年富士瓦斯紡績押上工場争議の分析——『団結権』獲得を巡る攻防の光と影」、『経営史学』2007年第3期。,关注铃木文治在友爱会建立前后的基督教思想或社会政策思想特征,但对其思想演变关注不足。鉴于此,本文以《友爱新报》《劳动及产业》和神户大学经济经营研究所新闻剪报数据库(3)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http://www.lib.kobe-u.ac.jp/sinbun。等报纸杂志史料,梳理铃木文治的思想特征及其演变脉络,为认识大正时期日本工会运动及社会运动的思想演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铃木文治工会思想的提出和展开
1885年,铃木文治出生于日本宫城县栗原郡金成村,从事酿酒业的铃木家在19世纪末迅速衰落,全家为挽救家业而投身宗教寻求精神寄托,铃木文治也在十岁那年加入了附近的正教会。(4)中村勝範研究会文集委員会編:『鈴木文治研究ノート きずな別冊』、東京:慶応義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中村勝範研究会、1966年、第6頁。在他考入山口高等学校后,结识了当时著名的基督教活动家本间俊平。本间所践行的是将宗教精神与社会事业相结合的一种“实践性宗教”,他的理念对铃木文治的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铃木晚年也在自传中坦陈:“这段年轻时的经历,让我无法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5)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東京:一元社、1931年、第20頁。除此以外,进入大学后的铃木文治也醉心于东京大学教授桑田熊藏开设的社会政策学课程。所谓社会政策学,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学说,桑田理论的重点在于“经济和道德的调和”,其基本构想可以分为国家、慈善、个人三个层面。从国家的层面而言,“对贫民弱者的保护就是高尚的道德”(6)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184頁。,强调立法保障弱者利益;从慈善方面而言,强调的是一套类似于“经营家族主义”的劳资协调体系;从个人的层面而言,赞同劳动者组建团体,但“劳动者组成团体来谋求各种各样的便宜必须以道德为前提”。(7)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192頁。奉行“实践性宗教”的铃木文治和桑田熊藏的理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促使铃木文治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中。
自1911年11月开始,铃木文治在统一基督教会的会馆惟一馆内陆续组织了人事商谈所、通俗演讲会和劳动者俱乐部这三项常驻活动,最终于1912年8月1日夜,铃木文治和15名劳动者同志,在惟一馆正式宣告友爱会的成立。友爱会最初的纲领规定了它是一个修养救济团体,并未展示出同日本政府和资本主义体制的对抗性,且在会则中展示了对知识分子以及开明派官僚的欢迎态度。铃木在自传中称:“在幸德秋水事件的两年后,想要组建这样的组织实在是过于困难。暂时就先满足于一个友谊、共济和研究团体吧。”(8)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54頁。实际上,这并非只是由于对日本官宪压力的避让,更多的还是因为铃木以基督教平等观和社会政策学思想为基础形成的一套关于工会的理论体系,其重点在于“生产主义调和论”和“劳动者人格论”。在这两种思想的指导下,早期的友爱会也只能是“修养救济”团体。
“生产主义调和论”语出隅谷三喜男。隅谷认为铃木文治的“调和论”和1890年代片山潜所提倡的“调和论”有部分的相似,不过片山的理论强调分配,铃木的理论则侧重生产。根据“生产主义调和论”,铃木文治将劳动者的素质和其社会地位、企业生产效率以及社会发展挂钩。首先他认为劳动者素质水平的低下导致了其社会地位的低下:“如今日本的工人人数已经上了百万大关,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却还是智识品性比较低下的群众。‘职工’这个名词听起来卑贱的原因不正是如此吗?”(9)鈴木文治:「五五一九論」、『友愛新報』第5号、1913年、第1頁。其次,他认为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也会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加总体受益:“假如劳动者的素质只有1分的话,劳动时长和资本投入就要凑够剩下的9分;但如果劳动者的素质有9分的话,那么劳动者与资本家的投入只需要1分就能达到结果。”(10)鈴木文治:「五五一九論」、『友愛新報』第5号、1913年、第1頁。在对国家和社会的认识上,铃木文治毫无疑问是 “社会有机体论”的支持者,认为“社会是人的集合,人就类似于社会的细胞”。(11)鈴木文治:「社会有機体論」、『友愛新報』第8号、1913年、第1頁。因此,劳动者素质的低下必然导致日本社会发展的缓慢,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必然会带来日本国家水平的提升。
正是因此,铃木文治极其重视友爱会在提升工人素质方面的作用。在机关志中,关于法律、卫生等与劳动者权益息息相关的科普文章几乎每期都有选登,试图缓慢而切实地开拓日本劳动者的眼界,提升他们的素质。除了在机关志上的潜移默化,铃木文治更希望劳动者们能够与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近距离接触,以此来提升劳动者的思想水平。在成功举办第一次通俗演讲会后,铃木文治如此展望道:“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演讲会,让劳动者创办自己的组织,让学问上的贵族(学者)和贫民(劳动者)之间能握手共进。”(12)一記者(鈴木文治):「第一回労働者講話会」、『六合雑誌』第32巻第2号、1912年、第102頁。友爱会改组为总同盟后,于1920年建立了东京劳动讲习所,以学校的形式更进一步地为劳动者提供知识及素质提升的场所。除此以外,1917年在野坂铁(参三)的提议下,建立了以研究劳动运动和促进工人与学生之间交流为目的的劳学会,铃木文治也参与了其中。
“劳动者人格论”是铃木文治的另一个主要思想。它是铃木文治在社会舆论的夹缝中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做出的尝试,其最根本的依据是“劳动者是人子,资本家也是人子”(13)鈴木文治:「資本と労働の調和」、『友愛新報』第2号、1912年、第1頁。这样的基督教平等观。他提出:“今日是四民平等的时代,不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都只是工作上的分工,在人格上他们其实是平等的。”(14)鈴木文治:『日本の労働問題』、東京:海外植民学校出版部、1919年、第50頁。针对不同的社会层面,铃木文治也有不同的看法。在企业层面而言,铃木文治将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看作对劳动者人格的尊重,他向当时的中小企业主们提出质疑:“各位难道就做到了一个资本家该做的一切了吗?工厂的设备如何?救护的设施如何?养老保障如何?”(15)鈴木文治:「五五一九論」、『友愛新報』第5号、1913年、第1頁。对于国家层面而言,铃木文治认为颁行并完善《工厂法》就是对劳动者人格最大的尊重,并认为《工厂法》 的“制定和实施都如此艰难(指制定后推迟5年施行),可以说原本的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16)鈴木文治:「労働者の立場より工場法を評す」、『労働及産業』第58号、1916年、第3頁。对此,铃木文治运用法学专业知识,对《工厂法》进行逐条分析和批判。尤其是对于夜间劳动和童工相关的法条(17)“有以下各种情况的不适用于前一条(指完全禁止未成年和妇女进行夜间劳动):因为有临时的理由需要进行加班的;必须要彻夜生产的某些特产业;有理由需要昼夜连续工作并配备两组以上工人进行轮换作业的。”参见鈴木文治:『工場法釈義』、東京:友愛会本部、1916年、第30頁。,认为“这根本不是对幼者弱者的保护,不如说这是将虐待通过法律的形式给予承认”(18)鈴木文治:『工場法釈義』、第32頁。, “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不得不承认本法律完全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来制定和实施的”。(19)鈴木文治:「労働者の立場より工場法を評す」、『労働及産業』第58号、1916年、第3頁。对劳动者提供人权保障并非仅停留在思想层面,自友爱会建立之初,就陆续设置了法务部、救济部、职业介绍部等部门,为劳动者们提供法律咨询、职业介绍以及友爱会员内部的社会保险等,在企业和日本政府都无法或不愿给予关注的领域,尽可能地为劳动者提供帮助。
“生产主义调和论”和“劳动者人格论”构成了铃木文治早期工会思想的两大支柱。其中“劳动者人格论”提出了给予劳动者最低限度的保障是什么,是为“救济”;而“生产主义调和论”则提出了劳动者们想要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该怎么做,是为“修养”。然而这二者内部蕴含的协调倾向还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生产主义调和论”,铃木文治在尝试将劳动者素质与企业、社会和国家紧密相连时,在实质上就蕴含着对日本天皇制国家体系的服从:“只要能够让每一个劳动者都变得比以前更好的话,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也能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20)鈴木文治:「社会有機体論」、『友愛新報』第8号、1913年、第1頁。“劳动者人格论”也同样,在呼吁加强对劳动者保护的同时,并未对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主导地位提出任何挑战或质疑,更进一步地,还试图向资本家们“推销”这种对“人格”的尊重将转化为劳动者的回报: “请先尊重我们的人格吧,那样的话我们心中自然会涌现士为知己者死那样的感情。”(21)鈴木文治:「労働者より資本家へ」、『友愛新報』第28号、1914年、第1頁。这样的协调主义倾向的形成诚然有“大逆事件”的影响,但铃木文治本人的思想知识构成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此,在此后大正时代社会思想的旋涡中,铃木文治虽然也呈现出激进的一面,但协调主义倾向却仍旧存在。
二、民本思想下围绕团结权而激进化
在以“生产主义调和论”和“劳动者人格论”为骨架的铃木文治的工会思想的指导下,友爱会自1912年建立开始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至1916年10月,友爱会员总数已达21 892人。(22)「友愛会会員数統計(大正五年十月)」、『労働及産業』第64号、1916年、第37頁。尽管铃木文治为缓解美国排日情绪两次渡美,在日本官方处取得了一定的信任,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让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友爱会等工人组织的态度。作为渡美介绍人的涩泽荣一也向铃木文治警告道:“群众通过多数人的暴力不讲道理地强行实现自己意志和富人或者权贵暗地里使用手段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两种行为的罪恶不分轻重。”(23)平澤計七:「五周年記念大会の記」、『労働及産業』第69号、1917年、第17頁。而对于政府和资本家关于“煽动罢工”的指责,铃木文治予以否认,并称:“现在的劳动者认为自己和资本家是对等关系,但资本家却并不尊重劳动者的自由意志,而是依然将他们看作奴隶一样,实行专制支配,这是专制思想和立宪思想的冲突”(24)鈴木文治:「如何にして罷工を減すべきか」、『大阪毎日新聞』1917年2月22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2-084)。,是“基于民本主义的政治运动给予了劳动者强烈的刺激”。(25)「同盟罷業の新傾向—労働者の自覚と社会の一転期—その予防と解決 鈴木友愛会長は語る」、『読売新聞』1917年8月28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2-109)。然而铃木文治并不赞同这样激烈的手段,尤其是斗争的结果往往不利于工人。他不得不不断重申“我们主张资本和劳动力的调和,而非反抗和背离”(26)鈴木文治:「資本家諸士に告ぐ」、『労働及産業』第70号、1917年、第2頁。的劳资协调立场。在1918年初甚至向全体成员发布“谨慎行动”的布告:“无须多言本会的宗旨并非将劳动者团结起来以对资本家造成破坏,而始终是通过调和与合作,用合理的手段谋求劳动者地位的改善。”(27)鈴木文治:「会員諸君に告ぐ」、『労働及産業』第78号、1918年、第21頁。
不过这样的退缩和遮掩随着“米骚动”的展开而消失。铃木文治在自传中热烈地歌颂“米骚动”的意义:“(米骚动)向民众传达了名为‘力量’的福音,给予了劳动阶级‘当多数人团结起来天下就没有无法完成之事’这样的自信。也就是说米骚动一扫劳动者们的自卑心,给予了他们强烈的自信和自尊。”(28)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164頁。虽然从数据上看“米骚动”后日本的工人运动数量有所下滑,但劳动者之间的团结度却是先前不曾拥有的。而在“米骚动”期间,跨工厂甚至跨地域的罢工潮,让铃木以及日本的劳动者们认识到了团结的伟力,友爱会也逐渐承担起了将工人们团结起来的责任,于1919年改组为大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这样的局面并不是日本政府希望看到的,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其表现就是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代表问题以及劳资协调会的设立。
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设立源自巴黎和会。早在1916年铃木就向美国工会的负责人提出,想要出席战后举办的万国劳动者会议(29)鈴木文治:『日本の労働問題』、第226頁。,1918年铃木文治也以非正式成员的身份随使节团前往巴黎。巴黎和会上确立了国际劳动九原则,并决议组建国际劳工组织。这让铃木认识到:“日本的劳动运动已不再是小岛国的劳动运动了,而是世界劳动运动。”(30)「巴里の国際労働会議から帰った鈴木氏の報告演説」、『大阪毎日新聞』1919年8月4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国際労働問題(1-106)。然而日本政府对此次会议的消极态度让铃木文治深感失望,他尖锐地批判道: “在整个世界都像白昼一样的时候,日本却酣睡于极东之地,这完全是回到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将日本隔绝于世界之外”(31)鈴木文治:「労働運動と国際関係」、『労働及産業』第89号、1919年、第3頁。;“如果全世界都像条约所说的那样进步的话,日本就会被孤立起来。日本政府是对世界大势盲目了吗?”(32)「巴里の国際労働会議から帰った鈴木氏の報告演説」、『大阪毎日新聞』1919年8月4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国際労働問題(1-106)。
归国后,围绕着下半年即将召开的国际劳动代表人选问题,铃木文治和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由于友爱会的巨大体量和铃木文治本人的威望,日本社会大多认为铃木文治会将劳动者代表的名额收入囊中。但日本政府却以“日本没有工会组织”(33)「労働会議に出席する労働者の代表、内務省は官選の方針;労働者は選挙を主張」、『河北新報』1919年5月11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国際労働問題(1-048)。这样的理由,试图钦定代表。此举遭到以友爱会为首的各劳动团体的反对后,又尝试通过扩大官营工厂投票权的方式来操纵代表选举。以至于在最后的会议上,铃木文治因“不屑于出席这种无法选举真正代表劳动者意志的人的会议”(34)「嵐の如き怒号と攻撃の矢と 農商務省の労働協議会第一日」、『大阪毎日新聞』1919年9月16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国際労働問題(2-090)。愤而退席。年底国际劳动会议正式召开时,铃木文治委托美国劳动同盟会会长龚帕斯(Samuel Gompers 1850—1924)向会议组委会提交了关于日本政府操纵劳动者代表选举的提案。这让铃木成了日本政客和御用文人争相攻击的目标,认为他是“将国辱暴露给外国”的“非爱国者”,铃木文治反驳道,“只有如同此次批判政府错误行为那样,在大会上展示日本劳动者的声音,才能增加劳动者乃至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35)吉田千代:『評伝 鈴木文治』、第196頁。,并提出世界劳动运动的使命就是“打破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等一切少数专制制度,谋求民本主义的确立”。(36)鈴木文治:「官僚主義か民本主義か」、『労働及産業』第99号、1919年、第3—4頁。
除了直接对铃木文治本人进行打压以外,日本政府也在尝试削弱友爱会的影响力。在政府的授意下,以涩泽荣一为组织者,创办了“资本劳动问题协调会”,简称“协调会”。目标是“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中间严守中立,设立的本意一方面在于当资本家有不当态度时给予社会制裁,另一方面也谋求劳动者精神上的提升,在劳动者们轻举妄动的时候至少促进双方的互相理解”。(37)「同盟罷業を解決の為に生れ出ん協調会:資本家と労働者の談合 発起人渋沢男の談」、『東京日日新聞』1919年7月24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8-023)为保证其顺利成立,涩泽荣一曾邀请铃木文治加入,作为交换他将在国际劳动代表选出问题上为铃木发声。但铃木文治果断地表示了拒绝,并针对协调会撰文,指出所谓的协调必须使参与协调的双方实力对等,他认为“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单独的劳动者不过是孤立无援的弱者,而没有获得永久团结权的劳动者是无法保卫自己已有的生活的”。(38)鈴木文治:「労働協調会を評す」、『労働及産業』第97号、1919年、第3頁。然而协调会的资金来源存疑,并且和内务省警保局有着密切的联系,更不支持工人们行使自己的团结权,实际上是“(日本政府)通过温情主义、救济主义组建的用来取代其他工会作用的组织”。(39)鈴木文治: 「労働協調会を評す」、『労働及産業』第97号、1919年、第8頁。
这一系列的事件都表明,铃木文治及友爱会和日本政府之间围绕着团结权的对立已经越发尖锐。为表示对政府保守主义的不满,1920年,友爱会以“‘大’字带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为由,改称“日本劳动总同盟友爱会”,显示自己对日本政界的反抗心;同年机关志就由《劳动及产业》改名为《劳动》,以示不再将日本的产业发展凌驾于劳动运动之上。同时摒弃了曾经宣扬过的“温情主义”,认为“在现代的工业制度下,雇主和雇员根本没有相互熟悉培养感情的时间,虽然(温情主义)不至于完全没有效果,但绝对是被过分夸大了”。(40)鈴木文治:「労働問題の将来」、『国民新聞』1920年4月19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14-124)。同时“温情主义”一词往往带有强者对弱者的怜悯意味,“温情主义”的采用就代表着资本家和劳动者力量的不平衡,这和追求团结权的确立是背道而驰的。
但实际上,铃木文治及友爱会态度上的转变并不彻底。围绕着团结权友爱会与日本政府形成的对立,实质上是日本自上而下的专制行政体系与自下而上自发组建的民主团体之间的对立,在思想上而言就是“专制主义与立宪思想”的冲突。换言之,此时的铃木文治并非反对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反对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封建性,也正是因此,围绕团结权问题,铃木文治与日本政府形成的尖锐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当后续大正民主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冲击下日本政府逐渐承认工人的团结权,甚至更进一步打算给予劳动者选举权的时候,铃木文治及友爱会的态度又将回归保守,重新在日本资本主义体制内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三、“无布论争”中的铃木文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大正时期政治风气的开放,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迎来又一个新的高峰。1921年神户川崎·三菱大争议失败后,让日本的工人运动愈发激进化,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日本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无政府工团主义在路线上否定已有的工会组织通过议会或者其他途径谋求劳动条件改善等行动,认为这属于“改良主义”,主张通过怠工或者总罢工,一举完成社会革命。(41)隅谷三喜男:『日本の社会思想―近代化とキリスト教―』、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第120頁。
铃木文治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此时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在团结权问题上围绕着铃木与友爱会,与日本政府进行斗争。因此当他得知一些青年人在总同盟内部宣扬这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时候并不以为意,而是抱着“平常日本料理吃多了偶尔尝尝法国菜也不错”(42)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285頁。的乐观心态。在政治方面,铃木作为坚定的普选支持者,却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否认工会组织更进一步地参与议会政治。他认为日本的议会只是“煽动性的政治家以当选为目的,并非真正地关心劳动者的福祉……最终不过是陷入同有产阶级的妥协”。他同时反对将工人团体政党化,他认为劳动运动当以产业运动为主,政治运动为辅,提出政治运动“应仅限于劳动团体或和劳动团体利益相关时,对政府或议会采取政治行动,绝非直接将工人团体政治化”。(43)鈴木文治:「議会と労働者」、『国民新聞』1920年8月1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問題(15-034)。总同盟内部以麻生久和棚桥小虎为代表的反普选派,逐渐胜过了以贺川丰彦为代表的普选派,在1920年后,总同盟内部关于普选运动的热度骤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铃木文治的工会思想之间的矛盾不断暴露。
从斗争目的上而言,铃木文治自建立友爱会以来,一直将劳动条件的改善作为其工会活动的主要目的;而从斗争手段而言,铃木文治对于怠工或罢工的态度始终是比较谨慎的,并且倾向于通过工人运动将资本家逼迫到谈判环节来解决劳动争议。这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所主张的目的与手段几乎完全相悖。这些理念上的矛盾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铃木文治等知识分子领导者的排斥运动。他们对铃木文治等知识分子领导层“懦弱”的斗争手段表示强烈不满,称“劳动者一直是惨败的一方,那些称惨败为胜利、钝化劳动者的阶级意识的人是谁?由量变到质变逐渐让劳动者拒绝阶级斗争的是谁?图谋自己地位和生活安定的又是谁?”(44)隅谷三喜男:『日本労働運動史』、第122頁。批评铃木文治等人“自认为是指导者,而非劳动者的伙伴,他们的心底只有自己的利益和名誉”。(45)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編:『日本労働年鑑(大正拾壹年)』、東京:同人社書店、1922年、第40頁。大杉荣也站出来赞成这样的说法,他认为“知识分子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理想强加给还未形成独立理想的劳动者而已”。(46)大杉栄:『正義を求める心:大杉栄論集』、東京:アルス、1921年、第238頁。1921年爆发的足尾铜矿劳动争议,在总同盟的代表麻生久与日本政府代表萱场军藏的调解下,以劳资双方均做出让步告终。但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看来,这种调解是不可接受的,“劳动组合主义就是在和这样的制度(指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笔者注)妥协”。(47)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編:『日本労働年鑑(大正拾壹年)』、第38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在包括总同盟在内的日本各工会组织的内部,掀起了一场排斥知识分子领导者的运动。总同盟中,即便如麻生久、棚桥小虎等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领导者,也被迫离开总同盟,铃木文治则辞任会长,只保留了名誉会长的头衔。
在工会组织形式上,铃木文治延续了自1919年来的一贯主张,坚持“少数人的英雄主义行为无法带来胜利,必须要由能够和资本主义体制对抗的工会组织”(48)隅谷三喜男:『日本の社会思想―近代化とキリスト教―』、第120頁。的方针,一直在尝试将日本各工会团结起来,组建一个强大的横跨企业、地域、产业的日本总工会。与之相对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倡导“自由联合论”,认为“在强调各组合的相对的独立与自由的同时,也强调各组合内个人的独立与自由”(49)大杉栄:「労働運動の理想主義の現実主義」、『大杉栄集』、第394頁,转引自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241页。,并组建了数个工会联合组织与总同盟相抗衡。在对抗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被总同盟引为盟友。以自英国归国的原总同盟干部野坂参三为代表,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与劳动运动的联系不断深化。这些倡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者们同样支持建立统一且强大的工会组织,双方在对抗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联合论”上逐渐取得一致,合作程度也不断加深。1921年日本政府取缔日本共产党之时,警察甚至以怀疑收取某国(苏俄)宣传资金为由,对铃木文治以下的各友爱会干部都进行了传讯调查。(50)「労働総同盟幹部 厳重な取調」、『東京朝日新聞』1921年10月8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労働者保護(3-059)。
总同盟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矛盾在1922年9月举办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大会上彻底爆发。会上总同盟系工会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在警察的干涉下解散了此次会议。此后不久举办的大正十一年总同盟大会上,总同盟进一步强化了与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决裂的意志,称“我等认为东京、大阪等地的劳动组合同盟和他们理论上存在共鸣的诸工会所赞同的自由组合论会导致劳动者阶级战斗力的分散,无法与本总同盟主张的战斗力集中原则相容;本次大会旨在表明本同盟坚守战斗力集中原则,因此在以上的诸工会和我等主张上达成一致之前,不会再参与总联合的交涉”。(51)古賀進:『最近日本の労働運動』、東京:聚芳閣、1924年、第88頁。此后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总同盟内部的影响逐渐减弱,1923年大杉荣在关东大地震中被宪兵队虐杀,更是让日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走向衰落。
在“无布论争”中,铃木文治的工会思想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存在诸多矛盾,这些矛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实际的劳动运动中展现了出来,并带给总同盟极大的打击,也让日本的工人运动陷入各工会之间的内耗之中。最终,铃木文治及总同盟选择了同样赞同建立集中体制工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作为盟友。但这次合作并不意味着铃木文治认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念,思想上的矛盾仍旧存在。然而此时铃木文治因此前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知识分子排斥运动的影响而辞任会长,实际上并无掌控总同盟的权力,因此共产主义在总同盟内部得到了广泛传播,为铃木文治重新掌管总同盟后工会的两次分裂埋下了伏笔。
四、“现实主义”策略与总同盟的分裂
1920年代初期愈演愈烈的社会运动让日本政府感到了一定的压力,尤其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挑战。而震后日本政府对社会运动释放出的缓和态度却又给铃木文治以新的希望。灾后不久,在铃木文治的带领下,总同盟便设立了罹灾救援委员会并广泛开展救灾工作,展现了工会组织的力量,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正视。更进一步的,为缓解灾后愈发紧张的社会氛围,一部分进步的官僚和资本家承认了工会组织的存在,认为“工会组织即使没有完备的工会法也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同时宣布“国际劳动会议代表的选定,应当遵循(巴黎)和平条约的条款,尊重各工会组织的推荐”(52)上井喜彦:「第一次大戦後の労働政策——一九二六年労資関係法をめぐって」、『社会政策学会年報』1979年第23巻。,在实质上承认了总同盟在日本劳动界的地位,也承认了日本劳动者的团结权,自1917年以来铃木文治与日本政府对立的根本矛盾就此消失。再加上普选运动的逐步推进,以及总同盟庞大的会员基数所代表的其在政治化后的巨大潜力,让铃木文治看到了通过融入日本议会体制,进一步推动工人运动的希望。
在地震后总同盟内部的人事震荡中,铃木文治得以名誉会长的身份重新掌握实际权力,开始逐步淡化共产主义的影响。铃木文治将1920年代初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对工人运动中知识分子领导层的批评扩大化,认为先前日本的劳动运动已经完全不是在为劳动者的切身利益而斗争,而是为了让自身信奉的理论得到实现而斗争(53)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28頁。,以此来减弱组织中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各理论派的影响。关东大地震的惨状更是让他坚信日本工人运动必须“行动胜于言辞、实践胜于议论、现实胜于理想”。(54)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44頁。因此铃木文治根据当时日本政府和资本家的妥协情况,认为劳动者没有必要进行绝望的抗争,某种程度上利用资本家和政府也是贤明的斗争方式。(55)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27頁。于是铃木文治结合山川均的“方向转换”,在总同盟大正十三年年度大会上发表了总同盟自己的“方向转换”宣言,根据日本政府的妥协态度、普选运动的进度等,认为“现在已经到达了我国工会运动由少数人的运动向大众运动转变的时机,必须一改之前对改良主义的消极态度,转而积极地利用它”。在手段方面,提出通过推动普选和工人团体的政治化,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框架下推动工会的发展,即:“我们自然毫不期待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实现劳动阶级的解放,然而可以通过在普选实施后有效地行使选举权来获得政治上部分的利益、促进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觉醒、又或者在国际劳动会议上慎重考虑对策,来谋划我国工会组织的发展。”(56)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22頁。
但是此时总同盟内部的思想并未统一,以共产主义者和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代表的左派,与以铃木文治“现实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右派并存。1924年起,双方的矛盾就不断加深,至1925年,围绕日本政府修订《治安维持法》一事,该矛盾被彻底激化。左派以“该法律是对劳动运动的压迫”为由,举行了激烈的抗议运动;而右派则希望能够通过选举完成对法律的修改。(57)隅谷三喜男:『日本労働運動史』、第128頁。最终当年的总同盟年度大会上,左派疯狂地攻击赤松克麿领导的总同盟政治部(以推动普选为主要活动内容),彻底扰乱会场秩序;右派则在会后要求将山本悬藏、渡边政之辅、杉浦启一、辻井民之助、中村义明和锅山贞亲这六位共产党员自总同盟中除名。至5月16日,总同盟将左派的数个工会开除,这些被开除的工会迅即便于24日自行组建了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这也就是总同盟的第一次分裂。
对于此次分裂,评议会一方认为总同盟的领导们“不给会员以公开讨论交流意见的机会,只是以一小部分最高干部的意见为标准(典型的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要求会员服从”。(58)協調會大阪支所:『最近労働組合運動史:協調會大阪支所創設五週年記念』、大阪:協調會大阪支所、1927年、第96頁。称呼总同盟中的少数领导者为“劳动运动官僚”或者“堕落干部”,提出要纠正总同盟中的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与此相对的,总同盟方面则认为评议会的干部们在先前“同时隶属于日本共产党又参加总同盟,在总同盟内部建立小团体来谋求更高的地位”。铃木文治更是毫不留情地将这次分裂定义为“革命的梦游病人,或者说披着革命理论外衣却对权力贪得无厌的家伙们进行的扰乱活动”。(59)松沢弘陽:『日本社会主義の思想』、東京:筑摩書房、1973年、第247頁。虽然铃本的言论在尽力淡化此次分裂中双方的理念分歧,试图将评议会等人认定为争夺权力的野心家,但实际上铃木文治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他的“现实主义”与左派的革命理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在此后的无产政党运动中也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分裂后的总同盟似乎完成了思想上的纯化,日本政府也于1925年5月公布了《改正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现实主义”倡导的议会手段终于集齐了最后一块拼图。法案公布后不久,铃木文治就旗帜鲜明地反对评议会等左派团体提出的建立全国单一无产政党的提案,认为“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也存在着明确的对立”。(60)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61頁。因此,虽然1925年8月总同盟便参加了日本农民组合主导的第一届无产政党组织委员会,但最终以“此次农民劳动党的建党,借建党之名,行我团体无法容忍之共产主义之企图”(61)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67頁。的理由退出。次年3月在排除了评议会的影响后,总同盟与其他六个右派劳动团体合作,建立了劳动农民党。然而又因对于是否接纳评议会等非右派无产团体仍旧存在争议,总同盟又于10月退出该党。
接连两次组党失败的铃木文治,选择与安部矶雄、吉野作造、堀江归一等人合作,于1926年11月4日发布了关于组建新政党的声明书,决定于12月5日组建社会民众党。但在11月23日,时任总同盟政治部长的麻生久突然发表了建立新政党的声明,并于12月9日建立日本劳农党。总同盟不得已对麻生久及相关人员进行了除名处分,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关东合同劳动组合和关东纺织劳动组合近7000名会员退出总同盟,造成了总同盟的第二次分裂。
对于总同盟的第二次分裂,铃木文治认为既有思想上的因素也有组织上的因素。从思想上而言,铃木认为麻生久等人自共产主义传入后就深受影响,不论是第一次分裂还是在后续的无产政党运动中,都对评议会等左派无产团体抱有一定的好感。而从组织上而言,麻生久领导下的矿工工会自加入总同盟之日起就地位超然,麻生久在总同盟内部也像是一个“外样大名”。(62)鈴木文治:「総同盟の分裂と社会民衆党の結成(一)」、『時事新報』1926年12月8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議会政党および選挙(29-184)。因此铃木并不像第一次分裂面对评议会时那样抱有强烈的反感,在铃木文治看来,日本的工人没有政治活动的经验,在一次普选的实际操作都没有经历过的时候,日本的无产政党却开始党同伐异,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糟糕。(63)鈴木文治:「総同盟の分裂と社会民衆党の結成(四)」、『時事新報』1926年12月11日、神戸大学経済経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議会政党および選挙(29-184)。所以对于这一次的分裂,铃木文治抱有的更多是遗憾:“无产运动的前途本就漫长,我无疑坚信着还有与诸君共同提携进步的时候,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遗憾。”(64)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71頁。
综上可以看出,铃木文治选择“现实主义”并走向保守化,既是对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总同盟“左”倾化的反拨,也是日本政府承认工人团结权并推动普选运动的必然结果。在铃木文治看来,“我国的资本主义并未经由自由主义阶段,而是直接军国主义化且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对无产阶级的自由运动多有压制”(65)隅谷三喜男:『日本労働運動史』、第128頁。,因此他否认通过工会运动进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反而主张采用“现实”的议会手段是更为合理的诉求。并且铃木文治虽然认为“资本主义终将消亡”,但他似乎更加看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极意义的论述,即“资本主义有着重大的弊害,但是不能忘了它最重要的优点,即将生产过程组织化、集中化、统一化来达到提升产业效率”。(66)鈴木文治:「労働問題と其の運動」、『講演No.1』、東京:東京講演会、1926年、第30頁。此外关东大地震时大杉荣被宪兵队虐杀致死,铃木文治的好友,曾经友爱会的重要领导者平泽计七也被龟户警察局批捕杀害,这一系列的惨案也让铃木文治感叹“若是他们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话,就不至于落入如此悲惨的境地了吧”。(67)鈴木文治:『労働運動二十年』、第344頁。这种日本政府高压下的无奈,或许也是促使铃木转向“现实主义”,推动普选和无产政党组建的原因之一。
余 论
大正时期铃木文治的工会思想清晰地呈现出由协调到激进,再由激进到保守的变化曲线。协调是因铃木文治在自己信奉的宗教以及接受的社会政策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生产主义调和论”和“劳动者人格论”为代表的协调主义思想,在大正前期指导友爱会的活动;激进则是在大正民主的风潮中,接受了民本主义等政治思想的影响,并将其移植到工会运动的理论中,在大正中期围绕工人的团结权与日本政府形成对立;保守则是在大正中后期,确保了工人的团结权后,以普选和组建无产政党为目标,执行议会路线的“现实主义”政策。最终在1925年与铃木一同建党的人物里,安部矶雄是统一基督教会的领袖,铃木文治正是在该教会的会馆内建立的友爱会;吉野作造是民本思想的倡导者,也是铃木文治在东京大学的同乡前辈;堀江归一是著名的经济学者,也是友爱会最初建立时便施以援手的评议员之一。经历了十数年劳动运动的风雨后,铃木文治似乎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最终通过组建无产政党的形式,将工人运动与工会组织融入了战前日本的国家体制中。
铃木文治的工会思想与其他在大正民主时期大放异彩的社会主义思想相比,的确显得保守而又暗淡,乍一看似乎就如大杉荣所言:“铃木文治无法算是理论家。”(68)大杉栄:『正義を求める心:大杉栄論集』、第287頁。但铃木文治工会思想的转变过程,恰恰反映了日本大部分的工人运动与工会组织,在大正时期由协调到对抗,直至最终自发性地融入日本国家体制的过程。即使脱离大正这段时间来看,铃木文治的工会思想也对战后日本工会组织施加着持续性的影响。尤其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工会斗争的总体路线,由“政治斗争主义”和“经济斗争主义”,转变为强调制度内行动的“企业工会主义”和“政治的交换”。(69)程多闻:《工会路线变动与战后日本劳资关系转型》,《日本研究》2017年第2期。这一转变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倾向,无疑可以看作是战前铃木文治工会思想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