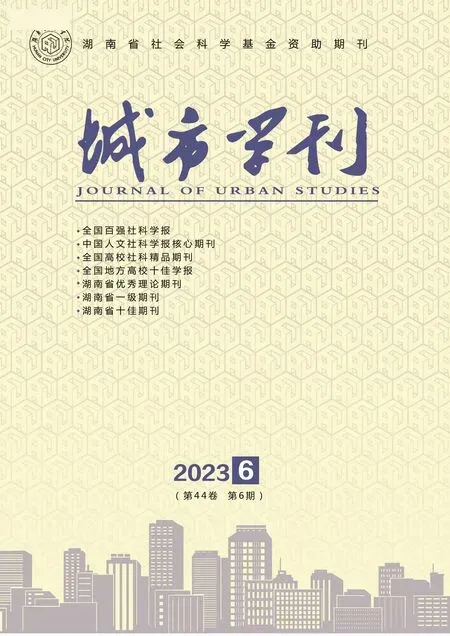空间诗学视阈下打工诗人身份的自我追寻与确认
——以郑小琼诗歌为例
吴 晗,伍 丹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06)
恩斯特·卡西尔曾言:“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1]空间作为人们感知世界的基本维度之一,并不是一种被动的,空洞的存在形式。人与空间处于不断地互动之中,人以空间来容纳生命的激情,其自身也被空间赋予意义,人们在对于空间的感知中寻求身份的认同。从这种意义上讲,空间场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显在或潜在的影响,所有的文学都是空间的文学,作家赋予空间“特质与奇想”,而自身也通过各类社会空间及其结构的表述,获得确认自我身份的力量。
空间的存在奠定人生存的意义,空间的转移重塑着人的感知,人们在原空间所生成的身份认知被涂抹,不得不于新空间中再次确定自身的意义。随着中国市场化、资本化的程度加深,许多农民放弃了家乡的土地,到城市开启了打工生涯,打工诗歌应运而生。打工者的地理空间发生位移,社会关系由此重组,语言、文化等精神层面的连接也随之断裂,这种断裂直接导致了打工诗人自我身份的迷失,正如已故打工诗人许立志于诗歌《担忧》中所记载:“我在担忧什么,一张暂住证还是一个/明天早晨的馒头/在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我被昏暗的灯光呛到咳嗽不止”,[2]离散的冲击、地区的差异、贫富的差距、空间的游离使得打工诗人如“暂住证”般四处飘零。以怎样的视角书写空间,或是构建出怎样的空间形成诗人的身份认同,是打工诗人创作的必由之路,也正是支撑打工诗人写作的动力之一。在打工诗人代表郑小琼的空间诗学中,我们能够寻找到打工诗人寻求自我认知所作的努力,从而见证其诗歌主体精神的形成。
一、纠缠:与城市的对抗
“亿万打工者驮着生活的火车/修建通往新世纪的康庄大道。”[2]12城市空间的形成是中国现代社会形成的标志之一,为解决“跨域”后的身份迷失问题,打工诗人企图与城市进行亲密的交互,实现自身在城市中“扎根”的身份诉求,这使得打工者的身份被城市边缘同化,陷入了自我与空间的无限纠缠。
都市包罗万象,千变万化,如同迷宫充满魔力。打工者怀抱着对于城市的憧憬来到城市,现代城市空间景观的喧闹与繁忙带给其视觉与心理极大的冲击,或是为了对抗离乡所带来的孤独症候,或是出于生活的必需,或是对美好未来的展望,初至城市的打工群体与同时代的人们一样,试图去亲近城市空间的中心,迫使自己对城市空间产生归属感,从而在人与城市空间的互动中建立亲密关系,“将我的梦想/释放在上海这个天堂之上”。[3]20 岁的郑小琼同样怀揣着对现代文明的憧憬,跳上南下的火车,期待着在异乡扎根,“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4]诗人极力与空间进行互动,在本具客观性的空间中安放充满热情的主观情绪,将“自我”与都市同构,从而使得都市空间转化为自我的隐喻,成为自我诠释与自我定义的关键因素。可见,打工者在城市空间中极力发现与构建“我”的身份认同与身份理想。
但打工诗人诗歌中所展露的迷恋,遭到了城市冰冷的回绝。都市的空间分配体现并制约着人的社会关系,使打工者“扎根于异乡”的幻想失落。除了极少数打工白领外,绝大部分打工者并非生活在城市的核心区域,他们活动的场域是城市的边缘空间:打工诗人许立志居住在一栋握手楼的五楼,张守刚在中山市一个叫坦洲的小镇打工十年,曾在五金电镀厂打工的谢湘南,生活环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城市边缘即使与“核心区”具有联系,也只是承载着城市因功能分区所产生的碎片。
为了确认身份,打工者对城市空间进行体验与阐述,但人又会成为空间所定义的客体,乃至被空间所同化。城市边缘混乱拥挤,逼仄驳杂,人与物的空间关系被翻转,物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绝对化”,打工者既无法触碰到城市的中心,无法与社会定义的成功保持一致,又被城市空间挤压与规训,人被迫“居住”在既定的、封闭的世界中。黄麻岭这个位于珠三角的南方小镇,在郑小琼笔下形成了城市边缘空间,“惨淡的白炽灯的车间,它的空洞、乏味/白围墙与黑铁丝网围住疲惫的五金厂”,五金厂被“白围墙”与“黑铁丝”所包围,更加接近于一个幽闭空间,打工者与空间中的物能够赤裸直观地进行交互,在这种交互中,打工者已成为被物禁闭的存在:
在黄麻岭,万物是易朽的,我在听雨
在机台上腐朽,不安的自动滑杆推动
……
薄薄的工卡、薪水、不眠的加班
在仓库的拐角处,纱布与伤痛的手指[4]146
在这样的密闭空间中,打工者的生活被以物为主的工厂劳动所绑架,个性被淹没,活泼的意识被流水线桎梏,工厂空间将每个人都改造成服务于物的附属品。厂区超快的节奏与机械式的重复,使得打工者脱离既定的时间,眼中只存在单调的效率与加班,万物易朽,时间生锈,伤痛只能安放于仓库的拐角,打工者已经沦落为物的一部分,是机台的某个螺丝钉,甚至是“一处锈迹”。
打工者身份疲惫,无处遁逃,被城市中的物束缚同化,或许是每个打工诗人“亲近”城市后的命运,物占据了都市中主要的凸显位置,人被人造之物所奴役,成为“物的延伸”,如徐非《在城市啃麦当劳》所言:“我被迫进入城市的胃/自己就是一根瘦瘦的薯条/只不过穿着一件肥肥的西装”,[5]打工者一头栽进城市,灵魂随着跌宕的生活一同摇晃,昼夜由白炽灯控制,温度由空调控制,速度由交通工具控制,农民工自觉或不自觉成为“物”的延伸,人的五感变得迟钝,甚至消失。“但是走进这边的工厂时,面对形成系统的社会程序组织,他们是那样弱小,他们正被一种看不见的系统异化,坚硬的个体面对组织系统时只有无力与屈服感。”[5]21
斑马线。红灯。工厂。写字楼。证券交易。海关大厦。咖啡因。红头文件。经理人。法律。地铁。躁动的人海。假证件。香口胶。安全套。烟蒂。救护车……飞机场。迪斯高。栎木吧台。商业沙龙。HI 族。电视新闻。[4]92
诗人的目光如同城市街道的监视器,将完整的城市分割为零散的状构,再将碎片以无序的形式拼接。诗人跳出城市的高楼大厦,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待城市的全貌,从而展现都市空间的欲望与孤独。郑小琼不仅关照着由农村来到城市的打工者,更关注着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所有个体。诗人无奈地发现,整个城市已呈现出异化的生存状态,独属于电子元件的冰冷、独属于混凝土的冷漠已取代了肉体的鲜活,整座城市充满着繁华的假象,电视新闻中的主流话语因经济进步而激动不已,而个体却变成城市的零件,生命活力由此消散。诗人将所涉及的“物”与“人”用冰冷的句号隔开,时间被压缩,只留下充满着距离感的“都市人”。这样的都市空间竟如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所演绎的名场面:羊群涌入围栏,工人涌入工厂,轴承以夸张的速度转动,工人无法休息。主人公夏尔洛被机械式的忙碌工作逼疯,一见到圆形的东西,忍不住用扳子纠正。但城市仍呈现着三分小资、二分时尚、一分慵懒情调,试图抹去灯红酒绿下的血肉辛酸。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
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
奔波,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
灯光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
慢地移动[4]65
人的价值,同样被工业时代计算商品价格的方式所定义。“我”首先被视为工具,而在经历了多年损耗后成了“次品”,遭到来自同时代人的嘲弄与市场的“减价”处理。“我”的遭遇并非个案,郑小琼诗中的城市不会对因“机械劳动”而损耗躯体的人做出任何保障,他们只会无条件地索取“人”的青春。在城市边缘,诗人将个体的“认知”疼痛诉诸于外,身体的伤痛、身份的迷失、精神的焦虑使得城市的“边缘人”被无边的苦难所绑架。
诗人之所以敏锐,是因其不会无意识地被城市空间所同化,郑小琼的诗歌始终伴随着诗人的“亲眼见证”与“切肤之痛”,“我”无法融入城市,在厂房中难以寻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台前身心的耗损,这更加深了诗人对于苦难的认知。劳动者试图亲近城市,却因劳动的异化丢掉自身,本不丰腴的生命在日复一日的机械操作中愈发贫乏。“虚弱加浓职业病,荒凉的咳嗽/给无味的生活带来血迹、尘肺/我的影子消融于白炽灯的寒冷中”(《穿越星宿的针孔》)。在打工者与城市空间的纠缠中,城市空间毫无疑问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工厂制度消磨了打工者的身体与灵魂,无休止的工业对于个人的“暴力”被掩盖于现代机制的话语体系中。而为力证自我仍存在,维持自己的精神平衡,诗人只能利用“感知”的力量,走向“原乡”。
二、对抗:“镜中”原乡的构建与失落
为了对抗城市边缘空间对人的异化,打工者选择突破人的感知经验,唤醒人的主宰地位,构建以人为中心的“原乡”空间,但在“原乡”的背后,存在着打工诗人无法安顿自我的巨大焦虑。
在城市边缘空间中,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被制造成了一模一样的机器,留下的只能是“功能”价值,而并非是对身份的指认。为了弥合物与“我”的巨大缝隙,使作为主体的人从空间的“绑架”中解脱,打工诗人不得不借用“唯心”的外壳还魂,极力纠正城市中“物”与“人”的颠倒地位。将“人”与“物”融入自我的“同一”中,走向以“人”为中心的“原乡”是打工诗人必然的选择。
空间的移动带来自我的分裂,打工者在城市与乡村两个空间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从离开故土的那一刻起,打工者往往开始进行着记忆中乡村的重构。帕蒂古丽在《隐秘的村庄》中提到:“离开故土后,身份意识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离开得越久越是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想要通过记忆来确认自己生命的位置。身份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恐怕只有那些有共同体会的人才能够回答。”[6]当打工诗人在城市空间中漂泊,在身份认同过程中面临挫折时,乡村记忆的意义由此凸显,如同张守刚的《农田》:“我又看见农田了/在列车上/像浪一层层涌进/我长途跋涉的眼里/真想伸出手去抚摸它们”,[7]或是王小妮的《11 月里的割稻人》:“一个省又一个省草木黄了/一个省又一个省/谁来欣赏这古老的魔术/割稻人正把一粒金子剥成一颗白米”。[8]为抵抗城市空间“物”的侵袭,打工诗人记忆中的乡村空间充满精神的慰藉,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走向了毫无苦痛的“原乡”。
在刻画阴冷、孤独的城市空间时,郑小琼毫无遮掩地追忆着记忆中的乡村,在《触摸》中,诗人写道:
在窗口,晨雾间的笑语,朦胧中鸟鸣嘹亮
拐角处的槐树,它们悬起串串槐花
……
那瓦蓝的天空还停留着奇异而奢侈的童年
它纯净而明亮的气味被我的回忆触摸
在《一些,另一些》中也是如此:
童年的月光、草垛,一些午夜的犬吠
梦幻般辽阔的往事,沿着一缕秋日的阳光
弯了下来,垂临在我的回忆上
诗人站在窗边,视线延伸至拐角的槐树、天空,最后穿梭回屋内,指向近距离的“纯净而明亮的气味”。第二首诗中诗人随着回忆向外远眺,月光、草垛,甚至远处的犬吠,往事沿着那一缕似乎可触的阳光,垂临在诗人的脑海中。诗中的空间构建,如同本雅明的阳台理论:“街道成了游手好闲者的居所。咖啡店的阶梯是他工作之余向家里俯视的阳台。”[9]观察者位于阳台之上,视线延伸至外部的空间,他自己又置身于自我空间之内。零散的意象形成了诗人记忆中的村庄,这些意象由远及近,即使隔着“窗”的距离,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小,在诗人所想象的乡村中,内与外,公与私,远与近没有任何阻碍地连接在一起。本雅明所述的空间,不仅是人类生活的社会空间,更是其形成身份认同、体现其心灵认识的精神空间。而郑小琼等一系列打工诗人笔下的乡村皆如此,故乡被美化,乡村成为田园,具有城市所不具备的宁静与纯洁,成为某种乌托邦,这样的乡村异于打工者所生活的故乡,是更贴近祖先所生活的“原乡”。
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打工诗人通过构建原乡的方式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郑小琼在《故乡》中写道:
记忆中燕子剪开四月的细雨
万物的生与死,痛苦与欢乐都那样平静
……
凋零的花与睡眠的人,珍藏着一颗颗善良
的心
在古老而缓慢的节气里用爱,用明亮的词语
度这岁月,倦怠的生活,有罪的灵魂
“原乡”依天而设,靠地而居,田野与空间具有无尽的延展性,若是想要搭建居所,单靠人类自身便可完成。在郑小琼所打造的“原乡”愿景中,节气“古老”而“缓慢”,空间不再由机械化的流水线、封闭的厂房所决定,而是由时间绵延形成,“原乡”成为诗人游荡的场域,诗人不再被物所束缚。反之,“原乡”之中万物皆备于人,人再度成为万物的主宰,生活皆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都市空间中,人被物挤压、限制,但在“原乡”,人的穿梭不仅超越物理空间的纬度,也模糊了自我与外界的边界,与万物形成了精神的同一。人是“原乡”空间的主角,在城市失落的打工者,似乎于“原乡”中寻找到了存在的意义。
王德威在《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中认为,现实中的家园从来不同于回忆中的样子,因此乡愁不那么重要,“想象的乡愁”才是重点所在。[10]乡土作家从描写“失去”中得到了写作的理由,因此乡愁是“缺席的因”,很多的写作都是“奉乡愁之名”。在作家的意识中,这种“想象的乡愁”已构成一个象喻空间,它涵盖了人类祖先往昔岁月的生活经历,这种具有深度情感体验的原始意象刻入了人的心灵结构中。从古至今,中国人对乡土具有特殊的亲近感,作家们也在“原乡”空间中寻找着生命的意义,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意识与无意识这一系列看似对立的概念都被注入了新的可能性。沈从文在“原乡”空间中书写湘西边民健康的人性与理想的生命状态,张承志通过回归大地在“天人合一”中进行精神漫游。部分作家甚至塑造“反向的移动”:席慕蓉以“原乡”为坐标,以内蒙古文化为根基,唤醒自我的民族记忆,重新锚定自我身份,这些少数民族作家重归“原乡”,在象喻空间中展开对本民族文化的寻根之旅,从而寻求到主体身份自觉的契机。
以想象的方式重构乡土,塑造出“原乡”这样的“第三空间”,是打工诗人确立自身意义的方式,打工诗人将人生与信仰的全部意义投入“希腊小庙”中。但郑小琼所重构的“原乡”空间也许是易破碎的“镜中之物”,诗人与亲人同居,作家的精神靠乡土的血缘支撑,打工者在“原乡”空间的身份维系仍是由他人或是他物共同完成。身份认同的核心的问题通常被视为人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在“原乡”空间中,诗人因血缘寻找到了自身的意义:他们是谁的子女、谁的父亲或是母亲、谁的兄弟姐妹。但自我认同作为内在化与内在深度感的体现,需要人生阅历的积攒,需要蓬勃生命力的爆发,单靠童年的模糊印象,诗人如何能够深度地“认识我自己”?又如何能够实现自身意义的彻底觉醒?
“原乡”看起来是能够使打工诗人“诗意栖居”的一角,但乡愁是美好理想与真实境况之间巨大落差的产物,以黑格尔“哀怨意识”解释“原乡”所产生的原因是:“欲望和劳动所指向的现实性,对这个意识来说,已不复是一个本身虚无的东西,对它只消加以扬弃和消灭就行,而是一个象意识本身一样的东西,一个分裂为二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只在一方面是本身虚无的,而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神圣的世界。”[11]少数民族作家重返“原乡”空间,是因感悟到了民族的召唤,他们追寻着大地之母的呼唤,将充满民族精神的“原乡”视为生活与写作的精神之泉。但打工者之所以要进行空间转移,是因为他们故乡的经济难以发展,真正的童年无法承载自然的记忆,城市的肯德基、麦当劳、口红与短裙吸引着年轻人,而“乡村逐渐成戈壁,剩下弯曲的霜”。当城市的闯入者受挫后,对于乡土世界的认可情绪才浮出潜意识,打工者需要塑造“原乡”形象对城市进行抵抗,但对于“原乡”,他们并未注入某种文化与精神的自觉,他们在离乡之前,便自行将根切断了。
如镜般的“原乡”空间濒临破碎,郑小琼的返乡之旅直接造成了乡村愿景的失落,2004 至2007 年,郑小琼屡次返乡并创作了《变异的乡村》《玫瑰庄园》《黄斛村记忆》等一系列关于真实故乡的长诗,同时坦言:“其实我一直想说,在血汗工厂背后有一个更血汗的农村,而现实中,我们传统写作者都将这个更血汗的农村美化,包括打工者一些怀乡诗歌……农民工的精神却是荒芜的,无援,更脆弱的。”[12]回到乡村的诗人并没有减轻心理的迷失感,反而被迫承担了文明侵袭的疼痛:
喝多农药的土地间残剩的桑枝
瘦小孱弱支不起斑鸠们的巢
它们叫着在浑浊的江水中
破旧的街道与河滩上新修的龙王庙
对岸倒闭的丝绸厂它阔大的阴影
这片低矮的事物令人胆寒的虚幻[13]
——《在龙门》
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家屋”等空间意象进行了原型分析,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载物容器,更是人类身份与意识的栖息之所,[14]郑小琼的《在龙门》中,桑枝无法筑起斑鸠们的巢,街道变破旧,土地被侵蚀,这些意象所唤起的心理感受,始终与诗人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城市的入侵没有带来文明,反而是阴影与胆寒。即使在郑小琼的想象中,城市被构建成了喧哗、浮躁的异质空间,但“原乡”同样不是诗人们的“乌托邦”,迁徙者与“原乡”似乎相亲相爱,但仍存在着精神隔膜,这一切使得郑小琼对于以往心心念念的“原乡”空间产生了异质感,“原乡”与故乡的失落,再度与诗人身份的认同形成了同构关系,打工者的身份走向迷失。于是在《雨水》中,作者见那“衰老的天空/面目全非,衰竭的云朵步履艰辛”,决定“将返回我的命运,在祖居的庄园间/我用诗句来道别亲人告别。”[13]87
三、正视:创造生命“构境”
无论打工诗人如何去贴近城市,其仍处于城市的底层,陷入了人与物的纠葛。当打工诗人希望依靠重构乡村愿景而达到诗意的栖居,原乡空间虚无缥缈,现实中的乡村荒芜没落,缺少精神的根基。如此尴尬的身份不但使打工诗人成为城市与乡村的局外人,更使其成为迷失身份的“自我分裂者”,在重重压力之下纷纷“失语”,一部分打工诗人走向迷失,回避诗歌的精神价值,空洞地书写着城市的苦难,如学者景立鹏所言:“遗憾的是,关于工人诗歌的中国语境往往被诗人们个人苦难的倾诉和对工业理性的批判所淹没,这造成工人诗歌在反思与批判个人处境及历史真相时遭到新的蒙蔽。”[15]若打工诗人无法挣脱出城与乡的空间限制,打工诗歌也将会落入陈旧的观念窠臼。
在这种情境下,作为异乡者的打工诗人就必须正视“在城市中生存”的命题,打工者的身份是否能从城市中脱离,在生命的交互中走向与他者相适应的和谐“同构”,这便是郑小琼等人所需要思考的,如何去寻求生命“构境”。
情境主义国际创始人居伊·德波提出了“构境”概念,创作主体根据自己的真实愿望重新设置、创造人的生命存在过程,人类基于自身的潜在想象而构建出的意向空间,将人嵌入社会,从而在诗意层面实现人的价值。[16]在城市挣扎生存的郑小琼,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与折磨后,开始拒绝苦难的模式化与重复化:“对于这世界也许我们批评得太多,承担的太少,”她再度去探寻“自我寻找”的可能性,这一次,郑小琼选择了在“构境”中体味生命,重建内心的秩序空间,如诗歌《五金厂》:
在忧郁的五金厂
我爱上起起伏伏的群山,它们在机器的
轰鸣中摇晃,我爱上油腻浑浊的事物
冷却油间的铁屑,机油里的螺母
转动的轴承,污秽,黑暗的角落
某个磨损的零件,深夜机台的嘶吼[4]60
“我”竟能够爱上铁屑、螺母、轴承或是黑暗的角落,这些意象能够适应语境的变化,从而演变成新的内涵。即使时代希望将打工者的棱角抹去,将他们的信仰遗忘,将人民装进集体主义的锡罐头,但在郑小琼的《时间》中,工厂中机械化的时间被凝滞,定格在了某一瞬间,工厂与流水线被遮掩,读者由此接近了打工者的生命历程——如同深夜机台的嘶吼,自由的信仰会在黑暗的角落再度释放。诗人超越了冷酷的城市与失落的乡村,突破了虚幻的表象,在个体的生命之上构境了能够重返本真的空间。
在诗歌《灯光》中,我们足以见到郑小琼的“生命构境”:
我爱着的尘世生活,忙碌而庸常的黄麻岭
风张开翅膀,轻轻吹过五金厂,纸片厂
毛织厂……一直地吹,吹过冬天开裂的手掌
想起善良的温情,我缄默的唇间
颤栗着,那些光,那些生活会漫过
我的周身[4]59
“五金厂”“纸片厂”“毛织厂”本是冰冷的工厂,在此刻却由“风”串联,化为了诗人的生活经历。具象化的空间被抽空,所留下的是诗人所热爱的“尘世生活”,个体的温情体验盖过了开裂手掌的苦痛记忆,而这也预示着郑小琼放弃了对城市的抵抗以及对原乡的寻觅,最终,打工者将顽强地生长在这片城市与乡村的交叉地带。
郑小琼等打工诗人更将“生命构境”的场域锁定于打工者的身体,特纳在《身体与社会》中说:“他们拥有身体而且他们就是身体。”[17]身体与自我联系密切,不可分割,且被社会种种不断建构与生产,诗人在身体之上进行“构境”,尝试着将真实的底层生命历程复原于自我的记忆中。诗人郭金牛在《秋天的加法,春天的减法》中这样写道:“张。一个四川女子,与我一起,一手拿着米粉,一手拿着工卡,在春天的减法中,奔跑。”[18]他将个体还原成具有动感的诗性意象,在强大的系统将打工者打造成具有“机械化”“同质化”的物的附属品时,郑小琼等诗人以“身体”表述了对城市的拒绝,以“身体”表述着情感的个人性:
我的体内收藏一个辽阔的原野,一列火车
正从它上面经过,而秋天正在深处
辛凉的暮色里,我跟随火车
辗转迁徙,在空旷的郊野种下一千棵山楂树
……
跟着火车行走,一棵,两棵……它站在灰茫
茫的原野
我对那些树木说着,那是我的朋友或者亲
人[4]82
——《火车》
许多人将《火车》看成作者的乡愁体现,但这首诗更像是超出现实空间的“生命构境”,“火车”作为离乡的交通工具,在诗人体内不断穿梭辗转,并不归属于现实所存在的空间,而是指涉着内在体验,我即使预见到前方失落的命运,仍种下意喻美好的“山楂树”,负重前行,火车留下的是打工者厚重的生命历程。而那些随着火车行走的树木与影子,又何尝不是在“我”生命历程中留下足迹的“他者”,他们一同与“我”感受生命的活着状态,在身体流浪、迁徙、受难、承受的过程中,人已经到达了生命的本质,体验到生存的真正价值,在这样的生命重构中,没有排挤,没有歧视,皆是我的朋友与亲人。
郑小琼是一个书写疼痛的高手,她以自己敏感的心记录底层生活的艰难,“断指”往往概括着特定群体所经历的饥饿、血泪与恐惧,如同郑小琼的《疼》中所述:
她站在一个词上活着:疼
黎明正从海边走出来,她断残的拇指从光线
移到墙上,断掉的拇指的疼,坚硬的疼
……
机台的齿轮,模板,图纸,开关之间升起,
交缠,纠结,重叠的疼
“黎明”从海边走出,大海升起灼热,时间在郑小琼的诗中绵延扩大,生存的痕迹取代了物理性质的空间。“她”在工伤中遭遇了“断指”之疼,因为身体的疼痛,“她”的心灵也感受到了屈辱与损伤,诗句切实使读者体味到了疼痛的真实感,但正是这来自“现实主义的疼痛”才能唤起人们生命意识的自我觉醒,只有“疼痛”才能带来生命的存在体味,才能戳破视觉表象,唤醒人们对于“生”的认知,从而脱离商品对于人类的“殖民”,诗人不仅在书写疼痛,更创造了脱离奴役的生命空间,在生命“构境”中即使存在血泪、苦难,但人们能够超越生存的困境,从而实现精神的飞升。张连敏在《一条不知疲倦的河流》中写道:“在蓬勃的水藻间∕我是一条不知疲倦的河流∕液体的质感 使我有了∕流动而自由的生命∕请不要鄙夷我这份执着的向往……不想让沙尘埋住的意念∕使我一次次让血液沸腾。”[19]打工诗人们不断地书写个体于社会中的感受,“感觉”带来“存在”,而“存在”的觉醒是身份认同的开始。
郑小琼等打工诗人的诗歌中那个控诉城市,借“原乡”躲避现实的独立个体似乎被某类歌颂生命的苦难英雄所代替,而苦难英雄所处的,正是郑小琼们通过诗歌绘制出的生命“构境”,生命包含热血,底层人民如同被社会塑形的弹簧,因挤压而蓄力,在黑暗的角落中往往持续着恒定的力量,他们描绘出当今社会的种种面向,他们的生命力形成了超越物理空间、上升至精神的存在,在那里,每个人皆有存在的意义,因为生命本身因“存在”而珍贵,与诗人的身份认同形成同一,自我存在的意义由此完成。
光阴不断地迁徙着 我站着没有动
黄昏的光线如同生活的重轭压了过来
我伸长脖子承担着这巨大的沉重[4]43
在郑小琼等打工诗人的后期诗歌中,那些之前苦苦追问的“社会真相”似乎已不再重要,正如德波所言:“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16]3阿吉克优对自我生命的确认转移至《砸铁工》:“一捶捶都是生命的延续”,[20]陈年喜也在数十年的爆破生涯中寻求到了自我的“铁骨”,而罗德远的《我们是打工者》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自我觉醒后的追求。郑小琼们以打工者的生命历程对于人性进行宏大的观察,并且经由日常生活的众生相摘除现实的肿瘤,书写着生活的不幸,却在“生命构境”中赋予这种存在真正的出路。
四、结语
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别让“80 后”个体与个体之间有了强烈的差别。打工潮的来袭加剧了人口的流动,空间的转移也意味着精神的错置与身份的迷失,在郑小琼的诗歌中,我们能够看到诗人的精神主体在“待不下去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中辗转游移,最终选择了在生命中实现“诗意地栖居”,郑小琼诗歌中的“空间诗学”,见证了打工诗人在身份认知中的迷失与转变,作者也由此将仄狭视野一变而为广阔的天地,完成了一次精神洗礼。可以说,郑小琼等打工诗人为寻求存在意义而构建出的各类空间,是一部个人精神的转型史,而最后,郑小琼们借“生命之构境”,挣脱出冰冷的现实囚笼。
打工诗人的身份认知看似在“生命构境”中走向终点,但此刻,写作给郑小琼带来了社会地位与财富,曾经的打工诗人罗德远成为作协会员,谢湘南获得广东省鲁迅文艺奖,身居深圳,曾经的打工诗人们似乎已经脱离了底层行列。即使他们如何宣称与底层人民同在,但在其诗歌的“生命构境”中,俨然包孕着充满怜悯的、富有道德感的英雄主体,脱离了“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英雄主体,即便拥有了生存意义,又如何能够代表一切打工者?郑小琼们逐渐由诗中的主人公变成了旁观者,由情绪高昂的“写自己”转向更为清醒从容的“他者视域”审视社会和历史,他们可以是一名成熟的诗人,但也许不再能够代表千千万万的“打工者”,郑小琼等打工诗人的身份认同之旅走向生命与精神,而千千万万的“大多数”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