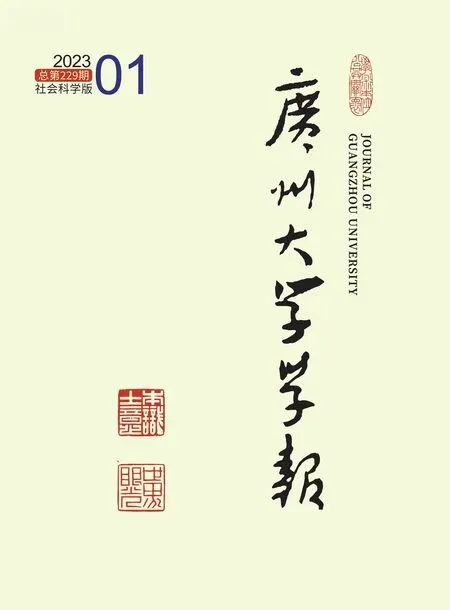《三国演义》历史观论略
纪德君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历史观就是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在历史研究中,每每遇到一些重要的事件,尤其是朝代的兴废争战之事,人们就难免要思考: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事情又怎么会这样?是什么因素左右了事情的发生与变化?这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问题多了,研究者就会进一步抽象地思考: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等等。一部历史小说的作者,对其所写的历史人物事件怎么看?对朝代兴亡怎么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思想与艺术水平的高低。《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代表作,研究《三国演义》不可能不审视它的历史观。《三国演义》的历史观比较复杂,以往学者曾讨论过《三国演义》的正统史观、英雄史观,[1-4]对天命史观、道德史观也略有涉及,但未作系统探讨。这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三国演义》的历史观。因此,笔者尝试对《三国演义》的历史观进行全面的审视与述评,并在此基础上谈谈如何比较客观地看待三国的历史兴亡问题。
一、《三国演义》表现的正统史观
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证明其统治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既得利益,蒙骗老百姓,以便使其帝位能够代代相传,所以就编了一套政治谎言,说皇权的获得,是受命于天的,是上天赐予他的,即所谓的“受命于天”“奉天承运”。皇帝自称为“天子”,是上天之子,也就是说,是上天选择了他来做人间统治者的,所以他的政权是合法的,是天经地义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既然如此,张三家的王位就只能由张三家的子孙才能够接续统治,李四、王二麻子都不行。张三死了,张三的儿子来继承皇位。张三的儿子死了之后,就由张三儿子的儿子来接替皇位。这样代代相传,就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古人就称之为“正统”。可见,“正统观”是建立在“天命论”和“血统论”基础之上的,用“天命论”来支撑“血统论”的合法合理性。因此,一个人如果不是皇帝的子孙,那么他就与帝王之位无缘。不管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多么有权谋,但他要是想篡夺皇位的话,就会被天下之人视为乱臣贼子。对于正统的政权,臣民们要无条件地忠诚与拥护,绝不能凌驾于国君之上。这样,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正统观念与忠君思想。
《三国演义》对于正统观念与忠君思想的表现是很明显的。比如曹操,其文治武功都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但由于他篡夺了皇帝的实权,野心勃勃,所以当时的诸侯们多骂他为“国贼”。而刘备呢,则因为是汉景帝的第十八代玄孙、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所以就受到尊崇,人称“皇叔”,这对其创业立国起到了很好的政治宣传与推动作用。小说写刘备一出场很注意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作为其打天下的政治本钱。如第一回写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幽州太守刘焉出榜招兵,刘备见了榜文,慨然长叹。不料,张飞在他身后厉声喝道:“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刘备答道:“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5]3张口就标榜自己是汉室宗亲。于是,张飞、关羽便与刘备举行桃园结义仪式,并推刘备为兄。这显然与刘备出身正统不无关系。
后来,刘备及其部下在与其他诸侯角逐天下的过程中,就经常拿“正统”出身作招牌,或试图打压对手,或博取他人的同情,或扩大其社会影响。如第三十一回,刘备与曹操两军对垒,就指着曹操鼻子骂道:“汝托名汉相,实为国贼。吾乃汉室宗亲,奉天子密诏,来讨反贼!”[5]228第三十七回写刘备一顾茅庐,自报家门:“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5]269二顾茅庐时,留下书信一封,信中特意强调自己是“汉朝苗裔”。第三次见到诸葛亮,开口第一句话是“汉室末胄”。可见,刘备总是不失时机地标榜其汉室后裔的高贵身份。而刘备部下在与对手较量时也常喜欢拿“正统”说事。如第十三回写吕布宴请刘备,见刘很客气,就说:“贤弟不必推让。”按说吕布比刘备岁数大,这样说没毛病,但是张飞听了却瞋目大叱道:“我哥哥是金枝玉叶,你是何等人,敢称我哥哥为贤弟?你来,我和你斗三百合!”[5]86张飞一直以大哥出身皇族而倍感自豪,怎么能容忍一个三姓家奴称他大哥为贤弟呢!第五十四回写鲁肃奉命前来讨要刘备所借荆州,不料孔明竟勃然变色道:“子敬好不通理,直须待人开口。自我高皇帝斩蛇起义,开基立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各据一方。少不得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岂不可分茅裂土?况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顺?汝主乃钱塘小吏之子,素无功德于朝廷;今倚势力,占据六郡八十一州,尚自贪心不足,而欲并吞汉土。刘氏天下,我主姓刘倒无分,汝主姓孙反要强争?”[5]388一席话驳斥得鲁肃哑口无言。第六十回,庞统对张松说:“吾主汉朝皇叔,反不能占据州郡,其他皆汉之蟊贼,却都恃强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5]439
《三国演义》不仅写刘备集团多次使用“正统”作为其夺取天下的政治资本,还在刘备称帝后,直接改用蜀汉的“章武”年号接续汉献帝的“建安”年号进行纪年叙事,明确以刘蜀绍继大汉正统。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有13处使用“章武”纪年;“章武”之后是“建兴”,小说中有22处用“建兴”纪年。但却有意不用曹魏政权的年号来纪元叙事。毛宗岗父子评点本《三国演义》第八十回,还直接用“曹丕废帝篡炎刘 汉王正位续大统”作为回目。可见,《三国演义》标举刘蜀为正统的历史观是显而易见的。
若推究其因,这大概与《三国演义》“依史以演义”[6]1时受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有关。《资治通鉴纲目》把刘蜀政权作为汉王朝的一部分,这曲折地反映了汉族人民在民族矛盾比较尖锐时期的民族感情,自南宋以至明代,对汉族民众特别是文人士子影响很大。笔者考证,《三国演义》在东汉被曹魏取代后,坚持用刘蜀政权的年号来纪年叙事,并且采用一字见褒贬的方式表明其倾向,的确是受《资治通鉴纲目》的影响。[7]毛泽东曾指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光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8]258翦伯赞也指出:“《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9]显然,毛泽东、翦伯赞等对《三国演义》以刘蜀为正统的历史观是持否定态度的。
正统史观本来是封建时代“家天下”的产物,如梁启超所说:“故夫统之云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钳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不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此统之名所由立也。”[10]因此,正统史观不过是一种为某一政权之统治者辩护、粉饰的工具,而并非对历史发展合理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正如翦伯赞指出的,它是“以‘皇帝至上’、‘封建世袭’为原则辩护现存的政权之合法性的工具”[11]。
《三国演义》的确表现了一种正统史观,但如果仅仅因为刘备姓刘,是皇室后裔,就觉得应该同情、肯定、赞美他的政权,那么《三国演义》的思想性也未免太差了。实际上,《三国演义》对同样是汉室后裔,与汉室关系更近,曾割据一方的刘表、刘璋等,并没有加以肯定与赞赏。它之所以以刘蜀为正统,选择以刘蜀集团等作为其重点描写与肯定的对象,除了正统观念起了一点作用外,恐怕主要还是因为它继承了民间“说三分”拥刘贬曹的传统,觉得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的所作所为更符合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如仁政爱民、忠义为本等。因此,《三国演义》所秉持的历史观,主要还是儒家的道德史观。
二、《三国演义》表现的道德史观
道德史观,就是把历史的着眼点放在个人的道德品性上,认为历史是由有道德修为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儒家有所谓“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政治理论,指出治国理政者或有志图王者,只有加强内在的德性修养,实施仁政,以民为本,才能据有天下。儒家所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12],“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13]255,“仁人无敌于天下”[13]255,“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14],等等,都意在说明,讲“仁义”道德,乃是夺取天下,保住君位的必备条件;反之,若行“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13]258,“虽得之,必失之”[15]205。
罗贯中深受儒家道德史观的影响,他在写人叙事时习惯于从道德角度看问题,强调道德在政治事功中的作用,赞美历史人物对宽仁忠义等伦理道德的坚守,鞭笞不讲道德的暴行暴政。在《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百十九则中,他明确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16]574而刘备就是他心目中的“有德者”,他与关、张结义,是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复兴汉室。他自觉地以“仁义”作为建基立业之本。如《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写徐庶因母亲被曹操所执,不得已与刘备拜别,孙乾劝刘备切勿放去,刘备说:“不可!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5]264-265第四十回写孔明劝刘备乘刘表病危,取荆州以拒曹操,刘备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说:“今若不取,后悔何及。”刘备说:“吾宁死,不忍作背义之事。”[5]290第六十回写庞统劝刘备听从张松、法正的建议,入益州取刘璋而代之,刘备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曹以急,吾以宽;曹以暴,吾以仁;曹以谲,吾以忠。每与曹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吾不忍也。”[5]442第八十回写孔明等上书劝刘备即皇帝位,刘备大惊道:“卿等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5]589凡此皆意在突出刘备的宽仁忠义之德,彰显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其实,按史书记载,刘备固然宽仁忠义,但毕竟是“枭雄”,周瑜、鲁肃等皆称他为“天下枭雄”,他曾不止一次设计大败对手,也曾一怒之下怒鞭督邮。可是,罗贯中却着重从伦理道德角度去写刘备,刻意将他塑造成理想化的“仁君”,遂使其枭雄一面荡然无存。
至于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也都专主忠义于一人,因此成为贤臣、义友的典范。实际上,对于“忠义”之士,不管其出于哪个阵营,《三国演义》都不吝赞美之词。如第三十三回写沮授、审配、王修等人在袁绍兵败身亡后,均甘心受死而誓不降曹,这让曹操深受震撼,并由衷地赞叹:“河北义士,何其如此之多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用,则吾安敢正眼觑此地哉!”[5]243而对于曹操前期激于“忠义”,谋刺董卓;以“忠义”之名号召诸侯,讨伐董卓等,作者显然也是持赞赏态度的。只是后来曹操对上不忠、对部下不义、对百姓不仁,所以才不断遭到作者的口诛笔伐。在小说中,作者刻意选取了一系列颇有表现力的逸闻琐事,诸如装病诬叔、杀吕伯奢全家、霸占张绣婶婶、借王垕之头以解众怒、割发代首、计害祢衡、梦中杀人、处死杨修、设红白旗诱杀百官、虚设疑冢等,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终于将曹操写成了奸诈残忍的一代奸雄、目无君上的奸臣国贼。
由此可见,忠义仁爱是作者描写、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标准。作者也非常渴望刘备这样的“有德者”来统一天下。所以,他明确主张尊刘抑曹,歌颂以刘备为典范的仁君仁政,鞭挞以曹操为代表的暴君暴政,虔诚地渴望以忠义仁爱为本的刘备集团能平定奸邪纵横的乱世,解民于倒悬,重建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社会秩序。因此,有论者指出,《三国演义》的作者是“伦理地、而不是历史地,情感地、而不是理性地观照社会历史的律动”[17],其体现的道德史观是显而易见的。
“道德史观”自然会导致《三国演义》的作者过多地关注人物的伦理道德品性,塑造人物时也主要着眼于人物的伦理道德表现,这无疑将人物复杂的性格简化了,从而造成人物性格内涵的单一性与类型化倾向。不过,由于作者在人物形象中灌注了比较浓郁的道德情感力量,并且这种道德情感又渗透了下层民众的情感好恶,因此这种伦理道德色彩鲜明的人物形象,也颇能产生一种兴发感动的艺术力量,特别是当承载忠义仁爱之道德理想的刘关张与诸葛亮等功业未竟而中道殂陨时,小说带给读者的悲剧感受是相当强烈的。
三、《三国演义》表现的英雄史观
英雄史观,就是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由少数英雄人物和帝王将相的意志﹑品格﹑才能决定的。梁启超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18]在他看来﹐若干大人物的“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19]。中国古代史书主要记载的就是帝王将相的业绩,被称之为帝王将相的谱牒。
《三国演义》也是如此,它主要叙述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这些斗争又主要是由诸侯、豪强操纵的,正是这个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组织与指挥的战争,决定了战争与和平,推动或阻碍了历史的进程。因此,《三国演义》主要突出的是以曹操、司马懿、刘备、诸葛亮、孙权、周瑜等为代表的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及其对三国历史演变所起的极重要作用。
虽然《三国志通俗演义》也曾多次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但这不过是乱世英雄想要夺取天下的一种口实。例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十五则写王允怂恿董卓称帝时就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自古‘有道代无道,无德让有德’,岂过分乎?”[16]73-74第一百○一则写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争夺南郡,周瑜说:“待吾取不得南郡,从公取之。”孔明答道:“都督此言极是公论。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先尽东吴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是也。”[16]491因此,天下从来都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只是少数诸侯或英雄豪杰的天下,他们才是“天下人”的主宰,而“天下人”则往往是英雄的附庸,借用董卓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事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5]22!
与此同时,《三国演义》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人民群众的疏远和轻视。曹操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昭示了天下黎民在他眼中草芥不如的地位。如他为了给父亲报仇,起兵讨伐徐州,欲尽杀当地百姓。又如,第六回叙董卓与袁绍、曹操等十八镇诸侯交兵不利,为避其锋,决定迁都长安,群臣苦谏:“丞相若欲迁都,百姓骚动不宁矣!”董卓大怒道:“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5]38无论是曹操还是董卓,人民群众都是任人摆布、宰割的羔羊,他们哪里会把“天下”“小民”的利益放在眼里。
当然,有志图王的杰出人物,基于平治天下的政治需要,有时也会意识到百姓的重要性。如《三国志通俗演义》第六十一则,写众人劝曹操攻打冀州,曹操说:“冀州粮食极广,审配又有机谋,急未可拔。见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废民业,姑待秋成,取之未晚。”众人道:“若恤其民,必误大事。”曹操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其民,纵得空城,有何用哉?”[16]307《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写刘备败走当阳,十万民众追随其后,其部下皆劝其丢下民众轻装逃走,刘备哭道:“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5]299
实际上,处于乱世的老百姓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寄希望有一个像刘备这样仁政爱民的英雄,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例如,《三国演义》第十二回写曹操讨伐徐州,百姓将遭祸殃,刘备前往救援,陶谦于是三让徐州给刘备,徐州百姓也拥挤府前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5]80第三十五回写刘备治新野,新野百姓作童谣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处,民丰足。”[5]259《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七十二则写徐庶走马荐诸葛亮,有诗赞曰:“四海苍生在倒悬,豫州天下谩求贤。不因徐庶临岐荐,怎得西川四十年?”[16]356《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写曹操奔袭新野,刘备、诸葛亮巧施妙计,击退曹操大兵,终于保一方平安,于是新野百姓遮道而拜:“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5]289可见,像刘备、诸葛亮这样仁政爱民的英雄,才是“天下人”的救世主,而老百姓崇拜的也正是这样的英雄。
总之,由于作者秉持英雄史观,因而他把笔墨主要集中于描绘那些影响三国分合的重要历史人物,着重展现他们的“英雄气”,这样便使主要人物富有活力、生气勃勃,即使对于曹操这样的“奸雄”,作者也并不讳言其雄才大略,因此曹操的性格既特征鲜明又内涵丰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当然,在作者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不仅要有才略武勇,更要崇忠义、讲仁爱、重民本,而这也是他把赞美和同情给予刘备、诸葛亮等人的主要原因。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英雄史观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有其深刻的社会的﹑阶级的和认识的根源,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总是集中地体现在他们的代表者──领袖人物的活动中,并在领袖人物的领导下从事历史的创造性活动。当人们看不清隐藏在领袖人物行为的动机背后的﹑推动一个民族或阶级行动起来的物质动因时,他们就会把个人看作推动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四、《三国演义》表现的天命史观
罗贯中虽然推崇出身于正统、讲仁爱崇忠义的英雄刘备、诸葛亮等,希望由他们来建立符合儒家政治道德的理想政权,可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个玩笑,让他心目中邪恶势力的代表曹魏集团夺取了政权,统一了天下,而他倾注了一腔痴情的刘蜀集团,竟然悲惨地败亡了。残酷的历史事实对他奉为圭臬的道德理想的无情嘲弄,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和困惑中,于是他将这一切都视为“天命”,用“天命史观”来消解其浓厚的悲剧意识。
所谓“天命史观”,就是认为朝代的兴衰、历史的循环、历史人物的命运等都摆脱不了天命的主宰,人只能顺天而为。如《尚书·汤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0]《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21]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15]11;“死生有命,富贵在天”[15]147;“不知命,无以为君子”[15]255。董仲舒曰:“天者,百神之君也”[22]402;“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22]319;“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22]286。
“天命史观”对《三国演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37次使用“天命”、21次使用“天数”、19次使用“天意”、10次使用“气数”,此外还有大量以灾异、天象、谶纬、童谣、占卜、术数等形式呈现的神秘描写,也都是“天命”作用于人事的具体反映。小说第十四回,曹操与众谋士密议迁都之事,太史令王立与宗正刘艾回应道:“吾观大汉气数将终,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又密奏汉献帝:“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5]97这便是借仰观天文来预示汉魏兴替。第三十五回,水镜先生为刘备指点迷津时说:“公闻荆、襄诸郡小儿谣言乎?其谣曰:‘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到头天命有所归,泥中蟠龙向天飞。’此谣始于建安初。建安八年,刘景升丧却前妻,便生家乱,此所谓‘始欲衰’也;‘无孑遗’者,不久则景升将逝,文武零落无孑遗矣;‘天命有归’,‘龙向天飞’,盖应在将军也。”[5]256-257一首童谣居然预示了此后十几年将要发生的事。第三十七回写司马徽与刘备辞行时说:“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5]268而诸葛亮好友崔平州也对刘备说:“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5]270这也提前预告了诸葛亮生不逢时,刘备逆天而为、徒劳无功的结局。第三十八回,孔明说:“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归将军。”[5]277也对即将发生之事做了精确预言。而一些重要人物的命运也是由天注定并以天象呈现的。如第四十九回写赤壁战后,孔明说:“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5]358第五十七回写孔明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于是笑道:“周瑜死矣。”[5]411刘备使人探之,周瑜果然死了。第一百○三回写孔明踏罡步斗、禳星乞寿失败,弃剑而叹道:“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5]776第一百○四回写孔明临终前对姜维长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吾旦夕将死。”[5]777第一百十七回,邓艾指出诸葛亮“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数耳”[5]869。凡此皆表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另外,第八十回写魏王曹丕派人逼汉献帝禅位,李伏向汉献帝奏道:“自魏王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当代汉之象也。”[5]585许芝也接着奏道:“臣等职掌司天,夜观乾象,见炎汉气数已终,陛下帝星隐匿不明。魏国乾象,极天察地,言之难尽。更兼上应图谶,其谶曰:‘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以此论之,陛下可早禅位。‘鬼在边,委相连’,是‘魏’字也;‘言在东,午在西’,乃‘许’字也;‘两日并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5]585可见,魏受汉禅,实乃天意。
由以上所述可知,天命史观一方面被诸侯们用来验证其“感天而生、应天而王”之神圣性、巩固其既得利益的一种常用手段;另一方面也被作者用来解释朝代兴衰更替、历史人物命运播迁的理论武器。小说结尾云:“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5]893对于三国的分合特别是蜀汉兴亡和历史人物的命运,罗贯中无法寻求合理的解释(正统史观、道德史观、英雄史观等都帮不了他),于是只能归之于天命的安排,也就是说刘备集团的命运是由天数或天意决定的,尽管后人从情感上接受不了刘蜀的败亡,但也只能发发牢骚,听天由命了。可是,既然如此,人的所有努力还有什么意义?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放弃追求,何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天命史观的引入以及由此敷演的一些故事,无疑也为小说叙事着染了一层神秘、奇异的色彩,尽管今天看来那些神秘叙事荒谬不经,但是在天命论流行的年代,还是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助添阅读的兴味,抚慰读者因英雄之死而产生的悲伤情绪。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的历史观是比较复杂的,正统史观、道德史观、英雄史观、天命史观,以及循环史观①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并且往往交融在一起、相互为用。作者崇尚英雄,但他崇尚的主要是出身正统的、以忠义仁爱为本的英雄,也是能体现天心民意的英雄,因此它呈现的是以儒家政治道德为核心的多元历史观。这种多元历史观虽然包含某些合理的成分,但显然无法对三国的兴亡作出富有诠释力的科学说明。既然如此,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三国历史的演变尤其是蜀汉的衰亡问题呢?
五、唯物史观观照下的三国兴亡
唯物史观认为,一切历史事变都是在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自然环境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军事、外交、法律、道德、宗教等上层建筑,彼此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演变的动力。恩格斯说:“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3]
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从社会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解释历史发展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原理。只有秉持唯物史观,我们才可能对蜀汉兴亡、三国归于一统等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三国纷争及其演变,就是由地理、人口、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道德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合力推动所致。
就地理环境、人口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三国中蜀国偏安一隅,在天时、地利上处于劣势,人口数量相对有限,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魏国、吴国,仅是守成已勉为其难,何况还频频出击,攻打魏国呢?如果领导人不考虑物质生产生活条件与综合国力的制约,仅凭个人的主观意志与愿望去行事,其失败的命运是难以避免的。《三国演义》写蜀国、吴国被魏国吞并时曾列了一笔清单,交待它们的家底。请看蜀国的家底:
共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仓粮四十余万,金银二千斤,锦绮丝绢各二十万匹。(第一百十八回)[5]872
试问仅凭这点家底,怎么去与国力雄厚的曹魏抗衡?再看吴国的家底:
东吴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县,户口五十二万三千,军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皆归大晋。(第一百二十回)[5]892
吴国实力虽然也较有限,但比蜀国还是强多了。实际上,在司马氏篡魏立晋,攻打蜀、吴时,西晋有370万户,而蜀、吴相加也只有80余万户。陈寿《三国志》卷二十二《魏书·陈群传》裴松之注记载,西晋太康三年,“晋户有三百七十万,吴、蜀不能居半”[24]。
从政治、军事、外交、道德等方面看,也不难发现蜀汉在战略、决策与战术等方面因一些人为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外交上,本来孙、刘两国凭自身实力,均无法对抗曹魏,所以诸葛亮制定了“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外交政策,但后来却被关羽破坏了,导致荆州丢失,关羽被杀。政治上,刘备后期与诸葛亮、刘禅与诸葛亮、刘禅与姜维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与矛盾,导致诸葛亮、姜维不能充分发挥其才干。如第八十一回写刘备执意讨伐东吴,诸葛亮上表劝阻,但是刘备看毕,竟然掷表于地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5]595军事上,蜀汉军事人才凋零,后继乏人,蜀军内部矛盾也未能很好化解,如诸葛亮遗计斩魏延;军事决策与战术也出了问题,如诸葛亮误用马谡,导致街亭丢失,首次北伐失败。道德上,刘备讲忠义、信义、仁义,但有时缺乏变通,不计利害。如他因为要对病危的刘表讲仁义,不愿乘机接管荆州,才导致刘表之子将荆州献于曹操,后来荆州又被东吴所占,刘备只能暂借荆州以栖身,这为后来孙、刘失和埋下祸根。他出于兄弟义气,不顾诸葛亮等反对,大举讨伐东吴,结果大败亏输,重伤国本。而诸葛亮也是受“忠义”束缚,不计成败利钝,也要维护其忠贞的政治形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第九十七回)[5]720于是连年用兵,加速了蜀国的败亡。
总之,根据《三国演义》的描写,借用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三国历史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刘蜀集团的兴亡,是不难作出合理、有力的诠释的。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分析《三国演义》的历史观,不仅有助于认识其历史观的局限,对于当今的历史文学创作,无疑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如果今天有人写历史小说,还在有意无意地宣扬正统史观(血统论),搞英雄崇拜甚至是帝王崇拜,片面地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而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那么对于这样的历史小说,我们就要对之进行质疑与批判。
【注释】
① 《三国演义》开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第三十七回,作者又借崔州平之口说:“自古以来,治乱无常: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这便是把历史演变视为治乱相间的循环,属于典型的循环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