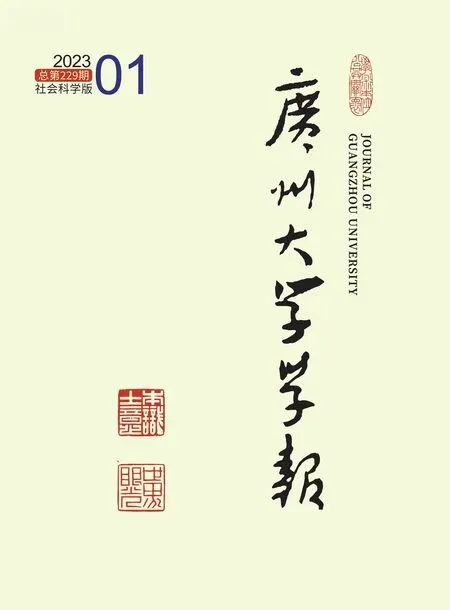倾听沉默的“创伤之地”
——《广岛之恋》中创伤经验的空间建构
王莹雪,陶东风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引 言
据英国驻日代表团1945年11月的调查报告:“1945年8月6日,早上8点后不久,一架在30 000英尺高空飞行的美国超级堡垒(American Super-Fortress,即B-29远程轰炸机)于日本的商业城市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在广岛,超过4平方英里的城市被摧毁,且80 000人丧生。”[1]基于详实的数据材料,该报告宣称:所有数字都“生动地”说明了灾难的规模,并将适用于评估英国城市或其他西方城市的核爆效应。由此可知,在两军对垒和科学试验的视阈下,这是一个用数字堆砌而成的“广岛”。
1946年,美国《纽约客》的遣派记者约翰·赫塞(John Hersey)到广岛进行实地考察。通过为期一个月的采访,赫塞还原了六位幸存者当时的所见、所感和所思,以此从真正的证人身上获得故事。在他最后完成的《广岛》(Hiroshima)一书中,所有文字都以生动却又近乎克制的表征形式,将受访者们的创伤经验原原本本地汇聚在一起。透过这些灾难幸存者的眼睛,读者们看到了一个由证人故事构筑而成的“广岛”。
1958年,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应“左岸派”导演阿兰·雷乃之邀创作了剧本《广岛之恋》,通过引用《广岛》的原文语句,杜拉斯向赫塞及其著作致以崇高敬意。1959年,影片《广岛之恋》还入围了第12届戛纳电影节。尽管它当时面临着被禁演的命运,尽管在一个两千五百人的大厅里,支持它的只有不到三十人。[2]但同年6月,该影片在法国上映,霎时轰动了整个西方影坛,它被誉为“一颗在精神上爆炸了的原子弹”,引发了人们对电影及其传达内容的空前审思。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开篇那一幕——两个在(原子弹的)灰烬、雨水、露珠或汗水里紧紧互搂的、肤色各异的赤裸肩膀——便深深震撼了所有观众。依凭这样一个虚构的、关于萍水相逢的爱情故事,杜拉斯和雷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极具诗性的、且铭刻着独特历史指涉的“广岛”。它带来的冲击力似乎远远超过了那个以公允的数据、抑或生动而真实的证人故事铺展而成的“广岛”。这是为什么?许多年过去了,“所有事物之上是一层洁净、鲜亮、葱郁、乐观的绿色……杂草已经掩盖了灰烬,而野花在城市的骸骨中盛开”[3],但固着于广岛的创伤经验为何能在历经看似遗忘之后,在杜拉斯和雷乃的时代、乃至我们现时处身的时代唤起一种更为强烈的共鸣?在《广岛之恋》中,“广岛”是如何进行建构的?它最终如何关联起个体记忆与集体历史经验?
二、作为“创伤之地”的广岛
故事发生在1957年8月的广岛。一个三十多岁的法国女人来到这里,她是来参演一部有关和平主题的影片。就在影片拍摄几近完成而回国在即之时,这个法国女人邂逅了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男人,并与他产生了一段过眼云烟、但却痴狂到极点的恋情。电影里,日本男人自陈道,“我是个跟妻子一起过得很幸福的男人”;那个法国女人答道,“我也是个跟丈夫一起过得很幸福的女人”。[4]99两个原本有着相似幸福家庭的人,却在广岛发生了一段不太可能的爱情,这显然并非任何一个城市每天都能发生的风流韵事。作为曾经的原爆发生地的“广岛”,它似乎在以某种必然的因由,使这两个偶然相遇的人恰好能相互吸引、相互爱恋。那么,该如何阐析这样一种居于确切地点之上的必然关联?德国著名的文化记忆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或许能给予我们以深切启发。
在《回忆空间》一书中,阿斯曼指出,“地点”对于文化回忆空间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就像一个被收藏的物体一样,‘地点’是‘过去与现实之间的掮客’;我们也可以说:它们是记忆的媒介;它们指向一个看不见的过去并且与它保持着联系。”[5]384换言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记忆载体,“地点”本身具有一种导源自空间的媒介维系力,它能够维系不在场的“现实”的现时在场,并使我们与看不见的“过去”保持直接的接触和关联。
同作为文化记忆媒介之一的“身体”一样,“地点”也可以敞开感性化的经验和记忆。具体说来,该“地点”可以是“代际之地”:即“地点”与家庭历史之间被赋予了一种固定而长期的联系;它可以是“纪念之地”:即通过标明过去和现在的非连续性,被中断的历史记忆从废墟中获得其物质形式;它可以是“回忆之地”:其中,被毁坏之地仍保存着的那些残留物,为了使自身继续存在和有效,它们借由讲述一个补偿性的故事,使自身成为新的文化记忆关联点。当然,它还可以是“创伤之地”。阿斯曼发现,在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中,主人公海丝特会强迫自己留在通奸的地方,让她的罪孽、耻辱保持持久在场。就此而言,“创伤之地把一个事件的险恶固着下来,这个事件是一段不会消逝、不愿远离的过去”[5]381。同样地,“奥斯维辛”也是一个典型的“创伤之地”,它维系的是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工厂式屠戮的创伤经验与记忆。
关于这种“地点的维系力”,如果说,“在代际之地上这种力量来自活着的人与死者之间的亲属链条,在纪念之地上这种力量来自于被重新建立和重新传承的讲述,在回忆之地上这种力量来自一种纯粹好古的历史性质”,那么,“在创伤性地点上这种力量来自于一个不愿结疤的伤口”。[5]392由此“创伤之地”区别于其他“地点”类型的显著特征就在于:它所承载的创伤过往永远无法被历史化(即不愿成为过去)、无法被治愈而只能强迫性地保持持久在场。
从《广岛之恋》来看,“广岛”显然是一个特殊的“创伤之地”,它使那两个来自不同国度、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找到了他们“共有的场所”与“世界上惟一的场所”。[4]4只有在这里,在这个确切的地点上,“他”和“她”各自无法成为过去的伤口才会被唤醒,他们由这一创伤地点所寻获的吸引和爱恋才会必然地呈现出来。
我们知道,在1957年的广岛,日本男人的创伤来自1945年8月6日。原爆发生时,他的家庭就在广岛,他却被派去战场。这个日本男人为此错过了在广岛的灾难,他什么也没看到,并且幸存下来了。因而,他不理解的是:自己当前所能看到的只是外在的事件症象(诸如博物馆陈列的照片、医院中失去健康的肢体、局外人正在摄制的影片、举着标牌进行反核宣传的游行队伍等),而不是事件本身。
在1957年的广岛,法国女人的创伤并非来自广岛,而是来自她的故乡(或原初的创伤之地):法国涅勒夫省的小城“内韦尔”。1944年8月2日,她的德国初恋情人被射死在卢瓦尔河畔。这一天,法国解放了,她正准备和他一起私奔到巴伐利亚;也是这一天,她被村里人剃成光头,以示对爱上敌人这桩罪行的惩罚。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内韦尔成了她最魂牵梦萦的城市,同时也成了她最少想念的城市。对她而言,让自己伤痛的倒不在于被剃光了头而身败名裂这一事实,而在于那天她没有在卢瓦尔河畔殉情身亡。
关于两位主人公呈现出的创伤固着,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那是由于创伤事件在发生时不能被及时处理、不能被纳入已有的指涉框架,所以它会超出受创者的意愿和控制,使自身的原本性进行反复回归。就此而论,虽然创伤经验的固着作用(从“潜伏”到“复归”)确实扰乱了时间单向的线性运行,但它本质上仍依附于时间之维,并且仍处于“过去”对“当下”的反复纠缠之中。从阿斯曼的文化记忆视阈来讲,“创伤之地”实则使创伤固着的时间之维在一定意义上凝缩、置换为空间之维。也就是说,只有当受创者置身于一个确切的地点或空间场域时,那个“不愿结疤的伤口”才会在当下被唤醒与显现。这正是作为创伤之地的“广岛”的特殊维系力之所在。
但吊诡的是,现时的“广岛”不仅成为故事主人公踱向各自创伤过往的地点触媒,还使他们在同一空间场域中产生了某种奇特的交集。最终这个日本男人在该女人“一生所经历的成千上万件事情中选择了内韦尔”[4]105,法国女人反过来也在该男人一生所经历的万千事情中选择了广岛。他们的爱欲和永不结疤的伤口在同一创伤之地(即“广岛—内韦尔”)上突破了惯常的指涉链条、线性的时间秩序的同时,也变而为一种由特定空间所建构的、亟待被言说的经验。这是为什么?
三、倾听沉默的伤口:从“我看见了”到“听我说”
影片里,法国女人和日本男人自始自终都沉溺在“看”的行为及其忠诚与否的自陈当中。故事开篇,女主人公诵诗般的话语便反复响起,她说,“我看见了一切。所有事物”;而男主人公则不停反驳道,“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无所见”。[6]15
在广岛,法国女人确信自己看到了当前所有现实。她说:她去了四次博物馆,看到了原子弹轰炸的种种物证;她去了空荡荡的和平广场,看到了和原子弹爆炸时温度相当的夺目阳光;她还看了报纸、新闻纪录片;最后看见了广岛又遍地鲜花、生命又从灰烬中复活。正因为毫无遗漏地看到所有这一切,女人说,她“始终在为广岛的命运而哭泣”。但男人不相信她在哭泣,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她的“胡编乱造”罢了。[4]23-26
在广岛,法国女人还坚信自己看见了过往爱情的幻觉。当她瞅着熟睡中的日本男人那只微微颤动的手时,却猛然间看见了德国恋人濒临死亡的躯体,这个躯体上的一只手正在无声地痉挛和抖动。通过“一只手”,法国女人从视觉上把日本男人置换为原先的德国恋人,同时也把广岛置换为原初的创伤之地内韦尔。
现时的广岛使她终于记起那个久被遗忘的伤口。她说,14年前,在德国恋人被射杀的那一天,她像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她疯了,突然大喊大叫,然后就被关进地下室。在历经了死人般的无知无觉之后,某一天,她听见了圣艾蒂安教堂的钟声。她的疯病突然好了,不再大喊大叫了,大家都说她变得有理智了。她确切记得,那天自己又“开始看见东西了”:她不仅“看见墨水”“看见白天”,还看见了自己“正在继续的生命”。[4]132
法国女人(也包括日本男人)所看见、所言说的一切始终以黑白画面呈现。在这里,失却色彩的视觉影像不仅仅从形式上意指一种特殊的摄制技术,而且还从内容上显明了“一段不能穿透/不能理解的过往”(an impenetrable past)[7]61。它最终指向了伤口本身不能被确切看见的空白,以及不能被确切言说的沉默。就像美国创伤理论研究专家凯茜·卡鲁斯反复强调的那样:创伤经验标划了一个理解的缺失之域,它无法被表意和指涉,不可被定义和框范,更不能被简单地缩减为任何理性的叙述与言说。因而,创伤经验只会是一种“未被认领/未被宣称的经验”。
借由对《广岛之恋》的解读,卡鲁斯认为,法国女人所言说的“看”实际上是“一种表面的知觉”(a literal perception)[8]32-35,它等同于惯常的理解或某些已然拥有的知识,而这恰恰背离了创伤经验“不可认领”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带来了对创伤现实的遗忘。当法国女人把自己的过往创痛转化为可以被看见、被理性叙述的故事而向日本男人进行倾诉时,她便不由得使自己的德国恋人遭致了“一种道德背叛”(a moral betrayal)[8]29。因为通过叙述,她遗忘了德国恋人之死这个独一无二的、不能被言说的事实。正如她自言自语道,“瞧,这件事是可以对别人(即日本恋人,引按)叙述的”,“我向别人讲述我们的故事”,但结果是“我今天晚上同这个陌生人一起欺骗了你(即德国恋人,引按)”。[4]151
讲述过程中,法国女人将日本男人全然当作自己的德国恋人,与此同时,她还逐渐分不清自己的躯体与死去的德国恋人的躯体。日本男人不由得掴了她一记耳光,这突如其来的介入与否定,使女人重获清醒,并将故事讲完。故事的最后,正值战争结束,原爆事件在法国女人眼中仅仅意味着战争结束了,意味着自己国家的胜利以及国民苦难的终止。卡鲁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结束”恰恰使广岛被遗忘了。因为“战争的结束”作为一个不甚起眼的“视觉指涉”,它从根本上抹煞了日本的过去,(即将其整合为法国历史的叙述),由此在道义上背叛、亵渎,甚至消弭了另一民族的创伤与历史。[8]33
然而,在广岛,在这座天生就适合恋爱的城市,法国女人注定要开始热烈呼唤她昔日的德国恋人,注定要敞开遗忘已久、沉默已久的历史伤口。通过此时无尽的交谈,她渴望将自己的故事倾诉给那个广岛男人,而她所欲诉说的东西也在无限迫切地等待倾听。置身于作为同一创伤之地的“广岛—内韦尔”,法国女人像克洛琳达①那般,敞开了“哭泣的伤口”,发出了“听我说”[6]22的深切召唤与请求。在广岛,法国女人面向“倾听”的言说姿态让“一种话语”[8]34成为可能。这种话语只有借助发生于广岛的相遇,只有诉诸“看”与“知”的中止,最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对沉默伤口的倾听,才能够进行言说。
综上所述,创伤之地凭借其特殊的媒介维系力,凝聚的终究是不能被充分整合为“叙述记忆”(即能付诸理性言说的记忆)[9]的创伤经验。所以,理想状态下,创伤之地只会是永远沉默的。但在广岛故事中,法国女人的言说姿态展现了另一种可能:即借由倾听本身对视觉指涉的反拨,创伤之地及其承载的伤口能够开始被触及、被穿透。这种通过倾听所召唤的新的言说经验,或许正是一种让两位主人公最终得以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经验。它不仅使言说者对倾听者发出询唤与邀请,而且也使他们以及他们各自所属的创伤之地必然地交叠在一起。
四、“广岛,我的名字”:创伤经验的诗性言说与地域表达
按照卡鲁斯的经典创伤理论,一方面,创伤经验不能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付诸理性叙述与言说,但另一方面,它在抵抗我们常熟的认知与理解的同时,又亟需我们去倾听与认领。对于创伤经验这样一种难以调和的表征危机,卡鲁斯显然还是乐观的,她认为,“不管创伤经验是出现在一个严格的文学文本中,还是出现在一个更具理论性的文本之中,它都不能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被发问,实际上,它必须以一种不知怎的总是文学化的语言(a language that is always somehow literary)——甚至像它宣称的那样,即一种抵抗我们的理解的语言(a language that defies our understanding)——来被言说”[8]5。
通过这一特殊的折中方案,我们知道:尽管卡鲁斯没有明确承认创伤经验可以被直接表征和认领,但她也没有否认创伤经验能被倾听和“言说”(区别于诉诸理性理解的言说)的可能性,以及文学本身间接担负见证之责的应然性。或可质言之,恰恰是文学话语使创伤经验传达出来。作为一个全然虚构的文本,《广岛之恋》正是以卡鲁斯视阈下极具诗性的(即感性的、想象性的)文学言说,将创伤经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地域表达,从而迂回地对创伤过往施行了认领与见证。
电影结尾处,法国女人和日本男人相互看着彼此,却又仿佛视而不见。她说,“广——岛。这是你的名字”;他答道,“这是我的名字。是的”。随着故事的推进,“广岛”这一称谓非但没有从对白中褪去自身确切的地点意指,而且还被法国女人用作人的名字赋予了日本男人。与之相应,通过日本恋人的赠予,法国女人的名字从此就是“内韦尔”,“法——国——的——内——韦——尔”。在这里,将“地名”作为“人名”相互赠予,应该是两位主人公的创伤经验在广岛产生奇特交集的、最耐人寻味的展现。
诚如《广岛之恋》标题的字面义(即“广岛,我的爱人”所示),“广岛”首先是法国女人发自肺腑的言说与呐喊,它询唤的是能够倾听内韦尔故事的“我的爱人”,即那个日本男人。②到故事最后,法国女人用“广岛”来命名日本恋人,说明她确指了那个使她转换了“看”的理性认知,而开启真正言说的倾听者(即一直在耐心聆听的日本男人,而不仅仅是那个抽象的“他”)。反过来,法国女人还承认自己被赋予的新名字是“内韦尔”,这实际上阐明了日本恋人倾听他者伤口的结果,即让她重新记起并认领了内韦尔的创伤过往。同理,日本男人通过“内韦尔”这一地名的赠予(也就是确指了倾听自己创伤经验的法国女人,而非那个抽象的“她”),也同时应承和接纳了自己被赋予的新名字“广岛”。可以说,“广岛/我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原初缺失的身份归属,使他重新认领了那段恰好被他错过的创伤记忆。由此,这个“长相有点西方化”③[4]213-214的、仅仅叫作“他”的日本男人,最终与“广岛”成为一体:“他”即“广岛”,“广岛”即“他”。
再有,从“你的名字”到“我的名字”,从“命名”到“接纳”,作为同一创伤之地的“广岛—内韦尔”展布为一种独有的“地域记忆”(place memory)[10]:经由占据着特定空间的创伤地点,故事主人公所遭致的创伤过往从时间维度中被凸显出来。“地域记忆”最终“转化记忆的时间性(记忆乃回溯过去的经验)成为空间性(回溯事件之所在),藉以给予记忆一个聚焦的处所,一个名字,以替换‘压抑’,包容记忆”。[11]至此,创伤经验的地域表达与空间建构已超出了个体精神层面的创伤固着,它明确地勾联起了个体记忆与地域记忆,乃至更为宏阔的灾难记忆和国族记忆。
关于影片故事对创伤经验的表征,雷乃特别强调:“我不喜欢使用‘闪回’这个词——于我而言,《广岛之恋》总是处于现时之中(always in the present)。”[8]123在他看来,广岛故事不能在可被确知的“过去”中,而只能在影片“现时”中生成与呈现。如果说,创伤之地将创伤经验的“时间性”转化为“空间性”的话,那么,“现时性”则进一步将这种筑基于“空间性”的创伤经验限定于当前的在场状态。而当创伤故事在现时银幕上进行展演时,能被观众领受的就并非原则上不可被宣称的创伤经验,相反,它会以现时为契机,对难以触及的伤口进行新的表征与言说。与其说,这是凭借现时的理性言说而叛离、抹煞了“过去”,毋宁说,这是以一种特殊的电影叙述方式提供了见证、并忠实于过往。但关键是:我们该如何阐释雷乃这种有意为之的电影言说策略?从法国“左岸派”坚执的创作信念来进行考量,也就不难理解了。
众所周知,“作家电影”的导演们一直“把电影视为文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12],并且把文学与电影的同构视作其创作的终极旨归。他们认为,电影拍摄本质上就是文学写作,这两者之间可以被赋予一种崭新且可行的关联。不仅如此,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这些导演还热衷于通过切身的创作实践,来展现人类无法避逃的创伤经验。比如,早在《广岛之恋》之前,也就是1955年,雷乃受法国二战委员会之托,摄制了一部叙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通过影片接连交替的彩色和黑白画面以及极富文学性的旁白,雷乃带领观众造访了被野草覆盖着的集中营遗址,并重新审视了这个“死亡工厂”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
对于广岛事件,雷乃却毅然拒绝将它拍摄为一部像《夜与雾》那样具有档案意义的纪录片。在他看来,当我们用银幕表征历史事实的时候,“任何电影都是一种虚构”[13]。他强调,《广岛之恋》惟有通过一个“不是关于广岛、但却在它的地点上发生的虚构故事”,才能使创伤事件及其历史特殊性得到“传递”[8]27。换言之,电影中的文学话语、特别是立足于虚构的文学话语,对雷乃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表征意义,因为它更能够向观众传达某种被纪实性档案隐没的感性体验。而且在电影的现时银屏上,这种虚构的文学叙述带来的往往不是创伤经验的逃逸,反而是该经验的另一种迂回的、但却忠实的展现。
回到《广岛之恋》中,我们不难发现,最打动观众的正是影片中现时呈现的,且诗一般的文学故事。当然,对于原爆事件的确切发生地,该诗性言说并不直接去呈现原初的伤口,它采取的是迂回的方式——即以虚构的文学叙述建构起同一创伤之地“广岛—内韦尔”——让两段不愿愈合的创伤过往保持现时在场。正是“广岛”勾连起了“我的爱人”与“我的名字”,那些曾被遗忘的创伤经验与历史记忆,终于从沉默的废墟中显现出来。
五、“卡萨布兰卡咖啡馆”:创伤经验的空间症候与历史意指
美国知名的电影理论研究者约书亚·赫希(Joshua Hirsch)认为,创伤与其说是一种经验内容,毋宁说是一种经验形式。因而,透过电影话语,创伤经验可以“从形式上”(formally)被表征出来,由此成为“一种出乎意料地看见不可想象之物的经验”(an experience of suddenly seeing the unthinkable)[7]185,亦即一种能被认领的经验。赫希的观点启发我们:作为特殊的媒介话语,电影可以有效地表征创伤。它不仅能赋予被搁置的创伤经验以形式上的可触及性和可再现性,而且也能赋予难以想象的历史真相以外部的症候与声音。
从影片《广岛之恋》来看,创伤经验的表征形式显然就是一种空间建构。它不仅在总体上表征为一个可以触摸的空间场域(即“广岛”),而且也具体呈现出一些细部的空间症候,比如,内韦尔的卢瓦尔河畔、地下室,广岛的和平广场、博物馆、旅馆的房间、碎石堆、火车站候车室等。其中,位于广岛的“卡萨布兰卡咖啡馆”显得尤为特别,因为它既是一个被架构起来的组合空间,同时也是对其他民族历史的一种隐微暗指。
细言之,卡萨布兰卡本是摩洛哥北部的港口城市。二战期间,它成为许多欧洲人逃离纳粹铁蹄、奔往美国的中转站。匈牙利电影导演迈克尔·柯蒂兹(Michael Curtiz)就曾以卡萨布兰卡作为背景,执导了同名电影《卡萨布兰卡》,它于1942年11月在美国上映后,便获得热烈反响,并膺获无数殊荣。同《广岛之恋》一样,该影片也虚构了一个具有鲜明历史意指的爱情故事。具言之,在卡萨布兰卡的“里克美式咖啡馆”里,老板里克借其经营咖啡馆之机,周转、接纳受纳粹拘禁的欧洲人。一日,里克的旧日情人伊尔莎携其丈夫维克多(一个反纳粹和法国维希政府的、地下抵抗运动领导人)也来到这里。几经择度之后,里克将自己仅有的两张通行证赠与了他们。在机场,他还开枪打死了企图追捕这对夫妇的纳粹上校,最后目送那架开往美国的飞机安全起航。
电影里,美国人里克无疑扮演着一个欧洲解放者的角色,尽管他有过挣扎与抉择,但他最终还是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创伤过往(即作为小我的爱情),而选择站在反纳粹同盟的阵线上。临行前,维克多对里克说道:“我现在知道了,我们这一边将会取得胜利。”[8]48在此,维克多所说的“胜利”不仅仅意指纳粹将会被击败的必然趋势,而且还强调了一种必然会到来的救赎允诺。就此叙事的逻辑而论,位于卡萨布兰卡的美式咖啡馆自然也就成为了“自由”和“胜利”的代名词。
但卡鲁斯认为,影片其实还隐藏着另一套政治逻辑和另一种历史真相,即美国人明显的“盲视”。她特别摘录了里克和黑人钢琴师山姆的对白,里克说道:“如果在卡萨布兰卡是1941年12月,那么在纽约是什么时候?……我打赌在纽约他们都睡了,我打赌在整个美国他们都睡了。”[8]48很显然,在这个咖啡馆里,里克的酒后醉语并没有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正面的解放者形象,而是对自己的祖国同胞进行了一番控诉。因为1941年的美国确实没有从睡梦中清醒,没有意识到转变外交政策的紧迫性。因而,该电影实际上就是以“卡萨布兰卡咖啡馆”这一空间症候,来敞开历史那缄默的另一面。
同样地,当“卡萨布兰卡咖啡馆”出现在《广岛之恋》时,它也通过影片对创伤经验的空间表征,而认领了另一番创伤现实与历史蕴意。值得注意的是,该影片呈现的“卡萨布兰卡咖啡馆”还是一个特殊的组合空间,④它由广岛一家“美式咖啡馆”和一家名叫“卡萨布兰卡”的夜总会同构而成。在影片的第四部分中,夜幕降临,日本男人和法国女人面对面坐在美式咖啡馆里,他鼓励她讲述了内韦尔的故事。当他得知对方的故事连自己的丈夫也不知道时,他站起身,当众抱住她,并欣喜若狂道:“只有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4]141两个人不在乎周围的眼光,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之中。而在影片的第五部分,夜将结束,法国女人漫无目的地走进卡萨布兰卡夜总会,独自坐在一张桌子前;日本男人也跟了进去,在她不远处坐下。一个陌生的日本男子走近法国女人,试图用笨拙而蹩脚的英语向她搭讪。
就前者“美式咖啡馆”而言,它纯然是一个无关旁人的密闭空间。因为倾听与言说使这两位主人公各自的创伤经验被认领:在这特定场所,女人记起了被遗忘的过往,男人则获得了确切的身份归属。由此,同里克的咖啡馆一样,广岛上的美式咖啡馆也向内汇聚了不同的个体受创者,使他们相互见证了彼此不愿面见、抑或故意掩埋的伤口。就后者“卡萨布兰卡夜总会”而言,它同样也是一个密闭空间。尽管置身其中的两位主人公彼此相隔,但他们通过一个陌生人、一种对他们来说可能都不甚熟悉的语言(即英语)勾连在一起,并变为一个沉默的共同体:在这空荡荡的夜总会中,原先的日本男人一直保持缄默,而法国女人也是如此,面对另一陌生男子的搭讪,她仅仅点头作答。卡鲁斯认为,“英语”在这里其实意指的是“一门遗忘的语言”,缘由就在于:虽然它力图在日本文化里拙劣地模仿美国文化的话语和声音,但对美国观众来说,它仅仅是一种“伪相似”(a false resemblance)[8]49。他们没办法真正触及他者的创伤之地和创伤经验,更没办法触及自身历史的另一面,并终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对广岛事件的遗忘。同里克对同胞的控诉一样,那个操着笨拙英语的日本男子恰恰将美国人的遗忘和盲视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别有深意的语言移植,“卡萨布兰卡夜总会”最终向外揭橥了隐匿已久、缄默已久的历史真相。
如上所言,从夜之将至到夜之将歇,从美式咖啡馆到卡萨布兰卡夜总会,影片《广岛之恋》以时间的推移,有意区分开了两个彼此独立、且彼此封闭的空间场所。它们不但据此与《卡萨布兰卡》展开了一场别致的跨时空对话,而且更是追随故事主人公在“广岛”必然进行的创伤漫游,将其内部的个体记忆和外部的整体历史指涉潜在地构筑为一个有机体。由此,借助影片中特殊的空间组构,“卡萨布兰卡咖啡馆”才完成了创伤经验的形式表征与历史意指,而这或许是卡鲁斯直接将它视作单一的空间症象时所不曾留意的地方。
六、结 语
概言之,《广岛之恋》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广岛”的爱情故事。杜拉斯和雷乃有意让两位主人公用简短而又极富文学性的对白贯穿影片始终,以此勾嵌出个体创伤背后那个更为宏阔的历史事件,及其浇筑的创伤经验和创伤记忆。但问题是,在虚构的文学故事中,在“广岛”这一确切且沉默的创伤之地中,以个体记忆关联起集体历史经验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再有,故事主人公“她”与“他”均表示对特定个体的强调,有“这一个”⑤的意味。就此而论,如果“私人故事总是把必然带有论证色彩的广岛故事压倒”[4]82-83,那么该如何调和个中的悖谬之处?
卡鲁斯反思道:“大众灾难”与“历史上不那么重要的个体损失”之间不可作“一种约减式的等同”(a reductive equation),抑或“一种类比或比喻”(an analogy or metaphor)。[8]124因为在她看来,所谓的“等同”“类比”与“比喻”,在惯常意义上只适用于能够进行清晰感知和理解的对象,这与创伤经验的本质特征恰好相违。为此,创伤经验间的关联抑或交叠就亟需另一种模式,它必须以特别的方式允诺不同的受创者之间相遇和交流的可能性,同时还能使其保持彼此的差异与独立。卡鲁斯认为,《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在某种意义上有对上述问题作过反思。但反思的结果是什么?创伤经验间的关联又是如何成为可能?卡鲁斯都没有在正文中做出明确回答。本文认为,从创伤经验的空间建构这一视角出发,或许可以厘清其中的部分困惑。
首先,“创伤之地”依凭其特殊的地点维系力,将过往事件的时间之维置换为空间之维,从而保持了伤口在现时的持久在场。其次,“创伤之地”在使对话者各自的伤口汇聚到一处的同时,也使他们具有了可以相互吸引、相互爱恋的必然关联。再次,只有选择面向“倾听”的话语姿态,受创者才能对沉默的伤口进行新的言说。在广岛故事中,具有空间意指的“地名”,以及在对话中被受创个体接纳的“人名”,两者可以被构建为创伤经验的同一体;它超越了个体自身的记忆,指向了更为广阔的地域记忆、灾难记忆乃至国族记忆。尤为重要的是,创伤经验只有借助文学的诗性言说,才能对过往创痛进行认领,才能将有别于档案纪实的感性体验传递给观众。最后,通过电影的形式表征,创伤经验可以被再造为一种能够看见不可想象之物的经验:即透过“广岛”和“卡萨布兰卡咖啡馆”,被隐匿的创伤现实与历史真相终于得以显明。
【注释】
① 在 《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弗洛伊德借用意大利著名诗人塔索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来说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强制性重复”现象(即病患被迫反复体验着本应被压抑至无意识深处的创伤经验)。故事中,主人公坦克雷德不自觉地重复刺杀他心爱的女人克洛琳达:第一次是在战斗中,坦克雷德误杀了伪装成敌军骑士的克洛琳达;第二次是在魔法森林中,坦克雷德手举宝剑劈向一棵大树,不料树干的创口却流出了鲜血,同时还传出了克洛琳达的哭泣声,原来是他恋人的灵魂恰好被囚禁在这棵树上。参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周珺,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第16-19页。
② 《广岛之恋》的法文标题是“Hiroshima mon amour”。其中,“amour”是一个阳性单数名词,它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即只能指那个日本男性恋人。相应的,该名词前面的主有形容词才用“mon”。由此,这个语句只能是法国女人所发出的言说。如果没有相应的文本语境,单单从英文标题“Hiroshima,my love”来看,则无法看出有这层含义。另外,“amour”及其对应的英译词“love”均有“爱”和“爱人”之意,在此选择翻译为“爱人”,缘由在于它含有“这一个”的意味,即只能指那个日本男人,译为“爱”略显空泛。
③ 杜拉斯在剧本的附录里指出,缩小两位主人公/演员的相貌差别是有意为之的。她和雷乃意图让这部“法国—日本电影”看上去是一部非“法国—日本电影”。因为“如果观众念念不忘这个有关一个日本男人和法国女人的故事,那么影片就不存在其深刻的意义”。换言之,杜拉斯和雷乃借由这个故事所欲传达的应是某种人类共有的经验和记忆,而不仅仅限于国族、文化的差别。
④ 卡鲁斯在分析过程中,仅仅把在广岛的“卡萨布兰卡咖啡馆” 当作单一的地点或空间。
⑤ “elle”和“lui”都是法语中的重读人称代词,强调的是特定的个体,在《广岛之恋》的英译本中,译者用的是大写的“SHE”和“HE”,它们都表示对“这一个”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