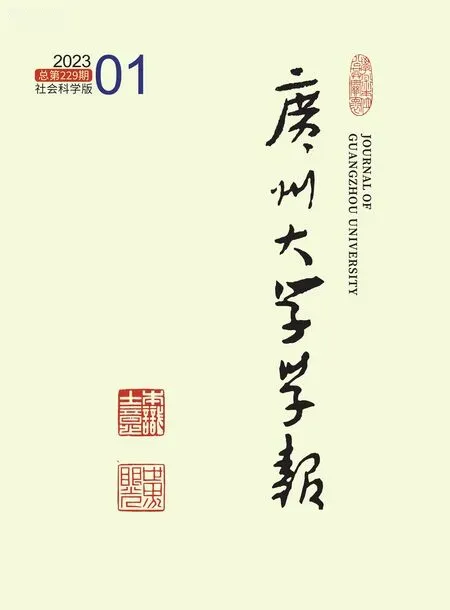“翻译中国”的文化政治
——从“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谈开去
周宣丰,闫培香
(广东药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012年,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译介学创始人谢天振先生提出翻译方向的变化是当前时代语境下发生在翻译领域中众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1]近两年,原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黄友义也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提出新时代语境下中国翻译使命发生了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历史性转向,中国翻译的主流方向也相应地出现了从“译入”到“译出”的大逆转。[2]翻译使命和主流翻译方向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是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亦是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虽然实践意义上,中国的翻译使命和翻译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但译学理念因深受传统翻译方向观念影响,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变化,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译界“对翻译的认识和科学定义要坚持发展观,要挣脱旧有概念所附的陈见桎梏,对学科基本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构建完整而开放的翻译知识形态,不断地走向理论独立与自觉”[3]。若不溯源纠偏、挣脱传统翻译方向观念的桎梏,置变化中的翻译方向现实于不顾;若不弄清楚“翻译中国”的主体之责、之能这些问题,对中国翻译研究者全面认知翻译行为的时代性和复杂性,对中国本土译者增强自觉与自信,对国家,特别是弱小民族国家正确认知扭转翻译方向的文化战略意义都是不利的。
一、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
(一)术语命名
在翻译研究中,翻译方向主要是针对译者而言的,指的是“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是从外语译入母语还是从母语译入外语”[4]。翻译规范论者基迪思·图里 (Gideon Toury)将译者译入母语的翻译命名为“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译者译出母语的翻译则是“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5]英语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逆向翻译”命名为“服务型翻译”。[6]52我国译界用“译入母语”来指称“直接翻译”,用“译出母语”来指称“逆向翻译”。[7]本文为了规避“直接翻译”“逆向翻译”术语背后潜在的意识形态之嫌,为了延续中国翻译术语传统,皆采用“译入母语”和“译出母语”之说。
(二) “译入母语”与“译出母语”的优劣之辩
中外翻译史上,两种方向的翻译实践除了在特定时间、特定区域有所侧重之外, 一直都是比肩前行,皆为常态,大量的“译出母语”翻译实践还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例如西方翻译史上,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西班牙托莱多翻译运动和意大利诺曼西西里翻译运动属于典型的“译出母语”翻译实践,对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翻译史上,千年佛经汉译亦是外来译者主导的“译出母语”翻译实践,对汉语和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很大。为什么翻译方向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有了优劣之辩并成为了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这得从民族—国家概念的兴起、语言民族主义观念的提出、民族中心主义的抬头以及翻译被纳入民族主义日程说起。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提出,语言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撒播,语言被视为民族国家建构和想象的重要构件,“语言往往成为民族政治诉求中的重要内容,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起着对内唤醒民族意识、凝聚民族向心力,对外同其他民族相区隔的重要作用”[8]。在这样的思潮和运动之下,以语言为媒介的翻译也被纳入了民族主义政治理念和运动日程。由于民族语言的对内向心力和对外区隔力,民族语言的主体地位日益提升,涉及到译入母语和译出母语的翻译方向就有了价值取向,优劣之辩也由此拉开序幕。德国宗教改革家和圣经翻译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翻译方向优劣之辩的首倡者。他在德国宗教改革的趋势下,基于民族语言的主体地位意识和强烈的受众意识,开启了将希伯来语《圣经》版翻译成德意志民族语言,并根据德语《圣经》版对德国宗教改革和民族语言统一以及文学发展等的效果,自证了“从外语译入母语方能令人满意,这样的译作才算得上真正的翻译”[9]110。
20世纪,正如著名民族问题研究专家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10],民族语言的社会政治力量和民族语言翻译的构建力量在20世纪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再加上英语取代昔日的国际性语言如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成为新的国际通用语之后,使得本就深受德国民族语言翻译观滋养的现代西方译界为了进一步凸显和巩固英语的地位以及英语母语译者的地位,将翻译方向的优劣之辩推上了高潮。他们基于“母语译者=优质的翻译质量”“非母语译者=劣质的翻译质量”命题,对“译入母语”和“译出母语”进行了真理/谬误之分,维护和抬高“译入母语”,将其视为翻译的黄金原则,排斥和贬低“译出母语”,将其视为翻译的“笑话”。早于1979年,路易斯·凯丽(Louis Kelly)在《真正的译员:西方翻译理论与实践史》一书中就提出从母语向非母语的翻译,除非要说明翻译的困难,否则不值得讨论。[9]111纽马克的言论更具代表性,他说:“从外语译为母语才能获得自然 、准确以及最大限度有效沟通的译文,如果目的语不是译者惯用的语言, 就没办法翻译好”,“虽然现实中的确有译者进行逆向翻译,只是徒增他人笑料而已”[6]3。同样,享誉美国译坛的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也强调翻译的目的语必须是译者的母语。[11]37如此强势的“译入母语原则”自然而然就成了以英语为主要工作语言的行业和机构的职业准则了。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要求“译者应该尽可能地译入他自己的母语或者译入他或她掌握母语一样的另一种语言”[12]。英国翻译工作者工会也规定切不可要求译者从本族语译成外语,因为译者的外语水平无论怎样高,决不会高过本人的母语水平。至于非欧美国家,长期以来一直被如此强势的“译入母语原则”翻译话语所支配和左右。哥本哈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翻译理论家道凯·勒拉普(Cay Dollerup)在英语语言霸权和强势的译入母语原则面前流露出强烈的自卑感,他说:“非母语译者要是相信能跟母语译者的英语水平一样是荒唐可笑的,我们掌握的英语永远不完美,因此我们不能译出好的译文。”[13]我国翻译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也很严重,长期以来对中国本土译者要不要、能不能“翻译中国” 举棋不定,对“译入”“译出”孰优孰劣持续争论不休。
当然,翻译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即便如此得势的“译入母语原则”也受到了挑战。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译入母语原则的规范性与译出母语实践的现实性之间存在冲突。全球本土化的持续推进催生了大量的双向文化交流和文化翻译,而母语译者人数,尤其是英语母语译者,远远满足不了其他民族语言文化译出的需求。因此,在非通用语言国家内,非母语译者“译出母语”就成为了一种“屡禁不止”的国际化现象。即便是在发起翻译方向优劣之辩的德国,尽管很多行业和权威机构反对译出母语翻译实践,但是译出母语翻译和译入母语翻译一样常见。 第二,英语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和谐共生、英语语言的国际通用功能和地方特色本土功能的互补互荣、全球非英语母语使用者对母语使用者人数的赶超及其英语语用能力的大大提升,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内圈/外圈、英语母语/非英语母语之间的二元等级结构。“北美人和英伦三岛人独霸英语文坛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有人会用英语写作”[14],既然如此,译入英语的所有权也不再是英语母语者的专属权了。在这样的语境下,主要来自非“内圈”英语和非英语国家的译者对“译入母语”的传统原则发起了声讨。 西班牙学者阿利森·毕比(Allison Beeby)为翻译理论家对译入母语翻译的过度关注和对译出母语翻译的极度冷落而鸣不平,并针对译出母语翻译的市场需求和特征而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教学法。[15]澳大利亚学者斯图尔特·坎贝尔(Stuart Campbell)揭露了英语在欧洲拓展中的殖民作用及英语翻译裹挟下的语言帝国主义。[16]斯洛文尼亚学者耐克·博康(Nike Pokorn)在《挑战传统原则——译入非母语》一书中瓦解了理想化本族语者双语、双文化能力的幻像,颠覆了翻译质量与译者身份的单一归因,提出了影响翻译质量的多元因素。例如,译者的个人能力、翻译策略、对源语语言与文化及所涉及领域的了解程度等等。[17]除了这些多语言、多种族国家之外,弱势文化国家如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国家、东亚三国也越来越重视译出母语的作用和翻译教学。 第三,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国际转向,翻译的概念、语境、领域和功能都得到了扩展。 越来越多具有学术反思和学术自觉精神的英语语言学者开始反思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英语中心主义。潜藏于“译入母语”传统原则背后的语言文化霸权、翻译话语权力、对他者语言文化的操控、生产他者知识的权力、维护文化等级结构等“野心”被揭露,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译出母语”翻译的文化抵抗性和自我赋权意义引起重视。例如,著名文化研究专家和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列斐弗尔(Andre Lefevere)指出,“译出母语”翻译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但处于边缘化的语言国家同样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译者试图要扭转以前诗歌翻译所造成的形象的扭曲。[17]35美国比较文学教授、翻译理论家玛丽亚·铁木志科 (Maria Tymoczko)指出,早期那些规定性的翻译话语没有任何益处。她认为这些提出者缺乏自省意识,他们把根植于欧洲语言和欧洲翻译史的地方化翻译知识视为具有普遍性的翻译理论, 这些规定性翻译话语受制于话语提出者的信仰、行为和意识形态。[18]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茨勒(Edwin Genztler)挑战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欧洲中心”和“英语中心”思维方式。他认为翻译的语境需要扩大,过去的翻译研究和产生的翻译话语主要基于欧洲的翻译现象、翻译经验和翻译传统,当下应该多关注非欧洲和少数族裔的翻译经验和传统。而且,翻译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并非只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转换,还关涉到知识的生产、语言文化的生态发展、文化身份形象的建构和民族文化的记忆和存活。[19]这些翻译研究的自省为“译出母语”的正名和扬名提供了契机。“译出母语”对于弱势或者非通用语言文化国家来说具有自我赋权和文化抵抗等多重意义。
二、“翻译中国”的优劣之辩:西方声音和中国声音
中国翻译历史悠长,历经多次翻译高潮,既有“翻译世界”,亦有“翻译中国”。在不同历史阶段,无论是“翻译世界”还是“翻译中国”,翻译之舟联通着中国与世界。从时间上来说,根据马祖毅的研究,“翻译中国”可以追溯到中国南北朝的北魏时期,其标志性事件为汉文佛教典籍的梵文和突厥文翻译,但当时主要局限于在东方内的交流和传播。[20]从翻译主体上来说,“翻译中国”的主体主要包括外来译者和中国本土译者。外来译者翻译中国始于明末清初的传教士,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成为翻译中国的绝对主体。中国本土译者翻译中国始于唐朝的玄奘,他率先将《老子》译介到了异域。因此,从翻译方向来说,外来译者“翻译中国”的翻译实践属于“译入母语”,中国本土学者“翻译中国”的翻译实践属于“译出母语”。
(一)西方声音:“翻译中国”的歧视之音
“翻译中国”, 如同 “翻译世界”一样,本应都是“经世之伟业,不朽之盛世”[21],因为,“他者”是“自我”身份构建过程中缺一不可的构件。据翻译史记载表明,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翻译中国”之伟业一直由外国译者主导,中国本土译者缺失。也就是说,“翻译中国”的主流方向是“译入母语”翻译实践。 罗列和穆雷道出了其中缘由: “主流中国知识分子从未将学习他族语言和文化作为己任,因而主要翻译活动在语言和文化技能上都倚重外来译者并不奇怪”,“没有形成培养本土外语人才的传统,更少有从本土知识分子中产生有影响力的译者”[22]。“译入母语”翻译实践,如前所言是西方译界的黄金原则。但关键是,外来译者,尤其是传教士外来译者,在中西经济、政治、语言、文化势差严重失衡的历史语境中,在认知、阐释和翻译中国方面虽然有得天独厚的目的语优势,但因受源语语言文化的理解度、译者文化身份和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等多方面影响,他们体现出非常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法国传教士雅克·布罗斯(Jacques Brosse)在《发现中国》一书中指出,传教士作为“发现”中国的主体,对中国的描述充满了误解和扭曲,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文化形象和文化身份的呈现和建构。[23]例如,美国早期传教士汉学家塞缪尔·卫三畏(Samuel Williams)将中国定位为“现存异教国家中最文明的国家”,即便后来他想纠正19 世纪以来西方对于中国的轻蔑与无知,“但他没有从当时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中解放出来, 他确信, 虽然中国绝不是未开化的国家, 但中国在文明程度上要落后于基督教国家”[24]。深陷“西强我弱”跨文化结构关系中的“译出”与“译入”, 西方翻译中国的翻译话语也被镀上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虽然西方的中国态度随着自身文化变迁而有所变化,但早期西方建构的中国观作为背景知识对后期汉学家的翻译中国话语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从他们的翻译中国话语中可以窥见一二。20世纪50、60年代的英国汉学家、《晚唐诗选》的译者亚瑟·葛瑞汉(Arthur Graham)毫不隐讳地说:“……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7]曾在中国外文局工作并翻译过《西游记》《鲁迅诗选》《中国现代小说选》《丁玲小说选》等作品的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威廉·詹纳尔(Wiliam Jenner)断言道:“中国译者的不足之处倒也显得无可厚非,毕竟,这份工作本来应该是我们英语国家的人来做的。”[25]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歧视之音并未消减。美国汉学界的翘楚和公认的领军人物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这样评价由中国政府资助并由中国本土译者翻译出版的英文版大中华文库系列丛书:
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作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资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26]
瑞典学院院士、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对中国本土译者的“译出”更是语出惊人:
一个中国人, 无论他的英文多么好, 都不应该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 要把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 需要一个英国人, 文学修养很高的一个英国人, 他通晓自己的母语, 知道怎么更好地表达。 现在出版社用的是一些学外语的中国人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 这个糟糕极了。 翻得不好, 就把小说给“谋杀”了。[27]
(二)中国声音:从无声到有声
面对西方用“译入母语” 传统原则来规约、评论翻译中国的“译出母语”实践, 中国译界在21世纪之前的态度基本是集体“无声”,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在实践层面上,如前提及过,自近代以来,东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从未真正平等过。而且,由于华夏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作怪以及本土译者“舍人”的不堪地位,中国人学习外语缺乏外在环境和内在动机,故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懂外语者寥寥无几。虽然曾一度出现过能与外来译者相匹敌的本土译者玄奘,但翻译世界和翻译中国的主力军一直都是外来译者。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文化和占绝对主体地位的外来译者,面对外来译者对“译入母语”原则双重标准化(他们一方面高呼“译入母语”原则,将母语译者与上乘的翻译质量等同,对他们“译入”中无意还是有意的翻译错误选择性的不见,对“译出”翻译实践进行污名化,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事着大量的“译出”实践),处于边缘地位的有着文化自卑情结的中国译界缺乏逆流而译的语言和文化资本。另外,历史上,中国本土译者主导的“译出”翻译实践的失败案例一方面作为反例验证了“译入母语 ”原则的正确性、“译出母语”原则的荒谬性,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挫伤了原本就自卑的中国本土译者从事文化外译的自信和自觉。即便有少许成功“译出”翻译案例,中国的英译作品也局限在汉学家和把文学文本当作社会科学档案一样的文学评论家中传阅。由于受限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加上文化傲慢心理作怪,即便是强势文化在某个时代受过外来文化的滋养,也会努力营造出不假外求的形象。如此,中国本土译者的“译出”翻译功能和地位又怎不会被故意贬低和“隐身”呢?
其次,理论层面上,中国的翻译理论话语严重西方化。翻译话语作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层级性概念,包括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都属于翻译话语,而且,翻译话语强调权力和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28]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译界一直在引进、阐释和整理西方的翻译话语,虽然一直在展望和建设中国本土化翻译理论话语,但“影响的焦虑”挥之不去。因此,即便“译入母语”原则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即便中国翻译传统中“以母语为译入语不是个常规”,即便中国本土译者“译出母语”是既成已久的翻译事实,西方译界“译入”/“译出 ”的优劣之辩对中国译界“翻译中国”的“译入”与“译出”观以及中国翻译史书写观还是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译出”翻译不入西方译界法眼,即便为“东学西渐”的开启和推进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陈季同,在《中国翻译简史》(1997)、《中国翻译史》(2006) 、《中国翻译词典》 (1998)、 《中国翻译家词典》(1998)和 《译学大词典》 (2001)等著作中也被集体“静默”和“遗忘”。[29]
可喜的是,在21世纪, 中国译界对西方“翻译中国”的歧视之音发出了抗议之声,这源于以下因素。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及世界新格局的形成,英语世界了解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多,中国与英语世界互动交流的诉求也越来越强烈。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外合力驱动催生了大量的“译出英语”需求,而能向英语世界翻译中国的、愿向英语世界翻译中国的英语母语译者人数远远满足不了这一需求。而自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国家翻译能力不断攀升。2021年,我国国家翻译能力仅落后于美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这都为新时代语境下中国本土译者“翻译中国”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国际化转向和本土化转向的趋势下, 越来越多的中国译界学者意识到基于当下中国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重建中国本土翻译理论越来越重要。因此, 以潘文国、龙明慧为代表的众多学者质疑了“译入母语”传统原则的不合理性和翻译方向中的民族中心主义,分析了海外汉学家,特别是传教士汉学家翻译中国的历史局限性以及本土译者肩负“翻译中国”责任和使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三、新时代语境下“译出”中国的自我赋权和文化抵抗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方向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尤为凸显。语言文化的流向、国际翻译市场中译入/译出的占比都与译入国与译出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息息相关。越是强势的语言文化,操控翻译方向的话语权越大,译出本族文化比例越高,译入他族文化比例就越低;越是弱势的语言文化,操控翻译方向的话语权越小,译入他族文化比例越高,译出本族文化比例就越低。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索引”数据库的统计显示,全世界每年有8万多本译自200多种语言的译著。其中,处于“超中心位置”的强势语言英语,译出比例高达50%-60%,而译入比例却只有2%-4%。处于中心地位的德语和法语在全球翻译市场中的译出占比为10%,译入比例为12%-18%。处于半中心位置的7、8种语言,例如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等,译出比例为1%-3%,而译入比例为20%以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中文、日语和阿拉伯语译出比例低到不足1%,而译入比例却高达30%。[30]中国译入与译出的比例在整个20世纪存在巨大的落差。 “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 800 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不是古代典籍)仅仅近千册。”[31]即便是21世纪的当下,中西文化贸易的逆差和各自在国际上的接受度和影响力逆差依然很大,中国声音还是太弱小。
韦努蒂曾指出:“翻译中的每一个步骤——从译语材料的选择,到翻译活动的进行——都受到浸润在译入语环境中的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制衡与调节,通常情况下,还会出现等级秩序。”[11]95深陷势差结构的翻译方向并非只引发翻译逆差等经济问题,更须警醒的是强势文化在操控翻译方向之余还通过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翻译叙事等途径操控着弱势民族文化的书写权力。这于弱势民族的文化安全、文化形象、文化软实力以及语言文化生态文明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 因此,纠正翻译方向的传统认知,反思、打破“译入母语”翻译的霸权局面,赋予“译出母语”翻译合法性地位,自主译出民族文化对于弱势民族文化来说至关重要。当然,这需要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秉着文化互补、平等交流的文化心态才能合力改变翻译流向的失衡局面,才能借翻译之舟,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于强势文化而言,首先须坚守翻译的“初心”,自省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英语中心主义,以“了解之同情”阐释和表述其他民族语言文化最为关键。翻译的“初心”和使命本是一种平等的文化交流、客观的文化生产和美好的异文化学习经验。虽然自我文化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阐释都是基于“前理解”和“先见”之上的,虽然“前理解”不可避免, 但“不能把前理解非历史化(从来如此)、本质化(一成不变)、神秘化(无法解释)或自然化(不可反思)”[32]。 在清理先见、先知之后,以“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了解”之心,摒弃“牵强阐释”和“强制阐释”,才能构建一种理想的“和而不同”的翻译话语模式。其次,强势语言文化,特别是处于超中心位置的英语语言文化须反思“译入英语”传统原则中的语言文化霸权和在“译入英语”翻译实践中出现的种种翻译暴力,须意识到“译出英语”翻译实践对弱势语言文化、非通用语言国家的文化政治性意义,让两种方向的翻译合力推动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动交流。
当然,更为关键的还是弱势语言文化自身的意识和行动。首先弱势文化要有自觉意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全球化语境中在面对英美语言文化的超中心地位和霸权时,弱势文化须突破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克服文化自卑,建立民族文化认同意识。与此同时,弱势文化学术共同体须警惕西方中心主义在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中的“移植”,基于本土文化立场建设本土理论话语体系,努力改变本土理论话语的隐身、边缘或者失语状态。就翻译方向而言,“译入母语”/“ 译出母语”之间的真理/谬误之分是以权力为基础的话语实践。因此,弱势文化不能受其左右,不能在言说自我的“译出”上举棋不定,当然也不能置“译入母语”翻译的优势和“译出母语”翻译的问题和困境而不顾。毕竟,“翻译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译入’与‘译出’并不是同一回事,把文化从弱势文化国家和民族向强势国家和民族译介更是涉及一系列特别的因素制约”[33]。于中国而言,我们要意识到相比20世纪的“翻译世界”而言,新时代“翻译中国”的目的取向、基本特征和翻译行为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翻译中国”从以前的无足轻重变为当下的举足轻重了。“翻译中国”是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外国正确理解中国、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经之路。为此,中国译界须将翻译研究的中心从“译入”转向“译出”,须以“译出”翻译活动为基础,基于中国当下翻译实践和国家重大文化政策开拓翻译研究新方向、形成新的翻译传播理念,再反过来认识和指导新时代“翻译中国”实践。 因为“简单地用建立在‘译入’翻译实践基础上的翻译理论(更遑论经验) 来指导当今的中国文学、 文化‘走出去’的‘译出’翻译实践, 那就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34]。毕竟文化外译不能简单归结为语言文化转换,相反是“一个与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传播的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密切相关的问题”[35]。其次,除了树立科学发展的翻译观念和建构本土的“译出”翻译理论之外,还需通过翻译教学、培训等多途径不断建设“译出”中国能力。 因为民族文化真正要独立,除了在特定历史阶段靠“拿来”和依靠外来译者“送出”之外,关键还得靠自己有能力“送出”。东西方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变迁和盛衰消长规律证明了东西方只有秉承文化互补和平等交流的观念才是正确的,[36]“‘全取’或‘全弃’都是中西文化交流不成熟的反映”[37]。鉴此,“译入”与“译出”的双向流动对于任何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来说都是必要和可能的。至于谁主谁次或者均衡发展取决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和民族文化主体意识。以“翻译世界”为主的中国近代翻译史是特定中西失衡的文化结构关系的产物,以“翻译中国”为主的中国当代翻译也是新时期世界文化格局变化和中国意识觉醒的使然。 因此,新时代的“翻译中国”相比西方霸道的文化格局而言有更好的传播环境,西方主动“译入”中国的态势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当然,相对于巨大的“译出”需求以及真实、立体、全面翻译中国的使命而言,挑战依然严峻。“外国译者数量少,外译者且存在错译、歪译、恶译等现象”[38],被西方译者主动译入的作家作品往往集中体现出“异质”“政治敏感”两大特征。[39]既然这样,中国本土译者主动担“翻译中国”之责是新时代的要求。近现代林语堂、许渊冲等成功的“译出”翻译以及全球国家翻译能力中国排行第二也都说明了中国本土译者(个人意义上和集体意义上)能堪以重任。基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之上,由中国本土译者主导的“翻译中国”是一种自我赋权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输出变被动为主动,自我形象变“他塑”为“自塑”,他者代言变自我发声。只有这样,文化话语权的获取、文化形象的纠偏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才能成为可能。 同时,中国本土译者“翻译中国”也是一种文化抵抗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能抵制强势语言文化(尤其是英语语言文化)霸权,消解强势语言书写和叙述弱势语言的专权。
在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语境下, 原本价值无涉的翻译方向却有了优劣之辩,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浓厚。“译入母语”原则的真理性和优质性,“译出母语”原则的荒谬性和劣质性,折射出了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英语语言文化霸权意识。西方“翻译中国”的歧视话语以及中国译界面对这些歧视话语的抗议之声也透视了中西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变化,是翻译方向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真实写照。新时代语境下,随着中国翻译使命从“翻译世界”向“翻译中国”的历史性转向,随着中国翻译主流方向从“译入”向“译出”的转变,随着中国本土译者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的觉醒,随着国家翻译能力和对外传播能力的提升,具有自我赋权和文化政治抵抗性的“译出母语”翻译更具时代战略意义。为了推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世界文化格局的健康发展,重构中国真实形象,中国本土译者须以“绵绵用力、久久之功”主动承担“翻译中国”这一伟大的、意义深远的文化政治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