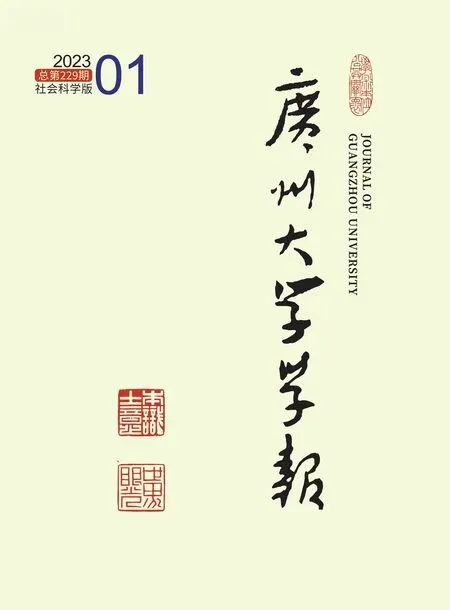历史、当代与经验:“公共阐释论”的方法论视域
孙士聪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论”,中国阐释学建构走过十年历程,十年间引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反思、批判与建设。2022年,张江先生新作《公共阐释论》试图进一步深思“阐释何以公共;阐释的公共性如何实现;阐释学意义的公共空间、公共理性如何界定;如何坚持阐释自觉,提升阐释水准”[1]等核心命题,标识中国阐释学建构进入新阶段,愈发清晰地呈现出异于西方阐释学的浓郁本土气质、中国气派。就西方阐释学而言,从方法论到认识论、再到存在论、最后回归方法论,被认为大体构成了其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其间经历了包括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的方法论阐释学到认识论阐释学转向、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从认识论阐释学到存在论阐释学转向、以哈贝马斯和利科为代表的从存在论阐释学到方法论阐释学转向在内的三次转向。[2]毋庸讳言,对中国阐释学进行更加从容的历史回顾尚有待进一步展开,但十年前“强制阐释”命题提出伊始,就已然标识出中国阐释学当代思考的强烈问题意识、鲜明本土气质、坚定批判立场,而关于阐释学方法论、认识论、存在论的讨论则贯穿始终。随着《公共阐释论》的发表,初步回顾中国阐释学十年行程,反思其方法论,深思诸方面努力,抽绎总结其当代建构的本土性中国性,当非无根游谈,或如张江所言,“学习借鉴西方,但不是用西方阐释学的已有框架来裁剪或规制中国阐释学经验和思想;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提取和改造中国传统阐释学资源,从本体论到方法论,提出和建构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命题,以至完备的体系”[3],而方法论问题被列为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阐释学所面临的六大难题之一。
一、本体论抑或方法论
对于中国当代阐释学建构的回顾,有必要越过这十年、乃至越过新世纪二十年而延伸至新时期。事实上,公共阐释论当代思考尽管肇始于新世纪,但其致思逻辑则可追溯至20世纪中国现代文论建构,这里将反思边界延伸至新时期,则是指向20世纪80年代所谓“方法论年”。将1983年、1984年称为文学研究“观念论年”“方法论年”,回溯来看似乎多少显得有些小题大做,尤其是那种颇为自信地将包括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在内的研究方法径直挪用至文学研究领域,尽管在当时推出诸多颇具突破性研究成果,但终归难免削足适履之嫌。然而这一“后见”却无疑是割裂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抽空了彼时彼地的具体性而难免超拔于理论抽象之中。文学研究方法在借鉴中外文论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取得突破和创新,有力推动了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拓展和更新。时过境迁,如若从强制阐释论问题域的开启来看公共阐释论思想视域的当下拓展,四十年前的学术努力中未必不是早已播下批判性重思的种子,具体到西方现代阐释学在中国的接受与研究,则可以用本体论阐释学与方法论阐释学案例稍作讨论。
在当代本土学界关于西方阐释学理论知识图谱中,存在一幅由主要西方古典语文学、古典阐释学、狄尔泰与施莱尔马赫传统阐释学、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构成的西方阐释学知识地图,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在这幅阐释学地图中占据突出的位置。从历时性角度看,阐释学地图中又蜿蜒着一条西方古典语文学、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本体论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对于青年学子而言,本体论阐释学可谓耳熟能详。然而,上述西方阐释学基本知识地图中,却存在着忽视方法论阐释学的知识论盲区,在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浓重阴影下,贝蒂为代表的方法论阐释学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单从本土学界对于伽达默尔与贝蒂阐释学的接受来看,1963年《哲学译丛》中就出现了伽达默尔的名字,迟至20世纪90年代,以洪汉鼎《真理与方法》全译本与夏镇平、宋建平合译《哲学解释学》为代表,标志着本体论阐释学真正研究的开始。而贝蒂进入本土学界视野,则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余英时1981 年的文章《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以及张汝伦出版于1987 年的《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始有论及,至新世纪初,洪汉鼎先生《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一书探讨了贝蒂与伽达默尔的阐释学论争,方法论阐释学和本体论阐释学被归结为两种相互对立的阐释学立场。相对而言,在本土接受与研究中方法论阐释学相较于本体论阐释学明显处于边缘弱势位置。然而,就阐释学理论创造与知识生产而言,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却是早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一般认为贝蒂方法论阐释学与伽达默尔本体论阐释学都建构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贝蒂《解释的一般理论》出版于1955 年,而伽达默尔出版《真理与方法》则迟至1960 年。[4]依朱立元先生之见,当代中国文论对于西方阐释学资源的译介与接受具有鲜明的选择性,在狄尔泰传统阐释学之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所代表的哲学本体论阐释相较于贝蒂“作为精神科学一般的方法论的诠释学”,前者更显西方学术的主流话语,占有强势地位,而后者则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这种西方学术历史状况与基本情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文论偏重于接受前者而忽视后者的理论格局”[5]。而进一步琢磨则可以发现,本土接受与选择中的主体性、主动性无疑也是造成上述格局的重要因素,这种主体性、主动性深深扎根于20世纪后30年社会文化土壤与具体情势之中。比如,钱中文先生在新世纪之交就明确判断中西文论发展存在“三个错位”[6],而高建平先生则在回顾70年文论建设时提出当代本土文论建设中贯穿性的理论资源层次性问题以及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循环问题。[7]
贝蒂方法论阐释学与伽达默尔本体论阐释学作为阐释学两条进路,既对立分歧又相通共通,为西方阐释学知识图谱建构出面目各异的阐释学理论景观。相对而言,贝蒂在阐释类型、阐释有效性标准等诸方面更侧重于发展延伸西方阐释学的方法论传统,同时又与伽达默尔分享了真理性追求。本体阐释学与方法论阐释学在本土学界的基本境遇,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观察公共阐释论方法论视域的症候,要点有三:一是历史性语境规导,二是主体性理论诉求,三是普适性话语指向。无论是阐释学方法论抑或阐释学本体论路径,理论思考本身需面对既定学术实践历史性语境,开辟走向特定理论建构鹄的,试图在公共理性边界内展开可公度的有效阐释,因而阐释路径本身并非先在的、绝对的。事实上,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纲》,从《再论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方法论抑或本体论问题就一直在强制阐释论、公共阐释论讨论过程中如影随形。代表性观点有三:一是强调辩证认识并超越阐释认识论与本体论,厘清其有效性边界,超越其限度而敞开阐释方法论“视域融合”空间,实现理论的螺旋式上升;二是强调无论何种范式或方法,归结到阐释规则上则是服从于阐释的说服力、可交流性与可接受性原则,协商性是解决所有阐释规则冲突确凿无疑的最有效路径;三是在目前四种阐释模式中,相较于以艾柯为代表的小说家阐释模式、罗蒂为代表的哲学家阐释模式、卡勒为代表的批评家阐释模式、张江所代表的理论家阐释模式,致力于倡导伸张公共阐释之阐释权力,是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张目。[8-11]这些思考不无深刻,而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的方法论视域,在过去十年致思行程中不断拓展变化,其方法论新质则尚有待进一步深究。
二、辉格阐释与库恩的困惑
早在2014年,张江先生在《强制阐释论》一文中,指认强制阐释四大特征,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这一“问题式”诊断,不仅内在地呈现出面对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元素”,而且逻辑地开启建构本土阐释学的方法论视域;而至于公共阐释,张江先生则给出简明界定:“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1]诸如普遍历史前提、基点、对象、公共理性、边界、可公度、有效等范畴,无疑兼具公共阐释内涵厘清与公共阐释论方法论指引,个中诸如历史、生产、理性、普遍之谓,恰与强制阐释论四大特征一正一反相对、方法论视域一以贯之,而在方法论与本体论关系层面,张江先生坚持中国阐释学建构上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而“方法论优先”“为重”[3],在此前提下则可进一步讨论方法论视域中所谓辉格阐释与反辉格阐释的两种范式,为进一步考察公共阐释论方法论视域廓清地基。
辉格阐释范畴可追溯至19世纪英国历史阐释中的“辉格史学”,其核心在于论证辉格党政治理念不断进步的历史性,英国学者巴特菲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将“辉格史学”拓展为普遍性阐释模式,由此,辉格阐释越出了历史学、政治学研究领域。巴特菲尔德概括辉格阐释要义为三:一是进步论,二是目的论,三是简单化。辉格阐释学“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这样就有了一个非常简便的经验法则,历史学家可以据此进行选择、拒绝或强调。依照这样的参照系,历史学家必然会认为他的工作要求他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关注相异之处。从而,他会很容易地说从过去中看到现在。”[12]10辉格阐释的结果则是“把一种特定的形式强加于整个历史情节之上,并且产生一个表现整个历史必然美好地汇聚到今日的通史图式。所有的一切都显示了数个世代以来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原则在起作用”[12]11。巴特菲尔德批判辉格式阐释沉迷于因果链条之中、勾画过去必然走向当下的进步史,而事实上,如此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并不存在,“我们对事件发生过程的考察越深入,我们就越从简单走向复杂。……我们才能认识到,那些当我们回望时显得自然而简单的、走向当代的、进步式的历史变迁,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12]15-16;对于历史与传统的回眸,其价值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时的那种丰富性”[8]41;所有的理解与判断都只能相对于实践和情境而存在,“真正的历史理解与其说是通过使过去从属于现在而达成的,不如说是通过把过去变成我们的现在或者通过另一个时代的眼睛去看生活来完成的”[12]13。显然,巴特菲尔德认为辉格阐释并非局限于辉格党人的历史学研究,而是具有某种理论范式意味。
与巴特菲尔德对辉格阐释的批判路径不同,托马斯·库恩的批判源自他自己的现实困惑。库恩自言在1947年研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时注意到,亚里士多德谈论起物理学经常会出现一些根本性的错误,但如果涉及物理学以外的领域,却往往表现出很好的观察力与洞察力,能给出深刻、透彻的解释。这让库恩大惑不解,亚里士多德如此出众的才能“为什么一旦用到运动问题上就一败涂地呢?他怎么会对运动发表那么多明显荒谬的论点呢?而且最重要的,对这种观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后继者那么长久地认真对待呢?我读得愈多,就愈感困惑。亚里士多德当然会犯错误,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怎么能想象他会错得那么显眼呢”[13]Ⅲ?库恩回忆说,有一天他突然领悟到,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思考之所以凸显荒谬,并非源于亚里士多德而是源于不合理的“阅读方式”:在彼时科学语境中,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思考虽然面临重重困难却可以理解,而在牛顿物理学框架中就突显错误而荒谬了。由库恩思路则可以推论,文本自身具有阐释可塑性,文本阐释具有方式多元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阐释就不能是在牛顿物理学框架内、也无法适用于牛顿物理学话语,而应回到亚里士多德时代语境,并且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思考。库恩对于辉格阐释的批判直指知识线性进步论、累积论、因果论,如果说辉格阐释执着于以今论古,而库恩则强调以古论古;而由此进一步提出的范式论则更是直指传统知识生产与理论创造上的连续性,而力主一种新旧范式不断革命、不断更迭的断裂性。
相对而言,面对辉格阐释的进步论、目的论倾向,反辉格阐释的巴特菲尔德与库恩给出不尽相同的批判路径与理论进路。比如,前者强调复杂性,后者则用范式革命予以简化;前者关注历史经验丰富性,后者则径直越过价值领域而进入事实领域;前者立足历史当代化,后者则力主当代历史化;同时二者又分享了进步论、目的论的批判。当然,库恩范式论在当代学界所受关注程度远超过巴特菲尔德辉格阐释批判,而对于原发于自然科学的库恩范式论不同程度遮蔽人文学术传统传承性、累积性也值得警惕,由此再回到关于公共阐释范畴、命题、图式、体系建构,则可以在方法论视域中进一步思考新范式、新范畴、新命题取代旧范式、旧范畴、旧命题时的断裂性与累积性,以及价值领域与事实领域、当代性与历史性、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等诸关系辩证问题。
三、思想与经验
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面临的六大难题:“一、基础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重在方法论还是本体论;三、与语言文字学研究之关系;四、多学科交叉与相融;五、理论的实践与应用;六、形态的系统和完备性。其中的核心和要害是,中国学术传统中虽无阐释学的概念和学科,但有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3]这一段文字至为紧要,六大难题之指认明确托出中国阐释学当代致思的问题框架,而将中国学术传统中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视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构建的可靠资源和坚实基础,并断言此为理解六大难题之核心与要害,更为意味深长。事实上,从2017年至2022年六年间对于公共阐释论建构中“理”与“性”、“阐”与“诠”、“解”与“释”、“衍”与“生”、“通”与“达”以及训诂与阐释等系列核心范畴的深刻辨析[14-19],已然勾画出日益清晰的逻辑路线;而指认中国学术传统中丰富的阐释学思想和经验为要害,则通向“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方法论优先”之断言,或如巴特菲尔德所言过去生活的“丰富性”。在此,面对传统阐释学经验的两种阐释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对于他者性的热情,其要害在于自洽的话语逻辑遮蔽丰富的阐释经验;二是对于普遍性的恐惧,其要害在于坚守某种特质而画地为牢、怯于追求普遍性、世界性。公共阐释论则显然与此不同,比如对于“生产公共观念”来说,“其实现过程是,进入阐释空间的独立意识主体、同类质的精神共同体、各类不同形式的意识客观化载体,以其独有的思想观念与意志情感,大范围地向外展开,并以相互之间的抵抗、博弈、交融,获取不断扩大的观念共识与情感共鸣,生产新的可靠知识,推进人类精神进步”[1]。在这一具体实现过程中,共同创造新的可靠知识、推进人类精神进步,无疑体现出世界性、普遍性理论指归,而思想观念与意志情感的外展、互动则指向传统阐释经验的丰富性、生动性。
在中国阐释学当代建构的方法论视域中,历史、当代、经验似可视为其重要方法论要素,这在张江先生对中国阐释学当代建构规划中有明确表述:“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照、选择、确义,由概念起,而范畴、而命题、而图式,以至体系,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建立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15]首先,当代不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中介,也不是走向未来的一个过渡与环节,毋宁说因其所具有空间性而成为结构化的历史架构,因而面对中国传统阐释学也就不会执着于将古人现代化,正如以西方阐释中国早已成为强制阐释论的批判对象,以现代阐释过去也正是公共阐释论批判之鹄的,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拓宽了反辉格阐释的方法论视野。其次,当代中国阐释学之“当代”一词,逻辑地包含对于中国阐释学的前提性预设以及对其历史形态的追问,与库恩范式论框架下的理性不可通约性不同,当代中国阐释学“不仅需要绕道西方进入中国,更需要绕道历史进入现代”,而中国阐释学开放性的传统也将成为最具活力的资源,[20]这就意味着中西阐释学已为既可通约又各各不同的阐释学范式。再次,中国阐释学的实际建构必须立足中国传统阐释学经验,进而使之被广泛接受和应用,才有现实存在的可能与意义,因而在当代阐释学建构视野中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内在统一的,统一于丰富生动的阐释经验之中。以汉语中“在”为例,“在”意指特定形态的具体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存在之状态,或可径直理解为一种“去—在”。在这一理解结构中,对象敞开自身而不是封闭自身,主体则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对象,尽管对象之待走进以及走进本身都已先在地被意识到。甲骨卜辞中的“在”类“才”,字为象形,形状“草木初生”,意即草木从地面冒芽而出。草木生长、新陈代谢,初生无疑是草木生命历程活力迸发的一个阶段,因而“在”所描摹的,不仅是初生草木的形与态,而且呈现出其形其态的发展变化。于草木而言,生命如其所是的展开,而于人而言,初字则包含了某种惊奇意味,初生也是初见,“在”字打开的是生生不息的、鲜活的世界图景。因而“在”兼具时空意,又意指前后紧承的两个时空交叉点:在前时空看来为“终”,而从后一时空看则为“始”,这种正反矛盾统一,似可视为中国传统阐释学智慧的一种体现。
综上,从强制阐释论到公共阐释论,在中国阐释学当代建构十年理论行程中,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问题一直贯穿其中如影随形,而方法论问题被视为当代中国阐释学建构所面临的六大难题之一。以历史、当代、经验为主要方法论元素的中国阐释论当代建构的方法论视域拓展了辉格阐释批判的视野,本体论与方法论并重、而“方法论优先”“为重”的中国阐释学当代建构,已确立中西当代阐释互可通约、各各不同的阐释学范式,而且随着概念、范畴、命题、体系等深入探讨,中国阐释学史研究新视野也将逐步开启。
——意象阐释学的观念与方法》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