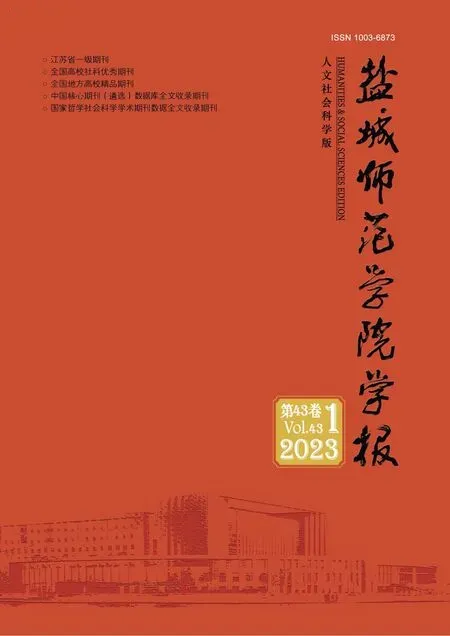莎拉·蒂斯黛尔诗歌创作论
陈义海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莎拉·蒂斯黛尔(Sara Teasdale,1884--1933),无疑是20世纪美国诗坛的一个独特的存在,也是世界诗歌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
在美国诗坛,与出生更早的朗费罗、惠特曼、狄金森、弗罗斯特等诗人相比,蒂斯黛尔在文学史上所占的篇幅极小;而与她同时代的W. C.威廉斯、庞德、杜利特尔,以及稍后的E. E.肯明斯相比,她似乎又有点生不逢时----当庞德等诗人横空出世,以空前的激进打破传统的诗歌规范、推动美国诗歌进行新的革命时,蒂斯黛尔却仍然沉湎于萨福式的激情、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式的唯美、勃朗宁夫人式的缠绵,在美国中部的一个急剧现代化的内陆州,追寻、呼应着万里之外的维多利亚风,坚定不移地用她独特的、典雅的方式把爱与美、生与死的诗篇写得精美绝伦、荡气回肠。
蒂斯黛尔生前无疑已成为20世纪初美国诗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她的《恋歌》于1918年获得了首届哥伦比亚诗歌奖(即普利策诗歌奖的前身),拥有大量的崇拜者。然而,1933年,蒂斯黛尔却在她纽约的寓所以不寻常的方式结束了她的歌唱。虽然她的诗歌一度被现代主义诗歌浪潮淹没,但她的作品却始终在印行,她始终拥有稳定的读者群体。近40年来,一些研究者更是不断挖掘蒂斯黛尔作为抒情诗人的独特价值,以及她诗歌创作的唯一性。纽约大学的威廉·德拉克教授给予蒂斯黛尔极高的评价:“莎拉·蒂斯黛尔在美国诗歌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no parallel)。”[1]1谢丽尔·沃克尔则认为,当我们着迷于现代主义所追求的新奇与智力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莎拉·蒂斯黛尔是她那个时代的一个革新者,“一个安静的革新者”,因为她继承了西方诗歌的伟大传统,开创了属于她自己的“恋歌体”[2]44。中国学者张子清认为,在20世纪初,特别是整个20年代,“莎拉·蒂斯黛尔在美国广大读者中的名气远远胜过T. S.艾略特和庞德……在当时不知使多少痴情或多情的男女心荡神迷”[3]241-242。鉴于国内对这位诗人的研究十分贫乏,本文重点从传记批评的视角对蒂斯黛尔的诗歌创作生涯作一概览式的研究。
一、美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淑女
莎拉·蒂斯黛尔1884年8月8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蒂斯黛尔出生时,父亲45岁,他有两个儿子,一个14岁,另一个19岁,还有一个女儿17岁。在英国,这时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晚期,虽然这时的美国已经独立一个多世纪,但是很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依然保持着维多利亚风尚。根据这种风尚,夫妇间的性爱主要服务于生儿育女,当生儿育女的任务完成后且人到中年时,性爱几乎成了一种不符合伦理的行为。蒂斯黛尔的父母万万没有想到,在停止生育14年后,家中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加之蒂斯黛尔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诚的新教徒,在生活上是十分保守的,所以,她的出生让她的父母感到十分难堪。
虽然“中年得女”很尴尬,但蒂斯黛尔的父母对这个突然闯入的女儿宠爱有加。蒂斯黛尔从小崇拜自己的父亲,在她的眼中,这个父亲更像一个慈祥的爷爷。蒂斯黛尔自小体弱多病,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热咳嗽,所以,全家人都把她当作幼鸟呵护,什么时间吃饭、什么时间睡觉、什么时间散步,都规定得非常严格,直到9岁时父母才敢把她送到隔一条街道的私立学校洛克伍德夫人学校去念书,而这之前,比她大17岁的姐姐则充当她的家庭教师。蒂斯黛尔的一个朋友这样回忆蒂斯黛尔的童年:
莎拉过着修女般严格的生活,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里该做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写诗,什么时候应约接待朋友……我记得我是怎样先被一个女仆引进客厅,而这个女仆接着上楼通报我已经到达,我好像是到皇家参访……莎拉过着塔楼里的公主的生活……她什么都不缺,就缺健康。[4]4
1898年,14岁的蒂斯黛尔结束了在洛克伍德夫人学校为期5年的学习生活,被送到本城的玛丽学院读书。这是一所有名的女子学校,是T. S.艾略特的祖父威廉·艾略特创办的。由于蒂斯黛尔体弱多病,在体力上无法承受每天乘城市交通去上学,所以她在玛丽学院的学习只持续了不到一年。1899年,蒂斯黛尔进入霍斯默·霍尔学校读书。在该校读书期间,蒂斯黛尔热衷于法国文学和德国文学,并翻译过德国诗人海涅的一些抒情诗。大概是在该校读书时,蒂斯黛尔开始写诗。她自己曾说过,最初开始写诗是在15岁,但自认为写得很差,不能见人。然而,她从该校毕业时,已经是全校师生公认的“诗人”了。
蒂斯黛尔的童年和青年时光基本上都是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度过的。无论在美国地理上,还是在美国历史上,密苏里州的地位都十分特殊:它是美国一个很“居中”的州,同时又是美国“西进”的起点。而圣路易斯城一般被看作是美国版图的几何中心。虽然如今圣路易斯的人口已经萎缩到了30多万人,但在蒂斯黛尔的青少年时期,它却已经是一个接近60万人口的大城市。或许正是因为它处于西部农业区与东部工业区的交汇点上,它注定拥有独特地位。“宽广的厂区,工厂林立,烟雾笼罩着城市;水边码头和火车站,连接东部和西部,成为东西部的枢纽。”[4]1独特的地理位置、发达的交通、蓬勃的工业、多元的移民文化,使圣路易斯在19世纪末成为中部的知识之城、艺术之都。在19世纪末,它便有了大学两所、艺术学校一所,以及室内和露天剧院各一处。总之,这个时期的圣路易斯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在急剧上升,与芝加哥齐头并进,成为美国第四大城市,并有望成为美国的中部之都,甚至有人呼吁要把首都从华盛顿搬到圣路易斯来。可见,蒂斯黛尔的家乡在美国文学史的地位虽然不及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但文学艺术的氛围还是比较浓的。此时处于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的英国,正是其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期。与美国的其他城市相比,蒂斯黛尔所生活的圣路易城,其维多利亚特征更加显著。这便是蒂斯黛尔成长的环境。
1904--1907年期间,蒂斯黛尔参加了圣路易斯城的“陶工社”,一个由年轻女性发起成立的俱乐部。这期间她阅读了大量的欧洲经典作品,而诗歌写作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蒂斯黛尔一生都在和自己的体弱多病作斗争,起初是生理上的多病,后来则逐渐发展成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她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去疗养院进行康复治疗。即使这样,阅读和写作几乎从来没有中断过。优裕的生活、封闭的成长环境、弱不禁风的体质、多愁善感的气质,赋予了蒂斯黛尔诗歌的基本特质:敏感、唯美、感伤。而这些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史文朋、勃朗宁、罗塞蒂等诗人的影响。
二、“圣路易斯女孩”的诗歌之旅
虽然在蒂斯黛尔出生时,艾米莉·狄金森早已确立了她在美国诗坛的不朽地位,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女性从事文学创作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蒂斯黛尔起初写诗,并不是为了成名,而是为了表达内心的孤独与苦闷以及对爱的向往。1907年,23岁的蒂斯黛尔在波士顿一家出版社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献给杜丝的十四行诗及其他》(收入诗歌29首),对她宠爱有加的父母为她支付了290美元的出版印刷费。这本诗集的出版,使蒂斯黛尔在圣路易斯城获得了一定的声名,当地媒体开始报道她的创作情况,她由此获得一个雅号“圣路易斯女孩”。这本诗集的出版坚定了她从事诗歌创作的决心,她开始不断地向各地报刊投稿,并着手准备她的第二本诗集。
1908年到1910年,是蒂斯黛尔在情绪上十分低落的一个阶段。她无需工作,在父母的关爱下整天做着白日梦。她的身体常常出现状况,需要不断到温暖的地方去疗养、治疗。
1910年年底,蒂斯黛尔的诗歌之路出现转机。10月份,她的第二本诗集《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在被美国和英国的多家出版社退稿后,终于被帕特南公司接受,并且不需要作者支付出版费。这一年的10月,美国诗歌学会成立,蒂斯黛尔被邀请加入该协会并参加当年12月28日在纽约市举办的学会年度晚宴。
蒂斯黛尔虽然错过了12月28日的学会年度晚宴,但她还是于1911年1月18日乘火车抵达纽约,27岁的她第一次只身一人远离宠爱她的父亲,逃离控制欲很强的母亲,离开在她看来像囚室一样的公主象牙塔。国际大都市纽约给她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学社交圈。她参加了2月7日和3月7日的诗歌学会集会,见到了著名诗人、诗歌活动家杰西·里滕豪斯(Jessie Rittenhouse),见到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蒂斯黛尔并不喜欢庞德本人,这恐怕也是她与核心意象主义诗群保持距离的一个原因。1911年1月到3月的纽约之旅虽然是短暂的,却改变了她诗歌之路的轨迹。虽然回到了故乡圣路易斯,但每次想到纽约居然有思乡的感觉。
1912年到1915年,蒂斯黛尔频繁来往于圣路易斯、纽约和当时美国的另一个文学中心芝加哥之间,1916年11月婚后的蒂斯黛尔定居纽约。
如果说她的第二本诗集使她获得了全国性的声望,那么,她的第三本诗集《奔向大海的河流》则确定了她在美国诗坛的地位。这本诗集于1915年10月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由于非常畅销,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重印了三次,从此,她所有的诗集全部由该公司出版。当时,美国《诗刊》主编哈里特·门罗在社评中评价:阅读这本诗集“就像欣赏六月的鲜花”,因为蒂斯黛尔的诗歌“清澈,精确,优雅,散发着花朵的芬芳”[5]。
从《奔向大海的河流》的出版,我们也可以看到,蒂斯黛尔是一个极其入世的诗歌的经营者。该诗集出版前,她与丈夫菲尔辛格一起做了大量的推介工作,在媒介上刊登预告,给各大书店、大学图书馆及各地的诗人写信,以求拓展销路,产生影响。与狄金森不一样,蒂斯黛尔非常在乎发表。她是一个孜孜不倦的投稿者,让自己的诗歌不断“行走在路上”。收到退稿后,她会在修改后再投出去,坚持每年发表十多首诗歌。特别是在婚后,她更在乎将自己的诗“卖”出去,更在乎出版社所给的版税。她也善于跟各地诗人、评论家、刊物编辑打交道,不但不介入到诗坛的纷争中去,而且能使争论的双方都成为她的朋友。
《奔向大海的河流》获得巨大成功后,麦克米兰公司于1916年2月又向她约稿,希望出版她的下一部诗集。由于没有最新作品可出版,蒂斯黛尔提出要给麦克米兰编一本女诗人的爱情诗选,收录近六十年间女诗人的爱情诗,诗选定名为AnsweringVoice(《回声》),并于这一年的6月份将稿子发出。在选编《回声》时,蒂斯黛尔突发奇想:她的第二本诗集《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中有一辑的辑名叫“恋歌”,何不从那本诗集中精选部分,再从第三本诗集《奔向大海的河流》中精选部分,再加上新创作的诗歌,编成一本新的集子呢?她的构想于1916年年底得到麦克米兰公司的认可,该公司同意出版她的第四本个人诗集《恋歌》。
1917年的秋天,蒂斯黛尔迎来一个丰收的季节:她所编选的《回声:女诗人爱情诗100首》和她自己的第四本诗集《恋歌》几乎同时面世,她的第三本诗集《奔向大海的河流》则第四次印刷。《恋歌》无疑是当时最畅销的个人诗集,初版不到两个月便第二次印刷。随着诗集的出版,诗歌朗诵会便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等地方进行。蒂斯黛尔的声望进一步提升。
1918年,普利策奖第一次颁发,但并没有把诗歌列为奖项。美国诗歌学会觉得诗歌应该列入其中,并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奖金则由一个匿名的捐赠者提供,奖项由哥伦比亚大学和美国诗歌学会共同颁授。蒂斯黛尔的诗集《恋歌》从1917年出版的十几本诗集中脱颖而出,荣膺1918年度哥伦比亚诗歌奖(Columbia Poetry Prize)。由于普利策诗歌奖直到1922年才正式增设并颁发,哥伦比亚诗歌奖常被看作普利策诗歌奖的前身。哈里特·门罗在评价蒂斯黛尔的获奖时认为,她的这部诗集中的一些作品,“是英语世界中最美的爱情诗”,认为她的作品“极其清澈、明晰”,“极其生动而富于魅力”,“尽管采用的是旧的形式,但旧的形式却可以持久”[6]。至此,蒂斯黛尔达到了她文学生涯的又一个高峰。
如果说,1907年出版的《献给杜丝的十四行诗及其他》还显得有点“女生气”,1911年出版《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是初露才华,那么,从1911年到1918年,则是她在诗艺和诗坛影响上突飞猛进的七年。
1920年10月,蒂斯黛尔的第五本诗集《火焰与阴影》面世,该诗集收录了她从1914到1920年的92首诗。由于这时她在美国诗歌界的声望已经很高,在读者中的影响已经很大,所以她并没有像《奔向大海的河流》出版时那样做大量的推介工作。尽管如此,《火焰与阴影》还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两个月后便第二次印刷,一年当中重印了四次。无论是艺术的表现力,还是思想的深刻性,这本诗集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自我评价道:“这是我最好的一本书。跟我以前的书相比,它表现生活更加深刻,在手法上也更加灵活。”总之,这本诗集的出版,使蒂斯黛尔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诗人”[1]200。
《火焰与阴影》之后,蒂斯黛尔的诗歌创作进入后期,由于健康原因和婚姻问题,创作量日渐减少。她与诗歌界的交流不如以前频繁,她更愿意深居简出,很多时光都是在疗养地、假日酒店度过。由于生理、心理的疾病一直困扰着她,加之婚姻出现问题,诗歌的悲观气息日益浓郁。1926年,她的第六本诗集《月黑之时》仍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其中的诗篇,色调晦暗,透露出她苍凉的心境,包含着对人生的悲观、对衰老的哀叹、对死亡的恐惧。1911年时,蒂斯黛尔把参加美国诗歌学会的年度聚会看作朝圣;1924年1月,正值学会举行年度聚会时,她却故意离开纽约到外地度假以回避。
1926年出版的《月黑之时》再次证明了蒂斯黛尔在当时美国诗坛的声望、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初版5000册一销而空,随即开始第二次印刷。然而,这却是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收录新作的诗集;她1930年出版的诗集《今夜星辰》是针对儿童读者的一个选本,是从她已经出版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
蒂斯黛尔诗歌生涯的最后十年是在病痛、婚姻的矛盾、情绪的压抑中,挣扎着度过的。死亡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她。在与死亡较量了多年后,她最终无力抗争。她的诗歌人生像流星划过的一道轨迹,这轨迹最终消逝在1933年1月29日的早晨。然而,蒂斯黛尔,这个“圣路易斯女孩”,凭借着她诗中独特的美丽和忧伤,占据着一代又一代爱诗者的灵魂。
三、“独一无二”的诗歌
蒂斯黛尔生前一共出版过七本个人诗集:《献给杜丝的十四行诗及其他》(SonnetstoDuseandOtherPoems, 1907),《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HelenofTroyandOtherPoems, 1911),《奔向大海的河流》(RiverstotheSea, 1915),《恋歌》(LoveSongs, 1917),《火焰与阴影》(FlameandShadow, 1920),《月黑之时》(DarkoftheMoon, 1926),《今夜星辰》(StarsTo-night,1930)。《奇怪的胜利》(StrangeVictory, 1933),是蒂斯黛尔去世后才整理出版的。从数量看,蒂斯黛尔不属于高产的作家,但从她二十多年短暂的创作生涯看,她为我们留下了四百多首诗歌,算是一笔非常丰厚的文学遗产。
蒂斯黛尔的诗歌是美国诗歌新旧传统交替时期的历史印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独立一个多世纪的美国,其诗歌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一部分诗人坚守欧洲诗歌传统,捍卫着传统诗学,另一部分诗人则成为新风尚的开拓者。从1874到1894这二十年间出生的美国诗人特别密集,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桑德堡(Carl Sandburg,1878--1967)、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林赛(Vachel Lindsay,1879--1931)、威廉斯(William C. Williams,1883--1963)、蒂斯黛尔(Sara Teasdale,1884--1933)、怀利(Eleanor Wylie,1885--1928)、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1886--1961)、穆尔(Marianne Moore,1887--1972)、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米蕾(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肯明斯(E. E. Cummings,1894--1962)……他们虽然出生时间相近,但他们却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传统或现代----使美国诗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所谓“美国诗坛五巨擘”,全都诞生于这一时期[3]103-197。但传统或现代取向的分化跟诗人出生时间或者出生地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比如同样出生在圣路易斯城的艾略特比蒂斯黛尔小四岁,但他却成为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而蒂斯黛尔却执著于传统的形式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在这杰出诗人辈出的年代,蒂斯黛尔始终坚守着诗歌的“歌唱”属性、音乐特质,这使得她与这个时期的其他所有诗人显著区分开来。从声望上看,蒂斯黛尔也是这一批诗人中成名较早、在当时拥有读者最多的诗人。当她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创作生涯的巅峰时,庞德和艾略特在美国本土的影响还很有限。在形式上坚守传统、在内容上表现美国本土生活的弗罗斯特,虽然是获得普利策诗歌奖最多的诗人(曾在1924、1931、1937、1943年四获该奖项),但蒂斯黛尔在1918年能获得首届哥伦比亚诗歌奖(普利策诗歌奖前身),足以证明蒂斯黛尔在美国诗坛的声望,无论在传统诗派中还是在现代诗派中,都是非常高的。她的影响力下降主要是在她去世后。肯明斯、庞德、艾略特等诗人在经历了最初的“争论期”之后,到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成为经典。“大树底下寸草不生”,他们的声望越高,蒂斯黛尔那一派的诗人便越是被遮蔽,最终成为“被忽略的”的诗人。正如纽科姆所说:“由于现代主义对于性别和体裁与生俱来的偏见,莎拉·蒂斯黛尔的作品被不公正地矮化了(miniaturized)。”[7]111梅丽莎·吉拉德认为:“莎拉·蒂斯黛尔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典型的‘女性诗人’:端庄娴静、温文尔雅,而且显然是守旧的。”[8]她甚至认为,现代主义使感性的张力变得不时尚,因此使蒂斯黛尔相对默默无闻[9]389。于是,一个问题就可以被提出:诗人究竟是为公众写作还是为文学史写作?这或许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但现实中,一个诗人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和在公众读者中的影响力,经常是不一致的,这值得深思。诗人的作品事实上就存在着两种价值: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蒂斯黛尔的诗歌无疑属于后者。在意象主义诗人抛弃诗歌的传统规范时,蒂斯黛尔坚定不移地走在“守旧”的道路上。在文学创作上,能不能说“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不好的呢?事实证明,文本的持久力和学界的关注度之间出现“剪刀差”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
蒂斯黛尔的诗歌较为忠实地继承了欧洲的“夜莺传统”[2]47。她有一个习惯,凡是她所读过的书,她都要在记录本上记下来。蒂斯黛尔一生的阅读量非常大,她几乎读遍了从萨福到浪漫主义最优秀的欧洲诗人拜伦、雪莱、济慈的作品。如果说,遥远的萨福对她的青年时期人格产生过极大的影响,那么英国诗人罗塞蒂、史文朋、叶芝、豪斯曼对她诗歌创作的影响则更加直接。她一生共七次赴欧洲旅行,其中六次到英格兰。在她生命的最后三年中,她两次赴英格兰。每次抵达英格兰,她都有回到家的感觉。她一生都迷恋罗塞蒂,并在1930年制定了“罗塞蒂传”的写作计划。她从罗塞蒂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人生的悲剧性,她似乎是想通过研究罗塞蒂来克服自己的精神抑郁,走出死亡的阴影。可以说,蒂斯黛尔就是美国的罗塞蒂。可惜,她这部传记只写了六十几页。蒂斯黛尔不仅延续了英诗的血脉,而且在诗歌的外形上也追随着英诗的传统。在她的同时代美国诗人纷纷打破传统诗歌的格律规范时,蒂斯黛尔严守着英诗的传统样式。虽然她严守格律,力求抑扬格(iambic)、扬抑格(trochee)所规定的音节的准确,但她依然给我们展现了带着镣铐的优美舞姿。
蒂斯黛尔的诗歌题材并不广泛,所采用的意象也极其有限且常见。她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是花、鸟、大海、月亮、星星,表现的是人类最古老的母题:爱、生、死、美、悲伤。如果说她早期的诗歌更多抒写的是爱和爱的惆怅,那么,她后期的作品则更多表达的是爱与爱的绝望。但不管是表现爱的欢悦还是爱的忧伤,美,始终是蒂斯黛尔诗学的最高准则。当同时代的许多美国诗人都摩肩接踵地挤进现代主义诗歌的长廊里时,坚持传统诗学的蒂斯黛尔却在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使得她的诗歌创作在同时代的美国诗人中显得别有风格。
四、泥淖中的爱之“恋歌”
蒂斯黛尔的绝大多数诗歌都是跟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对爱的梦想,对爱的期盼,对爱的苦苦追求。几乎可以说,把“爱”字去掉,蒂斯黛尔诗歌会一下子黯然失色。她总是喜欢称自己的诗是“歌”(songs)。她的第二本诗集《特洛伊的海伦及其他》的第二辑被她定名为“恋歌”(Love Songs);1917年她把这部分诗歌作了精选,再加上她新写的爱情诗,出版了她的第三本诗集,诗集的书名还是“恋歌”;在此后出版的几部诗集中,爱仍然是其中最常见的主题。所以,蒂斯黛尔是唱着“恋歌”走上20世纪初的美国诗坛,唱着“恋歌”走完了她悲情的一生。
作为富商家庭的晚生女,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蒂斯黛尔是一个养在深闺里的女孩。她出生时,家中的哥哥姐姐最小的比她大14岁。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成年人的环境里,没有玩伴,只有孤独。孤独,常常是幻想的温床;快乐的诗歌难作,痛苦的诗歌好写。从懵懵懂懂地幻想爱,到苦苦追求自己的真爱,到建立起被社会习俗认可的家庭,再到后来她义无反顾地离婚,蒂斯黛尔把爱的欢欣,更多的是爱的苦涩,清新或隐晦地写进了她诗歌的字里行间。而要理解这些诗行间所洋溢着的复杂的爱的情绪,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了解一下影响了她诗歌创作的几桩恋情:
“通信恋人”约翰·迈耶斯·欧哈拉(John Meyers O’Hara),是一个居住在纽约的诗人。1908年,虽然蒂斯黛尔已经于前一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但24岁的她仍然是一个被父母呵护着的孩子。因为欧哈拉翻译过萨福的一些诗歌,蒂斯黛尔因此跟他开始了通信联系。渐渐地,欧哈拉开始在信中越来越多地表达他对蒂斯黛尔的爱慕之情。受到保守家庭的影响,蒂斯黛尔对他始终保持审慎、矜持的态度,但她一直把他作为一个情感表达和诗歌交流的对象。直到1911年1月去纽约蒂斯黛尔才第一次见到欧哈拉。这是一次令人失望的见面,使得这桩由距离产生的恋情,因为见面而瞬间“气化”。
“海上恋人”斯塔福·哈特菲尔德(Stafford Hatfield),是一个在音乐、文学和科学等方面都颇具才华的英国人。1912年夏天,蒂斯黛尔与女诗人杰西·里滕豪斯同游欧洲,在回程的游船上她与哈特菲尔德一见钟情。这个男士的侃侃而谈、温柔体贴让蒂斯黛尔不能自拔。他们在纽约上岸后,蒂斯黛尔仍然陷在这段感情里不能自拔。然而,这个英国男子在她回到圣路易斯约一个星期后便乘船离开了美国,再也没有出现。这番萍水相逢的罗曼司,给蒂斯黛尔的打击非常大,更增添了她恋歌的感伤气息。
“永不表态的恋人”约翰·霍尔·惠洛克(John Hall Wheelock),是一个因为诗歌才华而打动蒂斯黛尔的纽约诗人。她1912年秋天读到惠洛克的诗集,折服于他的诗才。1913年1月,蒂斯黛尔在纽约第一次见到惠洛克。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与惠洛克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但他始终没有同意与她结婚。蒂斯黛尔的不少爱情诗是献给惠洛克的。
“一文不名的恋人”维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是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小城的、才华横溢却一文不名的诗人。林赛曾在芝加哥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他属于芝加哥诗派,但他厌恶工业文明。他的诗歌吸收了爵士乐的特点,节奏感很强;他经常靠朗诵诗歌或唱诗维持生存。1915年出版的《中国夜莺》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蒂斯黛尔大约是在1913年6月认识林赛的。她非常仰慕林赛的才华,但两个人的生存方式完全不同:蒂斯黛尔自幼养尊处优,林赛家境贫寒;蒂斯黛尔一心要生活在纽约那样的大都市,而林赛则深爱着他所生活的中西部,并希望蒂斯黛尔能跟他一起到中西部去。更主要的是,蒂斯黛尔体弱多病,而这时她的父亲已经年迈,她必须寻找一个能为她提供经济基础的伴侣,所以,到最后时刻,她还是忍痛离开了林赛。虽然蒂斯黛尔后来与菲尔辛格结婚,但她婚后仍非常尊重林赛,且始终心怀自责。林赛于1931年自杀,结束了自己吟唱的一生。这给蒂斯黛尔沉重的打击,两年后,她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鞋匠恋人”恩斯特·菲尔辛格(Ernst Filsinger),是一个商人,圣路易斯城一家制鞋工厂的合伙人,与蒂斯黛尔是同乡。他是1914年三四月间蒂斯黛尔的朋友尤妮斯从芝加哥到圣路易斯时介绍的一个熟人。菲尔辛格早就知道蒂斯黛尔的诗名,读过并且能背上她的不少诗作。蒂斯黛尔苦苦寻觅,遇见了那么多的才子,但最终还是与本城的一个商人结婚。他们于1914年12月19日在蒂斯黛尔的家中举行了低调的婚礼。
虽然从当初写诗时,蒂斯黛尔就在诗中梦想爱情,但是,从1912年到1914年,在两年多的时间中,蒂斯黛尔却非常迫切地要找到一个终身伴侣而不只是爱情;特别是在1914年,她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写诗,主要精力放在终身大事上。这也可以理解,因为这时她已经30岁,而她的父亲已经风烛残年。一年当中会有几个月在旅馆和疗养院度过的她,必须找到一个能在经济上给她保障的丈夫;为了诗歌创作,在生活上她必须有一个依靠。“通信恋人”欧哈拉虽然还和她保持通信,但早已被她排除;那个风流倜傥的“英国恋人”哈特菲尔德,已经杳无音信;她所钟情的惠洛克始终含糊其辞,似乎另有所爱;她所迷恋的林赛要等挣足了钱才有勇气跟她结婚。可是,她不敢再等,最终与崇拜她的菲尔辛格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对于蒂斯黛尔的选择,媒体很是不以为然。《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标题是“女诗人嫁给男鞋匠”,虽然这个标题显得粗鲁,但美国《诗刊》主编哈里特·门罗的确为蒂斯黛尔没有和诗人林赛结婚感到遗憾,因为她着实希望看到伊丽莎白·芭蕾特嫁给罗伯特·勃朗宁的英国诗坛佳话,能在美国诗坛再现[1]143。但婚姻的确让蒂斯黛尔无处着落的心有了安放之所,婚姻也的确使蒂斯黛尔获得了人们所认为的幸福。一时间,蒂斯黛尔甚至觉得幸福得写不出满意的诗歌。“幸福的诗歌要比不幸福的诗歌更难写。”她自己也在书信中写道:“爱既圆满,情诗难作。”[1]155事实证明,蒂斯黛尔与菲尔辛格的婚姻是仓促且没有基础的,它甚至成为蒂斯黛尔的精神负担,并于1929年走到了尽头。蒂斯黛尔也因此重新“获得了自由”[1]156。
蒂斯黛尔的一生除了体弱多病,还忍受着不时发作的精神抑郁。离婚之后,生理与心理状况更是每况愈下。她与行吟诗人林赛仍然保持着交往,1931年,他们最后一次在纽约见面。林赛离开纽约不久便自尽离世,而蒂斯黛尔两年后也永别人间。爱情不幸诗歌幸。婚姻的不幸福,似乎让蒂斯黛尔又找到了抒情的支点。如果说,1915年之前蒂斯黛尔的诗歌多写追求爱的痛苦,那么,1915年之后她的诗歌则多写对所谓“爱”的失望。她的第四本诗集《恋歌》(1917)似乎是“承上”,第五本诗集《火焰与阴影》(1920)大致可看作是“启下”。纵观蒂斯黛尔的诗歌创作,虽然她也涉及其他题材,甚至写过以“一战”为背景的《细雨终将来临》,但是,爱情是她一生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近一个世纪的世界诗坛上,还很少有诗人如此执著地将爱作为诗歌的表现主题。爱的梦想、爱的惆怅、爱的欢欣、爱的失落、爱的绝望,串起了她一生宝石一样璀璨的“恋歌”。
蒂斯黛尔的“恋歌”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类:一类是幻想的,诗中的“你”或者“我”常常是虚拟的,这种情况在她早期诗歌中尤其明显;一类是有一定指向性的,有的作品甚至明确标明献给谁;一类是模糊的,难以确定的。蒂斯黛尔的“恋歌”表达得最多的是对爱情期待而不能获得的忧伤之情。加之她的诗歌多用常见的意象和较为传统的形式,这使得她的诗歌具有很强的“普世价值”而深得各个时代的读者喜爱。当然,爱情不仅是蒂斯黛尔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同时诗歌创作也是她表达内心苦闷彷徨的媒介方式。就是说,她的不少诗作虽然以爱为名,但实际上是要表达她内心的某种情绪,于是,她的爱情诗便成为承载各种情绪的百宝箱。
蒂斯黛尔除了写出许多脍炙人口的短小的恋歌,她还写过一些古代题材的长诗。这些诗歌多以历史上敢爱敢恨、热情奔放的女子为抒写对象,如古希腊抒情诗人萨福、特洛伊的海伦、意大利修女贝尔特丽齐、葡萄牙修女艾尔柯福南多等。这些女子,要么以大胆的、不顾后果的爱而著称,要么宁愿为爱情放弃荣誉甚至生命。作为一个出身于新教传统家庭、深受维多利亚社会伦理影响的中产阶级女子,她只能激进到借助歌颂历史上这些“大胆女子”的方式曲折地表达她对爱的渴望的程度。
五、在中国的回声
蒂斯黛尔1933年去世时年仅49岁。在之后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岁月中,蒂斯黛尔虽然未在文学史上占据多少篇幅,但她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她的“歌声”一直在文学史的长廊里回响。不太为学界关注的是,蒂斯黛尔的诗歌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在她生前就已经开始,并对发轫时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19年2月,胡适曾翻译蒂斯黛尔的诗作《在屋顶上》(OvertheRoofs),但他在翻译时,却将原标题“在屋顶上”译成了“关不住了!”。胡适这样翻译,大概是依据了这首诗后两行的内容:“他说:‘我是关不住的,/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这首译诗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上[10]135,后收入《尝试集》。胡适在译文末写明:“八年二月十六日译美国新诗人Sara Teasdale的OvertheRoofs”。
胡适所翻译的蒂斯黛尔的这首OvertheRoofs,1914年最先发表在美国著名诗歌刊物《诗刊》上。同期还发表了蒂斯黛尔的另外三首诗OldLoveandNew、Debt、SeptemberNight。这首OvertheRoofs在《诗刊》发表时是十二行,但收入《奔向大海的河流》(1915)时,它却成为一个组诗的第四部分,但总标题没有变。蒂斯黛尔将这组诗编进另一部诗集《恋歌》(1917)时,则将总标题OvertheRoofs改成了MayWind(《五月的风》)。可见,胡适应该是依据1914年的《诗刊》翻译的;否则,他大概会把前面的三首连带译出。胡适1910至1917年在美留学时,十分关注美国诗坛,并特别关注对意象主义运动发展起过关键作用的《诗刊》。他在《文学改良刍议》(1917)中所提出的“八点主张”,显然是受到了庞德在1913年《诗刊》上所发表的《意象主义的几个“不”》(AFewDon’tsbyanImagiste)[11]的影响。由此我们更有理由认为,胡适是依据1914年的《诗刊》翻译了蒂斯黛尔的这首OvertheRoofs。
蒂斯黛尔在当时的美国诗坛虽然很活跃,诗集的发行量也很大,但她一定还算不上当时的美国主流诗人。然而,很奇怪的是,胡适偏偏选中了这一首,并且将他翻译这首诗看作他“‘新诗’成立的纪元”[10]84。这正是《尝试集》所体现的“尝试”精神之所在。今天总览《尝试集》,我们发现这是一本极其芜杂的集子。既有诗学品质较高的抒情诗,也有在今天看来有点可笑的打油诗;既有对古诗的串译,也有对外国诗歌的翻译。而且,作者自己的创作与翻译作品常常是混排在一起的,就好像外国诗人的作品也成了自己创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胡适是在尝试找到新诗的话语方式,而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世纪之前,这些中国新诗开拓者们的探索是何等的艰难。正是“经过英汉互译以及古诗今译等多重实践,反复阐发,终于窥得白话入诗的门径,成就一部影响深远的白话诗集《尝试集》”[12]。同时,胡适等诗人也是通过翻译的手段建构起中国新诗的格律方式[13]。
胡适之外,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胡怀琛、罗念生、叶灵风等诗人和学者也都翻译或关注到了蒂斯黛尔的诗歌。
胡怀琛在其《小诗研究》(商务印书馆,1924)中,曾用旧体诗翻译了胡适在1919年翻译过的蒂斯黛尔的诗歌OvertheRoofs,但胡怀琛将这个标题译为《爱情》[13]。郭沫若和闻一多都曾翻译过蒂斯黛尔的LikeBarleyBending一诗。郭沫若于文革期间(1969年3--5月间)翻译该诗,其去世后由郭庶英、郭平英整理收入《英诗译稿》出版[14]61。闻一多则将蒂斯黛尔的OvertheRoofs译为《像拜风的麦浪》,并于1927年10月29日在上海《时事周报·文艺副刊》上发表[15]299。罗念生曾翻译蒂斯黛尔的名作LetItBeForgotten(译为《忘掉罢》),并于1933年8月发表在《青年界》第4卷第1期,后收入《现代美国诗》[16]367。邵洵美曾翻译蒂斯黛尔的四首诗收入他的译诗集《一朵朵玫瑰》(金屋书店,1928年)[17]77。刘延陵不仅翻译过蒂斯黛尔的诗,他自己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蒂斯黛尔的影响。他1922年发表在《诗》杂志第1卷第5期上的《现代的恋歌》一文,评价并翻译了蒂斯黛尔的NightSongatAmalfi(《亚马尔菲底夜歌》)等四首诗歌,称其诗歌“音调清凉,柔媚,如缓缓地流的溪水”[18]。林以亮主编的《美国诗选》收入蒂斯黛尔诗歌七首,其中,六首由余光中翻译,一首由林以亮翻译[19]232-236。进入21世纪,作为非主流诗人的蒂斯黛尔在中国仍然受到翻译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的青睐,但译介多是零星的。刘荣跃翻译的蒂斯黛尔《恋歌》[20],则是蒂斯黛尔诗歌最集中的一次呈现;遗憾的是,这部译诗集重点翻译了蒂斯黛尔1917年出版的《恋歌》,集中翻译的是她的爱情诗,而未能对她的其他几本诗集进行更全面的选译。
值得注意的是,1918至1920年曾在美国留学的徐志摩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蒂斯黛尔的影响。他1924年所写的名作《雪花的快乐》与蒂斯黛尔1910年左右年发表的SnowSong,无论在意象的选择、诗句的构成上,还是在诗歌的意境上,无疑都十分相近[21]。1922至1925年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同样受到了蒂斯黛尔的影响。他的名作《忘掉她》与蒂斯黛尔的LetItBeForgotten有着高度的相似性[22]。由此可见,蒂斯黛尔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虽然不及其他一些外国诗人,但她还是在中国百年新诗史上留下了不少清晰可辨的印迹。
蒂斯黛尔虽然辞世近一个世纪,但近三十年来,美国学界不断有学者关注20世纪初美国诗歌革命期间这位“被忽略的”诗人,研究蒂斯黛尔的著作和论文明显增多。相信国内也会有更多的学者和读者关注这位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留痕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