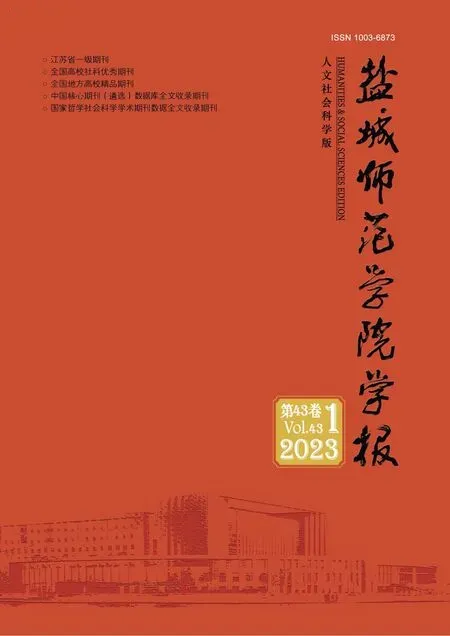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
----以《儒林外史》为中心
张兴龙,徐 畅
(江苏海洋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对明清金陵小说帝都文化书写展开讨论,需要从学理上解决两个命题:一是金陵小说概念界定问题,即哪些小说属于金陵小说;二是帝都文化书写的内涵或角度,即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包括哪些方面。
一方面,金陵小说概念的界定。本文所说的金陵小说,专指明清时期小说作者(包括创作、编纂、刊刻)为金陵籍,或者非金陵籍但是因为长期生活在金陵“为金陵文化所化”之人,小说以金陵作为故事发生的重要地理场景,以金陵社会生活、文化风情、价值观念等为内容特征,且典型地体现当时金陵人的心态、表达对金陵生活独特反思的话本、文言、笔记小说等。本文界定明清金陵小说概念,借鉴了明清西湖小说(或杭州小说)的命名方法。葛永海认为,明清时期小说作家普遍具有的“金陵情结”,他强调地理环境是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明清时许多作家生活于此,情之所系,魂牵梦绕,留下了许多追忆和抒写南京的篇章”[1]。这些作家自觉创作表现南京风物人情的小说话本,其实就是“金陵小说”。按照这个界定,《儒林外史》是金陵小说的最重要代表,另外,金陵小说包括散落在东鲁古狂生《醉醒石》、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古吴金木散人《鼓掌绝尘》以及“三言二拍”中的部分篇章(节)。
另一方面,帝都文化书写的角度。帝都宫廷建筑的恢弘壮丽、威严显赫,礼仪制度的崇尚遵守、严谨规范,都不是普通城市具备的。而且帝都还是承载世人名利梦想的中心。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至少可以从恢弘的城市景观与深沉的城市衰落思辨,尊崇礼仪的城市制度,名士云集的儒林形象等三个层面加以阐释,这三个方面依次对应了帝都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审美文化三个向度。金陵怀古是有唐以来中国文学的传统题材,并非明清小说中的帝都文化书写所特有,但是不同于唐代金陵怀古诗对城市盛极而衰的个体性感怀,金陵小说中的帝都兴亡更具深刻性,更彰显出当时文人对历史兴亡的思辨性。在明清小说的帝都书写中,只有金陵小说对士人的书写形成了一个以《儒林外史》为标志的士人集团形象,这是金陵小说帝都书写不同于一般帝都书写的独特之处。因此说,帝都兴亡思辨情结和儒林世界是金陵小说帝都文化书写的两个重要向度。
一、龙盘虎踞随流水:宏伟壮丽的“帝都文化气象”与“帝都兴亡情结”
明清金陵小说中的南京,凸显了其作为帝都城市的特殊政治、军事、经济地位,对这座城市文化的书写具有帝都色彩。
(一)壮观宏伟、天下盛景的帝都文化气象
《醉醒石》第一回就写了南京的雄伟景象:
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盘虎踞,帝王一大都会……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衙,三衢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娈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2]3。
南京较之一般城市,政治中心的独特地位给这座城市积淀了独特的政治文化内蕴,体现在小说作品中,往往形成一种浓烈的政治情怀和地理条件独特的优越感。纵观明清小说对南京的书写,大都喜欢渲染城市的“王者之气”。南京坐拥长江天险,龙盘虎踞,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繁华的经济,奠定了其成为封建王朝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政治中心地位。
相比之下,明清小说中常见的同为江南著名都市的苏州、扬州、上海等,作品或凸显城市商业繁华、富庶奢华,或突出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总是少了金陵的龙盘虎踞的“王者之气”。如,《女开科传》第一回如此描写苏州:
却说这苏州,古名阳羡。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沃衍,江南之都会也。佳胜第一是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一名海涌峰,上有剑池、千人石、生公说法台、吴王阖闾墓。[3]
《海上繁华梦》开篇描写的上海,则是一副奢靡腐化的升平景象:
况乎烟花之地,是非百出,诈伪丛生,则又梦之扰者也;醋海风酸,爱海波苦,则又梦之恶者也;千金易尽,欲壑难填,则又梦之恨者也;果结杨梅,祸贻妻子,则又梦之毒者也;既甘暴弃,渐入下流,则又梦之险而可畏者也。[4]
明清小说中的扬州则是和风月纠结缠绕在一起,盐商的财富风流、挥金如土和扬州风月华糜、骄奢淫逸血脉相连。张岱《陶庵梦忆》中的扬州风月被渲染为“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其间”[5]。
在这里列举明清小说中苏州、扬州、上海的例子,是因为这些城市都是明清小说书写的重要内容,而且,明清这些城市形成了当时国内最庞大、城市化水平最高、地域文化特征最类似的江南都市群落。在同类城市中比较南京文化景观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才能从学理上证明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文化景观书写的独特性。
明清小说对南京城市景观空间的叙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在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算得上是“为南京文化所化之人”,《儒林外史》全书一共56回,其中近乎一半的章节发生在南京或者与南京直接相关,这些章节往往不惜笔墨对南京城市帝都宏伟气象浓涂重抹:
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船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6]187
《儒林外史》对南京城市空间的描写,涉及秦淮河、莫愁湖、玄武湖、清凉山、雨花台、燕子矶、鸡鸣寺、水西门、泰伯祠等著名景点,展示出南京特有的宏大壮丽的城市文化底蕴。《玉娇梨》第四回写灵谷寺的南京梅花,称赞为“金陵第一盛景”,“到春初开时,诗人游客无数”[7]。
除了四通八达的街巷,水路也是南京交通的重要渠道。《儒林外史》对秦淮河的描写尤其突出,其第二十四回、二十五回和四十一回都对秦淮河的特点大费笔墨,小说中的秦淮河里城门有十三个,外城门有十八个,绵延蜿蜒穿过整个帝都,仅城内的长度就有四十里,沿着城市一转一百二十多里,如此长的秦淮河,勾连数十条大街,数百条小巷,尤其是夜晚来临,街上灯火通明,河边画船笙歌,恍如人间仙境。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中,小说中渲染了秦淮河的交通发达、画舫争辉的场景,“酒馆十三四处,茶坊十七八家。端的是繁华盛地,富贵名邦”[8]。
(二)历史兴亡、民族盛衰的深层次“帝都兴亡情结”
在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看来,城市并不仅是建筑物的群集,还是各种密切相关并且相互之间经常发生影响的不同功能的集合体,这就意味着城市在本质上不仅是权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极”[9]。这在明清小说对南京的描写上尤其明显。南京在明清小说中的存在是个“有意味的形式”。南京成为留都后,衙门官制都是给予保留的,其实质上扮演了南方政治中心的角色。所以明清时期的文人更愿意将之视为帝都,并鲜明地体现在小说创作上。《醉醒石》第一回就描写了南京的“龙蹯虎踞”的帝都气象,渲染了明太祖时期“真是说不尽的繁华”,虽然迁都北京之后,失去了帝都的雄风,但是山川如故,自然和其他州府拥有不同的气象:
自东晋渡江以来,宋、齐、梁、陈,皆建都于此。其后又有南唐李璟、李煜建都,故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虽迁都北京,未免宫殿倾颓,然而山川如故,景物犹昨,自与别省郡邑不同。[2]3
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积淀了深厚的帝都文化底蕴,但是,政权更迭频繁,过于短促的命运总是不断落到这座城市头上,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乃至后人提起这座城市就充满了伤感,甚至把南京作为风流云散的象征,变迁和流逝似乎成了南京文化的品格。这意味着明清小说对帝都城市王者气象的渲染有多么宏大壮阔,就会对其衰落感伤多么沉痛。如《西湖二集》卷二对南京从帝都衰落的感慨:
又因金陵是六朝建都风流之地,多有李后主、陈后主等辈贪爱嬉游,以致败国亡家、覆宗绝祀,所以喜诵唐人李山甫《金陵怀古诗》,吟哦不绝,又大书此诗,揭于门屏道:“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10]
对此,《儒林外史》的篇首词表达得更为深刻:“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这是深刻理解南京的帝都兴衰历史后的感叹,在这里,历史情绪已经逐渐演变为人生情绪[11]。也就是说,金陵小说中的帝都情怀首先站在国家、历史和民族命运的角度上,然后才是个体的感伤。而描写扬州、苏州、上海等小说中的感伤更多地着眼于生命个体对城市繁华不再、风流云散的悲哀,两者还是有微妙区别的。南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后被江南其他城市所取代,在前朝的荣耀和后世的衰落对比中,强烈的反差和失衡是后帝都时代不得不面对的困窘。于是,在强烈的失落中滋生出越发浓重的“东南第一州”的梦华和“金陵帝王州”的怀旧情结,这就成为帝都城市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这种情结深深影响了历史上有过帝都经历的杭州和金陵,也正好契合了金陵小说作者的创作心理和动机[12]。所以,“帝都文化气象”宏伟壮丽的书写背后,不可能没有沉郁浑厚、历史兴亡的“帝都兴亡情结”。
相比之下,明清小说中有关扬州、苏州的文字也抒发了城市衰落的感伤,但是,这种感伤明显少了历史兴亡和国家命运的味道。这在扬州小说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如《品花宝鉴》第五十五回通过扬州富商精心构筑的园林庙宇的荒废中看到文化的凋敝:“又见几处阁楼,有倒了一角的,有只剩几根柱子竖着的,看了好不凄凉。”[13]同样是城市衰微,扬州的盛极而衰是无可挽救的事实,苏州的江南中心城市被迫让位于上海,则是无可奈何的失落与不甘,而上海从小镇崛起后陷入娼妓、赌博昌盛的深渊,凡此种种,促使晚清知识分子们在一种失落无奈、愤恨郁闷的现代性情感体验中咀嚼无尽的苦楚[14]。这些城市在明清小说中的书写,都普遍缺少了帝都兴亡的沉重思考,这是南京作为帝都城市有别于明清时期其他繁华城市的重要区别。
这种帝都特有的“王者之气”以及饱经历史盛衰沉浮的情怀,终究会潜移默化地浸染到帝都底层市民的身上,由此形成了南京市民屡经政治风云变幻而宠辱不惊的气质,这种举重若轻的风度,依稀有帝都饱经历史沉浮沧桑的影子。
二、礼乐教化不僭越:崇尚礼仪的帝都科举文化
帝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具有浓郁的政治文化氛围。南京作为当时东南地区的文化中心,是举行乡试的考点,设有国子监,由此形成了封建帝都城市特有的科举文化景观。
(一)聚焦江南贡院、河房等科举文化符号的书写
明清南京的科举文化景观离不开江南贡院。封建科举考试等级繁多,士子科举场所并非帝都专有,但是,在整个明清小说书写的城市中,能够借助贡院等科举场所,把士人科举盛况渲染如此浓烈的,只有金陵。余怀《板桥杂记》中描写了江南贡院与士子科举的盛况:
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若夫士也色荒,女兮情倦,忽裘敝而金尽,遂欢寡而愁殷。虽设阱者之恒情,实冶游者所深戒也。青楼薄幸,彼何人哉![15]
江南贡院规模最大的时候,占地约30万平方米,东起姚家巷,西至贡院西街,南临秦淮河,北抵建康路,为夫子庙地区主要建筑群之一。这是中国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而秦淮河畔也因贡院、夫子庙的存在而繁荣起来。《儒林外史》对南京的科举文化有生动的描述:
话说周进在省城要看贡院,金有余见他真切,只得用几个小钱同他去看。不想才到“天”字号,就撞死在地下。众人都慌了,只道一时中了邪。行主人道:“想是这贡院里久没有人到,阴气重了。故此周客人中了邪。”金有余道:“贤东!我扶着他,你且到做工的那里借口开水灌他一灌。”行主人应诺,取了水来,三四个客人一齐扶着,灌了下去。喉咙里咯咯的响了一声,吐出一口稠涎来。众人道:“好了。”扶着立了起来。周进看看号板,又是一头撞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也劝不住。[6]27
同样的情景在小说《醉醒石》中也有所体现,《醉醒石》第一回写主人公姚一祥去南京纳监。《欢喜冤家》第十回写许玄到南京应试,直接去贡院寻找住处,结果发现“家家歇满,再无寻处”,无奈之下,在贡院对门,发现“内有静室,安歇状元”[16]187。小说第二十回写到南京考试的举子太多,城中出现了大户人家专门租房给这些参加科举考试的人的现象。这些房屋环境“极其清幽”,利用科举考试期间,各地举子云集南京的机会,出租给他们,“常收厚利”[16]334。
明清小说对金陵科举文化景观的叙事,还出现了一个南京独特的地理空间----河房。所谓河房就是一种临水而建的楼阁。一方面,南京的河房是参加科举的士子们居住的地方。明代科举取士的贡院建在秦淮河边,进京赶考的举人或是做官的人便居住在河房内。达官显贵的到来,促使秦淮更加繁华,河房也成为人们娱乐享受之地。如《儒林外史》第四十一回,杜少卿邀武书泛舟秦淮时,便是在河房里吃的午饭。河房沿岸,风景独佳,交通便利,且周边邻近贡院和市场,所以前来应试的人多爱居住在这里。《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刚到南京找房,恰逢乡试期间,众多应考的文人租住河房,也将河房的价格哄抬而上。文人骚客的求学入仕之道,带动河房经济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名声大噪。另一方面,秦淮河边的河房也是风月文化的符号。众多王孙子弟、富商绅士常在这里狎妓吹唱。每当乡试之年,天下应试者云集于金陵,文士们往往在居住河房期间狎妓以排遣苦读经书的寂寞和枯燥。科考以后,焦急等待张榜之时,河房是他们排遣寂寞的最佳选择。能金榜题名的考生毕竟少数,众多落榜士子为了打发内心失落惆怅,也会在河房里纵情声色。
由此,南京河房形成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科举文化符号:科举是无数士子博取功名的捷径,入住河房就应该自觉遵守礼仪之道。而河房又是当时南京最著名的风月场所。二者原本水火不容,但是,在明清江南城市文化中,科举士子和青楼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故事,在无数诗文中显现。士子和妓女联姻,前者排遣读书的枯燥乏味,后者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二者似乎缺一不可,其完美结合恰恰成为了明清科举文化的典型符号。
(二)恢复礼乐祭祀文化传统的思想
研究《儒林外史》对南京的叙事可以发现,作家借助这个城市以及城市中的人,想要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恢复礼乐兵农的传统。这正是封建帝都重视的传统。如第三十三回:
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乐……[6]309
小说对南京雨花台和清凉山的叙事,并不仅仅停留在描写自然风光美景层面上,正如吴敬梓在《金陵景物图诗·雨花台》中写的:“缓步上平岗,怀古寻断碣……柳阴酒旗扬,柳色茶烟结……都人修礼乐,用以祀仓颉。”[17]44雨花台的魅力还在于体现了礼乐文化的人文景点,如,方、景诸公的祠,“夷十族处”和泰伯祠大殿,这些都明显具有礼乐的浓重味道。对南京文化气象的描写,不能绕开泰伯祠。这是尊重礼教的典型文化符号。《史记》对吴太伯的记载具有丰富的政治文化内蕴,一方面,司马迁人物评价体系的核心是品德而不是才能,这一评价体系直接承继于孔子,包含了他对文明礼乐传统的肯定。另一方面,《史记》记载太伯有国号:句吴。国号是国家的标志,而太伯能聚集民众,无疑是以“义”为凝聚力,如此一来,太伯奔吴就有了明确的政治礼教文化的色彩。
《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描述了泰伯祠的气概以及隆重的祭祀礼仪场景。小说通过杜慎卿以世俗的眼光评价坚决维护礼乐制度的方孝孺,描写礼乐文化在世俗中遭受的质疑和嘲笑,侧面表达了作者极力主张振兴礼乐文化的意图。
诸葛天申见远远的一座小碑,跑去看,看了回来坐下说道:“那碑上刻的是‘夷十族处’。”杜慎卿道:“列位先生,这‘夷十族’的话是没有的。汉法最重,‘夷三族’是父党、母党、妻党。这方正学所说的九族,乃是高、曾、祖、考、子、孙、曾、元,只是一族,母党、妻党还不曾及,那里诛的到门生上?况且永乐皇帝也不如此惨毒。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6]273
在杜慎卿的眼中,宁愿被诛灭十族也不违背礼乐正统的方孝孺,只不过是一个“迂而无当”的腐儒,他的死“不为冤枉”,作者借此批判当时的礼乐传统在现实中遭遇的阻隔,力图呼唤恢复礼乐传统。
小说中的雨花台是作为礼乐文化的符号描写的,《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通过小说人物迟衡山的口,批评世人全然不问礼乐兵农之事,倡导要重振礼乐兵农。而这样写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让大家学习礼乐,给社会培养一些人才,更可以为国家政教服务[6]381。正如吴敬梓在《金陵景物图诗·雨花台》中写的“都人修礼乐,用以祀仓颉”[17]44。雨花台不仅具有世俗的休闲景观,还承载了那个时代文人试图恢复礼乐正统的情感。
三、魏晋风流成记忆:儒雅旷达的士林文化气象
追溯南京城市文化的底蕴,无疑要从魏晋风流说起。虽然从魏晋到明清,已经间隔了上千年,但是其帝都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产生的影响力,浸润了魏晋以降的南京城,加上明朝初年,南京再次成为整个封建王朝的帝都,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南京市民的政治情怀。
吴敬梓深受魏晋六朝风尚的影响,仰慕六朝人物的不拘礼俗、诗赋人生的风流倜傥,他的南京情结自然而然地寄托在南京城市的一草一木之上。他是明清儒林中的一分子,他的政治梦想希望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得以寄托,《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就有着作者的影子。他对儒林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儒林政治理想空间的描写,其实质上就是把南京作为当时文人士子的活动舞台。《儒林外史》的人员构成极其复杂,既有以王冕、杜少卿、虞博士、庄绍光等为代表的真名士,也有以匡超人、杜慎卿等为代表的假名士。这些人虽然皆为名士,但是在品行和人生追求上却有天壤之别。
又如《鼓掌绝尘》月集中的金陵秀才王瑞,为了争夺教习职务,和另一个儒生李八八大打出手,完全一副无赖形状。除了王瑞、李八八这类士人形象,《鼓掌绝尘》还塑造了陈珍这类无耻文人形象,甚至写了私塾先生携学生一起嫖妓的故事,形象勾勒出帝都“礼崩乐坏”的现状。小说中南京名士文人形象的差异性、丰富性、复杂性,反映了南京作为政治帝都的文化历史的深厚。在封建科举时代,帝都是天下士人实现政治梦想的地方,金榜题名是士人普遍的追求,越是士人扎堆的地方,其政治性、文化性特征就越明显,这也是帝都和一般经济发达城市的区别之处。
(一)塑造了南京儒林名士怀慕隐逸、逃避现实的精神世界
《儒林外史》中的庄征君和虞博士就是这类代表。庄征君远离庙堂,退隐南京,享受南京湖光山色之美。他的隐逸就是看淡功名富贵后的举动。虞博士毕生愿望是能够积攒点散碎银两,每年能够让夫妻二人“不得饿死罢了”[6]263明清小说家们喜欢借助秦淮河表达落寞感伤之情,《儒林外史》中士人们的秦淮郁闷伤感情结还弥漫于秦淮河边的清凉山和莫愁湖上。这种回归自然的隐逸情怀,直接传承了魏晋风尚。明清时期的封建文人面对的政治环境虽然不同于魏晋时期,但是政治腐败加上江南地区一向崇尚奢靡,士人们往往因仕途不顺而多产生郁结颓废心理,因而寄情山水、游历山川成为诸多士人的精神追求。《儒林外史》第三十三回写杜少卿夫妇游山,作家借助所谓的名士们游玩清凉山,鲜明地揭示出隐逸士人的真面目,表明了作家对隐逸的看法:
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内,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喜喜,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嬉嬉笑笑跟着,两边看得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6]403
较之清凉山的文人游玩,《儒林外史》对玄武湖游玩的态度虽则看似不同,但是殊途同归,最终指向的都是文人心灵空间的自由。《儒林外史》写庄尚志游玩玄武湖时,夸赞玄武湖自然景色之美以及物产之丰富,然后笔锋一转,只说“这些湖光山色都是我们的了”,并且与杜少卿去清凉山看花喝酒相比,显示自己更为悠闲惬意,“在湖中着实自在”[6]418。这种行为被理解他的人视为“风流文雅处,俗人怎么得知”[6]451。
(二)观赏戏曲、怡情愉悦的帝都盛世下的烟火气
六朝风尚深深地遗存在广大南京市民尤其是名士文人身上,成为南京市民普遍存在的精神气质,虽然六朝风尚的内涵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展开,但是“六朝烟火气”可以说是六朝风尚的主流,也是南京名士文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梦想。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自然吸引众多士人来南京,从而形成南京一道文化景观。明清时期,每逢重要节日,城市一般都要举行各种隆重的庆祝活动,作为政治的中心,帝都的娱乐形式更是丰富而隆重。南京市民主要的文化生活为观剧和观灯。《儒林外史》对其进行了具体刻画。小说中提及的戏班多达一百三十个,它们大多分布在淮清桥和水西门一带,可谓戏班无数,而当地戏人也是唱功了得。人们无论是闲是忙都是将戏曲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因而戏曲的欣赏群体不分彼此。《儒林外史》中鼓楼街薛乡绅家请酒,邀请了淮清桥的戏子钱麻子,而钱麻子行程太赶,没办法给大家娱乐,高翰林顿感无趣。戏子鲍文卿病故后,他的戏班子一蹶不振,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南京都市,到周边县城盱眙、天长一带演出,挣口饭吃。莫愁湖大会时,杜慎卿组织了一场彻夜狂欢的“宴席”,其中就以唱戏、观戏为主,引来城内各阶层的捧场和叫好。《儒林外史》第三十回,五月初三日,杜慎卿等人组织莫愁湖湖亭大会,邀请了萧金铉等文士以及梨园戏班子,挑选一个好日子,找一个“极大的地方”,再把“一百几十班做旦角的都叫了来”[6]377。让这些人每个人都做一出戏,最后由这帮士人给他们每个人的表现评分,按照色艺表现评出优劣等次,将名单张贴于通衢。这凸显了那个时代文人的集体行为。如此热闹的景观,自然引发当时众人围观,尤其是那些有钱人,只要听说有莫愁湖大会,都雇佣湖中打渔的船只,张灯结彩,来到湖中观看,往往直闹到天明才散:
到晚上,点起几百盏明角灯来,高高下下,照耀如同白日;歌声缥缈,直入云霄。城里知晓莫愁湖大会的都急急忙忙凑过来,争抢着观看叫好,场面壮观,一时传遍水西门,闹动了淮西桥。[6]280
看似是文人们的娱乐消遣活动,本质上则是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魅力外显,文人雅客们的泛舟秦淮、赏灯观火、登高作文,都在为南京不同于江南其他都市做了注脚。如杜慎卿登雨花台、杜少卿携着妻子到清凉山姚园游玩、庄征君搬住玄武湖等。不论是普通百姓的文化礼俗还是文人墨客的登山论词,都呈现了帝都市民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
从小说叙事技巧的层面上看,文人雅集不仅是一个空间单位,同时也是一个时间单位,就前者而言,文人雅集活动可以为小说中的人物聚合交流,以及故事的演变提供了特定的地理空间,就后者而言,小说中的人物聚合交流以及故事情节的推进,都将随着集会的时间流程而逐步进行[18]。如果我们再从文化心理的层面上看,文人们雅集唱和于秦淮河畔,大多是为了排遣内心寂寞,或附庸风雅。优美的景色吸引了无数游人观赏游玩,秦淮河就成为了小说中描写的一个娱乐空间。但是,明清江南小说城市地标的一个变化就是不再局限于地理空间的层面,而是到达了文化的层面。以士林儒生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纷纷搭建自己政治梦想的舞台,由此形成了江南城市中独特的儒林世界。
(三)崇尚清谈、诗酒人生的风流旨趣
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崇尚清谈、诗酒人生的追求。《儒林外史》第二十九回写杜慎卿邀请萧金铉、季恬逸等人到寓所聚会。宴席上萧金铉说:“今日对名花,聚良朋,不可不诗。我们即席分韵,何如?”杜慎卿却道:“先生,这是而今诗社里的故套。小弟看来,觉得雅得这样俗,还是清谈为妙。”[6]362明清士人对仕途无望之时,就会寄情于魏晋风度,通过这种清谈暂时麻醉自己。小说中没有详细描写杜慎卿的清谈内容,究竟是人物品评,抑或是谈论《老子》《周易》《庄子》等“三玄”,但是,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塑造了这些名士对魏晋风尚的推崇。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他们试图在生活中有意识地模仿历史上的这种行为,以表达对政治生活失意后的淡漠。饮酒是魏晋风度的标志性文化符号,酒可以麻醉人的生理神经,也可以麻醉人的精神思维,魏晋时期的名士饮酒是为了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倾诉无力改变现实的无奈与无助,企图用醉酒的方式麻醉自己的仕途失意,也躲避随时而至的杀身之祸。受到这种风尚的影响,历代的文人都会借助这一生活方式表达内心世界。明清时期的名士面对政治仕途的失意或各种原因导致的内心失落,纷纷效仿魏晋名流。但是,明清士人的诗酒风流毕竟不同于魏晋,他们当中许多人扛着名士的大旗,却难以掩盖刻意的模仿和虚伪造作的本性,是所谓假名士、假风流。《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天长县同访豪杰,赐书楼大醉高鹏”中,杜少卿、张俊民和韦四太爷等人饮酒大醉,但是,杜慎卿表现出来的诗酒风流无不散发着矫揉造作的味道。这也表现了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内心世界、精神追求的虚伪。
从以杜慎卿为代表的这些士人热衷于魏晋风流、诗酒人生的生活趣味可以看出,明清南京的一批无所事事的士人,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假扮名士,刻意模仿名士风流,以此掩盖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士人们热衷于高谈阔论的行为,又反映了城市政治文化氛围的浓厚。因为只有热衷于政治理想却因为政治理想屡屡失败的士人群体,才会热衷于这种清谈。所以,当小说中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士人群体,而且,通过这些士人的娱乐休闲、高谈阔论去展示他们内心世界的时候,就可以看出南京作为政治帝都,在历史上积淀了深厚的科举文化底蕴。
当然,在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金陵小说中,士人群体呈现出来的生活趣味、价值观念仅仅是当时南京市民阶层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实,这种追求魏晋风流的高雅旨趣并不局限于文人群体,而是普遍存在于广大市民阶层中。吴敬梓把南京描绘成为文化的中心和礼乐规范的中心,这是对南京作为士人文化中心的充分肯定。小说第三十二回娄太爷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让杜少卿去那里才能凭借才情做出些事业来,这也体现出作者对南京帝都文化的认可。
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同样描写了江南的其他众多城市,如同为江南大都市的杭州和扬州,但是,在这些城市的书写中,南京始终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其城市士人云集的文化气象,远不是其他江南城市能够比肩的。小说中的南京宛如一个众星捧月的中心,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量和文化示范作用[11],这正是南京作为帝都具有特殊地位的文化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