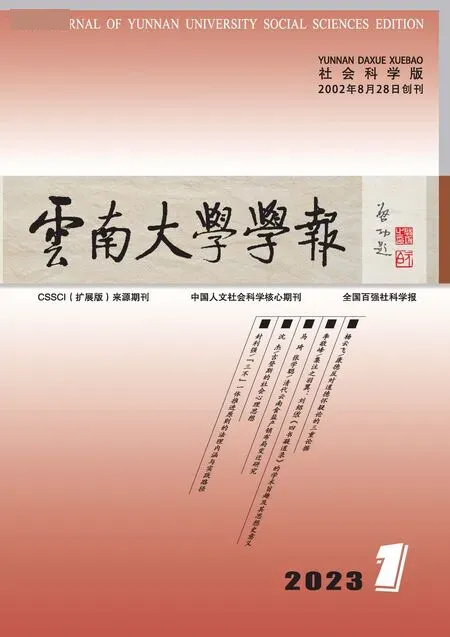《春秋》与《孝经》相表里
——曹元弼《孝经》学管窥
刘增光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一、曹元弼的《孝经》学著述
曹元弼(1867—1953),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谷孙,又字师郑,晚号复礼老人,故时人称他为复礼先生。曹元弼为清末至近代的重要儒者,名重一时,身处清末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之际,曹氏以承继绝学、发明圣道自任,专治经学,尤精于《易》《礼》与《孝经》三学,其造诣所至而精之尤精者则在所宗之郑氏学。时人评价其学“泯汉宋之成见,启后学之津途”,“尊汉学而不薄宋儒,详训诂而兼疏义理”,甚至比之于顾炎武。(1)《吴县吴郁生致曹元弼书三》,《昆山李传元致曹元弼书一》,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7、40页。又谓其能“正人心,辟邪说”,(2)《昆山李传元致曹元弼书一》,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友札》,第40页。“振纲常,扶名教,为宇宙间特立独行之真儒”。(3)《吴县吴郁生致曹元弼书四》,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友札》,第28页。其生平著述有《礼经学》七卷、《礼经校释》二十二卷、《周易郑氏注笺释》十六卷、《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卷、《孝经六艺大道录》一卷、《孝经学》七卷、《孝经校释》一卷、《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复礼堂文集》十卷、《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等等。此外,尚与梁鼎芬(4)梁鼎芬(1859—1919),晚清著名学者,曾因弹劾李鸿章而名震朝野。后应张之洞聘,主讲广东广雅书院和江苏钟山书院,为《昌言报》主笔。辛亥革命前有反帝主战思想,之后任溥仪的毓庆宫行走。梁氏师承陈澧,与曹元弼为好友。共同编著《经学文钞》。
据曹元弼所述,他起初治《礼》学,服膺郑学,但他夙夜庄诵《孝经》,以为礼根于孝,由此转而关注郑玄的《孝经注》。但郑《注》残缺,故欲“据近儒臧氏庸、严氏可均辑本,拾遗订误,削《群书治要》伪文,为《孝经郑氏注后定》。因遍辑经传周秦汉古籍各经师注涉《孝经》义者为之笺,而博采魏晋以来《孝经》说之有师法应礼道者,贯以积思所得疏之,约之以礼,达之《春秋》,合之《论语》,考之《易》《诗》《书》,疏文有所不尽,则师黄氏之意而扩充之,兼采史传孝行足裨补经义者,别为《孝经证》”。(5)曹元弼:《吴刻孝经郑氏注序》,载《复礼堂文集》卷六,国家图书馆藏1917年刻本。此《孝经证》即是他在《礼经纂疏序》中所说的《孝经纂疏》。(6)曹元弼:《礼经纂疏序》,载《复礼堂文集》卷四,国家图书馆藏1917年刻本。此二书很可能并未真正完成,但必须辨明的是,未成之因并非他没有撰述的动力,而是因为时事的刺激,他无法置身事外。及至后来,他的撰述想法发生变化,转而撰写《孝经郑氏注笺释》,以毕二书之功于一役。显然,《后定》和《孝经证》基本是考证性著作,无法纾解其挽救世道之热肠。《孝经郑氏注笺释序》中说:“寻世变日亟,邪说并兴,反天明,扰人纪,承阁师张文襄公见商,窃欲以《孝经》会通群经,撰《孝经六艺大道录》一书,以明圣教,挽狂澜。”(7)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国家图书馆藏1934年刻本,第11页。这意味着曹氏的想法变得更为通达宏阔,从先前的关注《礼经》与《孝经》的关联,变为以《孝经》汇通六经。但《大道录》只完成了《述孝篇》与目录,也未竟全功,今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刻本。未能写竟同样是因其想法之变化,在他将《述孝》拿给张之洞看过后,张“斟酌体例,欲经别为书,属撰十四经学”,由此才有《孝经学》一书的产生,此书完成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印成则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8)曹元弼:《周易礼经孝经三学合刻序》,载《复礼堂文二集》卷一,复旦大学图书馆藏1948年钞稿本。亦可参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3、85、89页。但张之洞于第二年遽然离世,此后的治经生涯,正如曹元弼所言,“孰意天降大戾,中原陆沈,闭户绝世,笺释《周易》十有七年,至痛在心,精力消耗,重以两昆皆逝,百感填膺,自顾衰颓,深恐数十年治经心得遗忘消沈。既成《大学·中庸通义》,复致力《孝经》,考定郑《注》,补其缺文,昭析区别,传信将来,博稽古训为之笺,而以积思所得贯穿群言释之。战战兢兢,如临父母,如临师保,覆更详审,历一年余,成书三卷。”(9)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12页。清朝灭亡,人世已换,曹氏又回到了他治《孝经》学的早期想法,完成对郑《注》的复原以及为《孝经》作别证和笺释,这就是《孝经郑氏注笺释》,此书正是以《孝经学》一书为基础,集合了《后定》《孝经证》《大道录》等三书的内容。仔细阅读《笺释》,会发现《大道录》目录所列的内容,《笺释》皆有阐发。据此可说,三书虽未完成,实则皆已完成。据《孝经郑氏注笺释序》之末尾所标时间,此书当完成于1934年,而刊印则是在1935年。《孝经校释》的刊印亦在是年。但《孝经校释》的写作应该也历时较长,至迟在宣统元年(1909年)时就已经开始。(10)马季立在致曹元弼书信中提到:“《孝经疏》校文体勘入微,足称经神。”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第86页。其写作过程很可能正好与《笺释》相始终,故二书亦一并刊印。《笺释》今有刻本、活字本(仅有一册一卷)。《孝经集注》则成书于1943年。据此以观,曹元弼治《孝经》,确然如其所言,“出入四十年矣”。(11)曹元弼:《孝经校释》,国家图书馆藏1934年刻本,第9页。
二、《孝经》为六经之总会
“《春秋》与《孝经》相表里”可以说是曹元弼《孝经》学的基础命题,他在《孝经郑氏注笺释》全书的开篇就说:
昔孔子兼包尧、舜、文、武之盛德,著之《春秋》,以俟后圣,遂檃栝六艺大道,探本穷源而作《孝经》。(12)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1页。
这一说法代表了他对孔子之学的理解,这一理解得以形成的媒介正是郑玄。追溯历史,《孝经》和《春秋》相表里的观念,在汉代即已形成,其首倡者当为董仲舒,虽然他并未明确提出这一命题,但其论述中已蕴含此义,只待临门一脚,而《孝经纬》终于将此概括提炼了出来。东汉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亦贯穿了这一思想,遗憾的是,何休的《孝经注》未能流传于世。而在郑玄看来,这一观念的正式提出却并不是董仲舒,而是在先秦,尤其是子思所作《中庸》,或正如《孝经纬》所载“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所示,这一观念在孔子那里便已形成。而在郑玄这里,这一命题更为基础的背景则是孔子删定六经,这一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未必真实的历史事件——但肯定是真实的思想史事件,也就是说,六经是折衷于孔子的,正如孟子所言,孔子是尧舜禹汤文武以来的“集大成之圣”。郑玄《六艺论》言:“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经》以总会之。”曹元弼在《孝经郑氏注笺释》的序文中就将这段话揭示了出来。(13)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 2页。郑玄之言意味着,《孝经》为孔子晚年所作,既是六经之总会,又是夫子的“晚年定论”。汉儒继承孟子之说,以《春秋》为孔子据鲁史所作,《春秋》由当代之史变成了孔子之经,《春秋》自然就有了特别的地位,而如果说《春秋》尚在经史之间的话,那么,《孝经》就是纯粹的经了,因为《孝经》并没有所据之史,亦没有尧舜禹汤文武的历史遗传,故此书才纯然是孔子所作,纯然是经。曹元弼对于《春秋》和《孝经》的区别有清晰的意识:“子曰:‘《春秋》属商,《孝经》属参。’但《春秋》经既成,而以义属之。《孝经》则授以大义,即笔之为经,此记事、论道之别也。……此经为夫子所自作,即录由曾子,所录固一如夫子本语,且必由夫子审正定名,故于《春秋》并为圣作之书。”(14)曹元弼:《孝经校释》,第5页。以《孝经》为纯然论道、讲大义之书。当郑玄说“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之时,似乎已然是说,六艺是不能称经的,因为经是普遍的、万世不易的常道。故从《易》《诗》《书》《礼》《乐》五者的删定到《春秋》,再到《孝经》,一方面是孔子被圣化乃至神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纯然之经形成的过程,这也正是汉儒强调《孝经》之名含“经”字而六艺却不含“经”字所包含的意蕴。曹元弼即认为“圣人之书皆本天经地义,此经论孝,直揭其根源,故特名曰《孝经》,此孔子所自名,明孝为万世不易之常道也”。(15)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国家图书馆藏1934年刻本,第4页。“此经为夫子所自作,即录由曾子,所录固一如夫子本语,且必由夫子审正定名,故与《春秋》并为圣作之书”。(16)曹元弼:《孝经校释》,第5页。这就意味着,经名始于孔子,六经之称经,也正是赖于孔子。故而对于孔子思想的真正理解必然不能脱离《孝经》,故朱熹之作《孝经刊误》自然会被曹元弼所批评。曹元弼解释郑玄《六艺论》之“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一段文字,并藉以申发孔子删定六经之意:
此郑君《六艺论·论〈孝经〉》逸文也。古者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而乐正以《诗》《书》《礼》《乐》造士,谓之四术。《易》为筮占之用,掌于太卜。《春秋》记邦国成败,掌于史官,亦用以教,通名为经。《礼记·经解》详列其目,至孔子删定《诗》《书》《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其道大明,学者亦谓之六艺,七十子之徒身通六艺是也。六艺标题名目不同,如《易》取易简、变易、不易之义,《诗》之言志,《礼》之言体、言履之等。指归意义殊别,如《易》明天道,《书》录王事,《诗》长人情志等。六艺皆以明道,而言非一端,时历千载,既名殊意别,恐学者见其枝条之分,而不知其根之一,见其流派之岐,而不知其源之同,如此则大道离散,而异端之徒且得乘间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为天下后世大患。故孔子既经论六经,特作《孝经》立大本以总会之。盖六经皆爱人敬人、使人相生相养相保之道,而爱敬之本出于爱亲敬亲,故孝为德之本,六经之教由此生。(17)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郑氏六艺论》,第1页。
依此,《孝经》之所以为六经之总会,正是因为《孝经》所发明者为爱敬之旨,这是天下治乱的根源所在,故曹元弼言《天子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两句是“全经要旨,五孝通义”。(18)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57页下。唐文治在读曹元弼著作后,谓:“兄日来往复展读‘身体发肤’节,并《天子章》《士章》,探索无遗蕴,可谓扩之极其大,析之极其精,裨益世道非浅。”见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第167页。“爱、敬二字为《孝经》之大义,六经之纲领。六经皆爱人敬人之道,而爱人敬人出于爱亲敬亲”。(19)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58页。曹元弼阐发《孝经》爱敬之义,正可与其早期的《原道》《述学》《守约》三篇文字互相参看。其详尽之说如下:
《孝经》之教,本伏羲氏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易》《诗》《书》《礼》《乐》《春秋》一以贯之。盖六经者,圣人因生人爱敬之本心而扩充之,以为相生相养相保之实政。《易》者,人伦之始,爱敬之本也。《书》者,爱敬之事也。《诗》者,爱敬之情也。《礼》者,爱敬之极则也。《春秋》者,爱敬之大法也。爱人敬人,本于爱亲敬亲。孔子直揭其大本以为《孝经》,所以感发天下万事之善心,厚其生机而弭其杀祸,故战国暴秦积血暴骨之后,有天下者得由此以拨乱反正,胜残去杀,天下屡乱而可复治。(20)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6-7页。他在解释《庶人章》时说:“圣人之道务在有始有卒,故《周易》首乾‘自强不息’,《尧典》始钦,《礼》主于敬,《论语》首‘学而时习’,称‘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学本于有恒,化成于久道,真积力久则强力不反,政如农功,日夜以思,思患豫防,则身安而国家可保,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诗》曰:‘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此正是强调六经皆言“敬”。见《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120页。
六经一以贯之,贯之以爱敬,爱敬则本于孝,故《孝经》为总会与根源,而这也意味着《孝经》蕴含的是伏羲以降历圣修己治人之精义。这是曹元弼对郑玄《六艺论》论《孝经》之旨的理解,也是他对孔子作《孝经》的理解。虽然严格说来,郑玄并未像他这样强调爱敬之义。又据他对郑玄之理解,修《春秋》诛乱臣贼子以定天下,作《孝经》以辟异端而明大道,“辟异端”并非自孟子始有之。《孝经》即是孔子担忧后世“枝条之分”“流派之歧”,预见“异端之徒且得乘间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为天下后世大患”,故而作此经。曹元弼在《孝经学·孝经微言大义略例》中亦曾阐发此意说:
凡《孝经》为六艺之总会,以《孝经》通《易》而伏羲立教之本明。以《孝经》通《诗》《书》而民情大可见,王道益灿然分明。以《孝经》通《礼》,而纲纪法度会有极、统有宗,法可变,道不可变。以《孝经》通《春秋》,而尊君父、讨乱贼之大义明,邪说诬圣不攻自破。以《孝经》权衡百家,如视百辰以正朝夕,是非有正,异端自息。异端之说不同,而归于无父无君则同。父子君臣之大义明,则百家之毒尽去,百家之长皆可用。以《孝经》观百代兴亡,而爱敬恶慢之效捷于影响,昭若揭日月而行。(21)曹元弼:《孝经学》,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1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8-609页。
这段话的论述方式体现了曹元弼自己对《孝经》为六经之“统宗会元”的理解,即以《孝经》为阐明父子君臣大义之书。反之,异端则归于“无父无君”。换言之,孔子作《孝经》即是要杜绝异端无父无君之说。所谓“法度”或“纲纪法度”,即是指父子君臣大义,也就是三纲。以儒为宗,以《孝经》为经,百家皆折衷于此,即意味着在现实中要以天子为尊,故而曹氏特重《孝经·天子章》。这也正是其通过解经而响应当时现实的体现。
三、《春秋》和《孝经》相表里
以父子君臣大义或三纲为《孝经》主旨,这也正是曹元弼“《春秋》和《孝经》相表里”说的旨义所在,在他这里至少又可分几层含义:首先是德主刑辅,亦即黄道周《孝经集传》所言“贵道德而贱兵刑”。曹元弼说:
《孝经》于《天子章》特引《甫刑》,恻然胜残去杀太平刑措之思。《纪孝行章》深重丁寍,戒孝子深防祸乱兵刑。《五刑章》怵惕震动,为万世将干天讨者大声疾呼,出之禽门而返诸人,出之死地而返诸生,凡欲以道德化兵刑也。董子曰:“天道大者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使阳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22)《汉书·董仲舒传》文。此《春秋》义,即《孝经》义也。夫孝,德之本,刑自反此作。(23)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7页。
在曹氏之前,清儒简朝亮已注意到《天子章》的“刑”字,谓“今《甫刑》言一人有德之善,众民皆赖之以善,其意谓天子尚德不尚刑也”。(24)简朝亮:《孝经集注述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曹氏当受此影响,此外,他更是深受乾嘉汉学阮元的影响,依阮元之说,“《春秋》以帝王大法治之于已事之后,《孝经》以帝王大道顺之于未事之前”,(25)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9页。“惟其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经》之顺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弑父、臣弑君,亡绝奔走,不保宗庙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乱也”。(26)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10页。此为阮元《孝经解》文。曹元弼概括说:“天下之治,治于君臣,而本于父子,此《孝经》《春秋》相辅为教,所以为万世不易之圣法也。”(27)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序,第11页。此即是其第二层意涵,即曹氏常说的忠孝一体或忠孝同理。《孝经·士章》明明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以事父为爱敬兼尽,但曹元弼则论证说:“事君亦爱敬兼尽,但父子主于恩,君臣主于义,虽元首股肱,休戚一体,而上天下泽,名分綦严,故事君以敬为主,忠孝一理。事父之敬,敬之至也。敬君与父同,则爱在其中矣。”(28)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104-105页。由此,他认为“《孝经》此节三纲大义,自伏羲定人道以来,至周公制礼而其理始曲尽,学者以此治礼,若网在纲,一以贯之矣”。(29)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108页。简言之,《孝经》已有三纲、五常之说:
人情莫不怙恃父母,而父尊母亲;人类莫不倚赖君父,而君尊父亲。经文此数语,人伦之大本,礼教之纲领。“盖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子者,父之子。母统于父,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夫为妻纲,故父为子纲。父者,子之天。君者,臣之天。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君为臣纲。三纲者,人伦之本,爱敬之原。(30)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105页。
这段论述体现出曹元弼有以“三纲”等同或替代“孝”的倾向。因为按照《孝经》之说,“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孝是爱敬之原,五教之本,但若按曹氏之意,三纲成了本原,显然与《孝经》以及他的其他论述是不相应的。
正因为强调忠孝一体,故与董仲舒针对君主的天谴灾异说、何休的《春秋》黜周王鲁等公羊学的重要观念不同,曹元弼对这些观念完全不赞成,他取消了《春秋》公羊学的革命义和“贬天子”义,而重点发挥了“尊王”和“退诸侯、讨大夫”之义: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以其奠安万世之父子君臣也。乱臣贼子欲致难于君父,必先殚残圣法,是以往者大慝未作之先,黜周王鲁、素王改制之诬说(31)曹元弼在早期写作《孝经六艺大道录》时所列的目录中就有“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第五:辟黜周王鲁、素王改制之谬”。,先已簧鼓鼎沸,岂知《春秋》讨乱贼,《孝经》明君臣父子大义,圣人之教自相表里,炳如日星,且《孝经》言以孝顺天下之道必推本先王,严父配天特称后稷、文王、周公,《中庸》述《孝经》《春秋》之义,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曰:“宪章文武。”尊王之义,所以立人伦之极,而维天地之经,布在方策,岂奸逆所能诬。特风俗日非,人心好亡恶定,凶德悖礼之说横流日甚,胥天下而裂冠毁冕,拔本塞源,浩劫弥天,杀机遍地,不胜为乾父坤母之赤子忧耳。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君子反经而已矣。聚百顺以事君亲,明圣法以息邪暴而已矣。(32)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51页。
所谓“黜周王鲁、素王改制之诬说”,正是针对康有为等人的公羊学而言。曹元弼曾作《素王说》专辟素王改制之谬,认为素王绝不意味着“以《春秋》当新王”。且素王依照《庄子》之说,“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有德无位之称”,比如,乐尧舜之道的伊尹、陈述洪范九畴的箕子,皆是素王,孔子亦是。孔子所言“茍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及“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即是“素王之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即是“素王之法”。所以,素王就是指不得位而尤有道济天下万世之用的圣人。郑玄《六艺论》言孔子“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曹元弼强调,自号素王是“自伤之辞、自任之辞”,而非“自尊之辞”,孔子“不复梦见周公”“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即是“圣人之欲明王道自伤而自任”的证明。后世论者如杜预、孔颖达认为,董仲舒、郑玄皆主“孔子以王号自尊”之说,这是完全错误的。(33)曹元弼:《素王说》,载《复礼堂文二集》卷四,复旦大学图书馆藏1948年钞稿本。他看到了康有为公羊学对礼法人伦的破坏性,欲从根源上澄清“素王”之意。唐文治在阅读《素王说》后,致书谓:“《素王说》义正辞严,笔挟风霜,为万世人心世道计,洛诵拜服。”(34)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第159页。
正因如此,虽然曹元弼认为郑玄批注《孝经》是在早期,以今文之义解经,但他却屡屡援引《春秋左传》之文作解。与《公羊》之义长于权变不同,左氏之义则深于君父之伦。(35)《后汉书·贾逵传》记载贾逵对《左传》的发明:“《左氏》……斯皆君臣之争议,父子之纪纲……《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惩恶。”沈玉成先生指出:“礼的作用在《左传》里被空前强调。”沈玉成:《春秋左传学史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5页。曹元弼解释《天子章》就引《左传》襄公十四年文谓:
天子至尊,皇建有极,锡福庶民,故首明之。《曲礼》曰:“君天下曰天子。”《表记》曰:“惟天子受命于天。”《白虎通》曰:“天子者,爵称也,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又说帝王俱称天子。按:《春秋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又曰:“天之爱民甚矣。”天子者,天之子。(36)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55-56页。
这正是对《孟子·滕文公下》中“《春秋》,天子之事也”之说的接续。由此,即不难理解,他为何会认为《天子章》“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两句是“全经要旨,五孝通义”,并极力阐发爱敬之义了。既然《春秋》和《孝经》相表里,那么,《孝经》也包含以“天子”为重、为尊之意。他分析五等之孝说:
《孝经》于诸侯以下皆著“然后能保守”之文,见反是即不能保守。于天子独不然者,诸侯以下之不保,或由于上之削黜,天子则至尊无上,当时王室衰微,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圣人志在尊王,故总著其义于后,而深没其文于此,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即《春秋》书王以制叛乱之意。且引《书·甫刑》特见“刑”字,有奉天子诛乱贼之义,所谓《春秋》作而乱贼惧,《春秋》天子之事,于此见矣。(37)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63页。
这一分析,将诸侯、卿大夫、士之孝的成就与否皆系之于天子,足以显示曹元弼对尊王的强调。“圣人志在尊王”,《春秋》开首书王,《孝经·开宗明义章》开篇称“先王”,皆尊王之意,他说:“称先王者,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孔子论孝道必称先王,即《春秋》发首书王之义。以上治下,以圣治愚,以祖宗训孙子,一出言而法祖尊王之义昭若揭日月而行。”(38)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31页。而《天子章》末引《甫刑》语,郑注谓:“《书》录王事,故证天子之章。”也是其说之佐证。不仅如此,在曹氏看来,《天子章》引《书》还有另一层深意:“当时王室道衰,乱贼横向,《孝经》于《天子章》特引书《甫刑》,盖见尊王以制叛乱之义。且《甫刑》虽言刑辟,而其辞哀矜恻怛,不胜恤刑之仁,与《康诰》相类。春秋之末,天子微弱,陪臣放恣,德教无闻,刑肃俗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夫子欲变鲁尊周,使天子德教光于四海,而兆民无即于刑,正与《甫刑》恤刑之意相合。且引《书·甫刑》特见“刑”字,有奉天子诛乱贼之义,所谓《春秋》作而乱贼惧,《春秋》天子之事,于此见矣。”(39)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66页。《孝经集注》的批注中则说:“《孝经》于《天子章》特见‘刑’字,即《春秋》尊王以讨乱贼之义。”见曹元弼:《孝经集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王氏抱蜀庐钞稿本,第23页。据其所述,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阮福《孝经义疏补》的影响。此仍是发挥了《春秋》和《孝经》相表里之意。
不难看出,曹元弼深受《孟子》孔子作《春秋》之说的影响。在他看来,这恰恰表明,孔、孟之志行皆符合尊君之大义,他说:“孔子潜心文王,梦见周公,学礼从周,如有用我其为东周,盖欲以此道顺天下也。《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孝经》其大本乎!”(40)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41页。“或疑孔子谓鲁昭公知礼,而言卫灵公无道;孟子称齐宣王犹足用为善,而言梁惠王不仁。盖孔子之于鲁,孟子之于齐,臣也,故为尊者讳,虽去而有余望,其于卫于梁,应聘而未用,客也,故不在其国,则从《春秋》褒贬诸侯之正,论事是非之公。昔人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鲁国,盖皆体夫子爱君之心也。”(41)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51页。此又以《春秋》书法为孔孟辩护。
他尤其反感后世将《谏诤章》之“诤”解为“争斗”之“争”,认为这是“诬借争字以饰逆节者,岂知经所谓谏争,务以安利其君亲,忠孝之至也。彼乃敢肆行争夺以危害其君亲,此《孝经》所谓五刑之罪莫大,《春秋》所必诛之乱臣贼子也”。(42)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33页。相反,“孝子忠臣,极爱敬之诚以救其君父之失”,这才是“《孝经》与《春秋》一贯之大义”。(43)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32页。《孝经》之有《事君章》,也正是“承子道而特说臣道……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发《事君》章,而《春秋》之大义著矣”(44)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三,第46页。。不仅如此,“凡《孝经》言义即《礼运》十义。《圣治章》曰:‘君臣之义。’义之最重者”。(45)曹元弼:《孝经学·略例》,第6页。可见,他强调了《礼运》中的君臣之义,而非康有为所强调的大同说。
余 论
曹元弼曾撰写《礼运大同说》,批评清末至近代鼓吹大同的思潮,此文显然有针对康有为主张维新变法之成分。他的写作很可能受其友人李传元影响,后者在与曹氏书信中言及:“近有人创建孔教会,其名甚美,而莅盘敦、执牛耳者,乃属之离经叛道之渠魁,执《礼运》‘大同’数语及孟子‘民为贵’一章,遂强指孔孟为革命巨子,犹堪喷饭。不知《礼运》一篇虽出于子游氏之儒,说有似乎庄周,细绎词旨,盖谓三代以后非礼无以治人。如谓圣人薄禹、汤、文、武、成、周而慕大同,亦可曰圣人非宫室而慕窟巢、非火化而慕茹毛饮血乎?是不通之论也。至‘民为贵’一章,乃对君人者言之,决非扇耕凿之民而使为乱,是不待辩而明者。以孔教会之说为教,直是诬圣,岂云尊孔。……公意如何?”(46)崔燕南整理:《曹元弼友朋书札》,第41页。此说正是在消解孔孟思想中的革命义,而主张礼教义,反对以儒家为基督教化的孔教。这也正是曹氏《礼运大同说》一文的主旨。这与康有为主张孔子思想包括“微言大义”——以“微言”为大同,以“大义”为小康的说法差别甚明。曹氏及其友人否定此说,而直以小康为孔孟宗旨。当然,这也就与后来的现代新儒家熊十力以孔子思想唯有“大同”微言的观点又截然有别。此三者构成了清末以来儒者士人思考儒家与中国未来的三条路径。而曹元弼以三纲为伏羲以来之教的坚持,又似是在回应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批孔非儒论,如陈独秀即认为孔子是三纲的创始者,是中国的马基雅维利。(47)参见李源澄对陈独秀的评论:《与陈独秀论孔子与中国》,载《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第1195页。
此处有必要进一步交代清末今文经学与《孝经》学的交织。光绪年间,吕鸣谦作《孝经养正》一书,此书正文前有《条议》一篇,其中,最为新颖之处是提出了设立孔圣教堂的提议。这主要见于《条议》的第六、七、八条。第六条“推广孝道必设教堂议”,认为若期待人们自己买《孝经》、自己读《孝经》以及自己践履孝道,“断无此理”,因此,必须要“设立孔圣教堂,傍设曾子坐位”,然后定期行礼拜的仪式,且由掌教官主讲,对官员进行训导,同时“罗致绅耆士庶人入教,临期来堂听讲,音乐备奏,祭器俱陈”。以此施行于府厅州县。第七条认为这样做是振兴孔子之道的必由之路,正犹如孔子周游列国讲学习礼于大树之下一样。他认为施行这一做法,“纵然释、道、天主、耶稣等教盛行,孔子之道不至浸衰”。第八条为“设教堂可以明礼习乐议”,他设想的是兴复儒家礼乐文明,尤其是冠婚丧祭之礼,以此四礼的内容编辑为成书,然后“斟酌尽善,月以劝忠劝孝播为乐章,至于淫辞艳曲,宜禁革之。《孝经》讲毕,可以演礼习乐”,此正合《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的经义。(48)吕鸣谦:《孝经养正》,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五年刊本。由此可见,吕鸣谦关注现实,注重孝、礼二维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尤其是他关于设置孔圣教堂的提议,与康有为等人所持孔教说不谋而合,(49)吕鸣谦是否受到康有为影响,不得而知。更体现出了他对儒学以及中华文明前途的思考。也就是说,设立孔圣教堂也是推行孝弟礼乐教化的一种方式,看重的是庶民之教的问题,这与康有为的关怀是一致的。曹元弼大概因其名称而对孔教说多少有所误解。
在革命说与否定中国文化论调的举世汹汹之潮中,曹氏等人对于孝与礼的维护大概多为新潮知识分子所冷眼,1898年,沈曾植在阅读曹元弼《孝经六艺大道录》后致书黄绍箕说:“叔彦新著……粹然儒言,有关世教,而此间名士多轻之、讪笑之者,汉宋之障,乃至此乎?今日世道之大患在少陵长、贱犯贵,其救之术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开章首言学,举世知之;第二章重言孝弟,乃举世忽之。犯上之于作乱相去几何?而有子之言警切如此。夏间尝与叔彦言而太息,谓暇时当以弟字、顺字贯串作一文字,与渠书相为表里,初不料文字未成,而其言已不幸而中也。……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50)许全胜:《沈增植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0-211页。此所述正是当时维新党人如日中天时之情形,这绝非“汉宋之障”四字所能说明。沈氏欲以弟、顺二字为中心作文章,以发明孝顺之义,正与曹元弼强调《春秋》和《孝经》明王道讨乱贼的意图一样。不过,他大可不必为未能作成此文而感到遗憾,因为曹元弼在后来的《笺释》一书中以阮元相关著述为中心,对“顺”之义做了更加丰富的阐发。
唐文治亦极重《孝经》,他在《孝经大义序》中自述写作缘由谓:“近世家庭之际,日嚣日薄,丧失本真,于是恣睢残忍,杀机日出而不穷,夫杀机多则生机窒,生机窒而人道灭,于是造物遂以草薙禽狝者待之。呜呼,恫孰甚焉!”(51)唐文治:《孝经大义》,施肇曾刊本,1924年,第2页。他哀叹家庭的瓦解,正是有见于清末民初之非孝毁家论的破坏性。曹元弼之发明《孝经》,亦同样是在忧思中国之贫弱、中学之失传:
圣人垂训,炳如日月,万世治乱莫之能外。即今西国之所以能富能强,亦不过上下情通,同心协力,有合于爱之义;实事求是,弗能弗措,有合于敬之义,故西学富强之本,皆得我中学之一端。中国之所以贫弱,不在不知西学,而在自失我中学圣人之道。得其全者王,得其偏者强,有名而无实,甚至背驰而充塞之者亡。夫必实践我中学,而后可以治西学,而后可以富强无患。(52)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第121页。
可以想到的是,虽然曹元弼强调君臣之义的重要性,但他并非单纯为君臣一伦作辩护,也不是为他所身处的一朝一代作辩护,毋宁说他是在为三纲五常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做辩护。清末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为张之洞所赏识、与唐文治交好的曹元弼对于当时的朝廷政治、社会风气耳濡目染,其毕生用力于群经,以郑玄为宗,正是有着传统士大夫的以道自任之精神。正如他所说:“制礼自士始,士可不以名教纲常为己任乎!”(53)曹元弼:《孝经集注》,第37页。曹氏尤其强调《孝经》所含尊尊亲亲之义,“郊祀、宗祀配以祖、父,此周公立人伦之极,为制礼之本,孝莫大于严父,故周礼以尊尊统亲亲,万世彝伦于是叙焉”。(54)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二,第40页。“周人之诗,美太王、王季、文王之功德,并及太姜、太任、太姒,且上溯后稷而推本于姜嫄。惟严父,故历千载之久而统系一贯,报本追远,考妣同享,永永无极,此伏羲作《易》乾元统天坤元顺承之大义。至周公制礼,而其道始尽者。”(55)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二,第42页。以尊尊统亲亲,方符合“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的道理,如此,“则血统相传,百世不乱”。(56)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二,第39页。
据此可见,曹元弼欲辩护和维持的是圣王百世所同之道,“以孝治天下”意味着道统的流传尚须基于血统,曹元弼谓:“‘明王以孝治天下’一语实括人伦王道之全,此中国盛隆之时,所以为普天下大地中至治之国,而圣人至德,所以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也。”(57)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二,第17页。在中西交通的变局之下,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仅仅在于三纲五常,而且在于三纲五常背后的一贯相传的血统,换言之,倡言西化与变法者实则不明白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所在。那些毁家非孝者,欲决父子君臣之伦,乃至夫妇之伦,也正是不仅仅要废弃三纲五常,实则也是在置一贯相传的血统于不顾。此论与章太炎批评当时西化论者“徒知主义之可贵,不知民族之可爱”相近。显然,与张之洞一样,曹元弼是不会认同西体中用或全盘西化之说的,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之道是亘古不变的。这体现了他对中国之为中国、中学之为中学的体和用的坚守。他以《易传》为据,论及中西道器关系,认为《易传》既然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不是“上者为道,下者为器”,正说明道器不离,“自古无外道之器,亦无离器之道”,“器者,行道之实也。道者,制器之本也。今日东西洋各国器械日精,所以然者,人人有自奋之心,各为其主,各为其民也。中国习西器三十余年而无一器能及西人,所以然者,自秦愚弱黔首以来,大率视君父之忧、生民之祸,漠不关心,莫肯殚精竭力以求之也。夫道也者,纯则亡,杂则霸,咸无焉则亡。三代以上之中国纯则王者也,今日之东西洋杂则霸者也。若今日中国之人心负国殃民,安危利灾,本实先拨,何器之能制?”可见,他也认识到西方民主制之优处是“各为其主,各为其民”,主民一体。而中国之所以危亡衰弱,“器之不精”“器之不立”,其根本原因还在于“道之不明”“道之不行”。(58)曹元弼:《读〈易系辞〉知道器原始说》,载《复礼堂文集》卷二。但他终究还是回到了中体西用的思路,并没有认真对待西方的文化与制度,认为应当“以圣经贤传人伦道德为本,以西学声光化电为用,上保皇极,下济苍生”。(59)曹元弼:《〈周易〉〈礼经〉〈孝经〉三学合刻序》,载《复礼堂文二集》卷一。简朝亮《孝经集注述疏》中亦言及《孝经》之于中国为中国之意义:“或曰:‘《孝经》,中国之教,何也?’盖非先王者,非中国所以教孝也。夫中国而遵先王教孝焉,虽一衣也,不忘中国,彼其言其行,有不惟中国是尊者哉?”简朝亮:《孝经集注述疏》,第32页。而归极言之,此本即是《孝经》所立之本,故他在《孝经集注序》开首即言:“夫《孝经》之书,全体大用,固蟠天际地以治万世之天下而有余……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在此。”(60)曹元弼:《孝经集注序》,第1页。在《大学通义序》中亦言:“六经同归,千圣一道……作《孝经》以总会之,因极论道之全体大用。”(61)曹元弼:《大学通义序》,载《复礼堂文集二集》卷三。如此,则就文化政治而言,体用俱在《孝经》,此正是曹氏《孝经》学之根本大义。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