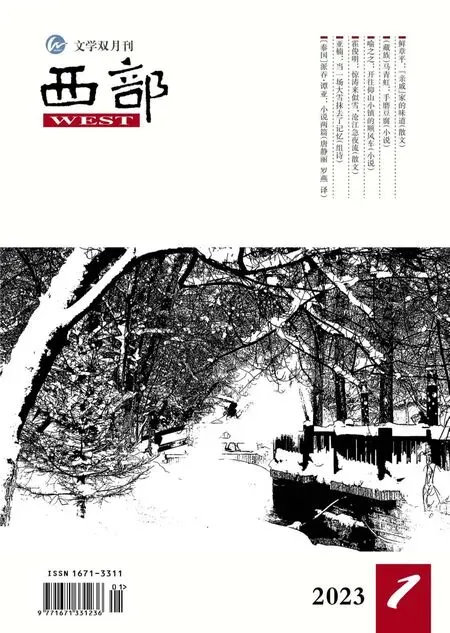手磨豆腐
(藏族)马青虹
请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
她左右探探头,用手摸座位下面,寻找着调整靠背的机关。这已经是广播里那个好听的声音第三次提醒了。她又双手伸到靠背的后面使劲掰,但靠背就是纹丝不动。她想,再找不到机关,自己就有被赶下飞机的可能。
她看了一眼旁边闭目养神的中年男子后,没有说话。就在她焦急寻找时,广播里的声音再次响起。
她把身上带着补丁的花布外套脱下,横放在腿上。看了眼正在关行李舱门的空姐,没有说话。
终于,在第五次广播响起的时候,刚才摆放行李箱的空姐注意到这个一头灰白短发的土气的奶奶。空姐利索地帮她调正了座椅。这时,她才发现机关就在扶手上。她抬眼正想说声谢谢时,空姐已经走了。
就在她刚准备打量周围环境的时候,飞机开始加速。
人在慢慢变小,机场在慢慢变小,城市和大地在慢慢变小。直到一切都被大雾笼罩。
她没有看窗外,也没有睡着,只是闭着眼睛缓解高速移动带来的眩晕感。这种感觉远比晕车更让她心惊,毕竟没有站在地上。不只是心,她整个人也悬着,像秋天里一片始终不能落地的叶子。
在这之前,她最远的一次出行就是十年前坐车到县城给准备办结婚证的儿子送户口本。提着起早磨好的豆腐,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客车。刚走到工厂门口蹲下,胃里就一阵翻涌。晕车的症状在看见儿子领着儿媳过来时才缓解了些。
晕车了没?儿子问。
没有晕车,身体好得很。她往旁边挪了挪,刚好挡住花坛里的呕吐物,顺势从包里拿出户口本,让儿子赶紧去办正事。
妈,那我们走了,你回去慢点。儿子办好结婚证就得立马赶回去上班,她看着载着儿子和媳妇的车子消失在前方的弯道,才想起忘了把豆腐交给儿子。那次媳妇叫她伯母,没叫她妈。
想到这里,她摸了摸脚下的蛇皮袋。如果凑近,还能闻到豆腐的味道。
今天,要坐飞机去儿子所在的城市,天还没亮,她就起床把豆腐磨好,到机场时豆腐还带着温热。过安检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不能带上飞机。辩解无果,她只好把豆腐丢进安检处的垃圾桶。
我不要这个,我不饿。她冲着空姐使劲摇头,摆动粗糙的手掌,小心地把递到自己面前的餐盒推远。
三个多小时过去,她想了许多,又觉得什么也没想,飞机便要落地了。她被窗外林立的高楼所震撼,也似乎明白了是什么吸引着儿子要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她试图猜想出儿子的家究竟在哪片楼房里。
由于不识字,她只好采取笨办法,刚才一起下飞机的人往哪里走,她就跟着走。
干妈,这边。她循着声音看见了正在接机口伸直了脑袋的干女儿小芝。小芝早在一周前就到了这里。
干妈,飞机应该不晕吧,我叫你吃点上次给你买的晕车药,你吃没?她刚从人群中走出,小芝就挽着她的手臂抛出一连串的问句。
没有,没有,身体好得很。她摸了摸小芝的手臂回答。
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说着小芝就带着她坐上出租车离开了机场。
雨水适时地洒落,由细微的毛毛雨到越来越多的雨滴从天上坠落——半透明状的,透明的是眼前的街道正不断积水,不透明的部分是整座城市的样貌越来越模糊。
车流从她这一侧过,车窗上已经挂起了珠帘,那些被车轮压碎的水发出手磨转动的声响。她捋了捋花白的鬓角,感到没有什么话可说。
你们运气不太好,刚好遇上台风,这雨估计得下一阵子了。司机感到不说话那些雨水便会淤积在胸口,沉默使他感到疲惫。
下雨就是不方便。小芝接话。
她们乘着车继续在宽阔的道路上行驶,被碾碎的雨水升上了半空,将这座城市装扮得更加迷离。她又回头看了一眼刚才的玻璃大楼,感到没有什么话值得说。
我们先去吃点东西,然后坐车去——小芝说的是那边,没有直接说殡仪馆。
一碗面,她象征性地吃了几口,然后放下筷子,如往常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时一般将手揣在怀里。
干妈,快吃啊。小芝利索地将面搅拌一番后才注意到她没有动筷子。
闺女,你吃吧,我不饿。她没有将揣在怀里的手拿出。
你怎么还带着馒头啊。小芝从她的背包里捏到几块硬物,取出一看是十来个凉透了的馒头。
有我在还能饿着你不成?而且飞机上都有免费的饭,你带这干啥?小芝的音调提高了不少。
我——怕——吃不惯这边的东西。她说话时顿了两次,也记住了飞机上的饭菜不要钱。
不是我说你,你看你都带了些什么,馒头、秋衣,还有,你带毛衣干啥?不怕热?我看看你还装了些什么,怪不得大包小包的。小芝拖过她脚下的蛇皮袋,三棵白菜下面斜躺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陶罐,陶罐旁挤着一捆蔫了的油菜薹。
你怎么不把锅碗瓢盆味精盐巴都带齐呢?小芝还想再补充两句,但一口气堵到喉咙口又咽了回去。
城里的菜打了农药的,这个是自己家的,没打农药,我就想着既然要来,就给你带点儿。她的声音很小。
小芝的喉咙咕哝了一下,没有再说话。
她们走出面馆的时候,雨滴落得更大了。馒头被干女儿扔进了面馆的垃圾桶,蛇皮袋以及里面坏掉了的菜叶丢进了刚好经过的垃圾车。陶罐是她硬抢出来的,用两层大号塑料袋包裹着。有些重,累了便换着手拎。
她跟在小芝后面再次坐进出租车,路面已经积水了,几乎看不见行人,车轮来回在她的耳旁碾压着。
车子一直行驶到城郊又朝左拐了十来分钟,才在一棵树边停下。树的左边立着一块高大的牌坊,像墓碑。中间开有一大一小两扇门,她们是从小门进去的。
殡仪馆背靠一座低矮的土丘。这里的地倒是宽敞肥沃,不种些好庄稼有点可惜,但是山一点也没有老家的雄实。
小芝走在前面,同工作人员交谈了一番。两人跟在工作人员的身后坐电梯上到二楼,拐进左手边的第二个房间前。
她的步子放慢了一些。右手边的墙面上是一个个铁皮抽屉,她明白儿子就睡在其中一个匣子里,便死死地盯着那面墙。
工作人员走上前,翻看着手里的工作簿。唐小军,母亲罗英是吗?
她点点头。小芝向左挪了一小步,挽住没有说话的干妈。
这里。工作人员走到铁皮墙前,再次用食指戳了一下工作簿。
终于,铁皮抽屉被拉开。罗英上前的步子不快,前脚掌的鞋底还在光滑的瓷砖上摩擦出了细微的响声。一个明黄色的袋子呈现在她眼前。她的手掌沿着拉链滑动到头才摸到拉环。
呲啦……拉链的声音在寂静的房间里持续了十来秒。
儿子的面色苍白了不少,紧闭着眼,眼皮上又起了不少白色的脂肪粒,鼻孔和耳朵被一团白色棉花状的物体堵了起来。隔着湿润的空气,那股沁骨的冰凉感仍然能传递到她身上。冰冰凉凉的,像早冬结霜的菜叶。
她没有哭,伸出短小、布满皲痕的手,像每次儿子出门前站在公路边一样理了理儿子的衣领,也像那时一样,嘴角以微小的弧度上扬,并不言语。
拉链重新拉上后,儿子的遗体被抬走。她则被引领到大厅,坐在左边靠墙的一个位置。她低着头,揉了一下太阳穴。
阿姨您好。一双黑色的皮鞋停在她面前。
她缓慢地抬头,一张彩印宣传册挡住了来人的脸。她坐直了些,那人也弯下腰,宣传册移开,露出一张精瘦的脸,头发留得很浅,衣着也很城里人,除了下巴上那根长长的胡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您节哀。来人开口了,第一个字发音有些高,后面的声音被迅速地压低。
谢谢。
逝者已矣,您节哀,我们是跟殡仪馆合作的公司,所有的骨灰盒都是厂家直供……
她没有听完后面的话,瞥到了宣传单上的价格,摆了摆手,没再说话。
来人没有离开,而是从手里那一叠宣传单上抽出一张递到她手里了。纸张两面都印满了骨灰盒的图片,图片下都是文字和数字。数字她认得,但文字却是一个不识。
我不识字。她将所有图片看了一遍后开口了,又将宣传单递还那人。推销员没有伸手去接,而是顺势坐在她旁边逐一介绍着上面的产品。看是好看,就是价格听得她心惊。
小伙子,不用,我自己带了。她摸了摸手边的陶罐。
恕我冒昧,您这不是骨灰坛,倒像是装酸菜的老坛子。年轻人说完又有些后悔,生怕得罪了来之不易的客户,他也是刚从业不久,要不是和家里闹翻,怎么也不至于干这每天和死人打交道的工作。
够了,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农村人不讲究,你说的瓷器也好、玉石也好,我的老酸菜坛子也好,能装得下他就行。
见她执着,刚好门口又进来两个穿着华丽的人,小伙便没再逗留,用手掸了掸西装领低着腰凑上前去。
干妈,你怎么坐在这里,我找了半天。小芝去了一趟厕所后找了好几圈才找到她。
小芝走到她旁边,坐在刚才推销员坐的位置上,将手上的包放在腿上,理了理裙摆。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去买个骨灰盒吧。许久没有说话的小芝用手轻轻地靠了靠她。
不用,我带了坛子。
什么坛子?你说的不会是你带的那个酸菜坛子吧,那哪能行,一点都不像样,走,我出钱买。
那么贵,太浪费了。她伸手挡住正欲起身的小芝。
不行,这事得听我的,你这酸菜坛子一点都不像样,多叫人笑话呀。小芝有些急了。
干妈,这个怎么样?小芝指着传单上方的一款白色玉石骨灰盒。
这款很不错,这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卖得很好的……刚碰壁又被叫回来的推销员补充道。
不好看。她虽然不识字,但图片下方拖得很长的那串数字一直在她眼前晃。
这个吧,你哥打小就喜欢兰花。她指着缩在宣传册最下方的一张印有兰花图案的材质不明的盒子说道。
这是我们去年的存货,打折卖的,便宜是便宜,我给您说实话吧,就是有些小毛病。推销员的声音拖长了一些。
坏掉的你还拿来卖?
姐,你知道的,干哪行都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
那这个呢,这上面也有兰花,还有云。小芝指着背面的一个木制方形盒子图案说道。
刚才那个盒子就挺好。
争论良久,推销员递过兰花盒子后悻悻离开。小芝还在埋怨她选得不好时,她已经揭开盖子用手擦拭里面的灰尘了。
不久,儿子就装进了兰花盒子,她粗糙的掌纹盖住了兰花的一半。盒子里的那撮灰尚且温热,像鸡叫时分的暖脚瓶。
小芝还有其他事情,没办法和她一路回,将她送到安检处便走了。
她挎着一个方形的红布包裹,用右手护着,左手拎着两层塑料袋套着的陶罐。走到安检口才取下红布包裹小心翼翼地放在传送带上。
大妈,您这里面的粉末状的物体是什么?安检员眼神里带着一丝戒备。
这是骨灰,我儿子的。
请您出示一下死亡证明。
哦,好。姑娘,你帮我看一下哪一张是你说的死亡证明,我不认识字。她从包里取出一叠,身份证她认识,但是其他各种文件她却分不清楚。
是这张。安检员指着手里那张纸说道。
这张是机票,这是……随后,这个胖胖的女孩又耐心地解释了一番。
哦。她并没有分清楚每一张的区别,但她记住了带方格和红色印章的那张是死亡证明。
您把这些都保管好就行啦。胖女孩看出了她的疑惑,便再次嘱咐道。
走进候机室,她仍不知道该去哪里等,便找到一个警察问路——实则是一个穿着工作服的地勤人员,在这人的带领下,她终于找到了登机口。
外面的雨未见停歇,雾气的环绕使她只看得见近处的几架飞机,和飞机旁边显得异常渺小的车辆。由于天气原因,飞机晚点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她看厌了飞机的时候,终于开始检票了。
她跟在一个穿碎花短裙的女孩后面一步一步地挪动,走到检票员面前时,她放下手里的骨灰盒,掏出兜里的死亡证明——她特意将这张带方格和红色印章的纸放在了左边衣兜里。
不用这个,您把身份证给我就行了。这是一个高挑的女孩,头发盘在后脑勺。
她找到座位后,把陶罐放在了行李架上,把座椅调直后,把红布包裹的骨灰盒抱在怀里。雨水已经停住了,雾气却还没完全散开,像是给城市罩上了蚊帐。
飞机开始滑动,左转右转,过了十几分钟才进入跑道。跑道旁边的人挥动着一根棒子,一股推背感传来,她闭上眼睛的瞬间,飞机轮子的声音也消失了。最先消失的是挥舞棒子的人,随后是飞机、机场,那些望断脖子也望不到顶的高楼慢慢变得低矮。城市的面貌逐渐显露出来。
她对儿子来这里的原因感到不解。但这种不解很快便被飞机划破云层的声音取代,她端详着窗外疾驰而过的云——不过是浓雾而已。
当她出神时,窗外的云开始明亮起来,渐渐刺眼,太阳光出现,她也置身在云层之上。云又变成了一朵一朵的棉花——尚未采摘的棉花——柔软、轻巧,有着躺上去便能很快入睡的舒适感。她不倦地看着下方厚厚的云层,手指摩挲着怀里红布包裹的兰花盒子。
女士,请问您是要牛肉饭还是鸡肉饭?一个挂着标准笑容的空姐推着小推车走到她旁边。
牛肉饭。她吃完后,又要了一份,第二份吃到一半便有些撑了,最后几根榨菜是强咽下的。
飞机开始下降前,她喝了两杯牛奶、一杯橙汁,咖啡只喝了一口,实在喝不惯,便又吐回杯子里。
师傅,走汽车站。
你这抱的是骨灰盒吧。
是。
你还是问问别的车吧。
说罢,车子迅速地启动,然后离开。
飞机落地以后,她跟着人潮很轻易地就走出了机场。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她已经拦了好几辆车了,每个司机见她抱着骨灰盒都不想触霉头。
她悻悻地站在候车处没有说话。半晌后,她身体向下微微一沉,像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她沿着出来的路,避开一辆大巴,重新回到机场。问了个警察,找见厕所,选了最靠里的一间走进去后,回过头再次确认关好了门。
她出来时,没有再背那个红布盒子,只拎着那个两层塑料袋套着的酸菜坛子。拦下一辆车,朝着车站的方向去了。
酸菜不能上飞机,你这是空坛子吧?司机搭话。
她坐在后排,将坛子抱在怀里,紧紧地盯着前面的路,没有说话。
车子左转右转,她已经分不清到底会将她载向何方。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了,村里人都来了,虽然只是一撮灰,但毕竟是死了人,毕竟是喝这里的水长大的人。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除了张大爷还在灌菜,其余人都到齐了,到齐的概念便是五个年近七十的老年人围在院坝里。
由于是死在外面,进不得屋。陶罐用张红布包裹,放在门前的木板上。归置好骨灰后,老李跟老杨两人扛着锄头上山帮着挖坑去了。
她又点上一炷香插在香炉里,走进厨房取了两瓢黄豆,淘洗干净后泡在洋瓷盆里。明天,她要早起,洗净手磨,给儿子推一锅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