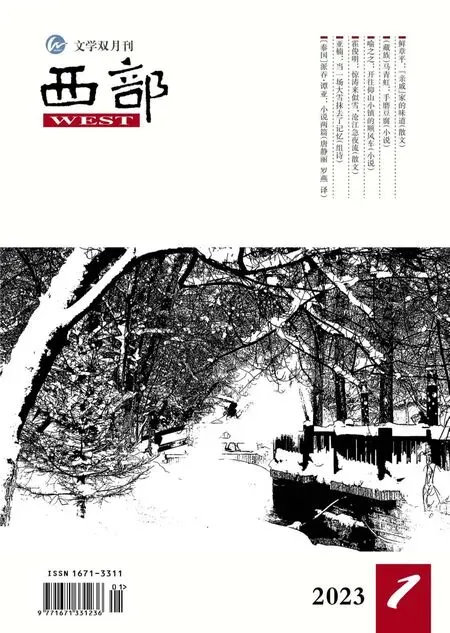心安之处是吾乡(散文)
熊晓丽
有一首歌我们从小就会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家……”是的,我的家就是一路伴随着石油而存在的。
我记忆里的第一个家应该是在四川一个叫“八角”的地方,可能字不准确,音却是这个音。那时,父母所在的井队在这里打一口探井,我之所以这样笃定,因为只有打探井的时间会长一些,井队的驻地才会有拖家带口的场面。
井架耸立在山坳里,驻地分区有序,生活区依山而建。说是山,其实不过是海拔一百米的小山坡。
站在山坡下的操场上,放眼望去,几排工整的平房依山而建,不讲究任何布局,见缝插针而已。所谓的操场只是一块较为平整的地,两头搭着简易的木篮球架,旁边还有双杠、单杠、高低杠,这里就是“文化中心”了。我们是这操场上最活跃的存在,滚铁环、打陀螺……高兴地和小伙伴们吵嘴、打闹、叫嚷、追逐……高低杠和双杠当然也是我们的玩具,我们可以比谁先爬上去,比谁在上面翻的跟斗最多,谁的动作最快。
操场的左边就是食堂,食堂里总能飘出让人馋得流口水的香味。我家就在食堂后面,站在家门口就能看见食堂屋顶的烟囱冒着炊烟,有时候根本就不用听食堂的钟声,只要站在门口,闻到炒菜的香味,就知道食堂要开饭了。
我家门口的草棚下也垒了一个灶。我妈很会做饭,倒班休息的叔叔阿姨总是想办法弄些食材来,找我妈加工。
用“非”字来描绘我们的宿舍区最恰当不过了。几排平房呈阶梯状依山而建,房前屋后总被勤快人种满了蔬菜。整天无所事事的我们,常跟在种菜人身后,看他们锄草、掐秧,看菜苗一点点长大、长高、开花……
宿舍的背后就是山了,不过是个小山包。我们不会背什么“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只知道这里是我们的“神秘花园”,我们可以在灌木丛里“躲猫猫”,藏得小伙伴们都找不到;我们可以找一根竹竿,用细细的树枝和篾条绕个圈,紧紧地绑在竹竿上,去粘蝴蝶、蜻蜓、知了;我们还可以爬上山顶,爬到高高的树上,一边掏鸟窝,一边朝着井架鬼叫……
井场是我们小孩子的禁地,它在宿舍西边的开阔地,离宿舍还有一段距离。井场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钻杆、钻头……总之,所有的范本几乎都和铁有关,我们再怎么贪玩,也知道这井场不让我们靠近的死命令,只是绕着井场周围转,寻一些丢弃和不小心遗失的“宝贝”,好在附近村子的孩子们面前炫耀。
井场周围有好几间小房子,什么泥浆、测井、发电的都在那儿。
发电房,就是我妈工作的地方,那个地方吵死人。后来,我们只要一说我妈嗓门儿大,她就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职业病。
操场后面的一排房子就是队部,也是我每天必到的地方,谁迟到谁早退我门儿清。
跟着父母过着搬迁的日子,对我来说是愉快的。习惯了不断地搬家,不断地更换小伙伴,习惯了对一个陌生地方的探索,这样一直“散养”到该上小学了,我才回到外婆身边。可我刚上完一年级,因父母支援边疆油田建设的原因,又随父母搬到了新疆。
那是1980年夏天,路途上的各种辛酸就不一一赘述了,总之不是一个“难”字能说清的。那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满眼都是对陌生环境的打量,哪怕是睡在火车硬座下,在兰州大包小包地背着再转趟车,都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哪有什么“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叹呢。
我们在库车大涝坝停了下来,这是我们一家五口人真正意义上的团聚。
这次我家住上了砖房,还带着一个小院儿。地板不再是泥地了,是红砖铺的,整整齐齐的,很好看。不用再担心和姐姐洗脚时踩翻洗脚盆洒一地的水了。
我记得那是夏天,阳光是刺眼的,打开门就能感受到热浪袭来。即使是这样,还是出门去观察环境了。我家在马路边上,周围都是一模一样的屋子,一排排的,像一个个盒子摆放得很整齐。正是暑假,我很快就和一般大的小朋友熟络起来。搞笑的是大家都是从各地汇聚到一起的,多少都操着点乡音,有听不懂的就连比带画起来。还好我们都是石油子弟,能迅速适应陌生环境,并很快融洽起来。
那时候,日子过得很简单,娱乐少,看场电影就跟过节一样。刚到大涝坝不久,就遇到放电影。电影是露天的,除了离家近一点,凳子得要自己带。看的什么早就忘记了,只记得电影还没放完,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打断了,一时间,整个场地都乱了起来,叫妈喊娃的声音被呼啸而来的风刮跑了。我们一家人一个牵着一个,空下来的手还要拿着家里的小板凳,风吹过来,睁不开眼,只能低着头跟着大人向前走,腿上被风吹起来的小石子打得生疼。
后来,马路对面修了露天电影院。一个水泥台子,上面还有一个挡风墙一样刷着石灰的水泥幕布,台子前整齐地垒着十几条水泥凳子。条件好了,不用自己搬凳子了,至少不用跑得很远了。更妙的是,有一次,我发现爬到自家厨房的屋顶上居然能看到电影院的水泥台子,虽然角度倾斜了点,但是一点也不影响看电影。
露天电影院隔壁就是学校,没有院子,就是几排教室。教室前自然也是有一些活动器材的,水泥垒的乒乓球台,台面中间立着几块砖当球网。单杠、双杠立在一边。没有操场,眼光所到之处皆是操场。总之一切都在满是石砾的土地上,有人跑过就会带起尘土。学校最吸引人的是一个叫“秋千”的设施,就是一根高而粗的木头牢牢地矗立着,顶端牵下数根麻绳,绳的末端挽了一个小圈,可以放一条腿进去,然后大家抱着绳子一起跑起来、转起来。
教室的前后有两个可以生火的炉子,这对于我们从内地来的人来说很是稀奇。到了冬天才知道,这个炉子是用来取暖的。每个班到了入冬前都要去“打柴火”,就是到戈壁滩上去捡一切能生火用的芨芨草红柳枝什么的。
出家门朝右,走不了多远就有一个旱厕。上这种厕所一开始还是有点害怕的,毕竟下面的坑有点深,担心一不小心掉下去。再往前一点是食堂。父母因工作原因,有时候顾不上一日三餐,没时间做饭的时候,食堂就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朝左走,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口“水井”,住在周边的人家都会从这里挑水回去。从老家来,还没挑过水,怎么试都不行,我们只好“两个和尚抬水喝”。
外婆把我们送到新疆后,就手把手地教我们做饭,确切地说,是教我姐做饭。这里的炉子和老家的不一样,是带一圈圈炉盘的,不好焖饭,米不小心就会糊。炉子连着火墙,到冬天它的好处就显现出来了,有了它,整个漫长的冬天,屋里都是暖和的。
我家的院子相较别人家的院子来说,是比较浪费的。别人家种瓜种菜,很有“烟火气”,而我家院里空空,院中央挖了个深坑,养了一窝兔子。这窝兔子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我们时常忘记它们,它们却自娱自乐地把这个“家”挖得四通八达的,只有在我们把菜叶子扔进去的时候,它们才来光顾一下。也不能说我家的院子完全是空的,我们还种了一种叫“满天星”的花,它的生命力是很顽强的,秋天没有收种子,来年它仍然会发芽,开出美丽的花。现在我知道它叫格桑花,真正的学名叫波斯菊。可是在我的少年时代,这种花似乎因和星星形状相似,便有了“满天星”这个称呼。
在大涝坝,我们一家并没有住多久,最多也就两三年,刚和周围的小伙伴们熟悉起来,就又要离开搬到别处。搬家对于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可是一次次的离别,也会生出些愁绪来。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一家又随着父母搬到了乌尔禾。那是冬天,坐在车里,可真是冷啊。也不知道坐了几天的车,晕头晕脑中就到了。
我们住的是一个有两间平房的小院,院子比起大涝坝的院子小了一半。这里的记忆却比大涝坝多了一些,毕竟我上四年级了。
乌尔禾是钻井三大队的所在地,这里比起大涝坝大了许多,隔着217国道还有137团呢。
这里只是一个钻井大队的所在地,却五脏俱全,学校、幼儿园、卫生所、商店等等什么都有。我家住在二区,第几栋忘记了。一切重新开始,像极了现在的网络游戏,不好玩了,就重新开辟一片新天地。
乌尔禾,就是一片新天地。
在我的记忆里,乌尔禾是灰色的,因为尘土太大。那时的“魔鬼城”叫风城,从春刮到冬的风总是让一切都弥漫在灰尘里。唯一的绿就是那条叫“柳树街”的街道,它是连接217 国道和137 团的主干道,街道两旁的柳树长得很茂盛,枝干遮天蔽日的。
我们的学校大门就在这条柳树街上。放学我是不会走正门的,学校还有一个后门,从那个门回家比走正门要远一些,但是就是这么怪,我宁愿绕路。从学校边上的五区一直走到我家的二区,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土路,路两边长着不知名的野草,半人多高,有时候还开出红的白的小花。这片野草是我们放学后的“战场”,学校院里那片荒芜的操场无人问津,这条路上却人声鼎沸,好不热闹,藏猫的、“斗鸡”的……这是放学后的美好时光。
基于共词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本研究中笔者运用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院开发的书目共现分析软件 [2] (Bibliographic Item Co-Occurrence Matrix Builder,Bicomb)提取文献数据集中的关键词,经数据清洗后,统计关键词频次。由于频次为1次的关键词在网络可视化中是孤立点,故在后续的网络分析中将其去除,只纳入频次2次及以上的关键词共69个,形成69*69的关键词共现矩阵,以供后续的网络可视化分析。
其实从学校到家,走这条路不过十分钟,可我们总要花半小时。
住宅区的房子都是一样的,只是住的人不同了,就有了不同的味道。
三大队的味道不外乎两种——四川和湖北,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从这两个地方来支援新疆的,即便有其他省份的,也是从这两个地方调入新疆的。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从这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才是“发小”。如今微信里的“发小”,放眼看去,老家大多是四川的。
沿着小区旁的主路往前走就是大队的机关,也就是行政中心,俱乐部、食堂、卫生所、澡堂、商店、幼儿园也都集中在这里。
往机关的背后走就是一片农田,是农业队的所在地。再往前走就是白杨河大峡谷,虽然离家有点远,可这里是我们的乐园。
小学毕业前夕,同学们约着去大峡谷徒步。大家带着吃的,高兴地走了一路。那时的大峡谷不是什么旅游景点,是只有放牧人才去的地方。
峡谷内胡杨、柳树、红柳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生长着,俨然一个植物的王国。我们一起朝峡谷的最深处走去,到了“龙口”,白杨河的水就大了起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我们下河去吧!那时正走得汗流浃背的,大家一拍即合,于是会游泳的不会游泳的都往河里奔去。不知道谁从岸边拖来一棵干枯的胡杨树干,推进了河里,大伙儿你推我搡地爬上了这棵漂在水上的树,骑在上面,向下游冲去。现在想起来,都忘记了是玩到什么时候才回家的,但那一刻的开心,都留在了大伙儿心底。每每回忆起那段少年时光,骑在树上的我们仿佛都闪着耀眼的光。
有了自行车后,就能跑得远了,就算只能是一条腿从大杠下斜着身子蹬在自行车上,一样骑过了217 国道,去了137 团溜达,去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魔鬼城,去了沥青矿……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父母这一代人都是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的,很少有近亲在一起生活,我们也没有七大姑八大姨,可和父母井队上的同事相处得却如一家人一样。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吃起团圆饭来,没有半个月是吃不过来的。你家吃完吃他家,他家吃完吃我家,往往是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家里能摆桌椅的地方都摆上了,那个热闹劲儿别提了。后来,大家陆续搬到白碱滩后,依然都是这样过年,那个年代建立起来的友情如同亲情,我们就是一个不同姓氏的大家庭。再后来,条件好了,人口也多了,过年不是一两桌能解决的了,就进了饭馆,摆上几桌,也是团圆。
1986年夏天,我初中毕业了,我们家搬到了白碱滩,住进了一楼带小院的三室一厨的楼房。虽说也就六十多平方米,可刚住进去时,我们姐妹三个高兴得整天都咧着嘴笑。怎能不笑呢?首先,上厕所不用到外面了,自家就可以上,只要没人催,想蹲多久就蹲多久,哪怕是脚蹲麻了,也比旱厕强啊,冬天冷不了,夏天热不着。其次,家里有自来水了,再不用去外面挑水、在自家抽水井里打水了。打开水龙头,水就哗哗流出来了,多美。再有,用上液化气罐了,不再生火烧煤做饭了。还有,家里有暖气了。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虽然我们三姐妹还是挤在一间屋里,睡着上下床,但是家里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客厅。小院里还有一个菜窖,秋天可以储存一些土豆白菜,冬天除了干菜也有新鲜菜了。学校就在我家楼后的马路对面。
我们终于在白碱滩停了下来,再没有搬家。
今天,家仍然在白碱滩。就算是在白碱滩,我自己的小家现在也搬了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宽敞,住在十一层的电梯房,望着窗外那片仍然生机勃勃的油区,怎能没有些许感慨呢。
起初我在电脑键盘上码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是想写乌尔禾的,可是写来写去才发现,从乌尔禾蔓延出去的回忆,居然是我们家无数次的搬家经历。“搬家”不仅串起了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和中年,也串起了一个石油工人家庭这些年来的艰辛和不易。有时候我想,如果父母没有从四川来新疆,我们家又会如何呢?如今,父母已退休回四川颐养天年,对他们来说是叶落归根了吧,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始终是要回到故乡的。还有许多和他们一起从内地来支援新疆油田建设的同事们却留在了这里,用他们的话来说,是已把异乡当故乡了。那么我们呢?我看向窗外,入秋了,可是一样烈日炎炎,这刺眼的阳光,应该和我刚来这里时的阳光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