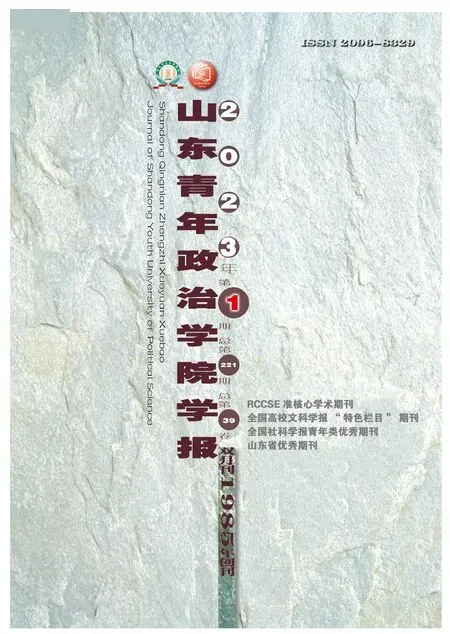李杞的易学思想及其家国情怀
赵敬仪
(山东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1)
李杞,字子才,号谦斋,四川眉山人,南宋隐士,易学家,仕履未详。《四库全书》曾考证,宋代有三位名叫李杞的名家。一位是北宋人,官至大理寺丞,曾与苏轼说文唱和。另一位是南宋朱子门人,字良仲,平江人,即尝录《甲寅问答》者。然此两人与作《用易详解》之书的李杞均非一人。作此书的李杞既没有做官,也不曾拜朱熹为师,但他生活的时代却与李良仲接近,大约在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时期,此时恰逢南宋内忧外患、国破家亡之际。他曾作《用易详解》十六卷。据传该书原二十卷,焦竑《经籍志》作《谦斋详解》,朱彝尊《经义考》作《周易详解》。然李杞《自序》称:“吾于《易》多证之史,非以隘《易》也,所以见《易》为有用之学也。因取文中子(王通)之言,而以‘用易’名编。”[1]351可见,他对书名之义的解释非常明白,有可能焦竑及朱彝尊皆未见原书,故传闻有误。《用易详解》除缺《豫》《随》《无妄》《大壮》《睽》《蹇》《中孚》七卦及《晋》卦后四爻外,其余卦爻辞及《文言传》《系辞传》《序卦传》《说卦传》《杂卦传》皆完整,基本可以反映李杞易学哲学思想。
李杞是南宋以史证《易》的重要代表人物,《四库》称其“经必以史证”,但并未将其列入史事宗的原因是:“杞之说《易》,……其中不可训者,惟在于多引老庄之文。夫老庄之书其言虽似近《易》,而其强弱攻取之机、形就心和之论,与《易》之无方无体而定之以中正仁义者,指归实判然各殊。”[1]350《四库》馆臣囿于门户之见,认为其解《易》引老庄之言,与儒《易》“中正仁义”之旨判若两途,加上其仕履未详,导致学界对他的思想关注不足。目前所见学界关于李杞的研究文章仅有两篇[2][3]92-97,主要是对其思想进行了简单梳理,但对思想主旨及为何援引老庄之文则未暇致思。
其实,李杞易学具有南宋易学的典型特征。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易学较北宋易学,存在两个方面的范式转向:一是透过象数说义理,即象数和义理皆不偏废。朱熹就曾对程氏易学有这样的评价:“《伊川易传》亦有未尽处。当时康节传得数甚佳,却轻之不问。”[4]1653自朱熹重申“《易》本卜筮之书”之后,透过象数来明理成为研《易》的根本途径。二是以史证理,关切现实,针砭时政。南宋内忧外患,以杨万里为代表的史事宗本着拯救国运的时代责任感,希冀通过以史证《易》,阐发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李杞《易》也不例外。但其易学思想既不完全同于当时的义理派,也不完全同于史事宗。略其大观,可概括为:以象数为据,穷究其理;以史证《易》,经辩其理;引老庄之言,未离儒道。
一、以象数为据,穷究其理
《周易》是圣人“观象系辞”的结果,是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把握客观自然世界之后,形成的自身对世界的经验和总结。李杞认为,“易有四学,象、数、辞、义是也”[1]528。圣人设卦观象,为象;六爻之动,三极之道,数也;系辞焉而明吉凶,辞也;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此义也。故圣人作《易》,以象观吉凶,以辞观变化。圣人观物取象是“外观”,如乾为龙,坤为马,山泽之象,雷风之象,飞鸟之象等等,但圣人所观者,非拘泥于物象,而是求于义理,故“泥乎物,则拘而不通。观乎理,则周流万变而不穷矣”[1]528。可见,李杞认为,“设卦观象”仅是一种显示与澄明,必须经历由对象性的“物象”向非对象性的“内观”转化才可以。因此,“象”是对万象概括性的最大的效法和模拟,“辞”是具有抽象意义的价值与功能,最终通过象辞来阐发其义。就此而言,格物以穷理才是最终目的。
李杞易学不废象数体例,旁及卦气、纳甲、卦变、互体、之正、旁通等,但又有独到的发挥与创建。例如其解《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曰:
《复》之道,夫孰能害之哉?所谓朋来者,众阳是也,自《复》而为《临》,为《泰》,为《大壮》,为《夬》,为《乾》,皆吾朋也……七日来复,先儒论之详矣,阴生于午,终于亥,而为《坤》,自《坤》而为《复》,历变凡七,此子夏之说也。冬至卦气起《中孚》,历七日而为《复》,此京房、郎顗之说也,二者相非,未有定论。要之,自阴而复于阳,此天运虚盈消息之理也,然《临》言八月,而《复》言七日者,《临》为阴长而言之也,《复》为阳复而言之也,此日与月之所以异也。[1]424
显然,李杞解《复》卦是用了十二消息说,从《复》到《乾》,皆阳息阴消,为吾朋也。关于“七日来复”,他认为子夏、京房、郎顗之说各有说辞,未有定论,实际未得其中要领,因为消息卦最重要的是揭示了天地盈虚消息之理。如《临》卦为阴长,故有“八月有凶”,《复》卦为阳复,故“利有攸往”。然天地无常心,为何《复》能见其心?他解释道:“天地之心未尝不喜阳而恶阴,喜刚而恶柔,喜君子而恶小人,盖至于《剥》,而阴阳柔刚,君子小人易位倒置,而天地之心始晦矣!”[1]424-425天地之心乃纯善至诚之心,亦喜阳恶阴,喜君子恶小人。而君子之《复》,得乎一心,与天地相似故不违,故一人私己之心,要反复内省关照,才知吾心有天地,也即天地之心即吾本然之心。也就是孟子强调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人能反身而诚,则天地之大莫不在我,是之谓复其见天地之心。这也由此体现了李杞常怀忧深之思,喜君子,惕小人的情怀,也是其以象数明天道,以天道推人道的典型特色,同时表明了他以象示理的逻辑旨归。
除以象解《易》服务于穷究其理之外,其象数体例也不例外。例如汉魏都非常重视的卦变说。李杞卦变系统虽多遵虞翻、朱熹卦变系统,然并不完全同于他们体例。如其解《噬嗑》:“《噬嗑》者,《颐》六四之变也,《颐》以养为义,而《噬嗑》,颐中有物,则失其所以为养矣,颐中有物,是物有以为之间也,欲去颐中之间,必噬而嗑之,而后可以亨通。”[1]416按照虞翻和朱熹卦变体例,《噬嗑》为三阴三阳卦,当为《否》五之初,而李杞认为皆非,《噬嗑》是《颐》六四之变而来。究其原因,与其构建的道德性命之学有关。李杞说:
夫子论性之说,至于《易》之《乾》,其理亦曲尽矣。盖尝因是而推之,《乾》《坤》二篇之策皆有性情之妙,不可不察也。《乾》再索而得《坎》,故付正性于《坎》,《坤》再索而得《离》,故付正性于《离》,《坎》《离》为正性,谓其得中也,《乾》以偏情,付于《艮》《震》,《坤》以偏情,付于《巽》《兑》。《艮》《震》《巽》《兑》为偏情,谓其不得中也,是故卦之自《乾》《坤》变者为情其性,《颐》《大过》是也;其自《坎》《离》变者为性其情,《中孚》《小过》是也,《颐》《大过》情其性,故不能为《中孚》《小过》,《中孚》《小过》性其情,故能反而为《颐》《大过》,中与不中之所以异也。然则《乾》《坤》之情付于《震》《艮》《巽》《兑》,而独正性付于《坎》《离》,《乾》《坤》退藏于不用,以《坎》《离》为用,其利而复贞之说乎。[1]361
李氏所论的《坎》《离》《颐》《小过》《大过》《中孚》六卦自古以来就是卦变体例争论的焦点,在虞翻卦变体系中就是变例。如《颐》《小过》卦为二阳四阴之卦,当由消息卦《临》《观》而来,但虞氏认为,此两卦并不从《临》《观》卦变系统,而是分别由《晋》四之初、《晋》上之三来;《大过》《中孚》为四阳二阴之卦,当由消息卦《遯》《大壮》而来,但虞氏认为,当分别为《大壮》五之初、《讼》四之初而来。李杞解易与之不同,他认为,此六卦之所以不遵卦变系统有其特殊原因。他赞同《乾》《坤》为诸卦之祖,卦变始于《乾》《坤》,然《乾》《坤》二篇之策皆有性情之妙,不可不察。根据《乾》《坤》生六子,《乾》《坤》为体,《坎》《离》为用,因《坎》得《乾》之中气,《离》得《坤》之中气,故《坎》《离》为正性,谓得中也。除了《坎《离》之外,《震》《艮》《巽》《兑》四子皆因互体而生,《坎》互体出《震》《艮》,《离》互体出《巽》《兑》,故《震》《艮》《巽》《兑》为偏情,谓其不得中也。《颐》《大过》为旁通卦,由《乾》《坤》变来,为情其性;《中孚》《小过》为旁通卦,由《坎》《离》变来,为性其情。综上所述,究其原因,李杞以此卦变系统来说明性为体,为本,为未发;而情为用,为末,为已发,而最终决定体用关系的根本乃是中与不中也。要之,他赋予了“中”以形上本体之意,由此落实到人事上乃中正之德,包括治世之道的公正、执政者的自正、君子贤臣的公心等等,皆表现出其对天道正义在人道价值的落实与阐扬。可见,他透过象数穷其理,并不是发现事物“所以然”,而是归结为人伦日常的“所当然”,其论述大衍之数目的时即可证明这点。李杞曰:
以吾考之,大衍之数当以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求之,而郑氏则求其说而未得其要者也。……此河图自然之数也。然天地五行惟以十为用,故乾得九一成十,坤得四六成十,艮震合得三七成十,巽兑合得二八成十,坎独得十共为五十,而天五无偶,寄于离为虚位而退藏于密,五不为用,而以十为用,此大衍之数实出于天地之数,而止于五十者也。[1]538-539
宋人内部针对河图洛书有“图九书十”与“图十书九”分歧,前者以刘牧、朱震、朱元升、李简等为代表,后者以邵雍、蔡元定、朱熹为代表。可见,李杞从邵雍、蔡元定、朱熹之说,认为大衍之数源自天地之数,乃河图自然之数。河图是以十数合五方、五行、阴阳,以符示天地之象。他说:“天一,乾之始也,地六,坤之终也。”[1]536在《归藏》和早期《周易》中都曾使用一、六(∧)两个数作为爻的名称数并来表达阴阳合和。另外,郑玄注《易纬·乾凿度》中也说:“象一、七、九也。夫阳则言乾成者,阴则坤成可知矣。”也就是乾阳为一、七、九,则坤阴为二、六、八。李杞吸收了该思想,他认为,乾为阳始,为天数一,坤为阴终,为偶数六。他以十为用,故有乾得九成十,坤得四成十。那艮、震,巽、兑何以得十?推之当根据奇数配阳卦,偶数配阴卦的原则,三、七配艮、震(阳顺排),八、二配兑、巽(阴逆排)。又坎离阴阳互根,在中,故离为五、坎为十。李杞说,“天五在离,离为戊,而坎包之,坎起于戊,而终于己,坎得十,则五藏其中,故天五不为用也。”[1]545按纳甲,离当纳己,坎当纳戊,戊己乃中央土,坎离互根,位中央,故离五,坎十。故有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十为用,天五寄于离为虚位,五不用,故大衍之数止于五十,由此得出结论,大衍之数实际是出于天地之数,蓍法的过程就是描述天地自然之理的过程,推而广之,则天下之能事毕矣。这其中隐藏的是道,而显现出来的却是德,所以他说:“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而其妙则超出乎道德之表,学者当深味之。”[1]540也就是说,卜筮之法其妙在于超乎道德之外,亦存乎人,故学者当深刻体味其中要义。他说:“《易》之大,何所不有,而圣人得之以为穷理之学。”[1]530关于《易》与理的关系,其主张从于宋代道学思想,认为理在天地先,“是故《易》之未作,天下具是理,而不能自知易之既作,天下得是理而有以自足。人皆知蓍数卦爻为卜筮之用,而不知乃所以为道德性命之本也。”[1]563李杞认为,圣人作《易》之前,理已俱在,圣人作《易》的目的是为了以示后人道德性命之理,而道德性命之理不是凭空而出,可以借助蓍数卦爻为工具或基础。可见,他精研象数之鹄的,在于沟通天人,探求义理之流行。象数是基础,义理才是归宿。故《四库全书·提要》称:“宋世李光、杨万里等,更博采史籍以相证明,虽不无稍涉泛滥,而其推阐精确者,要於立象垂戒之旨,实多所发明。杞之说《易》,犹此志矣。”[1]350蔡方鹿先生也说:“就李杞注重探讨象数而言,保留了汉易象数之学的特点;就其以穷理为目的而论,又体现了宋易义理之学的治学宗旨和时代特征。”[5]此论确然。
二、以史证《易》,经辩其理
李杞易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史证《易》”,这一特点贯穿其解《易》的全过程。《四库全书·提要》曰:“书中之例,於每爻解其辞义,复引历代史事以实之。”[1]350至于其中原由,他在《用易详解·自序》中解释道:
夫圣人之经,所以示万世有用之学,夫岂徒为是空言也哉?故经辩其理,史纪其事,有是理,必有是事,二者常相关而不可一缺焉。自后世以空言为学,岐经与史为二,尊经太过,而六经之书往往反入于虚无旷荡之域吁!是亦不思而已矣。夫经固非史也,而史可以证经,以史证经谓之驳焉可也,然不质之于史则何以见圣人之经,为万世有用之学也耶?[1]351
他认为,圣人作经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具有高度的用世精神。经文包含义理,历史记录史事,但义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透过史事来表现的。因此,理与事互为发明,两者缺一不可。他批评后世尊经太过而陷入空言性理之中,将经与史割裂开来。《易》之为书,圣人处忧患之地所作,在日用常行中有无穷妙用,吉凶悔吝,治乱安危,得失祸福,莫不寓于书中。因此,因经证史,因史通经,援引史事以为通经致用之津筏,接身待物而有所参稽而归于实用,使《易》不沦为空言,由此奠定了李杞几乎卦卦引经、爻爻援史的体例。其在援史证《易》的过程中,诠释了其政治主张,也抒发了其家国情怀。
首先是对明君、贤君的赞赏,以及对昏君、暗君的讽刺。他常举唐明皇及周武王为例,赞赏他们能够发扬其父之德者,让祖先增添光彩。如其解《蛊》六五“干父之蛊,用誉”曰:
柔居尊位而得中正,故能承之以德,而以誉归之,此善则称亲之义也。睿宗在唐,本中材之主,惟明皇有大功而推尊于父,故睿宗至今犹得贤君之名,可谓干父用誉者矣。武王卒伐商,以广文王之声,亦此类是耶?[1]409-410
唐玄宗开创盛世,武王伐纣,皆是承继父亲之德,使唐睿宗及周文王功业水涨船高,声名远播,得以获贤君之名。与之相反,他也论及“迷复失则”的昏君。如他在解《复》上六爻辞“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时说:“迷复者,昏迷而不自复也。长恶不悛,纵情肆欲,而不之悔。灾眚已见而犹不悟,方且用师以求逞于人,故终至于大败。国破君亡,虽十年之久,而不克征焉。盖其反君道之常,是以祸败如此之极也。楚灵王不能自克,以取干溪之祸。至于平王之世,救死扶伤,日不暇给,而不敢起南征之师,此岂特十年也哉!”[1]426-427他认为,上六迷不知复,因此有凶险。若以之行师,必遭败绩,以之治国,则有国君之凶。由于危害加重,延祸子孙,虽十年仍然无法解除灾难。他举例楚灵王穷奢极欲,昏暴之君,败于干溪,致平王之世仍受其害。
其次是对良臣、贤臣的呼唤,以及对乱臣、奸臣的鞭挞。如其解《大过·象》九四:“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曰:
四居近君之地,大臣之象也。有阳刚之德以胜天下之重任,故能卓然自立,以支大厦之倾,四之为栋,可谓隆矣!……周公之于成王,其负荷亦重矣。作室肯堂之任,梓材朴斵之勤,皆周公以身任之,是“栋隆之吉”也。而周公之心,欲天下之一乎周,是以终身不之鲁焉,夫岂为流言之变而有所桡哉?呜呼大臣若周公可谓能任重矣![1]436
九四为近君之臣,为国之桢干,如同大厦将倾时的支柱。因此,大臣要坚定自守,有阳刚之德,成为国家最强有力的基石。李杞称赞周公之德,如栋隆般,是国家的依靠,不因管叔、蔡叔的中伤而改变信念,仍然专心辅佐幼主而终获吉祥。李杞在解卦过程中多处称引周公的德业,如《坤》六五,《蒙》九二,《小畜》初九、九二、九三,《履》上九,《观》上九,《噬嗑》六三,《遯》六二、九五,《明夷》六五,《解》九二、六五,《益》六二,《萃》九四,《升》九二,《鼎》上九,《丰》六二,《涣》六四,《贲》九三,《颐》六五、上九,《复》六四,以及《蒙》《晋》《需》《渐》《兑》《旅》卦辞等。另外,尧舜、文王、武王等盛明贤君也是李杞处处引证的。
与此相对应,李杞引史证《易》中,也有对奸臣的憎恶及对现世的警示。其解《离》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曰:“九四之离,恃其刚以犯上者也。其来也,突如,其炎也,焚如。其势若不可向御矣;而其极也,卒至于死如,弃如,何也?以其恶为人之所共弃,而无所容于天地之间也。梁冀之跋扈,董卓之暴逆,气焰炎炎,不可制遏,适足以戕其躯而已矣! ”[1]441九四爻自恃刚强而犯上,或许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举东汉梁冀、董卓为例证之。梁冀是梁商之子,曾靠外戚身份显达。后来梁冀日渐骄纵猖獗,独揽大权,甚至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桓帝心生不满,遂诛杀其党羽,灭其族。同样,董卓凶残暴逆,惨绝人寰,百姓无不恨之入骨,死后不仅将其尸体暴尸街道,更是燃烧几天几夜。由此证之,曾经权倾一时,倘若作恶多端,罪孽深重,终难逃“焚如”“死如”“弃如”的下场。这种以历史史实来证明易理的方式在其书中比比皆是,由此来“切近明理”“切中人事”,充分体现了其对现世政治的诉求和期望。
三、引老庄之言,未离儒道
前文所述,《四库》馆臣将李杞排除于史事宗的门外。究其原因,大抵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援引老庄思想解《易》。在《用易详解》中,他援引老庄思想解《易》大约二十几处。《四库》馆臣指出:
自叶梦得《岩下放言》称“《易》之精蕴尽在庄、刘”,程大昌遂著为《易老通言》。杞作《易编》,复引而伸之,是则王弼辈扫除汉学流弊无穷之明验矣。别白存之,亦足为崇尚清谈者戒也。[1]350
历史上虽有叶梦得、程大昌提出过《易》与老庄的通约关系,但就其实质而言,二者并不相同。叶、程之所以以老庄释《易》,实际上是王弼尽废汉代象数流弊的结果。这大概就是《四库》不录李杞为史事宗的重要原因。然而仔细分析李氏解《易》思路,可以发现他对《易》理的发挥与儒家之旨并不矛盾。
如其解《系辞传》“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曰:“天地惟无心,故视万物如刍狗,而无所忧。圣人不免于有心,故以天下为心,而不能无忧天地,圣人盖理一而分殊者也。”[1]532“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出自《道德经》第五章,比喻天地待万物无所差别,自然而然。王弼曾注:“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6]75也就是说,天地自然的理法没有人类所具有的意志、情感与目的性的价值意识存在,只是自生自成而已。李氏引此句仅为证明天地万物无所偏心,顺其自然而发展,天地万物是平等的,无所忧虑的。但圣人不同,圣人以天下为心,要仁爱万民,不能无所忧虑,以此突出了圣人实践仁德、引导世界向善的主体自觉。可见,其与道家思想的核心之旨并不相同。李杞认为,圣人要忧患天下,圣人的盛德大业就是充塞于天地的恢弘德业。
再如,其解《乾·文言》“乾始能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曰:“利而可言,则其及物也浅矣,故不言所利而后为利之大。《庄子》‘天下有大美而不言。’”[1]361意为乾阳创生万物,以善仁之美来利天下,但乾阳并不言说其利天下的恩惠。“不言所利”也是老庄的重要思想。老子喻示非可道之“道”必至称举“不言之教”[6]232,“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6]293。意为以无为的态度去作为,以无事的态度去做事,以无味来当做有味,显然这并不是李氏所表达的思想态度。李杞认为,可言可利仅言及物,是在浅表层次,而不言所利,才是最高境界。正如程子解释:“乾始之道,能使庶类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盖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赞其利之大曰‘大矣哉’。”[7]10儒家讲的“不言所利”是无所不利,是大利,而非道家的无为而任自然。
再如李杞解《损》卦“损之义有三:有自损之损,有贬损之损,有损益之损。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是自损之损,尽性之学也。”[1]464他解释“损”的其中一个含义是“自损之损”,即减少自己利益或克己之欲望。接着他举例说明孔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颜渊的德行也如此。他引用《史记》中对尧帝的描述,“贵而不骄,富而不舒”来解释《损·象》“君子以惩忿窒欲。”[1]464可见,其引老子“为道日损”的目的是希望君子能够效法圣人减损私欲,复归于天理,以尽人性,而非道家的无为。再如解《升》卦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君子之德积于微小。”[1]478“神知之妙,斋心服形,游于清明湛静之境,以为卜筮之本,故能以静而知动,以一而知万,以神明其德,天下见夫蓍龟之神也!”[1]543等等,不一一列举。可见,李杞引老庄思想与引史证《易》一样,仅是作为史料或者工具,并未以此阐发道家思想,目的是如何通过史料或工具最终呈现经典之意,并将经典之文本内容与时代精神结合,变成现实的思想动力,以解决其自身遭遇的时代课题,以期获得新的动力。
另外,《四库全书》不将李杞列入史事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同于同时代的李光、杨万里一生主力抗金,多次遭贬谪,忧郁而死,李杞乃南宋隐士,加上其著作更是坊间久无传本,易被忽略。但这与儒家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也并不矛盾。在退隐还是入仕方面,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112“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8]160君子遇不遇者,皆为“时”也。孔子认为,仕与不仕,进与退,要“唯道是从”。孟子也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8]424士在困穷时不失其义,通达时不背离其道,那么百姓就不会失望。君子得志,泽惠于民,不得志,自己保持节操,进德修业,同样是君子所为。如果在困顿处,能保持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也不会失之己,失之人,失之道。所以,儒家讲内圣外王,倘若在乱世,国君不行仁义,奸臣当道,此时忠君就会失民,但不忠君又失道,君子当何为?《礼记》曰:“三谏而不听,则逃之。”正如李杞这样的隐士,虽未处庙堂之上,却心系天下,相较于那些以儒者名义行苟且之事的人,这何尝不是卫道。他著书立说,其易学思想承载着对国家、对社会,对君、对民的期望,这也是其家国责任的担当。
四、结语
李杞生活的南宋时代,是朝廷偏安一隅,军事力量羸弱,政治派系斗争激烈的时代。他著述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就是针砭时政、唤醒君王。他说:“尧舜之逊,汤武之征伐,伊周之达,孔孟之穷,在天下有如是之时,在《易》有如是之理,在圣人有如是之用,盖不独十三卦制器尚象为然,而孰谓可以虚文轻议之也哉!故吾于《易》多证之史,非以隘《易》也,所以见《易》为有用之学也。”[1]351
正是将《易》视为有用之学,所以,无论是以象数沟通天人,还是以史事经辩其理,其最终目的皆是证人伦之理。这是本天道立人道,从形上到形下的贯穿统一。李杞说:“其实圣人之忧天下后世,亦仁矣哉!”[1]563“仁”即《中庸》之所谓“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穷天地万物之理,以尽己之性;尽己之性,以尽人物之性,而后至于天道之命。故道止于仁,止于知。性也,是性命之理,未有外乎阴阳者也。人应该效法天道,感应阴阳,循天之理,开显出人的道德规范。他说:“盖知与礼,成性之善者也。一性之成道,义之所从出,诚能以知效天,以礼法地,而存其一性之自然,则道义之用。散于变通阴阳,易简者无一而不存矣!”[1]534天之性即人之性,天道与人性实通一无二,天道自然,性之善也,自人道言,则表现为仁义礼智四端,也为道之自然。可见,李杞是以人为本的有为哲学,是将《易》回归日用伦常。正如林忠军教授所言:“宋代史事宗要用史证的方法,把《周易》阐发为一种普通的、近人事的理论,虽然他们有时亦引老庄‘天道’和程氏‘天理’,但经过论证归根到底,把它变成一种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的理论。”[9]261此论确然。说到底,史事易的典型特点就是在历史中寻找能够解释《周易》卦爻辞,以支撑其义理思想建构的史事加以阐发,进而指导社会实践。因此,李氏无论是引用历史史事还是引老庄思想,皆是服务于切近人事的目的,对此不应持有太深的门户之见。
基于此,从思想体系构建来看,以史事论理相较于程朱义理之学还是有所区别。潘雨廷先生曾指出:“夫此书(李杞的《周易详解》)与《诚斋易传》同时同类,然内容殊不同。杨氏于《易》义全从《程传》,乃一心致力于史事之配合,故所取之史实极精细,而李氏于《易》义有所自见,其于史事得其概要而己。”[10]209此乃道出李杞易学的最大问题,他虽崇尚理学,但未曾像杨万里一样全从《程传》,构建精微细密的义理学思想体系。概言之,李杞并未与汉儒象数易学划清界限,同时又纳入宋河洛先后天之说;虽以王弼、程朱义理解易为主,然也重视以史证易的魅力和殊胜之处。从其易学思想中不难看出,他一方面对前人成果加以吸收,另一方面又大胆创新。同时,他对于主流思想,邵雍程朱亦未全盘接受,而是融会诸家,为我所用。然也正因为如此,其思想也略显粗糙与庞杂。
总体来说,李杞肯认《易》乃万世有用之学,反对空谈性理,以象示理,以史证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民族情感、精神归旨和价值目标,他借《易》之言,诠释了其政治主张,寄托了其家国情怀,这也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