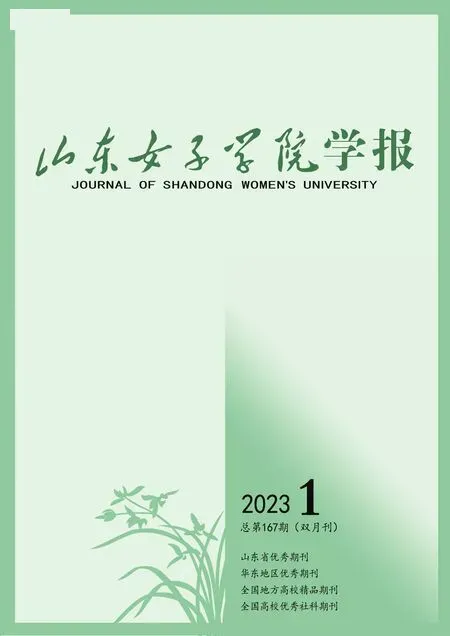傣族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历史发展研究
邬远遴,李守雷,2
(1.昆明学院,云南 昆明 650214;2.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00)
傣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和红河流域的河谷平坝等地区,傣族文学题材丰富,作品浩如烟海,诗意地记录着傣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该民族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封建领主社会、封建地主社会和近现代社会四个时期。社会形态的演变在傣族文学特别是女性形象的演变中清晰可见。从狩猎到农耕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傣族文学以口头神话为主,创造了“大母神”女性形象。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和地主经济社会,叙事长诗蓬勃发展,“贵女”形象和“平民女”形象产生。进入近现代社会,傣族推行民主改革,小说中出现了大批“中西合璧”的现代女性形象。
西双版纳和德宏是傣族人口居住最多的两个聚居区,这两个区域既经历了傣族发展的所有社会形态,也囊括了历史上产生过的傣族文学形式,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因而,本文以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文学作为考察对象,在“大母神”“贵女”“平民女”和近现代女性四种类型女性形象的发展中,探讨傣族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内涵。
一、具有强大繁衍力的“大母神”形象
原始社会时期,傣族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斗争。傣族人靠采集、狩猎为生,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严苛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生存艰难,生计活动需要更多劳动力,傣族人民迫切需要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便产生了生殖崇拜。因此,在傣族的创世神话和图腾神话中,女性往往以“大母神”的形象出现,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强大的繁衍能力。
创世神话《布桑嘎和雅桑嘎》中的雅桑嘎是傣族女性始祖。她和丈夫布桑嘎带着天神英叭给的仙葫芦来到地上,一起把葫芦里的生命洒在大地上。他们用泥巴捏人,布桑嘎捏男人,雅桑嘎捏女人,让男人和女人结为夫妻繁衍后代。这则神话中破开仙葫芦产生生命的故事是傣族女性生育的转喻。葫芦多籽易繁殖且形如怀孕女子腹部,故被视作强大繁殖能力的象征。这则神话中的仙葫芦正是生殖崇拜思维对女子孕育力的隐喻[1]。雅桑嘎不仅能造人,还能与丈夫一同生产农作物。女性不仅是生命之源的象征,同时也有辛勤劳作的形象,反映了原始文化中傣族对女性生殖和生产两个功能的倚重。
“大母神”的形象在图腾神话中也有体现。原始社会的傣族人将他们认为与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这些图腾也就成为傣族人文学性的化身。在《鸟姑娘》《神象的女儿》《神牛之女》等图腾神话中,女性或本身是神,与人结合生下了儿女;或自身是人,通过“感孕”的方式产下神的孩子。“鸟姑娘”“象的女儿”“牛的女儿”都是女性与自然力的结合,展现了傣族人对自然力的追求和敬畏。原始傣族人对自然充满敬畏,他们渴望如自然一般强大,能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些神话反映了当时的傣族人对女性的生殖崇拜,女性因此衍生为民族始祖,显示出女性在原始傣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在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环境恶劣,生命的繁衍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傣族先民对分娩的知识知之甚少,对于生命的产生更没有科学的认识。他们看到女性孕育后代,就认为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是生殖的决定性因素,通过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傣族先民表达了繁衍生命的热切期待。比如创世神话中的女性形象总是与生殖崇拜相关联,原始傣族人将多籽的葫芦类比为女性子宫。图腾神话则将女性形象构想为强大自然力的化身,是对自然的审美,也是对女性生殖的崇拜。原始社会时期产生的傣族神话中,女性形象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融合点,升华为敬畏自然力、向往种族繁衍和自然崇拜的偶像。一系列“大母神”形象的塑造显露了原始傣族母系社会的痕迹。在原始社会时期的神话中,男性一般为创造自然万物的形象,女性则是孕育后代的主体。因此男性形象在创世神话中占比较大,如创造天地、江河湖泊等的创世神英叭。傣族的口头文学最开始是通过章哈(2)章哈,即傣族的歌手,在傣族狩猎经济初期就已经产生,章哈最开始既负责祭祀,又负责治病,同时还要唱歌。迫于社会的需要,章哈逐渐分化为了专管祭祀的摩赞和专门唱歌的歌手。章哈在傣族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傣族的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们传承着傣族最古老、最原始的歌谣和神话,并且在祭祀和生产活动中开拓和发展了傣族的诗歌。章哈的传承往往是家族传承制和师徒传承制,为傣族文学的创作培养了人才。创作和传承的,据史料显示,傣族的第一个章哈是名女子,因此女性是傣族文学最初的传播者。生育是女性乃至整个部族的大事,加之原始神话的传播者是女性,于是具有强大生育力的“大母神”形象在神话中大量出现。
二、美丽聪慧、富于反抗精神的“贵女”形象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傣族社会逐渐由蒙昧转入了封建领主制,出现了阶级划分。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使得傣族人不再囿于和自然的斗争,生活物资的富余,使社会产生了阶级,使族人产生了矛盾。封建领主制时期的西双版纳,社会阶级主要由贵族阶级与奴隶阶级组成,傣族社会从部落主体向家庭主体过渡。生产力的发展使生存条件得以改善,加之佛教的传入,傣族文学中的叙事长诗便应运而生。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叙事长诗多以贵族间的爱情为主,美丽聪慧、富于反抗精神的“贵女”大量出现。相较于“大母神”,“贵女”形象的塑造不仅仅停留在人物的外在,内在精神的丰富使其具有了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
《召树屯》是西双版纳地区流传最广的傣族长篇叙事诗之一,诗中所塑造的婻婼娜公主,可以说是傣族人对女性的终极想象。诗歌通过对婻婼娜公主外貌、表情和语言的描写,以及召树屯和百姓们看到婻婼娜时的行为和心理呈现,衬托出婻婼娜的美丽、可爱。“这是一朵正要开放的蜡梅花,勐板加地方找不出这样一个美女”[2]。婻婼娜不仅外貌美,内心更是机智、坚贞不屈,具有丰富的精神风貌。召树屯出战时,婻婼娜为其出谋划策,最终在她的帮助下,作为丈夫的召树屯取得了胜利。被摩古拉(3)摩古拉在故事中是傣族的巫师,代表傣族的原始宗教,与故事中代表佛教的叭拉纳西一恶一善,反映了当时西双版纳傣族原始宗教与佛教的斗争情况。诬陷时,婻婼娜心知难以分辩,于是借临终一舞的机会要回了孔雀衣,飞回了孔雀王国。回到孔雀王国的婻婼娜,即使在父亲的强压下也始终没有改变心意,一直坚持着等待召树屯[3]。
《松帕敏和嘎西娜》中的嘎西娜王后同样是极为美丽的女子,“蝴蝶在她面前不敢扇翅膀,孔雀在她面前不敢把屏开,萤火虫在她面前不敢放光芒”[4]17。正是她的花容月貌,导致她在独身等待丈夫和儿子的时候被船长垂涎霸占。嘎西娜是心软的、热爱百姓的王后,尽管无法反抗丈夫的决定,但在离开宫廷的时候,嘎西娜仍不断流泪回望家园,对故土与人民有着深深的眷恋。与儿子重逢时,嘎西娜看到两个王子满脸的伤痕悲痛至晕倒在地。但是嘎西娜的内心虽柔软却又极为坚强。她追随丈夫离开繁华温暖的王宫,甘愿在黑暗寒冷的森林里采摘野果。她祈祷猛兽只拿自己充饥,放过丈夫和两个孩子。离开松帕敏的十年里,嘎西娜从未被船长的花言巧语和金银珠宝哄骗诱惑。相反,对丈夫和孩子的思念使得她内心充满了愤怒,“她用眼泪磨洗锋利的箭,她用锋利的箭保护自己的坚贞”[4]65。嘎西娜十分聪慧,早就看穿王叔是一个心肠狠毒的人。但她懂得隐忍,从而能在阴狠的船长手下保全自己。
封建领主制时期,阶级压迫更趋严峻,自然界成为傣族人美好理想的寄托,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与自然的关系也非常亲近。从人物设定上看,《召树屯》仍延续着图腾神话中女性与自然力结合的特点,如婻婼娜被誉为“孔雀公主”。从故事细节上看,婻婼娜在面对生死危机之时变成了孔雀,嘎西娜随丈夫躲避残暴的王叔时在森林中生活,展示出自然界由原始时代人类的斗争对象变为逃避压迫的理想乐园。叙事长诗中的女性基本上以公主、王后这类高贵身份出现,则反映了阶级社会出现后傣族人对贵族血统产生的崇拜。
傣族女性美丽、聪慧、温柔形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和文化持有者由女性过渡到了男性。首先,《召树屯》和《松帕敏和嘎西娜》主要流传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当时佛教文化逐渐在傣族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了支配地位,影响了作品中女性真善美形象的刻画。《松帕敏和嘎西娜》以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贯穿始终,婻婼娜和嘎西娜在面对强悍的恶势力时的忍辱负重也是佛教思想的折射。其次,文学由女子传承的情况随着佛教的传入发生了转变,傣族文学的持有者和传播者转为了男性[5]。此时的傣族文学作品由寺庙中的僧人创作、传唱、补全,在创造和传播的过程中就带有了男性对女性的思考与审美。温柔漂亮、做贤内助、对待丈夫忠贞……这些美好品行正是傣族男子心中追求的女性美德。这一时期傣族封建领主的政权正在逐步兴盛扩张,因而文学故事中的男性需要四处征战,其形象往往具有刚毅勇武的特点,与女性形象的聪慧柔美形成了鲜明对照[6]。在政治立场控制和男性作者视角的影响下,长相美丽、坚贞善良、勇于对抗恶势力性格的女子成为傣族文学创作中的重要角色。
三、与阶级制度作斗争的“平民女”形象
西双版纳封建领主制和德宏地主经济并存于不同的地域空间,德宏地区因为交通条件的便利而与汉族有更深入的往来交流,在汉族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德宏傣族人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比西双版纳地区更先进,地主经济从而兴起。与西双版纳地区封建领主制土地归领主所有不同,德宏地区的地主经济导致的土地商品化则使商人成为地主,德宏地区的傣族也就从封建领主制踏入了封建地主制[7]。封建地主制的阶级矛盾在德宏地区的傣族叙事长诗中,体现为家庭内的“母女矛盾”和“婆媳矛盾”。处于母女、婆媳矛盾之下的女性形象更具体更情景化地刻画了傣族阶级关系的情感牵绊、人与人争斗的悲苦和对爱情、幸福的热烈追求。在阶级、经济的多重压迫下,叙事长诗的内容集中于平民对封建政权、婚姻束缚和封建伦理的反抗,诞生了一批勇于反抗封建土地制度的平民女性形象。
《娥并与桑洛》是傣族三大悲剧之一,主要流传于德宏地区,表现了傣族人民平民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极大反响,与叙事长诗《召树屯》齐名。诗歌中的主角娥并和桑洛都是平民,日常化的情节设置使他们的爱情故事不像《召树屯》中王子和公主的爱情那样远离世俗、过于抽象,而是让人感同身受、痛彻心扉。桑洛以外出经商为由躲避母亲的包办婚姻,与娥并在赶街(4)云南、贵州一带的方言,指前往特定日期汇集起来的贸易市场买卖东西。时相识相爱。娥并虽然出身贫贱,但对爱情大胆执着、勇敢决绝,毅然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而与桑洛结合。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桑洛母亲非常看不上娥并,要求儿子与门当户对的阿扁成婚。娥并与桑洛母亲的矛盾表层是婆媳矛盾,深层却是阶级矛盾,是已然形成的封建地主制度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傣族受汉族婚配观念的影响极深。来自社会下层的娥并明知桑洛的母亲不同意自己与桑洛的婚事,仍怀着孕千里寻夫,与其柔弱、单纯的外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娥并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桑洛家时,等待她的并不是爱人甜蜜的拥抱,而是桑洛母亲无情的折磨。最终,娥并被赶出家门,生下孩子后在森林里悲惨死去,桑洛也举刀自刎。娥并是反对封建婚姻束缚的女性的化身,她们不再忍受阶级的压迫,不再等待他人的救援,而是敢爱敢恨,积极追求自己的爱情。然而,面对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娥并与桑洛只能以死抗争,将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形态中阶级的对抗形象地再现出来,底层平民被压迫的现实和反抗的愿望清晰可见[8]。
如果说《娥并与桑洛》是平民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那么《叶罕佐与冒弄央》就是平民对封建伦理纲常的反抗。叶罕佐和冒弄央有着诗意的相遇、甜蜜的爱情,但是叶罕佐的继母为了十坨银子的聘礼要把叶罕佐嫁给自己的侄子罕布。为了逼迫叶罕佐就范,继母囚禁并折磨了叶罕佐三年,但是叶罕佐仍旧不肯向恶毒的继母低头,以致于在私奔失败后被继母残忍地杀害,得知其死讯的冒弄央也殉情而死。受汉文化的影响,德宏傣族女子的地位、婚姻、追求受到家庭制约。所以纵使叶罕佐是头人的女儿,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但是她还是会被继母派遣做粗活甚至被毒打至死。作品对叶罕佐与继母激烈斗争的细腻描写不仅无情鞭笞了继母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贪婪、罪恶,更体现了叶罕佐坚持不懈争取权利、反对包办婚姻的抗争精神。
恋人的爱情越纯洁,他们无力与现实抗争的悲剧结局就越能激发傣族人民的反抗精神,引起人们对傣族封建地主制度的反思[8]。封建地主制时期的文学倾向由对统治阶级的歌颂和隐晦的嘲讽转为直接的揭露和批判,文学内容由想象性描绘变为具体写实的控诉。地主经济制使得傣族人对领主制贵族血统的崇拜逐渐消弭,文学主角从王公贵族下沉至平民百姓,叙事长诗中国王、王后、王子和公主的角色很少出现,纵使出现也多是反面形象。从桑洛的父亲去奘房(5)即通常所说的寺庙,一般特指小乘佛教的寺院。拜佛后有了子嗣、叶罕佐父亲出远门请佛等情节可以看出佛教仍旧在德宏这片土地上盛行,娥并和桑洛死后化作两颗星星永远结合,这种理想化的结局也是大团圆思想和佛教轮回观念在叙事长诗中的关照。在封建地主势力的迫害下,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便将佛教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把美好的祈愿寄托在死后的世界。此时文学作品的话语权仍旧掌握在男性手中,他们在刻画阶级矛盾时关注到了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不自由,便以家庭恋爱纠纷为引子反映阶级斗争的残酷。这些有文化的男性创作者都是僧人,于是他们的文字书写与形象描绘都有了佛学的影子,如将娥并比作仙女,以佛教的思想对阿扁的丑恶与娥并的美善进行对比塑造。在这些爱情故事中,男主人公温和而忍让,他们在婆媳或者母女的纠纷中总是缺位的,这使得女主角在为幸福抗争的过程中缺少有力的支点,也就注定了结局的悲剧走向。这些具有反抗意识的“平民女”形象反映了在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受到汉文化宗法制度的冲击,德宏地区的下层傣族女性受到的统治阶级、婚姻家庭、封建伦理的三重禁锢。
四、追求自由与平等的近现代女性形象
近现代以来,傣族携手各族人民逐渐消除了阶级矛盾,傣族文学的主要矛盾聚焦为国内外文化与傣族文化之间的碰撞。无论是西双版纳地区还是德宏地区,都推行了民主改革,傣族女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傣族地区开始兴办学校,培养傣族女性知识分子。傣族文学逐渐吸收了新文学的养分,出现了一批反映傣族人民新生活的题材,家庭关系由母女、婆媳变为男女主角直接交锋,其中以小说最具代表性。这些傣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一改往日风格,明显展现出了近现代特色。
《南国情天》是傣族文学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述了缅甸少女丹瑞为了救治弟弟而嫁给傣族土司刀承宗,历经波折后二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女主人公丹瑞是意大利和傣族混血儿,是受过学校教育且成绩优异的女性,她的形象兼具傣族女性的传统特质和近现代女性的时代特色。丹瑞的身上散发着进步开放、开朗活泼的气息,她在与男友约翰玩笑时称自己为“反殖民主义的女战士”,打趣母亲与 “继父”刀承宗时神采飞扬,道别时会与母亲调皮撒娇。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丹瑞认为爱情是平等且专一的,所以无法忍受刀承宗有数个妻子,在得知自己是刀承宗第七个妻子时,打算离开刀承宗以抵抗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制,追求自由恋爱。丹瑞有求于刀承宗才委身于这个可以当自己父亲的人,二人不仅身份地位不匹配,学识眼界上也格格不入。一个是世袭的土司,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佛教文化、汉文化与新思想的熏陶,同时具有傣族的民族性格和土司的贵族性格;一个是受东西方文化影响、追求精神共鸣、具有现代意识的女子。丹瑞在新婚之夜顶着暴雨逃婚,是其不屈意志和反抗精神的写照,也是其追求自由与平等心声的身体力行。小说在丹瑞的形象塑造上用了许多笔墨,生动展现丹瑞傣族人温柔善良的本质和现代女性的平等自主精神。整个故事中丹瑞与刀承宗的冲突与交融其实是现代思想与传统文化对抗与调和的反映。最初,丹瑞学习的是外来西方文化,在与刀承宗结合后,又学习了傣族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民族文化。丹瑞的挣扎与反抗是两种文化互相排斥、斗争的人格呈现,丹瑞最终爱上刀承宗且愿意留在丈夫守护的土地上,则是外来思想与本民族文化和谐融合的表现。
在短篇小说《边境线上的开场戏》中有四方人物登台亮相:代表社会主义的文工站女负责人迈罕、受现代文化影响的傣族少妇依嫩、保留着传统思想的依嫩的丈夫孟靖和资本主义代表人物冒阴冷。孟靖在冒阴冷的挑拨下误以为妻子依嫩与舞伴埃喊亮有暧昧关系,坚持不让依嫩继续演戏,但其最终在迈罕的劝说下认识到这场演出对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及时悔改。在孟靖与依嫩的婚姻关系中,依嫩率先觉醒,她渴望参与戏曲演出,希望能通过表演傣族的传统戏曲对傣族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调适,丈夫孟靖则是她实现追求的一股阻碍力量。同时,迈罕作为文工站女负责人,站在时代前沿,对孟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品中女性魅力的彰显、女性之间的互助成为作者重点刻画的对象,孟靖的偏听偏信和小肚鸡肠在其妻子依嫩面前黯然失色。依嫩和丈夫之间的矛盾,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依嫩通情达理、心怀大义,拥有理想追求,被丈夫阻挠也坚持自己的信念;孟靖踏实肯干、会照顾人,具有傣族人的优良品性,但是难免受人挑拨,陷入小情小爱的桎梏之中。最终孟靖同意依嫩表演,代表着传统思想与现代思想的融合。冒阴冷与其他人的矛盾则是东西方思潮的矛盾,他秉承着资本主义价值观,希望通过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以娱乐的方式获取傣族人民的认同,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明显受到傣族民众的唾弃。小说通过对冒阴冷与两位女性的对比,突出了资本主义阵营对传统文化的摒弃,社会主义阵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场“开场戏”是社会主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沟通的桥梁,它的顺利开展意味着傣族人民运用现代化的方式来表演传统的傣族戏剧,达到传承自身民族文化和认同社会主义价值的目的。
在阶级消亡、阶级地位平等后,描绘女性故事的视角由阶级问题转移到了个人的生活问题和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上。爱情与工作的和解、外来思潮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成为女性故事的新话题,突破桎梏也成为现代女性的特色。时间与距离的飞速缩短让傣族人民与全世界人民都有了接触,傣族传统文化在与各国、各族的交往中得以巩固、创新与发展,傣族文学也展现了各种新思潮在本土的发展路径。《南国情天》反映了傣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和自身传统文化的调适涵化,以傣族女性生命历程的多环节穿插、文化震惊的消解、社会审美的矫正等方面作为集中体现,将多文化关系凝聚在一个女性形象上。《边境线上的开场戏》则通过两个对照组,对比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细致展现了国家对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调适以及构建民族意识共同体的过程。这两篇小说男主角的共性是前期思想较为固执传统,后期支持并帮助妻子成就事业及其思想上的成长。他们一开始的古板守旧更突出了妻子自由开放思想的难能可贵,后期在女性引导下发生观念的转变体现了女性独立人格的魅力。他们不将妻子禁锢在婚姻和家庭的琐碎里,而是尊重其独立人格、认可其社会价值,是女性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可靠支柱。随着时代包容性的增强,女性话语权得到重视,作者身份也不再只归男性所有,《南国情天》正是一位德宏傣族女性与一位西双版纳傣族男性共同创作的。在知识的普及下,傣族文学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家,他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往往也具有现代文明融合的特色。如《彩虹》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干部玉香,《凤还巢》中女承父业的民间歌手玉波,《调解员玉叫》中爱岗敬业、不徇私情的玉叫,等等,她们身上既有傣族女子美丽温柔、善良坚贞性格的烙印,又有现代女性自由与平等思想在她们身上留下的痕迹。
五、结语
历数傣族文学作品,纵然社会背景殊异,女性形象却都寄托着本民族的审美传承——善良与美貌并存,性情如水般温柔却又不失坚韧。但是傣族女性形象随着傣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改变。傣族文学形式发生了从神话、叙事长诗到小说的变化,傣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也随之变迁。神话具有魔幻色彩,神话中的女性形象不仅仅是以人的形态出现,更是以人与动物等结合的形态出现,是自然崇拜意识的产物;叙事长诗语言优美、含蓄深情,在描绘女性形象时具有突出其柔美特点的艺术效果;小说篇幅较长,能书写更多内容,因而刻画的女性形象相较其他文学形式更为丰满而生动。
在傣族女性形象变迁史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女性意识的一步步觉醒。原始社会时期,傣族女性的思想还比较蒙昧,虽然部族的领导者为男性,但是女性由于天然的生殖优势而受到了地位上的优待,她们只需要负责本部族的繁衍。到了封建领主制时期,傣族文学中女性的身份从普遍的母亲身份上升为“贵女”,她们开始为消灭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她们的反抗是被动的,无论是婻婼娜还是嘎西娜,虽然她们反抗了丑恶势力,但都是在等待丈夫来解救自己,从未主动去寻找幸福,所以还只是反抗意识的初步觉醒阶段。封建地主制时期的女性形象则是女性精神普遍觉醒的体现,这时的女主人公们都主动反抗阶级制度,在压迫下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光芒,她们追求婚姻与爱情的统一,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女主人公的平民身份也暗示了反抗群体的扩大。进入近现代以来,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民族交往日益增多,傣族人民的精神需求也从单一转向多元化,他们在继承固有文化特色的同时或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适应新文化。在新旧文化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傣族文学也在探讨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问题,并将写作的重点由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转向了对婚姻与爱情关系的反思、女性的个人价值与权利上。这一时期作品中的女性不再把婚姻和生育看作生活的全部,除了爱情外她们还自觉地追求亲情、友情、事业。现如今,傣族文学的创作中涌现出了各种角色身份、敢于追求自己人生价值的女性角色,这反映出傣族文学中的女性意识已然全面觉醒。
本文梳理了傣族作品中女性形象随傣族社会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的历程,为认识傣族先民的原始思维、旧社会普通民众对于阶层社会的情感态度以及社会发展对傣族女性意识觉醒的推进提供了文学性的视角。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角色之一,女性形象在傣族文学的发展中,成为傣族认识与描绘人与自然关系、阶级关系、文明关系的寄托,展现了傣族人民的价值审美和文化开放性。
——以傣族舞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