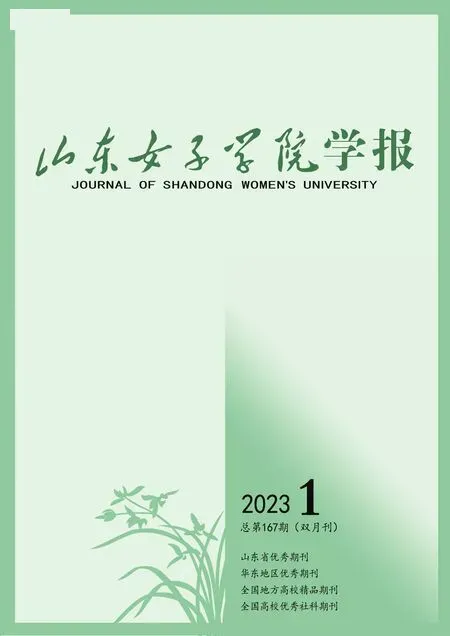性别微暴力研究:理论透视与干预策略
王海媚,李英桃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消除性别暴力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针对该问题的研究也随之深化和细化,近年来学界就将性别暴力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和平和非和平状态之间加以区分进行研究。进入21世纪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拉尔德·温格·苏(Derald Wing Sue)等学者从微暴力(microaggressions)和宏暴力(macroaggressions)的角度研究基于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1)“微暴力”有microaggression和micro-violence两种主要英文对应术语。micro的释义为“微”“小的”“微观的”,与表示“宏”“大的”“宏观的”的macro相对应,而在对微暴力特点的描述中的subtle还具有“微妙的”“细微的”等义,因此,文中的“微”具有多重含义,不仅仅是指规模上的微小,还有形式上的微妙。aggression指“挑衅”“侵犯”,violence指“暴力”,两者都表示具有一定攻击性和侵害性的行为,在本文语境中语义差异不大,因此文中“微暴力”涵盖这两种用法。参见[英]梅厄主编、王立弟等译:《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于灵:《警惕“微暴力”》,载《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5月21日。此外,国内学界也有“微侵犯”“微歧视”等用法,与本文的“微暴力”意义大致相同,参见肖鹏:《当偏见与歧视隐于日常:图书馆与信息服务领域中的“微侵犯”初探》,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18年第4期。,并提出微干预(microintervention)和宏干预(macrointervention)等应对策略。在上述研究中,性别宏暴力(gender macroaggressions)是指存在于社会结构、政策体系和法律制度中的系统性的性别偏见,对女性等弱势群体产生宏观的影响,这与传统认识中的性别暴力相对应。性别微暴力(gender microaggressions)则是指在日常交流和互动中,无意间通过微妙的、不屑的表情、手势和语气等途径,传递基于性别的歧视、侮辱和贬低等信息的行为[1],该行为及其负面影响充斥于人们的生活。需要注意的是,性别微暴力的施动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和多样的,男性和女性在不同场景或者说不同权力关系中都既有可能成为性别微暴力的施动者,也有可能成为接受者。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基于性别的、针对女性的微暴力行为。
性别微暴力是父权制的产物,被掩盖于性别宏暴力之后,直到晚近才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除了性别微暴力本身,同时被忽视的还有这种暴力行为对目标群体造成的难以言状的、长期累积的负面影响。研究、识别和应对性别微暴力,打破长期对其“视而不见”的局面,使人们意识到性别微暴力的存在与危害,有助于形成关于防治性别微暴力的社会共识,从而在更深层上更彻底地解决性别暴力问题。
一、“发现”被隐藏的性别微暴力
性别微暴力是有意识的、直接的性别暴力的下意识的、隐晦的表达形式,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被忽视,甚至被视为是“自然”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国际社会普遍倡导消除性别暴力的影响下,在社会道德规范的作用下,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减少或避免发生直接的、公开的和带有明显攻击性的性别暴力,深藏于性别宏暴力底层的性别微暴力行为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从被“视而不见”转而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
(一)性别微暴力研究产生的背景
消除基于性别的暴力是联合国针对性别议题的会议重点讨论的内容。1975年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墨西哥宣言》强调应该“根除对妇女和少女施行的侵害人权行为,例如:强奸、卖淫、人身侵害、精神虐待、童婚、逼婚和买卖式的婚姻”[2]。1980年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后半期行动纲领》认为,应该“为消除对妇孺的一切形式暴力和为免除各种年龄妇女遭受家庭内暴力行为、性强暴、色情剥削及任何其他形式凌辱造成的身心损伤,制定政策和方案”[3]。1985年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指出,“在所有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都存在有对妇女的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殴打、残害、烙烧、非礼和强奸。这种暴行是实现和平及妇女十年其他主要目标的一个主要障碍”[4]。1995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申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侵犯了妇女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认识到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历史上男女权力不平等关系的一种表现……它迫使妇女陷入从属于男子的地位”。这份宣言还明确界定了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含义,即“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而不论其发生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5]。早期国际文书中将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按照两种大类进行划分,包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性别暴力,以及和平状态与非和平状态下的性别暴力。
第一类,公私领域中的性别暴力。《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详细列出了公私两大领域具体存在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私人生活领域的性别暴力主要是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对女童的性凌虐、因嫁妆引起的暴力行为、配偶强奸、阴蒂割除和其他有害于妇女的传统习俗、非配偶的暴力行为和与剥削有关的暴力行为。公共生活领域的性别暴力主要是在社会上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性凌虐,以及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扰与恫吓、贩卖妇女和强迫卖淫。国家所做或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无论其在何处发生[5]。
第二类,和平和非和平状态下的性别暴力。和平状态下的性别暴力是指非战争和冲突状态下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普遍存在于公私领域,几乎涵盖第一大类中所述的全部暴力行为。而在战争和冲突状态下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同样十分常见,并可能带来更严重的伤害。“武装冲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与恐怖主义以及扣为人质仍然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侵略、外国占领、种族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是影响几乎每一区域妇女的现实状况”[6],战争中对于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包括“迫害、拷打、惩罚性措施、屈辱待遇和施行强暴等”[7]。国际社会“呼吁武装冲突各方采取特别措施,保护妇女和女孩在武装冲突局势下免受基于性别的暴力”[8]。
尽管上述两种划分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从形式和效果上看,它们都属于直接性、系统性针对女性群体的暴力行为,并且是显著可见的,传统认知中的性别暴力主要为这种直接性的暴力行为,它们与21世纪以来德拉尔德·温格·苏等学者们提出的性别宏暴力概念相对应。学者们同时提出,除了性别宏暴力之外,还存在一些非直接性、具有一定隐蔽性的暴力行为,也即性别微暴力,这种暴力行为通常在施动者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接受者往往无法对其进行准确捕捉和描述,但这些暴力行为同样对女性群体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由此,性别宏暴力、性别微暴力被引入性别暴力研究,成为针对性别暴力的新的划分方式。
直接的性别宏暴力与非直接的性别微暴力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可大致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性别微暴力一直存在,但长期被更加显著的性别宏暴力遮蔽。第二,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直接的性别宏暴力行为有所缓解,隐蔽的性别微暴力行为开始被关注到,并成为学界研究的新议题。第三,在数字化时代,虚拟网络空间刺激了性别微暴力行为的发生,匿名发布的性别微暴力信息数量巨大,并且其中的一部分正在演化成隐藏在非实名背后的公开性、直接性的性别暴力信息,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融中,性别宏暴力与性别微暴力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二)性别微暴力研究的缘起与发展
微暴力这一概念最早在针对种族歧视的研究中提出,随后,有学者关注到基于性别、性取向等多重因素的微暴力行为,提出了性别微暴力的概念,并研究了它的内涵、类型、危害及应对策略。在性别微暴力研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同时,也有学者对该研究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第一,微暴力概念的产生与发展。1970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育和精神病学终身教授切斯特·皮尔斯(Chester Pierce)首次在《进攻机制》一文中针对种族歧视提出微暴力概念,认为其是针对非裔美国人日常的、微妙的、通常自动发生的羞辱和侮辱等行为[9]。基于皮尔斯对种族微暴力的研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玛丽·罗维(Mary Rowe)于1973年提出微不平等(microinequities)概念,将其定义为短暂的、难以证明的、隐蔽的微小事件,通常在施动者感知到“不同”的时候,对接受者无意识做出的行为[10]。在此框架下,罗维研究了招聘过程中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养老金发放中的性别差距、新教徒占多数的环境中少数派信徒的境遇等问题[11]。2006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杨(Stephen Young)提出微信息(micromessaging)概念,研究在政治观点、婚姻状况、职务任期和个人风格等因素影响下,施动者无意识地通过手势、语气等超越语言的“微信息”来影响接受者,造成施动者与接受者之间“微不平等”现实,并阐释了其对接受者的工作表现和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12]。2015年,美国加州大学学者佩雷斯·胡贝尔(Pérez Huber)和丹尼尔·索洛尔扎诺(Daniel Solorzano)提出了宏暴力概念,将其定义为现有或潜在的社会安排,使主导群体的利益和/或地位在非主导群体之上,并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13]。2020年,德拉尔德·温格·苏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卡桑德拉·卡莱(Cassandra Calle)等学者指出性别宏暴力是一种系统性的性别偏见,出现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制度和法律安排中[14]。自此,对暴力的微观和宏观研究形成了呼应。
第二,性别微暴力概念的提出。德拉尔德·温格·苏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兼职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娜·卡波迪卢波(Christina Capodilupo)认为微暴力不仅针对少数族裔,还针对社会上所有边缘群体,它们可以基于性别、性取向、阶层或者残障等各种因素[15]。在《日常生活中的微暴力:种族、性别和性取向》一书中,苏提出微暴力存在于日常生活交流中,施动者无意传递出隐含贬低和歧视的信息,接受者很难准确描述这些微妙的(subtle)、模糊的(nebulous)和不具名的(unnamed)暴力行为,但却被它们严重伤害。该书归纳了性别微暴力的微攻击(microassault)、微侮辱(microinsult)和微贬低(microinvalidation)三种形式。(1)微攻击通常是有意识发生的,将带有基于种族、性别或性取向的偏见的举动或态度,通过环境、语言或行为举止传达给边缘群体,这些信息会使他们感到不受欢迎和不安全,比如在公开场合讲关于妇女或者性少数群体的笑话,当面评论女性的容貌或身材等。微攻击多是有意识发出的,需要满足一定的外部条件,即施动者拥有一定的安全感或者具有一定的匿名性,比如在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群中,或是在不需要实名的网络平台上。(2)微侮辱通常是无意识发生的,通过环境和人际交流隐蔽地传递基于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侮辱性信息,比如“女强人”“铁娘子”等标签暗含“能干的女性没有女人味”“属于异类”等意味,使女性成功案例变得特殊化,从而否定妇女普遍拥有智慧和能力的事实;否定歧视行为,认为竞争环境是公平的,男性和女性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女性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其自身;自动将妇女身份降级,比如默认女性医务人员为护士而不是医生,默认妇女为秘书而不是管理者,等等。(3)微贬低往往是无意识发生的,是一种针对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否定态度,否认这些边缘群体或个人的文化、现实经验及感受。例如当男女两位员工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时,领导很可能会自动忽略女性的声音,甚至是在女性员工先发言的情况下。这实质上是否认主流群体的权力和特权,否认某些特权群体是在不平等对待边缘群体的基础上获得的个人利益,同时限制边缘群体定义现实的权力[1]。吉娜·都灵和卡波迪卢波主编的《微暴力理论:影响与启示》一书收录了20余篇论文,对微暴力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交叉性视角下进一步探讨了种族、性别、性取向、社会阶层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微暴力问题。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副教授乔尼·刘易斯(Jioni Lewis)等学者提出种族性别微暴力(gendered racial microaggressions)概念,并开发了针对种族性别微暴力的定量分析框架——性别种族微暴力量表,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赛琳·德布莱尔(Cirleen DeBlaere)等学者研究了少数族裔和性少数群体双重身份带来的微暴力行为,等等[16-18]。
第三,性别微暴力的危害研究与应对建议。性别微暴力对于妇女、性少数等弱势群体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苏曾系统梳理了性别微暴力对于弱势群体的自信心和情绪造成的损伤,还有一些学者选取特定的施动者和接受者对性别微暴力的危害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比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学者雪莉·马库斯(Cherry Marcus)和路易斯安那理工大学学者威尔科克斯·梅兰妮(Wilcox Melanie)以近400名顺性别女性为样本,研究了性别微暴力作为创伤性压力源的作用,她们认为持续性的性别微暴力会造成妇女群体将性别歧视内化,并削弱她们的自我同情,女性的低自我同情是性别微暴力导致的创伤性应激反应[19]。美国大峡谷大学学者林恩·桑福德(Lynn Sanford)以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调查了性别微暴力对美国女性军官的影响,利用交叉性视角论证了军队系统内部多重的歧视和微暴力对女军官发展的限制[20]。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系学者塞拉·丁伯格(Sierra Dimberg)选取压力等级、军衔和性取向等变量,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军队性别微暴力与女军人患抑郁症之间的关系[21]。美国卡佩拉大学学者罗伯特·沃尔夫(Robert Wolff)分析了父母、教育工作者、医生、牧师、执法部门、雇主等不同身份的施动者如何对性少数群体做出微暴力行为,以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22]。总的来说,性别微暴力可能导致妇女发展受阻、自信受损,甚至可能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因此,积极应对和消除性别微暴力具有重要意义。以苏为代表的学者们对比分析了基于性别的宏暴力和微暴力的含义、表现形式和影响,并提出结构、制度和法律层面的宏干预以及个人层面的微干预等应对策略。宏干预是从结构、制度和法律层面消除暴力行为,比如修改法律或者改革不合理权力结构,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微干预包括微肯定(microaffirmations)、微保护(microprotections)和微挑战(microchallenges)等具体措施,可以通过个体努力实现,更具可操作性,当个体努力不断积累并且形成一定规模时,便能够比较有效地应对性别微暴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性别宏暴力[14]。
可以说,目前对于性别微暴力的含义、类型、危害和应对途径的论述基本完备,但在性别微暴力研究不断发展和成熟的同时,学界也开始对微暴力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首先,有学者认为将微小事件上升至暴力的程度是不合理的,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并表示很难观测到这种所谓的“暴力行为”对互动双方的影响。比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者肯尼斯·托马斯(Kenneth Thomas)将苏关于微暴力的观点称为“多元文化中的宏废话”(macrononsense),他否认《日常生活中的微暴力:种族、性别和性取向》所列举的案例具有歧视的意味,认为它们只是生活中令人厌烦的小事情,但是不应该上升到歧视和暴力的程度,因为这种做法会在人群中产生寒蝉效应[23]。其次,有学者认为现有研究忽略了性别微暴力可能对施动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国东田纳西州立大学医学院学者托马斯·沙赫特(Thomas Schacht)认为跨种族的“微互动”(microinteractions)不一定是微暴力的证据,在两者的互动中,双方都可能受到对方的影响,他据此认为,在这种无意识的微暴力互动中,没有一方仅仅是加害者,在某种意义上双方都是受害者[24]。再次,既有研究认为性别微暴力由直接的性别暴力行为伴随人类文明不断进步逐渐演化而来,这就忽略了性别微暴力一直与性别宏暴力共存的事实。实际上,性别微暴力自古有之,比如不听“妇人之见”便属于由来已久的无视女性声音的性别微暴力行为。但其长期处于“不可见”的状态,随着直接的性别暴力与性别微暴力的关系发生的变化,以及对性别暴力研究的不断全面和深入,隐藏于性别暴力深层的性别微暴力直到晚近才得到应有的关注。
二、性别微暴力的成因与危害
性别微暴力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并且通过社会内化过程获得了“合理性”,这是其不被关注的原因。性别微暴力带来的危害同样处于“视而不见”的状态,但这不意味着伤害程度更轻,性别微暴力带来的伤害可能是更加深层的,比如其对女性自信带来严重损害,这刚好给促进性别平等最有效的途径——妇女赋权带来削弱甚至消解的后果。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性别微暴力可以通过代际传递,因此,其产生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累积甚至是不断强化的。
(一)性别微暴力的成因分析
性别微暴力是父权制和暴力文化的产物。父权制本身就与暴力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不仅体现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针对妇女的直接暴力,以男女不平等和歧视妇女为特点的结构暴力;而且在文化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如宗教、歧视妇女的法律规范、迫害妇女的社会习俗、色情暴力文学、社会性别化的语言等”[25]351。暴力文化是指“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为主导,推崇以战争暴力作为解决冲突的基本方式,以文化暴力为主要构成部分的文化”[25]349。构成暴力文化的文化暴力往往是基于性别的,它通常深藏于心,不易觉察,难以改变,并且能够带来难以平复的伤害,“如女性,出生时是生了一个‘赔钱货’,没结婚的是‘老处女’,结婚后是‘泼出去的水’……事业顺遂的‘女强人’多半气势凌人……中国大陆近年则有笑称人有三种:男人、女人与女博士,等等,这些价值观明显地将女性特别是与传统性别角色不符的女性加以贬抑,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皆可能自然而然地接受这些价值观并加以内化,难以拔除”[26]。性别微暴力根植于基于性别的暴力文化的深层逻辑,并且在内化作用下成为施动者下意识的自发性行为。性别微暴力持续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首要原因是其可维护以男性为主导的统治者的既有权力和利益。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是社会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者,在各个领域和各个级别的决策中享有话语权,他们也是现有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和坚定维护者。因此,他们拒绝承认现有制度和社会秩序存在问题,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从中受益,而更愿意相信一切都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比如,美国的精英神话(myth of meritocracy)声称,种族、性别和性取向对于个人成功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假设所有社会群体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在此逻辑下,成功和失败都可以归因为个人因素,包括智力、努力程度等。所有的成功都是个人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努力的结果,而失败则被看作个人缺陷或者努力不足[27]。男性对于权力的把控还体现为女性晋升困难,女性也许可以被提拔为中层干部,但是很难进入高层领导层,因为女性掌控权力被视为对男性权力的威胁。
对于女性群体的“同化”和“异化”都是性别微暴力得以存续的手段:(1)在对女性群体的“同化”过程中,男性主导者在亲强疏弱、亲多数倾向和反少数倾向的情感影响下(2)关于“亲多数倾向”,参见Dovidio John., et al:Why Can’t We just Get along? Interpersonal Biases and Interracial Distrust,载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002年第2期;关于“反少数倾向”,参见Sue D.W:Overcoming Our Racism:The Journey to Liberation,John Wiley & Sons, 2003年。,希望利用他们认可的主流文化对少数和边缘群体进行主流文化同化,从而达到弱化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掩盖其基于差异的歧视行为的目的。“性别盲视”(gender-blind)即是很好的例证,比如在应聘过程中,男性考官声称看不到性别,“人就是人”,即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会得到公平对待,但只有最具能力和最符合职位要求的人才会入选,这就否认了制度性性别歧视的可能[1]。同时,在单一主流文化的影响下,边缘群体的主体性可能会逐渐变弱,少数人的利益被损害和少数人的压力会变得更加“不值一提”。(2)在对女性群体的“异化”过程中,男性通过强调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男性角色定位和女性角色定位的差异,将“感性”“软弱”“属于家庭”的她们置于需要被保护和被统治的地位,从而巩固了男性对女性群体的支配权。社会性别的建构就是一个性别身份异化的过程,它建构了公共领域和家庭私域中男性与女性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使“属于”男性和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成为制度化的行为规范,进而确立了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性别身份异化的结果使得男性往往与积极、理性、独立、支配等特征相联系,而女性往往与消极、非理性、依赖和被支配等特征相联系,这样制度化的安排会进一步将妇女限制在她们“应该在”的位置,比如家庭劳动和家庭照护的外延职业等[28]。
(二)性别微暴力的消极影响
性别微暴力的危害是双向的,对施动者和接受者都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对于接受了社会公正、性别平等的价值观,并且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善意的、无辜的”的施动者来说,实施性别微暴力的指责也会引发他们的愤懑委屈等情绪。而接受者遭受的消极影响更为严重,性别微暴力通常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微小片段,它们不易被捕捉也很难被证实,正因为性别微暴力是时常发生的,这种不断累积的危害就更严重。总的来说,性别微暴力是社会边缘群体持续不断的真实经历,这些微妙的歧视行为会对接受者产生多重影响。
首先,性别微暴力会使女性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同时会产生愤怒、沮丧和不安全等情感,幸福感和价值感被降低,真实的能力被抑制,甚至可能引发身体健康问题,缩短预期寿命。性别微暴力给女性带来很大压力,这会引发应激反应,使她们持续警惕,最终增加其患冠心病、高血压、头痛、哮喘和抑郁症的几率,这些压力还会降低她们自身的免疫功能[29]。其次,性别微暴力阻碍女性在教育、就业和获得医疗服务方面享有与男性一样的平等机会。以职业发展为例,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工作环境中,女性可能会受到来自领导、同事甚至其他女性的性别微暴力,从而影响她们实际能力的展示和发挥,她们的贡献可能直接被忽略。比如人们熟知的“玻璃天花板”现象,就是“指妇女在攀登职场阶梯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通往权力顶层的道路上遭遇的看不见、摸不着却通不过的障碍”[30]。女性在选择职业时面临许多障碍,有很多工作被认为是不适合女性的,比如有些国家依然保留以保护妇女为名义的妇女职业禁令(3)苏联政府于1974年制定了《禁止雇用妇女从事繁重劳动和有害或危险劳动条件的工作清单》,目前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还保留着关于“禁止妇女从事的工作”的法律,乌兹别克斯坦于2019年取消了女性职业禁令,但仍然在《劳动法》中列出了40余种认为对女性有害的工作。,这会影响用人单位招聘过程中的性别选择,同时也在无形中限定了妇女的择业范围。再次,妇女在应对性别微暴力的时候,往往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她们需要投入精力确认那些隐约感到的不公正对待是否确实暗含性别歧视的信息;另一方面,她们还需要面对难以提出问题并且寻求解决的困境。“‘妇女不提要求’的原因与她们所处的不利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联系,比如社会发出的信号、对行为规范的要求、孩子的社会化过程、成年人的期待……‘不提要求’给妇女带来的不仅是金钱上的损失、健康上的问题,更给其工作态度带来消极评价。”[31]女性很难讲出自己遭遇性别微暴力的事实,在讲出之后,她们也可能会遭到质疑和反击。最后,性别微暴力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尽管每一次微暴力行为本身的影响可能是微小的,但当它们不断累积,便会产生量变到质变的效果,无论是在心理健康方面还是在个人发展方面。这种负面影响还会通过代际传递,使女儿在母亲的话语、情绪和应激反应中感受到性别微暴力的消极影响,并通过自身体验强化这种感知。
探讨性别微暴力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其在当今社会的新形式和变化趋势。在数字化时代,与过去面对面的交流相比,网络互动越来越成为人们沟通的主要方式。而虚拟空间似乎更加能够满足性别微暴力的发生条件:一定的安全感和匿名性、拥有相同观点的群体等。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数字化的微暴力行为也许会变得更加频繁,基于阶级、性别和性取向的微暴力行为更有可能组合出现;另一方面,微妙的、非直接的暴力行为可能重新转向直接的歧视行为,隔空对话和匿名发言的方式可能会减弱发言者被指认为性别歧视者的顾虑。但直接歧视的转向并不意味着微暴力行为必然会减少,隐晦的和公开的歧视行为很有可能会同时增多,这些变化都会加剧性别微暴力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性别微暴力的识别与应对
性别微暴力通常在下意识的情况下发生,无论是施动者还是接受者可能都难以捕捉、识别和确认这种暴力行为的存在,这就使性别微暴力具有双向模糊的总体特征。因此,明确性别微暴力的基本特征,掌握识别性别微暴力的方法和指标十分重要,这有助于使不同性别的人群,或者说使施动者和接受者群体都意识到性别微暴力存在的事实,进而达成防治性别微暴力的社会共识,以便从根本上消除性别微暴力,缓解性别微暴力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性别微暴力的特征分析
性别微暴力来源于暴力文化,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使暴力本身被掩盖,将暴力行为掩饰为合理的和自然的。“改变暴力行动的道德色彩,从红的(错的)变为绿的(对的),至少是变成黄的(可以接受的)……另一种方式是混淆真相,结果使得我们看不到暴力的行动或事实,或者至少不认为它是一种暴力。”[32]由此,性别微暴力具有双向模糊的特征。一方面,施动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何不妥或者说暗含歧视的意味,他们的很多行为是下意识地、自然而然发出的,通常还是“出于好意”的,在他们看来这些行为是善意的、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另一方面,接受者很难准确捕捉、证实这些暗含的信息,充满日常生活的性别微暴力确实令接受者感到不适和压抑,但是她们很难确定这是何种行为并且无法对其进行明确定义,对于接受者来说,性别微暴力是普遍存在的,同时也是转瞬即逝和不可言状的。
除了双向模糊性以外,性别微暴力还具有一些具体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导致其容易被忽视的原因。第一,它为非直接歧视性表达。多数情况下,性别微暴力可以是非直接歧视性表达,甚或是非语言表达,歧视性信息通过不屑的表情、语气和手势或者有贬低意味的环境传递,同时,这些歧视性行为也是难以描述和证明的。比如,当女职员向男性领导汇报工作时,男领导会时不时地看手机,而其他男同事发言的时候,男领导却很少看手机。充满“不欢迎”意味的环境也会给人带来无形的压力,如当女生进入由男生占多数的理工科专业学习时,能够感受到周围环境带来的排斥感,而在她作选择之前,很可能首先会面对包括父母在内的身边人的反对。第二,它是微妙的、无形的。由于性别微暴力是非直接歧视性表达或者非语言性表达,因此很难直观且清晰地证明和辨别出其中的歧视性信息,且这些歧视信息总是隐藏在看起来公平公正的信息背后。比如,当一位老师夸奖女生的数学成绩非常出色,“是女生中的佼佼者”的时候,看起来是夸赞的话语,但背后隐含的信息是:“一般认为,女生普遍数学成绩不好”“女孩子逻辑思维能力差,更适合学文科”“女孩子不适合学理工科”。当一位男性领导总是记不住女职员的姓名时,很难说是因为男领导记性不好,还是他认为这位女职员不重要。第三,它是自动的、通常是无意识发生的。性别微暴力也会是受过良好教育且接受了社会平等和性别平等观念的人“出于好意”发出的行为,在遇到某些特定的情景时,潜意识里的陈旧性别观念就会自动发挥作用,使得施动者作出“自然而然”的反应。比如,当人们遇到一位婚育年龄的女性时,通常会问对方“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孩子?”这样的问题,在得到否定答案之后还会补充提出“那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打算找吗?”之类的问题。这样的发问源于传统观念中“女人到了年龄就得结婚”或者“结婚是女人成熟/成功的标志”的观点,而忽略了女性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第四,它是可继承的、持续性的。没有人能免于受社会偏见影响,所有人都会在家庭、学校教育和其他社会化过程中接触到那些由来已久的、可能会一直传下去的传统观念,并将其融进潜意识里。在这些传统观念里,或多或少地包含同样“由来已久的”性别差异观念和对不同性别的区别对待。另外,尽管在意识层面人们认可社会公正与性别平等,但可能在潜意识里还是具有“亲多数疏少数”的情感倾向,这会造成人们对妇女、性少数群体等弱势群体下意识的排斥。
(二)性别微暴力的识别依据
如前文所述,性别微暴力的施动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做出微暴力行为,而接受者感受到了负面影响却无法准确找到背后的原因。因此,了解和掌握性别微暴力的不同类型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是准确识别和判断性别微暴力的重要前提。既有研究将性别微暴力划分为“性客体化”“二等公民”“使用性别歧视的话语”等类别[1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还有更多类型的性别微暴力陆续被“发现”。根据强调和针对的内容不同,可将最常见的九类性别微暴力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强调妇女的“性”属性,剥夺女性对身体的掌控权,损害她们的主体意识,使其成为“男性凝视”甚至嘲笑和戏弄的对象。属于这种情况的性别微暴力具体包括:(1)性客体化。这类性别微暴力使他人(主要是男性)获得愉悦和满足占有欲,而女性的主体性则完全丧失,比如男性对女性进行长时间的上下打量或凝视。工作或学习场合中的性客体化会使女性有被冒犯的感觉,同时会对自己的能力是否得到足够的认可和重视而产生焦虑,她们担心只有自己的外貌被看到,而业绩完全被忽视,或者反过来对自己的真实能力产生怀疑,担心自己获得好评仅仅是因为外表好看。有学者认为,女性的自我客体化也是真实存在的,当她们受到过分的性关注甚至遭遇性骚扰时,有可能会将自己和其他女性客体化为单纯的性存在[33]。(2)性别歧视的幽默(“开黄腔”)/笑话。人们在聚会中、广告上以及娱乐节目中经常听到或看到性别歧视的幽默或笑话,比如揶揄女性相貌或身材、在女性面前故意讲黄色笑话、在娱乐节目中进行夸张的女性装扮等。这些行为是对陈旧性别印象的固化和宣传,影响了受众的认知,同时暗示了女性可以被当作公开嘲笑的对象等。
第二,强调性别差异,否认女性同样优秀的事实,将她们视为在能力、智慧和贡献方面都低于男性的次等群体,她们的观点和需求被轻视。这使得“理性”“勇敢”“积极”“有领导力”“有创造力”“善于运动”等男性特质和男性的主导地位被一进步巩固和强化。属于这种情况的性别微暴力具体包括:(1)二等公民。这类性别微暴力通过环境、语言和行为举止传递贬低性信息,表明女性不应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机会和利益。比如,女性领导在边缘位置;男性创业者更容易获得支持;女性运动员通常不能享受与男性运动员对等的待遇;女性顾客可能会获得更少的关注和服务;当男性顾客和女性顾客预约时间冲突时,往往是女性顾客被更改服务时间;等等。(2)劣等假设/智力分配。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更善于语言表达和交际,而在智力和身体素质方面有欠缺,或者依据性别不同进行智力等级分配。此类观点包括“女生不适合做学术”“女生逻辑思维差不适合学理工”“女性体力偏弱不适合这项工作”等。197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心理和大脑学家杰里·利维(Jerry Levy)基于脑部构造性别差异提出了“拥挤假说”,即女性大脑更具对称性,左右半球共同处理语言功能,导致处理空间感知的右脑发生“拥挤”,因此得出“男性具有更强的空间感知能力、女性更擅长语言表达”的结论[34]。这似乎为此类性别微暴力提供了支持,但随着脑科学研究的发展,实验证明大脑结构差异不能简单映射为行为差异,学习、训练等后天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等都在其中发挥影响[35]。(3)隐形。在很多情况下女性是隐形的,女性声音被无视,女性经验被认为不重要。比如,在团队合作中女性员工的贡献较少被提及;在高校课堂上女生较少被点名;男性员工的姓名更容易被记住,等等。
第三,强调社会性别,否认存在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认为目前的性别分工和性别角色定位都具有合理性,男性和女性分别处于其“应该”在的位置,认为男性作为主导性群体没有通过歧视和不公正对待女性等弱势群体获益,弱势群体的不利处境都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性别微暴力具体包括:(1)使用性别歧视的话语。话语是父权制下的职业性别分化和社会性别角色固化的重要工具,人们往往将职业按照性别加以区分:医生、警察、消防员、建筑师等习惯性地被认为是强壮的男性的职业,而护士、秘书、售货员等被认为是柔弱的女性的职业。用“他”或者“男人”代替全体人类也属于这一类型,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开头写道:“所有男人生而平等”,这就意味着“天赋人权”只有男性可以享有,女性被排除在外。在此背景下,1848年7月美国第一次以女权主义为主题的妇女代表大会通过的《权利和意见宣言》提出要在“所有男人”后面加上“女人”,以示无男女之别的平等[36]。(2)限制性性别角色。许多性别微暴力都与女性“应该”扮演的传统角色有关,她们被告诫不要打破传统性别定位,一旦违规便会遭受惩罚。比如人们认为妇女就要足够温柔,有女人味,女人嫁个好男人和相夫教子更重要,女人不应该过于能干、过于要强,否则就会面对孤立和非议。如前文提到的“女博士”一度成为年龄大、性格怪异的单身女性的代名词。(3)否认性别歧视现实。男性群体普遍不愿意承认存在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否认女性经验的有效性。类似观点包括:性别歧视已经成为历史,女性在现代社会已享受了“得天独厚”的待遇,很多对于性别歧视的抱怨都是因为女人太敏感,她们只是在外化自己的负面情绪,等等。同时,女人也被善意奉劝,“每个人都被公平对待了”,女性的不成功是出于她们自身的原因。(4)否认个人性别歧视。一些接受社会公正、性别平等观念的男性个体倾向于否定做出带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行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性别平等的支持者,比如解释说“我不是性别歧视者,我也有妻子和女儿”“我提拔手下的时候非常公平,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在此逻辑下,女性的不成功被认为是她们自身的原因导致的。
上述性别微暴力行为往往不是单独发生的,施动者可能通过语言、表情和动作等多种途径同时传递歧视性信息,并涉及不同种类的性别微暴力。对于施动者来说,以组合形式发生的性别微暴力与单发的歧视性行为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对于接受者来说,多重的性别微暴力带来的负面感知会更加强烈。
此外,还需注意少数或边缘群体之间的交叉性问题。多重边缘身份必然会带来多重的交叉性的歧视和微暴力,比如黑人女性可能遭遇到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三重压迫[37],而这种交叉身份可以持续叠加,当这位黑人女性同时具有残障且为性少数个体时,她就有可能会面临五重压迫,甚至更多。面对同种微暴力,不同身份的个体遭受的歧视级别也有差异,比如在种族微暴力面前,黑人女性比黑人男性的处境更差,黑人同性恋男性的地位低于黑人异性恋男性,而黑人同性恋男性与黑人女性之间的等级关系是不固定的,在强调男性优于女性的情况下,黑人同性恋男性的等级也许会高于黑人女性,在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影响下,黑人同性恋男性的等级也许低于黑人异性恋女性。同时还应该看到,在不同微暴力情况下,施动者和接受者身份是可变的,甚至是可以互换的,比如黑人男性既可以是白人男性和白人女性发出的微暴力行为的接受者,也可以是针对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的微暴力行为的施动者,等等。
(三)性别微暴力的应对策略
在当今社会,针对女性和性少数等边缘群体的微暴力行为是持续存在的社会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发生不同情况和类型的性别微暴力的时候,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施动者或者接受者,并且都可能受到性别微暴力的负面影响。但由于这些暴力行为是“隐形”的,因此,根据前文列出的识别依据,准确捕捉、识别和界定性别微暴力,承认存在性别微暴力的事实,是积极应用性别微暴力的重要前提[1]。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别微暴力的应对策略可以分为下列三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明确性别微暴力存在的事实及其带来的危害,尽可能达成关于消除性别微暴力的社会共识。性别微暴力具有的双向模糊的特征使得施动者无法真实感受到微暴力存在的事实,接受者无法对其进行准确描述,这对双方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不了解性别微暴力的情况下,双向模糊的互动导致施动者和接受者两方都会积压很多负面情绪,施动者不能理解自己的行为被看作歧视性行为,从而产生不满和愤怒;接受者无法确认自己遭遇了何种歧视性行为,也无法准确描述,导致其产生更多不安全、不信任和压抑的情绪,这可能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相反,使施动者和接受者都意识到性别微暴力的真实性,并了解到性别微暴力带来的伤害,在两者之间达成关于消除性别微暴力的社会共识,发挥社会共识的导向作用和秩序作用,将有助于更好地解决性别微暴力问题。关于消除性别微暴力的社会共识可能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成为道德律令,依靠伦理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同时还可能“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阻碍合作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38]。可见,关于消除性别微暴力的社会共识可以发挥与暴力文化相反的作用,促使施动者有意识地减少微暴力行为,接受者敢于“发声”和“提出要求”,以积极应对性别微暴力的危害,这些都有助于从根源上防止性别微暴力的发生。
第二步,赋权妇女、性少数等边缘群体,鼓励她们实现由微暴力的被动接受者向积极应对者的身份转变,并在彼此之间建立广泛联结,实现相互支持,以便缓解性别微暴力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最终消除性别微暴力。在此阶段,根据手段和目标的不同,还可以划分出通过给予彼此“微肯定”以缓解性别微暴力带来的消极影响,预先告知彼此可能发生性别微暴力的事实以起到“微保护”的作用,对性别微暴力进行公开的、积极的“微挑战”以消除性别微暴力这三类应对措施。(1)通过妇女和性少数等边缘群体之间彼此做出让人感到自己被看到、被尊重、被支持的举动来缓冲性别微暴力的消极影响,其中,既包括鼓励和肯定性质的语言表达,也包括传达善意的肢体语言等。这些做法是与带有否定、排斥和异化意味的性别微暴力完全相反的过程,目的是肯定边缘群体受到性别微暴力的真实感受并对其进行支持。(2)采取针对性别微暴力的消极影响的预防措施,边缘群体预先告知彼此可能会遭遇到的性别微暴力情况以建构相应的心理防护机制,肯定她们的个体价值和平等社会地位,使其树立起对不平等社会结构和性别微暴力行为的批判意识。(3)公开反对和消除性别微暴力的行为,在应对态度上更加积极主动,并且需要边缘群体广泛参与以形成合力,通过指出施动者的性别微暴力行为或带有性别偏见的制度、政策的不合理性来实现消除性别微暴力的目标[1]。此外,如前文所述,在达成关于消除性别微暴力的社会共识的情况下,社会主导性群体也有可能成为应对性别微暴力的合作者和支持者,因此,在赋权边缘群体积极应对性别微暴力的同时,还应该寻求更大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第三步,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根源于历史上和结构上男女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暴力行为的形式和表现各有不同,情景、背景、环境和关系也不尽相同”[39]。性别微暴力是性别暴力的组成部分,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也将无法根除。因此,实现性别平等是消除性别微暴力的根本途径,反过来,消除包括性别微暴力在内的性别暴力也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必经之路。
四、结语
性别微暴力根植于父权制和性别的暴力文化,代表的是不对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在暴力文化的合理性被内化的作用下,性别微暴力被视为“自然的”或者“可以接受的”,因此,其长期被掩盖在性别暴力行为的底层,一直处于“不可见”的状态。性别微暴力研究发现并将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歧视行为揭示出来,有助于性别微暴力的施动者和接受者清晰地认识到存在性别微暴力的社会现实,并且能够根据性别微暴力的类型特点对其进行准确识别和辨认,从而为消除性别微暴力奠定基础。
性别微暴力双向模糊的特性可能会带来双向伤害,施动者和接受者往往都会接收到性别微暴力的负面影响。让不同群体的人了解到性别微暴力的实质和危害,有助于建构关于消除性别微暴力的社会共识,这对于团结更多的人积极应对和防治性别微暴力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强调的是,对性别微暴力的研究并不是对性别暴力行为的割裂,也不是对传统意义上的性别暴力的忽视,而是挖掘更底层的性别暴力行为,使性别暴力研究不断深化,从而消除性别暴力,转变暴力文化,并最终实现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