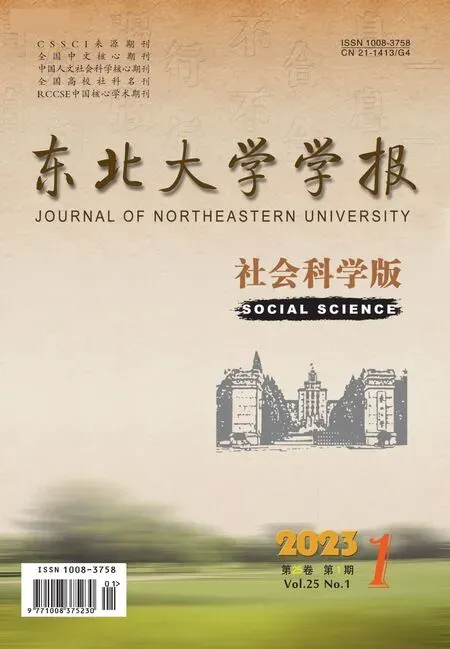亚里士多德论感觉的接受活动
赵 奇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DeAnima)(1)文中引用的《论灵魂》文本内容由本文作者译自Shields版本,参见Aristotle: De Anima, trans. Shield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详细论述了感觉能力,这是灵魂的基本能力之一。感觉能力在灵魂的能力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在《论灵魂》中讨论的篇幅最多。对感觉能力的具体分析应以明确其定义开始,但《论灵魂》第二卷第五章对感觉的定义不够完整,因为亚里士多德仅从感觉对象出发来规定感觉能力。因此,他在《论灵魂》第二卷第十二章对感觉的定义进一步补充,将感觉定义为感觉者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的形式,此定义规定了形式的重要性以及感觉活动的非质料特征。然而,该定义存在的疑难是即使一些无生命物也能够无质料地接受某物的形式,因而似乎不足以概括感觉活动的本质特征。事实上,这种定义是正确的,只不过范围较宽泛,需要对其加以澄清。本文首先在质形论的基本视域之下,论述感觉活动的接受性;其次,认为区分能力是感觉的具体发生方式,这种区分能力不同于判断能力;再次,从Bradshaw“双重逻各斯”的视角出发,基于感觉能力双重性的维度,将中间性视为感觉者与无质料对象形式的比例;最后,认为感觉接受能力的器官是大脑和心脏,两者保证感觉活动的热冷均衡,从而为感觉接受活动提供生理基础。
一、感觉活动的接受性: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
在《论灵魂》第二卷第五章至第六章,亚里士多德论证了感觉对象的优先性和感觉对象的分类方式[1]32-35。然而,感觉者并非对感觉对象的所有内容都进行感觉,而是对内容的选择性接受。在《论灵魂》第二卷第十二章,亚里士多德认为,所谓对感觉对象的感觉,其实是对形式的感觉,这不包含质料:“就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感觉能力而言,本质上是认为,感觉活动是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的形式”[1]47-48。这种定义适用于每种个别感觉:视觉对象、听觉对象、嗅觉对象、味觉对象和触觉对象的形式分别是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热冷干湿[1]35-47。不过,即使诸如颜色、声音等作为个别感觉对象的形式,但在具体的感觉活动中,仍能将其称之为感觉对象。一方面,虽然形式与质料性实体在存在上不同,但在数目上同一;另一方面,将质料性实体称之为感觉对象,只是就感觉者而言。就感觉来说,客观实存物不能作为感觉对象,只有感觉对象的形式方可作为真正的感觉对象。
无质料的感觉活动是必要的,感觉对象只有作为形式,感觉者方可辨别感觉对象及其活动。例如,当我们感觉某对象时,它包含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方面,如果我们仅从对象本身来感觉,就无法区分不同的感觉对象,因为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都存在于同一对象之中。若无法辨别感觉对象,就无法相应地辨别感觉活动。据此,Polansky归纳“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的意义:第一,感觉者不被质料性的对象施加作用,否则对象在实现过程中将进入感觉者之内;第二,感觉者无法接受感觉对象的质料成分[2]341。Polansky在此所强调的两点存在差异,前者表明感觉对象施加作用的行为,后者表明感觉者的主动行为,即不接受质料性成分。第二点应基于第一点,感觉对象对感觉者所施加的作用,是感觉者能否接受感觉对象的前提条件。亚里士多德通过“蜡块类比”的例子来论证这一点。如果指环压于蜡块上,蜡块仅仅接受其质料[1]47-48。
Polansky据此断言,印记与指环的相反性可印证两者不相关[2]342。遵循Polansky的论证路径,我们能够以蜡块类比感觉的发生机制:感觉对象与指环相类比,感觉者与蜡块相类比。当感觉对象作用于感觉者,类比于蜡块是无效的,因为蜡块无法接受与呈现指环的质料,感觉者也无法接受及呈现感觉对象的质料。即使感觉是无质料地接受形式,也不能脱离质料来感觉,而是以质料为基底——从潜在印记向现实印记的转变,所以“潜能—实现结构比作用—受作用模式更清楚地解释了在感觉灵魂中究竟发生了什么”[3]。
因此,我们不能否定质料的重要意义。Polansky所断言的观点“以相反性证明无关性”潜藏着关键疑难:即使印记与指环完全相反,也不意味着两者完全无关。一方面,这种相反性并非指印记与指环的形状无关,而是呈现为对称性关系,对称性关系并非无关;另一方面,虽然蜡块仅仅接受印记,但接受活动以质料为基础。印记自身不能按压蜡块,只有通过指环的质料方可实现;虽然蜡块无质料地接受指环印记,但以蜡块的质料性为前提。我们可类比证明质料对于感觉活动的必要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谈论任何事物作为‘拥有’,是作为可接受的质料,即存在的某物。例如铜有雕塑的形状,身体有疾病”[4]。若无铜则无雕塑;若无身体则无疾病。无论是对人造物还是生命体而言,形式与质料皆互为奠基:形式是质料性感觉对象的形式,质料是感觉对象形式的基底。若无质料,感觉对象就无法作用于感觉者;感觉者若要接受与呈现感觉对象形式,就不可作为纯粹的形式,而应为质料性的生命体。
至此,我们已经阐明感觉的模式,但仅以“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来定义感觉活动是否充分?例如,如果将有气味的无生命物a与b置于一处,b就会具有a的气味——b无质料地接受a的形式,却不能承认b可进行感觉活动,因为b是无生命物。虽然“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对于定义感觉能力不充分,却不表明此定义是错误的。接下来将遵循亚里士多德的思维路径,论证区分行为作为接受活动的本质。
二、区分行为: 作为感觉接受活动的具体方式
对于“接受定义”,我们已从感觉对象形式的视角论证分析。然而,感觉者如何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感觉者不仅被动地承受感觉对象,也主动地接受感觉对象。因此,“蜡块类比”并不完全恰当,蜡块只被动地承受指环的作用,进而留下印记,但不能主动地接受印记。
一般性的被动感觉行为并非解释接受能力的全部方案,否则就会像Slakey所说,走向同义反复的死胡同。在此以嗅觉为例:我们不能将嗅觉单纯地定义为感觉,因为嗅觉本身就是五感之一,如此定义嗅觉是同义反复[5]。在《论灵魂》第二卷第五章至第六章,感觉被定义为一种被动行为,亚里士多德对感觉的探讨都是从感觉对象入手。不过,第二卷第十二章的定义“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表明感觉活动的主动性。事实上,主动性相比于被动性更重要,植物和无生命的自然实体皆可受感觉对象的作用,但它们无感觉,这是由于无主动的接受能力之缘故。
如何定义主动的接受能力呢?感觉者并非承受感觉对象所施加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对内容的选择性接受。亚里士多德用to krinon表述这种接受能力,学术界关于to krinon的含义存在争议。亚里士多德说:“区分者就其不可分而言,它是在同一时间进行区分者,但就其可分而言,它同时使用了相同的点两次。”[1]55Hamlyn将to krinon译为“判断”[6],但Ebert不认同Hamlyn的译法,他认为to krinon不是判断。Ebert从to krinon的希腊语词源入手,认为这是对不同事物相似性及相异性的区分,虽然to krinon在希腊语中也有“判断”的含义,但在第三卷第二章这里,其含义是“区分”[7]。Hamlyn译本对to krinon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混淆,他将其译为“判断”或“区分”,但两者的含义存在本质差异。判断作为一种述谓结构,即“X是Y”或“X是X”此类事实判断,是思辨性上的理智活动;“区分”无需事实判断,只需感觉到对象之间的差异。以红与蓝为例,to krinon表明感觉者能够区分红色与蓝色,而非得出“红色非蓝色”的判断。秦典华和吴寿彭的《论灵魂》中译本分别将to krinon译为“辨别”[8]和“审辨”[9],两者皆为恰当的译法。
“区分”活动不存在正误之分,只是感觉到对象的差异。“区分”只表明主观动机,而非述谓结构的判断活动。感觉者主观动机伴随时间、地点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Ebert将to krinon表述为抉择能力[7]。“判断”与“区分”不同,它有正误之分,是一种“命题”。例如,当我们作出判断:“红色不是蓝色”或“红色是颜色”,这是述谓结构的命题,皆包含正误差异。一旦得出某种命题,此命题就不随着感觉者主观动机的变化而变化。Ebert从词源学的视角论述to krinon的含义,这种方案正确地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意图,若将to krinon定义为判断,就会混淆感觉与理性,因为判断行为基于理性能力。命题的存在包含其独特的必要性,但不契合于感觉活动。
Scaltsas仍质疑“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的充分性。对于这个定义,他否认这是完全意义上的定义方式[10]。至此,我们尚未彻底论证接受能力的实现方式——仍要说明感觉活动为何不会将质料变化包含于其自身之中。“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仅说明:在感觉过程中无生灭性的标准变化。据Ebert的看法,“接受”能力是区分的能力,但这只表明此能力存在之事实,却未进一步说明原因。若不能对此原因进行说明,就无法彻底理解感觉活动进程,进而造成感觉者与非感觉者无异。
三、比例意义上的中间性:作为感觉者与无质料形式的本质特征
“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这种定义太过宽泛,无生命物也能无质料地接受某物的形式,那么为何只有动物有感觉?究其缘故,就在于动物有中间性。植物不像动物具有感觉能力,就是因为缺少中间性:“它们缺乏中间性,也无承受对象形式的始基。恰恰相反,它们被质料施加作用”[1]48。感觉对象不是质料性的对象,而应作为形式,此形式是某种性质或比例,即中间性。这表明“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与中间性的本质关系,即中间性是感觉能力与感觉对象形式的基本性质。按照字面主义的看法,感觉者在感觉活动实现的过程中,在字面上类似于其感觉对象。这事实上是一种误解,感觉是一种非标准变化,而不是标准变化,所以不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此变化。无论是感觉能力的中间性,抑或是感觉对象的中间性,皆为某种比例:“感觉者是某种有广延之物,但感觉能力并非如此;感觉也不是广延,而是彼物的某种比例和潜能”[1]48。
Bradshaw以长笛为例论证此观点:长笛的和声不是其质料,而是长短音之间的比例,此比例应保持为“中间”[11]。通过这种长笛类比可知,感觉者及其感觉对象同样契合于和声式的比例关系,从而使感官、中介及感觉对象之间保持持续性。Bradshaw也强调,仅通过中间比例,不足以感觉不同程度的感觉对象。中间比例仅为潜在状态,它只能保证感觉者有感觉能力,不能保证该能力会实现,因此还需要包含波动比例[11]。比例因而是双重的:中间比例造成感觉的存在可能性,波动比例造成感觉的实现可能性。
关于Bradshaw的观点,我们首先应持有肯定态度:只有在双重比例的前提下,才能认为感觉者有可实现的感觉能力,否则动物将会与非动物无异。通过感觉活动的实现,感觉者潜能地类似于感觉对象自身之所是,但它不能变得与感觉对象完全等同。即使感觉对象的比例作用于感觉者,继而使感觉者类似于其感觉对象,却不表明两者比例相同,两者在现实中并不完全一致。Bradshaw全面论证此相似性:颜色的比例在于白与黑之间,当感觉对象比例作用于眼睛时,其比例不会直接进入到眼睛中,而是经过中介的调节作用,成为眼睛的专属比例。类似的情况还有嗅觉和味觉,其中嗅觉对象的比例处于甜与苦之间,嗅觉器官的比例处于干与湿之间[11]。
然而,应该对Bradshaw的观点予以补充:感觉活动中有感觉对象与感觉者比例相同的情况。不过,这是由于两者比例原本就等同,而非由感觉对象施加作用所造成。当声音比例作用于耳时,不会直接进入到耳中,而是经过听觉中介,成为听觉器官专属的比例,即尖锐与迟钝[1]37-41。类似的情况还有触觉,触觉对象的比例处于甜与苦之间,触觉器官的比例同样处于甜与苦之间[1]44-47。但器官比例不是由感觉对象所同化而来,而是恰好原本的比例一致。
Bradshaw认为,虽然亚里士多德并未述及双重比例,但这是其感觉理论的内在逻辑。之所以在文本中未明确提及,是因为双重比例作为“自明之理”,从而是“高度省略化的工作”[11]。对于Bradshaw的自我辩护,我们应该辩证看待:一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确未述及双重比例,只承认中间性。从忠于文本的视角来看,Bradshaw的“双重比例”是对《论灵魂》的过度解读。另一方面,从亚里士多德的论证逻辑上看,“双重比例”存在合理性,因为中间性不仅包含感觉者接受感觉对象形式的潜能,也包含接受感觉对象形式的现实。中间性不仅包含中间比例,也包含波动比例,这是一种隐性概念。Bradshaw将波动比例从中间比例中剥离出来,波动比例的确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不过,他应对其予以说明,而非直接从中间比例中分化得出,这样容易造成误解,使自身的看法遭到批判。
虽然Bradshaw以中间和波动的双重比例阐明感觉接受行为的具体方式,但这仍不充分。首先,Bradshaw将感觉者与感觉对象的比例理解为极端相反物之间的混合比例,但仍不能说明为何只有动物具备感觉行为。通过比例可恰当地阐明感觉对象,但对于理解感觉者的中间性远不够充分。其次,将感觉活动理解为极端相反物的比例,并未真正深入到感觉者的接受能力中。双重比例仅解释接受能力的具体状态,却未解释感觉者为何拥有这种接受能力的原因。双重比例的核心在于中间比例,它使感觉能力成为其本质之所是,若无中间比例,那么波动比例也将失去其前提条件。然而,为何只有动物具备中间性,非动物却没有中间性,从而不能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这需要在生理维度上保证,接下来将论证感觉活动的生理基础。
四、大脑与心脏:感觉接受活动的生理基础
关于《论灵魂》第二卷第十二章对感觉的定义——“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字面主义(literalism)和精神主义(spiritualism)持有不同的立场。虽然他们都赞同感觉者的感觉能力具有中间性,但对于中间性的具体实现方式,他们的看法截然不同。根据字面主义解释方案,感觉者通过中间能力观看颜色。不过,眼睛被红物染成红色,从而眼睛在字面意义上变红,此种立场的代表学者是Sorabji[12]。与之相反的是精神主义解释,此观点的代表学者是Burnyeat。在他看来,眼睛不会被染成红色,否则红色将进入眼中。我们的眼睛仅仅意识到红色,除此无任何变化产生[13]。
无论是字面主义还是精神主义,皆非恰当的解释方案,两种观点对感觉活动发生机制的理解都是片面的。Grasso对此问题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批判字面主义的合理性,认为字面主义解读方案忽视了感觉者固有的感觉能力:“若感官变为F,那么接受F的能力就会消失”[14]。这种观点正确认识到字面主义的致命缺陷,感觉者之所以可以始终持有感觉能力,是因为中间性为感觉能力所本质固有,它不会由于感觉对象过度施加作用而失去感觉能力。首先,据字面主义的解释方案,感觉者被其感觉对象所取代,自然也表明能力的中间性被感觉对象的比例所取代,如此所造成的恶劣后果是:一旦感觉到普遍对象,感觉者的中间性就会彻底失去其比例。显然这是荒唐的,否则感觉者会丧失其本质特征。其次,精神主义方案也不合理,虽然该方案强有力地批判了字面主义,但此观点过于极端。因此,既不能将感觉理解为质料性变化,也不能将感觉理解为纯粹意识。如果感觉者单纯意识到感觉对象,就无法对其区分,这种区分行为包含生理维度。若按照精神主义的阐释路径,亚里士多德的感觉理论除了历史考据价值之外,无任何其他价值可言。
然而,目前的问题在于,字面主义与精神主义是否只能作为完全错误的解释方案?两者是否具有融会贯通的可能性?根据Ducharme的观点,不可全盘否定字面主义和精神主义,他希望在重新审视字面主义和精神主义的视域之上,获得对“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的正确理解。据其看法,字面主义和精神主义具有兼容性,生理学解读并非字面主义者的独创见解,意向化解读也不仅作为精神主义者的独家理论[15]。学者们只片面地注意到字面主义与精神主义所存在的冲突,Ducharme却深刻地发现两种解读方案的兼容性。一方面,即使是Burnyeat这样的精神主义者,也应当承认:感觉者之所以能够具有意识能力,是因为它作为质料性的生命体。另一方面,字面主义不片面地述及质料变化。例如,眼睛接受视觉对象之形式,而非质料,这是由于颜色只是有颜色物之形式。由此可见,字面主义和精神主义具有融会贯通的可能性,它们皆有一定程度上的合理之处。
按照Ducharme的看法,字面主义可以“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对生理学和器官的强调,并理解感觉者潜在地是感觉对象现实之所是”[15];而精神主义可以“更好地理解感觉能力为何作为一种不同种类的变化,以及中介如何作为区分或辨别在起作用”[15]。Ducharme的论述非常恰当,他一方面注意到,字面主义的解读方案为感觉活动提供生理基础。另一方面,他深刻地认识到:精神主义的解读方案证明感觉是一种非标准意义上的变化,后者使感觉者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前者确保接受活动具有质料基础。不过,虽然字面主义和精神主义可以融会贯通,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皆有合理性,但皆不能为“感觉为何具有中间性的接受能力”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案,因为字面主义不能解释非标准变化,精神主义不能表明感觉的生理基础。在此基础上,Ducharme致力于综合字面主义和精神主义的合理之处,同时规避两者的疑难,认为感觉者感觉能力的中间性从大脑而来。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部分》中认为,大脑对于保证对立物的需求平衡十分关键:“所有的平衡都处于对立物的需求中,以便具有调和能力与中间性”[16]。Ducharme指出,动物在感觉时,外部环境会对其恒定加热,但在加热的过程中,却可保持温度守恒。这是因为动物的大脑能够调和极端相反物,它可以保持生命体的恒定状态,从而始终持有感觉能力,而植物之所以没有中间性,其原因在于它没有大脑[15]。这种解决方案非常富有创见性,Bradshaw只是描述“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的运作模式,却未阐释此种模式产生的内在机制。Ducharme从生理学角度确定了接受活动的原因——大脑作为生命体平衡的控制器,由此得以保持为中间性,从而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的形式。Grasso持有类似的看法,在他看来,无论在外部环境中将何种极端性作用于感觉者,它都能保持为“内环境均衡”的状态——感觉者自身不同极端程度相互对抗、相互抵消的“零矢量总和”[14]。例如,无论外界环境的热如何加热生命体,生命体都能通过大脑来防止自身过热,从而具备感觉能力。通过热冷之间的抵消活动,可以实现生命体的内环境均衡。之所以大脑作为对外界热度的控制器,是因为大脑是全身最冷的部分。Ducharme和Grasso精准地断言中间性的生理维度,心理学问题需以生理学问题为基础[14-15]。
然而,Ducharme和Grasso在注重大脑作为感觉者状态平衡“控制器”的同时,却忽视了心脏作为平衡控制器的必要性[14-15]。诚然,由于外部环境的不断加热,最冷状态的大脑可以维持感觉者的内在均衡。但外部环境不仅能够加热感觉者,也能够冷却感觉者。如果外在环境冷却感觉者,感觉者若要达到自身的内在平衡,应通过内在的热来抵消冷却活动。这种抵消活动由心脏来完成,正如Johansen所总结的看法,心脏与大脑正相反,它是全身之中最热的部分[17]204。通过心脏与大脑的共同协作,方可实现感觉者的内在均衡,从而使生命体具有感觉能力,并能够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事实上,通过五种感官所处的位置就可看出大脑与心脏作为控制器的必要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器官都处于大脑处,触觉器官位于心脏周围[17]204。五种感官的位置之所在,充分证明了大脑和心脏如何起到对极端相反物的调和作用,从而使感觉者持有“中间”能力。正是由于中间性的生理学基础,可证明为何植物没有中间性:植物没有心脏和大脑,从而无法使其自身达到内在平衡的恰当状态。若按照Bradshaw双重比例的解释方法,仍然无法说明为何植物没有感觉能力,因为植物也具有极端相反物之间的比例。所谓中间性,并不仅仅是指极端相反物的中间性,而且也是感觉者以心脏和大脑作为平衡控制器,从而达到的中间性。这种中间性是感觉者的调节能力,而非极端物混合而成的中间比例。因此,感觉能力中间性的获得与运用并非相反者的生灭运动,而是秉性的保存与完善。
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第二卷第十二章深入分析了感觉活动的具体运作模式。之所以动物具有感觉,而植物及无生命物没有感觉,是因为动物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的形式,而非接受感觉对象的全部,感觉者的感觉过程是一种非标准变化。感觉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而且这种接受活动也在主动的区分意义上,所以曹青云指出,“心理活动的原因机制不是物理线性的,而是外在的物理原因和内在的灵魂原因协同作用的双层结构”[18]。然而,感觉者如何实现其对感觉对象形式的无质料接受,仍存在着巨大疑难。这种接受能力不是判断行为,而是区分行为。这种区分行为介于感觉者及其感觉对象之间,而感觉者的感觉能力与感觉对象形式皆以中间性作为其本质特征。感觉能力中间性的比例奠基于生理学的维度之上,即由心脏和大脑协作实现感觉者的内在均衡,从而得以具备中间性的感觉能力。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感觉是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但形式与质料在定义上不可分割,这是“无质料地接受感觉对象形式”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