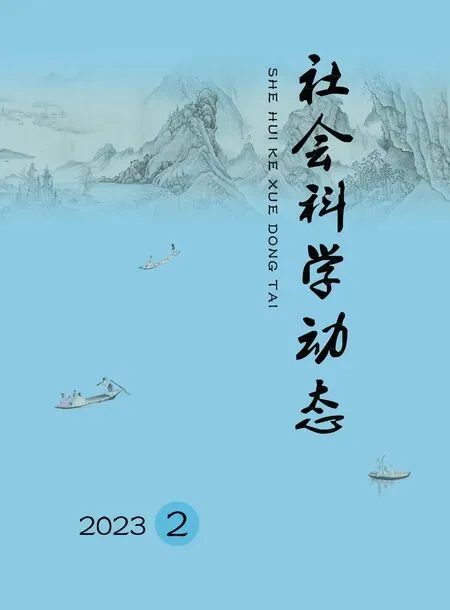内丘神码信俗实践与女性情感世界展现
赵帅鹏 李振鹏
内丘神码作为一种民俗产品或民俗消费品,属于中国传统年画中的一种门类。2006 年,内丘神码入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今已成为冀南区域型的文化现象。作为冀南民间信仰体系的典型文化事象,内丘神码长期以来受到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美学等诸多学科的重视,且多基于表象化的图像内容。从各自学科视域与方法着手研究,既有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围绕神码图像的内容进行艺术赏析①;二是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角度探讨内丘神码的当代传承问题与路径②;三是在宗教民俗学视域下透视民俗实践的生成机制③。现有成果对内丘神码信俗实践主体——女性行动者的相关研究关注较少。
从当前女性民俗学研究来看,一般集中在民间宗教信仰视域探讨作为实践主体的女性“因何参加”④“如何参加”⑤“影响效果”⑥等三个层面予以讨论,将宗教信仰与女性实践者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耦合思考,但此类朝山进香的宗教信仰均表现为“长周期性”的特点,不具备日常生活化特征,无法形成和展现女性较为完整的情感世界。同时这些研究不曾引入身体民俗学的视角,思考女性如何在具体的身体实践中完成自我性别意识和身份认同的建构,使得该研究领域存在拓宽的空间与可能。
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选择以河北省邢台市东望村内丘神码信俗实践主体——女性行动者为研究对象,从其信俗实践出发,聚焦于活动仪式过程、女性主体实践和想象性空间建构,探讨内丘神码何以形成唯有女性群体参与的民俗特征,进而揭晓和展现隐秘其中的女性情感世界,这对传承内丘神码信俗与丰富现代民俗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符号与图像:内丘神码信俗的内容与意义生产
内丘神码(以下简称“神码”)是被表征为民间宗教信仰的民俗事象,人们通过将各类神像或具象或抽象地描摹在纸上,形成初始意义的图像系统,并以庭院作为信俗活动场域,将神码张贴在家宅四壁,成为活动“道场”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与此同时,这些图像被编码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升格为民间宗教的崇拜对象,并通过现实生活化演绎,逐渐形成地方性的日常民俗信仰。
一方面,神码图像的生成具有深刻的现实导向特点。中国曾在很长时期内是传统农业社会,随着历史的发展更迭,民间逐渐建构出一套系统性的乡土文化生产机制。神码同样经过这一机制的生产浸润,使得现实情境的“众生相”投射成为宗教世界中的“众神像”。神码系统主要神祗由天地、灶王、南海观音、名仪、老母、财神、车神、仓神等神灵组成。“天地神”以其在农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神码系统的主位,它寄托了农耕社会生产主体对于土地的特殊情结,以及对操控雨水的上天的敬畏之情,进而形成“天地神”的特殊地位。“南海观音大士”作为佛教神,其神祇职能在于回应信众祈求平安的心理愿望,因而配享在与“天地神”遥相呼应的南面影壁墙内,同样体现出较高的殊荣。 “灶王爷”位居厨房,是联结人间和上天的中介,配享也很丰富,但待遇稍次于主位的“天地神”。“老母”张贴于西屋或卧室里屋,同“灶王”和“天地神”一样,拥有完整的供案,体现出其由民间创造出的贴近世俗的救世主地位。⑦“财神”一般摆放在东或西厢房里,配享规模也较大。同时,散落在庭院各处的小神码,将依据自身的神祇特性得到相应的安放,如贴在水井上的“井神”和落在梯子上的“梯神”等。从神码的位置摆放不难发现,大神码由天地神、南海大士、财神、灶王和老母等构成,小神码则是现实生活中由“物”升华形成的人格化的神。神码的众神形象,多源于“自然崇拜、儒道释信仰和著名历史人物”⑧,一定意义上具有中国本土宗教泛神论的倾向。神码图像并无恒定的系统,因此表现出弥散型的特征。图像内容来源于生产生活的实践。人们动态地进行图像制造、无限地丰富图像内容,进而满足信俗实践的客观需要。可以说,神码信俗“作为一种强化仪式,具有强化生产活动的安全性和满意度、刺激生产力的功能”⑨,与现实社会生活以互动形式构成双向意义,其想象、制造与成型借此烙印上深刻的现实生产生活的内容意涵。
另一方面,神码信俗实践遵循日常化的周期规律。借助列斐福尔“日常生活”理论⑩可以发现,社会生活在时空关系中得以存在,同时也由这种关系的互动而被建构。神码信俗的开展通常以“天”作为周期,强调日常化的实践周期。信众通过每天晚饭后时间的祭祀,完成崇拜神码的信俗要求。这种基于日常时间建构其神性的民俗事象,所散发出的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正是源于日常的仪式时空媒介。换言之,神码信俗以日常作为时间单位,不仅蕴藉着深厚的内涵,同时也赋予时间以深刻的人文价值。神码信俗所营造的时空状态中,原本毫无意义的物理时间,经过神码信俗实践活动的参与而增添了文化属性,变成一种人为结构化的“社会时间”。神码可谓形象化时间的必要参照物,其周期性的重复展演并非毫无意义,而是由此具备了丰富的信俗意涵。
与此同时,女性化参与的行为也盘活了神码信俗意义生产机制。意义必须借助于符号才能表达,神像群像既是一种图像内容,也是一种富含意指的符号。⑪神码信俗的文化特质不在于表面的图像内容,而是其思想精神深处的象征意味,即支撑内丘神码成为信仰力量来源的意义系统。在邢台市东望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进行关于神码崇拜的信俗活动,实践主体也多为女性。传统的意识形态认为,女性的专属领域为家庭空间,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则为男性的特权,社会性别文化结构性地影响着女性身心的发展。作为当地民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所生发出的文化事象,神码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变为一种宗教化的民俗事象,成为农耕社会中人们祈福免灾的心理期盼对象。⑫神码不是简单意义上对日常生产生活的描摹,实践主体的女性也并非将其视作审美意味的艺术产品进行欣赏,而是从心理需要出发,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寄托于神码信俗的实践之中。学者赵世瑜认为,中国传统妇女的闲暇娱乐活动往往都与一些宗教性的活动有关,女性参加娱乐活动与投身宗教活动往往具有被动选择的特征,并与其寻求心理需要的动机相符合⑬。基于性别和心理等原因,女性践行神码信俗的动机和行为构成神码意义生产的机制。经历意义生产机制的升华再造,神码不再仅仅是物质性的神码,更是拥有神性灵验功能的神,女性行动者对神码的供奉实践所达成的两者关系的建立,体现出女性自我的物理时空朝向情感空间的转变。
在普遍意义上,神码与其他地区的民间纸马一样,都存在从日常生活拾取建构文化特质的材料内容和表现为民间宗教信仰形式的特征。但不同之处,内丘神码蕴含着相对更为深刻的日常生活色彩和鲜明的单一性别化的实践主体。
二、空间与身体:内丘神码信俗的实践媒介
场景原指用于叙述戏剧和影视表演中时间、空间和人物关系所构成的具体场面。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如今场景已由单纯的空间转为描述人与周围景物的关系的总和⑭。神码信俗活动的展开主要由作为行动者的女性和担当空间载体的庭院进行要素的组合,并按照日常生活的节奏,通过一系列仪式完成信俗活动的祭祀要求。
庭院空间承载神码信俗活动的展演,其张贴布局制造出信仰的空间形态。神码的不同神祇内涵表征相应的配享、在庭院中占据对应的座次,表现出一定的等级制倾向,同时与冀南传统院落形制契合。中国北方的传统四合院一般坐北朝南,故而神码张贴也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北墙壁上张贴“天地神”,前方摆放天地桌,天地桌底下是“土神”。侧面南墙的面窑里贴“南海大士”。影壁墙正面是“镇宅神”,直面家门;穿过甬道,家门两侧的墙底部张贴“四路路神”,保护出入平安。“灶王”张贴在厨房墙壁。“老母”“财神”在西屋墙壁。此外,东、西、北墙外墙壁均会预留出一段深凹空间,以张贴“窗神”。其他小神,譬如“井神”会被张贴于井上,“仓官”主管粮仓,被张贴于存放粮食的屋中。还有张贴在梯子上的“梯神”,鸡窝边的“鸡神”,等等。除主要神祇配享固定的位置外,其他小神祇多依附于具体的现实载体,多样化的神祇共同构成系统性的神码体系。这种根据一定规则将神码张贴于庭院的处理方式,是神码信俗实践的前提准备,即初始的信俗空间布置。神码在庭院摆放的空间格局并非人们无意识的结果,而是人类活动广泛介入且富有社会文化内涵的空间建构。其错落有致、泾渭分明的特征,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社会等级制的映照,进而形成神码摆放时需要遵循的隐性规则。这种神码张贴规则,使得庭院成了一个以神佛图像为主干骨架搭建起来的神圣空间架构。
家庭场域的庭院不仅是显而易见的、可以勾勒出来的实体性质的空间,还是一个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在人类活动介入之后,其原初的自然性被披上了文化外衣。在显性层面,家庭场域提供的是庭院实体空间,用以盛放各种神码,构成活动开展的场域。而隐性层面是依托实体空间呈现出的性别文化内涵,即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活动范围被限制在“家”的空间⑮。受制于传统社会性别分工的结构,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寻求自我的超脱多寄托在家庭空间之中,神码祭祀活动此刻不再是民俗事象的集合,而化身为女性展开情感想象的媒介和路径。依托于家庭场域的实践,不是机械性的身体参与,其背后烙印着深刻的性别文化特征。女性民俗实践者将家庭场域同想象的社会空间进行联动结合,制造出现实和想象互为一体的空间形态,而想象的载体则依托于身体实践所创造的意识内容。
从身体参与的仪式过程来看,作为一项类似于宗教性质的信俗习惯,在祭祀神码过程中女性实践者通过烧香、跪拜、念香词等动作完成仪式要求的行为,充分体现了身体民俗学“与身体有关、主客体双方的身体应用与身体经验、身体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与学术史等”⑯理论设想,并通过身体实践完成情绪表达与情感想象。具体而言,神码实践周期为一天,即日常化的朝拜,一般在晚饭后的时间段进行,距离从内到外,祭祀对象从天地神到路神,仪式过程大致沿着这一路径进行。正如内丘神码非遗传承人所介绍的:
“不同的神供的方式不一样。像天地和财神这种大神码,摆供的时候就得多摆,供奉时上香磕头,烧三炷香,拜三下,磕一个头。剩下那些小神码就上一炷香,不用摆贡品,也不用磕头。家里要是有老太太,她们一边上供一边念叨,现在年轻人都不念叨了。”⑰
信众在践行宗教信仰仪式时往往会携带一个蒲垫,面对大神码时行跪拜,具体步骤为先放下蒲垫,将香点燃后并手持于面前,双眼微闭,口念进香词。词的内容一般是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可望不可得的一些愿望和诉求,或关于家庭、国家和自身。通过朝向神明祈求,满足暂时性的精神需求。在念完进香词后,像鞠躬一样拜三下,再跪在蒲垫上行一个叩首,最后起身拿起铺垫去下一个神明面前。朝拜顺序没有仪式上的讲究,基本上按照方便的原则进行。梯神、井神和车神没有案桌,所以不做仪式上的供奉。窗神、镇宅神、路神等虽然只是小神码,但也有香炉的配享,所以要烧香。进香词不做要求,可放声也可选择沉默,跪拜同样具有可选择性。烧香、跪拜、念词等带有可复制性特点的连贯动作,作用于感官层面则具体表现为视觉、听觉、触觉三种体验形式。视觉体验意为面对神码图像时,大脑会将图像内容呈现在大脑中枢并形成视觉刺激;在口念拜香词时,耳朵会接受相关信息获得听觉体验;在烧香和跪拜时,双手和双腿也会经历触觉体验并反馈至中枢神经。这些具体的感性体验凝聚于身体实践基础之上的感受,为具体经验的生成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最终一套女性化的“体知”经验系统便由此走完建构之路。
实践作为人的对象性的活动,旨在通过实践的媒介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将真实的自然变为人化自然。神码信俗赖以支撑的图像系统是长时间农事实践的产物,人们将具象化的客观世界通过自我的想象编码成神码图像,在某种意义上彰显出改造自然的初始观念和行为实践。神码图像与女性信众之间的区隔通过实践的媒介尝试弥补,两者互动过程逐渐生成神码信仰机制。如此这般,女性成功将实践视野聚焦于“现实生活”,把追求“此岸世界的真理”视为“实践的任务”。⑱同时值得思考的是,实践作为主体的人所发起的活动,有效连接了实践者和被实践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实践的承载者毋庸置疑是人,人的意识推动实践的展开,实践反作用于意识的形成。然而真正承接实践的则是实在的身体,作为民俗实践的表现形式和民俗传承媒介,构成女性信俗实践者与神码图像之间的“双向凝视”。⑲女性以实践主体的身份在庭院中参与神码信俗展演,此时庭院充当的空间角色和女性扮演的实践主体深刻演绎了场景的动态形成,绘就一幅鲜活的神码信仰实践的场景。由此,庭院景观的形塑并不是神码图像的简单集合,而是女性想象性的社会关系,通过神码与庭院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此外,神码信俗流布地区的信众将家庭空间布置成宗教道场的方式,推动生活化的家庭和宗教化的道场彼此耦合,神码信仰就此区别于神圣化的朝山进香,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叙事的信俗。
三、性别与认同:女性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生成
性别概念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最早应用在人类学关于社会性别结构的研究中。立足于性别结构的解释视野,性别被定义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结合的二元结构。生理性别又被称作生物性别,是先天所决定的,即男女在身体结构上的差异;而社会性别是社会、历史与政治对两性认同建构起来的意义指向,是人们后天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被文化影响而结构化的概念。长久以来,性别认同的产生机制被归因到先天生理的差异,直至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后天社会文化建构性别文化”的观点才有所改变。⑳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女性主义以一种研究范式被引入学术界,试图通过理论的发现、建构和完善女性参与的民俗学研究,寻求在现实环境中女性的自我解放。民俗学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相同,女性视角长期被遮蔽在“男性视角”之下,处于衬托男性存在和主导的社会形态的“他者”地位,缺乏女性自身主体性的呈现。但女性不应处于被凝视的地位,在研究中更不能以男性视角解读和理解女性实践本身,而是强调从女性自身的立场去理解女性的感受与经历及主体性表达。㉑
在我国,“群体烧香念佛对于妇女来说具有世俗生活与宗教安抚的双重意义,进香和赶庙会成为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她们参与热情往往如痴如狂”㉒。女性作为神码实践主体,全程参与仪式。在谈起为何矢志不渝、日复一日参与到神码祭祀活动时,信众赵某谈到:“
拜码字子图个乐,你想啊,咱跟汉们不一样儿,没法去村儿哩街上转悠,聚一堆儿说话啥了。要么去别人家串门,坐下来说说话儿,那样也聚不齐多少人,就俩仨说说话行咯。到黑了拜码子时了,都是最得劲儿。总感觉是在和人说话,而且还是神人,觉着还挺自豪咧。”㉓
女性参与民间信仰活动是社会性别文化选择的行为,并非主动性的选择,抑或是在被动之下的部分主动性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这些女性放弃朝外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念想后,转而朝内以崇拜神码图像的祭祀实践安放身心,同时萌发了女性性别意识并形成有关心理认同。
神码以“客体”身份的出现并满足女性主体的情感需要。东望村女性实践者在具体活动中,不再将神码视为简单化的图像,而是支撑、表达和呈现女性情感世界的符号象征,承担了学者温尼科特所指的“过渡性客体”的功能,即实践的目标就是体验过程,实践中朝向的对象“为那些不断将外在现实和内在现实既区分又联系起来的个体提供了一个小憩之所”,帮助我们保持精神和心灵的健康。㉔同理,女性在庭院场域中进行祭祀活动时,神码图像作为拜香的对象,自然地成为信众心目中的“过渡性客体”,她们将自身的诉求、欲望投射在举头三尺的神明上,以期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社会性别差异建构了一整套区别男女生理差异的社会文化制度以及习俗惯例,同时这些习俗惯例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构成一种强大的话语力量,规范着女性的社会行为与思想情感。㉕传统农业社会里,性别界限分明的外在现实将女性蜷缩在一方天地之中,遭受到现实与想象的极大不平衡,失语的状态使她们迫切追求内在情感世界的解放。因此神码在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秩序里,以“休憩之所”的形式提供给女性一种平衡这种失语状态的价值、秩序和难得的心安。
在神码信俗实践中,对女性神像的崇拜更深入地激发和形成女性性别认同意识。“认同”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表达承认、认可、赞同。㉖神码信众的认同当以第一种解释为宜,即基于共同之处的心理认同。日常生活化的神码祭祀活动,使女性增加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情感所依,民俗事象不断融入日常生活叙事当中,形成女性实践者独具特色的生命体验。作为女性神明,“南海大士”神龛与其他众神码存在较大差异。如,其他神码直接贴在墙上,像前摆放香炉,此外并无鲜明特点。然而“南海大士”是被摆放在影壁墙深凹进去的地方。冀南传统民居格局中,从家门进去会经过一小段甬道,迎面可见一堵影壁墙,然后往左或者往右进入庭院。影壁墙一侧和南墙相连,另一侧深入庭院。深入庭院的这一侧,通常会在中间地方凿开一个长方小洞,里面贴上“南海大士”神像,并摆放香炉,这样关于“南海大士”的配享形制就已初具形态。从外在形制看,“南海大士”所处位置刚好是一块平整表面中凹陷的地方。依托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身体构造,“南海大士”所处的凹陷小洞符合女性身体结构特点,同时也适应于学者拉康“镜像理论”㉗的分析法则。由于“南海大士”和女性实践者在性别属性上相同,故而“南海大士”作为一个客体存在,很容易被女性信众视作理想化的自我。参拜神码时,“南海大士”成了女性实践者的性别认同对象。性别一致,但又客观存在着能力、地位的云泥之别,因此“南海大士”被女性视为仰视的客体。信众通过将“南海大士”配享形制做出“理想化自我”的改变,以此作为自我抒怀的载体,实现情感诉求表达。可以说,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都可在“南海大士”这个符号的象征意义中寻求满足。换言之,女性将诉求寄托在对“南海大士”想象上,试图借助一种超经验方式改写既定的社会规则,重新建构起适用于自我的规范,最终变现愿望。而寻求身心解放的过程,也成为萌发性别意识和推动性别认同的途径。
如果说个体或群体通过日常生活实践重构和维系个人认同、群体认同、文化认同,那么,女性对自我的性别认同则源于日常化的神码信俗实践所生成的经验。当女性无法充分朝外在社会场域中寻求认同和理解,更无法实现同男性一样的自我价值,她们就转而朝内,在家庭空间中寻求身心解放,神码图像为此提供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机会,使女性能够触碰到改变的可能,“破圈”前景俨然在眼前。“南海大士”所体现的母性、慈悲和普遍关怀的意涵㉘,便被女性投以巨大热情进行崇拜,并将此作为自己权力的印证。事实上,不仅“南海大士”具有此种功能,其他神码亦是如此。作为一种身体实践的活动,神码信俗使久处家庭空间中的女性得以进入到与神灵交流的互动过程,虽然这些是想象性的结果,但却与其现实境遇息息相关。在女性自我意识生成的意义上,神码信俗实践重构了一套权力想象模式,开拓了女性身心舒展的阈限。因为,神码信仰女性实践者所希冀的完美人生,正是对现实不完美人生的补偿,其自我性别意识也在持续想象中露出端倪。
四、身份与濡化:女性实践主体的独特生命历程
性别的生物属性只是提供了一具可供行走的躯壳,社会文化则创造了性别应具备的社会属性,集中表现在性别角色身份的内容和意义,并围绕家庭内外而形成了井然有序的性别空间。在性别分工更为明确的乡村,冀南东望村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产机制影响着男女成员的日常行为规范,男性成员广泛进入社会空间中并参与社会性劳动,家庭劳动则由女性成员承担。生产生活模式的固化造成女性极大的思维惯性,无论认同或是反对,家庭场域都成为其身心活动的主要空间,家庭身份也借此展开形塑。神码信俗实践在激发女性性别意识后,更推动女性角色身份多重面向的可能。从被动的角色期待到主动的角色表现,女性的自我身份濡化是延续整个生命长度的动态过程,同时从侧面彰显了作为行动者的女性的独特生命体验。
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男女之间的关系是“阿波罗式”的。所谓男女有别,是男女求同存异,并不排斥差别,而是生活上进行隔离。这种隔离不但有形,而且还表现在心理上。男女只有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而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㉙。因此,“男耕女织”模式下的生活分工,逐渐扩大了原初生物性别差异性,进而形成社会意义的性别差异。在传统思维和行为惯性下,当今农村依然残存着男女有别的旧观念,必然导致女性尤其是年长妇女缺乏朝外精神表达和寻求认同的主观能动性,只能被迫地向内通过神码的信仰活动完成欲望宣泄,家庭身份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在家庭场域中被“制造”成型。同时,女性家庭身份或角色建构还受到“中国传统儒家宗法伦理”和现代性观念中家庭被视为“女性特质归属地”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影响。㉚对女性性别角色身份的期待展现为女儿、妻子、母亲等多重形象。这种身份的内涵、意义与构建时常萦绕在女性群体话题中,集中体现为“怎样才算是一个好女人,以及作为一个好女儿、好媳妇、好妻子和好母亲,应该如何得体地处理和家庭成员的关系。无论是好女儿、好妻子、好媳妇和好母亲等身份”㉛,女性身份建构的前提多是立足于家庭成员的利益需要,并为之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期调和各成员之间的不同欲求,实现家庭关系的和谐美满。但集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必然以部分成员利益的损耗作为代价,女性受到不容忽视的、性别的家庭因素影响,在与家庭成员各种互动中,通过建构不同的身份属性完成和不同家庭成员的匹配,使家庭真正成为“家庭”。家庭职责既然成为女性这一性别身份所推脱不了的角色期待,那么如何完美履行这一职责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现实生活中尽力完成相夫教子等家务活动,神码象征的超经验所期许的功能,就成为女性为家庭成员祈福的不二之选。因此,在具体念词环节,女性实践者除了盼望自我顺心如意外,更多的还有为家庭其他成员祈福,其对象可能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内容多表征为身体健康、情感顺利、事业有成等方面,根据对象和境遇的不同形式展开各异的祈求。可以说,女性行动者通过神码实践,用身体感知和无意识的惯性行为回应家庭成员对女性作为家庭一员的性别角色期待。
神码信俗实践成为女性性别角色身份表现的媒介内容。学者李琳通过对南岳朝香群体的考察,发现南岳进香群众以女性为主体,活动目的在于缓解自身的精神压力,提供一种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在家庭和自我、物质生活和精神超脱等多种相对的空间中寻求一种平衡。㉜在由男性主导的话语系统限制之下,女性在民俗思想和行为上建构了自我和同性之间的身份认同,家庭之中的性别身份通过神码实践进行代际传承与谱系联结。活动时,主持者和实践者复合一体,一般由家庭女性成员中具有行动能力的年长者承担,这一责任自然落到了祖母这一辈人身上。待祖母丧失行动能力或去世,实践责任便顺延到家庭第二代女性(儿媳/妻子)肩上,日复一日参与其中,直至老去那一天。其后接力棒传给第三代女性(女儿/孙女),接续这一习俗的代际传承。同乡土社会四季更替的生产生活内容一样,以庭院祭祀为中心的神码信俗实践活动也循环往复、不曾间断。但也有例外,即如果家中缺乏女性成员,那么神码信俗也可能丧失了实践条件。神码祭祀围绕着女性展开的代际传承,充分呈现出“女性谱系”特征。这一概念指基于血缘上的女性关系,在母亲这边女性有她们的母亲、外婆、曾外婆以及女儿。通常来讲,母女之间和谐关系延伸至整个女性群体中,能够为女性创造一个爱的空间。女性能够通过女性谱系确保自己的身份,以及找到被男权文化遮蔽的女性历史。㉝一定层面上,村中女性群体的情感和生命的谱系联结依靠神码祭祀活动完成。每一代的女性实践者,因循相同的实践路径,进行相似的实践内容,不断衍生出相似的生命历程和人生经验,使得每一代人的个体欲望和精神诉求,不断融没在名为神码信仰的日常叙事之中。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相同身份的制造正如威利斯提出的“文化生产”理论,作为能动者的个人“在理解自身生存环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持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㉞,一代又一代的女性主动或被动地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中接受神码信俗实践内容对自我思想和行为习惯的建构,在“濡化”作用下势必也成为下一代女性逐渐产生认同的“惯习”。每一种由家庭延伸的身份都表征着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女性性别身份和家庭身份的身份内涵,就包含在女性群体代际传承的生命经验之内,并以“文化生产”的形式实现女性家庭身份和性别身份的不断复制和重现。
五、祛魅与再生:女性情感世界的展现机制
情感并非指代情绪这种单纯的心理现象,而是身心,如喜悦和悲伤能够揭示整个有机体的生命现状,情感表达了身体的某种状态,以及某种思维方式。㉟我们探讨实践神码信俗女性的情感世界,需要关注她们的身体对外界变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变化,即表现在心灵、思考、想法集合而成的观念系统。如前论述,女性参与神码信俗实践活动的行为呈现出身体的反应,而建构在实践经验上的性别意识和家庭身份等则是其思想上的变化。场景实践、性别认同、身份建构三个环节彼此交融又衍生出专属于女性信俗实践者的情感世界,离开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这一机制的完整性都有可能被削弱或消解。
女性情感世界的展现机制很大程度上是在父权制结构性压迫下的被动生成。传统父权制思维深刻影响着乡土社会心理结构,女性受社会文化对性别文化建构的影响,并习惯性地将自身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场域。然而有限的空间势必难以承载自我价值的全部实现,大量的田野民族志材料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往往更倾向于将自身的精神诉求投射到神灵宗教世界。诞生于乡土社会的内丘神码民间信仰,自然就成为冀南乡村女性广泛参与的信俗活动,作为行动者的女性试图通过神码崇拜建构起一套专属于自我的精神世界以盛放丰富多彩的情感。这一想象性的空间仿佛现实世界中的世外桃源,将女性实践者推到一个区别于世俗生活的彼岸世界,给予她们超现实的神秘体验,并以此获得身心“解放”。
女性行动者依托神码信俗实践而生成的情感世界,需要放置在特有的文化生态和相关的社会现实条件中才能展现其“价值”。女性性别认同和身份建构很大程度上不是主动性的选择结果,而是“女性对于自己身体和性的控制权的异化和丧失”㊱的一种被动接受。这种基于“他者”认同而形塑“自我”认同的方式,逐渐从依靠父权、神权的参照体系滑向作为行动者的女性自我意识上,具体表现在曾作为满足心灵抚慰和自我价值实现需要的媒介——神码,东望村女性实践主体对其代际传承现已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如今参与神码信仰主要为50 岁左右及以上的女性群体,其中70 岁以上者为主体。一方面是社会治理过程中“智力下乡”后“祛魅”程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城乡巨大差距导致乡村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失去乡土文化生态的神码无法在城市空间中立足。依然参与信俗活动的只剩下留守乡村的高龄群体,中间年龄群体尚有一些,低幼年龄群体已经缺乏接续继承的语境。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各种破除迷信的运动,以及改造社会性别结构的尝试,男女有别的传统经济形态和价值观念都在逐渐消解,关于神码庭院拜香的信俗正悄无声息地淡出民众的视野,而成为一段历史记忆。
将美好生活的向往单纯寄托于宗教性质的实践活动的行为,显然并不能带来现世生活的实质性改观。但无论基于何种层面所诱发的民间信仰实践,都具有共同的“敬神祈福”的意义指涉,也符合社会心理学的普遍共识,即女性相较于男性拥有更强的悲悯情怀,行为处事也符合文化建构性别的要求多了一份感性色彩。这也使得神码信俗不同于制度性宗教,而是已内化成当地女性情感世界中的信仰风俗意义上的思想行为习惯。如今,借助神码信俗实践实现“自主的情感个体”㊲正成为过去。当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到更广阔场域的社会分工,这无疑有助于女性群体摆脱家庭桎梏,走向广阔天地,也无形中获得了更多抒怀的机会,神码于女性而言的情感工具性质的功能也就适时的消退了。但随着一代一代人逝去,文化却仍然流淌潜藏于人们的物质精神活动而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如何正确对待表征为民俗信仰的内丘神码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常生活化的活态传承,是继续自然演绎民间的偶像崇拜?还是另作艺术价值层面遗产的审美之用?这依然是值得学界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⑫ 刘高平:《内丘神码的造型艺术探析》,《邢台学院学报》2014 年第2 期。
② 陈辉、黄君辉:《内丘神码艺术的当代阐述及其传承发展》,《美术观察》2017 年第12 期。
③ 参见耿涵:《弥散信仰与线性传统——从内丘神码看民间信仰的图像表达》,《当代社会中的传统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年版;姜彦文:《供奉,还是焚化——内丘神码的祭祀方式及其成因小考》,《长江文明》2013第4 期。
④ 漆凌云、严曼华:《敬神祈福、家庭职责与自我抒怀——河底江村女性拜香客精神世界研究》,《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2 期。
⑤ 华智亚:《人生仪礼、家庭义务与朝山进香——冀中南地区苍岩山进香习俗研究》,《民俗研究》2016 年第1 期。
⑥ 王均霞:《作为行动者的泰山进香女性》,《民俗研究》2009 年第3 期。
⑦ 孔庆茂:《民间宗教的创世女神——无生老母》,《文史知识》2008 年第3 期。
⑧ 鞠高雅:《神圣与解构:从内丘神码论原始文化艺术表达中的模糊性问题》,《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0 年第6 期。
⑨ [英]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年版,第226 页。
⑩ H. Lelebvre,C. Levich (trans),The Everyday and Everydaness,Yale French Studies,1987,pp.7-11.
⑪ 赵毅衡:《重新定义符号与符号学》,《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 期。
⑬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286 页。
⑭ 许晓婷:《场景理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连接变革》,《今传媒》2016 年第8 期。
⑮ 叶荫茵:《苗绣商品化视域下苗族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重塑——基于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的个案研究》,《民俗研究》2017年第3 期。
⑯ 王霄冰、禤颖:《身体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文化遗产》2019 年第2 期。
⑰ 耿涵:《内丘神码传承人魏进军口述史》,《民族艺术》2015 年第5 期。
⑱ 岳天明、张成恩:《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的中国化推进》,《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
⑲ 冯智明:《“凝视”他者与女性身体展演——以广西龙胜瑶族“六月六”晒衣节为中心》,《民族艺术》2018 年第1 期。
⑳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版,第2 页。
㉑ 陈秋、苏日娜:《女性民俗研究发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4 期。
㉒ 李媛:《16 至18 世纪中国社会下层女性宗教活动探析》,《求是学刊》2006 年第2 期。
㉓ 访谈对象:赵某,女,75 岁;访谈时间:2022 年2 月22 日;访谈地点:赵某家中。
㉔ 陶东风:《粉丝文化读本》,贺玉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155 页。
㉕ 刘晓春:《民俗与社会性别认同——以传统汉人社会为对象》,《思想战线》2005 年第2 期。
㉖ 李素华:《对认同概念的理论述评》,《兰州学刊》2005年第4 期。
㉗ [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版,第94 页。
㉘ 葛希芝、陈建、王文娟:《民间意识形态:女人与男人》,《民俗研究》2022 年第3 期。
㉙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45 页。
㉚ 鞠熙:《游观入道:作为自我修行的女性朝山——以明清碧霞元君信仰为例》,《民俗研究》2020 年第4 期。
㉛ 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75—76 页。
㉜ 李琳:《南岳朝香与当代女性宗教信仰调查与思考》,《民俗研究》2015 年第6 期。
㉝ Luce Irigrary,Body Against Body,In Relation to The Mother,Sexes and Genealogies,1993,pp.7-21.
㉞ [英]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文版前言,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 年版,第2 页。
㉟ M. Hardt,A. Negri,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New York:Penguin,2004,p.108.
㊱ 宋少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妇女——为什么中国需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批判》,《开放时代》2012 年第12 期。
㊲ 朱宇晶:《表征性父权:传统、女性策略与父权再生产》,《民俗研究》2017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