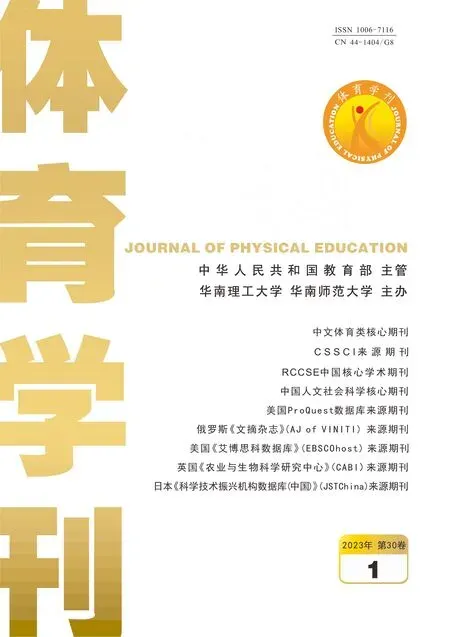“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
岳涛,戴国斌,苑城睿
(1.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学院(含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8;2.恒源祥(集团)有限公司 博士后工作站,上海 200021;3.黄冈师范学院 教育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1 “止戈为武”的训诂公案及尚存问题
“止戈为武”的训诂之争一直是学术界一段公案[1],在这段公案中“武”作何理解影响到人们对于武事本质的看法,也进而影响到人们对于“武德”的认知和判断。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夫文,止戈为武”典故之后,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正式将其作为会意字代表,从造字逻辑上确立“止戈为武”的意义生成。然而清代以来,有学者对此提出新见,如俞樾,以武字“从止”如“舞字之从‘舛’”“从戈”如“持干戚”,而训“武”为“舞”,引申为“勇武”[2]。同持此论的如清人毕沅[3]“武,舞也,征伐行动,如物鼓舞也”。此两种新见,虽未直接否定“止戈为武”,但事实上强调“止为足”的运动性和主动性,是对“止戈”传统理解的重要解构。而近现代以来的知名学者如唐兰、杨伯峻等,则沿此路线进一步推进。唐兰[4]认为“武”字是象形而非会意字,从戈从止,应该是“荷戈而行”,是“步武”而非“止戈”。杨伯峻[5]则提出“象人持戈以行,有“战以止战”“杀以止杀”之意。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较新观点认为,“武”字当作“疋戈为武”,以“疋”为足,以“戈”作为“神祇”,训“武”为“神的足迹”[6]。比较分析看,以武为“舞”,虽有音义相近相通可能,但缺乏有效字符源流依据,尤其是无法揭示“武”之暴力文化特征。而以“武”为“神明的足迹”,则略显牵强,且有抽空几千年来的武文化内核基因之虞。虽然在卢氏细致的考据中,甚至可以看到许多颇具闪光点的联想和文献论据,如提到屈原“先王之踵武”。但回避“戈”作为典型兵器象形事实,而以“戈”作为神灵,则在逻辑上存在“强扭”之虞。事实上,古人对于上帝神灵或人间圣王、祖先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在上古时代能成为人类之首领,赢得众人的崇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武力或对兵器的持有;如后羿持弓箭、刑天舞干戚等,这是人类早期神话中的共同记忆,“武”假如可以在此逻辑中指代“神明的足迹”,那也是因为“圣王”“神明”“祖先”在他们上古迁徙开拓之路上,保留“手持兵器”的英雄形象的记忆。“戈”上升为某类人(圣王)的符号标识。在这个过程中,“戈”或构成“神祇”的符号基础,但不能取代“神祇”本身。我们不可以选择性忽视“戈”作为武器原始面貌而片面放大其与“神祇”的相近关系,前者才是后者的逻辑根基和前提。随着包括武学研究在内的各界学者的逐渐加入考辩,对于“武”字的理解开始逐渐分化形成“持(荷)戈而行”与“止戈为武”并立争讼,并以前者(持戈而行)占据优势的格局。乔玉成[7]分析认为前人已有研究对“武”的训诂主要存在两种路径:一是从文字学的角度看,人们训“止”为“趾、行”,则“武”为“征伐”;二是从人们表达战争观、武德观的角度来看,又存在训“止”为“止息”,如此则“武”为“止息干戈”。杨建营等则从字源学的角度系统梳理“武”及“德”的初始本义,其中训“武”为“持戈为武”,“德”为“直心正行”;并从“核心义”“拓展义”和“升华义”3个层次论述中华武德的内涵。
综上研究无论是对于梳理“止戈为武”的训诂公案,还是对于“武德”的内核探究,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和补充的空间。第一,“武”的现代诠释,虽可以置于字源学和武德观两种不同视角将其分别训为“持戈”和“止戈”,但这两种视角并非对立,非对立视角下同一个字有恰好相反的含义,这是有悖逻辑的。第二,“止戈为武”之“止”,虽从“象形”的角度看,有“从足”的指向,或可解读为“持戈行军”之象形义;但先秦训“止”为“停、息”已是集体默认用法,其中当有字义转变或生成的背景和根源,而不能轻易把训“止”为“止息”当做许慎的“附会”或“强加”。第三,“武德”作为历史概念与现代语境下的“武德”存在核心文化基因的延续,对“武”之原始义的理解变化也势必影响到人们对于“武德”文化内核的理解。鉴于此,继续追问“止戈为武”的原始字义生成,追溯“武德”之文化生成,是我们分判公案,进一步认知中华“武”文化独特本质,确立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
2 字源学意义上“武”字的形义再探
2.1 “六书”逻辑下的“武”是会意字而非象形字
然而,这里有一个不小的疑问:造字逻辑上“看起来像”就是象形字吗?这需要进入古汉字造字语境看待此事。中国古人造字逻辑主体为“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序》将其概括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6大种方式。象形为最原始的造字逻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但象形字有一个特点:指物为主,如日、月、山、羊、马、鱼、鸟等,都是用最简单原始的字符,描画天地间各种具体的物类。也正因为如此,象形字的范围和意义极其具体有限,不能满足人们语言表达丰富性的需要,因而有其他“五书”;但其他“五书”多立足于象形字符与字根基础之上。如此,一个很容易造成人们误会的现象浮出水面——许多看起来生动形象的字符,其实并非象形字,而是属于其他“五书”范畴。如所熟知的案例,“本”“末”二字,主体形象就是一棵树,从木;唯一的区别在于多了一点,这一点标在树木的下部,指代树根,则为“本”;标在树木的上部,指代树梢,则为“末”,这两个字画面感十足,其实是“指事”字。
那么反观“武”字的造字逻辑,也刚好存在相同的思路。《说文解字》认为“武”是会意字,不仅如此,还把它作为会意字的典型代表,这就值得进一步思索。作为中华文字学奠基者的许慎,如果在细微处有判定失误或可理解,但在他著名的“六书”理论中提出典型代表居然存在自相矛盾的“错误”,则实属异常。再细究《说文解字·序》所言“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8]500的解释,则再无违和处。“比类合谊”不正是要把两个及以上字符放在一起形成“合谊”吗?虽然“止”“戈”两个部首均属象形字,但二字根原本是两个“物”。当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以“合谊”的方式,让这个新字符获得一个抽象而不具体的新含义。杨国荣[9]指出,原初之“物”有其本然性与自在性,而“事”就其静态而言,是进入人知行之域的“物”;就其动态而言,“可理解为广义之行以及与知相联系的活动”。“武”字包含两字根“止”与“戈”,此二“物”既已然参与人类知行,其“合谊”的本质又表现为“关系”的属性。由此可知,“武”属“事”而非“物”,“物”具体有形,可以象形描画;而“事”属抽象,只可物物关联以意会。因而,“武”字属会意字而非象形字,许慎原本应当没有错。
2.2 “止”字的赋义逻辑:双“止(足)”为行,单“止(足)”为停
除楚庄王“止戈为武”典故之外,还必须回到“止”作为单独的字或字根的古代使用环境中来看。其实在先秦大多数“止”字的使用场合中,“止”为“停止、止息”或与之相近之意是人们集体使用,并无意义争讼。《诗·商颂》:“邦畿千里,惟民所止。”[10]止为“住所”,有安顿之意。老子《道德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11]125“知止”同“知足”,意指“停下脚步”。《庄子·德充符》:“人莫鉴於流水,而鉴於止水,唯止能止众止。”[12]178此处“流水”与“止水”构成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作为“流动”的反义词,“止”即停滞不动之意。而《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13]4则将“止”作为“定”“静”之基础和前提……种种案例表明,早在许慎之前,在文字运用渐趋成熟的先秦时代,人们对于“止”字已约定俗成将其作为指代“停止、止息”的符号在使用。根据年代越早就越靠近真相的法则,先秦诸子显然比今人更清楚“止”字的意义源头,那么其根源到底在哪里?
回到“止”字的赋义逻辑中,则一切有望得到一个根本性解释。根据“止”字最初的甲骨文形象,为“”,大约是一个脚印的形象,金文则更为直观,为“”。《说文解字》解释为“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爲足。凡止之屬皆从止”[8]49。意思是“止”表示物类下部的根基,就像草木的根脚一样,因此也以“止”表示“足”。段玉裁注“许书无趾字,止即趾也”。[14]118进一步认定“止”字最初为“足”“趾”的象形符号,余者不赘述。那么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后人的注解,皆以“止”为“从足”,这一点是大家公认的。然而,造成人们对“止”赋义争讼之处也正在于此。“从足”似乎与“行走”相通,因而有学者认为“武”字亦可理解而为“持戈而行”“荷戈而行”,所以导致今天学界争讼不休的地方,不在于是否“持戈”,而在于“武”字脚下之“止”到底是该训诂为“行”还是“停止”。那么,到底是许慎“误会”古人,还是今人“误会”许慎,都聚焦于此。
横向考证获得新的思路:古人表“行走”之字符与“止”是否有关联?如果有关联,是以何种方式关联?从目前来看,与“止”字符关系最密切的表行走的字符是“步”,篆文作“”,甲骨文作“”,而金文作“”,又作“”,从字形上看,就是两个“止”字的叠加,换句话说,“步”字就是一前一后两个“脚印”。《说文解字·步部》解释为“行也。从相背。”段玉裁注解说:“止少相竝者,上登之象;止少相随者,行步之象,相背犹相随也。”[14]120“止”与“少”相背者,就是“前后两个脚印相跟随”,这才是行走之象!至于“行”字,虽无“止”部,甲骨文作“”,金文作“”,从原始字义来看,似乎表示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因而才与行走有关系。但从“步”字的金文字符“”造型与行金文字符“”相通来看,“步”字本也有在路上行走之意。根据《康熙字典》的集注:《说文》解释“行”为“人之步趋也。《类篇》:从彳,从亍。《韵会》:从彳,左步;从亍,右步也。左右步俱举,而后为行者也”。[15]因而,“行”与“步”不仅在所表达的字义上是可通的,在赋义上也是一以贯之的。分析至此,不难发现:原来古人在“步”“行”与“止”的赋义逻辑上,虽然皆为“从足”,但是以双足一前一后跨出为“行”为“步”,而单一的脚印则意味着“另一脚并未跨出”而为“止”为停。
2.3 “止”的先秦使用语境:“行-止”作为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
以“止”为停,不仅在于“步”“行”“止”等字的构字赋义逻辑的对比上;还在于在先秦的语言文字使用中,“行”“止”二字本来就是相反相成的一对范畴。“行”与“止”对,如同老子所言“有无相生、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一样,是人们心中常有常在的概念范畴。如《孟子·梁惠王下》:“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13]210《管子·幼官》:“动静不记,行止无量。”[16]这里的“行”或“止”就是一对明显反义词,但又相对相成:“行”是相对于“止”的行为而言;而“止”是在“行”中停顿。《汉语大词典》解释说“行步和止息,犹言动和定”[17]。这些都昭示着,在“止”字的使用语境中,它本来就是“从足”的,但在“从足”的语境之下中,它恰恰表示与“行”相对应概念,也就是“停下来”的意思。这与《道德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用法,也是可以相通解的。
综合前述分析可以明确3点:第一,“武”属“事”而非“物”,在中国古人“六书”造字逻辑中,其属于会意字而非象形字。第二,在“止”字的赋义逻辑中,“止”作为“脚印”的象形字符参与赋义,根据人们以前后两个脚印指代“步”(意思为行)的逻辑推断,人们以单独的脚印也就是“另一只脚没有迈出”代表停止。第三,在“从足”的使用语境中,先秦人们以“行-止”作为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而使用,因而也不能以“从足”认为“止”有行走之意,它恰恰在“从足”的范畴中表“停止”。
因此,从多角度看,对于“武”的形义训诂,都不应该排斥和否定自楚庄王至许慎以来武字“止戈”的认知传统。但同时也值得关注的是:“止戈”事实上也并不拒斥“持戈”,因为从整体上看,对于“止戈”完整的“比类合谊”的理解应该是“有(持)戈止步”,其所否定和拒斥的是“以止为行”的训诂误会。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武”字的意义生成,事实上在“止戈”与“持戈”间保持不小的文化张力,而这种张力也让中国古人在对待“武事”“暴力”的态度上,保留着“进可攻退可守”的中庸智慧,也内在地生发出立体浑圆的中华武德内涵。
3 “止戈”命题下中华武德内涵结构的生成
3.1 从“在德论武”到“在武论德”:“武德”定义逻辑回归
有学者倾向于在“军事的武德”与“武术的武德”之间展开并行的探讨,如兼顾如上两套“武德”的发展实践史梳理其文化异同[18]。但也有学者逐渐将“武德”考察重心偏落于“武术的武德”。如直接将武德定义为“在中国道德伦理文化长期影响下,被习武群体所自觉认同的有关传武、习武、用武的行为规范”[19]。一般来说,将“武德”理解为“武术的道德”这种界定紧贴“武术”的当代性,符合当代人们对“武德”的常规性理解,是“武德”的核心话语之一。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界定也映射在现代语境下,尤其是当“武术”“中国武术”成为一门近现代学科和有意识的文化现象之后,人们对“武术”“武术人”的应然价值作反向推定的一种理解。但这样不免会带来对“军事武德”的割裂与贬黜,况且今日之武术与冷兵器时代之军事是有文化基因的延续性的。那么对“武德”的认识和界定,能否不偏落地、跨越时空诠释带有原初文化基因的“武德”?这是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事实上,在救亡图存、民族精神觉醒的近现代中国,无论是民国在“去病夫”的情结[20]里通过“尚武”的锤炼以强国强种,还是新中国“增强人民体质”“武术外交”的话语,都构成今天武术教育及研究的政治文化底色。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近现代“武侠”精神,还是“武德”价值,都是经历“民族精神”陶冶之后的“再造与重塑”[21]。那么这意味着,当前所认识的那个“武德”,是带有现当代底色的“武德”;如果想认识原初、整全、历经历史流变还依然存在着不变的文化基因的“武德”,就需要回溯到文化的源头,回到“止戈为武”的文化初心来寻找。
回到武事发生的原初语境中,“武德”本身不应是在某种有色伦理照射下对“武”的价值规定(武文化的发生不晚于儒墨百家的伦理建构),而应该是对“武事”本然之貌和具足之理的自然投射。如此,则可合“军事”与“武术”为一,合“武事”与“武人”为一,亦没有不同年代之伦理与话语底色之分,但可涵盖在家国为军事,在个体为技击的一切“武”的现象。鉴于此,本研究对“武德”作如下界定:从“武德”概念结构看,作为一个合成词,是“武之德”的偏正合义,也即武事及武事关系中的人所应然具备的风貌品格德行。
3.2 “止戈”命题的“暴力规训”:中华武德内涵的逻辑生长点
“止戈为武”的原始赋义代表了中国古人对于武事也即暴力工具或暴力行为的最初态度和看法,也内在地生发出中华武德的核心命题——“止戈”。戈为战争杀伐之器,是暴力的符号象征,“止戈”暗含对于暴力的合理运用、规训与控制——这意味着,“止戈”的命题“两位一体”地生发天然具备“武德”内涵规定的中华武文化。在这个层面上,“止戈”构成中华武德之本体依据与意义根源。中华武德在“止戈”的意义前置基础上,沿着人们对于“暴力”规训的逻辑,而逐渐开显和确立。
而在“止戈”的情境解读中,总体无非存在这3种可推演的情形。其一,“以暴制暴”的“止戈”:面对侵袭,如“以战止战,以杀止杀”,不得已运用暴力而制止暴力,有“持戈而杀,止人之戈”指向。其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止戈”:处于矛盾冲突中的一方,为减少暴力冲突可能带来对人、对物的戕害及损失,通过智谋博弈而非刀兵相见的方式,取得胜利或利益最大化,有“戈无所用,兵不血刃”指向。其三,“有戈不杀”的“止戈”。在己方掌握暴力主动权的情况之下,而能存有仁人爱物之心,不滥欺凌和杀伤,主动停止暴力输出的“止戈”,有“止我之戈,罢战休兵”的指向。当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还有一种极具迷惑性的“伪止戈”,也即无论处于何种情境下,己方主动放弃兵器和暴力所有权的所谓“止戈”。这种类似“投降”的情境虽有“止戈”的表象,但从其本质看,是对于“武”的彻底反动和否定,这种性质的“止戈”,客观上根本上不能阻止“暴力”的进一步侵害。因而,该情形不可计入“止戈”的情境诠释范畴。
1)“以暴制暴”的“止戈”:武德之“勇”内涵的生成。
前文对于“止戈为武”的形义分析指出:武字“止戈”的完整意思其实是“有戈止步”,以“止戈”与“持戈”保持张力。“止戈”之“武”,非“弃戈”之“武”,其前提在于“有戈”或“持戈”,是对于武器也即暴力工具的掌握和占有,而行动主体之“止”,是“从足”之“止”,其既可以是“去制止”,也可以是行军中的“止步”,还可以是“站立(与行相对的静止)的持戈”(警哨状)。这些都暗示:止戈不是“放下兵器”的投降主义,而是首先要具备“持有武器”的抗暴实力,然后可以抵距侵暴,最终实现“止息干戈”的理想行为,这既是对于国家民族而言的“国之大事”,也是对于个体而言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这一向度的“止戈以禁暴”的逻辑之下,“勇”德天然地成为中华武德首要前提和内在要求。“勇”者“从力”,是人所具备的“暴力性”被赋予英雄情感色彩的表达,“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勇者被视为英雄,而怯懦者被众人嫌弃,人们认可并呼吁具有暴力能力却可以为众人带来安全的人或组织,并进而认可他们对于侵暴者或敌人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在现实性而言,当外在、非正义的暴力对于国家或个人形成侵害之时,当言语情理的游说变得脆弱而不堪其用时,唯独个体或群体武装起来的暴力力量,可以为主体之国或主体之身赢得生存之机,这也为个体生命和文化留下传承的可能,是生命和权利最后的仰仗。这既是米尔斯口中的“终极权力即暴力”的写照,也是阿伦特与法农用以“反抗压迫”和实现“解放”的“正当性暴力”的追求[22];还是孙中山“尚武精神”的觉醒。
“勇”德作为中华武德核心内涵之一,源于“制止外在暴力”的客观需要,并表现于诸多方面。首先,在“建制”层面体现于国家制度对“暴力”的垄断和鼓舞,如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使得人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形成“暴力国有”[23],在“与子同袍”的共情文化中渲染和深化群体“暴力”的凝聚力,使个人之勇力升华为国家之勇力,“勇毅”成为国家精神,成为保家卫国乃至开疆拓土的现实力量。其次,在器物的层面体现于武器的精进,武器作为武者身体的延伸,铠甲的坚固与戈矛的锐利都会放大和倍增身体之勇力和暴力属性,是“勇”德的物化显现。此外,在个体武术技击层面,“勇”德表现为武者基本功夫之扎实,力量之大之猛,身体之勇武,以及在临敌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硬打硬进无遮拦”的“勇技合一”……那么回到“止戈”的初心,具足各种表现之“勇”德,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个人层面,皆可归于期待更高效实现“止战禁暴”梦想的前提和基础。
2)“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止戈”:武德之“智”内涵的生成。
“止戈”在其最现实的层面上,需要以暴力来对抗暴力,最后实现“止息兵戈”的和平愿望。然而,暴力与暴力的对抗,无论结果如何,其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充满血腥和残酷,伴随着对鲜活生命的剥夺,即便主观方、正义方取得胜利,也可能付出“杀敌一千,自伤八百”乃至更大的代价,这从根本上是有违于人类福祉的。因而老子就一针见血指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12]83其实也暗含对暴力的保留性批判和对天下生灵的悲悯。就连一代职业军事家孙武,也不以杀伐好战为能事。《孙子兵法》言:“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24]1417那么,对于圣人都为之忌讳的暴力,当人们“不得已而用之”之时,如何用最小的代价,尤其是以最小的生命伤亡代价,换取可贵的胜利而达成“止戈”,就成为“武德”所“能指”的应有之义——因而“智”之德,也构成“止戈”命题下所生成的中华武德之核心内涵之一。
当然,除此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止戈”,也生发出“武礼”可能性。中国古人向来有“先礼后兵”的文化传统,如此既包含慎重使用暴力的德性考量,也表现为一种用兵智慧。例如,兵临城下的盟约、以展示武力为目的的仪式性武舞,其本身就具有威慑敌人、不战而胜的功用于其中。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武礼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实体,有其物质外壳和外在形式,似乎不能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德性内核看待。尽管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所派生之“礼”包含对暴力的节制,又表现为一种工具性手段策略,暗合武德之“智”,而增进和丰富了中华武德内核的层次性。
“武德”中的“智”,就其军事领域(国家层面)而言,表现为战争的艺术,也即在使用国家暴力时“智慧”与“谋略”。这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让战争从原始野蛮的“搏力”中走出来,成为文明社会的“博弈”,也让战争从总体上消减了暴力杀戮的烈度。《孙子兵法》认为:“兵之五事”也即“道、天、地、将、法”是战争取胜的根本;而首先就在于“统治者”的行为合于“天道”,能得“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一个国家在暴力使用上的“道”。[24]1626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暴力”本身站在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一边——这种对于“暴力”的顶层规训的自觉,充分体现中国古人对于“武德”的理解以及在武事中的“大智慧”。而与之相对应的“胜之不武”,也即使用非道义的手段而获取的战争或搏斗的胜利,被认为是“不合武德”的。在“智谋”方面,中国古人在军事战争中所创造的各种谋略,如“兵不血刃”“攻心计”“以逸待劳”“擒贼擒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都为小代价迅速结束暴力冲突但同时获得战争胜利筹码创造可能,“武德”之智的属性,充分体现中华武德的艺术品质和审美格调。
而具体到个体的“武德”之“智”,则表现为在身体对抗上的“暴力转化”策略。如“动口不动手”的言语转移;如庄子论剑的“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发而先至”[12]895的“佯动”;太极拳的“引进落空”“借力打力”的“埋伏”;形意拳的“连消带打”,化拙力为巧劲的“化劲”。这些都不约而同地回避“暴力”的硬碰蛮打,而获得“以弱胜强”“四两拨千斤”的妙用。同样,为避免武术较技中暴力对人的伤害,而通过“体育化”“规则化”“游戏化”的暴力规训方式,将直接的身体暴力对抗,转化为动作舒展优美的“武术套路”包括“套路的对练”“点到即止”的切磋、弱暴力属性和高文化属性的“推手”“讲手”等方式,最终将“暴力”消解于无形,以“曲线救国”之方式诠释了“止戈”之“智”。
3)“有戈不杀”的“止戈”:武德之“仁”内涵的生成。
在“止戈”最为显性的阐释情境,用武主观方能在保持暴力强势、拥有生杀征伐主动权的情形下,而能以宽仁为体,和平时不欺凌弱小,已获胜时主动停止己方暴力输出,不滥杀伤,爱人利物的“主动止戈”,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止戈”。该情境在其最本质的层面上,生成中华武德之“仁”的核心内涵。武之仁德,不仅具足道家“道生之,德畜之”“长而不宰”的“自然之德”;也具足儒家“仁者爱人”的“生生之德”;还有墨家“非攻”的“兼爱之德”;更涵盖兵家“全国、全军……全卒”的“成全之德”。正是中华武德“仁”之核心内涵的存在[25],让“武”这一暴力性行为变得温情和正义,也让武德之“勇”与“智”被赋予人性的光辉,而不仅仅是冷静现实的工具理性。
“武德”之“仁”,在军事(国家)层面体现为老子所说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的“兵之道”。老子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11]80这是他作为天子之师,对春秋时期军事强国以“兵强”称霸诸侯的暴力泛滥的深度反思,而这恰恰也意味着“武德”核心命题的伦理觉醒。几乎与老子同时期的楚庄王,事实上也不约而同地用他的行动和语言历史性地赋义了“止戈为武”的核心要义。作为春秋时代最后一位“霸主”,他的行为恰恰是对于“兵强天下”的暴力霸权思维的反动,而走向合乎天道人情的“兵之道”的回归。在老子和楚庄王之后的两千年历史中,武德之“仁”德也被后人继承和诠释。以言语诠释者如孟子对于“好战”的梁惠王,以“王道”加以启蒙开导的著名对话(寡人之于国也);又如杜甫“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规劝。而行动诠释者如岳飞在江西平定吉虔二州叛乱时,力拒宋高宗屠城密令的“为民请命”,还有他平定洞庭湖割据政权时对主犯之外数万胁从徒众的“给钱粮放归田里”的宽厚仁慈。而在几千年军事斗争史上,人们也形成“穷寇莫追”“网开一面”“好战必亡”“仁者无敌”的常识与经验。
在个体层面,“武德”之“仁”表现为武者“内化于心而外化于行”的对暴力的自我克制。发乎“恻隐之心”而践于“忠恕之道”,于其至诚精微处具足“武者发自内心不想滥用暴力”的慎独和纯善,而于其文化载体处,则引申为武林人士“匡扶正义”“保护弱小”“为国为民”的江湖道义和社会责任;还有武艺绝学“宁可失传,不传歹人”的底线和操守;进入现代社会后,又有“习武先习德”“遵纪守法”的教育原则;以及在比武较技中的“点到为止”“不打要害”“练习点穴必先会解穴”的技术控制;还有现代中国竞技精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价值转换。如上种种,都是中华武德之“仁”内核的多元注解。
人类史是一部战争与和平交织的历史。然而中国古人早在直面暴力并尝试驾驭暴力的文化觉醒之初,便使用“止戈之武”命名这项“国之大事”。而“止戈”的原始赋义也使得“武”即暴力征伐之事,天然地具足对暴力自身的规约,这不仅内在生成中华武德“勇-智-仁”的核心要义,也事实上构成中国武术“德(仁)-智-力(勇)”的文化基因[23],还使中国在暴力治理上,一直秉承着“既主动面对暴力并掌握暴力,又积极控制并消解暴力”的“文武之道”,并在“持戈”与“止戈”的合理张力中,维系“天下”体系的动态平衡。
今日之世界,各国的深度交流和融合已将人类的利益和命运牢牢绑定在一起。然而,源于国别、种族、异质文化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萦绕不去,战争与暴力的威胁似乎也从未真正远离。在此意义上,“止戈为武”的武德话语将不仅仅是挺立中国武术“立德树人”价值追求[26]的参赞力量,也有望成为破解人类21世纪“战争与和平”矛盾之文化密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