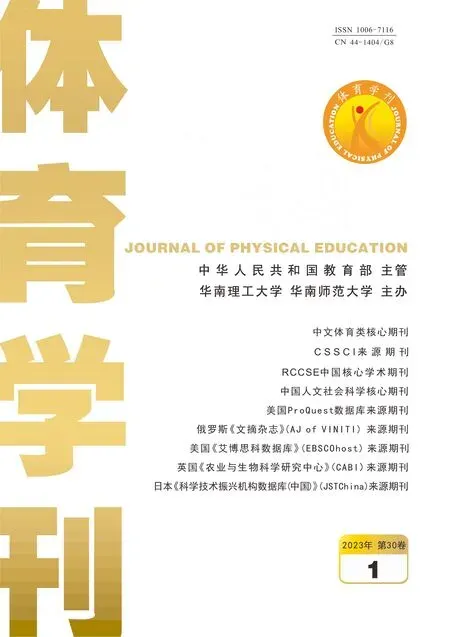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关系研究
李传奇
(华中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考证,旨在通过严格史料考察以还原历史的真相,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中国近代体育史领域依然存在亟待澄清的重要体育历史事件,其中就包括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相关问题。2024年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法国巴黎举办,这也将是继1924年巴黎奥运会百年之后的回归。1924年巴黎奥运会与近代中国体育存在着交集,在国家体育总局官网介绍1924年法国巴黎奥运会时,有一段关于中国与巴黎奥运会的相关信息“中国有3名网球选手参加了这届奥运会的网球比赛,但预赛时即被淘汰。尽管他们是在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后自行去参赛的,但这却是中国人首次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1]。目前,随着档案史料的挖掘,这段表述明显呈现多处与历史不符之处。首先,中国网球选手并没有出现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其次,中国网球选手也不是在澳大利亚而是在美国参加的戴维斯杯网球赛。再次,巴黎奥运会网球比赛的时间早于美国戴维斯杯网球赛中国队的比赛时间。最后,中国网球选手并非自行报名参加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而是由葛雷以远东体育委员会名义负责报名的。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临近,1924年中国与巴黎奥运会的历史必然会被更多提起。因此,通过考证去还原历史真相,不管是对近代中国体育史的研究还是对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参与和宣传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研究充分利用《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以及作者所收藏的葛雷1923—1925年间相关信札、电报等,同时广泛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和史料,对葛雷与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相关内容进行以史料(特别是原始史料)为基础的考证。
1 葛雷是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推动者
葛雷是1924年中国参与巴黎奥运会的推动者,然而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国内对葛雷的介绍都是寥寥数语,这与我们对诸如饶伯森、晏士纳、麦克乐等基督教青年会的体育干事的了解形成鲜明的对比。要深入探究葛雷是如何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就有必要对葛雷的成长与经历,以及他在中国的任职等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
葛雷(John Henry Gray),美国人,1879年11月30日出生于印度,1964年10月19日去世,父母是传教士。1883年从印度回到美国,并在美国完成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完成教育后,长期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2]。值得注意的是,葛雷曾于1902—190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春田学院(当时称为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培训学校)学习,主修体育并取得相关学历。这为其服务于基督教青年会期间长期担任体育干事奠定了基础。1908—1919年间,他曾任印度加尔各答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以及印度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1913年开始)。受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国际委员会的委派,葛雷于1920年来到中国,来华后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干事。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是西方竞技运动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主要推动者,可以说在1920年葛雷来到中国前,基督教青年会就已经控制了中国体育发展的主导权,主要体现在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以及重要的区域性运动会均由基督教青年会主导,体育人才也多有其背景,运动会举办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包括编印的秩序册)多为英语。因此,葛雷来到中国,担任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干事后,就自然而然接收中国体育的主导权。于是,他在1921年担任第5届远东运动会的名誉书记,1922年接替麦克乐担任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名誉书记,1923年担任第6届远东运动会中华代表团领队,1924年负责中断10年的第3次全国运动大会的前期组织和沟通工作,同年主导了中国参与巴黎奥运会和美国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的组织和报名工作。
葛雷在华任职情况时,最重视的一个职务就是远东体育委员会(也有译远东竞赛委员会,但其官方文件抬头用的是远东体育委员会)名誉秘书,这个职务也是当时的中国体育权力的核心。虽然仅仅是一个类似于顾问以及书记员的职务,但由于当时王正廷、张伯苓等多忙于政务或其他社会事务,再加上葛雷在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的地位以及从事体育方面的工作经验,远东体育委员会的事务基本就全权交于葛雷负责。客观讲,葛雷在主导中国体育权力时期,凭借其熟练的业务能力和丰富的对外体育交流经验,确实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葛雷不仅不懂汉语,而且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也缺乏深入的了解。其领导方式相对独断,缺乏与中国同行的深入沟通和交流,这无疑也会对其工作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2 葛雷推动中国网球选手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过程
1924年巴黎奥运会于当年5月7日—7月27日举办,参加这届奥运会的亚洲国家有日本、印度、菲律宾,其中日本和菲律宾都是远东运动会的参加国,印度也曾在1921年参加远东运动会。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官方报告中,已经明确中国报名参加网球比赛的选手名单,分别是韦荣洛(W.Lock Wei)、邱飞海(H.H.Khoo)、吴仕章(W.U.Szecheung),吴仕光(N.G.SzeKwang)[3]。最终的结局是他们虽然报了名但没有去巴黎参赛。下文将重点探讨中国参与本届奥运会的报名过程,寻找具体的没有去参赛的原因,以及葛雷和远东体育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2.1 中国网球选手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报名过程
1923年6月10日《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敦请中国加入》[4]的新闻,内容为:“第八次万国运动会,将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在巴黎举行,中国运动协会名誉书记葛雷博士已收有该会正式请帖,敦请中国加入,该请帖内所订之各项比赛日期为苏格兰式足球五月十三日至十九日,足球五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赛枪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其他各种运动,如田径赛、游泳等,定于七月五日至二十七日,葛雷博士现已函覆该会,中国当予万国运动会各项运动极力之扶助,且如有机会,当派遣代表参与比赛。”同一天上海《申报》也对此作了报道。此时正值第6届远东运动会(1923年5月21日—5月26日)在日本大阪结束没有多久,在这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华代表队除足球一项外,几乎全军覆没,在国内引发不少的批评。再加上当时动荡而混乱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在这样大背景下,大规模派体育代表团甚或从内地选派部分运动员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足球队表现虽然优秀,但人数众多,经费和管理在当时也是重要问题。同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除少数社会精英,民众对奥运依然缺乏最基本的认知)。这也可以参照1928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当时中国也仅仅派出宋如海先生一位前去观摩和考察。因此,如果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历史性开启中国奥运之旅,最优选择或许就是寻找香港或者海外的华侨运动员,因为他们对国外环境相对比较熟悉,语言也便于沟通,同时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纵览当时各比赛项目,可以说网球项目符合现实条件。当然,选择网球项目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24年的戴维斯杯网球赛。在这之前,中国同样没有组队参加过戴维斯杯。因此,组建一支可以代表中国的网球队,如果既能参加巴黎奥运会,又能参加戴维斯杯,就可谓事半功倍。
1923年12月18日葛雷同美国草地网球协会通信①明确表示中国对参加戴维斯杯的强烈愿望。美国草地网球协会行政秘书则在1924年1月15日给葛雷回信②,告知比赛报名截止日期为3月15日,并将在该日期后的一天到两天时间内进行抽签,同时要求葛雷选择具体的比赛区域。因此,对葛雷而言,选择运动员是一件急迫的事情。在网球运动员的选择方面,基本的参考就是最近两届远东运动会上的中国网球选手,1921年远东运动会中国网球选手是刁作谦、罗文惠、潘文焕[5]。1923年远东运动会中国选手则是吴仕光、韦荣洛、刁庆欢。1924年2月11日葛雷正式发电报给美国草地网球协会③,报名参加美国戴维斯杯。随后,也就是1924年2月12日葛雷复电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执行秘书④,给出了一个可能的参赛名单,分别是韦荣洛(队长,曾长期在美国和英国读书)、吴仕光(当时在英国大学读法律系)、刁作谦(时任北洋政府驻古巴公使)以及几位有潜力的在美留学生。在1924年2月18日葛雷还与王正廷有过一次简短的通信,信中葛雷向王正廷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报,表达了对中国参加巴黎奥运的乐观态度:“尊敬的王先生,在你离开上海之前,能在火车站和您共度片刻真是太好了。我希望我们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一起讨论中国在体育方面面临的一些国内以及国际上的问题。我们最近采取的行动之一是让中国参加戴维斯杯锦标赛。附件是我给执行秘书的一封信的副本。他回复了我,说我给他发的电报已经收到了。这将确保我们能参加今年的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韦荣洛先生很想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我们一收到报名表就给他和他的搭档报名。我相信你会很高兴我们至少能有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经历。”⑤
另外,笔者所收藏的葛雷系列信函、电报中,有韦荣洛以及吴仕光与葛雷的相关通信,其中也透露出一些细节。1924年2月14日吴仕光写信给葛雷⑥,表示自己还不确定能不能去参加巴黎奥运会和美国的戴维斯杯,但会努力去。同时,建议邀请马来西亚华侨邱飞海,认为他网球打的更好。在信中他还询问巴黎奥运会举行的时间以及是否需要自己承担食宿等费用。1924年2月21日葛雷致电美国草地网球协会⑦,表示中国球队已经出发前去参赛了,远东体育委员会已经任命韦荣洛担任1924年戴维斯杯中国网球队队长,全权授权他挑选球员。同时表示马来西亚华侨也可能代表中国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在这之外,他还会去参加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和巴黎奥运会。1924年4月22日葛雷收到韦荣洛的来信⑧,信中讲邱飞海正在前往英国参加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的路上,并明确邱飞海已经接受了代表中国参加巴黎奥运会和戴维斯杯赛的提议。但是吴仕光依然没有告诉他最终是不是参加巴黎奥运会和美国戴维斯杯的决定。葛雷正式向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报名参加戴维斯杯是在1924年2月11日,而给巴黎发电报报名参加奥运会是在1924年4月28日⑨,不过在电报里并没有出现运动员的名字。可以确定的是报名过程是由葛雷与组委会负责沟通,但具体人选是由韦荣洛根据当时具体情境确定的。在当时,由于葛雷以及大部分运动员都身处不同的地方,只能依靠电报和信件进行沟通,这无疑增加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这不仅影响最终名单的确定,同时给是否能够最终走向戴维斯杯和巴黎奥运会增加不确定性。这是葛雷在运作中国参与这两项赛事时考虑不够周全之处。
最终,出现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秩序册选手名单的中国选手是韦荣洛(W.Lock Wei)、邱飞海(H.H.Khoo)、吴仕章(W.U.Szecheung),吴仕光(N.G.SzeKwang)。而出现在1924年戴维斯杯秩序册选手名单的中国选手是韦荣洛(W.Lock Wei)、江道章(Poul Kong)、C.K.Huang(有人译作黄景康,当时为康奈尔大学学生,其他信息不详)。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最终结局是中国网球选手虽然成功报了名但没有去参赛(这在其官方报告中有明确信息)。至于没有去参赛的理由,1924年7月24日韦荣洛给葛雷发的电报做出了解释:“很高兴通知您,尽管之前由于吴仕光和邱飞海两人因故缺席,一段时间以来能否组队一直悬而未决,但我最终还是组建了一支相当棒的球队,代表中国参加即将到来的戴维斯杯。我放弃了参加奥运会的念头,一来是是因为网球项目要到七月中旬才开始,二来因为我的老搭档吴仕光没法与我一同参赛。”⑩也就是说,由于吴仕光的缺席,以及两项赛事间隔时间太近(1924年巴黎奥运会网球比赛日期是1924年7月13日—7月21日,1924年戴维斯网球赛中国队比赛日期是1924年7月31日—8月2日),中国网球队不得不放弃前往巴黎参加奥运会的计划。1924年9月22日葛雷回电韦荣洛,他在信中说:“我已收到您7月24日的来信,很高兴能够收到您给的消息。非常遗憾中国没能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但在这种这种情况下,我理解你不去参加比赛的想法。中国队在戴维斯杯上的表现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也祝贺你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至此,整个事件画上句号。
2.2 葛雷及远东体育委员会在整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在1923年6月份左右,葛雷收到巴黎方面的邀请函。其后,葛雷决定选派网球运动员代表中国去参加巴黎奥运会。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首先就需要给运动员报名。而给运动员报名,按照《奥林匹克宪章》,应该由国家奥委会负责。国家奥委会是“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规定建立起来,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并负责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奥林匹克运动唯一合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唯一有权选派参加奥运会运动员的机构”[6]。1894年10月的《国际奥委会公报》指出:“每个国家都应成立国家奥委会,其任务是保证该国每4年参加奥运会。”[7]但是,直到1909年,国家奥委会数量还是十分有限,很多国家都是由该国的体育协会代行其职责。在1914年巴黎召开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赋予国家奥委会明确的职责,即国家奥委会负责选派运动员,并保证其业余身份[8]。
中国奥委会何时建立并被国际奥委会承认。学界一直有争论,有1922年说、有1924年说、有1926年说、有1928年说、有1931年说。我国台湾地区的奥运研究专家汤铭新[9]认为,1922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当时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中国奥委会。汤的理由是“依据国际奥委会的惯例,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先组成国家奥委会,方可派选手参加奥运会,如果没有国家奥委会亦不可能提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于1922年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汤的另一个依据是,“国际奥委会前任秘书长柏丽奥克斯夫人所发表之专文——中国问题(1973年5月份公报66-67期Olympic Review)所载:国际奥会于1922年票选上海的王正廷为委员,同时接受并承认中国奥会”。遗憾的是,汤老师也并没有找到直接的历史证据。罗时铭教授[10]认同汤铭新老师的观点。1924年的说法,目前也缺乏有力的直接证据。1926年说法的依据则是,1926年4月的国际奥委会公报里明确记载中华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委会,“我国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奥委会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总干事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Mr.WilliamZ.L.Sung,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a 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通讯处为上海Chinese Recreation Ground,Routes Amirei,Bugle and Observatorise”[11]另外,1923年8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表决通过由孙和宾提议,宋如海、麦克乐、陆礼华、曾绍舆、刘慰先、张瑞珍等修正的提案。该提案的内容为“由本社联络各机关发起组织万国运动会委员会于明年春季选派专员赴万国运动会调查运动情形案”[12]。该提案可以间接说明当时我国还没有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因此,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奥委会被确认的时间应该在1923—1926年间,但具体是不是1924年则有待史料证实。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早期被邀请参加奥运会不一定就代表这个国家已经有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比如,菲律宾在1924年就被邀请参加奥运会,但其国家奥委会在1929年才被国际奥委会承认[13]。因此,巴黎邀请中国参加本届奥运会,不一定就代表中国有了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中国奥委会。当然,即便没有国家奥委会,同样可以报名参加奥运会,但最基本的要求也需要一个官方的国家体育协会或管理机构作为依托。那么在葛雷向巴黎报名的过程中,他所依托的是哪个组织,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从理论上讲,当时名义上官方的中国体育管理机构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于1922年4月3日在北京青年会正式成立,会长张伯苓(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副会长郭秉文(南京东南大学校长),会计袁敦礼(北平),书记麦克乐(南京),顾问分别为刘福基(香港)、郝伯阳(上海)、马约翰(北平)、司马德(苏州)、柯乐克(保定)。上述顾问,除刘福基不能确定外其余均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系。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的初衷是支配和管理全国的体育事业,这在其《宗旨》中可以看出:“(一)在中国提倡有程序之运动及体育。(二)为全国业余运动比赛制定统一之标准规则。(三)推广并改善业余运动员之运动游戏。(四)设立并维持业余运动之划一标准,因以增进高洁之运动精神。(五)在中华全国提倡并组织分区运动联合会,使之隶属于本联合会。(六)设立记录部,专司记录全国各分会业余运动游戏事宜。(七)遇有国际竞赛举行时,由本联合会负责选定代表中国之运动员。”[14]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不久,麦克乐就因东南大学课务繁忙而辞去了书记一职,当时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干事的葛雷接任[15]。然而,遗憾的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成立后,松散的组织结构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用葛雷的话说,就是这个机构一直不活跃。
基于史料,可以肯定的是在葛雷向巴黎奥组委报名的过程中,代表官方发挥功能的机构是远东体育委员会,而非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葛雷在运作巴黎奥运会报名的同时,也在运作为中国网球队报名参加戴维斯杯。1924年1月15日美国草地网球协会行政秘书在给葛雷的信函上,明确提出需要葛雷提供官方的中国体育管理机构或者协会的名称。1924年2月12日葛雷复电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执行秘书:“根据您的提议,我很高兴向你准确传达关于中国体育管理机构的如下信息。正如你所知,中国的现代体育起源较晚,在某种意义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在全国范围内与体育发展关系最大的管理机构是远东体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群知名的中国绅士组成,至少有一名外国成员,通常是书记的身份。我们协会内部的情况如下:尊敬的王正廷先生是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中国是远东体育协会的成员,其他成员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过去12年中,中国会定期参加两年一次的远东运动会的全部项目,其中包括网球。在各种场合我们都对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管理机构进行了讨论,虽然现在已经有一个名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的组织,我也担任该组织的名誉书记,但到目前为止,它基本上是一个不活跃的机构。因此,我认为,远东体育委员会可以为中国网球队正名,同时远东体育委员会是可以代表中国参加戴维斯杯比赛的最合法的机构。”在这封信里,葛雷向美国草地网球协会明确了远东体育委员会作为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合法机构。同时,1924年2月22日葛雷在一封《致编辑》的信中也证明了这一点:“远东体育委员会任命韦荣洛作为中国网球队的队长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戴维斯杯,这次任命赋予他全权挑选运动员的权力,做好各种安排,以官方身份代表中国参加这两项比赛。”
3 对葛雷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过程的审视和评价
尽管中国网球运动员最终没有能够站在巴黎的赛场上,但葛雷对于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值得我们去肯定的。正如1925年葛雷在退出中国体育主导权后所写《远东体育委员会的过去》结尾处所表达:“远东体育委员会这些年为中国引入现代体育运动,并通过为国家服务而光荣完成它的工作。如果不提及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在所有这些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贡献,那么是不公平的。从一开始到现在,它一直很感兴趣;它对时间、精力和资源毫不吝啬,几乎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无私开创和引领了整个中国的体育事业。”[16]客观讲,在1924年以前,中国体育的发展确实是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主导并引领。葛雷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体育部的干事以及远东体育委员会的名誉书记,无疑发挥着核心作用,在这期间葛雷积极推动中国体育的对外交往,尤其以积极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为重点,期望通过体育的国际交往带给“外界全新、健康的中国印象,让那些对中国人一无所知的国家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16]。他的这种思路直到今天依然是有积极价值的。然而在实践中葛雷却忽略一点,那就是中国的奥运梦想以及中国的体育事业,根本上讲是中国人的奥运梦想以及中国人的体育事业,中国人应当是参与的主体。缺乏中国社会普遍参与支持的一手包办式的奥运参与,注定是有先天缺陷的。
在葛雷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实质性缺席。根本上来说,不管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还是远东体育委员会都不足以代表国家,因为一方面当时的政府对于体育方面的对外事务根本无暇顾及,另一方面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以及远东体育委员会一定意义上讲依然具有很强民间自发性(即便有王正廷、张伯苓等官方人员出面任职),国家权力与这些体育组织之间尚没有产生积极而有效互动。再者,这两个组织本身具有非常强基督教青年会背景,在当时整个“非基运动”的背景下,这两个组织也很难获得更多有效社会支持。根本上讲,也正是因为“国家”与“社会”的缺席,才使得葛雷在推动中国参与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并最终以失败告终。最后,也正是基于对当时中国体育管理现状的不满和反思,也才有其后根本性体育管理机构和机制的变革,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诞生。
注释:
文中所涉及到的葛雷相关信札和电报均为作者收藏
① Gray to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1923-12-18.
②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 to Gray,1924-1-15.
③ Gray to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1924-2-11.
④ Gray to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1924-2-12.
⑤ Gray to C.T.Wang,1924-2-18.
⑥ N.G. SzeKwang to Gray,1924-2-14.
⑦ Gray to United States National Lawn,1924-2-21.
⑧ W. Lock Wei to Gray,1924-4-22.
⑨ Gray to Paris,1924-4-28.
⑩ W. Lock Wei to Gray,1924-7-24.
——以基督教青年会档案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