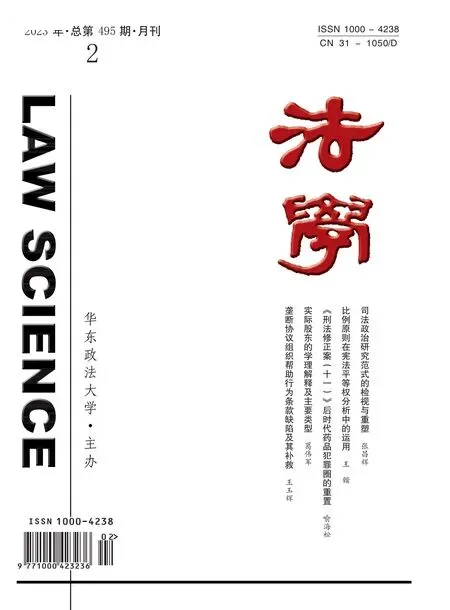《民法典》体系下共同担保人分担责任之实质理据
●李 宇
一、问题的提出:形式论证与实质论证的合力
共同担保人之间可否相互追偿或分担责任,系晚近我国民法学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明定共同保证、共同抵押和混合共同担保情形中有追偿权,原无争论,但原《物权法》第176条未规定混合共同担保情形中的追偿权,自此聚讼未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2020〕28号,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对各种共同担保一体采限缩分担的立场,成为否定论的最新依据。
然而,《民法典》虽未就共同保证再特别规定追偿权,但其关于债与责任之一般规定中已含有肯定论的立场。共同担保人内部分担责任在《民法典》中的规范基础有二,一为连带债务人、连带责任人之间的追偿权,二为代位(债权法定移转)。连带债务、连带责任的发生根据限于法定或约定(《民法典》第518条第2款、第178条第3款),但因《民法典》对共同保证和混合共同担保均默认规定其连带性(每一担保人各负全部担保责任),已符合连带债务、连带责任定义(第518条第1款、第178条第1款),自然发生含追偿权在内的连带性之法效果。共同保证符合连带债务的定义;共同物保虽非连带债务,但属于《民法典》第178条所称连带责任(该条所称责任包含无债务的责任);混合共同担保的各担保人亦因各负全部责任而同具连带性。《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第524条第2款、第700条的代位规范皆可为担保人所用,担保人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取得债权人的相应权利,包括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主债权及对担保人的从权利,由此可主张其他共同担保人分担责任。〔1〕《民法典》颁布后肯定论的法教义学分析,参见杨代雄:《〈民法典〉共同担保人相互追偿权解释论》,载《法学》2021年第5期,第215-231页。兼从法经济学和法教义学视角所作的分析,参见贺剑:《担保人内部追偿权之向死而生—— 一个法律和经济分析》,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102-124页。
此种法教义学分析以《民法典》新体系下的解释论为主线,侧重于形式论证。但肯定论与否定论之争非止于形式层面,在实质层面亦多有较量。实质论证涉及不同面向的价值判断。肯定论若不能在实质论证层面抗衡争胜,则否定论仍有机会以实质判断之妥当性为由改变形式论证之方向,例如对《民法典》相关规定作狭窄的解释,甚而干脆对倾向于肯定论的新规则视而不见。不少否定论文献对代位规范的回避态度〔2〕如有释义书在论及共同担保时均未提代位规则,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67-469页;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511-513页。即为其例。价值判断常容易导向立法论,但立法论与解释论本非泾渭分明,立法论的立场会左右解释论的方向。因此,在开展形式论证作业之余,仍有必要回应否定论在实质理由层面的诘难。民法规范本身包含了自治、效率、公平等多重价值。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吻合诸价值的规则方为民法问题的更优解。因此,诸价值层面的论证应多管齐下,相互协力。
二、自治论:分担肯定论更契合意思自治
(一)意思联络
否定论认为,未一并提供担保的共同担保人之间不具有意思联络、不存在法律关系,故无追偿权。〔3〕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69页。但最高人民法院的释义书持相反见解:保证合同的签订无论同时还是分别都构成连带保证,保证人之间纵无意思联络,仍成立共同保证。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3页。另有否定论认为,原则上只有当事人之间的数项义务具有内在联系的共同关系时才有可能确立追偿权制度。参见崔建远:《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86页。实际上,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我国,所谓债务人之间的内在共同关系在法律及法理上均非连带债务或内部追偿权之要件。从正反两方面而言,此论均无依据。现代民法所普遍确立的连带债务人(连带责任人亦同)之间的一般追偿权,本就不依赖于债务人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追偿权是连带债务的内部效力,脱离连带性之前提、孤立地讨论追偿权人之间有无法律关系,并无意义。连带债务亦不取决于意思联络:有意思联络,未必有连带债务;无意思联络,未必无连带债务。就正面而言,连带债务一般规定并未将债务人之间有意思联络或特别法律关系列为连带债务要件,民法学理亦然。〔4〕迄今尚无任何国家的立法因债务人有无意思联络或目的共同而对连带债务适用不同的效力规则。参见章正璋:《论我国现行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债务》,载《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122页。就反面而言,债务人之间无意思联络或特别法律关系而负连带债务者,在我国法上即不乏其例。基于法律规定所生之债,连带债务人之间多无意思联络(例如共同危险行为、客观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基于法律行为所生之债,连带债务人之间无意思联络者亦所在多有,例如由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债务加入或者第三人基于无因管理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而债务人不知之,债务人与第三人无意思联络而负连带债务。进言之,意思联络原为主观共同侵权行为语境下的概念,与连带性及追偿权之发生本无关联。连带债务乃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之结果,非基于债务人之间的意思联络而发生。债务人之间的意思联络,不等同于创设连带债务之意思。例如,共同承揽人与定作人订立同一承揽合同,可谓有意思联络,但此事实不同于各承揽人有连带负责之意思;之所以负连带责任,乃法律特别规定使然。若无法律特别规定,共同债务人虽有意思联络、订立同一合同(如共同买受),亦不生连带债务。就实质理由而言,某一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为其他债务人连带负责,对其他债务人并无不利,既无须与其他债务人合意,又无须其他债务人知悉,意思联络纯属多余。退言之,若谓意思联络是连带债务构成要件,则无意思联络应无连带关系,逻辑上也可能成立按份债务,而非以不真正连带债务为唯一结果。〔5〕如在意大利法上,如有无意实现共同利益的多数保证人提供保证,则为可分之债。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4卷),于庆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6页。
《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第2款将各担保人在同一合同书上签章的情形与约定连带共同担保同视,其起草观念仍拘泥于意思联络说。〔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86-187页。但纵按此说,担保人虽不在同一合同书上签章但彼此知悉的,仍存在意思联络,何以不能同等对待?共同担保人虽在同一合同书上签章,未必有意思联络,例如债权人先后找保证人甲、乙在同一借据上签名,甲不知有乙,彼此并无意思联络,但该条仍以连带共同担保论。其逻辑上不能自洽显而易见。
(二)意思自治
较之连带债务,按份债务更符合意思自治和自己责任原则:各债务人自负其责,其他债务人不能清偿之部分由债权人自担风险,而连带债务中各债务人负担其他债务人不能清偿之风险,在效果上相当于相互保证。担保人未约定连带负责时,此种相互保证实则由法律无视担保人意思拟制而成。〔7〕《瑞士债务法》的共同保证规定(第497条第1款)即明文采此“拟制保证”构造,接近于连带共同保证。按份债务体现个人主义原则,连带债务则趋于团体主义思想(“一人为全体、全体为一人”),此种团体主义旨在确保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安全性与便利性,对于各债务人的一般意思则有所背离,故连带债务的成立须有约定或法定。而且,在债务人之一清偿后,服务于债权人之特别目的即已达成,该债务人得向其他连带债务人追偿,实质上还原为按份债务,可谓向意思自治原则回归,是法律将先前背于债务人意思(实际意思或默认意思)而夺走之利益“返还”于债务人。而依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中的相互追偿否定说,则连此种还原机会都不复存在,偏离意思自治原则更远。按照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吻合度之大小,以上三种模式可排列如下:按份债务>连带债务>不真正连带债务(无相互追偿权说)。〔8〕数人中有终局责任者的情形,在此不予考虑,此际由其最终负责符合意思自治和自己责任原则,自不待言。就共同担保而言,现行法以连带为默认规则,但担保债务毕竟以标的可分为常态,个别担保人担责后,担保人之间内部关系即有朝按份债务方向趋近的可能性。依现行法之默认规则,将未特约为按份共同担保的情形解释为按份债务已无可能,唯有解释为连带债务和不真正连带债务两种可能性。鉴于私法的性质及意思自治原则的基础地位,“有疑义,从自治”,〔9〕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载苏永钦:《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就数人责任形态出现疑义时,应尽可能作更契合意思自治原则之解释。解释为连带债务比解释为不真正连带债务更接近意思自治原则。
当然,否定论未必以不真正连带债务立论,但无论其理论基础为何,皆有内外混淆之弊病,而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中的相互追偿否定说相似。内外混淆,便是某一担保人在外部关系上被债权人选定承担责任,即等于在内部关系上承担终局责任。由此,否定论意味着各个担保人“最终命运的他主决定”。反之,在肯定论之下,挑选何人担责之主动权,虽仍操于债权人之手,但担保人在担责后却可自主选择分摊,避免完全由债权人决定自身命运。何种立场更契合意思自治原则,益已明矣。
否定论认为,各担保人不知有其他担保人的,本无连带负责及向其他担保人追偿的意思,但肯定论却硬性地令担保人连带负责,不符合意思自治原则。〔10〕参见崔建远:《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94页。类似见解认为,一般性地确立担保人内部追偿权,相当于法律强行介入担保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一项法定之债,在担保人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参见叶金强:《〈民法典〉共同担保制度的法教义学构造》,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3期,第66页。此说可谓倒果为因,令担保人连带负责、在担保人之间建立联系的不是肯定论,而是法律特别规定,肯定论不过是法定连带责任的内在效力而已(并非新确立一项法定之债)。若谓各担保人无连带负责、相互联系之意思,则依按份债务推定原则,本应各按其份、互不负责,不真正连带债务说(或不真正连带共同担保说)更无立锥之地;否定论既认同法定连带性(法律强行介入、使担保人连带负责),又拒斥法定连带性内部效力规则之适用,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二次背离。
否定论另以设想之案型为据,认为肯定论会挫败当事人排除追偿权的安排:保证合同约定债权人不得再觅其他担保人,否则保证人不接受其他担保人的追偿,但债权人背信另寻抵押人,抵押人在承担责任后向保证人追偿,由于保证人无力以保证合同约定对抗此追偿,致违背意思自治原则。〔11〕同上注,崔建远文,第94页。然而,债权人另觅彼担保人,必定减少此担保人的风险(分担或不担),债权人如不另觅彼担保人,则此担保人将独担全责。订立此种不得另觅担保人的特约,既不是理性债权人之所愿(自缚手脚、增加风险),又岂是理性担保人之所为?
否定论又以系列交易和整体安排为由,认为肯定论会破坏此类交易中某一担保人实际不愿承担担保责任或被他人追偿的安排。〔12〕同上注,第93-95页。但系列交易和整体安排形态繁多,否定论仅举孤例,自不能以偏概全。纵赖此类孤例,亦不足立论。其一,此种安排极可能构成虚伪表示,因而无效或不影响该人负担保责任。其二,否定追偿权之存在,只是有利于个别交易方而不利于多数交易方,既难谓公平,又不符合多方主体的预期。其三,若债权人与个别担保人有意达成该个别担保人不承受其他共同担保人追偿后果的安排,自可由债权人出面同其他担保人缔结特约,约定其他担保人放弃对该个别担保人的追偿。在担保交易实务中,债权人通常居于优势地位,真欲缔结此种特约并非难事。
(三)默认规则
民法关于担保人内部关系的规定,属于默认规则(default rule),即任意规范。默认规则之正当性,立基于对民事主体意思的模拟、反映民事主体的合理预期,即默认规则是一般人从事交易时将会选择的规则。造法者在创设默认规则时以当事人间假设意思为基础。当事人之间以有效约定表达出有别于该假设意思的实际意思时,默认规则即被排除适用。在实际交易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默认规则是否符合假设交易的意思至关重要。如果默认规则符合假设交易的意思,当事人从事该种交易即承受了合乎己意的结果;如果默认规则不符合假设交易的意思,则当事人无从排除不合己意的法律效果,只要从事该种交易就将被迫接受其全部结果。默认规则实为一种意思推定规则,当事人意思表示不明时推定为何方当事人的意思,会导致默认规则呈现不同的样态。理性的主体总会倾向于利益最大化的规则。
标的可分的多数人之债,以按份和连带为两大默认规则范式(不真正连带则为一种粗疏的理论,未被各主要立法例设为默认规则)。先就按份债务和连带债务的一般情形而言,自债务人立场着眼,一人债务与多数人债务的区分意义在于一人独担与数人分担,每一债务人在多数人债务中的负担理应轻于一人债务的情形。自债权人立场着眼,预期正好相反,债务人人数的增加意义在于加强债权之保障,连带债务更称其心。再就共同担保而言,如果默认规则定为按份共同担保,是着眼于担保人的意思和利益,从担保人着眼,既有数担保人,自应按份分担责任。连带共同担保默认规则是着眼于债权人的意思,债权人既然要求数人共同担保,通常意思即在于强化债权保障,连带胜于按份。当事人若未表示连带担保意思,应作何解?就担保人一端而言,共同担保人有按份承担责任的默认意思,数人分担胜于一人独担。担保人知道另有共同担保人时,固然如此(实际意思),担保人不知另有共同担保人时,其默认意思亦是如此。但从债权人一端而言,担保人连带负责更符合共同担保之目的。担保人与债权人各有盘算,其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在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形(如仅有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名而未约定如何承担担保责任),选择倾向于任何一方的规则,各具理由。在按份之债推定规则的作用之下,有疑义时推定为按份之债,会导出偏向担保人的结论。选择连带共同担保默认规则是偏重于保护债权人的立法政策。由此不难理解,立法例上存在推定为连带共同担保和推定为按份共同担保的两种默认规则范式。
罗马法于相当时期内认为保证人有分别利益,即以按份共同保证为原则。近世立法亦有此例,如《西班牙民法典》第1837条、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3055条、《日本民法》第456条。在罗马法系的大多数国家,保证人可以主张分别利益(如《法国民法典》第2303条)。〔13〕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4卷),于庆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7页。受法国法影响的混合法系立法亦不乏其例,如《魁北克民法典》第2349条。按份共同担保默认规则是按份债务推定原则在担保领域的自然延伸。处于中间状态的立法例区别对待不同情形,例如我国《澳门民法典》第645条规定,如数人分别独立提供保证,原则上负连带责任;如共同提供保证(即使在不同时间承担),各保证人均得主张分担责任之利益。另有立法例不采按份债务推定原则,反而对共同契约之债采连带债务推定原则(《德国民法典》第427条),连带共同担保自然同成默认规则。但采按份债务推定一般原则的立法例专就担保另采连带共同担保默认规则者亦有之,如我国法。在实行按份之债推定原则之大体系下,就共同担保特设连带性推定,乃是保护债权人的立法政策之产物,是一般原则之例外。〔14〕我国从原《担保法》以来至今的共同担保默认规则,在侧重于债权人利益这一立法思想上未有变化,无论是原《担保法》时代使用“连带”字样抑或原《物权法》与现行《民法典》不使用“连带”字样,皆无分别。
在各种模式中,按份共同担保默认规则最为合理。首先,按份之债最契合意思自治原则,已如前述。其次,担保合同通常是无偿合同,在价值判断上立法者预设的规则应较倾向于担保人。再次,按份共同担保默认规则无违效率原则。默认规则的设计本身蕴含减少交易成本的考虑。问题在于减少何人的交易成本。连带共同担保默认规则是减少债权人的交易成本,按份共同担保默认规则减少的是担保人的交易成本。若以按份共同担保为默认规则,债权人即需缔结特约,因而付出额外的交易成本;反之,付出特约成本者为担保人。但由债权人负担特约成本具有合理性。一方面,债权人在缔结担保合同时通常居于强势地位,担保人欲以特约减轻负担,势所难能,以致连带共同担保默认规则在实际效果上近乎强行规则。而由债权人另提特约并非难事。在交易成本固定的前提下,何方主体较能消化交易成本,将交易成本配置于该方主体是较有效率的。另一方面,债权人既然在缔约时居于强势地位,自可提出连带共同担保条款,从而向担保人发出明确的信号,使担保人更有机会认识到己方责任和风险,据而作出自主决策。相反,在连带共同担保默认规则之下,担保人不知法者所在多有,往往于不知不觉中即已负担连带共同担保责任(法律规定的信号功能弱于合同条款,即便是格式合同条款)。《民法典》对于保证方式改以一般保证为默认规则,其正当性亦在于此,就此而言,对共同担保采连带性之默认规则,立法原则不无矛盾。最后,按份共同担保并不必然背离共同担保之目的。有学者认为,使数人为保证,在于增强其担保之效力,但允许分别利益,则保证人中如有无资力者,可发生就其负担部分不得受偿之结果,对于债权人反较一人保证为不利,不合于共同保证之目的。〔15〕参见史尚宽:《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42页。但按份共同担保的担保力度未必弱于单独担保。例如甲对乙有200万元债权,欲请丙提供保证,但丙仅有资产100万元,遂又另寻丁作为共同保证人(丁有资产200万元)。即便丙丁仅按份承担保证责任(各承担100万元),仍胜于由丙单独保证。
连带共同担保虽不利于担保人,但因实行“内外有别”的法律思想,每一担保人对外全额担责的风险经由追偿权在内部分摊,担保人最终仅承受其他担保人丧失资力之风险。追偿权作为连带债务的配套默认规则,意义正在于此。〔16〕如德国学说所论,追偿权是多倍义务的必要补充,理性的当事人在意定连带债务中将会达成相互可追偿的协议,但因意定连带债务的当事人未必全是理性的(当事人可能虑不及此),且法定连带债务的当事人不可能预先缔约,因此,期望此种协议在每个连带债务中均存在自无可能,《德国民法典》遂以第426条一举解决。参见张定军:《连带债务研究——以德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页。此种追偿权一般规定因而具有默认规则的意义。即此类规定之作用在于,当数债务人的内部关系不存在或不明确时,用来处理债务人内部追偿权的存在、范围与调整方式等。参见管静怡:《不真正连带债务与连带债务之界限》,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第63期(2019年),第99页。而连带但否定分担的模式对担保人最为不利。每一担保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均处于“无知之幕”笼罩之下:无法预知债权人将来向何人行使担保权利,自己是成为先担责的“倒霉蛋”还是不担责的“幸运儿”,纯系于债权人一念之间。担保人由一变多,并未实质性地降低担保人的风险。否定论认为,承担全额担保责任本来就符合担保人的预期。但此种观点忽略了担保的本性。担保人向债权人全额担责并不是事情的终点。担保人终究只是为了担保他人的债务,无意成为终局责任人,因此,除担保人有赠与意思等非典型情形外,担保人一般期望从债务人处挽回损失,法律明定担保人对债务人的追偿权正是一项体现此种预期的默认规则。但若债务人丧失资力,担保人唯有向其他共同担保人主张分担。尽可能挽回损失乃人之常情。肯定论即为担保人留有挽回损失之机会,否定论则不符合此种预期。况且,如果认为担保人同意订立担保合同即意味着最终全额担责不违背其意思,则对于任何因法律行为发生的连带债务,皆可谓其债务人最终全额担责符合其预期,所有的追偿权岂非都将不复存在、不必存在?再者,如果认为某一担保人最终全额担责符合其订立担保合同的意思,则其他共同担保人未承担责任岂非有违他们的意思?
概言之,对担保人而言,从按份共同担保到连带共同担保再到采否定论的不真正连带债务,风险递增。对债权人而言,从按份共同担保到连带共同担保,风险递减,但连带共同担保与不真正连带债务对债权人的影响大体相当。〔17〕甚而在我国现行法之下,对债权人而言,连带债务比不真正连带债务更为有利,例如对连带债务人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具有涉他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第2款),而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通常将时效列为无涉他效力事项。对担保人而言,按份共同担保虽属最优,但在保护债权人的立法政策及现实缔约情势下,往往只能接受连带共同担保,而不真正连带债务则是最差模式。就此而言,连带共同担保不失为双方能够达成共识的折中选择。否定论是将理性的各方当事人都没有理由选择的模式定为默认规则,有违默认规则之原理。
三、效率论:分担肯定论更具效率
效率论涉及制度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与自治论实有重叠之处。作为经济分析之基本范畴,自主交易被推定为最符合效率原则。甚或可以说,效率原则乃自治原则之投影。但为照应否定论与肯定论相辩之脉络,仍将前处未予揭明之问题在此续作讨论。一种有效率的法律制度必为倾向于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共同担保规则所涉成本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和案件处理成本。
(一)交易成本
共同担保人相互知悉的(不限于在同一担保合同上签章,担保人之间亦可在担保合同外订立追偿特约),各担保人之间有机会缔结特约,无论是在肯定论之下约定排除追偿权,还是在否定论之下约定享有追偿权,该环节本身的交易成本大体相当,但因肯定论较符合一般担保人的预期,以其为默认规则可使大多数担保人免于另为特约之交易成本,否定论则反之。共同担保人互不知悉的,各担保人之间无机会缔结特约,唯有同债权人缔结特约一途。此时否定论与肯定论所引发的交易成本本身即颇有不同。法律如采肯定论,个别担保人(乙)如不愿受制于追偿规则,只需抛弃追偿权(不愿向他人追偿),或者向债权人(甲)提供非担保的增信措施(不愿被他人追偿)。法律如采否定论,个别担保人可与债权人约定,如债权人另觅担保人,愿与之负连带共同担保责任。但若如《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一般将连带共同担保限于担保人之间的约定,则此种缔约方式已不可行,个别担保人乙如期望向其他共同担保人追偿,可以和债权人甲约定,债权人另觅其他担保人时,有义务在和其他担保人(丙)订立的担保合同中约定,乙在先行担责后有权向丙追偿。此种特约对其他担保人设置了负担(丙将被乙追偿却无权向乙追偿),如其他担保人在缔约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难以为其所接受,又因此种特约对债权人并无实益,担保人即便不居于强势地位但坚持不允,债权人亦不便强人所难。两相比较,肯定论下交易目标的达成,至多只需甲乙双方缔结特约,否定论下则需甲乙双方、甲丙双方分别缔结特约,后者条款设计更为复杂、能否缔约变数更多,交易成本自然更高。
否定论不仅会增加追偿权交易的成本,而且会推高一连串交易的成本,引发“涟漪效应”。对债权人而言,共同担保人多多益善,反正担保交易成本通常由债务人负担(如向营业担保人支付担保费、向非营业担保人给与其他利益)。但否定论导致担保人难以向其他共同担保人分散风险,担保费率将因之上涨,进而增大债务人的融资总成本。
否定论对交易成本说的回应是,担保合同的订立是债权人和担保人双方的问题,契合担保人的心意不一定契合债权人的心意,如果债权人更强势,即使法律规定可追偿,债权人也完全可能要求缔约改变之,而在大多数担保交易中担保人不处于强势地位。〔18〕参见崔建远:《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98-99页。然而,追偿权是连带共同担保的效果之一,连带共同担保既可由担保人和债权人约定,亦可由担保人之间约定。担保人之间的追偿,并非债权人和担保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担保人之间订立享有或不享有追偿权的协议,不属于担保合同范畴,无须债权人同意。债权人在担保交易中相对于担保人是否居于强势地位,与担保人之间约定追偿问题无关。况且,担保人之间可以追偿通常无害于债权人(甚而因可减少提供担保的顾虑、增加担保交易机会而有利于债权人),债权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特约要求担保人放弃追偿有悖常理。再者,在前述担保人互不知悉而有求于债权人配合缔结特约的情形,若债权人处于强势地位而不愿意配合,特约享有追偿权比特约排除追偿权更为困难,则权利的初始配置将更具决定性,否定论对担保人更为不利。
(二)案件处理成本
否定论的理由之一是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在程序上不经济、可操作性差,追偿多少是一道复杂的计算题。〔19〕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469页。该理由难以成立。其一,担保人相互追偿制度自原《担保法》以来行之多年,未见有何操作上的重大困难足以否定之。其二,责任应否分担是前提问题,责任如何分担是后续的技术问题,二者本非一事,以后者之难度决定前者之方向属于本末倒置。其三,计算问题或程序不经济乃法律适用中的常见现象。举凡合伙合同终止时盈亏款项结算、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投资者损失计算和因果关系评估、数人侵权纠纷中责任份额确定之类,存在繁复计算或程序问题之案型所在多有,未闻以此为由拒绝给予司法救济者。其四,否定论无法避开计算问题,只要当事人约定了连带共同担保但未约定分担份额,否定论也不得不计算分担份额。〔20〕有否定论为“有追偿合意但对如何追偿约定不明”的情形设计了五步法的追偿规则,相当复杂。参见江海、石冠彬:《论共同担保人内部追偿规则的构建——兼评〈物权法〉第176条》,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118页。在计算规则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扩大责任分担的适用空间反而可以摊薄计算规则成本,取得更大的制度效益。至于追偿诉讼的增加,亦非肯定论所独有。否定论既然容许一定条件下可追偿,自然也无法避免此类成本。其五,当法律制度面临复杂问题时,根本之道在于简化问题,而非回避问题。在如何分担问题上,“先定责任大小,否则平均分担”不失为公允、简明的算法,操作成本甚低。
此外,否定论还会掉入几乎无解的计算陷阱。否定论更容易造成部分共同担保人之间有权追偿、部分共同担保人之间无权追偿的局面,〔21〕在肯定论之下,理论上虽不排除部分担保人预先放弃追偿权的可能性,但因放弃对其不利,实际上不易发生。而在否定论之下,担保人会尽量争取预先约定追偿权,但如果分别担保而相互不知,彼此难以约定追偿权,故形成部分有追偿权、部分无追偿权情形的概率较高。此时计算问题将更为复杂。以否定论所举之例说明。债务人的股东甲除自任保证人外,分别请友人乙、丙为100万元主债务提供担保,甲乙、甲丙分别在同一担保合同上签名。依否定论,甲乙、甲丙各自构成连带共同担保,乙丙之间无连带关系,故在确定追偿份额时不能将三人合计。〔22〕参见吴光荣:《共同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以共同担保的再类型化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3期,第71页。似只能将甲乙、甲丙分别计算,则甲乙间各负担二分之一,甲丙间也各负担二分之一,如此将出现甲在担责后有权向乙丙各追偿50万元、最终自己全身而退的结果(并无理由要求甲先向乙追偿后向丙追偿,或反之)。欲避免此种不公平结果,似别无其他算法。而依肯定论,每人均担三分之一既公道又简便。
诉讼案件的其他成本亦可通过相关制度或程序操作妥为解决。个别担保人不知另有共同担保人的,可能事实上难以行使追偿权,对此可借助附随义务(《民法典》第509条第2款):基于担保合同,债权人对担保人负有告知其他共同担保事实的义务,以便于担保人行使追偿权,怠于告知或不实告知致担保人追偿不能或追偿不足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在审理担保纠纷案件时,亦可释明债权人应向担保人告知共同担保情况,以便担保人尽速解决追偿纠纷,免于讼累。
对于非讼案件,否定论另有额外处理成本。如在破产重整、和解或债务重组之类案件中,破产管理人、法院等主持方会斡旋各担保人为债务人代偿,助其减负脱困。债务人将来能否扭亏为盈、向担保人偿还尚属未定之数。在否定论之下,因欠缺分散风险的机制,“谁先出钱谁倒霉”,各共同担保人势必设法拖延、回避、抵触,主持方的协调成本增大、回旋余地变小。主持方虽可尝试勉力说服各担保人事后缔结互有追偿权的特约,然此成本原为肯定论之所无。
四、公平论:分担肯定论更为公平
公平概念具有多义性。游离于实定法之外的公平究属何意,可能言人人殊,或谓“关于公平的客观结论是:公平是非客观的”。但鉴于公平价值已在相当程度上内化于法体系之中,以实定法为支点,公平论仍可有所依凭。共同担保人分担责任乃比较法之通例,〔23〕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全译本)》(第4卷),于庆生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154-1159页;[德]彼特·施勒希特里姆:《数个他债担保人的内部求偿》,陈欢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72页。莫不以公平为正当性基础之一。例如在德国法上,保证人与物上担保人得相互追偿,理由部分在于矫正正义与衡平理念所导出的补偿义务。〔24〕参见[德]延斯·科赫、马丁·洛尼希:《德国物权法案例研习》,吴香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德国联邦法院判决认为,将《德国民法典》第426条第1款所蕴含的各担保人按各自份额共同承担责任这一法律思想适用于担保人之间无特别约定的情形,是唯一符合公平原则的处理方式。参见《担保人间的补偿义务》,吴奕锋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又如在英国法上,保证人有权向其他共同担保人追偿(无论保证人是否彼此知悉、是否签署同一担保文书),乃衡平法上的古老规则。〔25〕See H. G. Beale(ed.), Chitty on Contracts, Vol.Ⅱ, Sweet & Maxwell, 32nd Ed., 2018, p. 45-135.再如在日本法上,学说认为,债务人资力不足时只有作出清偿行为的保证人负担损失,有违共同保证人之间的公平。〔26〕参见[日]我妻荣:《民法讲义Ⅳ:新订债权总论》,王燚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448页。着眼于共同担保之连带性,则可进一步追溯至连带债务人追偿权的公平基础。如萨维尼所言,只有追偿权方可防止连带债务最终成为其本质所不应有之“赌博”结果,且追偿可防止其中一人无端以他人之费用而获利,故追偿权是“公平且值得追求的”。〔27〕Savigny, Das Obligationenrecht als Theil des heutigen römischen Rechts, 1851, S. 229. 转引自陈聪富:《连带债务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0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217页。而否定论的公平性似还不如赌博。在遵循公平游戏规则情况下的赌博,胜负得失具有随机性,但由哪一共同担保人承担责任则并非随机,而是随意。各担保人财产之多寡、执行之难易、与债权人关系之亲疏,皆可左右债权人之选择。依否定论,某一担保人是否最终承担全责,不是听天由命,而是听(债权)人由命。对于纯粹由偶然事件决定权利义务的情形,民法或者采取严格控制的立场(例如对射幸合同的限制),或者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最后解决方法(例如《商标法实施条例》第19条以抽签方式决定注册商标申请人)。对于随机事件尚且如此,何况对于公平性不及的债权人随意选择,岂能以此决定担保人终局责任的承担?
我国法亦不例外。〔28〕在《民法典》之前即有判决以公平原则为据,解释出代偿的担保人依法取得债权人对其他担保人的权利。参见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冀09民终7090号民事判决书。具言之,民法各项规范体现了公平理念的多重意涵,包括公平分担损失、利益平衡、不同事物不同对待(重者重之,轻者轻之)等。将共同担保置入此规范体系中对比观察,益可见否定论之不公。
在客观关联的共同侵权行为以及共同危险行为中,责任人之间无合意、无意思联络,何以有权相互追偿,唯有公平(以及道德风险论)可解。此类场景下的公平自有公平分担损失之意。行为人各具同等程度的可归责性,法律仍然给予先担责者分摊责任之机会。〔29〕比较法上的佐证是,“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第338条曾规定数个故意侵权行为人无权相互追偿,但“德国民法典第二草案”删除了该例外,理由在于该规定与现代法理念不符,因为使一个通过赔偿积极消除不法行为后果的侵权行为人比其他什么也不做的侵权行为人处于更不利境地是不公平的。参见杨代雄:《共同担保人的相互追偿权——兼论我国民法典分则相关规范的设计》,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第57页。在瑞士法上,法律明定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可追偿,旨在避免出现不公平的结果,追偿权遂有填补损害或矫正正义的功能。参见[瑞]海因茨·雷伊:《瑞士侵权责任法》(第4版),贺栩栩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09页。担保人相互不知时共同担保的利益状况有相似之处。否定论另以被追偿人丧失资力会导致不能追偿为由认为肯定论也难贯彻公平,〔30〕参见崔建远:《补论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不享有追偿权》,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1期,第7页。混淆了权利应否享有与权利能否实现,从权利未必能实现倒推出不应有权利,不能成立。
就利益平衡而言,追偿权或代位是保持各方当事人利益平衡的必要工具。债权人的选择自由是连带债务在外部关系上的主要特征,选择自由通常也意味着债权人的恣意,这正是连带债务对于债权人的主要实益,但却导致各债务人在对外责任承担上的畸轻畸重乃至全有全无,而追偿权正是对此种恣意的补偿,即在内部关系上避免因债权人恣意而对连带债务人造成不公平结果。追偿权可视作连带债务人因付出对外关系上严苛性之代价所应得的内部补偿。此种利益平衡在任何具有连带性(对外各负全责)的场合皆应存在,无论是人的连带、物的连带、人与物混合连带抑或所谓不真正连带债务(责任)。正如德国学说早已论证的,连带债务人对外各负全责,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责任(formelle Haftung),此种过度的责任仅是为了简化债权人的权利实现,对于连带债务人内部的负担平衡,只有实质上责任(materielle Haftung)方可具有决定意义(超出实质上责任的部分以追偿的方式由其他债务人分担),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形式上责任在内部关系上缺乏基础。〔31〕参见[德] 扬·费利克斯·霍夫曼:《区分性连带债务理论体系中的共同担保》,孙新宽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11页。只有承认追偿权,始得防止连带债务在最终结果上沦为赌博,即追偿权乃连带债务的真正本质之所在、法自然衡平原则之要求,其存在不应取决于偶然达成或未达成的当事人特约、具有偶然性的具体规定或者具有偶然性的空泛概念(诸如目的共同、同一层次性等)。〔32〕详见陈聪富:《连带债务之研究》,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1990年度硕士学位论文,第126-127、223-224页;张定军:《连带债务研究——以德国法为主要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3-164页。德国判例亦指出,由债权人的任意性或由哪一个担保人先承担责任的偶然事实决定担保人内部的终局责任承担是不公平的,故有必要将连带债务人追偿规定类推适用于混合共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以填补法律漏洞。〔33〕该判例的中译文,参见《担保人间的补偿义务》,吴奕锋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133页。而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亦承认各债务人得经由无因管理、不当得利、让与请求权甚至类推适用连带债务人追偿权规定等途径处理其追偿问题,可证明在不真正连带债务人内部亦应有一个合理分配其负担之机制,否则将导致因债权人偶然的选择即足以决定由哪一债务人终局担责之不合理结论,而此类追偿后果与连带债务人的追偿几乎并无二致,足证内部求偿关系实为连带债务(含不真正连带债务)本质上所应然。〔34〕参见王千维:《论可分债务、连带债务与不真正连带债务(下)》,载《中正大学法学集刊》第8期(2002年),第41、47页。
再对比保证和债务加入可发现否定论在公平性上会造成更大反差。总体而言,债务加入人的风险大于保证人,保证人受众多法定规则的保护,诸如检索抗辩权、保证期间、无障碍地主张债务人抗辩权,凡此皆为债务加入之所无。故德国通说认为,债务加入应以加入人有自己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为要件,而保证人无须有此利益,若第三人无此利益,无论其语言表达如何,概属保证。〔35〕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页;[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20页。我国学说与之类似:保证人就他人债务负从债务人责任,而债务加入人负共同债务人责任,盖其对债务履行于自己亦有利益;有疑义时,第三人有直接利益者,可认为系债务加入,否则推定为保证。〔36〕参见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502页。类似见解,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页。《担保制度解释》更将难以确定为债务加入或保证的承诺文件一律认定为保证(第36条第3款)。但否定论却使保证人反而比债务加入人更为不利,形成体系违反之结果。设甲对乙享有主债权,由丙提供抵押。甲另要求丁作保。丁如出具保证函,向甲担责后,乙丧失清偿能力的,在否定论之下,丁将承担全部损失。但丁若出具债务加入函,则可依《民法典》第519条第2款规定,在超过自己份额之范围内取得甲对乙与丙的权利,最终由丙丁双方分担损失(代位人有数人时应分担)。甚而,否定论会迫使无偿作保的第三人弃用保证而转用债务加入方式,以致法律为保护保证人所设之诸多特殊规则目的落空,而此类特殊规则或旨在保护保证人免于仓促缔约,或基于公平原则而对无偿提供保证之人给予优待。否定论对公平之伤害更增一层。或谓此乃第三人自由选择问题,然第三人本可从容选用保证以受保护,却被否定论扭曲了选择空间,被逼陷入两害相权之困境。
公平性还体现于担保制度对债务人和担保人双方利益的平衡。担保人终究是为债务人代偿债务或代负责任,故债务人一方应负终局责任。在债务人和部分共同担保人存在关联关系的场合,否定论的不公平性更为显著。例如甲是母公司,乙是子公司,无论是甲为乙提供担保抑或乙为甲提供担保,如果另一共同担保人丙担责后无权向甲或乙追偿,即会发生类同于“债务人脱责、担保人全责”的不公平结果。否定论提出的对策〔37〕参见吴光荣:《共同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以共同担保的再类型化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3期,第69-70页。于事无补。对于乙为甲提供担保的案型,否定论谓丙可申请执行甲对乙享有的股权,但如该股权已被质押或另有其他债权人查封在先,则丙只能徒呼奈何。又或甲对乙仅部分持股,则丙执行该股权的力度不如直接执行乙的全部资产。再者,若甲乙并无持股关系而仅有实际控制关系,则无股权可供丙受偿。对于甲为乙提供担保的案型,否定论谓丙有权向甲追偿,因为“母公司提供的担保实际上是债务人自己提供的担保”,存在无视公司人格的基本逻辑错误(单纯提供担保并非母子公司人格混同事由)。
五、道德风险论:分担否定论独具道德风险
(一)道德风险的不同样态
道德风险论同时涉及效率和公平面向,兹单独讨论。分担否定论极易诱发道德风险(不等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道德风险),从已有的讨论观之,道德风险可表现为购买债权、买通债权人、贿赂执行法官等形态。〔38〕参见贺剑:《走出共同担保人内部追偿的“公平”误区——〈物权法〉第176条的解释论》,载《法学》2017年第3期,第84页;王欣新:《〈民法典〉与破产法的衔接与协调》,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11页。道德风险亦为德国学者所提及。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页;[德]克劳斯·蒂特克:《保证人和土地债务担保人之间的追偿请求权——兼对联邦法院民再字第175号判决(BGH Urt. IX ZR 175/88)的评议》,胡强芝译,载王洪亮等主编:《中德私法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2页。其一,个别担保人向债权人购买债权,进而向其他共同担保人主张承担担保责任、收回购买成本,其他共同担保人全额担责后无权向其追偿,从而该个别担保人完美地避开否定论所致风险,其他共同担保人则承受全部风险。其二,个别担保人向债权人给予额外利益(同时可能向债权人提供其他共同保证人的财产线索以将“祸水”引向他人),换取债权人承诺不对己主张担保责任。其他共同担保人亦可能如此行事。债权人在收取各担保人的“贿赂”之后,仍可向未“行贿”的共同担保人主张承担全额担保责任,加上此前“受贿”所得,获取超过主债权的额外利益。债权人取得额外利益,也可能发生于前述收购债权的场合。在先下手为强的形势下,各个担保人均有动因溢价收购债权。例如,甲对乙享有100万元债权,有丙丁戊三人共同担保。丙愿意向甲出价110万元买取该债权,丁愿意出价120万元。只要最终买得债权的丙或丁能从后知后觉的戊处全额受偿,虽多付一二十万元,较之被甲索偿100万元,仍属划算。债权人取得额外利益,非因付出劳动,非因提供商品或服务,纯粹是利用法律制度的不当设计(采否定论)而巧取豪夺,既不符合交换正义的要求,又不具有经济效益上的改进,因而既不公平,又无效率。其三,担保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或将产生执行法官寻租的风险。执行法官可以选择性地执行任一担保人的财产,面临全额担责风险的担保人将不得不予利避害。若执行法官收受利益,有损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应受处分固不待言,唯执行法官原无动力为此,乃法律制度“诱人为贼”,是法律之误也!
否定论对道德风险论有所回应,但首先在价值判断上自相矛盾。个别担保人受让债权或“贿赂”债权人,方式有别,结果无异:自己不承担担保责任,而由其他担保人承担全部担保责任。对此结果,否定论一方面认为,如果是采取受让债权的方式,并未直接害及他人,其他担保人因此受害至多属于反射效果,故在道德方面无可指责,甚而是“极富智慧的法律运用”,但如采用贿赂债权人的方式,则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共同担保人的利益,应为无效。〔39〕参见崔建远:《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96-98页。个别担保人采取何种手段,仅事关该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安排,对其他共同担保人的影响殊无二致,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难以自圆其说。否定论转又认为担保人借助于债权转让转嫁担保责任系“不法目的”,〔40〕参见崔建远:《补论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不享有追偿权》,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1期,第10页。前后矛盾。
1.通过受让债权规避否定论规则
关于受让债权的道德风险,否定论认为即使肯认存在道德风险,一是其成立场合极为有限,二是肯定论与否定论在此方面各有利弊,并列出十种情形和五点理由。〔41〕参见崔建远:《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96-97页;同上注,崔建远文,第9-10页。其说皆有商榷余地。鉴于该说所述情形与理由存在重复之处,兹归纳辨析如下。
其一,否定论以双务之债举例,但设保债权以借款之债(单务之债)最为常见。即便在双务之债的场合,债权让与无须债务人同意,债权人并非必须以债权债务概括转移的方式为之。
其二,担保人受让债权,其目的即为取得债权,此目的无所谓不法与否。至于恶意串通损害其他担保人利益,在否定论立场之下亦难构成,因为依否定论,只要债权人选择主张其他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其他担保人即应终局承担全责,此并非加害于其他担保人之行为,其他担保人并未受有不法侵害,不过是承受担保权利实现之合法后果。
其三,在抵押、质押合同约定仅为特定债权人的债权提供担保时,债权人仍可转让其债权,而担保物权将依法自动转移,个别担保人借助于受让债权而要求其他共同担保人实际承担物上担保责任之目的不会落空。
其四,债务人破产时,债权人的债权仍可自由转让,所谓“破产债权须依破产程序处理、不得按照普通的民事方式转让”一说于法无据。
其五,在物上担保人取得债权的情形,若承认担保物权因与债权混同而消灭,由于混同为法定或依法理而得出的当然效果,并非人的行为所致,故所谓“个别担保人借助于混同制度消灭抵押权、质权,除去抵押人和出质人的身份,违反诚信原则,其他担保人有权予以抗辩”,完全超出了诚信原则的作用范围(诚信原则系规范人的行为而非法定效果)。如不承认担保债权因与债权混同而消灭,此时兼具债权人身份的个别担保人对自己财产享有担保物权,在现行法上无从实现该担保物权(既无法自己与自己订立折价协议,又无法以自己为被告或被申请人向法院起诉或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系法律上不能行使担保物权,而非怠于行使担保物权,故既无所谓“违反诚信原则”,又不能认为“有违担保法解释第38条第3款规定精神”,其他担保人无权以此为由主张抗辩。
其六,在其他担保人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情形,实际担责的担保人取代债权人的地位,可主张债权人代位权,请求其他担保人履行对债务人所负债务。但此乃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之功并受制于代位权制度之局限(例如债务人对其他担保人的债权未到期则无从行使),且无法适用于其他担保人对债务人无债务的情形。
其七,其他担保人依《民法典》第132条规定抗辩个别担保人滥用权利,亦难自洽。关于权利滥用之构成有主观说与客观说,前者是指以损害他人之目的行使权利,后者是指行使权利所得利益微小而对他人造成重大损害。债权人对某一共同担保人行使担保权利,难谓以损害他人之目的行使权利,亦难谓自己得小利致人受大害。无论该债权人是初始债权人还是继受取得人,皆是如此。况且,如认为某一担保人自己不担责而由其他共同担保人承担全责乃“损人利己、构成不法目的”,岂不正是否定论自身运用之结果?
其八,某担保人受让债权以免自己实际担责,亦不构成滥用权利。受让债权并非权利行使行为;受让后所主张者乃原债权,行使该债权本身并非滥用权利。
其九,金融机构转让债权受有某些限制,不排除其他转让债权可能性的存在,而包括担保制度在内的民法制度具有普适性,并非专为金融机构而设。
其十,该说认为,某担保人在受让债权后所提供的担保类似于债务人以自己财产为自己债务提供担保。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该担保人是享有主债权而非负担主债务,与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保根本不相类似。
2. “贿赂”债权人的道德风险
关于“压榨”“贿赂”的道德风险论,否定论的回应〔42〕参见崔建远:《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97-98页。亦均难成立。
其一,“贿赂”行为是在债权人和个别担保人之间转移财富,社会财富并不因之增加,不符合效率原则,此正是否定论造成的结果。
其二,现有法律手段无法阻止债权人获得并保有“贿赂”利益。个别担保人向债权人“行贿”以换取债权人不向自己主张担保责任,不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其他担保人利益,此与个别担保人受让债权以换取同样结果相当,前已述及。“贿赂债权人”系为描述现象所用的方便说法,并不等同于贿赂犯罪,刑法上无此罪名。个别担保人与债权人如此约定,系有效协议,在刑法上不构成犯罪,在民法上不构成不法行为,无从发生刑事制裁和民法上的无效制裁、收缴制裁(况且原《民法通则》所定民事制裁已被《民法典》废除)。〔43〕否定论认为原《合同法》第59条、原《民法总则》第157条后段可作为“贿赂”款被没收的根据。参见崔建远:《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98页。然而,原《民法总则》第157条后段“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并非独立的规范基础。原《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此所谓收归国家所有,显然是指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形;如系损害集体、第三人利益,则应返还集体、第三人。个别担保人“贿赂”债权人的,即便认为该行为损害第三人(其他共同担保人)利益,因该“贿赂”款并非由第三人给与,无所谓返还第三人,更不应收归国家所有。纵然认为此给与构成不当得利,因系个别担保人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债权人可不予返还(《民法典》第985条第3项)。
其三,退言之,即便“贿赂”行为构成恶意串通,双方也无主张无效的动因:如债权人主张无效,将失去所得利益;如给付人主张无效,债权人必不甘休,而径行要求该担保人承担全部担保责任,该担保人将因小失大。而其他担保人往往难以知悉或证明“贿赂”行为,无法主张其无效。
其四,其他共同担保人知道债权人和个别担保人之间有“贿赂”行为时,其他共同担保人本应承担全责,债权人主张其承担全责也并非“主张大于其权利的权益”,故其他共同担保人无从援用诚信原则以减轻自己所负担保责任、使债权人目的落空。如其他共同担保人不知有“贿赂”行为而实际担责,因其担责具有担保合同依据,并不构成非债清偿,无权依不当得利制度请求返还。
3.选择性地锁定个别担保人的风险
关于债权人或执行法官选择性地锁定某一担保人的问题,否定论亦回应乏力。〔44〕否定论参见崔建远:《补论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不享有追偿权》,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1期,第8-9页。否定论所设想的“自作主张设立担保者与债权人或执行法官串通,放弃抗辩、抵销权,而后向其他担保人全额追偿”无法实现。某一担保人放弃抗辩、抵销权,效力不及于其他担保人,其他担保人仍可援用既有的抗辩、抵销权。况且,债权人如欲“专坑”某一担保人,径行主张该担保人承担责任即可(否定论恰可助其一步到位使该担保人最终全额担责),何必舍近求远,用此迂回手段?否定论又认为肯定论所举之例只是“别有用心”之人“歪用”否定论之结果。但正是否定论使债权人或执行法官的选择自由超出了应有的边界,产生滥用风险。何况采取执行措施必分先后,执行法官纵无寻租或滥用行为,亦不可能同时执行各担保人的财产,则因时间上的偶然性,必然发生先被执行者全额担责、其余担保人侥幸逃脱的结果。否定论亦知其患,遂建议“确立合理执行/便宜执行规则及其制裁后果以限制不当执行”,但此举实乃将内部问题外化、后端问题前移,此种欠缺可操作性的模糊规则将额外增加执行法官的被问责风险(何谓合理、便宜并非便于判断)、有碍执行效率,其根本缺陷在于不当限制了债权人的选择自由。执行法官有权执行任一担保人的财产,此系债权人权利行使自由在执行程序中的反映。今否定论为补救其在连带债务内部关系上自造的弊病,而不惜扭曲连带债务外部关系(为治对担保人保护不足之症,开出削减债权人权益之方),何异于头痛医脚、剜肉补疮乎?
以上种种道德风险皆源于“内外混淆”,即债权人的权利行使自由超出外部关系范围而侵入担保人内部关系。只要不能使内外关系各归其位,债权人逐利、担保人避害的各种操作必将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既有文献所论及的手法不过冰山一角而已。
(二)否定论所设对策之不足
《担保制度解释》第14条对担保人受让债权的情形特设规范,意在防范否定论所生道德风险,但并不成功。首先,该条将担保人受让债权定性为承担担保责任之行为,无视当事人意思,有违法理。〔45〕在罗马法上,为了实现担保人之间的追偿,法律将承担担保责任拟制为债权买卖;而我国相关司法解释为了否定担保人之间的追偿,却将债权买卖拟制为承担担保责任。其次,该条仅指向担保人受让债权的行为,担保人完全可由他人出面受让债权以规避之,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亦可通过受让债权以外的方式实现类似目的。2019年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该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第14条曾有第3款,规定担保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近亲属等受让债权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正式文本中未保留此款,但即便保留亦无济于事:担保人可先让非关联人收购债权,再向其他担保人全额行使权利,其他担保人通常难以证明此种行为系规避该条之行为,而债权人早已收款而退,纵然知情,亦无动力“揭发”。该条可谓治丝益棼。最后,道德风险不限于此,也可以表现为“贿赂”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寻租等,此非该条适用范围。《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所造漏洞无法堵塞。否定论亦承认道德风险客观存在,但又认为此系担保人应当预测并自行防范的交易风险,不宜由司法解释作出如何防范的选择。〔46〕参见吴光荣:《共同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以共同担保的再类型化为中心》,载《法律适用》2021年第3期,第69页。姑且不论其所谓当事人自主防范的途径或者欠缺可行性(分别担保时担保人无法互约为连带共同担保)、或者徒增交易成本(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其说本身便难以立足:正是新解释引发了道德风险(原《担保法》时代无此风险),却不加尽力防范,反推卸责任于民事主体,岂有此理?况且,倘若果真坚定认为此风险应由担保人自负,则又何必设计《担保制度解释》第14条?
(三)肯定论并无道德风险
否定论另外提出肯定论带来三种道德风险,〔47〕参见崔建远:《混合共同担保人相互间无追偿权论》,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98页。亦属可议。其一,债权人与个别担保人互负债务、予以抵销,因有追偿权制度,个别担保人又向其他共同担保人追偿,否定论认为此系个别担保人双重获利。但此现象乃追偿制度的应有之义,并非个别债务人的双重获利,而是多数债务人之间的合理分担。个别债务人以其对债权人的债权为抵销,在经济效果上等同于自己另行给付而为清偿,发生其他连带债务人同免其责之效果,在内部关系上当然应由全体债务人分别承受,其结果是数人按比例分担,先为抵销的债务人只是将超出自己份额的部分转由他人承担,并未受有重复利益。若谓此种现象为双重获利,岂非在所有关于追偿或连带债务的关系中均存“双重获利”,其论同现行法体系与法理皆有不合。其二,债务人和个别担保人为关联企业,个别担保人担责后以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为由向其他担保人追偿,并不构成非法获利。而且,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其他担保人原本即面临全额担责的风险。若债权人先向其他担保人主张承担责任,在否定论之下,其他担保人无权向与债务人有关联关系的个别担保人追偿,岂非诱发更大的道德风险?其三,否定论认为,债权人和个别担保人存在系列交易,依其内部相互制约关系,该担保人“宜不实际承担担保责任”,但因追偿权制度的存在,被其他担保人追偿时却实际承担责任。然则,既已订立担保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即为担保人愿意接受且理应接受的后果,如不愿接受此后果,自可另订他种合同(例如不构成担保的增信契约)或对风险另作安排(例如转由对方负担或另寻反担保)。焉可虚与委蛇,甚至以此手段引诱其他人提供共同担保?
六、结语
如同民法规范在外在体系上应圆融无碍一样,民法的内在价值也应构成一个兼容、和谐的整体。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根本原则,本身蕴含效率价值,同时与公平价值兼容。
共同担保人责任分担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连带债务一般规则在担保领域的投射。按份债务推定原则是多数立法例的共识,本身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法定连带债务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偏离,故须同步承认连带债务人的内部分担,以此最终回归意思自治原则。一般性的追偿权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和案件处理成本,也是公平理念的应有之义。作为特别规则的共同担保既然具备法定的连带性,并无理由偏离连带债务一般规则。尤其考虑到担保合同的无偿性,担保人的法律待遇至少不应劣于一般情形下连带债务人既有的法律待遇。
否定论依赖于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而创造出不真正连带共同担保之概念,但该理论在法教义学上缺乏牢固基础,并因实质理据上的不妥当性而式微。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往往倾向于否定债务人内部分担,形成因债权人的任意选择即可决定债务人内部责任全有全无的不合理结果。凡不真正连带债务理论所固有之缺陷,必与不真正连带共同担保理论同在。我国《民法典》上的连带债务一般规则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连带债务人内部份额规范可覆盖数人各有分担部分和一人承担终局责任等各种情形。〔48〕《民法典》第519条第1款所称连带债务人之间份额视为相同,系解释规则,其前提是“份额难以确定”;依约或依法可确定某一债务人应负终局责任的(如《民法典》第1203条第2款),不适用之。从而,不真正连带债务的内部效力,即完全被该条所涵括。因此,不真正连带债务在我国法上并无存在空间。以此为据的不真正连带共同担保理论同样无法立足。
——基于《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13条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