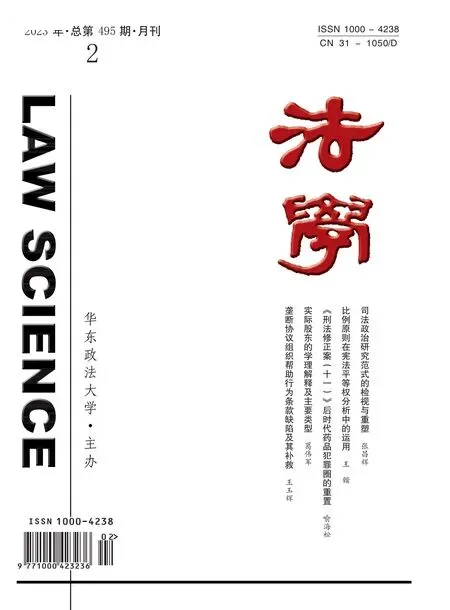论核废水排入海洋的环境损害赔偿
●王 慧
日本福岛核废水排入海洋是当下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议题,其是自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后全球最严重的核电事故,不仅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潜在损害难以估量,而且危及国际公共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的切身利益。如何有效应对核废水排入海洋对海洋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现实而紧迫的问题。针对可能引发的环境损害赔偿问题,如何准确辨别其国际法依据,如何解决诉讼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障碍,未来如何完善国际法制度来有效解决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都需要理论的回应。
近年来,国际环境法判例逐渐增加,其中跨界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成案不在少数。通过系统梳理这些成案发现,跨界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成案的争点主要聚焦在诉讼的国际法依据、适格的诉讼主体、诉讼场所的选择、举证责任的分配、损害的救济方法等方面,这些问题同样也会困扰核废水排入海洋的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深入研究成案或许能为如何针对核废水排入海洋进行海洋环境损害索赔提供思路和有益指引。
一、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国际法依据
从国际法律规范的角度看,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主要涉及国际核能法和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下分述之。
(一)国际核能法视角下的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
核能及其废物处置涉及各个层面的利益,既有安全的考虑,也有健康的思考,更有环境风险的顾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海洋常常是核废料的主要归宿地,但在当下,在海洋里处置核废物越来越被人们反对,南太平洋等诸多海域已禁止核废物入海。从国际核能法的基本规定看,核废水排入海洋是否合法并无具体的规定,但禁止向海洋人为排入核废物已是多数国家和区域的基本立场,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1〕1972年的《防止因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而引起海洋污染的公约》(以下简称《伦敦公约》)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或物质,《伦敦议定书》对相关禁止作了详细规定。核废水排入海洋虽是海洋环境陆源污染行为,无法直接适用《伦敦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规定,但从伦敦公约体系中不难推断出国际社会对核废物入海的反对态度。See Philippe Sands, Jacqueline Peel, Adriana Fabra,Ruth MacKenzi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563.
有关核能使用和发展方面的国际法是确认核废水排入海洋行为法律责任的重要法律渊源。〔2〕关于国际核能法的体系及其发展,See Kus, S., International Nuclear Law in the 25 Years Between Chernobyl and Fukushima and Beyond.., 87 Nuclear L. Bull. 7 (2011).核废水排入海洋所涉及的核能国际规范体系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与核能使用和发展相关的国际条约体系,包括《关于核能领域中第三方责任的巴黎公约》(Paris OECD Convention on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 the Field of Nuclear Energy)、《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s)、《核安全公约》(Convention on Nuclear Safety)等;〔3〕在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后,《核安全公约》缔约方外交大会于2015年2月9日通过了《维也纳核安全宣言》(Vienna Declaration on Nuclear Safety),向全世界展现了缔约方对于核安全的承诺。二是涉及核能使用和发展的国际标准和措施,典型代表是《国际原子能安全法则——核设施安全》(IAEA Safety Fundamentals on the Safety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二)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视角下的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
国际社会对海洋环境的保护可追溯至1926年针对可航水域石油污染现象召开的会议(Preliminary Conference on Oil Pollution of Navigable Waters),其时对海洋环境损害问题的关注点仅限于石油污染导致的损害。随着全球海洋环境保护议题的不断拓展,以及各国对海洋环境保护重视度的不断提高,〔4〕全球第一个海洋环境保护公约是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公约。See Mark Zacharias, Jeff Ardron, Marine Policy, Routledge,2014, p. 146.今天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已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的庞大体系。
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体系涉及的国际法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直接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法,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国际船舶压载水及沉积物控制与管理公约》等为代表;第二类为间接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它们虽非专门的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但均将海洋环境及资源保护作为公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为代表;第三类为涉及国际海洋环境保护的非强制性协定,主要有联合国环境署的全球行动计划(GPA)、〔5〕See UNEP Global Progamme of Ac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Land-Based Activities(GPA).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行动计划(Plans of Action)、联合国大会决议以及区域海洋环境保护计划(Regional Seas)。其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既有海洋环境保护的原则性声明,也有具体的制度设计,是其他国际海洋环境保护规范的基础,鉴于此,有关海洋环境的保护将围绕公约的相关规定展开。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4)条规定的海洋环境污染几乎覆盖了海洋环境污染的所有类型,并对不同类型的海洋环境污染情形分别给予了差别化规定,如第207、213条规定了各国在陆源污染防治方面的事宜,第210、216条就海洋倾倒污染海洋环境事项作了规定。由于不同污染类型适用不同的法律,所以如何准确识别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污染的类型便成为正确适用公约海洋环境保护条款的前提。从公约对陆源海洋污染和海洋倾倒的界定看,海洋倾倒指的是通过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设施在海上处理废弃物或其他物质,核废水海洋排放行为显然不能纳入该范畴,所以将其定性为海洋倾倒行为并不妥适,而应定位为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因为该行为更符合公约对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概念的界定。但问题在于,由于公约对陆源海洋环境污染的规定过于简单,所以在解释和适用陆源海洋环境污染条款时还有必要进一步参考1995年华盛顿宣言、GPA和21世纪议程第17章对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相关规定。
(三)国际环境法成案视角下的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
对于核废水排入海洋的环境损害赔偿议题,除了需了解前述诸多国际法律规范外,还需认真研判与此密切相关的国际环境法成案。
对于跨国环境损害行为,“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是讨论相关法律问题的起点。〔6〕See Alfred P. Rubin, Pollution by Analogy: The Trail Smelter Arbitration, 50 Or. L. Rev. 259, 259(1971).作为国际法历史上首例跨国界环境责任案,其为跨国环境损害创设了一条影响深远的原则——“任何一国不得对邻国造成跨界损害”。1996年,国际法院就《威胁使用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Legality of the Threat of Use or Use Nuclear Weapons)所发布的咨询意见中,对环境损害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指出“环境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代表了生动的空间、生活的品质以及人类(包括尚未出生者)的健康。各国普遍有义务确保本国管辖或控制区域内的行为尊重别国或本国控制区外的环境,这已成为有关环境保护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以来,国际法院的态度开始从对跨国环境损害赔偿的质疑转向支持。在2018年“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以下简称“Costa Rica案”)中,〔7〕See ICJ General List No. 150(2 February 2018). “Costa Rica案”是国际法院第一次解决环境损害问题的案件,也是国际法院第三次授予赔偿(award damages)的案件,在国际环境法中的意义重大。另外两个授予赔偿的案件分别是Corfu Channel(UK v. Alb),Judgement, 1949 ICJ Rep. 4(April 9)和AhmadouSadio Diallo(Guinea v. Dem. Rep. Congo), Compensation, Judgement, 2012 ICJ Rep. 324(June 19).国际法院第一次允许一国对他国遭受的环境损害进行赔偿,并且指出损害环境会减损其为人类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在国际法体系下环境损害应当得到赔偿。
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国际海洋法法庭作出的涉及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判决对于我们研究核废水排入海洋的环境损害赔偿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如何保护海洋环境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超级难题,有关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国际法规范较为庞杂,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直接规范缔约国海洋环境保护权利义务的国际法规范外,还包括其他与海洋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国际法规范,典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其已成为国际海洋法法庭要求各国承担海洋环境保护义务的重要依据。〔8〕《生物多样性公约》虽非基于保护海洋环境目的而创立,但其在海洋环境保护中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解释和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经常会援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相关规定,可见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核废水排入海洋对相关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在提起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时同样需考虑《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作用。
二、海洋环境损害赔偿中的程序法问题
研究国际环境法成案,特别是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国际法成案可以发现,适格原告、起诉机构、科学证据认定等程序法问题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讨论焦点。
(一)适格原告
在国际法理论上,针对一国境内的行为所导致的环境损害有权提出索赔的原告大致有国家、个人、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组织〔9〕国际组织虽理论上可成为原告,但鉴于实践中相关案件鲜见,故本文对其是否能成为适格原告不作讨论。,那么对于核废水排入海洋所致的海洋环境损害,谁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1.国家。国家是执行国际环境法及其规则的主要担当者,能提起跨国环境损害赔偿之诉的是遭受环境损害的国家。虽然依据国际法委员会(ILC)国家责任条款(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第48条,没有遭受环境损害的国家有时也可以提起诉讼,但是需要符合“被诉国家的环境损害行为必须达到违反了集体义务的程度”这一严格条件。〔10〕See Philippe Sands, Jacqueline Peel, Adriana Fabra, Ruth MacKenzi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44.依照国际法规范及实践,国家是提起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适格主体。
2.个人。国家之外的主体通常无权起诉一个主权国家,除了例外情形(在国际人权保护法领域,个人可以针对国家提起诉讼)。〔11〕同上注,第155页。需注意的是,环境保护与人权已经成为紧密相连且相互影响的两大议题,联合国决议将环境保护纳入人权保护体系,使环境保护成为国际人权法的组成部分。〔12〕See The Environment and Human Rights(State Obligation in Relation to the Environ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Protection and Gurantee of the Rights to Life and to Personal Integrity-Interpretaiton and Scope of Articles 4(1) and 5(1)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OC-23/17, Inter-Am.Ct.H.R.(Ser.A) No. 23(November 15, 2017).在此背景下,个人通过人权诉讼来实现环境损害赔偿有理论上的可能。〔13〕欧盟法院已明确承认环境议题与人权议题的关联性。See Lopez Ostra v. Spain(1995) 20 EHRR 277(Judgment 41/1993/436/515 of 9 December 1994).但是,针对核废水排入海洋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对于那些将环境保护纳入人权公约持保留态度的国家而言,个人通过国际人权法起诉会面临障碍。
3. NGO。在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NGO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诸多国际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诞生得益于NGO的不懈努力。在国际环境治理及其法律制度的演进中,大致有6种NGO发挥了积极作用:科学界、环保NGOs、私人公司、法律机构和个人(主要通过人权法实现环境保护)。〔14〕See Philippe Sands, Jacqueline Peel, Adriana Fabra, Ruth MacKenzi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86.尽管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发展受到NGO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但国际法并未赋予其起诉环境损害国的权利,其作用的发挥只限于协助受害国提起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二)起诉机构
针对核废水排入海洋所致的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如何选择起诉机构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以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为例,原告既可以选择起诉东京电力公司(TEPCO),也可以选择起诉日本政府。如果选择起诉TEPCO,原告通常是权益遭受损害的主体,由于日本没有参加核损害赔偿国际公约,所以相关诉讼只能在被告所在地法院(日本法院)、核事故发生地法院(日本法院)、原告所在国法院(原告所在地法院)之间进行选择。虽然日本的核能损害赔偿法规定了较为完备的赔偿责任制度,但鉴于法院长期对核电产业所持的支持态度,在日本的法院起诉TEPCO无疑障碍重重。〔15〕See Matsui, S., T-rex, Jurassic Park and Nuclear Power: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the Courts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42(1) Wm. & Mary Envtl. L. & Pol’y Rev. 145 (2017).在原告所在国的法院起诉TEPCO虽理论上可行,但碍于诉讼成本过高,一般民众通常无力承担。是故,选择遭受海洋环境损害的国家起诉海洋环境损害行为发生地的国家是更为现实可行的方案。〔16〕日本的核电历来有国家化的传统,在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防止东京电力公司破产。
在国际法实践中,针对核事故导致的索赔曾有成立专门仲裁庭的先例。〔17〕See David D. Caron, Harry N. Scheiber, The Oceans in the Nuclear Age, Brill/Nijhoff, 2014, p. 49.不过,鉴于日本政府对福岛核废水排入海洋所展现的态度及一贯立场,创设专门仲裁庭的几率不大。基于此,下面主要探讨非仲裁背景下的起诉机构问题。
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WTO争端解决机制和区域人权协定创设的法庭均处理过跨国环境损害赔偿事宜。对国际法院而言,一方面其通过作出裁决直接影响跨国环境损害索赔法制的发展,如“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共和国案”(以下简称“Nicaragua案”);〔18〕See Yoshifumi Tanaka, Costa Rica v. Nicaragua and Nicaragua v. Costa Rica: Some Reflecitons on the Obligation to Conduct a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26 Rev. Eur. Comp. & Int’l Envtl. L. 91(2017).另一方面又通过提供咨询报告(advisory opinions)间接影响国际环境损害赔偿法制的发展,如针对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议题发布的咨询报告。〔19〕See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1996] ICJ Rep. 242[29].对国际海洋法法庭而言,其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贡献功不可没,先后裁决了大量的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案件,表现出对海洋环境保护较为友好的态度,推动了国际海洋环境法的不断发展。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贸易纠纷争端解决机制在环境与贸易纠纷中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更值关注的是,近年来,区域人权协定创设的法庭也开始关注国际环境问题,其代表欧盟人权法院一方面允许个人、NGO等以人权受害者的身份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另一方面还将公民享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视为公民的基本人权。
理论上说,提起核废水排入海洋导致的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选择上述各种争端解决机制均可以,但综合各争端解决机制背后的政治现实与实际运作,笔者认为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核废水海洋环境损害赔偿之诉最为合理。首先,WTO争端解决机制当下已“名存实亡”,显然已不是提起核废水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理想机构。其次,通过人权法院起诉核废水排入海洋行为并主张相应的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这与各国在国际人权法领域的主张和立场密切相关,不易成功。最后,国际法院虽近年对生态环境保护态度较为友好,但在国际法院提起核废水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会面临如下障碍:(1)管辖权较为有限,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2)国际法院的裁判相对保守,通常不会针对海洋环境损害赋予临时措施;(3)即便存有海洋环境损害风险,国际法院还需要斟酌各种要素、获得各种信息、借助专家证据,使诉讼不易推进。〔20〕See Cymie R. Payn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 105 Am. J. Int’l L. 94, 100(2011).
(三)科学证据认定
环境问题及其司法化历来受困于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21〕参见郑少华、王慧:《环境法的定位及其法典化》,载《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第133页。国际环境损害赔偿案件通常因涉及科学判断问题而争论不断。〔22〕See Lucas Carios Lima, The Debate on the Use of Experts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 Inquiry through Sociological Lenses, 34 Temp. Int’l & Comp. L. J. 253, 259(2020).国际法院环境损害赔偿成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如何看待某一问题的风向标,可以此为参照展开进一步讨论。
国际法院法官在“阿根廷诉乌拉圭案”(Argentina v. Uruguay ,以下简称“Pulp案”〔23〕关于该案的分析,参见那力:《“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判决在环境法上的意义》,载《法学》2013年第3期,第79-86页。)中认为,根据国际习惯法的要求,每个国家有义务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发生在本国境内的行为不会对他国的环境造成损害。但是,判断一国行为是否导致了他国的环境遭受损害,需要借助科学证据对损害是否发生加以证明。由于国际法院法官通常缺乏案件事实认定所需的科学知识背景,所以对其是否有能力解决科学证据问题争议较大。为了解决科学证据的可靠性问题,通常法官会依赖专家证据来解决相关案件涉及的科学证据认定问题,但问题是,专家向国际法院提供技术证据时无需接受《国际法院规约》(ICJ Statute)第51条和《法院规则》(Rules of Court)第63~65条所规定的交叉询问,这有违证据规则的要求。而且,国际法院允许原告国和被告国均提交专家证据来助其裁决的做法,在原告国与被告国提交的科学证据不一致(几乎所有案件的科学证据均不一致)时,法院对相关事项的判断便会陷入迷茫。所以,尽管《国际法院规约》第50条规定国际法院可以寻求专家支持,但实践中其很少借助非当事方外的专家来帮助解决纠纷。〔24〕See Donald K. Anton, Case Concerning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 (Judgement) [2010] ICJ Rep. (20 April 2010), 17 Austl. Int’l L. J. 213, 214(2010).
即便如此,国际法院在处理跨国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积累的有益经验仍值得肯定。第一,对专家意见仅是合理参考。如在“Pulp案”中,专家意见成了国际法院裁决的重要参考标准,但在“Costa Rica案”中却未使用专家意见。第二,提出了判断是否存在重大损害风险的标准。如在“Nicaragua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判断是否存在重大跨界损害风险需要考虑项目的本质、规模及项目实施的背景,但对何为“重大损害”却未规定具体的参考标准,〔25〕之所以不明确界定“重大损害”的内涵与外延,一是何为“重大损害”涉及的科学认知本身难以界定;二是当案件事实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时,最好的处理方式便是确保相关决策具有适应性。See Jacob Katz Cogan,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Costa Rica v. Nicaragua); Constr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Nicaragua v. Costa Rica), 110 Am. J. Int’l L 320, 326(2016).这容易导致原告国无法事前充分且有效地准备科学证据。
三、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实体法问题
实体法问题主要涉及被诉国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下承担何种法律义务,其行为是否违反了相应的国际法义务。从国际法规范上看,《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缔约国承担的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有环境损害预防义务、环境影响评估义务、环境保护合作义务等。从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成案看,相关义务的解释及其适用主要围绕一国是否履行了“恪尽职守”(due diligence)义务展开,此义务最早在“Pulp案”中被提出,该案法官指出判断一国是否“恪尽职守”主要涉及三大事项:(1)一国在从事可能影响他国生态环境的行为前,应当确定相关行为是否存在重大的跨界环境损害(significant transboundary harm)风险;(2)如果一国初步判断发现相关行为存在重大的跨界环境损害风险,那么该国有义务按照本国法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IA);(3)如果EIA显示该国的行为确实存在重大的跨界环境损害风险,那么需要通知潜在的受影响国家,并同它们认真进行协商。〔26〕See Jacob Katz Cogan, Constr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 (Nicaragua v. Costa Rica), 110 Am. J.Int’l L 320, 323(2016).在随后的“Costa Rica案”中,国际法院对“恪尽职守”进一步作出了细化,详细说明了风险确定、风险评估、通知义务、协商义务等事项。〔27〕See Jacob Katz Cogan, Constr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Nicaragua v. Costa Rica), 110 Am. J.Int’l L 320, 325(2016).
(一)国家的风险评估义务
一国对具有跨国环境影响的行为进行评估是国家承担的国际环境法义务,国际法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如《跨国界环境影响评价公约》(Convention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a Transboundary Context, 以下简称《埃斯波公约》)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7年颁布的《环评目标和原则》(Goals and Principl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对跨界环境影响评价有专门规定,国际法委员会(ILC)在2001年发布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的越境损害的条款草案》(Draft Articles on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Harm from Hazardous Activities)则进一步重申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预防跨界环境损害方面的重要性及其应当遵守的法律程序和准则。〔28〕See Text of the Draft Articles on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Harm from Hazardous Activies with Commentaries There to.Arts.7-9, in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on the Work of Its Fifty-Third Session, 56 UN GAOR Supp. No, at 377, 402-12,UN Doc. A/56/10(2001).
在国际环境法实践中,国际法院在“Pulp案”中首次提出EIA是国际习惯法,其可以保护环境免遭跨界污染损害。在该案中,由于当时的国际法对EIA的本质、范围和内容缺乏细致的规定,法院有关EIA的裁决采取了一种制度进化的解释方法。〔29〕See Donald K. Anton, Case Concerning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Judgement) [2010] ICJ Rep. (20 April 2010), 17 Austl. Int’l L. J. 213, 214(2010).“Costa Rica案”的裁决使EIA的发展更进一步,解决了其过去缺乏标准的问题:各国如何实施EIAs并开展通知手段。
综合国际环境法上有关EIA的成案看,一国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下所承担的风险评估义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第一,存在环境损害风险时需进行环评。在“Pulp案”中,国际法院指出,各国有义务采取各种措施,确保避免自己管辖或控制区域发生的行为对其他国家的环境造成重大损害。若一国的行为存在损害他国环境的风险,就必须进行环评,在各国共享环境资源的情况下EIA尤为重要。〔30〕See ICJ 20 April 2010,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 [2010] ICJ Rep.14, para. 104.同时还强调,一国即便不是EIA相关公约的缔约国,其同样有义务按照国内法的规定实施EIA。环评义务要求相关国家必须在项目实施前进行,对跨国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的理解应当采取广义的解释立场,不仅指承担该义务的国家需要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而且要求相关国家在事后不断对相关行为展开监督和管理。
第二,环评的基本内容。国际环境法成案虽支持环评,但法官对环评并未提出统一的要求,导致其在不同案件中的呈现会有所差异。在“Pulp案”中,法官指出,每个国家可根据本国国内法来决定环评,评估相关项目的本质和范围,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可能影响。在“Costa Rica案”中,法官对环评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说明,认为合理开展跨境环境影响评估需考虑环境影响行为的本质、规模大小及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等因素。
第三,环评的公告和咨询制度。各国对EIA结果进行公告是重要的国际环境法义务,对此并无争议,但对一国开展环评时是否要咨询相关利害关系人则争议较大。虽然《埃斯波公约》等公约强调跨国环评应当咨询公众,但是国际法院未将咨询公众视为一国履行环评义务的组成部分,即一国没有国际法上的义务来咨询潜在的受影响人。〔31〕See Cymie R. Payn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 105 Am. J. Int’l L. 94, 100(2011).在国际法院看来,虽然潜在的受影响公众无权参与环评程序,但是受影响公众所在地的国家可代替他们维护环境权益。
正如审理“Costa Rica案”的法官所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是国际法上‘恪尽职守’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必须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以防止跨国环境损害行为的发生。”〔32〕See ICJ 20 April 2010,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 [2010] ICJ Rep.14.而从国际原子能组织及日本政府披露的相关信息看,日本针对福岛核废水排入海洋实施了环境影响评估,但相关评估是否做到了“恪尽职守”尚待进一步证明。
(二)风险通知与合作应对义务
根据国际环境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的规定,一国开展的环评如表明某一行为存在重大跨国环境风险,计划实施这一行为的国家必须诚心诚意地通知潜在的受影响国,并同相关国家认真协商确定合理措施来预防或减缓环境损害风险。之所以强调国家的风险通知义务,是因为通知潜在受影响国家有助于该国事先采取预防措施来应对环境损害风险。〔33〕See Donald K. Anton, Case Concerning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 (Argentina v Uruguay) (Judgement) [2010] ICJ Rep. (20 April 2010), 17 Austl. Int’l L. J. 213, 216(2010).在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审理的环境法成案中,法官将风险通知义务视为判断一国是否“恪尽职守”的重要标准。〔34〕需注意的是,一国承担的通知义务并非仅出现在环评确定存在生态环境损害后,有时在开展EIA时也存在通知潜在受影响国家的可能,因为在环境影响评估阶段亦不乏需要各国进行合作的情形。
一旦一国的行为经环评后认定存在重大环境损害风险,打算实施相关行为的国家除了需通知潜在的受影响国家外,还需同潜在的受影响国家积极合作来共同应对风险。国际法院在裁判跨国环境纠纷案件时,经常强调合作应对风险是各国承担的国际法义务,〔35〕See Cymie R. Payne, Pulp Mills on the River Uruguay(Argentina v. Uruguay), 105 Am. J. Int’l L. 94, 97(2011).并对国家的合作义务予以细化。在“爱尔兰诉英国案”(MOX Plant)中,〔36〕关于该案的案情说明,参见程保志:《从MOX核燃料厂争端看欧洲法院专属管辖权的扩张》,载《法学》2008年第4期,第109-110页。法官认为爱尔兰因没有分享环境影响信息违反了国际合作义务。〔37〕See P. Chandreasekhara Rao, Philippe Gauiter,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Elgar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2019, p. 324.在“南方金枪鱼案”(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中,〔38〕See Southern Bluefin Tuna Case(Austl. and N. Z. v. Japan), Provisional Measures Order(ITLOS), August 27, 1999.法官强调相关国家有合作保护巡回鱼类和生物资源的义务。在“马来西亚诉新加坡围海造地案”(Land Reclamation Case)中, 法官甚至认为基于强化合作的需要相关国家应当建立独立的专家组。通过这些环境法成案的不断推动,国家承担的合作义务既要求各国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又要求导致环境损害风险的国家创设相应的赔偿责任体制确保受害人得到补偿。〔39〕See David D. Caron, Harry N. Scheiber, Bringing New Law to Ocean Water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 p. 359.
虽然导致环境损害风险的国家及时通知潜在受影响国家被视为是预防跨国海洋环境损害发生或扩大的有效手段,但国际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只有重大环境损害风险符合EIA要求时,实施相关行为的国家才负有通知潜在受影响国家的义务。于生态环境保护而言,这种将通知局限于事后通知的做法极其不幸,因为只有事前通知才更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40〕See Jacob Katz Cogan,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Costa Rica v. Nicaragua);Constrction of a Road in Costa Rica along the San Juan River(Nicaragua v. Costa Rica), 110 Am. J. Int’l L 320, 325(2016).
(三)风险预防义务
尽管一国是否进行EIA是判断其是否“恪尽职守”的重要标准,但其本身在应对跨国环境风险时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EIA无法决定项目的未来走向,即一国实施EIA行为仅是形式主义——借环评掩盖行为的不当。第二,根据国际法院的要求,每个国家进行EIA时需先解决其行为是否存在导致重大跨国环境损害的风险,但何为“重大跨境环境损害风险”的判断主观性较强,一国的主观臆断可能会致其根本无需实施EIA。
鉴于此,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处理跨国环境损害问题需纳入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法院的努力下,风险预防义务成为一国在国际环境法下承担的重要义务。早在“科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便指出,风险预防是一项重要的国际习惯法,〔41〕See Corfu Channel(United Kingdom v. Albania), Merits, Judgement [1949] ICJ Rep. [22].各国应当预防自己的行为对他国造成伤害。在1995年的“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New Zealand v. France)中,法官再次强调了该原则,甚至认为国际法院据此可以颁发禁止令。在1995年的“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案”(Gabcikovo-Nagymaros)中,〔42〕See the Gabcikovo-Nagymaros Project(Hung. v. Slovak.), 1997 I. C. J. 7(Sept. 25).法官认为不确定的环境损害结果足以要求相关国家采取措施预防损害风险,这种立场体现了风险预防原则的基本精神。“Pulp案”是风险预防原则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该案中国际法院的多数意见第一次明确确立了风险预防原则的地位。国际海洋法法庭同样是风险预防原则的支持者,其对该原则的欢迎在“南方金枪鱼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该案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风险预防原则为依据起诉日本,国际海洋法法庭基于该原则要求日本限制其违法行为。
毋庸置疑,风险预防原则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其也存在争议。〔43〕See Daniel Kazhdan, Precautionary Pulp: Pulp Mills and the Evolving Dispute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over the Reach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38 Ecology. L. Q. 527, 529(2011).第一,该原则缺乏被大家普遍接受的清晰内涵,导致个案适用中差别较大。第二,在该原则的适用过程中,风险的不确定程度、环境损害的幅度及应对风险所需采取的措施均争议较大。第三,适用该原则所需证明的损害水平存在分歧,有法官认为环境损害风险必须严重且不可挽回时才能适用该原则,有法官认为只要大家对环境损害予以关注便应当适用该原则。第四,即便存在环境损害风险,谁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亦有争议,有法官认为应由提出索赔的国家承担举证责任,有法官认为应由被索赔国家承担举证责任。
那么,何种情况下可以适用风险预防原则?适用该原则的过程中由谁承担举证责任?考察国际环境法成案可以发现适用的线索。第一,该原则主要适用于具有潜在严重危害后果的环境事件,因为相关事件通常具有持久性、有毒性、严重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第二,必须有一定的科学证据表明环境损害有发生的可能性,否则不得使用。第三,必须能够确定环境污染的源头,否则不得要求一国为难以确定源头的环境污染承担风险预防义务。就举证责任而言,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时,人们通常认为法院应当降低环境损害的证明标准,甚至主张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44〕预防原则强调即便存在科学不确定性,也应当针对环境损害风险采用预防措施。See Arie Trouwborst, Precautionary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 Brill, 2006.国际法院倾向于适用风险预防原则不能降低原告的举证责任,且在“Pulp案”中对此作了说明:〔45〕See Daniel Kazhdan, Precautionary Pulp: Pulp Mills and the Evolving Dispute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over the Reach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38 Ecology. L. Q. 527, 528(2011).风险预防原则虽可作为条约解释的参考因素,但其未改变传统的举证责任规则,环境损害风险不能降低损害证明标准。〔46〕对国际法院如此行事的解释是,其不希望案件过多地进入司法程序,如果降低举证责任可能会导致大量案件进入国际法院,使其在国际环境纠纷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国际法院本身并无力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无法强制执行相关裁决结果,其裁决结果的执行由联合国负责。相较于保守的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对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则较为大胆,其基于风险预防原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未来甚至有望将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从原告转向被告。
四、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计算
依据《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和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21号案,〔47〕See Request for Advisory Opomsopm Submitted by the Sub-Regional Fisheries Commission, Advisory Opinion, 2 April 2015,ITLOS Reports 2015.每个国家需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承担国际法责任。〔48〕See Philippe Sands, Jacqueline Peel, Adriana Fabra, Ruth Mackenzi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702.在国际环境法责任体系下,一国承担国际法责任的情况大致有二:(1)一国许可的行为导致其他国家遭受环境损害,典型案例如“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2)一国许可的行为导致国家管辖区域外的环境损害,典型案例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诉请法国停止核试验案”。
赔偿的计算方法属于实体和程序交叉的问题,需先借助实体法的规定,才能进入程序使用阶段,加之如何计算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目前还存在很大的理念分歧,所以对此单独论述说明更符合当下的进展。要求一国对其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进行赔偿主要得益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努力,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案”(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v. Guinea) 和“巴拿马等诉几内亚比绍案”(Panama v. Guinea-Bissau)中,国际海洋法法庭对环境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证。受此影响,2011年海床争端分庭(Seabed Disputes Chamber)发布的咨询意见〔49〕Se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ctivities in the Area, Advisory Opinion, 1 February 2011, ITLOS Reports 2011.对海洋环境损害赔偿事宜作出了进一步规定。相较于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态度,国际法院近年也一改过去较为谨慎的态度,开始逐步认同环境损害赔偿,重大的转折点是在“Costa Rica案”中,国际法院指出损害环境以及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在国际法下应该得到赔偿。〔50〕See Jason Rudall,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Costa Rica v. Nicaragua), 112 Am. J. Int’l L.288, 288(2018).
从国际环境损害赔偿成案看,即便法院支持原告提出的环境损害赔偿诉求,但如何计算环境损害赔偿额往往因充满技术问题而争议不断。在不少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法院喜欢使用经济学家偏好的使用价值法(use-values)、市场价格法(market prices)和修复成本法(restoration costs)来计算赔偿额度。〔51〕See Jason Rudall,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Routledge, 2011, p. 2.但从充分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看,这些计算方法因未能完全考虑整体的生态损害而存在较大的弊端,比如,未将海洋因污染而出现碳封存能力减弱的情形纳入其中。笔者认为,理想的做法应是采取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这样能够对生态损害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估,在此方面国际环境法司法实践已有积极尝试。在“Costa Rica案”中,哥斯达黎加主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来评估环境损害,即依据环境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来确定环境赔偿额度,尼加拉瓜则以联合国赔偿委员会评估海湾战争中的环境损害适用类似方法为由主张采用替代成本法(replacement costs)来确定环境损害赔偿额。最终法院采取了整体价值评估法(overall valuation approach),即按照环境产品和服务的损失整体来计算赔偿额,而不是计算每种环境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另加修复时间来确定赔偿额。〔52〕See Jason Rudall, Cert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Nicaragua in the Border Area(Costa Rica v. Nicaragua), 112 Am. J. Int’l L.288, 289(2018).
对于国际环境损害赔偿采取惩罚性赔偿的主张,国际法院在不少案件中已明确指出此方法不可行,但同时也指出在确定被告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额时应考虑其主观过错。〔53〕See Jason Rudall,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Routledge, 2011, p. 3.在“Costa Rica案”中,有法官指出在计算被告国需承担的环境损害赔偿额时应考虑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但是不能支持原告国提出的惩罚性赔偿。法院对惩罚性赔偿的排斥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反映了国际法委员对主观过错作为考虑被告损害赔偿额的强调。〔54〕See Draft Articl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nally Wrongful Acts II (2) YBILC (2001).就生态环境保护而言,环境损害赔偿是迫不得已的次优选择,防止环境污染及损害发生才是最优选择。从国际环境法成案来看,针对重大环境损害风险,一国可向法院请求临时措施来及时制止环境损害行为。在“南方金枪鱼案”中,国际海洋法法庭正是基于预防原则支持原告提出的要求被告停止环境损害行为的临时措施。
五、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国际法完善
环境灾难往往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完善的重要推动力,这一点在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领域尤为明显。〔55〕参见郑少华、王慧:《中国环境法治四十年:法律文本、法律实施与未来走向》,载《法学》2018年第11期,第19页。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国际社会针对核能开发使用所涉及的安全运营、事故应对和赔偿责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不少人认为有效解决相关问题需要国际法的完善。就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而言,国际法的完善大致可通过完善国际核能民事责任法和完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两种路径来实现。
(一)国际核能民事责任法的完善
国际核能法主要覆盖核能安全管理、核能事故应对、核能民事责任等问题,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主要涉及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的完善。现行的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和《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虽对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作了明文规定,但对核能跨国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明显不足,无力解决大规模核能跨国环境损害赔偿问题。
从有效解决大规模核能跨国环境损害赔偿的角度看,未来的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应考虑在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第一,拓宽环境损害赔偿的资金来源。根据现行的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承担核能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限于核能设施的运营主体。这种责任主体专属的制度设计在国际环境法中较为普遍,以便于环境损害受害人找到责任主体追责为基本逻辑,但是,由于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同时又针对运营主体规定了责任限制制度,导致了核能环境损害无法得到充分的赔偿。
为了解决核能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不足,可借鉴《关于核能方面第三者责任的布鲁塞尔补充公约》的做法,〔56〕这一公约主要面向OECD国家,同样适用于OECD国家的另一核能民事责任公约是《核能领域第三者责任的巴黎公约》。要求核能设施所在地的国家设立核能环境损害赔偿基金,解决核能设施运营主体无法充分赔偿环境损害的难题。亦可借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成功经验,要求与核能设施运营主体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出资成立专项基金,对环境损害赔偿提供第三层资金保障。
第二,明确环境修复的合理性标准。根据现行的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核能事故导致的纯粹环境损害属于其赔偿对象,原告有权主张修改受害生态环境的成本。但是,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对环境损害赔偿作了限制,即针对受害环境所采取的措施应当合理。至于何为合理措施,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由采取修复措施的国家自行决定。由于各国国内法对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不统一,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无法对核能环境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商提供明确的预期,这十分不利于国际核能民事责任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长远看也不利于保护因核能事故受损的环境。鉴于核能环境损害通常具有跨国界特性,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应当对环境修复措施提供合理性判断标准。
需注意的是,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公约的完善应尽可能平衡环境损害赔偿与核能产业保护之间的关系。核能开发无疑威胁较高,但核能利用也为人类带来不少好处,如为经济发展提供能源、有助于温室气体减排。国际核能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一方面需要保护潜在的受害人,另一方面也应保护核能产业的发展。如果国际核能民事公约对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过于超前,容易导致各国不愿意参与相关公约的修订,或者抵制参加相关公约。
(二)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完善
鉴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及《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对核能环境损害赔偿只有一般规定,未来国际核能民事责任法专门规定核能海洋环境损害赔偿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解决核能海洋环境损害赔偿问题很大程度上仍需依赖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完善。
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为基础,覆盖了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海洋环境大气污染、海洋环境船舶污染和海底活动海洋污染等方面。核废水排入海洋行为涉及两方面的法律议题:一是核废物入海的法律问题;二是规制海洋环境陆源污染的法律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就已开始关注核废物入海问题,1958年的《公海公约》第25条规定各国参照国际标准防止倾倒放射性废料污浊海水、防止使用放射性物质污浊海水,1972年的《伦敦公约》及其议定书明文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物质。不过,由于《伦敦公约》体系仅适用于海上放射性物质倾倒行为,对陆上核废水排入海洋行为没有约束力。也正是基于此点,日本一直宣称自己的核废水排入海洋行为没有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有权向海洋排放核废水。〔57〕See Youngmin Seo, The Marine Environmental Turn i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Fukushima Wastewater, 45 Fordham Int’l L. J.51(2021).
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是导致海洋污染的最大凶手,但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的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国际公约。之所以无法达成国际公约,是因为对海洋环境陆源污染进行国际法规制会对各国的主权带来较大的影响,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各国也不愿牺牲陆上经济发展来保护海洋环境。为了解决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问题,国际社会于1985年发布了《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蒙特利尔宣言》,联合国环境署于1995年倡议通过了《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58〕关于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国际法体系的详细论述,参见王慧、陈刚:《跨国海域海洋环境陆源污染防治的国际法框架》,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25-29页。但是它们对各国均无强制性约束力。由于各国对达成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国际公约的意愿不积极,在短期内制定海洋环境陆源污染国际公约并不可期。而且,制定新公约还容易导致“条约堵塞”(treaty congestion),即繁多的公约通常面临缺乏协调、公约执行碎片化、公约执行能力不足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用好现行的国际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则,通过合理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来调整核废水排入海洋环境损害赔偿问题是更加务实的现实选择。申言之,国际海洋法法庭在解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时会及时反映国际社会保护海洋环境的最新动态,如在国际法院咨询意见明确规定危险物质的跨界损害赔偿问题后,〔59〕See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1996 I. C. J. Rep. 226, 241-242.国际海洋法法庭随即将其作为解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的国际习惯法,体现出第十二部分不断进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