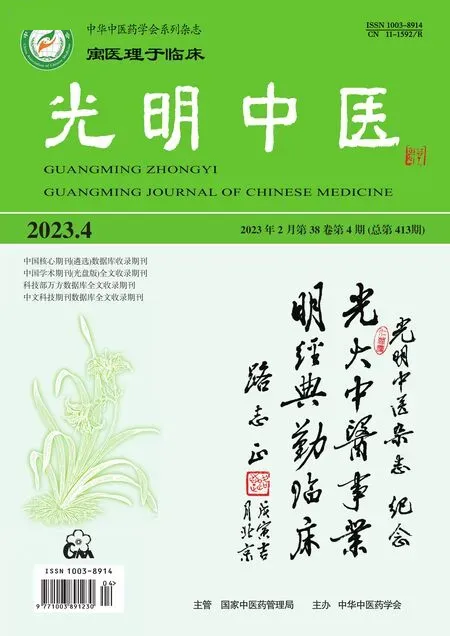基于脑-肠互动理论探讨从肝肺论治肠易激综合征
王 惠 闫雪洁 考延磊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一种以慢性、反复性腹痛为特点, 并伴有排便性状异常或排便习惯改变的功能性肠病[1]。按Rome IV的分类标准[2],IBS可以分为腹泻型(IBS-D)、便秘型(IBS-C)、混合型(IBS-M)和未确定型(IBS-U)。现代医学认为IBS发病机制较为复杂,主要与脑肠互动失调相关,还与胃肠动力学异常、内脏神经高敏感性、中枢神经系统对肠道刺激的感知异常和肠道感染、肠道微生态失衡、精神心理障碍等因素相关[3]。西医治疗方法较为单一,以对症治疗为主,药物主要为胃肠解痉剂、5-羟色胺受体拮抗剂、肠道微生态制剂、抗抑郁药物,治疗效果欠佳,并且不能达到根治效果,很容易复发,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有比较大的影响。传统中医暂无此病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可以归属于中医学的“腹痛”“泄泻”“便秘”“郁证”等范畴,IBS病机以肝郁脾虚、脾肾阳虚为主,以疏肝健脾、温补脾肾为治疗原则,遵循此原则在治疗此病过程中取得一定成效,但不乏有部分患者治疗效果欠佳。基于近年来研究发现,从肝肺论治IBS也取得较好疗效。因IBS直接病位在肠,肺与大肠相表里,病机关键在于肝郁脾虚,故治疗上可以疏肝健脾与调肝理肺相结合。脑-肠轴是大脑和肠道、肠道菌群的双向调节,这与中医的肝、肺与大肠之间气机、津液的相互调节作用有相似之处,所以本文旨在以脑肠互动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从肝肺论治肠易激综合征的可行性,通过剖析其相关性,为中医药治疗IBS提供新思路。
1 脑-肠互动与IBS
胃肠系统是人体较为独特的存在,是由自主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以及肠神经系统一起交互控制,通过复杂且精细的支配,共同完成其生理功能。这种脑-肠互动过程涉及脑肠轴、脑肠肽、肠道菌群等方面,是大脑和胃肠道之间双向调节的复杂神经体液通信网络[4],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着双向沟通渠道,对于维持大脑、肠道和肠道菌群3方之间的平衡有重大作用,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容易引起IBS的发生。
1.1 脑肠轴脑肠轴由大脑、肠道及肠道微生物共同构成,是控制大脑和肠道功能的双向交通系统,包括肠神经系统(ENS)、自主神经系统(ANS)、中枢神经内分泌系统(CNS),以及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系统(HPA)[5]。神经系统通过这3个不同层次对胃肠道进行分层调控:第1个层次是通过肠神经系统对肠道进行局部调控;第2个层次是自主神经作为桥梁,通过整合肠道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信息进行调控;第3个层次是中枢神经系统通过接收来自各级神经中枢和脊髓的信息,再通过神经-内分泌网络传导给肠神经系统或者直接作用于胃肠道相应细胞。当中枢神经系统受到刺激时,可以传导到胃肠道,而内脏感觉也可以通过肠神经系统影响中枢神经系统[6],因而这个通路在IBS的发生中具有重要意义。
1.1.1 CNS对肠道的整体调控作用CNS对胃肠道的调控主要是由脑的各级中枢和脊髓接收各种信息, 经过整合后由神经-内分泌网络将信息传到ENS或直接作用于胃肠道的平滑肌细胞, 以调整胃肠道各个平滑肌的协调运动而共同完成的[7]。现代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PET)技术表明IBS患者的直肠给予扩张等内脏刺激后,其大脑产生明显活跃区域[8],尤以大脑边缘系统居多,而大脑边缘系统主要功能是负责处理疼痛刺激、情绪调节反应等。据此可以表明,持续的肠道慢性刺激即可引起CNS异常反馈,从而影响HPA轴失调导致IBS[9]。
1.1.2 ENS对肠道的局部调控作用ENS由分布在肠壁的黏膜下及肌间2个神经丛组成,包含多种类型的肠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具有独立调节和控制肠道功能的作用,独立于CNS之外,被称为“肠脑”[10],也被称为肠道的“微型脑”,在胃肠功能的调节机制中起主要作用。内在初级传入神经元 (IPAN)是ENS 中的重要存在,负责检测胃肠道的分子和机械畸变[11]。实验证明,肠道微生物群可以影响IPANs的兴奋性,而这种变化可以调节伤害性反应,导致IBS的发生[12]。有研究证明,ENS通过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和外周初级感觉传入神经的反馈通路(脑-肠轴)与中枢神经系统相连,形成双向的脑-肠轴,可以影响个体的情绪、食欲和行为状态,由 ENS 功能障碍引起的胃肠功能障碍 (GIFD) 不仅可能导致胃肠功能异常,而且还与认知和情绪障碍有关,例如肠易激综合征(IBS)[13]。
1.1.3 ANS对肠道的协调作用ANS是ENS与CNS的桥梁,通过交感神经及副交感神经交通和协调脑肠神经的联系[14]。交感神经兴奋时,可以抑制平滑肌的功能,从而减缓胃肠道活动,而副交感神经兴奋时可以促进胃肠活动。一项实验结果表明 ANS 活动与 IBS 患者内脏感知的大脑机制之间存在着异常相互作用,在非便秘型 IBS 患者中,大脑介导的 ANS 活动和内脏感知的耦合可能会发生改变,这表明更复杂的层次变化可能会产生 IBS 症状,被认为是一种脑肠疾病[15]。肠易激综合征 (IBS) 患者经常出现由自主神经系统 (ANS) 调节的排便习惯障碍(腹泻、便秘)和腹痛不适[16]。
1.2 脑肠肽脑肠肽(Brain-Gut Peptide, BGP)是一种小分子活性多肽,在 CNS、ENS 及胃肠道均有分布,可作为神经递质传递信息,也可作为激素发挥双重作用,实现脑-肠互动[17]。目前研究较多的包括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P物质(Substance P,SP)、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CRF)等。VIP是一种抑制性脑肠肽,通过抑制平滑肌的收缩,减慢胃肠蠕动。SP是一种兴奋性脑肠肽,与VIP作用相反。多个动物模型已证实,CRF可以参与介导内脏高敏感性[18]。SP是参与外周伤害性信息传递的主要神经递质[19], 和CRF一起影响内脏神经高敏感性。IBS患者结肠黏膜SP、VIP水平与腹泻或便秘症状有一定的联系, SP、VIP与IBS发病密切相关[20]。研究证明,IBS患者的5-HT等多种脑肠肽呈异常表达,在中枢神经胃肠活动互相作用反馈的环节发挥重要作用[21]。
1.3 肠道菌群肠道菌群是人体最庞大、最重要的微生态系统,其基因组总和是人类基因组数的百倍之多,被称“肠道元基因组”,也是把控人体健康防线的“人体第二基因组”[22]。肠道菌群对于局部肠道微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与IBS的病理相关,IBS患者的菌群相对于健康个体发生变化。肠道菌群影响IBS主要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23]:①影响低度黏膜炎症和免疫活化;②影响内脏神经超敏反应;③影响肠道屏障功能;④影响胆汁酸代谢。经研究发现,IBS患者双歧杆菌数量明显减少,肠杆菌数量显著增加[24]。由此可以证明,肠道菌群是IBS发病因素中的重要一环,肠道菌群的失调导致对病原体的抵抗作用减弱,肠道感染疾病几率增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干扰肠道的正常功能,导致IBS的发生。肠道微生物群可以通过肠道衍生的分子作用于传入的迷走神经或脊髓神经末梢,或直接通过微生物产生的信号间接与大脑沟通,这些双向互动的增益在应对诸如社会心理或肠道导向(如饮食、药物、感染)压力的干扰时发生改变,可以改变这一系统的稳定性和行为,表现为脑-肠紊乱[25]。
2 IBS的中医病因病机
根据IBS临床表现可以归属于中医学的“腹痛”“泄泻”“便秘”“郁证”等范畴,病因与感受外邪、饮食不节、情志不调、脏腑虚弱等密切相关。任宝琦等[26]认为病位主要在脾、胃、大肠,与心、肝、肺、肾关系密不可分,脾失健运,心神失养,肝失疏泄,肺失宣降,肾阳虚损,皆与IBS的发生相关。因IBS的直接病位在大肠,病机总体可以归结为气机升降失调、津液输布失常,而这些生理功能的正常有赖于肝肺二脏升降得宜,故IBS与肝肺密切相关。
2.1 肝与大肠相通《五脏穿凿论》有记载:“心与胆相通,肝与大肠相通,脾与小肠相通,肺与膀胱相通,肾与三焦相通,肾与命门相通,此合一之妙也”。其中“肝与大肠相通”说明肝与大肠密不可分。肝为脏,性属木,木性升发,大肠属腑,性属金,金性肃降。陈英杰[27]将中医学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相结合,认为“肝寄腑于大肠”。在生理功能方面,肝主疏泄,包含了对气机的影响、对脾胃运化功能的影响以及对情志的影响。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主要功能是传导糟粕,而大肠的传导功能可以看作是胃的降浊功能的延伸。大肠的传导功能有赖于肝气疏泄,而肝气的疏泄升发也需要大肠的降浊功能的辅助,二者一升一降,气化相通。在经络方面,肝与大肠虽不是表里关系,但两者经气可以通过肺经发生联系。在病理方面,肝疏泄失常易引起大肠功能异常,易引起便秘、泄泻,而IBS患者常伴随此症状,因此IBS 中医治疗上宜疏肝为主。
2.2 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与大肠相表里,涉及经脉络属、气机升降及津液代谢。《黄帝内经》首见“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肺合大肠,大肠者,传导之腑”。肺与大肠相表里,《灵枢·经脉》云:“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大肠手阳明之脉,起于大指次指之端……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肺与大肠相互表里,通过经络互相联系。在生理功能上,肺气以降为和,肠道以通为用,二者通降相合。《素问·五脏生成》曰:“诸气皆属于肺”。肺主一身之气,大肠传导功能的正常依靠肺气的肃降,《医精经义》曰:“大肠所以能传导者,以其为肺之腑。肺气下达,故能传导”。反之,肺的气机升降协调也有赖于大肠的传导功能正常。肺主通调水道,大肠主津,二者相辅相成,有助于津液代谢。在病理上,肠病及肺,肺病及肠[28]。《证治百问》曰:“肺气虚,大肠亦虚,而不能紧固,时时欲去,后重不已……以升发益气之药同兜涩固肠丸主治”,指出肺气虚弱,气机升降失调,影响及大肠,大肠固涩减弱而成泄泻,治疗上需补益肺气,固涩大肠[29],这充分说明从肺论治IBS有充足的理论依据。肺在志为忧,而IBS患者大多存在抑郁状态,因此对于改善IBS患者的情绪状态,从肺论治不可或缺。
3 从肝肺论治IBS与脑肠互动关联性
叶天士云:“人身气机合乎天地自然,肝从左而升,肺从右而降,升降得宜,则气机舒展”。肝气以左侧升发为阳道,肺气以右侧肃降为阴道,肝气升则肺气降,肺气降则肝气升,二者升降相合,则气机条畅,以肝肺为枢纽,维持人体气机的正常运动。《素问·五脏生成》曰:“诸气者,皆属于肺”。人身之气,其主在肺,其调在肝,其根在肾,气之有纳有出,有升有降,才可不郁不壅。《灵枢·经脉》曰:“肝足厥阴之脉……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灵枢·本脏》曰:“ 经脉者,所以行气血而营阴阳”,人体的十二经脉互为表里,首尾相贯,如环无端,承担着运行气血之职能。 肺经与肝经是十二正经的起始与终止之脉,一首一尾,对于中间循行经脉的气机通畅与否有重要意义。IBS通常表现为腹痛且伴腹泻或便秘,此为“不通则痛”,说明是气机不畅而致腹痛,肠腑气机失调、大肠传导失司而致腹泻或便秘,故治疗IBS需首先考虑肠腑气机条畅与否,当需从气机枢纽的肝肺二脏论治。《景岳全书》曰:“若思郁不解致病者,非得情舒愿遂,多难取效”,IBS多迁延不愈,与患者的情绪有极大相关性,肝主疏泄,肺在志为忧,对于情绪的疏导,肝肺重要性显而易见,通过疏肝理肺,可以提高IBS患者的治愈率,减少复发率。
现代医学认为胃肠道与脑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行双向调节从而形成脑肠互动。肝升肺降通过气机运行和水液代谢来达到调节大肠传导通降糟粕作用,反之大肠传化糟粕功能失常亦可影响肝肺升降功能的正常发挥。这种肝肺与大肠之间的互动联系与现代医学中的脑肠互动理论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均从整体分析,可以用脑肠互动学说解释肝肺论治IBS的可行性。李晓红等[30]认为:肝主疏泄、调畅情志和协助脾胃运化的功能与脑一肠轴具有相关性。有研究表明,运用疏肝健脾法治疗IBS,观察组患者血清 5-HT、CGRP、SP、NPY 水平治疗后明显降低,分析患者血清5-HT、CGRP、SP、NPY含量的改变改善了肠道动力紊乱的现象,使患者肠道高反应性降低,增加了肠道微循环血流,从而减轻肠道黏膜的炎性反应,因此各种临床症状也随之缓解[31]。蒋天媛等[32]证实健脾理肺通便方可以改善功能性便秘脾肺气虚、胃肠气滞证患者便秘症状,并且对患者的肠道菌群有调节作用。这些研究都证实了从肝肺角度论治IBS在临床上有据可依。
4 小结
IBS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脑肠互动失调是其重要因素,基于脑肠互动学说,以脑-肠轴、脑肠肽、肠道菌群等作为重要切入点,研究中医药治疗IBS的新的发病机制。本文将肝肺功能与脑-肠互动相互结合,从脑肠肽、肠道菌群等微观角度来剖析中医宏观思想,为中医药治疗IBS提供新思路的延伸,以发挥中医药治疗IBS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