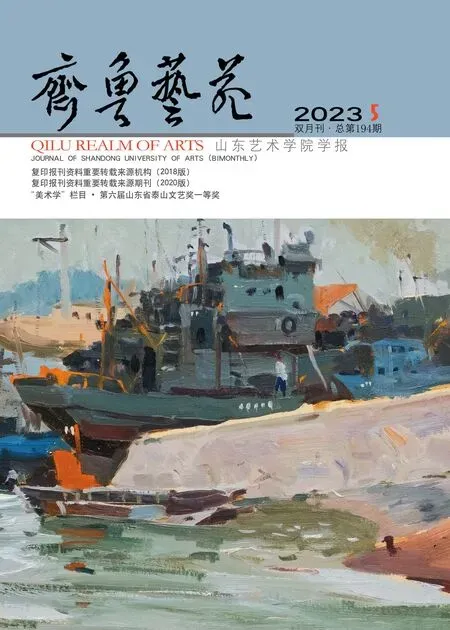从松年《颐园论画》看晚清中国画笔墨观念的嬗变
杨 宁
(山东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19 世纪的晚清,伴随着西方的入侵,以及国内太平军、捻军的动乱,进入了内忧外患、国事如麻的乱局。 帝国制度面临崩溃和民族危机加剧之际,连带这一时期的绘画史也被误解为“衰败”时期。1917 年,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中云:“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盖由画论之谬也。”[1](P21)康有为对明清绘画给予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并指出“衰败”的原因是由于过度强调笔墨情趣,导致作品因袭模仿、少有生气。 1919 年,陈独秀在《美术革命》一文中,更是将革命矛头指向了以笔墨见长的清初“正统派”,全面否定文人画传统,并且明确指出要以西画写实精神来改良中国画,其曰:“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 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2](P29)康、陈的“衰败-改良”理论几乎主导了近百年来的中国画坛,晚清绘画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晚清画论也被认为有创造力的见解不多,多为前人著述的转载,价值不大。
康有为、陈独秀对晚清画坛盲目的判断与偏激的主张,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因此,薛永年就指出:“我在研究十八九世纪中国绘画史中发现,晚近绘画史的研究存在一个弊端,那就是套用社会学、历史学和文化史学的既有结论,加以演绎……那既有结论的套用,离不开晚清的国势衰微,和为振兴中华而效法洋人,更离不开以西方写实观念改造中国画的潮流,为了弃旧图新,便出现了‘中国绘画晚近衰败极矣’之论。”[3](P20)熊宜敬也认为:“一直以来,几乎大多数东、西方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学者都抱持着19 世纪不值一书的态度,造成这一百年几成中国绘画史的边陲,令后进研究学子失去了探究19 世纪中国绘画史的兴趣,因而淹没了这一段原本精彩的史料与诸多艺术家的成就。”[4](P5)
近年来,随着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更新完善,以及对19 世纪绘画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对晚清的绘画和绘画理论有了重新的认识和全新的体认。 万青力试图重写晚清艺术史,他在《并非衰落的百年:19 世纪中国绘画史》的绪论中讲道:“涉及中国艺术史领域的学者大多认为,从许多方面来说,18 世纪的中国绘画已经呈现衰落去向,其后19世纪尤甚。 笔者不敢苟同这一判断,因此特拟‘并非衰落的百年’为题。”[5](P3)晚清的绘画确如万青力所言“并非衰落的百年”,中间既有“金石画派”的突破,又有“海上画派”的崛起;在绘画理论上,既能集前代之大成,使历代绘画思想得以归纳、整合和补充,并将其系统化和规范化;又能阐发画学精华,独抒己见,立一家之言,成为启迪后学的圭臬。 郑午昌说:“清代士大夫之能画及好画者,往往著其心得,或为断章,或成卷帙,著作之多,不下数百种。虽其内容,不无雷同之处,但要语名言,发画学之精微,与后学之圭臬者,颇有足录。 盖图画至于清代,凡关于绘事之各种问题,无不相当之解答及批评。”[6](P421)
在众多晚清画论之中,松年的《颐园论画》可谓独树一帜,建树颇多。 该画论成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松年主持济南枕流画社时所用课徒稿,语言平实,不仅阐述了用笔、用墨、用水、用色等绘画方法,而且对为画之道、学画之途也多有涉及,是对传统绘画创作理论的总结,更是晚清画论成就的集中体现。 俞剑华认为:“书中所论以画才节中独创一格,处处有我,为最正确,而最大胆,足破临稿家之惑,与石涛《画语录》之自己面貌,可谓若和符节。 其他所论,俱为甘苦有得,切于实用之言,尤以论皴法论用水为最精。”[7](P241)水天中考证“中国画”一词最早出现于《颐园论画》之中。①“中国画”这个词的产生是在“西洋画”出现之后,是近百年内才出现的事。 最初,在晚清画学之中,只在谈论西洋绘画作品时,偶而使用“中国画”这个词,如《颐园论画》谓“西洋画工细求酷肖”,“谁谓中国画不求工细耶”,这里的“中国画”是泛指一切非西洋画的中国绘画。 参见:水天中.“中国画”名称的产生和变化[J].美术,1986,(2),P8—11。邓乔彬则指出:“松年的《颐园论画》为古典绘画思想奉上了‘声部’齐全的绝唱,为古典时期的大厦添加了最后的砖石,是十九世纪传统古典画论集大成式的总结与提升。”[8](P1343)
笔墨是中国书画的形式手段和物化载体,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折射,具有外在应用性和内在学术性的双重价值,为历代书画家所重视。 董其昌讲:“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9](P231)董其昌在此将笔墨与造化并论,本质上是树立了笔墨独立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价值,给予后世以建构“笔墨”概念的启示。 松年在《颐园论画》中对于笔墨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讲:“余若殚学力,极虑专精,悟得只有三等妙诀:一曰用笔,一曰运墨,一曰用水,再加以善辨纸性,润燥合宜,足以尽画学之蕴,更能才华颖悟,随处留心,真境多观,涵泳胸次。”[10](P11)就作画的工具材料而言,传统画论多论述用笔、用墨,而与笔墨效果紧密相关的用水、纸性则几无涉及,松年在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 并且还针对笔墨与造型、色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以造化为师法”[11](P41)“用色如用墨,用墨如用色”[12](P30)等观点。 松年的笔墨论,从形而下的技法手段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晚清画论过于形而上的缺陷,切实为传统的笔墨技法增砖添瓦,也为我们观察和研究晚清中国画笔墨观念的嬗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一、笔墨与水法
笔墨是中国画独有的艺术语言和审美对象,亦是中国画的生命线。 笔墨相生,皆关乎用水,水法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笔法、墨法历代都有详尽的论述,早在南朝的“谢赫六法”之中,就针对笔法提出“骨法用笔”的要求,但还没涉及到用墨。 唐季五代的荆浩在“六法”基础之上,将用墨列入“六要”②(五代)荆浩《笔法记》云:“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 ……墨者,高低晕淡,品物浅深,文彩自然,似非因笔。”参见:[五代]荆浩.笔法记[G]/ /俞剑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1 编先秦至五代.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P175—176。之中,并将其上升为墨法的高度,自此墨法也开始进入画论研究的视野。 但是以水运笔、以水调墨的水法,历代论述却着墨不多,往往一笔带过,只云“水晕墨章”①(五代)荆浩《笔法记》云:“夫随类赋彩,自古有能,如水晕墨章,兴吾唐代。 故张璨员外树石,气韵俱盛,笔墨积微,真思卓然,不贵五彩,旷古绝今,未之有也。”参见:[五代]荆浩.笔法记[G]/ /俞剑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1 编先秦至五代.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P177。“水墨为上”②(唐)王维《山水诀》云:“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 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参见:[唐]王维.山水诀[G]/ /俞剑华.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1 编先秦至五代.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5,P150。等,浅尝辄止,辞衍义奥,让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20 世纪80 年代,王伯敏根据黄宾虹的论述与创作实践,相继撰写了《黄宾虹的用墨和用水》[13](P8-9)和《中国画的“水法”》[14](P69-74)两篇文章,自此,关于笔墨之中水法的研究才揭开序幕。 岂不知,中国画笔墨表现力的发展,与水法的演进一直有着密切的关联。
松年对于水法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方法,他讲:“万物初生一点水,水为用大矣哉。 作画不善用水,件件丑恶。 尝论妇女姿容秀丽,名曰水色,画家悟得此二字,方有进境。”[15](P35)水为万物之源,水法亦为笔墨的核心与关钮,只要运笔作画就离不开水,只有水之妙用,方能笔畅墨活,否则就是呆笔滞墨,板刻结弱。 水法如此之重要,松年更是将用水与用笔、用墨相提并论,其云:“万语千言,不外乎用笔、用墨、用水六字尽之矣,嗟乎! 古今多少名家,被此六字劳苦半生。”[16](P32)墨依笔运,笔靠墨现,笔不能离开墨,墨不能脱离笔,但笔与墨的结合却全部依靠水。 换言之,笔墨皆依水而存,墨分五色,浓、淡、干、湿、黑的变化都需要经过水的调和,墨色之妙全从笔出,笔头储水量大为湿笔,反之则为渴笔,水法就是笔法,水法就是墨法,诚如李鱓所言:“笔墨作合生动,在于用水之妙。”[17](P20)
水法的运用和绘画的工具也有着密切关系。松年善用特制的鸡毫笔作画,这种笔是用不去梗的鸡羽和鸡身上的绒毛制成,特别柔软,浸水后弹性差,由于梗硬而弯曲,锋端不能平齐,笔锋易散难聚,具有易吸水、濡墨快、运笔难的特点。 用鸡毫笔创作书画,笔锋不稳健,无自支之力,很难控制,使用时极易软弱臃肿,没有深厚的书画功底不容易掌握,范成大就曾批评此笔道“其锋踉锵不听使”[18](P32)。 然而,在松年腕下却充分发挥了鸡毫笔含水量大的特点,依毫势抒写,运势奇宕,如挥洒云烟,一笔之中有虚有实,轻重得体。 如其《猫蝶图》为鸡毫笔绘制,猫躯干部分的墨迹如一团棉花,水气淋漓,墨色的浓淡干湿变化自然,清秀浑厚,较好地利用水法表现出了毛茸茸的质感;猫眼、猫须则以渴笔写出,细如发丝,一笔之中外柔内刚、圆浑有力,线条劲挺,充分发挥了鸡毫笔肥腰而锋尖的特性。
对于不同的绘画材料,松年也相应地总结了不同的用水方法。 他讲:“画绢,要知以色运水,以水运色,提起之用法也。 画生纸,要知以水融色,以色融水,沉渖之用法也。”[19](P35)绢与纸是中国画所赖以显现的载体,绢是一种平纹类素织物,虽历代的织造方法、工艺不同,如唐绢丝粗而厚,宋绢匀净厚密,但大都经过明矾、明胶的处理,多平整光滑,性润不燥,渗水难积,适合多次反复渲染;纸的材料也很多,但清代以生宣纸为主,生纸纸性绵软柔韧,渗透晕化性强,承墨接水性好,可以表现复杂多变的笔情墨趣。 纸绢材料的属性不同,用水方式也截然不同。 在绢地上作画,要“以色运水,以水运色”,是充分考虑到绢本渗透性弱、耐磨性强的特点,就是指要用一支墨色笔和一支清水笔,先以墨色笔绘制物象暗部,紧接着用清水笔接触墨色,用水把色墨铺开,推向阳面,产生由浓到淡的变化,或者先以清水笔勾画物象暗部,再用墨色笔在水上推移提晕,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匀净的效果。 在生纸上作画,要“以水融色,以色融水”,是注意到生宣纸渗水受墨性强的特点,即可以用水来融洽墨色,也就是水破墨、水破色的破水法,可使画面墨色变化多端,产生韵味无穷的效果,如张式所言:“墨法在用水,以墨为形,以水为气,气行形乃活矣。 古人水墨并称,实有至理。”[20](P111)或用墨色来融洽水分,其方法与水破墨、水破色相反,是水先落于纸上,然后破之以墨色。 水破墨、墨破水的两种方法类似,只是工序先后颠倒而已,表现效果也差不多,实则二法为一法。 松年关于用水的“提起之法”和“沉渖之法”,虽然没有像20 世纪黄宾虹的“用水六法”那么全面,但已是晚清画论的高光之处,弥足珍贵,足以开启后学之正思。
纵观中国画论史,关于水法,清代之前几乎没有直接涉及,大都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感触与感想,并无系统论述。 清初孔衍栻的《石村画诀》还仅仅是“用水渲染,不易之法”[21](P1)的浮光掠影,石涛也讲“作画有三胜,一变于水,二运于墨,三受于蒙。 水不变不醒……”[22](P207),李鱓更是说“我善于水,笔墨关钮在于水”[23](P82),但这些先贤依然停留在观念层面,并没有落实到技法操作上。 由此观之,松年的水法论在传统画论中最为系统,也最具代表性,不仅从工具材料的角度详加叙述,而且还把用水之法与用笔、用墨相提并论,将水法升华为笔墨之津梁,提出“秀润皆关用水,墨彩皆在用笔”[24](P37)的观点,为20 世纪黄宾虹“水法”的提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笔墨与造化
在当代笔墨研究之中,对清人笔墨有一个普遍的误解,那就是笔墨本身的审美价值在清代完全独立,是一个艺术的主观存在,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意识,并且与造型相分离,其功能主要是精神性表现。笔墨的独立价值不仅体现在绘画创作之中,并且在绘画品评上,一幅作品的高下成败,已不是先观气韵,次品笔墨,而是直接从笔墨入手。 钱泳云:“画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轻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 余以为皆非也。 无论南北,只要有笔有墨,便是名家。 有笔而无墨,非法也;有墨而无笔,亦非法也。”[25](P298)王学浩则言:“作画第一论笔墨。 ……董宗伯云:‘画以造化为师。’唐六如云:‘画当为山水传神。’谈何容易? 何论前代本朝各家,即元季四家,亦只是笔精墨妙,未能为山水传神也。”[26](P46)钱泳不分派属,王学浩割裂笔墨与造化的关系,完全以笔墨论高低、品雅俗的观点,只能代表清人论画的部分观点。 但是后人将清人的这种笔墨独立性放大,以偏概全,尤其认为晚清的笔墨陈陈相因,亦步亦趋,在绘画理论上亦是笼罩在复古意识之下,绝无新的命题和大胆的突破,传统绘画和画论走上了无生机的穷途。 在此观念下,郑午昌就曾明确指出:“清人言画学者,力主仿古,如逐时好而自立门户者,必深毁之,以为蔑弃古法,误入魔道,纵极精妙奇突,不入鉴赏之目。”[27](P440)
但在19 世纪的晚清画论之中,笔墨又开始回归造化,重新建立了与真山水的联系,兼具造型性与写实功能,而且也对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超越了宗派门户之见,能够较为全面的审视和继承古代绘画遗产,从而冲破了正统派笔墨观念的束缚,促进了审美观念的转变,为20 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与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发展契机。 松年讲:“作家皴法,先分南北宗派,细悟此理,不过分门户、自标新颖而已,于画山有何裨益! 欲求高手,须多游名山大川,以造化为师法。”[28](P41)皴法原本是古人观察和研究自然山石的纹理与结构后,用笔墨把感受的意象表达出来的一项技法,目的是为了表现山石的质感与体积感,不同的皴法可以表现不一样的纹理、质地和脉纹,各家皴法都可追溯其取材之地,如披麻皴源于江南山,豆瓣皴源出照金山、斧劈皴来自中州山等。 质言之,皴法源于自然,是对山石纹理的笔墨组合,只不过在山水画的演进过程中逐渐被程式化、符号化。 松年在此直言“以造化为师法”,并进一步指出“皴法名目,皆从人两眼看出,似何形则名之曰何形,非人生造此名此形也”[29](P41),又回到了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唐宋传统,既要从大自然中求得形似,又要从心源之中创造神似,方此才“可悟心造神奇也”[30](P41)。 在松年的绘画理论之中,笔墨不仅是表达心绪的载体,更是造型的手段,笔墨与造型又重新建立了有机和谐的联系。 当然,松年并没有完全否定笔墨的独立价值,而是“以眼前真境为蓝本,以古人名迹作规模”[31](P16),是师造化与师古人的齐头并进,只不过是更强调笔墨原本具有的描绘与表现世界的活力,更重视笔墨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无独有偶,在晚清画论之中,对笔墨与造化关系的重视,并非松年一人而已,张式《画谭》中也讲:“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画之能事尽乎? 曰:能事不尽此也。 从古人入,从造物出。 试以古人之学证古人,古人岂斤斤笔墨之间者哉!”[32](P118)
自从董其昌提出“南北宗论”以后,“南宗”一路的文人画成为画坛正宗,尤其是在清代早中期崇南贬北的风气愈演愈烈,大凡画家十有八九都归在了“南宗”门下,这其中又以“四王”以及由其所衍生出的“娄东派”和“虞山派”最为典型。 方薰《山静居画论》曰:“海内绘事家不入石谷牢笼,即为麓台械纽。”[33](P562)一般论画者多以为“南宗”之风如方薰所言,笼罩于整个清代画坛,几乎尽皆为其所据,直至20 世纪才有改观,实则不然。 松年振臂直呼:“先分南北宗派,不过分门户、自标新颖而已,于画山有何裨益!”便是对崇南贬北之风的最大否定和冲击,他又进一步指出“必须造化在手,心运无穷,独创一家,斯为上品”[34](P12),意思就是无论南北都要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凡是好的技法都要吸收,只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才能独创一格。 放眼晚清画论,南宗画风实则已成强弩之末,盛极而衰。 邵梅臣《画耕偶录》云:“山水唐以前画家无分宗之说。笔墨一道, 各有所长, 不必重南宗轻北宗也。”[35](P209)李修易《小蓬莱阁画鉴》也说:“近世论画,必严宗派,如黄、王、倪、吴,知为南宗,而于奇峰绝壁即定为北宗,且若斥为异端。 不知南北宗由唐而分,亦由宋而合。 如营邱、河阳诸公,岂可以南北宗限之?”[36](P137)戴熙《习苦斋题画》更是说:“士大夫耻言北宗,马、夏诸公不振久矣。 余尝欲振起北宗,惜力不逮也。”[37](P999)由此可见,对“南北宗论”的反思和批判,或者说以振兴北宗的阳刚之气来中和南宗的阴柔软糜,并不是20 世纪的专利,早在19世纪已见端倪。
一般论画者,多以为写生是伴随着西方美术教育的传入而逐渐兴起,是一个近代的概念。 写生使中国画脱离了传统的束缚,是20 世纪中国画获得发展的有效途径,郎绍君更是指出:“重视写生甚至崇拜写生,是20 世纪中国绘画和绘画思想的一大特色。”[38](P222-232)写生的确是20 世纪中国画创新探索中最有价值的一种方式,但在19 世纪对写生的重视已见端倪。 松年云:“写生之作,皆在随处留心,一经入眼,当蕴胸中,下笔神来,其形酷肖。”[39](P65)可见松年十分重视师法造化,写生不仅是其素材的积累,更是他观察、表达方式的训练过程,是“得之于心,施之于手”的结果。 他又讲:“古人名作,固可师法,究竟有巧拙之分。 彼从稿本入手,半生目不睹真花。 纵到工细绝伦,笔墨生动,俗所称稿子手,非得天趣者也。 必须以名贤妙迹立根本,然后细心体会真花之聚精会神处,得之于心,施之于手,自与凡众不同。”[40](P68)意思是说若不写生,只是临摹前人稿本,纵使笔精墨妙,也难得天趣,很难表现物象的生命活力与生机。 在松年观念之中,仅仅重视写生还是不够的,他还说:“既得之于造化生成,当运之于笔端布置。”[41](P65)质言之,写生不是照抄自然,不是简单地记录对象的形态、结构,既要做到“形态既肖”,又要做到“笔墨怡情”,要把写实造型与笔墨表现高度统一,方能“得其形势,自然生动活泼”。松年对写生的论述,虽然着墨不多,但十分精辟,给人启示不少,尤其是对写生与笔墨辩证关系的认识,为20 世纪写生理论与方法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借鉴。
三、笔墨与色彩
中国画又称“丹青”,丹指的是朱砂,青指的是青雘,丹青是色彩的统称,可见色彩在中国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文征明说:“余闻上古之画,全尚设色,墨法次之,故多青绿。 中古始变为浅绛,水墨杂出。”[42](P710)但自唐代文人水墨画一出,笔墨就居于支配地位,色彩便退居其次,“绚烂至极而归于平淡”,故张彦远有“运墨而五色具”之说。 虽然文人水墨画是中国画的发展主流,但是色彩也没有完全从绘画中退去,而是与笔墨共生。 尤其是在清代,色彩与笔墨异曲同工,松年讲:“用色如用墨,用墨如用色,则得法矣。”[43](P30)强化色彩表现的“以色当墨”,既要见色又要见笔,是松年论画的一个重要特点。
清人论画虽然强调笔墨,但也未曾忽略用色,王原祁讲:“设色即用笔用墨意,所以补笔墨之不足,显笔墨之妙处。 今人不解此意,色自为色,笔墨自为笔墨,不合山水之势,不入绢素之骨,惟见红绿火气,可憎可厌而已。”[44](P23)在王原祁观念中,色彩从属于笔墨,可以弥补笔墨之不足,而且在具体使用时,要把用色与用墨结合起来,使颜色之中含有笔墨之气,色与墨和,方可去色彩浓艳的火气。盛大士也指出:“画以墨为主,以色为辅。 色不可夺墨,犹宾不可溷主也。”[45](P263)色彩作为一种辅助性手段,目的为了突出笔墨,仍然是以墨为里以色为表。 松年则云:“作画固属藉笔力传出,仍宜善用墨,善于用色。 笔墨交融,一笔而成枝叶,一笔而分两色,色犹浑涵不呆,此用笔运墨到佳境矣。”[46](P30)虽然还是与笔墨一起谈用色,但是更加突出了色彩的独立存在,不再像清代早中期画论那样将用色居于次要地位,而且强调“一笔而分两色”,力图将用笔的提按顿挫、点划使转融入到用色之中,讲究色彩的浓淡冷暖、阴阳虚实的变化,突出色彩的表现性和象征性。
用色与用笔、用水的关系也很密切。 松年云:“以笔运色,须一笔之内分出浓淡深浅,画花画叶,方见生动。”[47](P36)意思就是说用笔要活,不要拘泥,要能够变通,一笔之内色彩就要有浓淡深浅的变化,要注重色彩对比,切忌平板,才能达到色墨相融,自然生动的效果。 秦祖永也说:“淡设色亦要用笔法,与皴染一般,方能显笔墨之妙处。”[48](P91)由此可见,在晚清画论之中都十分关注设色之法,用色如用墨,把色当墨用,同样讲究笔法,皴擦点染互施,追求“以笔运色”的丰富与变化。 紧接着松年又讲:“分出两种颜色,其诀在于何处? 其妙处在于笔蘸浓淡两色,施之绢上,则笔头水饱,藉水融洽;施之生纸,笔头水少,藉毫端一顿捺,自然交涉浑含,似分不分之际,乃佳境也。”[49](P36-37)质言之,一笔之中同时蘸有浓淡两种墨色,笔尖含浓墨,笔肚含淡墨,或者笔尖含淡色,笔肚含浓色,笔行绢上之时,笔头水要多,由于绢地渗透性弱,浓色淡色便藉由水性相互融合,如同晕染之法;笔行生宣纸上时,由于生宣纸的渗透晕化作用强,笔头水要少,行笔速度要快,藉由这枯笔色墨交融,便会自然呈现浓淡层次和深浅变化。 因此,用色的成败不仅在于色彩本身,而且和纸绢材料、用笔用水也有密切关联,用笔、用水、纸性三位一体,其中水法居于核心关钮,但在作画时,什么地方水多些? 什么地方水少些?这个用水的度在哪里? 并没有现成的配方,画家要凭实践中积累经验,故松年无奈地说:“往往画师口不能道,只令他人意会而已。 此无他,仍是未能揣摩神理出来,所以不能口说也。”[50](P36-37)
松年不仅对设色技法十分重视,而且对颜料的制作和使用也颇有研究。 他讲:“市肆所卖铅粉,画家仍须自己加工漂治,去其渣滓,留其顶膘。 去铅不净,画人面花瓣,每犯旧铅黑黯之色,枉费功夫,佳画废弃,诚为可惜! 曾见去铅之法甚多,求其丝毫不犯,恐亦甚难。 古人用石研粉,后人因其难制,改用铅粉。 愚谓与其去铅,何若径用野茉莉花种,不必烧铅,研细亦颇洁白,画家可试用之。”[51](P97)铅粉为化学颜色,其鉴别与避忌较任何颜色为甚,其色虽白,但保存使用若不得法,偶一不慎,极易变暗变黑。 《本草纲目》载:“胡粉能制硫磺又雌黄,得胡粉而失色,胡粉得雌黄而色黑,盖相恶也。”[52](P277)松年根据多年的用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以野茉莉花种代替铅粉,以植物性颜料代替矿物质颜料,色泽“亦颇洁白”与铅粉无异,而且还可以与墨色相融,互为映衬,产生富有变化的色彩效果。
括而言之,松年的色彩理论虽然还在笔墨范畴之内,“用色如用墨,用墨如用色”,基本上还是沿着“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的笔墨中心论展开,但在用色、用笔、用水和纸性的论述之中,色彩的独立价值得以体现,尤其是关于用水与用色的技法分析,更是见解独到,不落古人窠臼。 而且对于白色铅粉颜料的创新,解决了困扰古代画家已久的“返铅”问题,为中国画色彩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表现路径。
结语
《颐园论画》中关于笔墨问题的论述,不仅表现了松年对中国画理论与技法的思考,更可以窥视晚清画论中笔墨观念的嬗变。 松年在用笔、用墨之中,更侧重于对水法的探讨,而且兼及纸性辨别和用色技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古代画论中“论水”的缺失与空白。 用水用色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和纸性、用笔有着密切关联,“其要决尽在辨明纸绢之性”[53](P36),要因材施法,还指出“二者皆赖善于用笔,始能传出真正神气”[54](P35)。 针对笔墨与造化的关系,松年更是撇开“南北宗论”的成见,直言“尤在于以造物为师”[55](P66),强调写生,观察真景,由表及里的进行“得之于心,施之于手”的艺术加工,创造笔墨的新意境。
过往的研究一般认为水法的运用或“师法造化”的写生是20 世纪中国绘画和绘画思想的一大特色,实则在19 世纪后期已经发轫或已具雏形。 19世纪的晚清画论并非处于凝滞状态,而是集前代之大成,开后世之先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命题,为20 世纪中国画改革破除了理论障碍和思想禁锢,作了必要的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