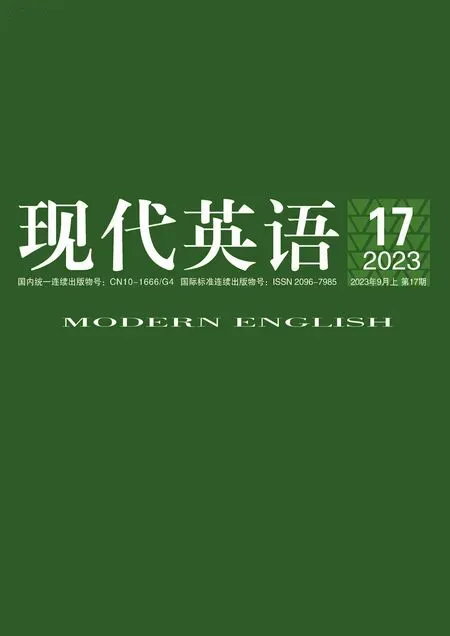从认知隐喻视阈议«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明喻翻译
程羽麒
(新疆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510000)
英语和汉语在表达上存在文化差异,无法逐字对应翻译,该体系下的隐喻翻译毫无疑问也存在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翻译存在一定相同点和不同点,其程度水平和实现途径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揭示。 因此,需借助跨语言、跨文化的研究来证明这些问题,以推动翻译研究朝科学实证方向发展。
一、 认知隐喻视角下的明喻
(一)语言与认知
在不同语言环境下,长大的人会有不同的逻辑思维模式和文化价值观。 利用语言认知世界,需要对事物组合归类,即范畴化。 但因为世界是变化的,认知也是不断深化的,为表达人类还未认识或发现的自然范畴,用常规语言表示非常规事物,就需要引入隐喻化的概念[1]。 总之,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记忆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
(二)语言与隐喻
语言不是静态,是动态的,导致语言变化的是隐喻。 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几乎离不开隐喻的运用。 隐喻也被认为是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之一。使用隐喻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抽象概念和思想。 从隐喻和思维方式来看,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现象,还可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通过观察隐喻的使用,人们可以了解到一个文化中普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隐喻不仅是语言中的常见现象,还可以影响人们的认知、思维方式以及文化传承。
(三)认知隐喻与明喻
明喻可以使文章语言鲜活,提升形象特色、层次感,增添内容生命力。 在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著作«修辞学与诗学»中,隐喻被定义为意义的转换,而明喻被列为隐喻的一种形式[2]。 明喻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本体、喻体和比喻词[3]。 有学者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明喻翻译,但是较少从认知隐喻视域探讨。 文章从该角度探讨了徐穆实«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的明喻翻译,旨在为往后需要英译的对外传播的汉语文学作品提供参考。
二、 徐穆实的翻译观及«额尔古纳河右岸»翻译研究
(一)徐穆实的翻译观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版作者是美国的翻译家徐穆实(Bruce Humes)。 徐穆实自2001 年开始,先后翻译了两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以及部分小说样章。 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也关注着中国的某些社会问题。 他希望透过自己的博客“Ethnic ChinaLit”,让国外的读者更多地认识到少数民族生存现状,并呼吁把话语权还给民族作家。徐穆实的翻译观点注重文化转化、信实原则、独立创造和沟通交流。
第一,正如徐穆实自己所说,虽然翻译文学的人并不能发家致富,但最大的乐趣就是能挑选自己喜欢的作品翻译,随着中国文学的不断翻译,中国文学走出去也就不远了[4]。 徐穆实认为翻译是文化之间的转化过程,翻译家应该具备深入理解两种文化背景和语言的能力。 他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和风格,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原作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第二,徐穆实强调翻译的忠实性,即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作的意义和表达方式。 他认为翻译不仅是文字的转换,更是要传递作者所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和艺术效果。 徐穆实觉得真实性和可信度都很重要,简单来说,就是看故事中的人物和事物是否令自己心悦诚服,而在作者所虚构的世界中,自己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具有真实性。 经研究发现,鄂温克语属于古斯语系,不属于汉语语系,于是把鄂温的人名、地名和一些特殊的词语,按分类处理的形式直接音译,保留了原文的特点[4]。 也正因如此,徐穆实才能忠实地将这部具有浓厚少数民族特征的作品向世界展示。
第三,徐穆实尊重原文内容和语言特点,但主张翻译家具有独立的创造性。 翻译并不仅仅是机械的语言替换,而是要根据目标语言和文化的特点进行灵活的再创作,使译文能够在目标文化中产生相似的效果[5]。
第四,徐穆实强调翻译家应该具备深入理解两种文化的能力,并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忠实于原作的意义和表达方式;同时根据目标语言和文化特点进行灵活的再创作,以实现与读者的有效沟通和交流。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及其英译研究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中国女作家迟子建创作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作品,该小说获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小说中描写了春华秋实、日月星辰、夏雨冬雪、高山流水、甘露苔藓、虫叫鸟鸣的四季轮回、自然更替,也谈到了生老病死、生命轮回的人生哲学[6]。 该书的英译本之所以能在国外传播效果俱佳,主要得益于美国汉学家徐穆实对其进行的翻译和传播。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译作研究方面,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关注译者主体性、翻译技巧、民族原生态方面。 吕晓菲和戴桂玉提出该译本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人类共同的希望、梦想、悲伤、恐惧、无奈,以及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上[7]。 陈美龄在归化和异化的视角下分析翻译策略,发现其中异化策略使用更多,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方法也较为常见,使读者更加身临其境,能够体会鄂温克族人的风俗与特色,充分表现了原文的语言特点与民族文化信息[8]。 就明喻翻译而言,国内基本有从前景化视角和纽马克模型出发研究的,但是鲜有从认知隐喻角度来讨论徐穆实的英译本。 张静静从前景化视角下分析这一少数民族作品中的比喻修辞翻译现象,认为徐穆实主要采用直译法、改译法、换译法这三种翻译方法[9]。 潘琪和肖维青基于翻译学者纽马克提出的隐喻翻译方法为基础,对译文中隐喻表达的处理方式进行了分析和归纳。 他们总结出适用于民族题材文学作品的隐喻翻译策略[10]。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隐喻修辞数量众多,因此文章选择«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明喻为对象,从认知隐喻视阈视角分析徐穆实与迟子建的汉英平行文本,做一番整体考察和系统性研究。
三、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明喻翻译研究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明喻概况
«额尔古纳河右岸»原文中用得最多的修辞格是明喻,小说中共有404 处比喻修辞,其中有283 例为明喻,占比为70.05%。 明喻与其他比喻修辞最区别的标志就是喻词,因此对作品的喻词进行了数量统计。 统计后发现,“像”类喻词使用十分突出,共有246。 其中,“像/好像”有164 处,“像/好像……一样”有72 处,“像/好像……似的”有10 处,“一样”有72处,“仿佛”有7 处,“如”有4 处,“似”有4 处,“般”有2 处,直接用“把……比喻成”的有2 处。 作者使用上述这些明显的喻词,能直截了当地让读者看到是在打比方,也体现出作者朴素直白的语言风格。 文章选取徐穆实译本中的明喻修辞翻译进行考察,以下是对«额尔古纳河右岸»明喻翻译的具体探讨。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明喻翻译探索
1. 保留本体、喻体及喻词的明喻翻译
徐穆实相信大部分的比喻都是可以为西方读者所理解的,因为人们的认识经验、认识模式都是具有普遍性的,而且这些模式都是开放的。 在此条件下,他通过直译,把源语中的比喻形象转移到译文中,并将其传递到译文读者,从而保持了原文想传达的内容。
例1:
ST:月亮升起来了,不过月亮不是圆的,是半轮,莹白如玉。 它微微弯着身子,就像一只喝水的小鹿。
TT: The moon has risen, but it's not round. A quarter moon of flawless white jade. It bends over gently like a fawn lapping water.
例2:
ST:所看到的那两匹布,一匹青蓝,一匹乳黄。它们一明一暗地站在那里,就像黑夜和黎明。
TT: I'll never forget the two rolls of cloth that I saw in the store, one milky yellow, one deep bluegreen. They stood there, one dark and one bright, like the night and the dawn.
以上两个例子中,月亮像喝水小鹿,青蓝和乳黄的两匹布像黑夜和黎明。 这种类型的对应性在汉语和英语中普遍存在,译者往往采用忠实于原文、符合目的读者认知规律的“直译”。 与此同时,隐喻也出现了多种形式,除了例子中“like”,译文中还使用了“as if”“as...as...”“resemble”等。
2. 保留本体、喻体的明喻翻译
«额尔古纳河右岸»英译本中的一些明喻翻译呈现为形容词性隐喻、名词性隐喻、动词性隐喻。 这种明喻翻译保留原词和喻词,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使得译文语言简练的同时让原文风格再现。
例5:
ST:马粪包总要咒骂那些伐木点,说它们是生长在山中的一颗颗毒瘤,把动物都赶跑了。
TT: They're like tumours growing in the mountains that scare off the animals.
例6:
ST:他刚来到我们中间时就像一块“湿柴”,毫无生气,但我们的热情和快乐很快驱散了他身上的阴郁之气。 他被我们点燃,化为了一簇快乐的火苗。
TT: When he came among us he was a piece of wet kindling, but our enthusiasm and joy quickly dispelled the air of gloom about him. We ignited him and he transformed into a joyful flame.
汉语的明喻翻译通常表现在英语的名词性隐喻。 上述中源域“伐木点”“他”的目标域分别为“毒瘤”“湿柴和火苗”。
3. 转换喻体的明喻翻译
尽管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的经验与模式具有共同之处,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仍有差异。 对民族题材这类极具文化特色的作品而言,按照原喻体直译,会抹杀了原语文化特色,无法真正实现原文最核心的文学价值。 徐穆实通过对喻体进行适当转换,采用转换喻体的明喻,翻译强化了原民族文化色彩,对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损失进行补偿[11]。
例8:
ST:虽然我没有被枪击中,但我也像是父亲手中的一件猎物,毫无生气。
TT: Even though a bullet hadn't struck me,I was lifeless like the kandahang.
例9:
ST:伊万的个子很矮,脸很黑,额头上有一个红痣,像颗耀眼的红豆。
TT: He was rather short,his face very dark,and he had a reddish mole that stood out like a ‘love pea’on his forehead.
从例8 和例9 可看出,译者在处理“猎物”和“红豆”两个喻体的时候,并没有直译为“prey”和“red bean”,而是转换成“kandahang”和“love pea”,意思即“堪达罕”(前文提到过的动物)和“相思豆”,一点点转换既译出了作者意思,又传达了浓厚的民族特色。
四、 结论
综上所述,从认知隐喻的角度来看,明喻的翻译是非常有意义的。 徐穆实的翻译思想,不局限于直译或意译,而是将中文著作忠实地译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易于西方读者理解接受。 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约有80%的明喻翻译保留了原词和比喻意象,旨在向英语读者忠实传递原著的文化信息和写作风格。 此外,汉语明喻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可直接译为英语,还可转化为英语中的形容词、名词和动词隐喻。 徐穆实的翻译具有创造性,在强调原文风格上迎合了目标读者认知。
——以《三体》明喻翻译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