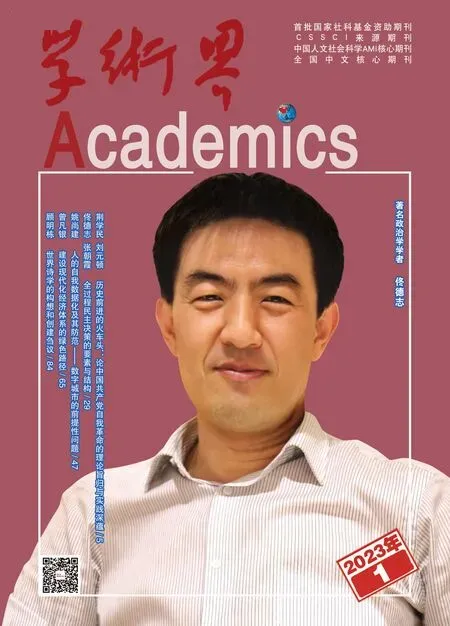晚清“文明”论语境中的西方文明批判〔*〕
张 勇(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迄今为止,学界已经对晚清“文明”论的兴起及其嬗变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这些研究勾勒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从拒绝到承认再到向往的转变过程,背后对应的则是晚清以降知识分子认识世界并探索救亡道路的历史实践的变迁。西方作为文明的象征而被接受,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唯一的文明,甚至一变而成为劣于西方的、停滞的文明。这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挫折,但是其中也存在着某种循环论的悖论:与其说西方文明优于中国文明是西方优胜、中国挫败的原因,毋宁说前者是由后者逆推而来的结果。因此,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可以说是未经实际验证的“伪”命题——既未经证实,也未经证伪,当西方文明被当作某种榜样而追逐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个陷阱,即西方的强者逻辑和霸权主义。
有研究者指出,19世纪欧洲的“文明”观念“把‘文明’的进步性看成是欧洲文明的特性”,“这种‘文明’优越感,正是欧洲中心主义与霸权主义心态的反映”,及至19世纪下半叶,这种文明观念又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1〕这种文明观念直接或者经由传教士、日本知识界传播到晚清知识分子那里,成为他们构建自身文明观时重要的知识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文明观念还得到了进化论、“公理”等其他观念强有力的支撑,后者比前者还要牢固得多。那么,晚清知识分子在认知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能否洞察并规避其中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关于西方文明的直接经验尤其是西方侵略的事实能否推翻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信念?哪些知识资源限制了或帮助了他们批判性地审视西方文明?本文试图在晚清“文明”论的语境中讨论这些问题,梳理不同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实践,以期对当下正确认知西方文明有所启示。
一、西方文明批判的阻碍:作为“公理”的一元论进化观
有研究者指出,以“文明”移译英文civilization较早可以追溯至外国传教士编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中。〔2〕不过,现代意义上的“文明”概念在中国精英知识分子中得到较多运用则是在甲午战后,其流行与戊戌维新思潮尤其是梁启超的“带动和示范”密不可分。〔3〕梁启超的重要性在于,他将文明论与进化论进行了融合,不仅以此作为变法的立论基础,而且用来概括世界发展的大势。在甲午战后撰写的《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借用“西国公理家”的说法,将“人种递嬗递进之理”概括为“其种日进于善,由猩猴而进为人也,由野番贱族而进为文明贵种也”。〔4〕这里的“西国公理家”是指达尔文,其进化论则被通俗地解释为由野蛮至文明的进步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也被赋予了“公理”的性质。及至1902年,梁启超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5〕
可见,梁启超的这种文明观是一元论的,背后暗含着一种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他将文明转换为文明化的问题,相信不同国家都遵循着同样的文明化进程。佐藤慎一指出:“变法派的文明观的特色在于从文明的条件中彻底排除了人种、民族这些实体性的方面。在他们看来,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与人种或民族的区别完全是不同层次上的问题”。〔6〕的确,在梁启超那里,中西文明的差异被归结为阶段的区别,“今日欧美所谓文明,过渡时代之文明也,若中国者,则又并过渡时代而未能达者也”。〔7〕野蛮和文明的界限是变动的,不同的国家都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故文明、野蛮之界无限也。我方自以为文明,而人之野蛮我者,不知凡几矣,故全在比例而已。今日我视欧洲为极文明,数百年后视之,则又为野蛮矣”。〔8〕西方文明本身也是不完美的,仍处于文明化的进程之中,这一看法使得梁启超既可以解释西方文明的缺陷,又不妨碍他将西方文明作为中国学习的对象。但是,其中遗留了一个梁启超并未深入思考的问题,即中国是否可以规避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陷阱。
梁启超的文明观与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的看法几乎一致,实际上,他也受过后者的“直接影响”。〔9〕福泽谕吉著作的第二章即题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尽管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他也注意到了“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而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但是福泽谕吉还是强调,“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因为文明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定的顺序和阶段,即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10〕显然,福泽谕吉持一种一元论的、进化的文明观,将西方文明视作普适的,并以此为标准去衡量东方文明。东方文明被认为是低劣的,在东方文明中,日本和中国又存在地位的分殊。正如子安宣邦所分析的,“福泽的《文明论概略》和西方的文明史论一样,将中国视为文明论的他者,日本则被纳入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而非过程之外”。〔11〕梁启超虽然与福泽谕吉不同,念兹在兹的是中国能够进入到文明的进程之中,但是他在接受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时,仍然不自觉地蹈袭了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对其霸权主义的立场也缺乏足够的警醒。
这些都决定了梁启超很难真正地去批判西方文明,即使他在现实中看到西方文明中残暴的一面,也难以撼动他对西方文明的信念。1903年4月,梁启超在谈及黑龙江贫民二百余人因淘挖金沙被俄国人枪毙一事时,联想到了八国联军的行径——一方面以文明而自居,将义和团称为“文明之蟊贼”,一方面在占领京津后杀害了百十倍的中国人。梁启超激愤地反问道:“文明乎?人道乎?待野蛮人之法例应尔尔乎?”但是,他迅速又转向了另一问题,将文明视作强者的特权,“德意志学者之论,惟强者乃有权利。岂惟权利,文明人道,亦惟强者所私有耳”。〔12〕1905年初,梁启超在提到上海租界当局封杀《警钟日报》时,也展现了同样的逻辑。他并未由此质疑西方所谓“文明”的本质,而是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文明国之法律,固文明也。虽然,不与非文明人共之。”〔13〕梁启超总是把文明的问题与富强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跻身文明国的关键在于成为强者,然后才可以与西方共享文明。
梁启超有时非常接近于识破西方文明的假面目,比如他在讨论到日本侵吞满洲的野心时指出,“今世所谓文明国者,罔不虎其质而羊其皮,其野心固路人皆见,犹必口仁慈貌义侠以自饰,此各国所同,而日本亦其一也”。〔14〕当梁启超还从越南流亡者口中听到,法国殖民者以“族株”“发冢”的野蛮法规遏制越南人民的反抗时,他的反应是,“余矍然曰:有是哉!以世界第一等专制之中国,近古以来,此种野蛮法律,且几废不用。曾是然以文明人道自命之法兰西,而有是耶?而有是耶?呜呼!今世之所谓文明,所谓人道,吾知之矣!”这段文字形象地传达了梁启超了解到西方文明真相后的惊诧、失望之情。梁启超进而对整个西方文明乃至其源头产生了怀疑:
今欧洲各国文明,皆滥觞罗马。罗马全盛时代,即略夺其殖民地人民之生命财产,以庄严其都会,以颐使其左右。罗马文明,实无数人类之冤血之苦泪所构结晶体也。天道无亲,惟佑强者,而罗马之声誉,遂数千岁照耀天壤。彼其嗣统之国,若今世所谓欧洲某强某强者,受其心法,以鸱张于大地,施者岂惟一法兰西,受者岂惟一越南?滔滔天下皆是也。
虽然梁启超甚至开始质疑“天道”的公平性,但是他未能由此上升到对“天演”合理性的审视,反而从“天道”中看到了强权的本质,相当于赋予了强权的合理性。梁启超固然痛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和残暴统治,不过,他只是把这些行为打上“伪文明”的标签,反而维护了“文明”本身的正面形象,“自今以往,世界进化之运,日新月异,其或不许此种披毛戴角之伪文明种横行噬人于光天化日下”。〔15〕遗憾的是,他并未继续追问“进化”如何能够淘汰“伪文明”,似乎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对于西方文明国的实际观察同样未能促使梁启超扭转自己的文明观。1903年5月,梁启超赴美国,在这片新大陆上游历了半年多。美国曾被梁启超誉为“今日最强盛文明之国”,〔16〕不过,他在这次实际考察中却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看到了贫民窟,他坚信“观于此而知社会之一大革命,其终不免矣”;看到了工人被奴役的状况,他感慨“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者也”。尤其令梁启超震撼的是美国黑人的非人待遇,他质问道:“美国独立檄文云:凡人类皆生而自由,生而平等。彼黑人独非人类耶?呜呼!今之所谓文明者,吾知之矣”。即使是梁启超最为关注的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他论及的也是“缺点居多”。然而,这些都没有动摇梁启超对于美国文明的信念,“其所长者多多,固不待问”,他坚定地认为,纵观世界,“文明西渐之潮流”不可逆转,“文明中心点日移于西”。〔17〕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潮流”便是体现了世界发展趋势的“公理”。
实际上,在近代知识分子中,像梁启超这样亲眼目睹过西方文明者不在少数,反应却不尽相同。比如早在1884年,黄遵宪就在致日本友人的书信中称,“美为文明大国,向所歆羡,及足迹抵此,乃殊有所见不逮所闻之叹”。〔18〕八年之后,黄遵宪在致梁启超的信中又谈及了他的民主信仰是如何被实际观察中所得的印象击毁的:“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这使得黄遵宪对当时知识分子高唱入云的自由民权之说不以为然,他希望在君权和民权之间求得某种平衡,“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19〕将关注点重新投向民智和民生的问题上。黄遵宪提供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虽然并不高明,但是他至少突破了西方文明制度的束缚。究其原因,恰恰缘于黄遵宪并没有如梁启超那样将西方文明与“公理”及进化观念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批判西方文明的真正阻碍正在于西方文明优越性的理论根基——作为“公理”的一元论进化观。
二、关于西方文明的文野之辨:公理还是强权?
对晚清知识分子而言,认知西方文明首先遭遇的一个困境便是:如何调适西方文明与其侵略行为之间的矛盾。在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西方侵略经常被美化为一种文明进步。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宾塞在其著作《社会学研究》中,不仅用野蛮、半开化、文明等区分不同民族,而且认为征服民族战胜野蛮、半开化民族,从而使分散的社会实现联合,是后者文明化的一个步骤。1903年,《社会学研究》由严复译为《群学肄言》印行,〔20〕从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知。尽管严复对斯宾塞颇为尊崇,但是他并未全盘接受后者的观点。1906年,严复在上海为中国环球学生会作演讲,针对的是当时知识界盛行的“有强权无公理之说”。严复举了一个例子:英国殖民埃及,“为之大变其政治,文明气象十倍于前。然自埃及人言,则英人虽有大造于埃及,其所用者,固强权也,而自欧美人观之,则英之所行,为大合于公理”。严复则试图以公理去驾驭强权,他强调,“无公理之强权,禽兽之强权也”,“惟主公理而用强权,斯真人道之最贵耳”。〔21〕当然,严复所说的“公理”并不等同于西方的“公理”,因此,他引入了“人道”的概念。
梁启超也深受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在辨析西方侵略是文明抑或野蛮时,同样触及了人道的问题,不过,他倾向于认为西方侵略符合人道。他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写道:“苟能自强自优,则虽翦灭劣者弱者,而不能谓为无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则然也,我虽不翦灭之,而彼劣者弱者终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视为蛮暴之举动,今则以为文明之常规”。梁启超所说的“天演之公例”或者世界发展的大势即是民族帝国主义,“近世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皆迫于事理之不得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为,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梁启超在前言中交待,他写作该文时参考了美国人和日本人的多本著作。由于对天演进化的迷信,他对这些著作中的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缺乏必要的警醒,他也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把“强权”解释为中性的概念——“惟强者有权利,谓之强权”。〔22〕狭间直树指出,梁启超所使用的“帝国主义”一词包含“绝对主义”或“历史发展的正常方向”的意思。〔23〕这两层意涵都含有进化论的色彩,也限制了梁启超从批判的立场上去看待帝国主义。
梁启超关于民族帝国主义大势的论断在当时留日学生中流布甚广,比如《湖北学生界》中的一篇文章就几乎重复了梁启超的论述,“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由民族主义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何?即曰野蛮人无开发土地富源之能力,文明人必代为开拓之;又曰优等人种虐待劣等人种,为人道之当然者是也”。不过,该文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却与梁启超背道而驰,“各国挟此主义,如贪狼恶虎,四出搜索,不顾天理,不依公法,而惟以强权竞争为独一无二之目的,杀人如草不闻声,此帝国主义之真本领也”。〔24〕如果说在梁启超那里,强权即公理、公法,那么这篇文章恰恰从公理、公法的角度对强权进行了批判,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有强权无公理之说”的普遍立场。
实际上,即使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也不乏批判帝国主义的文章,如署名“雨尘子”的作者在《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中称:“欧人之文帝国主义,或根尼这之极端之个人主义,或凭借达尔文之进化论,以为口实。然帝国主义,果如是乎?帝国主义,质言之,则强盗主义也。因己之不足而羡人之足,因己之膨胀而芟除世界之不如己者,乃有所谓文明、所谓野蛮、所谓天职、所谓义务等议论以文之。”〔25〕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了尼采的个人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经常被用来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依据,而且揭示了帝国主义以“文明”“天职”“义务”等高尚的名称来美化其野蛮的侵略行径。因此,对帝国主义的真正批判必然要涉及对这些理论根基及美名的辨析,需要进一步追问文明的内涵。
维新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康有为对殖民侵略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即与他对“文明”的理解有关。康有为认为,“文明国当崇礼义,不当不仁而自翦伐。然以文明国灭文明国,虽无道而文明无损也;若文明国从野蛮以灭文明国,则胥天下而为野蛮,而文明扫地、人道退化矣”。〔26〕“礼义”“仁”“人道”等词汇表明,康有为是从儒家义理的角度来理解文明的。他虽然也将文明与进化联系起来,但是他在其中融入了“夷夏之分”以及他的春秋三世说,从而赋予了文明很强的道德内涵。另一方面,康有为在其道德化的文明观念中保留了关于退化的思考,他也以此去看待“文明国”的侵略行为,甚至于整个现代文明。
康有为将文明/野蛮比附为夷夏之分,“夷夏之分,即文明野蛮之别”。〔27〕这种区分的标准是道德,“孔子之言夷狄,非论其地,非论其人,惟在其德;文明者则进之,野蛮者则退之而已”。〔28〕在康有为的文明观中,孔子被奉为“文明之教主、文明之法王”,“盖人道进化以文明为率,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29〕这种人道进化即文明化的过程正对应着“春秋三世”的变迁:在据乱世,常有野蛮吞并文明之事;“若今则渐入升平世,无复有野蛮乱文明者,只有以文明兼野蛮。至太平之世,则大地种族混合,天下如一,治化大同,无复文明、野蛮之别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文明兼野蛮”不是指文明国消灭野蛮国,而是指后者的文明化,“盖升平时小国亦日进文明,得与大国同也”。〔30〕
道德化的文明观以及关于大同世界的想象,使得康有为能够看到现代文明的问题,“愈文明则战祸愈烈。盖古之争杀以刃,一人仅杀一人;今之争杀以火以毒,故师丹数十万人可一夕而全焚”。〔31〕康有为并不像梁启超那样将竞争看作是文明进步的必要手段,而是反问道:“竞争之世岂有所谓文明哉?但见为武明耳。”〔32〕康有为流亡海外多年,足迹遍布欧美,这为他提供了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今世界之较文野,专就外观比之,非竞道德也。欧美愈称文明,而其人之嗜利、无耻、贪诈、不顾信义尤甚,与吾华乡曲人之心直言信相去万里。盖吾华都人品行之不如乡人亦甚矣。”〔33〕康有为颠倒了当时主流的中西文明彼强我弱的看法,认为欧美文明较于中国文明是一种退化,现代文明相比于前现代文明也是一种退化。
主要原因在于,康有为使用的“文明”概念不完全是英文civilization的对译词,而是保留了其在中文传统语境中“文教昌明”的含义。因此,康有为并不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那样,将文明划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在他看来,文明本质上即是精神的,富强与文明是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康有为承认西方的富强,但是他反对将富强等同于文明,也反对中国人将欧美当作文明的样板亦步亦趋。他批判道:“乃吾国人今但以欧美一日之富强,不加考察想象,视人如帝天,自视为野蛮,则其奇愚孰甚焉!其忌祖媚外抑何一至于此?而不克自立乃尔也?”〔34〕可见,康有为更接近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文明观——不承认西方也有文明。1905年,他提出“物质救国论”的论调,也就不奇怪了,在他看来,西方值得效仿的只有富强以及作为富强根本的“物质之学”。正如康有为在书中所强调的,“魏默深之论,至今尤为至论也”,〔35〕“物质救国论”其实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说相去不远,康有为只是把“长技”从洋务派所倡导的船坚炮利扩展到了“物质之学”而已。
与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相似的是,1907年,杨度祭出了“金铁主义说”。不过,与康有为不认可西方文明不同,杨度承认西方文明,且认为其中兼具野蛮的面向。杨度指出,“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则皆文明,对于外则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自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针对这一世界状况,杨度提出中国应取的对策——“金铁主义”,即“世界的国家主义”或曰“经济的军国主义”,“实因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36〕杨度关于文明国与野蛮世界的论述,延续了他对文明与野蛮关系的一贯看法。早在弘文学院读书期间,杨度就听取了院长嘉纳治五郎要学习欧美文明的建议,其中便包括“使文明其脑筋,而野蛮其体力”。〔37〕在1903年所撰的《湖南少年歌》中,杨度写道:“毕相拿翁尽野蛮,腐儒误解文明字。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在杨度看来,文明与野蛮不是对立的,而是融为一体的,西方文明之中包含了野蛮的强力。就此而言,杨度与梁启超的观点更为接近,虽然他不像梁启超那样将西方的强权视作“公理”或“公例”,断言“于今世界无公理”“公法何如一门炮”,〔38〕但是他并没有由此去批判西方的强权,而是把它当成了努力的方向。
三、西方文明批判的新的知识资源: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其他
关于西方文明的认知,不仅立宪派知识分子之间存在分歧,更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争中的焦点问题。20世纪之初,两派各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平台展开论争,其中屡屡涉及的即是中国能否走西方文明道路的问题。革命派并不完全排斥西方文明,孙中山认为,中国应“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不是“全盘照搬”。〔39〕他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贤良政府”和“纯洁的政治”作为保障,即使是“欧洲物质文明的应用品的输入”,也只会让中国的状况“越来越坏”,“因为这就为勒索、诈骗、盗用公款开辟了新的方便的门路”,所以,“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只有用根绝官吏贪污的办法才行”。〔40〕孙中山注意到,民生问题实际上与民权问题密切关联,没有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改良,民生问题也不能单独得到解决。
孙中山看到了欧美文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因此,孙中山所提的“革命”同时包含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内容。〔41〕胡汉民持论相同,他指出,“惟文明之进步速,则社会之问题亦接踵而生,不预为解决,则必有欧美今日噬脐之悔。夫欧美今日之富量,惟在少数,贫富阶级,悬绝不平,劳动者之痛苦,如在地狱。此亦社会主义者所恒道矣”。对于梁启超的看法——中国没有条件实行社会革命,胡汉民引用国外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予以反驳,“近世社会主义学者,恒承认一国社会主义之能实行与否,与其文明之进步为反比例”。〔42〕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非不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他同样观察到,“夫自生产方法革新以后,惟资本家为能食文明之利,而非资本家则反蒙文明之害”。但是,他否定社会革命论,依据的恰恰是他对中国国情的考虑,“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之趋均为期,质言之,则抑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梁启超认为,中国面临着“国际的经济竞争”,只有“结合资本,假泰西文明利器(机器)”,实现国家的富强,才能在这种竞争中立足。他甚至断言,“文明进步者,资本进步之谓也”,〔43〕“私有制度”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44〕因此,梁启超尽管知道垄断资本主义的弊端,但还是呼唤中国“托拉斯”的出现。“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夫政治界之必趋于帝国主义,与生计界之必趋于托辣斯,皆物竞天择自然之运,不得不尔,而浅见者从而骇之,从而尼之,抑亦陋矣”。〔45〕就像他赞同帝国主义一样,梁启超立论的基础最终仍然落脚于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革命派对梁启超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胡汉民驳斥道:“以资本包一切文明,可谓奇语。……然则资本家者,可称为一切文明之代表欤?究之此说万难自完。”〔46〕冯自由则从民生主义的立场批判了“托拉斯”,“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托辣斯(Trust)于民生主义为绝对的反对”。冯自由进而指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反文明本质,“盖世界文明之真伪,以人类能享权利自由之多寡为断,使大多数人民而蜷伏于少数资本家羁制之下,则其为文明乎?抑野蛮乎?进步乎?抑退化乎?”〔47〕
如同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当时兴起的无政府主义也为知识分子批判西方文明提供了新的知识资源。刘师培、何震在他们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上,介绍过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如刘师培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畧夺》,克氏在其中发问道:“处于文明之社会,则吾人当富裕,顾何以多数者陷于贫困乎?又何以群众沦于悲贱之役乎?”〔48〕《天义》上还两次刊载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一次为节译,一次为全译,足见编者对该文的重视。托尔斯泰此时被当作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去介绍,刘师培概括说:“俄杜尔斯德,其学术大旨,在于救济贫民及反对伪文明”。〔49〕托尔斯泰在《致中国人书》中比较了欧洲与中国的状况,认为欧洲只是军备上比中国强大,“然观其人民之境遇,非惟不足与支那人民较优劣也,且实为不幸之极端”,他告诫中国人“断不宜取法西人”。〔50〕这样,西方不仅不再是东方应当效仿的对象,而且变成了前车之鉴。托尔斯泰希望欧亚人民能够冲破“邪僻之欧洲文明网”,去探索真正的自由之路。〔51〕
凭借这些思想资源,刘师培、何震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对西方文明展开了批判。他们指出,“欧美、日本各国,仅有伪文明。若衡其政治,则较中国为尤恶;即人民无形之自由,亦较中国为减。惟物质文明似较中国为进步,然处政府擅权之国,则物质文明亦为民生之大害”。刘师培、何震对欧美和日本伪文明的论断看似与前文论及的梁启超的观点有所重合,实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他们所论述的是西方文明的全盘和性质,而梁启超只是针对西方文明中的某些面向,又将这些面向归诸于文明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缺陷。即使是对于西方物质文明,刘师培、何震虽然原则上并不排斥,但是他们也强调要有无政府主义作为其保障,“盖西人物质文明,均宜效法,惟宜用之于无政府之世”。〔52〕在这一点上,刘师培、何震与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的看法相近,尽管两派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同,但在反对资本主义文明方面,他们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天义》上刊登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译文,其中洞察了资产阶级将整个世界卷入到所谓的“文明”之中,不仅“使地方屈从于都市支配之下”,“更使野蛮及半开化诸国民屈服文明国民,农作国民屈从绅士国民,以使东洋屈从于西洋”。〔53〕遗憾的是,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未能充分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从而将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推向深入。
在革命派阵营中,对西方文明批判得最为深入的是章太炎。1907年3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人在日本发起“亚洲和亲会”,该会宗旨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54〕章太炎反抗帝国主义,其独特之处在于从学理上推翻帝国主义存在的根基。他不仅指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而且洞察到帝国主义以“文明”为旗号美化其劫杀行为,“综观今世所谓文明之国,其屠戮异洲异色人种,盖有甚于桀、纣。桀、纣惟一人,而今则合吏民以为之;桀、纣无美名,而今则借学术以文之”。〔55〕因此,章太炎试图破除的便是西方文明的“文明”假面及其背后的“学术”,他的知识资源主要是佛教唯识宗。
章太炎指出,“今之言文明者,非以道义为准,而以虚荣为准。持斯名以挟制人心,然人亦靡然从之者。盖文明即时尚之异名,崇拜文明,即趋时之别语”。也就是说,“文明”作为“名”的霸权左右了人们的是非判断。章太炎甚至激进地说:“诚欲辩别是非者,当取文明野蛮之名词而废绝之。”〔56〕因为章太炎清楚,要破除“文明”作为“名”的霸权是最为艰巨的任务,“大抵善恶是非的见,还容易消去。文明野蛮的见,最不容易消去”。所以,章太炎指出,“第一要造成舆论,打破文明野蛮的见”。〔57〕这意味着要生产新的知识,瓦解“文明”赖以存在的根基如进化、公理等观念。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四惑论》等文章便是循此逻辑所作的努力。章太炎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进化论,“吾不谓进化之说非也”,而是对其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善恶苦乐同时并进”的“俱分进化论”。从“俱分进化”的角度来看,“东方诸国,诚人人趋附势利矣,犹以此为必不应为之事。独欧洲则举此以为天经地义(除少数之持社会主义者)。此非其进于恶耶?”〔58〕章太炎突破了东/西二元对立视野,没有将欧洲视作一个整体,而是在其中区分出了社会主义者,而且在一种“恶的进化”观中同时获得了审视中西文明的视野。章太炎还据此指出,“世俗所谓文明野蛮者,又非吊当之论也”,“是则文明者,即斥大野蛮而成,愈文明者即愈野蛮”。〔59〕他注意到,“以蒙古游牧腥羶之国,其待印度,犹视今之英人为宽,然后知文明愈进者,其蹂践人道亦愈甚”。〔60〕可以看出,章太炎的中西文明比较观及文明退化观与康有为的看法有部分重合,他关于西方文明兼具野蛮性的论断则与杨度有所相近,不过,章太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将西方文明当作效仿的对象,也未整体上排斥西方文明,从而固步自封于中国文明之中。
在《四惑论》中,章太炎更是对包括进化在内的四种观念进行了拆解。章太炎在开篇写道:“昔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曰名分。今人以为神圣不可干者,一曰公理,二曰进化,三曰惟物,四曰自然。”他试图颠覆“公理”“进化”“惟物”“自然”类似于“名分”的原理性质,因为正是它们构成了“文明”坚不可摧的基础。比如,世人提倡物质文明都是以科学、惟物作为依据,“世人之矜言物质文明者,皆以科学揭櫫,而妄托其名于惟物”。〔61〕章太炎认识到,要想真正破除世人对于“文明”的迷信,最终需要瓦解以“公理”“进化”“科学”等为根基的科学世界观,构建别样的世界观取而代之。正如汪晖所指出的,章太炎“试图重新构筑一个与以‘公’、‘群’和‘进化’观念为基础的科学世界观截然相反的世界观”。〔62〕
在章太炎的影响下,青年鲁迅也开始批判性地审视西方现代文明。他不仅批判了中国当时所谓“志士”“喋喋誉白人肉攫之心,以为极世界之文明者”,反对将已是“迁流偏至之物”的西方文明不经思考地“举而纳之中国”,而且洞察了“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将“富有”“路矿”“众治”“物质”等一一从文明的内涵中排除出去,提出了文明“根柢在人”的主张。〔63〕在《破恶声论》中,鲁迅也如章太炎一样,对当时流行的种种“恶声”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拷问:“至所持为坚盾以自卫者,则有科学,有适用之事,有进化,有文明,其言尚矣,若不可以易。特于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乃独函胡而不与之明言,甚或操利矛以自陷。”〔64〕当科学、适用之事、进化、文明这些概念不再是不证自明的,如何认知和学习西方因而也就重新成为了一个有待探索的问题。
总体来看,伴随着晚清“文明”论的兴起,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便是“文明”,他们的“文明”观中既包含了对于西方文明的认知,也预示了他们为中国救亡图存所开出的“药方”。归根结底,不同的“文明”观的核心分歧在于中国是否要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梁启超、杨度等人并不是看不到西方现代文明的缺陷,但是他们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中国要想在世界上立足,就必须成为如同西方一样的存在,甚至对西方文明中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也失去了应有的警醒。康有为持一种儒家义理化的“文明”观,藉此发现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问题,不过,由于否定西方文明、只承认西方的富强和“物质之学”,他最后走向了类似于洋务派主张的“物质救国论”。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则认为,即使是运用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索社会革命的道路。正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新的知识资源的引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和文明的问题得以呈现,而章太炎、鲁迅则进一步对西方文明话语赖以存在的根基——进化、公理、科学等观念进行了追问,试图构建一种迥然不同的世界观,正是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中,弱小民族的发现及其联合才成为可能。
注释:
〔1〕刘文明:《19世纪欧洲“文明”话语与晚清“文明”观的嬗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方维规:《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史林》1999年第4期。
〔3〕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4〕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4页。
〔5〕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68页。
〔6〕〔日〕佐藤慎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7〕梁启超:《政治学学理摭言》,《梁启超全集》第3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36页。
〔8〕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箚记》,《梁启超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99页。
〔9〕〔日〕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10〕〔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1页。
〔11〕〔日〕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页。
〔12〕梁启超:《待野蛮人之法》,《梁启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4页。
〔13〕梁启超:《文字狱与文明国》,《梁启超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50页。
〔14〕梁启超:《读〈今后之满洲〉书后》,《梁启超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4页。
〔15〕梁启超:《自由书·记越南亡人之言》,《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5、177页。
〔16〕梁启超:《敬告当道者》,《梁启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1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梁启超全集》第1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9、186、229、188-189页。
〔18〕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函(1884年8月6日)》,《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38页。
〔19〕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6月)》,《黄遵宪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29-430页。
〔20〕Herbert Spencer,The Study of Sociology,London:Kegan Paul,Trench & Co.,1887,p.195.斯宾塞的原文为:Among existing uncivilized and semi-civilized races,we everywhere find that union of small societies by a conquering society is a step in civilization.严复的译文并非严格的直译:每见今世非墨亚澳诸洲,其间倥侗半化之民,经战胜而合,其于文明,皆有进步。参见严复译:《群学肄言》,《严复全集》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
〔21〕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语信欤》,《严复全集》第7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222-225页。
〔22〕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2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92-695页。
〔23〕〔日〕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高莹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8页。
〔24〕《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460页。
〔25〕雨尘子:《论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11号。
〔26〕〔28〕〔30〕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康有为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21,116,236、203页。
〔27〕康有为:《孟子微》,《康有为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96页。
〔29〕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5-446页。
〔31〕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32〕康有为:《德国游记》,《康有为全集》第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33页。
〔33〕康有为:《恶士弗大学图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
〔34〕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康有为全集》第8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4页。
〔35〕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8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36〕杨度:《金铁主义说》,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8、235页。
〔37〕杨度、〔日〕嘉纳治五郎:《支那教育问题》,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页。
〔38〕杨度:《湖南少年歌》,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页。
〔39〕孙中山:《与〈伦敦被难记〉俄译者等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6页。
〔40〕孙中山:《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8、105页。
〔41〕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7-329页。
〔42〕〔46〕民意(胡汉民):《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1907年第12号。
〔43〕梁启超:《杂答某报》,《梁启超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89-93页。
〔44〕梁启超:《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梁启超全集》第6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
〔45〕梁启超:《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梁启超全集》第4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9页。
〔47〕自由(冯自由):《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民报》1906年第4号。
〔48〕〔俄〕苦鲁巴金Kropotkine:《面包畧夺》,申叔(刘师培)译,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5页。
〔49〕申叔(刘师培):《读书杂记》,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40页。
〔50〕《俄杜尔斯托〈致支那人书〉节译》,忱刍译,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11-412页。
〔51〕〔俄〕杜尔斯德Tolstoy:《致中国人书》,忱刍译,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64页。
〔52〕震(何震)、申叔(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9-130页。
〔53〕马尔克斯Marx、因格尔斯Engels:《〈共产党宣言〉The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民鸣译,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5页。
〔54〕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0页。
〔55〕章太炎:《五无论》,《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2-463页。
〔56〕章太炎:《复仇是非论》,《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1-282页。
〔57〕章太炎:《佛学演讲》,《章太炎全集·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8-159页。
〔58〕章太炎:《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05-410页。
〔59〕章太炎:《驳神我宪政说》,《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27-329页。
〔60〕章太炎:《记印度西婆耆王记念会事丁未》,《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374页。
〔61〕章太炎:《四惑论》,《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8-479页。
〔62〕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 第一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012页。
〔63〕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50、57-58页。
〔64〕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