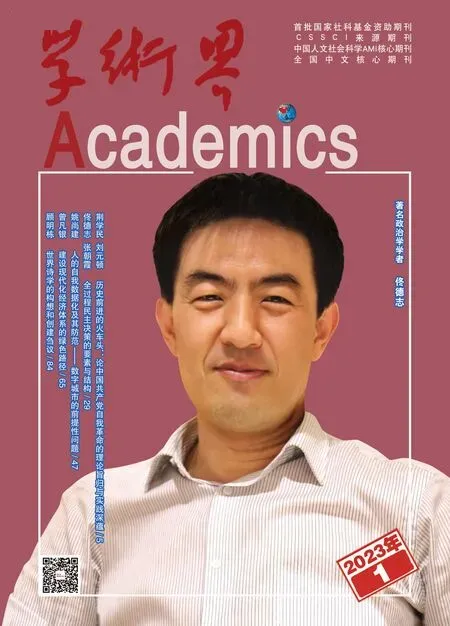规范主义者何以言自然〔*〕
——基于布兰顿哲学的阐释
周 靖(上海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自然”(what it is)与“应然”(what it ought to be)之间的关系自休谟始便是一个难解的经典论题。怀疑论者断然否定我们能够从关于世界的主观理解进展到关于世界本身的客观知识,其主要理由在于,在主体间达成的合乎规范的理解层次上,我们无法根除这种理解中渗透的主观性,从而呈现一个“清白”的世界本身。与此相关,布兰顿(R.Brandom)在其近作《信任的精神》中,借助对黑格尔哲学的吸收和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道“从最初(属于自然界)的单纯的生命有机体转变为精神的规范性领域内的居民”的思路,〔1〕在布兰顿对“自然”与“应然”关系的阐释中,我们既能够对“规范”提供一种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解释,也能够同时在“应然”的规范视野内谈论“自然”的世界之所是。
一、动物性“欲求”的意义结构
在《信任的精神》一书的“结论”中,布兰顿道明了其数十年来始终坚守的基本立场,即“不相容性和后果性的模态关系既有着真势的(alethic)形式,也有着道义的(deontic)形式。我们既可以对它们作出法则论的(合乎定律的,nomological)解读,也可以作出规范的解读。这些模态相应阐明了存在的客观领域(实在,事物的自在存在)和思维的主观领域(显像,事物的自为存在,事物被理解为什么)”。〔2〕其中,不相容性与后果性指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实质(material)关系,如“红”与“白”的不相容性,从吃下“红色的蘑菇”到“死亡”的推论,这类关系是合乎定律的自然关系;相比之下,在道义层面上对这类关系作出的规范解读则体现了我们对“自然”的“应然”理解。在布兰顿那里,自然法则和应然规范是深深捆绑在一起的,这种立场的基本理由在于,“意义(显像,现象,自为存在)的差别性和指称项(实在、本体、自在存在)的统一性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只有在它们包含彼此的语境中才能理解它们”。〔3〕
从表面上看,布兰顿的这一观点类似于康德立场,康德认为“直观和概念构成了一个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以至于无论是概念没有以某些方式与它们相应的直观、还是直观没有概念,都不能提供知识”。〔4〕然而,在康德那里,直观中把握的杂多已经有了一个综合,从而“直观虽然呈现杂多,但若没有一种此际出现的综合,就永远不能使这种杂多成为这样的杂多并被包含在一个表象中”。〔5〕康德因此面临两个进一步的问题,一是承诺为杂多提供来源的“物自体”存在,二是构建能够借以对感性杂多进行综合的知性范畴形式。与康德不同,在《信任的精神》中,
(a)布兰顿从对动物层次具有的欲求(desire)层面开始讨论,尝试在“紧扣”世界本身的意义上构建初始的意义(significance)和自我意识;
(b) 布兰顿用社会层面的社会规范性和历史性取代德国观念论中的先验性和超验性,尝试在社会性的承认(recognition)和历史性的回忆(recollection)中同时实现主体和社会、世界与语言的构建和发展。
本节拟讨论论题(a),下一节将讨论论题(b)。就论题(a)而言,我们的讨论将下降至动物性的欲求层面,此时讨论的动物至少需是一类理性生物,它能够以合乎理性的方式行事。但要注意的是,合乎理性地行动的能力不要求动物具备成熟的概念,仅要求它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如它不会吃下红色的有毒蘑菇,会避开捕食者的地盘而不会有意闯入等。
布兰顿首先区分了两类对周遭环境中的对象作出可靠反应的模式:
(1) 铁在潮湿的环境中生锈;〔6〕
(2)饥饿的动物对食物有着欲求(desire),它将事物(thing)视为可以满足其欲求的某物(something),即食物,从而在某物从树上落下时会直接吃下它。〔7〕
布兰顿的这一区分与布洛克(N.Block)对“取用意识”(access consciousness)和“现象意识”(phenomenal consciousness)的区分类似,〔8〕认为在情形(1)中,铁仅对潮湿的环境有着可靠的反应模式或倾向(disposition),但铁不具有自我意识。相比之下,在布兰顿看来,情形(2)则包含了一种基本的“立义”行为——动物关于事物的“欲望性觉识”(orectic awareness)体现了一种由如下三种要素构成的三位结构:态度(欲求),例如饥饿;回应性的活动,例如进食;以及意义项(significance),例如食物——这种“立义”行为将幽暗的“本体”(noumena)直接构建为“现象”(phenomena)。进而,现象意识中既敞开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同时动物在基于欲求的对事物的直接的“认知关系”中,在规定什么对“我”而言是有用的对象的意义上,也构成了初始的自我意识。
现象意识和自我意识是同时构建起来的,此过程需依赖于“事物本身”,因为“欲望不仅是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倾向,因为某动物倾向于对对象作出反应的活动是否能够满足其要求,这取决于那些对象的特征”。〔9〕布兰顿认同实用主义的一个基本观念,即“最根本的那类意向性(在指向对象的意义上)是关于世界中的对象的,这些对象是感性(sentient)生物所娴熟应对的世界中的对象”。〔10〕这些对象就是自然之物,是世界本身具有的朴素之物,而非某种掩藏在现象之后的、无法直接触及的“本体”。
关于本体和现象,布兰顿将前者阐释为“可以被认知的东西”,后者则是关于前者的“尝试性认知”。〔11〕世界是可知的,但这不意味着世界完全是在属人的(personal)概念范围之内的。与麦克道威尔(J.McDowell)认为“思维无边界”,从而“概念性”是一路向下地涵括世界的全部范围这种立场不同,〔12〕布兰顿认为,世界的可知性的确承诺了我们能够以概念的形式将它表达出来,但这不意味着世界没有自身的属性——恰是因为世界有其客观属性,我们在主观的实践活动中才会对之有着错误或正确的理解,这种现实存在的张力构成了推动认知活动前行的动力。例如,动物的“进食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它对饥饿的欲望有着工具上的适当性(instrumentally appropriate)。这是一种主观上适当的,因为这种活动实际上是饥饿的动物在饥饿的欲求状态下被迫做出的活动。它也是客观上适当的,因为它是一种对环境中的对象作出反应的活动,这一活动实际上通常(足够)会带来对欲求的满足”。〔13〕只有在这样的成功进食活动中,理性生物才能建制起有意义的世界:据其意义,将本体构建为初始的现象界;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其意义才是有效的。“自然”与“应然”携手并进、互为前提,不能用“应然”完全掩盖“自然”。
总结而言,布兰顿近来下降到动物性欲求的层面来讨论意义的缘起,在初始的意义和自我意识的构建中,“世界本身”无疑发挥着不可消除的作用。然而,具有自我意识的生物与如我们这样的规范主体仍然相距甚远,如何从这样的自然生物发展成社会生物,理性生物具有的合乎定律的反应倾向如何进一步呈现为我们的规范表达,这些构成了布兰顿下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
二、“承认”双层次的规范建制
“规范”通常指某一主体在公共空间内如何以正当方式行事的规则,因而它涉及到“我”与“他者”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自然层面的“物—我”单层次的、直接的认知(cognitive)关系进展到应然层面的“物—我—我们”双层次的承认(recognitive)关系蕴藏着一道从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进展到社会性的主体的思路,在此过程中,埋首于应对自然对象的理性生物遭遇到另一个类似的理性生物,他们彼此“承认”,携手迈入精神展开的“历史”。“承认”是布兰顿从黑格尔那里取用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将他人视为与我们一样的主体的社会实践态度。布兰顿“根据承认来从社会视角解释规范性,以及根据回忆理性(recollective rationality)来从历史视角解释概念内容的表象维度”。〔14〕其中,表象维度恰是在初始的“物—我”认知关系中获得的世界内容。
乍看之下,布兰顿这里的表述明显有着让人感到困惑之处:他似乎认为表象性的自然是通过回溯视角以合乎理性的方式重构而来的,而重构活动是一种以“承认”为态度的规范活动,那么,我们将面临本文所指的问题——规范主义者何以言自然?换言之,主体间的承认关系如何进入到“物—我”间的认知关系,从而能够保证在社会视角下展开的那些合乎规范的阐释确然是亦可从历史视角重构的那些表象内容?
这一问题的答案蕴含了两点关键认识:首先,动物性欲求层面建构起的内容(现象)和认知关系能够进一步被普遍化和范畴化,从而演化为更为高阶意识的内容和知识形式,这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在“物—我—我们”双层次的模式中伴随着社会性的交往活动,孤独应对世界的欲求性个体在与另一个理性主体的遭遇中发展为一个主体,这必然要求个体承诺的内容和理解能够同时得到他者的普遍认可。其次,在此意义上,后继从历史视角进行的回忆理性重构将仍然能够呈现对初始现象的理解,只不过此时的理解呈现了更高的综合或更完备的表达,但这种综合仍是对原先内容的综合,在此意义上,规范主义者仍可以言说自然。
具体而言,关于第一点认识,布兰顿指出,动物性欲求层面上“物—我”层次的认知关系中,理性生物获得了某种“自我意识”,而非如铁块具有的那般“取用意识”,这是因为理性生物在活动中对其周遭环境进行着有模式的反应,它能够根据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包括相容性和不相容性关系,以及后果性关系)作出实质推论(material inference),如“知道”吃下红色的蘑菇就会死亡这种“后果”,以及“红色”与“白色”的不相容性。理性生物不需具备成熟的概念便能够作出这样的推理。
具有作出实质推论的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理性生物因此能够对其认知过程(实质推理)以及对象(现象)进行普遍化或范畴化的处理,从而,在后继的活动或与其他理性生物的交互活动中,能够直接将普遍化的认知过程和已有意义负载的对象作为一个可直接调用的单位;进而,当遭遇到另一个类似的理性生物时,“承认”实际上将会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在个体内部展开的线索,个体会反省自身将事物理解为某物的“承诺”,如果其活动失败,他将会对其承诺作出一些修改和完善。另一条线索是人际间或理性生物间“沟通”的线索,个体的承诺在寻求合作的“规范”态度下,将会受到来自他者的审查,那些经受住审查的个体理解(意见)将会构成知识,个体承诺的“内容”则将构成建制世界的实质材料。〔15〕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仍是在讨论尚不具有成熟概念或语言的理性生物之间的交流,用托马塞洛(M.Tomasello)的话说,“在这种交流中,个体首先发出同合作任务相关的注意或意向性想象信号,接收到该信号后,他的伙伴则会推论信号所包含的社会性意图”。〔16〕“信号”将会引发推理反应,这意味着将发出信号的他人“承认”为一个与自身一样的他者,即第二人称,并且,从第二人称视角“反身”省察自己,省察性的互动将会再次确认第一人称的“我”,此时,“我”不再是一个直接与“事物”接触的孤独个体,而是与他者一道进行探查的主体。随着交往活动的丰富化和深化,推理进入递归的程序,“个体”被确定为总是有着“第二人”进行监控的“主体”,成为一个总是经由他者中介的反思性自我。在澄清信号意义的递归的主体间的活动中,信号既获得了越来越清晰和稳定的规范意义,信号所“表征”的因果关系也将在主体间最初的想象和符号化的认知活动中被固定为类别、图式和原型等。在类似的意义上,布兰顿指出,“具体的承认包含了认可另一个人对事物如何(作为Ks的事物是怎样的事物)有着某种权威。当我这样做时,我将你视为‘我们’(初始的规范意义上的‘我们’)的一员,‘我们’受制于相同的规范,相同的权威;‘我们’恰由这般态度所建制”。〔17〕其中,Ks指的是将事物理解为K的类别,只有“我”在“我们”中才能将原先对事物的具体理解拓展至普遍理解。
关于第二点认识,随着“我”发展为“我们”中的一个“我”,〔18〕具有稳定意义的符号演变为“概念”,进而我们最终能够根据成熟的语言,从形式上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理解。在其《使之明晰》〔19〕与《阐明理由》〔20〕等著作中,布兰顿重点发展了其推论主义(inferentialism)思想,即如何以推论方式阐明推论中使用到的语言表达式所“关涉”的内容。对布兰顿的工作心存疑窦的反对者们仍然会提出笔者曾称之为“语义学之幕”的问题,即在使用语言的判断活动或语义交往活动中将会出现一种以推论为方式、以概念为原材料织就的“语义学之幕”,它替代了近代哲学中横陈于心灵与世界之间的由因果关系织成的“因果性之幕”。〔21〕语义学之幕带来了“语言/世界”的划界,这种划界在以使用语言作出推理的方式所阐明或表达的对象(what is expressed)和外部世界中的实际事物(what there is)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在此意义上,布兰顿面临的问题是,推论的阐明能否刺破语义学之幕,从而达到事物本身。在布兰顿看来,这里的问题源于下述错误立场,“人们经常将推论的阐明等同于逻辑的阐明。实质推论因此被看作是一个派生的范畴。这种观点认为,所谓合理的(being rational)……可被理解为一种纯粹的逻辑能力。”〔22〕人们不仅将推论能力视为人所独有的理性能力,也认为形式上正确的推论是普遍有效的。然而,在布兰顿看来,“推论”实际上包含了实质推论和形式推论,前者是在应对周遭世界的实质语用活动中作出的推论,后者则是在主体间使用语言的话语活动中作出的推论,结合上一节中的讨论,我们看到布兰顿几十年来始终恪守的立场是:应该融合实质的语用学讨论和形式的语义学讨论;然而,尽管我们在现实的阐释活动(articulating)中,从方法论上来说,仅能以过语句和次语句(sub-sentential)表达式在推理活动(reasoning)中起到的作用来理解表达式的意义和内容——这种语义推论主义(semantic inferentialism)构成了布兰顿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支柱;但是,从实践的发生次序上来说,实质语用层次的阐明是在先的,我们终究需要根据在语用层次辨明的“知道—如何”“做”来理解“知道—什么”“说”出的话语,根据实质推论的“善”(goodness)来衡量后继的形式推论的“正确性”(correctness)。〔23〕
布兰顿持该立场的理由在于,对相同内容作出的实质推论和形式推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换句话说,“言”与“行”互相规定,“言行合一”意味着两类语汇的贴合。布兰顿否认关于世界的阐释和世界本身之间存在一道需要跨越的沟壑,在此意义上,根本不存在刺破语义学之幕这类任务。
布兰顿进一步为“物—我—我们”双层次的“承认”添加上了“历史”维度,“规范态度和规范身份之间所具有的有着社会性本质的关系,以及在关于概念内容的语义学方面,内容的自为存在(现象、意义、表象)和自在存在(本体、指称项、被表象物)之间有着历史性本质的关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种发展过程的两个维度,即承认的维度和回忆的维度”。〔24〕在历史的进程内,本体与现象彼此对照,指称与意义在我们的认知和承认活动中一道发展,“我”在“我们”中,“我们”在世界中。
总结而言,根据布兰顿的叙事,关于世界的客观理解和主观阐释始终是彼此成就的,在此意义上,自然与应然之间根本不存在需要跨越的鸿沟,从而规范主义者必然能够言说自然。然而,布兰顿似乎太过轻易地承诺可以从自然性的生物发展至应然性的主体。实际上,布兰顿对真正主体性到来的进程(其中,主要经历了从传统、现代性,再到后现代性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复杂、细致的讨论,限于本文主旨,不作赘论。
三、反对规范自然主义
前两节的阐释仍有些让人感到困惑之处。布兰顿一般留人以理性主义者的形象,这是因为他强调根据语言表达式间的推论关系而非语言和世界间的指称关系或因果关系来分析表达式的意义与意向状态的内容,其理性主义进路以概念性为哲学探究的起点,而非直接探查心灵与认识能力的自然源起。实际上,布兰顿在其所有著作中从未提供过对自然发展史的描述,那么,究竟如何在理性主义框架下理解他对动物性欲求的讨论?
作为理性主义者的布兰顿,他明确反对规范自然主义立场,即根据自然性的生物特征来理解我们的理性成就。规范自然主义者“……反过来认为实践态度源于情绪特征……由于这种态度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以诸如我们自身这样的社会生物所具有的自然历史的形式存在,因此它们建制或规划的规范身份也是如此”。〔25〕我们是历史性的生物,但需要区分开两种历史性,即理性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布兰顿哲学中渗透着一种黑格尔式的哲学精神,他始终认为“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并且记载在人的语言里。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必须牢记,那把人和禽兽区分开来的东西,是思维”。〔26〕哲学的探究应该以概念性为起点,动物性的欲求层面上已经有了意义的初始形态,因而我们可以从它开始讨论,探究它后继发展的历史。然而,这种历史不是对其生物性特征的历史描述,例如进化论叙事、动物行为学叙事,以及诉诸颅内神经状态的叙事等——需要尤为强调的是,布兰顿并不反对这类自然叙事具有的价值,他仅是认为这类工作是认知科学家们而非哲学家们的工作。〔27〕从哲学上说,规范自然主义的错误在于,混淆了自然的历史叙事和社会性的历史叙事,哲学工作者更应在后一类叙事中展开自身的独特工作。
我们可以根据丹尼特与布兰顿的思想差别来进一步理解布兰顿这里的立场或哲学态度。丹尼特哲学呈现了一种典型的自然主义进路,即从世界一方直接探究心灵的自然起源,可以预见的是,布兰顿与丹尼特之间有着无法调和的思想差别。
布兰顿多次援用丹尼特的“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以表明,理性生物关于某物的意向已然渗透有初始的规范维度,这些(可能仅是实质推论层次的)规范为语言表达式之间的理性(rational)关系奠定了基础,从而我们可以进一步将语言表达式所关涉的意向内容在推理活动中加以阐明。这种阐明的过程是在自然和应然之际,在“行”与“言”之际展开的认知和承认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活动。具体而言,丹尼特这样介绍意向立场的工作机制:“首先,你决定把要预测其行为的对象看成是一个理性自主体(rational agent);然后根据它在世界中的位置和它的目的,推测这个自主体应当具有什么信念。之后基于相同的考虑,推测它应当具有什么愿望,最后你就可以预言:这个理性自主体将依据其信念行动以实现其目的。从所选择的这组信念和愿望进行一些推理,在很多——但非所有——情况下都能确定自主体应当做什么;这就是你对自主体将做什么的预言。”〔28〕布兰顿将丹尼特的意向立场阐释为如下三个推理步骤:〔29〕
(1)首先认识到或被归因的(attributing)意向状态有着规范意义(significance),这意味着持有该意向状态的理性生物应该以某种特定的合乎规范的方式行事;
(2)将规范身份归派给理性生物的信念和欲求,这意味着该理性生物在持有那类信念和欲求时,持有理由;
(3)最后,基于前两点,界定一种意向系统,任何持有这种系统的生物均合乎理性地行动。从而,我们可以在规范的空间内谈论意向状态相关的信念和欲求内容。
实际上,丹尼特对布兰顿为何论及他的“意向立场”了然于心,因为在意向立场中已经建构好了布兰顿需要的初始意义或规范。〔30〕丹尼特承认“用语言来表达愿望的能力打开了愿望归属的闸门”。〔31〕语言带来了关于欲望更为具体的归因。然而,丹尼特同时指出,“并非有机体之间的一切互动都是交流性的”,〔32〕从而是语言性的。恰在这一点上,丹尼特开始与布兰顿分道扬镳,他对布兰顿主要有着如下三点批评:
首先,丹尼特认识到他与布兰顿在一阶的意向系统和二阶的意向系统何者为先的问题上怀有分歧。一阶的意向系统指系统怀有信念和欲求,但没有关于信念和愿望的信念和欲求;二阶的意向系统则更为复杂地包含了关于自己以及他者的信念和欲求的信念和欲求。也就是说,一阶系统体现的是单独个体的意向与对象(意向内容)的直接关系(如布兰顿所指的“物—我”认知关系),二阶系统则包含了对直接关系的反思,以及对其他个体相似系统的理解(如布兰顿所指的“物—我—我们”双层次的关系)。就此而言,丹尼特的解释顺序是从一阶的意向系统“自下而上”地迈向二阶的以及更高阶的意向系统,而在他看来,布兰顿则采取了相反的“自上而下”的解释顺序,即从二阶层次上意向状态已经渗透有的规范——主体此时能够将意向状态合乎规范地归属给其他主体——来解释一阶层次上的意向内容。
其次,解释次序上的不同构成了两人思想差别的底色。丹尼特批评到,如若采取自上而下的解释顺序,诉诸理性共同体规范的言语活动来谈及意向内容的话,那么,共同体如何而来,这便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在丹尼特看来,在初始意向性中,某主体认为他者“似乎”具有相同的意向系统,这种“似乎”态度将他者视为与我类似的存在,在进化的漫长历史中,“似乎”态度的成功与失败促成“我们”的联结以及对“我”自身的重构——共同体有着如此这般的自然源起。然而,布兰顿认为,“初始的、独立的,或非衍生的意向性已经全然是一种语言事态了”。〔33〕这一表述让布兰顿免除了对其中的自然起源作出直接的描述,也体现了布兰顿与丹尼特的思想之别,这不禁让丹尼特怀疑布兰顿何以在“无根”的共同体内谈论自然。
最后,即便我们将共同体如何而来的问题放置一旁,在规范本身的起源问题上,两人也有着类似的歧见。丹尼特指出,就人类这种使用语言的生物而言,布兰顿的确正确地认识到,我们仅能通过语言表达的方式来谈论意向内容,然而,仅在社会的范围内编织规范,这将省略掉“交流”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维度:我们人类可以出于获得快乐的单纯目的进行交流,但交流在自然史中并非偶然发生的,它涉及复杂的适应和调整机制,这意味着规范是自然选择这一过程的结果,而非单纯的语言构造。〔34〕规范与共同体一样有其自然源起,从一阶意向系统迈向二阶以及更高阶的意向系统是“成为人的条件”,是意义和规范衍生的条件,对此条件进行具体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在丹尼特看来,布兰顿仅在已经属人的语言、共同体和规范范围内进行探究,这将忽略掉自然主义一面的洞察。
基于上文中的讨论,我们可以帮助布兰顿对丹尼特的指责作出一个简单回应。在笔者看来,争议的根源在于,丹尼特将布兰顿所指的已经具有规范形态的“概念性”理解为共同体能够使用的成熟概念,从而他将布兰顿的事业理解为在二阶的意向系统内谈论一阶的意向系统内关涉的自然内容。实际上,布兰顿认为“概念性”一路向下至动物性欲求的层面——这体现在他对丹尼特意向立场的认可上——并且,如上一节中阐明的那般,自然与应然之间、实质的语用推理与形式的语义表达之间,或一阶的意向系统和二阶的意向系统之间从未存在本体论的差别,因而,在布兰顿那里,不存在简单的何种层次上的意向系统在先的问题:从实践的层次上说,低阶的系统为先;从阐明的方法论上说,高阶的系统为先;但“低阶”和“高阶”之别仅体现为认知和承认的语用和语义探究在发展程度和阶段上的不同,而无本体论上的差别。在这一点上,丹尼特无疑误解了布兰顿。
但就丹尼特倡导的进化论叙事而言,布兰顿明确指出两点:一是,他的理性主义阐明与自然主义的进化论解释兼容;二是,为心灵与世界间的因果关系提供科学模式,这是认知科学家而非哲学家应当为之的工作。丹尼特的相关立场是,“认为哲学考察并不高于或优先于自然科学考察,而是与这些真相探索事业构成合作伙伴关系,哲学家的适当工作是澄清和统一常常相互冲突的看法,以获得一个单一的宇宙图景。那意味着欢迎来自良好确立的科学发现和理论的礼物,并将其作为哲学理论建构的原材料,所以,做出对科学与哲学都是有见识的建设性批评是可能的。”〔35〕故而,丹尼特的讨论多以科学的发现为材料,相比之下,布兰顿则更加像是一位传统或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秉承着理性的思辨精神作出哲学探讨。
总结而言,布兰顿与丹尼特对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立场,布兰顿认为,自然发展的终点——概念性——构成了哲学讨论的起点,在这样的起点上,主观的规范理解直接与自然的世界本身根深蒂固地纠缠在一起,这种立场实质上是对世界的存在方式(ways of being)作出了解释,认为世界只有在我们的理解中才是可能的,但我们的理解只有依存于世界自身的特征才能是正确的。在此意义上,规范主义者必然能够言说自然。相比之下,丹尼特则试图通过对自然史的描述来理解规范的起源,尽管他将意识或规范视为仅是由语言构建的幻象,根本不存在意识这类东西,从而自然描述便能够充分地直接解释一切。〔36〕或许因为此,丹尼特在其著作中多是在对科学发现进行描述后便结束其思考,直接给出哲学上的结论。布兰顿无疑不会接受这类承诺了“规范自然主义”的探究方式。
四、结 语
布兰顿哲学的基本立场在于,认为阐明表达式之间形式(formal)关系的道义规范语汇需对阐明内容之间实质(material)关系的真势模态语汇负责。粗略言之,道义规范语汇能够使得我们“说”出在“做”什么,而关于“做”的真势模态语汇则限定了我们能够“说”什么;在“言”与“行”的关系上,“言”与“行”互相规定,“言行合一”意味着两类语汇根本上是关于同一类事件的不同表达。布兰顿实际上抵制在截然对立的自然与应然之间作出划分,从而对他而言,或许根本不存在“规范主义者何以言自然”这类问题。
注释:
〔1〕〔2〕〔3〕〔7〕〔9〕〔11〕〔13〕〔14〕〔17〕〔24〕〔25〕Robert Brandom,A Spirt of Trust: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238;667;451;240-247;242;666;242;12,245;253;303;264.
〔4〕〔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128页。
〔6〕〔10〕〔29〕〔33〕See 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 & discursive commi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pp.33-34,592,55-57,143.
〔8〕Block,Ned,“On a confusion about a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18.2(1995):pp.227-247.
〔12〕参见〔美〕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韩林合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51、30页。
〔15〕参见陈亚军:《实用主义:从皮尔士到布兰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67页。
〔16〕〔美〕托马塞洛:《人类思维的自然史:从人猿到社会人的心智进化之路》,苏彦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18〕布兰顿对此过程进行了复杂的具体讨论,限于本文论题,在此不作赘论,参见Robert Brandom,A Spirit of Trust:A Read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469-499.
〔19〕Robert Brandom,Making It Explicit:Reasoning,representing & discursive commit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0〕〔22〕〔美〕布兰顿:《阐明理由:推论主义导论》,陈亚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7页。
〔21〕参见周靖:《论语言在开显世界中的规范建制功能——基于布兰顿语言哲学的阐释》,《哲学研究》2021年第5期。
〔23〕See Robert Brandom,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Classical,Recent and Contempo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9.
〔26〕〔德〕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页。
〔27〕参见〔美〕布兰顿:《在理由的空间内:推论主义、规范主义与元语言语汇》,孙宁、周靖、黄远帆、文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44页。
〔28〕〔31〕〔32〕〔美〕丹尼特:《意向立场》,刘占峰、陈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8-29、32、332页。
〔30〕〔34〕See Dennett,D.,“The Evolution of ‘Why?’”,InReading Brandom: On Making It Explicit,Bernhard Weiss and Jeremy Wanderer (Ed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p.48,53-55.
〔35〕〔美〕丹尼特:《自由的进化》,辉格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20页。
〔36〕Dennett,Daniel C.,“Animal consciousness: What matters and why”,Social Research,1995,p.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