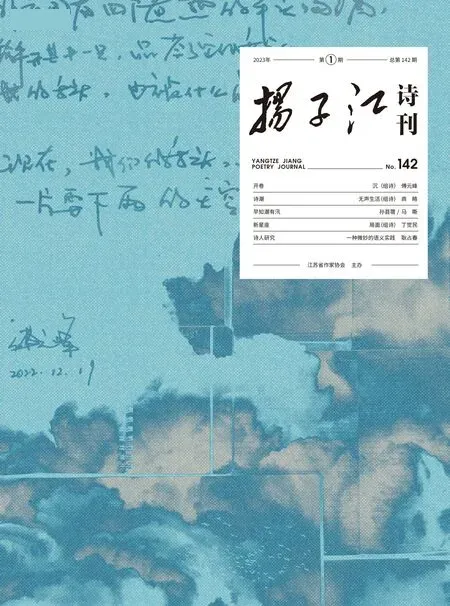拉美三诗人诗选
范童心 译
玛丽莎·卢索,1969年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诗人、编辑、文化传播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师,哥斯达黎加图里阿尔巴文学协会创始人,纽约诗歌出版社(西语)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流言三部曲——纪念何塞·费尔明·布兰科
Ⅰ 童年
你在公园中央坐下,
不管身处哪个国家,
都会听到:
“闭上眼睛,我正在你四周旋转。”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韦利亚内达公园中,
旋转木马在逆时针转动。
外公吐着烟圈,把票递给我。
我在动物们的背脊间蹦来蹦去,
从喷火的龙到哀伤的马。
“独角兽的角不见了。”
——操作员这样对我说。
理所当然的伤痛不是传奇,
却从历史的幽暗隧洞中浮现。
外公拉着我的手,
陪我一起乘上小小的火车,
穿过紫藤花桥。
蓝花楹在我们上方哭泣,
仿佛知道有一天,我们两人中的一个
会化为其他公园中,尘埃里的流言。
Ⅱ 少年
有一天,我踏上了旋转木马之外的旅途,
生命在顺时针旋转。
我已不再是孩子。
我来到图里阿尔巴,感受公园的呼吸,
也听到了同样的低语:
“闭上眼睛,我正在你四周旋转。”
火山口呼唤着我的名字。
我紧闭双眼,想象着缺席的怪兽,
和我骑在它们背脊上的前行——
那公园永远在我心中。
Ⅲ 成年
我睁开眼睛,发现对面是战神广场。
旋转木马的脊背在孤寂荒芜中上下起伏。
我童年的感官变得无家可归。
独角兽找到它的角了吗?
入口的一个男人对我说:
“小姐,这里只允许儿童入内。”
我周围的一切都是钢筋水泥,
与机械玩具旋转的方向背道而驰。
***
在纽约都会修道院博物馆里,
耳边响着铃铛般金属的嘶鸣,
我终于在一片古老的中世纪壁毯中,找到了那只失落的角。
胡丽娅·王·科姆特,1965年生于秘鲁北部切彭市的一个华裔家庭,父亲来自澳门。她曾在三个大洲生活,出版过多部诗集、小说集和散文集。对不同国家文化多样性的看法和体验是她写作的强大动力。现居秘鲁利马和葡萄牙里斯本。
斗牛的艺术
他们演习魔法,
知道自己的血液会与
加蒂斯章鱼的触角和内脏混淆。
我们女人在广场上起舞,
将耻骨抬向天空。
西班牙各省间距离遥远
安顿在祭天动物的滴落之下
在秘鲁北方遥远的鼓声中醒来。
他们宣示了另一片海洋,其中有蜜糖岩石的堡垒。
我们从不曾在圆环中心,
亦不曾长出抵抗敌人的尖角。
乳房中盛满了温热的乳汁,
太阳怜悯我们的四个肠胃。
它们反刍着我们的共生,在离开神圣的围栏时
我们屏住势不可挡的呼吸
公牛们踩踏在鲜花之上
全然不知
花瓣上亦有生命。
它们相信
自己衰老的脑
将保护年轻的族群。
牛犊们充满了大海与慈悲
它们使我们的乳汁酸涩。
我们已不再是那些繁衍生息的四足动物
从它的体重和乱转的大眼睛里搜寻一个盲点
它们宛如一场摧毁森林的洪水般沉重。
我们像被它们羞辱过的道路一样变宽
多少个日夜如此在伸出的舌头中流逝。
直到一匹邻家的小马冲破了栏杆
最终我们都发狂般跳进大海。
我们的驯化已经结束,
咸味的水中储满了几个世纪的唾液,
是我们中的一人在转化中发觉。
当头浸入一波海浪和灯塔的瞳孔之间
我重新呼吸
八角的词和冰冷在表面爆裂。
未知的遗产之中有什么正在发生
皮肤的巨大转变和对食物的需求
我们母性的尾巴正驱赶着苍蝇
它换上了太阳般金色的皮毛。
我们变成了黑暗的动词,我们的体重越来越轻,
为了在大麻的泡沫中升起。
没有后裔,没有宗族,
只有一个无比精致的针脚。
它覆盖着乳房上的累累伤痕,几样透明的物体。
(奶商的双手
拽动乳头,直到它们流血,患上关节炎)
乳汁忽然化作了河流,在一座蜜与茄子的城市中。
所有的书籍都刚好翻到了每头牛的眼睛阅读的那页中
解释如何走向教堂的那一段。
一个饮下甜水的人,
或是一个内心世界宛如凝视般可敬的空间。
对下一头牛来说,
没有被视为高人一等的存在,
只有可学习的躯体,我们都曾是可留下种种所学的圣坛。
是的,随后三月八日的飓风来临,
它如公牛们熟知的那般摧毁了海岸线。
大自然幻化出沟壑和板块
保护我们不被任何仇杀侵害。
我们知道,避难所和沉寂终将到来
彼时牛蹄将不再踏动。
有些乳房——比如我的——已经受伤,
另一些,则已被全部切下。
给住在荷兰的诺娅
诺娅,我不知道荷兰现在几点了……
若我在柏林想到荷兰,会觉得它是一只遥远的鸟儿,
那里的人说话像闪电,像牛奶中浸湿的面包,
在柏林,我们说话像一个玩着老橘子的天使,
能听出一种骄傲的口音,和用大蒜调过味的偏见,
在柏林,我不认识任何说荷兰语的人。
人们说夜晚是希腊史诗,
因为所有的人马兽和独眼巨人都会出现,
俄耳甫斯亲吻一个黑帮成员,
叙利亚工人在厕所中唱歌,
德国的俄耳甫斯住在最肮脏的角落,
老鼠化为机车骑士,
他们关上灯,
爱抚自己油腻的肚腩与身躯。
一个死去的女人(或许是我的母亲)唱着歌,
她此刻在的地方让她学会了爱我。
将我带到这世上的人并不理解我的所作所为,
也从未提起过荷兰。
那个女人惧怕德国人,
我的诗歌是怪异的物体,
就像北欧的苹果……或许
是她想要遗忘的词……
妈妈,为什么?我这样问过:
柏林的天空中有什么,让你如此困扰?
在荷兰有对柏林语言的偏见,
不满的时光搜寻着贡多拉,
我没有为看到未来清洗自己的鼻子,
柏林的天空吐出铬的狂风,
不是蓝色、不是灰色、也不是灰色……那是冬天的颜色,
是德国的天空。
我为住在荷兰的诺娅写下一首诗,
她尝试将名称中的光环去掉,
火车低语着一座倒塌的桥的恐惧,
诺娅在磨坊的活计中昏昏欲睡。
但在这里,在柏林,没有女妖,也没有水车,
只有发疯的天使邀请我们在他们背后哭泣,
弹奏着废料做成的乐器。
诺娅,你会明白的,俄耳甫斯
不是译者,他丢失了自己的祖国和船只,
因此我听到你说的话时大哭了一场。
石头做成的左眼爆裂,
没有人懂得你的声音,
诺娅,这里是柏林,俄耳甫斯正是在这里抿起嘴唇,
开启他的复仇。
娜提·塞尔瓦,1993年出生于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诗人、歌手、词曲作者、译者、环保倡导者。著有多部诗集,用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创作。曾在多国参与诗歌节和文化活动。
美洲豹之路
我赤脚向山巅走去,
我的脚与岩石融为一体。
这些印记,并非刚刚留下:
它们早已被浸透千百次,
留下一条泥泞的小径。
在一块据说来自天外的陨石之上,
我宽衣解带,
为了能坐上去时,
不被身上的布料阻断听觉。
我要倾听水边宇宙的繁衍——
那只手敲打出强劲的鼓点。
我用烟叶包裹住药草,
云与烟和我混为一谈,
我们慢慢飘上山巅。
阳光炙烤着我赤裸的身体,
我的皮肤散发出可可豆的味道。
绿宝石般的流水,
为我涂抹上永生的灵魂。
我已皈依。
此刻,这首诗即将结束,
它们从未知晓自己创作的笔迹,
那雷电轰鸣中隐秘的双手。
风暴
风,
是山峰收到的,来自大海的
叹息。
有时候,凶猛无比
——就像现在。
有时候,会带来厄运,
风起云涌,
令地平线前的双眼紧闭……
幸运的是,
黑暗是光明的序曲
(让我想起了黎明)。
风暴的第一滴雨落在了我的头顶,
我毫不担心。
怕什么呢?
至少,
我能感觉到天空
稍微近了一些。
河
橙色的树叶落入河中,
坠落
仿佛深嵌进鱼儿的深渊,
坠落
仿佛跃入水汪汪的蓝天,
坠落
仿佛它唯一的重力法则
已不再严格,
只剩下
河水静谧的节奏
包裹住岩石……
就这样,
我想就这样滑入你的身体,
像一粒气泡般滑落,
一个碧绿的呼吸,
一次无声的轻触。
将我自己溶入你
清泉般的肌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