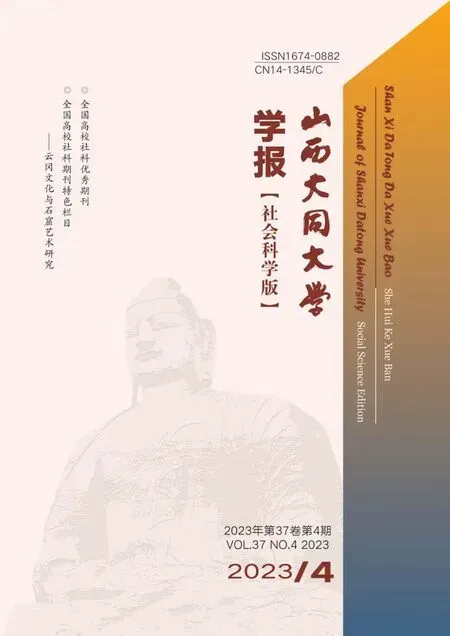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
霍省瑞
(1.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2.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乡村塾师作为清代特殊的士人群体,广布于民间社会。清人周石藩记载:“大凡乡鄙都邑,皆有塾师。”[1](P239)他们曾担负着乡村社会文化传承与建设的重要使命,但关于他们的生存状态,正史少有记载。然而,清代小说中却呈现了鲜活的塾师群体,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活化石”。正如顾颉刚所说:“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2](P115)近二十余年来,史学研究者逐渐注意到了俗文学中的塾师形象,但多以史料形式呈现,缺少对其社会文化的解读。有鉴于此,笔者试图通过清代小说探析乡村塾师的职业抉择、生存境遇及文化心理,继而管窥他们曾置身其间的历史文化场域。
一、乡村塾师的职业抉择
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大多出身贫寒,或为秀才,或为童生。他们读书力学,企图通过科举考试改变自身命运,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但他们往往屡试不第,久困场屋,便以授书为业。《儒林外史》中,周进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坐馆。虞育德祖孙三代兼为乡村塾师,小说写道“镇上有二百多人家,都是务农为业。只有一位虞姓,……读书进了学,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只在这镇上教书。……他儿子不曾进过学,也是教书为业。到了中年,……生下这位虞博士来。”虞育德后来又接替父亲“在祁家教书”。[3](P443)在他五十岁中进士前,主要以授徒为业。《醒世姻缘传》中,“明水有一个先生姓汪,名字叫是汪为露,号叫是汪澄宇,倒也补了个增广生员;他的父亲在日,也是个学究秀才,教了一生的寡学。”[4](P512)再如蒲松龄“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5](P1822)其长孙蒲立德为邑庠生,也“设馆授生徒,讲明正学,嘉惠后进。”[5](P1823)《坚瓠续集》亦载,“钱麟仲偶谈宜兴丁大恭(致祥)四十时尚未补诸生,为吴中某氏塾师。”[6]卷六可见,乡村塾师或坐馆授徒,或设馆讲学,大都是久试不售的底层读书人,往往子承父业。
他们选择授徒为业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治生需要。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阶层划分明确,底层读书人不能谋取功名,便首选授徒或卖文谋生。因为无论农业劳作或手工业生产,都要相应的体力与技能,而经商还需经济资本。蒲松龄《先生论》对此直言不讳:“时乖不遂男儿愿,家业萧条有谁怜?欲更别业非无计,举家齐赴首阳山。既不能推车打担,又不能播种力田,为农夫而身力懦弱,作商贾而少本无钱。”[7](P84)《醒世姻缘传》也曾分析穷秀才开书铺、拾大粪、卖棺材、结交官府等治生方式的利弊,论述“夜晚寻思千条路,惟有开垦几亩砚田,以笔为犁,以舌作耒,自耕自凿的过度。雨少不怕旱干,雨多不怕水溢,不特饱了八口之家,自己且还要心广体胖,手舞足蹈的快活。……所以千回万转,总然只是一个教书,这便是秀才治生之本。”[8](P478-483)清人陈芳生也说:“儒者不为农工商贾,惟出仕与训蒙而已。出仕不可必得,训蒙乃分内事。果尽其道,则教育人材,亦大有益于天下。已亦藉此代耕,诚兼善之本务也。余处馆十余年,时时以未尽其道为愧。所以然者,亦诚有不得已焉。”[9](P719)显然,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担任乡村塾师,既可规避跨行就业的难度,又可解决生计问题,还能参与基层文化传承与建设,践行读书人的家国情怀。
二是功名诱惑。清代乡村塾师大多是声名不显的童生或生员,虽被主流文人看作三家村学究式的乡村陋儒,但往往怀有读书求仕的梦想。他们选择授徒为业,也有备考科举的考量。《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告诫匡超人,“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等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他又说“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廪生是挣得来的,到后来,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3](P200-201)这是马二先生对教馆与进学的看法,也是底层读书人的普遍心理。在他们看来,坐馆授徒只是暂时的谋生方式,考取功名才是终极追求。晚清河南汲县王锡彤,“授徒林氏家,抗颜为人师矣,学生五人,每年脩脯铜钱三十千尔。时同学师弟同为预备考试之人,师自用其揣摩之功,弟子各以其年龄受相当之考卷预备。”他在《抑斋自述》写道,“自念乡里教授非长久计,惟有举人进士是前途发达之方。”[10](P28-30)又如,蒲松龄长期设帐授徒,并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这些都是坐馆应考的明证。
二、乡村塾师的生存境遇
清代小说中的乡村塾师,生存状况堪怜。郑板桥《教馆诗》写道,“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11](P93)此诗真切表现了乡村塾师的生存境遇。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位低下。作为民间文化传承者与建设者,乡村塾师本应是社会地位较高且受人尊敬的职业,但事实并非如此。清代乡村私塾,多是一家或数家乡民自发创设的教育场所,往往因子孙求学需求而短暂开设,也会因乡民收入欠丰而随时关停,具有很强的随机性,给塾师职业也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同时,清代科举考试体制完备,时间跨度长,难度系数高。童生考取生员须经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秀才考取举人又需参加三年一次、每次三场的乡试,举人考取进士则需通过会试、复试和殿试。[12](P3-135)因此,大量乡村士子难以取得生员资格,更别说成为举人,导致乡村塾师从业者众多,竞争非常激烈,时常面临失馆危险。《笑笑录》“改清明诗”写道,‘清明时节乱纷纷,城里先生欲断魂。借问主人何处去,馆童遥指在乡村。’”[13](P166)蒲松龄《闹馆》写道,“沿门磕头求弟子,遍地碰腿是先生。”[5](P813)为了养家糊口,维持生计,乡村塾师往往不得不斯文扫地,或央求他人荐馆,或曲意奉承东家。又如《小豆棚》记载,“吾乡富甲某,忽欲延师课子。会当夏月,晒麦于场,雨骤来,诸佣工皆为之盖藏。富甲问曰:‘教书匠何以不至?’。”[14](P37)《吴下谚联》记载,杭州莫姓乡宦聘请塾师金先生,解馆时馆童为其挑送行李。塾师途中即景口占“墙内桃花墙外红”,馆童应声续道“长工挑担送长工”。后来塾师向东家告发,东家以续全前诗为责罚,馆童遂续“虽然吃饭分高下,打发工钱一样同”。[15](P41)无论富甲随口而出“教书匠”,或馆童应声而呼“长工”,均表明时人已将乡村塾师与工匠相等同,并对其充满蔑视。
二是事务繁重。塾师因材施教,事务繁多。因清代乡村社会以欠发达的农耕经济为主,私塾往往由数家村民共同出资开设,同期在学学生往往年龄差距较大,差异化程度较高。《醒世姻缘传》中,程乐宇到狄家坐馆,“先生上了公座,与他们上书。狄希陈读的还是下《孟》,相于廷读的是《小雅》,薛如卞读的是《国风》,薛如谦读的是《孝经》。”[8](P487)每位学生学习进度不同,考核与抽检方式各异。学生单独送来作业,塾师随送随批,无形中增加了工作任务。同时,乡村塾师的工作压力巨大。传统社会,乡民希冀子孙彻底改变祖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状态,所以对考取科举、实现阶层跨越的希望尤为迫切。因此,《闹馆》中和为贵承诺:“三年功必进学六年中举,七年上会进士连中三元,一霎时就成了那富户乡宦,翰林院效力满出印做官。”[5](P814)然而,家长在渴望子孙成才时,又表现出舐犊情深的一面。《清波杂志》写道,“典蒙最难,其人严则利于子弟,而不能久;狎则利于己,而负其父兄之托。”[16](P35)《村学先生自序》也写道,“开口教书,人便拾着句读;动手改课,人又议着高低。记问偶不到,村妇也要盘倒;奇字倘不识,小子也索吃亏。又有一般难处的事务,正是担轻又不得,步重又难支。课少了主人嫌懒惰,功多了弟子道难为。”[17](P17)显然,家长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态度矛盾,令塾师左右为难,压力倍增。
此外,乡村塾师还是乡村文化代言人。他们帮助主人及乡邻读写书信,命名起字,拟撰对联、契约文书、寿文碑文等,甚至参与婚丧嫁娶、居间调停等基层社会事务,承担着多种社会职责。《歧路灯》中,惠养民为“几个村看当票,查药方,立文约儿。”[18](P264)蔡家驹“晚年专事古文,熟掌故而深于经学,文体近曾王,郡中碑版之文,半出其手”。[19](P12)这些繁琐事务,也造成诸多苦恼。《聊斋文集·自序》也表露,“缙绅士庶,贵耳贱目,亦或阙牛而以犊耕。日久不堪其扰,因而戏索酒饵,意藉此可以止之;而远近以文章相烦者,仍不少也。”[20](P2)显然,乡村塾师被乡邻频繁央求代笔书写契约文书等。这些琐事不仅占据他们的闲暇时间,甚至会因处理不当而招来不满与谩骂。但无论如何,乡村塾师在处理基层社会事务时,与乡土社会形成了良好地互动,为民众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他们作为儒学思想的传承者,在婚丧嫁娶、宗教祭祀等社会活动中,积极承担乡村的礼教工作,宣扬礼教文化,既满足了乡民礼仪文化活动的需要,也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教化职能。他们参与乡土社会居间调停事务时,积极调解乡民矛盾,在维护乡村社会自治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收入微薄。清代乡村塾师的收入,主要由脩金与节仪构成。《儒林外史》写道,“愚表弟虞梁,……每年脩金四十两,节礼在外。”[3](P564)周进除“每年馆金十二两银子,每日二分银子在和尚家代饭”,[3](P21)还有贽见。“把各家贽见拆开来看,只见荀家是一钱银子,另有八分银子代茶;其余也有三分的,也有四分的,也有十来个钱的,合拢了不够一个月饭食。”[3](P24)《歧路灯》中孔耘轩承诺:“大约二十金开外,节仪每季二两,粮饭油盐菜蔬柴薪足用。”[18](P265)《引凤箫》中罗夫人欲聘白眉仙为塾师,“罗夫人遂写于聘书上,又取白金三两,彩缯二端,同贮于盒内作聘仪,又于书上写明,每年束金十六两,节敬在外。”[21](卷二)同时,他们的收入往往因塾师身份、授徒对象等,各有差异。就塾师身份言,童生收入较低,而秀才较高。如童生周进在薛家集坐馆时,只有每年十二两银子的馆金,而同为塾师的虞育德“每年三十两银子。”[3](P444)就授徒对象言,蒙师收入较低,经师较高。《履园丛话》记载,常州有某学究父子同为蒙师,所得馆谷不过四五十两银子。[22](P413)《问俗录》记载,清代福建古田县“民间总角授书,终年脩金四百文。至成童作文,多不过二三千。如有脩金二、三十千专请教读者,士林莫不羡慕。”[23](P70)
乡村塾师的收入虽千差万别,但普遍微薄,有的难以维持生计。《青毡诉苦文》慨叹,“今天下生意之最微薄者,莫如教书矣!”[24](P90)《儒林外史》写道,“(虞博士)娘子生儿育女,身子又多病,馆钱不能(够)买医药,每日只吃三顿白粥,后来身子也渐渐好起来。虞博士到三十二岁,这年没有了馆。……偏家里遇着事情出来,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3](P444)虞博士每年三十两的馆金,仅够维持家庭的日常消费,尚不足给妻子买药治病,更无法应对突发事件。相比之下,周进每年十二两馆金,显然无法保证家庭日用开支。又如《清稗类钞》记载“板桥未第时,……以课徒自给,值岁俭,生徒尽散,因举债以偿急需,约至端午,质剂子本,届时而畀。然虑不得偿,先期避焦山,依其乡僧,饰词避暑,实避债也。五月下旬,未得家中耗,不敢遽归。”[25](P2691)郑板桥也曾因馆金无法养家糊口而被迫举债,又因无力偿还而外出避债。蒲松龄诗中也写道:“思欲贷知己,所识无膏粱。况遭天年凶,粟粒等夜光。……恨为啼号累,数载不能偿。”[5](P531)乡村塾师的落魄生活,令人感慨。
因坐馆收入微薄,且时有失馆之危,乡村塾师往往还会学习一些其他技能,藉以补贴家用,或利用帮助乡邻处理日常事务的机会,收取些许额外费用。《儒林外史》中虞育德失馆时,“远村上有一个姓郑的人家请他去看葬坟。虞博士带了罗盘,去用心用意的替他看了地。葬过了坟,那郑家谢了他十二两银子。”[3](P445)晋江秀才王命岳《家训》云:“吾十九岁入泮,二十岁有友以午饭邀余伴读,晨昏则自家吃饭,又无束脩。其明年,此友再邀余教子,初约云:每月米三斗、蔬菜银三钱,无束脩;子弟则自教,只藉看文章,不敢禁先生出入。……教读之余,并日夜佣书,日可得八分,籴米供亲。”[26](P2208-2209)《捧腹集·青毡生随口曲》十一云:“一岁脩金十二千,节仪在内订从前。适来有件开心事,代笔叨光夹百钱”。[27](P401)晚清李虹若《书春》诗云:“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日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28](P153)这些无不表明乡村塾师生活的艰难与无奈。
四是生活孤苦。乡村塾师最强烈的馆居体验,是物质清贫与精神孤寂,这在作品中多有描述。《学究自嘲》写道,“况今文风扫地,束脩甚是不堪,铺盖明讲自备,仅管火纸灯烟,夏天无有蚊帐,冬里不管煤炭,搬送俱在圈外,来回俱是自颠。”具体而言,“送出东家满屋看,不见茶具在那边。炕铺一块席,上盖一破毡,角枕锦衾不见面。……早饭东南晌午歪,粗面饼卷着曲曲菜。吃的是长斋,吃的是长斋,今年更比去年赛。……十月北风寒,有炉无火炭难添,睡宿冷被窝,早起不敢恋。……室如悬冰灶无烟,对生徒冻的牙打战。”[5](P1748-1752)可谓衣食住行,样样堪怜。《随园诗话》写道,“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元黄喊一年。”[29](P261)《村学先生自叙》也写道,“吃了无数冷冷热热的饭碗,奈了几多酸酸涩涩的酒卮。”[24](P17)再如《屈屈歌》云:“屈屈复屈屈,仰面长吁诉造物。……寂寥一饭小窗下,冷淡三杯孤灯前。先生道学徒自尊,主人供膳何曾闻。但愿先生不饮酒,但愿先生不茹荤。”[24](P84)这些作品虽难免夸张之嫌,但乡村塾师的清苦生活却跃然纸上,无不令人慨叹,催人泪下。
与清贫的物质生活相比,孤寂的精神生活更令乡村塾师苦不堪言。清代最具代表性的乡村塾师蒲松龄,曾在《先生论》写道,“晨钟初罢,生徒之足迹星散,暮鼓已鸣,闷的我起视庭前。月寒光,逼旅人,愁心怀宋玉,秉烛自伤神。怕的是,一盏孤灯惨淡昏,如年长夜暗消魂,酸风透骨无人语,夜雨潇潇独掩门。”[7](P84)每当生徒散尽,塾师独自客居馆中,自是孤寂无比。尤其逢年过节,更是倍感凄凉。《学究自嘲》写道,“七月有七夕,织女本是牛郎妻,他二人也有团圆期。馆舍孤寂,馆舍孤寂,白面书生正惨凄。算今生大半是鳏居,红颜娇妻,有夫守寡他怎知?到不如田舍农夫长相依。……八月是中秋,先生书斋暗添愁,……细雨帘前滴滴流,在外人正是凄凉候。”[5](P1750)《重阳》诗又写道,“中秋恨是在天涯,客里凄凉负月华。今日重阳又虚度,渊明无酒对黄花。”[20](P580)其中孤苦与相思之情,与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之意,有异曲同工之妙。
五是行为受束。清代乡村塾师的行为亦受到约束,因为私塾的设馆时间极长,没有假期可言。据《训蒙条例》记载,“正月十五日进馆,十二月二十五日散馆。中间祭扫完粮,约共去十日,每岁坐定十一个月。”[9](P719)如此安排,便意味着乡村塾师除了春节休息一月左右,几乎全年在馆。倘若塾师在外坐馆,离家较近尚可回家“祭扫完粮”,团圆过年,离家较远则需终年在馆。《儒林外史》中,余大先生即是“在虞府坐馆,早去晚归,习以为常。”所以,当他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后,便劝告其弟“我们老兄弟相聚得一日是一日。从前我两个人各处坐馆,动不动两年不得见面。而今老了,只要弟兄两个多聚几时,那有饭吃没饭吃也且再商量。”[3](P584)余大先生身为塾师,对馆居生活的不自由有强烈体验,言语间道出了无数苦楚与无奈。加之,乡村塾师大多从事蒙师的工作,而学生年龄相对较小,在馆时需要塾师随时看管。《父师善诱法·尊师择师之法》即言,“抑知蒙师教授幼学,其督责之劳,耳无停听,目无停视,唇焦舌敝,其劳苦甚于经师数倍。”[30](P2)《塾师四苦》也写道,“先生偶出门,小子满堂舞。”[24](P21)正因如此,《英云梦传》中塾师王云去拜访旧友慧空时说,“不期被吴府请去坐馆,一刻也不能脱身。”[31](卷五)显然,乡村塾师不仅需费心劳力,且很难有自由时间,行动受到极大限制。
此外,乡村塾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本身对从业人员要求较高。如《塾中琐言》要求蒙师,“端品:为师之道,端品为先,模范不端,则不模不范矣。不惟立言制行,随时检点,即衣冠瞻视,亦须道貌岸然。尽心:品固端矣,而不勤课学徒,则勤者虽知奋勉,莫知指南;惰者日事荒诞,丛生弊窦。素餐尸位,过将谁归?专严:官箴有清、慎、勤三字,师范则有专、严二字。然严而不专,肃于外者,无所得于中。专则督课勤而无不严矣。故师道尤以专为主。……”[32](P100-101)这无疑是对乡村塾师言行的极大约束。《村学先生自叙》亦说,“身子里好似严姑手里无缘的媳妇,踽踽凉凉,拘拘束束,一星星要循规矩。……有所言,必议之而后言,谁许你乱嘈乱杂?有所动,必拟之而后动,谁许你胡做胡为?步履必安祥,居处必镇静,谁许你懈懈怠怠?衣冠必肃整,容貌必端庄,谁许你离离披披?茶坊酒肆,昔日那慷慨高情,到此来满将抛弃;偷香窃玉,少年的风流狂态,从此后一笔勾除。”[24](P18)这正是郑板桥诗歌中“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的绝佳注脚。
三、乡村塾师的文化心理
乡村塾师的生存状态,充分说明清代社会底层士人群体的艰难处境。面对如此境遇,他们充满厌倦,渴望辞馆;但迫于生存压力与功名诱惑,他们又无奈坐馆。他们的内心,充满矛盾与纠结、尴尬与痛苦,始终交织着人生苦闷与现实无奈。
一方面,乡村塾师因不堪的生存境遇,对塾师职业缺乏基本的认同感,甚至对坐馆授徒充满厌倦。以蒲松龄为例,他常年在外坐馆,作品中突出表现了对塾师生活的厌倦,道出了乡村塾师的心声。如《学究自嘲》写道,“暑往寒来冬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东家嫌懒惰,工多子弟结冤仇。有时随我平生愿,早把五湖泛轻舟。……抛妻抛子出门,人口情事此悬,细思好无来由,挣了几串铜钱。”《卷堂文》写道,“一金虽簿,俯首于浊富之门,百里莫辞,委身于不亲之地。视生徒犹骨肉,遂弃子与抛妻,以馆舍为福地,遽离乡而背井。……事非由我,辜负雪月风花,身属他人,受尽咸酸冷淡。……也作卷堂之文,永白为师之戒!”[33](P63)《教书词》又写道,“无计去聊生,谋馆教书苟延性命。……《三字经》嚎的俺喉咙疼,‘上大人’使的我手腕肿。看起来这等书实在难教,到几时才得跳出火坑。”[7](P81)他甚至在《闹馆》中,借和为贵求馆而自叹:“咳!好苦哇!(唱)想当初念书时错了主意,到不如耍手艺还挣吃穿。你看那皮匠手锥鞋补袜,只是那锢炉子锯盆锯碗,还有那木匠家打箱打柜,铁匠家打锄头还打刀镰,锡匠家打灯台又打锡盘,窑匠家烧黄盆又烧黑碗。手艺人吃的是肉肥卤面,可惜俺念书人饿的可怜。”[5](P813)这些作品对乡村塾师地位的卑微低下,事务的繁琐难处,生活的困顿孤苦,都有鲜活地体现。他们因这般处境而产生无限苦楚与郁闷,并由此而生发出迫切的辞馆渴望。
另一方面,乡村塾师迫于生存压力与功名诱惑,又无奈地坚持坐馆。蒲松龄《辞馆歌》写道,“少年胸襟宽,一心痴想超俗凡。百工技艺不肯为,万卷诗书勤苦读。读书望登天子堂,谁知读书成劳碌。连年留落在江湖,江湖生意多萧索。一生去住由主人,三飡迟早由奴仆。放狂又恐玷儒风,已把身心频检束。悄然孤枕梦魂多,冷落书斋形影独。俨如有罪人,坐在无罪狱。利觅蝇头且莫言,弟子愚顽难教育。……此情此情述向谁?长叹一声自藏蓄。”[7]尽管境遇不堪,但为了生计,只能“长叹一声自藏蓄”。这长叹饱含了多少辛酸与无奈。正如晚清传教士明恩溥记载:“那些只能在小区域内竞争位置的乡村教师,常常只有一点点微薄的收入。这种收入不过是:仅够吃饭的谷物,一些作燃料的干柴禾,一小笔钱,一般一年不超过十元钱。有时,那些只有一两个学生的教师,除了供饭,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报酬。自然,有人会问,这样收入微薄的事情还值得去做吗?这个阶层的一位教师回答说,总比待在家里什么都没有吃要好。”[34](P73)对此,晚清乡村塾师刘大鹏说得更加明确,“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途,到后来入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分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他还在日记中反复申明,“教书一事,非吾所愿,余今出门教书为贫所迫也”[35](P70-71),“读书之士若能于他处寻出糊口之需,即可不从事于一涂矣。”[35](P59)对于乡村塾师来说,坐馆只不过是养家糊口的方式而已,充满了苦楚与无奈。
然而,乡村塾师的付出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认可与回报,有时会遭受蔑视甚至侮辱。蒲松龄曾说,“乃今斯文渐丧,世教日衰,师况之寂寥,谁堪告语?舌耕之苦楚,只可自知。”[7](P83)“迨如今世道反,重钱财重衣衫,先生素号叫穷酸,谁想也有这一番。”[5](P175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亦记载,“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甚且被东家欺侮,而犹坐馆而不去。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世道如此,无人挽之,则迁流不知伊于胡底也。”[35](P65-66)作为清代典型的乡村塾师,他们的人生体验,无疑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乡村社会的教育图景与历史文化现场。而他们“世教日衰”“世道如此”等充满痛心与无奈的慨叹,又足以说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在清代乡村社会的衰颓。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清代乡村塾师在坐馆问题上,始终怀着痛苦与纠结的矛盾心理,但他们在乡村文化传承与建设中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无论是他们坚守的坐馆授徒,还是兼职的乡邻杂务,都在有形或无形中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着百姓日用。比如,清代乡村社会新生代读写算技能的养成,生活经验的获得,基本价值观的确立,乃至民间文化知识的传播,都有赖于他们的辛勤付出。乡村社会的邻里和睦,稳定和谐,也离不开他们的协助治理。可以说,清代乡村塾师是传统社会民间教育的具体组织者与实施者,他们在乡土社会贫瘠的文化土壤上,参与着文化传承与文化建设,维护着基层社会的稳定,播撒着知识之种与希望之光。正因为此,清代乡村塾师奠定了自身基层文化精英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