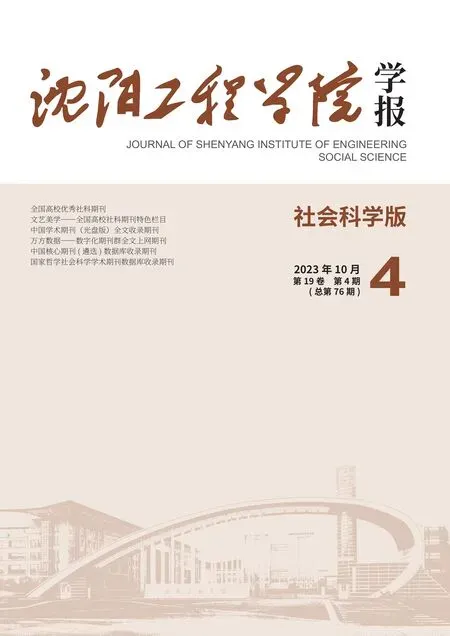异空间、深层空间与科外幻空间
——论《沙丘》中的怪诞场域书写
王丽媛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6)
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1920-1986)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的科幻小说《沙丘》是美国科幻新浪潮运动的产物。作为“软科幻”经典作品之一,以人物与其思想、身体、物质世界、政治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寄寓了对西方政治、生态、哲学和宗教境遇的反思。与新浪潮以前的科幻通俗小说不同,《沙丘》具有宏大而成熟的空间建构,“空间”是《沙丘》的书写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
事实上,任何一部科幻作品的叙事都开始于空间建构,空间作为叙事的必要构件,具有科幻叙事本体论的地位。正如王峰指出的,科幻作品的特异之处就在于每部作品所建构的特殊的世界,这一世界建立在时间与空间的基础上,“而在时间的表征之上,一个未来世界的展开依赖于空间形式上的描绘与建构。”[1]2在怪诞美学理论的视域中,从美学而非叙事的角度审视科幻小说的空间,可以将科幻小说的空间建构及其产生的美学效应称为“怪诞场域书写”。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将科幻小说的美学效应称为“怪诞”,它由身体表征、空间建构、人与物之间的空间政治共同生成,怪诞场域书写可以看作是科幻小说用以书写现实的一种策略。
《沙丘》的“怪诞场域书写”扎根于“异空间—深层空间—科外幻空间”这个三元结构之中,这个三元结构来源于福柯的“乌托邦”与“异托邦”这一关系性空间理论。根据福柯的观点,科幻小说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它在其物质意义上真实存在,并且能够凭借它所再现的社会景观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理想化或对立关系,对读者产生真实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小说是一个“整体异质的异托邦”[2]206,并且具有朗西埃意义上的审美异托邦的功能。综合以上两点,科幻小说的物质性文本及文本中基于再现的审美世界可以称为“异空间”。而“异空间”又是福柯所说明的“内部异质的异托邦”[2]206,也就是说,在“异空间”这个物质性和再现性空间之中,还存在着一个原始的、实在的感官世界,这个世界在科幻小说的书写中通过“异质性经验”[2]206被揭示和勾勒。它与“异空间”之间形成“僭越”,生成了“怪诞”的效果,也就产生了第二重空间“深层空间”。而作为“异托邦”的科幻小说,它与科学叙事所建立的空间之间存在“揭露”或“补偿”[3]27的关系,标示出其间“知识与权力叙事的位移”[4]502,并将科学叙事前景化,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陌生化,从而在认识现实世界的层面上达成其审美目的。
从诗学层面来看,在《沙丘》中,这个三元空间结构生成了小说的叙事空间与审美效应:首先,异空间把小说中奇异的人物与身体形象转化为可以被审美的对象;而深层空间则嵌套在异空间当中,它具有的“他异性”特质对异空间造成了僭越,产生了怪诞效果,“异空间—深层空间”共同形成了文本在叙事层面的空间结构,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小说出现了体裁上的不连续性,使小说的世界偏离乃至颠覆了科学原则,变成了一个从逻辑上比科学更接近实在的“科外幻空间”。这个三元空间结构为《沙丘》开辟了一条通往实在的现实主义道路。
一、异托邦:非怪诞的怪诞
科幻小说的叙事始于一个异世界空间,这个基于再现的文学审美空间为拟科学思维所构想的物理规则、奇异的生命提供了一个使之科学化、合理化的场域。我们借助朗西埃的美学异托邦概念,称之为“科幻异托邦”。朗西埃提出,“‘异托邦’意味着想象‘异’(‘heteron’)或者‘他者’(‘other’)的一种特定方式,这是作为位置、身份、能力分配之重构效果的他者……它并不为伦理构造所形塑的各种习惯看法多增添一种习惯看法。相反,它创造了一个点,在这里,所有那些特定区域及其所界定的对立都被取消。”[5]206这一美学异托邦,在科幻小说中表现为想象和“真实”交织而成的未来世界,这一空间扎根于其物质性和可感性层面,在将种种奇异的事物转化审美对象的同时,为小说增添了“科幻现实主义”[6]419所要求的真实效果。
在《沙丘》中,这一科幻异托邦就是叙事展开的重要舞台:厄拉科斯星球。小说通过“水”这一叙事因子,串联起一个行动网络,生产了这一空间的物质属性。在《沙丘》的故事中。由于水资源的珍稀,厄拉科斯人必须不断“回收自己身体的水分”[7]35,他们身体中的唾液和血液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源,人们通过向某人吐口水来表达敬意,人死后,尸体中的血液被回收、蒸馏为纯净水,再供活人使用。在这里,水将人体本身变成了被收取、被循环使用的物质资源。水的短缺被渲染到极致,表现为物与人在价值上的等同,分类上的侵越。在每个生活在厄拉科斯的人看来:“一颗枣椰树每天需要四十升水。而一个人只需要八升。也就是说,一颗枣椰树,相当于五个人。那儿有二十颗树,也就相当于一百个人。”[7]71水变成人和物共同的计量单位。于是,在小说的话语中,人与物的混淆为一,生产出迷惘恐怖的真实气氛。为了适应厄拉科斯极端艰苦的环境,人类需要特殊的储水装备“防护服”,这个装置切断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把人体变成了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进食和排泄两种分属身体上部和下部的行为,在这里发生了颠倒:“身体的运动,尤其是呼吸和某些渗透行为……会为装置提供动力……回收的水分流入积存袋”“尿水和粪便在大腿的棉块中得到处理……在沙漠里……通过口腔的过滤器吸气,通过鼻腔管子吸气。”[7]128-129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奇异互动,将小说的世界呈现为一个陌异的领域,但异空间的存在,使其符合了该空间的“物理现实”,赋予这些怪诞现象以可理解性,因其极具科学性的谨严与详细,对读者产生了吸引力,将这些险恶的事件转化为审美对象。
其次,《沙丘》创造了大量怪诞身体[8]53形象,生产了科幻异托邦的感性特征。为了将世界与其人物有机地结合起来,小说必须产生空间的感性特征,人无法想象超出感知或不能感知的物,于是“一种新的特性开始需要一种新的感知,而新的感知则要求一个新的感知器官,因此最终就要求一种新的身体”[6]164。
有论者将《沙丘》所塑造的怪诞身体称为“熟悉又陌生的普通人类”[9]27。这一怪诞人物谱系包括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门泰特、宇宙领航员、变脸人。主角保罗的母亲杰西卡夫人就出身于姐妹会,她不仅能通过语调和语气的变化像女巫一样对他人进行精神操纵,而且能调节细胞的代谢速度、控制胚胎的性别。而门泰特,是人战胜并毁灭了智慧机器的巴特勒圣战之后出现的一种智慧机器,能够代替人类进行高速精密运算。宇宙领航员与变脸人的身体形象更加怪诞,前者的身体与动物杂合,有的是人与蠕虫的结合,有的是鱼人;而后者则打破了性别二元界限,他们本身没有性别,却可以随意地变为男人或女人。这些人物依靠美琅脂的力量摆脱了“自然”束缚,超越了人类自然肉体的极限。在象征的层面上,这些怪诞形象表征着人与自然的断裂,异空间世界淡化了这些怪诞身体的非自然性,传达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后现代人类孤独与身份失落后无所归属的现实。
总而言之,《沙丘》在异世界的建构上,一方面通过独特的物理规律、生产生活方式,为异空间生产真实可信的细节,通过人类与这个空间的互动,生产出独属于这个世界的文化与伦理。另一方面,由诸多怪诞身体所传达的感性特征,为文本世界创造出“真实”的效果。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使得厄拉科斯星球这个借由“想象力堆砌起来的事物”[6]164具有了可认知性,似乎这个虚构的世界归根到底还是由“抽象的理性分子组装而成”[6]164,这就构成了科幻小说异托邦的“理性依据”。
这样一来,异空间就呈现出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的特征,同时包含了实践的空间即空间的感知、物理的物质层面,空间的再现即构想的、文本化的空间,以及再现的空间即具体的、现实的生活空间[10]83-89,这个空间的复杂性在于,厄拉科斯星球首先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其中组成它的各种空间构件,如沙漠等,在现实当中都能找到对应物,但它又在内容上超越了这个科幻小说的虚构地域,获得了普遍的、认知的和审美的意义,但是这个被文本化的空间一方面缺少其作为真实空间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超越了空间的物理界限。
因此,与之相对的是,异托邦的作用并不纯粹,其效果是反讽的:它既使异世界散发出怪诞的魅力,又没有使它的怪诞效果充分展开。作为一个非自然世界本身,它不断地把身处其中的事物自然化,使得两者“都没有得到正当的权利,每方都对对方起歪曲的作用”[11]52。小说世界中的物理规律、科学逻辑和理性模式,借助科幻异托邦这个特殊场域,将怪异之物纳入了由普遍常识和科学理性支持的“科幻现实主义”[6]419的世界观当中,使科幻小说的“怪”变成“正常”。简单来说,异空间这一科学化、合理化场域,在将险恶的事物转换为具有美感的对象的同时,也削弱了科幻小说中怪诞的表现效果。
二、深层空间:无法取消的怪诞
异空间与深层空间共同形成了小说叙事层面的空间结构。在物理范围上,深层空间属于异空间,但它却与异空间形成对立、“颠倒或抹消”[4]501,詹姆逊认为这种对立是“全新的、乌托邦的形式”,通往“差异性的新世界”[6]431。《沙丘》提供了经验、感知和审美意义上的深层空间形式,并最终在“身体”这个层面上得到表现。
深层空间中的事物、现象、逻辑、规律,与异托邦展现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强烈对比,二者之间存在无法抹除的差异。与异托邦的反讽效果完全不同,这一深层空间的性质、它对异托邦的僭越造成了科幻小说中无法取消的怪诞。
在《沙丘》中,厄拉科斯星既是叙事和审美意义上的异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深层空间。该星球是黄金能源美琅脂的产地,面对这个既富饶又落后的“异域”,“入侵”这片土地的主角们被赋予了征服者的身份。他们的视角作为读者考察异世界的观测点,使得读者跟随他们的意图和行动,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然而这个理性的发现只是作为对“奇怪的新空间的感知的一个纯粹的掩饰”[6]342,也就是说,读者首先将厄拉科斯识别为科学现实主义式的异托邦。但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个空间中逐渐出现了不可理解的新领域,读者也开始重新认识厄拉科斯,使它作为深层空间的一面显现出来,这个空间首先表现为沙虫这一宇宙怪物占据的地底世界。
在《沙丘》的叙述中,沙虫是一种出没于沙漠的巨大蠕虫,是厄拉科斯星最原始的生物。原初怪诞的“洞窟性”在沙虫的形象中表现得很突出:它生活在极深的地底,最大的个体可达一千米,其头部没有眼睛,只有一个巨大的口器,组成口器的瓣膜展开时如同巨大的花朵,露出密集的牙齿和深渊般的食道。沙虫的幼虫沙鳟可以产出早期香料,这些香料埋在地表之下,积累到一定的量时,才会经由爆炸而露出地面,在曝晒中变成香料美琅脂。沙虫这种来自地底洞穴的怪物,不仅在生活方式、身体结构上,与异世界的其他生物迥乎不同,被弗雷曼人视为神圣动物。而且它们能够区分人类的活动和自然因素导致的沙漠活动,不仅具有“人格化”[6]50的属性,而且具有很高的智慧,明白自身的偶然性和脆弱性,是一种具有智慧的他者。沙虫与人的相同相异,使得它和它的世界成为对异托邦有效的他异空间。
深层空间的怪诞,不只停留在它与表层空间的性质对比,还体现在它对表层空间的僭越。《沙丘》第四部中,雷托二世为了开启人类社会的“黄金通道”,将自己的身体与沙虫的躯体结合了起来,新的身体不仅保留了人的智慧头脑,而且变成了人和虫的肉麻而恶心的混杂:它“体长七米左右,直径两米多点,一道道横棱几乎布满全身;一头顶着我那张厄崔迪脸,与常人身高相当,稍往下就是双臂和双手(仍颇具人类的形状)。腿和脚呢?哎,萎缩殆尽,变成鳍足了,没错,沿身体后摆的鳍足”[12]15。“直径”“横棱”“顶着”“萎缩”等描述,突出了这非人肉体的物质属性。雷托二世和沙虫的结合,不仅使沙虫从宇宙中绝迹,彻底改变了厄拉科斯的生态环境,使其从干旱的沙漠星球变成了一个湿润的生态系统,而且把宇宙带回了残酷的封建时代,“他对宇宙的整体知识便以一种在形而上学上更为狭隘的方式束缚着人类”[13]237,沙虫对人类身体的僭越,即深层空间对表层空间的僭越,导致了物质世界和人类在认识论上的灾难巨变,雷托二世的怪诞身体作为僭越的表征,就提供了展开上述象征意义的叙事空间。
《沙丘》的第二个维度的深层空间与空间僭越表现为人物的“精神分裂”,即精神现实的多重分裂和相互侵越。小说中,保罗家族对未来的预见,具象化为精神现实:保罗在精神世界中看到的未来,裂变为多个平行时空;而厄利亚和雷托二世的精神世界更加复杂,他们的头脑中有许多别人的灵魂和意识,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同时存在,他人意识向自我的僭越导致自我意识被扰乱,甚至被抹杀。这种奇特的意识结构形成了自我分裂的怪诞空间,这构成了小说中后期叙事展开和运行的主要空间,小说不再遵循亚里士多德式的、由人物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串联起来的情节剧,而是由一系列在主角精神世界中发生的博弈、推理、争论缀连起来的“思想剧”。这形成了《沙丘》独特的风貌:以“思想而不是以人物为中心”[14]120,甚至也不以科技奇观和人物行动为中心。它的未来世界围绕着关于理性的推论而非技术的推论被建构起来,这也是《沙丘》在一众科幻作品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在《沙丘》中,这些怪诞的宇宙生物与人类奇异的精神世界,在表层空间之下划出一个深层空间。《沙丘》之后的科幻小说和通过其他媒介得以呈现的科幻作品中,也能看到相似的空间结构。异空间与深层空间共同构成的这种叙事结构,具有独特的表现效果和表现力度,与观众的审美感受勾连起来。例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范·沃特格经典作品《异形》当中,就捕捉到了其中的“双重外星情境”的叙事模式[6]426,詹姆逊认为此模式的实质即创造一个表层宇宙空间中的深层空间,暗示在作为主要舞台的外星世界中,还存在另一种更神秘、更高级或更危险的外星文明,它们常常以文明遗迹、文明废墟的幽灵形式、破卵而出的洞穴物形式或第三方力量的身份参与叙事,表现出其幽深的神秘感和强烈的他异性。这种双重空间的设置,为小说的表达效果和美学品格加入了无法取消的怪诞,使科幻小说或其他形式的科幻作品在形式上表现得更加“复杂、精密和有趣”[6]427。
三、科外幻空间:虚构怪诞
科幻小说以异空间和深层空间的嵌套结构,创造了这一文类的审美效果——怪诞。但科幻小说的终极怪诞来自“虚构”,这不仅指常识意义上的小说的虚构性,而且特指科幻作品的虚构原则:科学和超科学的合理调配原则。科幻小说这种富有科学精神的幻想活动,能够创造一个偏离乃至颠覆科学原则的“科学外空间”,从而打开一条突破了科学主义的“现实主义”道路。
要理解科幻小说中的怪诞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首先要明确的是,尽管科幻作品呈现着“想象的存在”[15]142,或者说只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含混意向,但读者能够凭借文化储备和理性的头脑,自动地把文本世界呈现的局部想象填补完整,这种填补既是“叙事文类上带来的无意识填补,也是理性有意识忽略的填补”[16]83。也就是说,科幻小说的科学逻辑与科学观念,往往由小说的叙事逻辑作为基础。其次,科幻小说的虚构实际上呈现出超越当下现实生活的特点。科幻小说对其描绘的世界所进行的科学推论,往往带有科学全能的先验性色彩,但它又经常无意识地通过把自身构造为一个“科学外空间”来推翻这种先验论。读者能捕捉文本与现实世界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因而在对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就采取了一种辩证的理解,“一方面把它认为是虚构的,另外一方面又认为可能是真实的,与实际产生微妙的呼应关系。”[15]146换句话说,建立在虚构之上的科幻世界,它展示的现实与我们当下的现实世界并没有完全的一致性,而是通过对科学主义的自我指涉来抵达了“现实”。
在《沙丘》的叙事当中,神秘的厄拉科斯“沙漠”就是一个典型的“科学外”空间。这个空间的超科学性首先体现于弗雷曼人的风俗习惯,弗雷曼人的部落有一种特殊的领袖:圣母,弗雷曼人遵循一个神话传说般的习俗,如果有人喝下死去沙虫的体液和香料混合形成的生命之水还能保住生命,就可以成为弗雷曼人的精神领袖,即圣母。在小说中,杰西卡夫人喝下生命之水还造成了另一个超科学事件:生命之水将数代圣母的意识植入了她腹中的胎儿厄利亚的头脑中,厄利亚一出生就拥有数千年的记忆和儿童的样貌。在小说的叙事中,这个事件的原理归于香料神秘和含混的作用,以及圣母自身的神秘能力。
这已经超越了小说怪诞人物谱系所体现的“科幻现实主义”传统。事实上,宇宙领航员和变脸人也同样显示出《沙丘》作为科幻小说在体裁上的不连续性,这些超科学的人和事把《沙丘》的叙事从科学幻想带向了“神话或者是一般性幻想文学”[6]343。而且这一系列超自然、超科学事件的物质基础:香料,其性质和原理也没有给出科学的解释,显示出不可认知的神秘特性。随着情节更进一步发展,香料对厄利亚和保罗的影响,使他们变成了比那些怪诞人物更恐怖的“异类”与“圣人”,这些叙事中突然出现的元素不仅落在了现实的科学原则之外,也被虚构文本中“科学世界”排除在外。就这样,小说的科学世界及非理性的、非“科学现实主义”的世界与人物,形成双重的“超科学”结构。
正如詹姆逊指出的,在所有的文类中,科幻小说对自然和非自然、科学和非科学世界的意识和分类是最为清晰的,但科幻小说的科学和自然书写呈现出鲜明的人造性,即它们扩展了这两个能指所可能指向的虚构现实的范畴,也在某种意义上使得这两个范畴“不再具有正当性和常识性”[6]337。也就说科幻小说的文本作为能指的编织物,首先不绝对地指涉外部现实,其能指逐渐滑向非科学认识的领域,以“非科学”“反常识”作为最终的意义指归。而这一趋向,与法国思辨实在论学者昆汀·梅亚苏所提出的“科外幻小说”的构想达成了耦合,梅亚苏认为科幻小说最终可能走向科外幻,即展现出一个超越科学和理性辖区的科学外世界,这个世界逃避了“真实”和“现象”的把捉,并且否定了构建任何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但依然能够通过知觉被认知,在这里“任何表现出来的不规则都不足以证明没有隐藏在无序的表面之下的法则存在”[17]772。
《沙丘》就展现了这样一个既遵循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容纳了梅亚苏意义上的偶然性的世界。梅亚苏认为,科幻小说有极大的叙事潜力,即便是一个“因果性和必然性统辖之外的世界”也“允许叙事,文学作品的包容性可以容纳它的反常离奇”[17]771。即科幻小说可以容许我们想象并接近一个非科学主义的理性世界,如今,我们生活的现实也逐渐表现出科外幻世界的特征,量子力学挑战了作为科学基础的因果律知识,科学主义的严格因果性与客观性也受到了质疑。而科外幻的书写则呈现出一种彻底的革命性和严肃的认识论诉求。纵观科幻小说的发展历史,偶然性和非理性因素与认知性、科学性之间的张力,贯穿了科幻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形成了这一文类独特的审美品格。
总而言之,科幻这一文类具有一种既贯彻科学原则又力求超越科学原则的张力,在自身的书写中不断地对科学主义进行自我指涉,只有这样,科幻小说及经由各种媒介呈现的科幻作品,它们所具有的乌托邦维度才得以实现。因此,从审美效果看,科幻小说的书写目标就是使我们“对于自己当下的体验陌生化,并将其重新架构”[6]377“唤起人类对时空和物的原初感受力,用以对抗被理性化概念化的日常世界”[18]16-17。
从认识论层面看,科幻小说展现了现实世界与科学主义所认知的世界之间存在的裂隙,也呼唤我们对于世界的新的感受与新的知识。
四、结论
科幻小说的怪诞场域书写建立在其空间架构的基础上,“异空间—深层空间—科外幻空间”这个关系性空间结构,将科幻小说的空间形式与其审美效果联系起来考察。作为物质存在和审美空间的科幻小说,它基于再现所建构的空间,作为环境与小说中的人物、事物发生互动,将怪异的事物转化为审美对象;另一方面,深层空间以其实在性,对异空间发生作用,使科幻小说走向了对自身的反讽和对科学叙事的“颠覆”。今天的科幻书写或延续或发展了《沙丘》式的“科幻史诗”路径,达成了达科·苏恩文意义上科幻作品的终极使命——“认知性陌生化”[19]4的目的,释放着现实世界的潜能。可以说,正是通过“怪诞场域书写”这一书写策略,科幻小说实现了其独特的现实主义路径,生成了其独特的美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