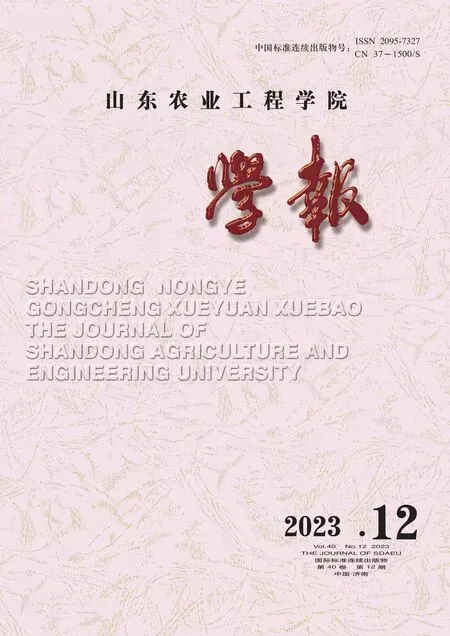新时代乡贤文化认同的价值证成与提升路径
周 玉
(亳州学院,安徽 亳州 2368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目标要求。我国目前有8亿农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重视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立足农村、面向农民、围绕农业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乡贤文化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儒家思想为文化基因、以乡村为特定场域、以农民为价值主体,在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建立了沟通的桥梁,能够接地气、暖民心、诉民情,较好地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农村的建设要求。新时代的乡贤文化有哪些特征,乡贤文化认同意义何在,乡贤文化建设走向何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关系到乡村文化建设力量的激发和凝聚,关乎是否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新时代乡贤文化认同的内涵与生成机理
新时代的乡贤文化,是新时代的乡贤和村民在党领导的乡村振兴行动中共同创造的乡村文化形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在乡村的赓续,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精神意涵和坚实的实践基础。乡贤文化认同,基于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是党和政府对于乡贤角色的肯定、人民群众对于乡贤工作的认可,以及乡贤对于自身形象与身份的积极维护。作为一种价值共识,社会对于乡贤文化的认同,源于深厚的儒家文化基因和鲜明的时代主题,形成于乡贤文化的内生与嵌入机制,具有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相结合的现实特征。
1.1 乡贤文化认同的内涵释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自然的人化。文化的产生,反映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人既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又是文化认同的主体。文化认同既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也是一种集体文化现象,“人的认识、思维的定式存于一个人的群体中,形成了对某一种文化现象一致认可,并反映到人的行为中,就成为文化认同。”[2]
乡贤文化认同,由“乡贤”“乡贤文化”“乡贤文化认同”等若干概念组成。乡贤,包括传统乡贤和现代新乡贤。学界对于传统乡贤的身份界定,意见基本一致。王先明认为,“具有功名身分、学品、学衔和官职而退居乡里者,是乡贤阶层的基本构成”[3];胡海鹏认为,乡贤的特质包含“在乡性”、资财、知识和道德四个要素[4]。较之于传统乡贤,新乡贤来源广泛,“指的是在基层民众广泛认同的基础上,能够为家乡经济文化建设提供各方面有益帮助的社会贤达人士,具有乐于助人、敦睦乡邻、无私奉献等高尚的道德品质”[5]。新乡贤包括“在场”的乡贤和“不在场”的乡贤。“在场”的乡贤,是指那些生长在农村、工作和生活在农村的乡村领头人,他们或是具有较高的道德威望、社会地位,能够为村民排忧解难;或是能够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参与乡村治理。一般由退休教师、退休干部、乡村医生、返乡创业人员等组成。“不在场”的乡贤,是指由乡村走出的精英,他们或是企业老板,或是体制内的精英,或是社会贤达,通过捐资助学、建桥修路等形式反哺家乡,获得村民的赞誉。
乡贤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精英文化、道德文化。王泉根认为,“乡贤文化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先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和教化策略”[6]。钱念孙指出,乡贤文化的内容包含三个层次,即“乡贤的构成及特质”“乡贤的作用及影响”“乡贤治理乡村所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7]。乡贤文化的精神内核,便是由血缘、乡情、乡愁所激发的担当意识、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乡贤文化展现的是乡贤回馈村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的美好愿望;是乡贤在立足农业、服务农村、面向农民而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彰显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时代新风。
乡贤文化的内容与乡贤文化认同相伴相生。乡贤文化认同,指的是乡村主体(包括建设主体、共享主体)对以乡贤为主体所展开的乡村道德实践、乡村政治实践、乡村经济实践、乡村文化建设实践的认可、支持、赞同。从乡贤文化的建设主体来看,新乡贤是应然的建设主体,但是由于乡贤的服务对象是身边的乡里乡亲,乡贤文化是建立在乡亲们和乡贤的良性互动基础之上的,二者构成了乡贤文化认同的双重主体。从乡贤文化的共享主体来看,乡贤和村民也是乡贤文化的共享主体。这是因为,乡贤在为村民做贡献的过程中,发挥了自身的能量,体验到了奉献的快乐,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村民的快乐、农村的欣欣向荣之上,成了真正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精神上得到满足。同时,村民的矛盾纠纷得到解决,脱贫致富找到了新路,乡贤的帮助带来了实际利益,文明新风带来农村环境的优化,奠定了乡贤文化认同的现实基础。
1.2 新时代乡贤文化认同的生成机理
乡贤群体因其特长不同而贡献各异,他们对农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脱贫致富、矛盾调解、乡村决策、文明创建、乡村教育等,涵盖了美好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乡贤文化的实践性特点,决定了乡贤文化认同的生成具有典型的社会心理机制。
第一,乡贤文化认同作为乡村文化的心理表征,来源于深厚的儒家文化基因和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新时代的乡贤文化是传统乡贤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从古至今,乡贤文化具有“变”与“不变”的双重主题。“变化”的是外在环境,社会制度、时代主题发生革命性变化,农村面貌得到根本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不变”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儒家提倡“内圣而外王”,以道德修身为起点,进而影响民族、国家,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自古以来,士人追求“学而优则仕”,无论身处顺境逆境,都不忘心忧家国、兼济天下、造福苍生,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儒家入世传统。乡贤文化是经过历代传承、积淀而形成的,实则是儒家文化的乡村形态。人们景仰乡贤、崇祀乡贤,建祠、树碑、铭记,感恩乡贤为地方百姓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乡贤文化得以传承,乡贤精神因此而不朽。在乡贤的影响下,人们安土重迁、重农固本、孝老爱亲、守望相助,这种道德情怀一直延续至今。新时代的乡贤,继承了儒家文化的思想精华,主动担负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彰显了传统农民的勤劳品质和当代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建构了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和时代气质的新时代乡贤文化。对乡贤文化的强烈认同,有利于增强人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时代使命的自觉体认,进而将这种思想意识转化为精神动力,投身在乡村振兴的建设实践中。
第二,乡贤文化认同作为乡村文化的思想共识,形成于“内生”与“嵌入”共存的乡村治理机制。从“内生”到“嵌入”,是乡贤逐步为乡村社会所认知与重视的过程,也是乡贤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因此,乡贤文化认同包含了对于乡贤内生性的认知、乡贤组织嵌入机制的认同。
一方面,乡贤文化是一种内生性文化。乡贤文化的“口碑”是乡贤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其形成于农村特有的熟人社会,不依靠任何外力的强制推行。乡贤文化的“内生性”特征表现为,“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各种行为模式、习惯和理念具有同一性,在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更好地同乡村居民保持彼此间的良好关系,促进乡村社会环境的和谐稳定”[8]。乡贤文化的内生性反映了乡贤与乡村社会、与村民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天然关系之上的,因而具有共同体的性质。乡贤文化的内生性还表现为,乡贤作为道德权威的内生性、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内生性。作为内生效应的延伸,乡贤文化认同突出地表现为村民对乡贤形象及其价值观的认同,这是在村民与乡贤长期良性互动中自然产生的,既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另一方面,乡贤文化的“嵌入性”是指,乡贤“作为一种半正式治理力量在乡村基层政治场域中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监政的主体角色,在嵌入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与村委会、村民们形成强大的合力,以稳定的三角治理结构来均衡调和国家治理要求和村庄内生需求”[9]。新时代,国家提倡构建“德治法治自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乡贤作为乡村重要的内生力量,需要有机嵌入乡村治理格局中。在这种嵌入机制中,由于官方的授权,乡贤以乡贤组织(如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乡贤咨询委员会)的名义参与乡村治理,能够有效弥补基层治理力量的不足。相对于传统的治理结构,乡贤组织是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补充,由村委会赋予其合法性,是半官方、半民间的结合。乡贤组织的嵌入特征,决定了乡贤文化的融合性,即作为嵌入的结果,乡贤文化融合了法治文化和德性文化,对于引领村民的文化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乡贤文化认同作为乡村文化的价值证成,有赖于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结合的调节机制。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0]。在农村熟人社会中,农民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取决于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协调机制。一方面,乡贤的作用发挥有赖于“利益表达”机制,使得乡贤文化认同具有鲜明的物质利益导向。乡贤组织嵌入乡村治理结构,被赋予官方与民间的双重“代理”身份,具有中枢的作用,不仅能够代表官方主持正义、协调利益关系,还能够代表乡村居民表达利益诉求,以及通过开办企业,推广养殖、种植技术,帮助村民实现物质利益诉求。村民对于乡贤文化的认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能够从乡贤的工作中受益,即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乡贤的作用发挥依靠“道德调节”机制,能够引导村民解决精神危机与价值缺失,获得精神利益。乡贤威望的建立,以道德调节为中介。发生矛盾纠葛的邻居两家,愿意接受乡贤的调节而不是选择诉诸法律,是因为他们信任乡贤这一乡村内生已久的道德权威。乡贤之所以能够取得农民信任,能够“一呼百应”,是基于乡贤较高的道德水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在上述场景中,村民和乡贤的关系,无论何时都无法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治理关系、现代企业制度下的雇佣关系或者现代司法体制下的法律关系去衡量,而较适宜用利益调节和道德调节的机制去考量。因此,利益调节和道德调节作为乡贤的作用发挥机制,是乡贤文化认同生成的必要条件。
2 新时代乡贤文化认同的价值证成
建设乡贤文化、弘扬乡贤精神,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场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提升乡贤文化认同,有助于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凝聚乡村振兴的精神力量,引领乡风文明建设,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2.1 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乡贤文化内生于传统乡土社会,其精神内核以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为特质,表现为“立功立德立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积极入世思想。“乡贤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蕴含着德治、善治的力量,是维护乡村社会祥和稳定的思想源泉”[11]。人们崇尚乡贤,表达了对正直、正义、无私、奉献的乡贤的感恩和回馈,渴望美好的乡村生活能够永续发展,因而形成了传承千年的乡贤文化传统。
乡贤文化代代相传,不仅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而且使得中国精神、主流价值观具有现实的文化载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乡贤文化在当代为社会所重视,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有了弘扬和发展的空间;乡贤文化的认同,能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的时代传承。一方面,乡贤文化认同有助于形成见贤思齐、知恩回报的社会环境。乡贤文化内蕴着乡贤精神,既包含了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也蕴含了扎根家乡、敢闯敢干的时代精神。新时代,在乡贤的帮助下,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邻里关系更加和谐。人们打心底敬佩乡贤、感恩乡贤,热情回报乡贤,能够主动弘扬乡贤文化,传承乡贤精神,促进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另一方面,乡贤文化认同能够对乡贤形成正反馈、激发乡贤进取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乡贤身上彰显了胸怀天下、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积极思想。乡贤的工作受到表彰,乡贤文化获得群众认可,乡贤的精神受到了赞誉,表明乡贤的努力取得了成效,这能够激励乡贤充分认识自身价值,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进取的精神投身乡村振兴。由于了解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了解乡村文化的薄弱之处,乡贤能够担负起文化传承和乡村建设的时代使命;作为乡贤文化的建设主体和认同主体,文化认同的正向激励能够促进乡贤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大舞台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和践行新时代的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脱贫攻坚精神。
2.2 丰富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
新时代的乡贤文化是实践性文化,这种实践包含了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道德培养实践、社会治理实践。各种实践性活动均是在乡贤与农民的共同参与下进行的。在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诸种关系网络中,乡贤作为黏合力量,发挥了核心作用,在乡村构筑了由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组合而成的命运共同体。从物质生产实践来说,乡贤帮助农民掌握畜牧养殖技术、蔬菜瓜果种植技术、抗旱保苗技术等,拓展了知识领域、提升了脱贫致富的本领,农民生活充实而有意义。从精神实践来说,乡贤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说过去、谈未来,为村民调节矛盾纠纷,促使双方握手言和、共续乡情,促进了社会关系的和谐,使得村民的精神生活摆脱阴霾迎来光明。从道德实践来说,很多乡贤本身就是孝老爱亲的模范,他们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付出,践行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华传统美德,将家庭道德实践引向乡村社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引领了乡风文明,净化了村民的精神世界。从社会治理实践来说,乡贤治村是推动乡村善治、实现乡村“三治”融合的有效途径,他们通过亲身实践,宣传党的政策,为村民排忧解难,扶危纾困,让村民了解国家发展现状,感受时代的发展变化、乡村面貌的日新月异,更新知识认知、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精神生活更加充实。因此,强烈的乡贤文化认同,有助于发挥乡贤的积极作用,推动乡贤文化建设,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需求。
2.3 凝聚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乡村振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占有重要位置。一般认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包括“村党委(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农民群体、社会组织”[12]等。在乡村建设实践中,部分村两委组织存在着战斗力不足、业务能力缺乏、进取精神弱化等问题,往往无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资源优势,形成乡村建设的有效合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的基层干部不熟悉群众的情况、不了解群众的需求、不能对群众的诉求有求必应,因而无法与群众建立有效的合作渠道。乡贤的出现,有效弥补了上述缺陷。
从乡贤的来源来说,新时代的乡贤不再如传统社会以“士绅”为主体,而是包含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种粮大户、返乡创业人员、乡村医生等多种职业。由于乡贤来源广泛,而且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他们在凝聚各种力量、整合各种资源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因而,乡贤文化具有精英文化的特质。人们信赖乡贤,以乡贤为核心织就了复杂的熟人关系网,将乡贤视为解决各类难题的金钥匙。乡贤文化具有超功利性,其建立在德性与感情之上,超越了乡贤本身的利益诉求,将群众、集体的利益视为最大公约数,能够获得群众的认同,因而能够引领群众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作用机制来说,乡村内生的乡贤群体,经基层组织的授权成立乡贤组织,嵌入到乡村治理体系中,不仅有助于处理村委会无法解决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等小事,还能够形成一种有效的黏合力量,发挥上传下达、协调左右的枢纽作用,增进村两委组织与群众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奠定乡村振兴的群众基础。因此,乡贤作为乡村建设主体之一,不仅提供了物质力量,还提供了智力支持以及精神力量。乡贤文化认同,作为乡村社会的普遍共识,体现人们对乡贤思想品质、业务素质、敬业精神的积极肯定,这种肯定性评价能够形成一种粘合力量,凝聚各方主体、形成合力,加快乡村振兴的进程。
2.4 引领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
乡风文明是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道德在乡村社会的体现,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风文明建设能够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不竭动力,为乡村生态宜居提供智慧源泉,为治理有效提供保障,为生活富裕提供丰富内涵[13]。国家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树立文明新风,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不少农村仍然存在一些陈规陋习,如天价彩礼、人情礼金繁多、攀比建房、封建迷信、重男轻女等,这种由传统社会演化而来的社会风气至今影响着农民的思想观念。在这种集体的观念约束之下,农民负担过重、精神困顿、无反抗之力,亟需破解。
乡贤文化是传统道德和时代精神的结合体。乡贤文化对于乡风文明的作用,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嘉言懿行、道德感化、榜样示范,在潜移默化之中,如春风化雨、成风化俗,带动周围群众主动破除陈规陋习。一方面通过乡贤组织嵌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介于官方和半官方,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乡贤协会、乡贤参事会、乡贤咨询委员会等乡贤组织,由于和群众具有天然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威,能够弥补官方在政策宣传、法律普及、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不足,能够较好地以善治良俗破除封建迷信,以村规民约破解不良风气,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引领乡村道德建设。各种陈规陋习得以破除,农民的社会交往、日常生活获得了自由,切身感受到乡贤给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带来的显著变化。人们对于乡贤文化的认同,实际就是对于以乡贤为代表的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认可,契合了新时代的乡村文化建设主题,体现了人们追求时代精神、渴望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望,能够为乡风文明建设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3 新时代乡贤文化认同的提升路径
提升乡贤文化认同,需要在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党建引领,构建和谐乡村,通过赋予乡贤身份的合法性,促进制度认同;大力建设地域文化,促进情感认同;固化乡贤文化建设成果,促进价值认同。
3.1 赋予乡贤身份的合法性,促进制度认同
所谓“乡贤身份的合法性”是指,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设计、乡贤文化建设的滞后,乡贤往往是在自主、自愿情况下开展工作的。这种“名实不符”的情况,不仅会影响乡贤工作的积极性,还会影响人们对于乡贤的认同。因此,需要以合理的制度设计赋予乡贤身份的法定性,从而固化乡贤文化的制度建设成果,增进乡贤群体与人民群众的制度认同。
一方面,优化乡贤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嵌入”机制。在县、乡政府的支持下,以制度形式将乡贤组织如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乡贤工作室等“嵌入”到基层组织(村委会)的管理体系之中,发挥乡贤自身优势以及协调上下、沟通左右的枢纽作用,在乡村调研、村务决策、村务监督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由于村委会具有自治性质,村委会下设的乡贤议事协调机构也并非科层制的管理方式,而是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相对于传统的治理结构,乡贤组织是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补充,乡贤组织与村两委角色分工应当坚持 “议与决”“谋与断”“监与行”“辅与主”的关系,既要避免“乡贤组织缺位、乡贤群体失势、乡贤建议失声的问题”,更要防范“村两委被架空的风险”[14]。
另一方面,完善乡村精英回流机制,不断扩大乡贤组织力量。当前,乡村精英流失严重,乡村空心化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改善。乡村内生的乡贤群体,以退休的教师、干部、道德模范等为主,即“在场的乡贤”,精力和资源均有限。这就需要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化设计,吸引“不在场的乡贤”。乡村是人才培养的摇篮,离家在外的游子无不心念故土。以乡愁、乡情、乡愿激发爱国、爱家、爱乡的情怀,开展“金凤还巢”“乡贤回归”工程,成立乡贤工作室、工作站,吸引离乡在外的乡村精英反哺家乡,或回乡创业就业,或发挥智力优势,或发挥资源优势,群策群力,能够形成建设乡村的强大合力,在乡村形成以乡贤为荣、甘愿奉献的良好氛围。
3.2 推进乡贤文化建设,促进情感认同
乡贤文化蕴含了农耕文化、家风文化、民间文化等多种形态。作为地域文化的特殊形式,乡贤文化还聚合了名人文化、家族文化、姓氏文化等独特的乡土类型。发挥地域文化特色,丰富乡贤文化内容,能够有效地提升人们对乡贤文化的情感认同。
第一,重视村史、村志的编修,发展乡贤文化。整理古代乡贤事迹与精神,是地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乡村哺育了无数乡贤英才,他们或在他乡功成名就,或在家乡勤恳耕耘。生前,乡贤作为乡村道德的权威具有较高的威望;死后,人们建立乡贤祠,以崇祀乡贤。他们的事迹或散落在地方史志中,或流传于民间传说中。建设乡贤文化,要加强村史、村志的编修工作,整理、搜集、发掘古代先贤人物事迹,延续乡村文脉,弘扬乡贤精神,增强人们对家乡的自豪感、对乡贤文化的情感认同。
第二,鼓励家谱、族谱的编修,弘扬姓氏文化。在乡村,姓氏与辈分是村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血缘关系、宗族关系、情感归属在个体身份上的体现。重视家族、族谱的编修、整理,不是要恢复传统的宗法关系,造成主观的门户对立,而是要以血缘、乡情维系农村逐渐破碎的社会关系,让人们在认祖归宗的同时,建立更加稳固的共同体意识;同时,了解本家族那些已经逝去的德高望重的古代先贤,更能激发现代人崇德向善之心,以及各级政府对传统的认同与弘扬。
第三,弘扬中华家风文化,以家庭美德涵育乡里。乡贤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这种德性鲜明地反映在乡贤的家庭美德中。很多乡贤是家庭教育的模范、孝老爱亲模范,亲身践行了家风文化。中华家风文化来自于农耕文化传统,对增强人们的乡贤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是节俭文化的体现;“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重视农耕、重视教育的家风对乡风文明具有重要意义;“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既昏便息,关锁门户”,传统的家庭教育理念仍然值得提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扬中华民族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引导人们自觉承担家庭责任、树立良好家风,强化家庭成员赡养、扶养老年人的责任意识,促进家庭老少和顺。”[15]因此,弘扬家风文化,传承家庭美德,对于引领乡风文明建设、促进乡贤文化认同具有积极作用。
3.3 固化乡贤文化成果,促进价值认同
乡贤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文化契合了乡村的地域特点,满足了农民的精神需求,适应了新时代乡村文化建设的趋势。立足乡村文化振兴的时代主题,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表彰乡贤人物,宣传乡贤先进事迹,凝练乡贤精神,从而总结与固化乡贤文化建设成果,能够较好地促进人们对于乡贤的积极认知,对乡贤文化价值观的强烈认同。
第一,完善乡贤评选表彰机制,增强乡贤的社会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涌现出了数不清的先进人物,他们是新时代的乡贤,解决了许多乡村久拖未决的难题,给乡村带来了希望的种子。党中央以及各级政府对脱贫攻坚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多次进行了表彰,凝练了脱贫攻坚精神,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获得了广泛影响。榜样的力量是无限的,要完善乡贤评选表彰机制,通过评选“最美乡贤”、建立乡贤榜等活动,让更多乡贤人物为人们所熟知,不断汇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激励更多乡贤的脱颖而出。
第二,宣传乡贤先进事迹,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尊贤”“敬贤”“尚贤”的良好传统。广泛宣传乡贤人物先进事迹,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尚乡贤的良好氛围。一是发挥乡贤文化的德育作用,充实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举办先进事迹巡讲、组织参观访问、乡贤现身授课等形式,让乡贤文化走进学校、走进课堂,培育孩子们正确的价值观。二是整合宣传载体,报道先进事迹。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等传统媒体,利用互联网、手机等自媒体的作用,形成热点效应,塑造敬贤、尚贤的网络环境。三是完善乡贤主题文化建设。通过乡贤文化广场、乡贤文化长廊、乡贤文化馆等文化空间建设,丰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第三,凝练乡贤精神,凝聚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在完善乡贤表彰机制、宣传机制的基础上,固化乡贤文化建设成果,总结本地区乡贤组织的结构特征、乡贤人物的个性特点、乡贤作用的机制与成效等,凝练出乡贤精神的思想渊源、区域特征、时代特点,形成乡贤文化建设的典型案例,带动乡贤文化的示范效应。将传承乡贤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不断增强乡贤精神的感染力、凝聚力,为乡村振兴促进价值共识、凝聚力量、激励人民;将弘扬乡贤精神与传承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结合,不断增强乡贤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激发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