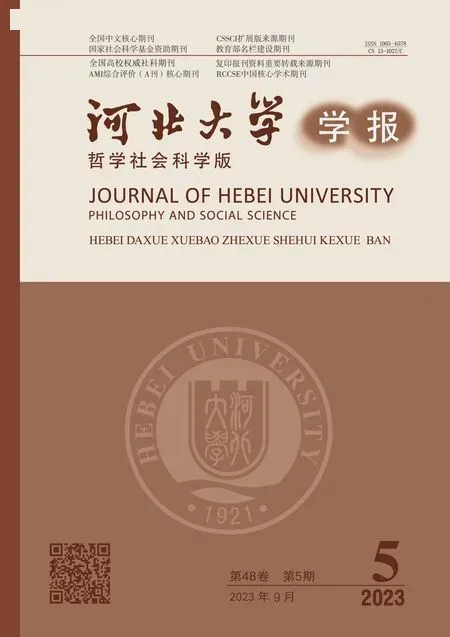宋仁宗朝进奏院案中若干疑点探析
顾宏义
(华东师范大学 古籍研究所,上海 201100)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中,监进奏院苏舜钦(字子美)等官员于进奏院内“祀神,会宾客,为御史所纠,坐除名”[1]卷一一五《苏舜钦传》,第755页。当时宰相杜衍与执政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夕会宾客。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等劾奏,因欲揺动衍。事下开封府劾治,于是舜钦与巽俱坐自盗除名,同时会者皆知名士,因缘得罪逐出四方者十余人。世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2]卷四四二《文苑传四·苏舜钦》,第13079页此即史上著名的“进奏院案”(也称“奏邸案”)。关于进奏院案,学界已有研究成果颇多①如: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第四章中有专节述及“‘进奏院案’与庆历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25页。李强《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第四章《“进奏院狱”:庆历士风的一曲挽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209页。专题论文有:朱瑞熙《宋仁宗朝“奏邸狱”考述》,《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291页,又氏著《朱瑞熙文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72-293页。李强《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学术研究》2007年第7期;《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苏舜钦的教训——对一桩宋史旧案的重新检讨》,《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苏舜钦与北宋“进奏院狱”》,《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1年第4期。顾友泽《“进奏院赛神会”与会人员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5期;《论宋庆历年间“进奏院案”的性质及兴起与扩大化》,《枣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北宋文人政治遭际与诗歌创作的标本——苏舜钦“进奏院案”前后诗歌之比较》,《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北宋“进奏院案”探析》,《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刘小凡《北宋进奏院案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王启玮《被惩罚的“醉歌”——北宋诗学与政治交错中的奏邸狱》,《华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期。,对其案始末经过的考述也颇为明晰、完备,故本文不赘言,仅对相关论著中若干未予充分讨论或尚未涉及之处再加辨析,以厘清其中之疑问。
一、进奏院会宴在何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于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日记载:“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勒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太常博士周延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监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绶监汝州叶县税。”①(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15页。按,以下省称《长编》。又,据王安石《赠礼部尚书安惠周公神道碑》云周起四子延荷、延让、延寿、延隽。则延让为兄,延隽为弟。《王安石全集》卷八九,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543页。按甲子日乃十一月七日。故诸论著或以此日为案发时间,或称“事发于庆历四年十一月”[3],或称此案发生在是年“十月到十一月间”,祀神宴会在十月上旬[4]272-274,或称在是年“秋冬之际”[5]。其实,十一月甲子日乃是进奏院案结案、宋廷宣布贬责涉事官员之日,并不是案发之日,更非进奏院会宴之时。
魏泰《东轩笔录》云:“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馔,至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庆历中,苏舜钦提举进奏院,至秋赛,承例货拆封纸以充。”[6]叶梦得《石林燕语》亦云“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7]。然张师正《倦游杂录》乃云:“苏舜钦监进奏院,因十月余赛神,会馆中同列。”[8]检《宋会要辑稿》云天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京城诸司当祈赛神者,无用十月二十日。时殿前司请以是日祈赛,帝以太祖忌日(原注:此下似有脱文),今从之,因广条制”[9]五七之三四,第2007页。又云“天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京城诸司赛神毋用十月七日,以太宗诞辰故也”[9]五七之三四,第2007页。则知京师百司秋天赛神一般在每年九、十月间举行,各司自选时日,并不一律。
苏舜钦于“得罪”以后尝“贻书”当时“按察河北”的欧阳修“自辨”云:“九月末间,尝与子渐、胜之邸中小饮,之翰、君谟见过,胜之言论之间时有高处,二谏因与之辨析,本皆戏谑,又无过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喧然以谓谤及时政。吁! 可骇也。故台中奏疏,天子辨其诬,不下其削。台中郁然不快,无所泄愤,因本院神会,又意君谟预焉,于是再削,其削亦留中不出。”②(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八《苏子美与欧阳公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按,尹源字子渐,王益柔字胜之,孙甫字之翰,蔡襄字君谟。孙甫、蔡襄时任谏官。由此推知进奏院会宴约在十月上旬举行。
二、参与进奏院会宴之官员数
当日参与进奏院会宴的馆职官员,周煇《清波杂志》称“朝士自翰林学士王洙以降连坐逐去者凡十人”③(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上,大象出版社2012年《全宋笔记(第五编)》,第152页。按,“凡十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波别志》卷一作“凡十八人”,似误衍“八”字。,据《长编》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所载,知此人数乃除去苏舜钦、刘巽二人,自王洙算起,故云“凡十人”。按《长编》又载是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刘元瑜劾奏“大理寺丞、集贤校理陆经前责监汝州酒,转运司差磨勘西京物,杖死争田寡妇李氏,并贷民钱,又数与僚友燕聚,语言多轻肆。监司缪荐其才,权要主张,遂复馆职,请重置于法,勿以赦论”。故诏遣官员“往按其罪,并以经前与进奏院祠神会坐之,责授袁州别驾”[10]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二月乙巳条,第3726页。则知当时与会者不止十二人。因陆经时以监汝州酒,受京西转运司“差磨勘西京物”,而未于京城任职。因此,作为馆职(集贤校理)的陆经当凑巧至京师而参与进奏院会宴,会后即离京城赴西京,故御史攻讦与会诸官员时,未论及不在京城的陆经。至十二月,陆经乃因其他过失遭到按察时,并以“前与进奏院祠神会坐之”之罪名加重处罚。
陈师道《后山谈丛》云当苏舜钦举行进奏院会宴,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欲举其事以动丞相(谓杜衍)”,而刁约“亦与召,知其谋而不以告。诘朝送客城东,于是苏坐自盗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而刁独逸”[11]。此说当属陈师道误信传闻,刁约实在与会被处罚贬官的十二人之内。
有学者认为当时与会者还有梅尧臣、孙甫等人[12]。魏泰《东轩笔录》即称当时与会“坐客皆斥逐,梅尧臣亦被逐者也”[6]。但欧阳修所撰的梅尧臣墓志铭与《宋史·梅尧臣传》皆未提及其尝参与进奏院会宴以及被惩处的经历,且史载梅尧臣乃侍读学士梅询从子,“用询荫为河南主簿”,历德兴县令、知建德县、监永丰仓等,“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2]卷四四三《文苑传五·梅尧臣》,第13091-13092页。迟至皇祐三年九月庚申,国子博士梅尧臣方赐与“同进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10]卷一七一皇祐三年九月庚申条,第4109页。则庆历四年时,梅尧臣亦为“任子官”身份,尚未得进士出身,魏泰所云似出自传闻,当非事实[4]285。
当时与苏舜钦等人交往密切且也为馆职的蔡襄、孙甫二人,据苏舜钦贻欧阳修书云,当日蔡襄“与赴会诸君同出馆,过邸门”,但未参与此会宴[13]。而据《长编》载庆历四年十月己酉,秘书丞、直史馆、同修起居注、知谏院蔡襄“以亲老乞乡郡”,遂授右正言、知福州。“襄与孙甫俱论陈执中不可执政,既不从,于是两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请,时甫使契丹未还也。”①《长编》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己酉条,第3708页。按,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则孙甫未能参与进奏院会宴的原因,实在于其正出使契丹而未在京城。
三、李定被拒与会的原因
魏泰《东轩笔录》载苏舜钦欲因“秋赛”而“举乐,而召馆阁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愿预醵厕会,而舜钦不纳。”[6]王明清《挥麈录》也称“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献公之甥,文亦奇。欲预赛神会,而苏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兴大狱”②(宋)王明清《挥麈前录》卷四,大象出版社2013年,《全宋笔记(第六编)》本,第42页。按,晏殊谥曰元献。。按李定,《宋史》无传,其事迹附见于《李虚己传》,云李虚己“其壻晏殊”;其弟名虚舟,虚舟之子宽、定,定“为司农少卿,为吏颇有能名”③《宋史》卷三〇〇《李虚己传》,第9975页。按,朱瑞熙《宋仁宗朝“奏邸狱”考述》(《朱瑞熙文集》第六册,第275页)云“李定之父是李虚己”,误。。欧阳修所撰晏殊神道碑也称“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己之女”[14],则知李定乃晏殊妻李氏之从兄弟,《挥麈录》称李定为“晏元献公之甥”者误。
王明清称当时有三位李定,“世亦多指而为一,不可不辩”:其一“李定字仲求,洪州人”,即“欲预赛神会”而被拒者;其二“李定字资深,元丰御史中丞”,扬州人;其三之李定乃济南人,“嘉祐、治平以来,以风采闻。尝遍历天下诸路计度转运使,官制未行,老于正卿”[15]。检《宋会要辑稿》载明道二年“八月十三日,赐国子博士李定同进士出身。以定七次献文,召试舍人院中等,命之”。又载“庆历二年正月六日,两浙转运使、兵部员外郎李定直史馆,充益州路转运使”[16]九之八、三三之六,第5437、5882页。洪迈云:“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为太子中允,无出身人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17]卷十六《中舍》即北宋前期转官之制,太子中舍转殿中丞,殿中丞“无出身者转国子监博士”[2]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24页。则知明道二年任国子博士、赐同进士出身,庆历二年自两浙转运使迁益州路转运使之李定,当是济南人李定,而非“欲预赛神会”而被拒的洪州人李定。
王明清《挥麈录》所谓“以其任子距之”,据洪迈《容斋随笔》云“苏子美在进奏院会馆职,有中舍者欲预席,子美曰:‘乐中既无筝琶筚笛,坐上安有国舍虞比。’国谓国子博士,舍谓中舍,虞谓虞部,比谓比部员外、郎中,皆任子官也”①《容斋随笔·三笔》卷十六《中舍》,第601页。按,(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五《仁宗初中馆阁失人末年得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0页)云“自苏子美监察奏邸,旧例鬻故官纸以赛神而宴客,时馆阁诸公毕集,独李定不预”。因李定不是馆职,可见陈鹄称“时馆阁诸公毕集,独李定不预”者不确。。即以李定仅为“任子官”而予以拒绝。又《诗史》亦称“苏子美监进奏院,因赛神,召馆中同舍。是时江南人李中舍因梅圣俞谒子美,且愿预此会,圣俞以为言。子美曰:‘食中不设蒸馒饼夹,坐上安有国舍虞台。’李衔之,遂暴其事于言语。为刘元瑜所弹,子美坐谪”②(宋)阮阅《增修诗话总龟》卷三五《讥诮门上》引《诗史》,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第347页。按,“国舍虞台”之“台”,当为“比”字之误。。宋时社会风气重进士出身者,任馆职者一般为进士及第、出身人,而通过恩荫任子入仕的官员则为世人所轻。此时苏舜钦于进奏院宴请“馆职同舍”,故有“坐上安有国舍虞比”之语。
在进奏院案中遭受贬官处分的十三人(包括陆经),右班殿直、监进奏院刘巽为武官,其余皆为文官:王洙进士登第,时官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刁约天圣八年进士,时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江休复于天圣年间进士及第,时官殿中丞、集贤校理;章岷于天圣五年中进士,时官太常丞、集贤校理;吕溱乃景祐五年进士第一人,时官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陆经时官大理寺丞、集贤校理。又,苏舜钦以父苏耆荫补官,初任县尉,辞官而去,登景祐元年进士第,时官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王益柔以父王曙荫得官殿中丞,经学士院试授集贤校理;宋敏求,真宗朝参知政事宋绶子,“天圣三年乾元节,以父任秘书省正字。宝元二年召试学士院,赐进士第。庆历三年,以光禄寺丞充馆阁校勘”[18]。而周延让、延隽二人,其父为真宗朝枢密副使周起,康定二年五月,赞善大夫周延隽因献其父家集,召试学士院合格,赐同进士出身,延让仕历未详,时延隽官太常博士,延让官殿中丞,则二人似皆以恩荫入仕,且未见有二人此时已授馆职的记载[4]280-285。此外,徐绶于景祐元年中进士第三名,至此已有十年,而仅官将作监丞,且至嘉祐四年“九月三日,学士院试屯田员外郎徐绶,赋三下、诗四上,诏充集贤校理”[16]三一之三五,第5859页,颇见特别,但似可推知庆历四年时徐绶尚未授与馆职。如此,则苏舜钦以“任子官”为理由坚拒晏殊姻亲、时称“文亦奇”的李定参与进奏院会宴,并出言讥刺,显然其中当别有缘故。
晏殊于庆历中拜相,“殊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权幸皆不便。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谏官奏留,不许”[2]卷三一一《晏殊传》,第10197页。范仲淹等推行新政,得到宰相晏殊支持。当时知谏院欧阳修与范仲淹等相“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于是遭到欧阳修等官员上言攻讦的夏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辨析,反而激起反弹,连仁宗也质疑道:“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10]卷一四八庆历四年四月戊戌条,第3580-3582页故晏殊虽“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论事烦数,或面折之。及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奏留修,不许”[10]卷一五二庆历四年九月庚午条,第3699页。由此,谏官孙甫、蔡襄遂翻出章献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晏殊撰作仁宗生母李宸妃(仁宗亲政后追册为章懿皇后)墓志之事,“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晏殊“坐是”罢相,降工部尚书、知颍州。“然殊以章献太后方临朝,故志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辅臣例宣借者,时以谓非殊罪”[2]卷三一一《晏殊传》,第10197页。蔡襄、孙甫因此遭受很大舆论压力,加上二人“俱论陈执中不可执政,既不从,于是两人俱求出”[10]卷一五二庆历四年十月己酉条,第3708页。与欧阳修、蔡襄、孙甫等关系密切、志同道合的苏舜钦,至此严词拒绝晏殊之姻亲李定参与进奏院会宴,也就颇可理解了。
检梅尧臣有诗答谢李定惠赠“建溪洪井茶”,有“乃思平生游,但恨江路赊,安得一见之,煮泉相与夸”之语[19],其交游颇密切,则知时人所称李定欲因梅尧臣绍介“预醵厕会”,当属实情。于是被羞怒的李定“遂腾谤于都下”,遂为欲“有所希合”的御史获知,“致兴大狱”。但因李定未能与会,当无法掌握此次聚会的详情细节,故李焘辨析云“舜钦等坐责,乃御史劾奏,又当时但借此以倾杜衍尔,李定无与”[10]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注,第3717页,即御史奏兴狱事当与李定无关。故陈鹄声称李定“遂捃摭其事,言于中丞王拱辰、御史刘元瑜,迎合时宰之意,兴奏邸之狱”[20],似不符合事实[4]276。
在李定“腾谤于都下”之后,众御史能获得会宴之详情细节以兴起狱事,可能与集贤校理何中立有关。史载进奏院“赛神会,预者皆一时知名士,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辞不往,后舜钦等得罪,中立有力焉”[2]卷三〇二《何中立传》,第10029-10030页。可证。
四、大兴进奏院狱事之诸官员
当时“根究”进奏院案的主要为御史台官员,而积极“助之”者为翰林学士宋祁、知制诰张方平,然这些与会宴者皆“一时英俊”,且多与宰执关系密切,故仅是诸御史、个别两制官,若无更高层的支持,显然难以兴起如此“大狱”。据《长编》卷一五三记载:苏舜钦聚众馆职会宴,御史中丞王拱辰“廉得之,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因欲动摇衍。事下开封府治”,而“拱辰既劾奏,宋祁、张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于是苏舜钦等与会者皆遭贬责[10]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第3715-3716页。
但御史鱼周询是否参与进奏院案,李焘颇有疑问:“据《正史·苏舜钦传》,御史不载刘元瑜姓名,《元瑜传》亦不云尝奏舜钦,独魏泰《杂记》载‘一网打尽’乃元瑜语,今并出其姓名于鱼周询下。然周询七月为知杂,九月为吏外,十月为省副,不属御史台矣。当考。”[10]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注,第3716页今有学者认为李焘之说还不够充分,乃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四、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指出鱼周询早在是年五月已以三司副使(省副)身份受命赴陕西相度修筑水洛、结公二城利害;次年正月一日,改任河北路都转运使,此段时间内鱼周询根本不在京城,故不会参与此次弹劾活动[4]276。但此说颇存疑问。《长编》载是年三月“甲戌,命盐铁副使户部员外郎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同都转运使程戡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10]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甲戌条,第3556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二也载庆历“四年三月十一日,命三司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相度钱宝、解盐,定夺修水洛、结公二城利害”[21]。则鱼周询出使陕西在三月中。又《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四云是年“五月九日,内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检刘沪降一官,著作郎董士廉移别路差遣”,因先前“诏遣三司副使鱼周询计度可否”,至此鱼周询自陕西“回,言水洛之利与(郑)戬议同,故有是命”①《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四之四五、四六,第4791页。按,刘沪降官,《长编》卷一五一系于庆历四年七月乙酉日。。则苏舜钦举行进奏院会宴之前,鱼周询早已回至京城。
据苏舜钦与欧阳修书札中言,以御史中丞王拱辰为首的众御史,尝先后三次上奏章弹劾苏舜钦等人:第一次乃在九、十月之际,御史赵祐因蔡襄、孙甫“二谏尝论其不才”,故上章弹劾蔡襄、孙甫、王益柔诸人于“邸中小饮”时“谤及时政”。但仁宗“辨其诬,不下其削”,即未予理睬。于是诸御史“郁然不快,无所泄愤”,遂借进奏院会宴之由头,并误以为蔡襄也参与聚会,第二次上奏弹劾。这两次弹劾的主要矛头当指向蔡襄。但还是遭到天子无视,“其削亦留中不出”。至此“诸台益忿重,以秽渎之语上闻,列章墙进,取必于君”[13]。其所谓“秽渎之语”,当指王益柔所作之《傲歌》。故史载王拱辰“讽其属鱼周询、刘元瑜等劾奏”,乃指其第二次上劾奏,时在十月上旬,鱼周询可能仍兼御史台职事,此后其专任“省副,不属御史台”,故诸书记载御史第三次上章劾奏,皆未有云及鱼周询者,原因当在此。
第一次上章劾奏的御史赵祐,《宋史》无传,据晁补之《殿中侍御史赵君墓志铭》云其字寿臣,磁州滏阳县人。中天圣五年进士第,累迁太常博士,“时贾公昌朝为御史中丞,言君方正,擢监察御史,弹劾不挠,仁宗眷待之”。后贾昌朝参知政事,“君引嫌请外官,遂以监察御史知棣州事,仍不废言事。俄迁殿中侍御史,兴利除害,州以治”。参知政事王尧臣“引为三司户部判官”。后“遣视汴口”,“得疾汴口,既还,卒,庆历五年四月六日也”[22]1096-1098。按《长编》载庆历四年九月庚午,“户部判官、殿中侍御史赵祐言:‘近乞上殿奏事得旨,寻牒閤门,须索申状,仍要出身文状两本,比至引对,已经七日。切缘台谏之官,俱职言事,台官则具奏候旨,谏官则直牒閤门,事体有殊,欲望许依谏官例,直牒閤门。’诏免供家状”[10]卷一五二庆历四年九月庚午条,第3700页。可知赵祐虽已任户部判官,但仍在御史台供职,故可以御史身份上奏弹劾苏舜钦等。晁补之《赵君墓志铭》又言“武功苏子美以诗豪,少所许可,与唱和盈笥”[22]1098,则其与苏舜钦关系颇为密切,但因“怒(蔡襄、孙甫)二谏尝论其不才”,赵祐遂上奏章弹劾,成为大兴进奏院案之先声。
对于翰林学士宋祁、知制诰张方平“同劾奏王益柔”,“力言益柔作《傲歌》,罪当诛”,李焘曾考证道:“宋祁、张方平,此据《韩琦家传》。李清臣《行状》但云近臣,盖讳之也。”[10]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并注,第3716页
诸书记载大多以为当时“章得象无所可否,贾昌朝阴主(王)拱辰等议”,苏舜钦也说“二相胆薄畏事,必不敢开口以辩”[13]。二相乃指章得象、杜衍二人。然宋人又多称“中丞王拱辰、御史刘元瑜,迎合时宰之意,兴奏邸之狱”[20]。或称刘元瑜兴大狱后,“刘见宰相曰:‘聊为相公一网打尽。’”①《东轩笔录》卷四,第41页。按,《倦游杂录》卷一《一网打尽》(第202页)云“刘谓时相贾昌朝曰:‘与相公一网打尽。’”其校勘记曰:“贾昌朝,原缺,据《记繤渊海》卷四八、卷五〇补。”然此时贾昌朝乃枢密使,非宰相。此处补“贾昌朝”三字似不妥。宋人皆以为章得象当时“无所可否”,在天子前不发一言,暗中支持王拱辰等的乃枢密使贾昌朝,故刘元瑜“一网打尽”实对贾昌朝所言,只是称贾昌朝“时相”为不确。不过,《闻见近录》又云:“庆历中,韩、范、富执政,日务兴作。时章郇公(章得象)为相,张文定(张方平)因往见之,语以‘近日诸公颇务兴作,如何?’郇公不答。凡数问之,曰:‘得象每见小儿跳踯作戏,禁止不得,到触著墙自退耳。方其举步时,势难遏也。’未几,三公悉罢。”[23]
史载庆历三年二月戊子,吕夷简罢相,枢密使章得象拜昭文相,贾昌朝参知政事。四月甲辰,韩琦、范仲淹拜枢密副使;乙巳,枢密副使杜衍拜枢密使。八月丁未,范仲淹拜参知政事,富弼拜枢密副使[24]。在仁宗支持下,范仲淹、富弼主持“庆历新政”,但新政推行遭到很大的阻力,“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范、富“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欲出避谗谤也”。范仲淹乃于六月壬子“宣抚陕西、河东”,富弼于八月甲午“宣抚河北”。至九月中,晏殊罢相,而拜杜衍为宰相,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为参知政事②《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五,第259-260页;《宋史》卷十一《仁宗纪三》,第218页。。未久即发生了进奏院案。据载范仲淹、富弼虽已离京出使,然“谗者益甚,两人在朝所施为,亦稍沮止,独杜衍左右之,上颇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罢政事,上欲听其请,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虚名,今一请遽罢,恐天下谓陛下轻绌贤臣。不若且赐诏不允,若仲淹即有谢表,则是挟诈要君,乃可罢也。’上从之。仲淹果奏表谢,上愈信得象言”,故于庆历五年正月乙酉,范仲淹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富弼罢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③《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条,第3740页。按,《长编》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己巳条(第3718页)载:“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诏不许。”。次日“丙戌,杜衍罢,以贾昌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2]卷十一《仁宗纪三》,第219页。新政推行就此终结。
因此,可知章得象的“无所可否”只是其表面,暗中对御史兴起进奏院案实取默许态度,以待范仲淹等“触著墙自退耳”。故史载刘元瑜“及仲淹迹危”时,“即希章得象、陈执中意,起奏邸狱,劾窜陆经”[10]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辛卯条,第3744页。
因陈执中于庆历四年召拜参知政事时,“谏官孙甫、蔡襄言执中刚愎不才,不可任以政。仁宗不听,遣中使赍敕告即青州授之。……明日,甫、襄又以为言,仁宗曰:‘朕已召之矣。’”于是陈执中遂与杜衍、范仲淹等为敌,“时章得象、杜衍为相,贾昌朝与执中参知政事,每议事,执中多与之异”[25]。《长编》载“自苏舜钦等斥逐,衍迹危矣,陈执中在中书,又数与衍异议”[10]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条,第3741页。是知陈执中“每议事”而“多与之异”者,不包括章得象。至刘元瑜奏劾陆经时,宋人明确记载刘元瑜乃“希章得象、陈执中意”而行事。
而“阴主拱辰等议”的贾昌朝,在此之前,并未有与杜衍、范仲淹交恶的记载,但此时其官拜枢密使,若攻罢宰相杜衍,则按宋朝惯例,其职一般当由枢密使升补,此可能即是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兴起大狱的隐衷。
此外,苏舜钦与欧阳修书中言及此狱事下开封府审理,“始府中敕断,追两官,罚铜二十斤;后六日,府中复遣吏来取出身文字,殊不晓”,并言“审刑者自为重轻,不由二府,苟务快意,坏乱典刑。(原注:丁度怒京兆不逐之翰也。)”即开封府初审“敕断,追两官,罚铜二十斤”,但六日之后情况遽变,即经复审,判苏舜钦、刘巽“以监主自盗定罪,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与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故“府中复遣吏来取出身文字”①《梁溪漫志》卷八《苏子美与欧阳公书》,第88页。按,孙甫字之翰。。因是时知审刑院为翰林学士承旨丁度,故有学者据此认定对苏舜钦等人的定罪量刑乃由丁度“一手作出”,并且“后来还取得了宋仁宗的同意”[4]291。对于丁度借进奏院案以撼动宰相杜衍的原因,陈师道有云:“杜正献公、丁文简公俱为河东宣抚,河阳节度判官任逊,恭惠公之子,上书言事,历诋执政,至恭惠曰:‘至今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进奏院报至,正献戏文简曰:‘贤郎亦要牢笼。’文简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苏子美进奏院祠神事,正献避嫌不与,文简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从坐者数十人,皆名士大夫也,正献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一时,故不可不慎也。”②《后山谈丛》卷四,第54页。按,杜衍谥正献,丁度谥文简,任布谥恭惠。此时丁度为翰林学士承旨,尚未执政,陈师道所述小误。又《长编》也载“帝尝问丁度用人以资与才孰先,度对曰:‘承平宜用资,边事未平宜用才。’(孙)甫又劾奏度因对求大用,请属吏。上谕辅臣曰:‘度在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度知甫所奏误,力求与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寝其奏。度深衔衍,且指甫为衍门人。及甫自契丹还,亟命出守”,自右正言、秘阁校理为右司谏、知邓州[10]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甲戌条,第3735-3736页。似是丁度因与杜衍有隙而有为难杜衍行政的举动,故孙甫上言攻讦丁度,然其语不实,引来丁度反击。此也是苏舜钦云“丁度怒京兆不逐之翰也”之语的由来。只是不详丁度为何要迁怒开封府“不逐”孙甫的原因,难道丁度欲让审案的开封府官将孙甫窜名于参与进奏院会宴官员名录中一起遭贬责? 史文有缺,难究其详。不过随着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先后罢官出朝,遭到孙甫攻讦“因对求大用”的丁度于是年四月终得升拜枢密副使[2]卷二一一《宰辅表二》,第5469页。
五、进奏院狱与庆历新政之关系
由参知政事范仲淹举荐的宰相杜衍女婿苏舜钦因进奏院案而遭受重责,自然在政坛上引起轩然大波,宋人对此多有记载与议论,大都以为此案实与当时吕(夷简)范(仲淹)党争、庆历新政之行废有着密切关联。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指出:庆历三年中,因时事艰难,“天子奋然用三四大臣,欲尽革众弊以纾民。于是时,范文正公与今富丞相多所设施,而小人不便,顾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动,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荐,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监进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纸钱会客为自盗,除名。君名重天下,所会客皆一时贤俊,悉坐贬逐。然后中君者喜曰:‘吾一举网尽之矣。’其后三四大臣继罢去,天下事卒不复施为”[26]。陈师道也称“王宣徽拱辰丞御史,吕申公之党也,欲举其事以动丞相”[11]。然今人颇有质疑此一说法者。
有学者据宋神宗时直讲陆佃回答天子之问云:“昔苏舜钦监进奏院,以卖故纸钱置酒召客,坐自盗赃除名。当时言者固以为真犯赃矣,今孰不称其屈。”[27]认为“大概在案发当时”,人们乃视作“一件经济案子”,“使同情苏舜钦的人们很难为他进行有力辩解”,只有韩琦仗义执言,说此只是“醉饱之过”。而后人视此为冤案,乃是因为欧阳修在撰写苏舜钦墓志铭时,将进奏院案与庆历新政、朋党之争相联结,于是“在‘君子’‘小人’的阵营划分中”,“苏舜钦本身仕履中的一个污点”被“完全洗清了”,而且如此之“政治解读,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看法”[28]。或以为当时吕夷简、范仲淹两人已言和,故“吕、范作为两个政治集团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而大兴狱事之诸人动机也各异。如王拱辰虽属“吕申公(吕夷简)之党”,却曾经与范仲淹一同举荐过苏舜钦,其兴狱目的是“出于对范仲淹等实施的庆历新政的不满”;张方平早年曾受范仲淹“知奖”,其思想与庆历新政也有相当“共通性”,故其攻击王益柔并非“出于吕、范之争”,也非反对新政,而是“对于范仲淹等人公开以党标举的不满”;宋祁攻击王益柔等人,“也是出于张方平同样的想法,即反对范仲淹等的结党自坚行为”,此外还存在因其兄宋庠与范仲淹的“交恶”,而借攻击王益柔“达到打击的范仲淹的目的”之可能[29]。或以为“和革新派结成‘君子党’不同,‘吕党’或说保守派并不足以构成政治朋党,他们中多数人只是在共同排击革新派这一点上步调一致,并且没有材料直接证明王拱辰和吕夷简过从甚密、党同伐异”,因此苏舜钦于自述中“通过梳理人际关系强调奏邸狱另有缘由”,强调“台官与宰执杜衍、范仲淹及谏官蔡襄、孙甫都有宿怨,故借奏邸之会牵连诸人以泄愤”,“知审刑院丁度也因怒杜衍不逐孙甫,不惜深文周纳,酿成冤狱”;而欧阳修在苏舜钦墓志中着意“把奏邸狱包纳于庆历新政成败的进程之中,弱化它的案件属性而凸显其作为党争‘附属品’的一面”,故“宋人对于奏邸狱的认知决定了他们历史书写的面貌。或不妨说,奏邸狱正是庆历士大夫的政治观念主导后世历史叙事的典型案例”[30]。但上述观点颇可再加讨论。
其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确实以“君子党”相号召,欧阳修还特意撰作《朋党论》,而相比较,“吕党”中人则政治上更为老到或“狡猾”,故矢口否认其有结党行为,并由此攻讦杜衍、范仲淹、欧阳修等为朋党。如史载当时右正言钱明逸“希(章)得象等意”攻讦富弼“更张纲纪,纷扰国经,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与(范)仲淹同”;又攻击范仲淹“去年受命宣抚河东、陕西,闻有诏戒励朋党,心惧彰露,称疾乞医”云云[10]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乙酉条,第3740页。翰林学士承旨丁度于所撰杜衍罢相制文中,更指斥杜衍“自居鼎辅,靡协岩瞻,颇彰朋比之风,难处咨谋之地”[10]卷一五四庆历五年正月丙戌条,第3741页,下语甚重。但吕党是否也结为朋党,其判定之标准不是看其如何辩说,而当根据其究竟如何做,以及当时其他人如何看。宋人大多认为吕氏有党,并直接指出王拱辰、张方平等人为“吕党”。如陈师道直接称王拱辰乃“吕申公之党也”。王称《东都事略》云“方平附贾昌朝以谮吴育,拱辰党吕夷简以撼富弼,固正士之所不与也”[1]。而朱熹也云:“吕公所引如张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终是不乐范公,张安道过失更多。”张方平是“助吕公以攻范”者[31]。因此,宋人指称王拱辰、张方平为吕党,以兴进奏院案事撼动杜衍、范仲淹,当不至于仅仅是因为其说出自苏舜钦之自述、欧阳修所撰的苏舜钦墓志铭中而普遍信从。
其二,吕、范是否解仇。两宋之际张邦基《墨庄漫录》尝记载云欧阳修“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吕公(吕夷简)擢用希文(范仲淹),盛称二人之贤,能释私憾而共力于国家。希文子纯仁大以为不然,刻石时,辄削去此一节,云:‘我父至死,未尝解仇。’”[32]于是范、吕解仇与否,遂成一重公案,至南宋时,朱熹认为已解仇,周必大坚持未曾解仇,后世更是频起纷争,迄今不息[33]。其实欧阳修、范纯仁二人所言皆属事实,但又都未将其事始末全部说出。史载康定元年六月己卯,宋廷任命起居舍人、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与吕夷简有隙,及议加职,夷简请超迁之。上悦,以夷简为长者。既而仲淹入谢,帝谕仲淹使释前憾,仲淹顿首曰:‘臣向所论盖国事,于夷简何憾也!’”[10]卷一二七康定元年六月己卯条,第3013-3014页司马光《涑水记闻》也载云:“范文正公于景祐三年言吕相之短,坐落职知饶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寻改陕西都转运使。会吕公自大名复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耶?’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上以许公为长者,天下皆以许公为不念旧恶。文正面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耶?’”[34]然叶梦得却称:“然余观文正奏议,每诉有言,多为中沮不得行。未几,例改授观察使。韩魏公等皆受,而公独辞甚力,至欲自械系以听命,盖疑以俸厚啖之。其后卒以擅答元昊书罢帅夺官,则申公不为无意也。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两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损益之,解后世之疑,岂碑作于仁宗之末,犹有讳而不可尽言者,是以难之耶?”①(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大象出版社2006年《全宋笔记(第二编)》本,第260-261页。按,文正为范仲淹之谥,韩琦封魏国公,吕夷简封申国公,宰相指范纯仁。因仁宗亲自出面劝和,吕夷简、范仲淹二人当然得努力“释憾”以赞天子之意,然据叶梦得“申公不为无意”之语,可见欧阳修所言者为范、吕解仇之“表”,而范纯仁所坚持者乃其“里”,即范、吕党争之暗流依然涌动。可能因其时尚在仁宗朝,欧阳修“犹有讳而不可尽言者”而不得不如此书写。
其三,苏舜钦于进奏院案被贬黜的原因是因为“监主自盗”,故仅属“经济案子”? 对此苏舜钦甚为不服,因为进奏院每年春秋两次祠神会是合法的,京师百司皆如此,“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馔,至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6]。其所用经费,一为售卖本司剩余物资所得钱款,二为本司胥吏凑份子钱。苏舜钦为免“胥吏辈率醵过多,遂与同官各出俸钱外,更于其钱(即售卖故纸钱)中支与相兼,皆是祠祭燕会上下饮食共费之”,且“卖故纸钱,旧已奏闻,本院自来支使,判署文记前后甚明,况都下他局亦然,(原注:不系诸处账管。)比之外郡杂收钱,岂有异也? (原注:外郡于官地种物收利之类甚多,下至粪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筵会。)”但苏舜钦于本院祠神会之余,又顺便宴会馆阁同僚。即使如此,据宋朝法律“私贷官物,有文记准盗论,不至除名,判署者五匹,杖九十,其法甚轻”,但判审刑院丁度却“自为轻重”,“深文以逞志”,以法条中“无文记以盗论者”定罪,即“以监主自盗定罪,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与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13],遂被除名为民[4]289-291。如此辩说,是否属于苏舜钦为解脱自己罪过的诡辩? 对此,且看当时其他人的说法如何。
如文彦博于皇祐元年上进《答御札手诏》中声言:“圣诏曰:‘德政阙修,刑赏差滥。’臣等近奏,以为刑不为贵近所屈,赏不为侥幸所求,则无滥矣。臣等请略举一端。如往年苏舜钦、刘巽以进奏院赛神辄用官钱,即皆坐除名。去年曾奭、宋永宗赛神,亦用官钱,其罚当与舜钦辈均,而曾奭等止停见任。”②(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一六《答御札手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683页。按,(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四〇作文彦博等《上仁宗答诏论星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5页。又蔡襄于《乞叙用吕溱状》中曾言:“臣窃见顷年苏舜钦监进奏院日卖官故纸,为(令之人)[伶人之]费,坐监主自盗,除名为民,遂卒贬所。事出仇人,情轻法重,至今天下冤之。”①(宋)蔡襄《端明集》卷二五《乞叙用吕溱状》,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540页。按,(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三四作知制诰刘敞《乞叙用吕溱状奏》,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36册,第669页。则知此奏状为蔡襄、刘敞等同上。因蔡襄奏状中有“臣伏见南京分司吕溱降官责废已来”云云,据《长编》卷一九〇(第4594页)记载,吕溱分司南京在嘉祐四年九月丙辰条。文彦博、蔡襄等所上奏状皆在仁宗时,仁宗并未因此作色动怒,反而在此前后,已明令遭除名勒停严惩的苏舜钦、刘巽二人皆得复官。嘉祐元年,因枢密副使韩琦奏请,此前已死的湖州长史苏舜钦追复原官大理评事、集贤校理[10]卷一八四嘉祐元年十月戊辰条,第4450页。而武臣刘巽,因未见传记传世,事迹未详。然韩维有诗《送刘巽殿直官蜀》,此仕宦蜀中的殿直刘巽当即与苏舜钦同遭除名者,诗云:“车马萧条西出门,怜君宦薄意能闲。并游多得贤豪士,久困独无憔悴颜。白酒园林休洛社,(自注:洛碧之里。)黄花风露见岷山。男儿荣滞古来有,收取功名晩节间。”[35]据诗句所云,可见其也已获复官,时间也约在嘉祐初。可证苏舜钦进奏院案纯属“经济案子”之说不能成立。欧阳修《苏长史舜钦墓志铭》中称“君初得罪时,以奏用钱为盗,无敢辩其冤者。自君卒后,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复召用,皆显列于朝。而至今无复为君言者,且其欲求伸于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详,而使后世知其有以也”[36]云云,也是因为当时天子仍为仁宗,而其言不得不有所隐晦。至于陆佃回答宋神宗时声称苏舜钦“坐自盗赃除名,当时言者固以为真犯赃矣,今孰不称其屈”,当属臣下不诿过先帝的机巧语。
其四,既然苏舜钦进奏院案“事出仇人,情轻法重”,又为何当时众人未为其辩解? 苏舜钦自言杜衍、章得象“二相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13]88。章得象“不肯开言”自可不论,而史称杜衍“为人清审而谨守规矩”[10]卷一五五庆历五年三月“是月”条,第3764页,故不肯为陷入案中的女婿发声辩雪。但杜衍却坚决反对加重罪于王益柔:“王益柔作《傲歌》,语涉指斥,欲下御史按罪。衍谓:‘罗织狱今起都下矣。’执不可。”[37]卷五《杜衍传》,第189页而与苏舜钦声气相通的诸少壮官员,或身罹此狱,或任职京外,不便发言相救。在京唯有枢密副使韩琦、知制诰赵槩,在外唯有直龙图阁、知潞州尹洙发声解救。当“狱事起”,韩琦“言于上曰:‘昨闻宦者操文符捕馆职甚急,众听纷骇。舜钦等一醉饱之过,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 陛下圣德素仁厚,独自为是何也?’上悔见于色”。又解救王益柔道:“益柔少年狂语,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国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为《傲歌》可见也。”于是“上悟,稍宽之”[10]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第3716页。赵槩当“苏舜钦为进奏院,以群饮得罪”,遂进言云:“与会者皆一时名人,若举而弃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38]尹洙更是直言:“近闻诏狱所治,类多善士,因醉饱之失,发暧昧之罪,臣窃以为过矣。”[39]但未为仁宗采纳。其余百官面对“诏狱”,因“上有怒意,皆不敢承当”[13],并非是因为“经济案子”,使得同情苏舜钦的官员也难以“进行有力辩解”。
因此,大兴进奏院案的诸官员虽然其动机可能各异,但其主要目标则相同,即借攻击苏舜钦而牵连杜衍、范仲淹,然后以“朋党”之罪名罢去杜、范等宰执官职,使庆历新政难以为继。故宋人普遍认为进奏院案实为朋党之争激化的产物,与庆历新政之废罢密切相关。如曾巩云“(杜)衍在相位,以直道自任。言者因舜钦连及衍,故衍遂罢政事”[37]卷六《苏舜钦传》,第208页。秦观云“臣闻庆历中仁祖锐于求治,始用韩琦、富弼、范仲淹以为执政从官,又擢尹洙、欧阳修、余靖、蔡襄之徒列于台阁,小人不胜其愤,遂以朋党之议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罢去”[40]。陈师道云“于是苏坐自盗除名,客皆逐,丞相亦去”[11]80。费衮云“苏子美奏邸之狱,当时小人借此以倾杜祁公、范文正,同时贬逐者皆名士,奸人至有‘一网打尽’之语”[13]。宋人如此认识,并非全出于苏舜钦、欧阳修的“将进奏院案与庆历新政、朋党之争相联结”之“建构”。其实,在十一月七日涉进奏院案的诸官员被贬后数日,仁宗于十二日颁下诏令云:“朕闻至治之世,元凯共朝,不为朋党,君明臣哲,垂荣无极,何德之盛也。朕昃食厉志,庶几古治,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或阴招贿赂,阳托荐贤。……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10]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己巳条,第3718页即明确点明了进奏院案的兴起与天子防范朋党之举措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