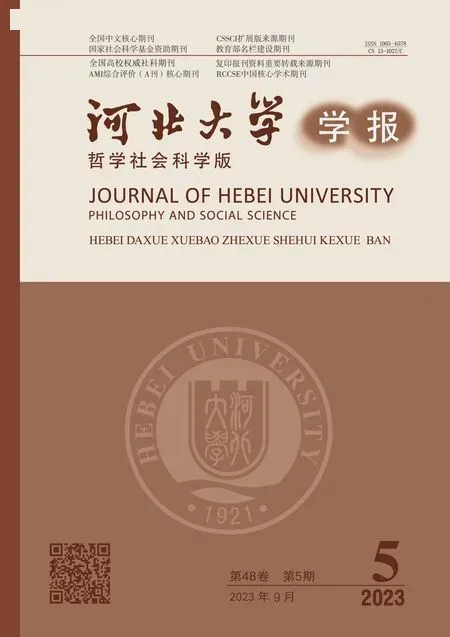孙犁抗战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
刘起林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一、风格何以“从他的灵魂里醒来”?
孙犁抗战题材小说历经当代文学70余年的历史演变仍然广受赞赏和推崇,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经典性究竟从何而来? 这是一个孙犁创作和革命文学研究中都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长期以来,文学研究界以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归纳孙犁小说的出类拔萃之处,茅盾所言“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1]成为定评。“小资产阶级情趣”[2]“革命队伍中的‘多余人’”[3]等思想辨析和“诗的小说”“美的颂歌”等艺术评点,则多方面构成了对孙犁小说风格内涵的具体解读与阐释。但前者在理论化的同时存在套用西方思想话语的痕迹,后者则于品味的细致、贴切中显露出审美鉴赏的感性色彩。总的看来,无论是政治与艺术关系维度的辨析还是艺术技巧、叙事策略层面的细读,均未正面地、深层次地揭示孙犁抗战小说艺术魅力历久弥鲜的缘由之所在。
孙犁抗战小说的基本特征是,表现“民族的觉醒和奋起”[4]“执干戈以卫社稷”[5]这种重大主题,却以“‘儿女情、家务事、悲欢离合’作为题材”[6];理性层面强调纪实、纪事,甚至将作品系列命名为“白洋淀纪事”“五柳庄纪事”,实际上却以抒情性和诗意的营造见长。所以,对于孙犁抗战小说大主题与小题材之间关系的形成基础,对其审美境界中抒情性、诗意美和浪漫色彩的魅力构件,对孙犁认定的“真善美的极致”[7]241应从怎样的历史、文化和文学脉络中去理解,都存在可以更深入、更贴切的探讨的空间。近年来,孙犁小说与民族传统的关系问题逐渐引起人们重视。从阐述孙犁小说“风趣之美”[8]的艺术分寸感背景,到揭示孙犁“浪漫多情的心性”、情节“潜文本”、人物“狐女”气与《聊斋志异》的“不解之缘”[9],再到分析孙犁“在战争与运动中”对“人伦亲情”状况的关注[10],这种种视野与思路内在地预示着一种新的研究路向和学术可能性。
事实上,孙犁虽然早在学生时代就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理论与文艺的知识结构相当宽广,但“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7]236,应该坚持“从生活走向表现生活的文学形式”[11]。具体地说,孙犁认为文艺的根基“就是人民的现实生活,就是民族性格,就是民族传统”[12],“只有在作家自觉地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视他的民族传统的时候,风格才开始在他的灵魂里醒来”[13]。正是以这种理论认识为基础,孙犁的抗战小说创作以“真实记录”我们民族的“伟大时代、神圣战争”[14]为己任,“自觉地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视他的民族传统”,以至在当时延安“大家长期的学外国……所形成的那种欧洲的、俄罗斯式的氛围中”,《荷花淀》的出现“就像是从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大家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15]。换言之,实际上是重视“现实生活”“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高度理性自觉及其成功创作实践,奠定了孙犁小说个人风格和艺术经典性的基础。
孙犁曾谈到,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既包括“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和“艺术师承爱好”等“作家的特征”,更以“思想主潮”“生活样式”“观念形态”等“时代的特征”[16]为基础,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17],所以,文学创作应该同时成为“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4]。事实也确实如此。孙犁抗战小说写的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18]57,既有《村落战》《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采蒲台》等作品的敌后抗战特征认知,也有《看护》《走出以后》《黄敏儿》等各类时代人物的速写,但他的审美重心和最为成功之处是表现与抒发一种抗日战士的思乡、怀人之情。身处延安却以遥远的冀中平原为想象空间创作《荷花淀》,孙犁就是因为“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却又“还难预料哪年哪月,才能重返故乡”[18]57,从而“诗缘情”“情动于衷而言于外”的。孙犁将这种情思拓展到普遍性、典型化的层面,认为“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18]57-58,从而获得了艺术的自信。直到1992年,他仍然表示,“《荷花淀》等篇,是我在延安时的思乡之情,思亲之情的流露,感情色彩多于现实色彩”[1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创作《山地回忆》和《吴召儿》等作品,孙犁也以岁月怀想的笔调开头。《山地回忆》是由“十年不见面”的“老交情”,想起了“山地蓝”,“想起很多事情”;《吴召儿》是因为“这二年生活好些,却常常想起那几年的艰苦”,“留在记忆里的生活,今天就是财宝”,进而展开了一段“亲身经历”“真人真事”[20]。所以,“战士思乡”“异地怀人”不仅是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主线,也是他表现民众“执干戈以卫社稷”却聚焦“儿女情、家务事、悲欢离合”的缘由之所在。
从这样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实践特征出发追溯其“民族性格”“民族传统”的具体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孙犁抗战小说积淀了深厚的中国文学征戍抒情传统,以“潜结构”形态深切地体现了其中以农业文明家庭结构为基础的“征夫-思妇”创作母题。
二、征戍抒情传统与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文化根脉
中华文明几千年坷坎、动荡而生生不息,传统中国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21],中国古典文学也以雅文化领域的诗词创作为主流,形成了内蕴深广的“兵戎”“征戍”抒情传统,并建构起多种题材与主题相交融的文学母题。从汉乐府“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战争灾难书写,到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天数山”“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的江山残缺遗恨;从杨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贺“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的建功立业豪情,到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的征戍寒苦慨叹,这种种母题的创作均源远流长、名篇绝唱层出不穷。在成就辉煌的唐代文学史上,还形成了以高适和岑参为代表、与“田园诗派”相媲美的“边塞诗派”。
但中国文学史上更普遍而日常、更贴近平民百姓生活与情感样式的母题,当属“征夫-思妇”格局的征戍抒情。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这类创作的高峰、典范之作。思妇怀人诗中,《卷耳》表现思妇“嗟我怀人”而“采采卷耳,不盈顷筐”的情态,《伯兮》书写“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而思妇“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挚爱;征人怀乡诗中,《陟岵》的征夫“陟彼岵兮”瞻望父、母、兄而追忆全家殷殷叮嘱的凄楚情感,《击鼓》的征夫渴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的心理遗憾;征夫归乡诗中,《东山》“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而怀想“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妻子“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而面对家乡“行道迟迟,载渴载饥”。在这些“互文性”特征鲜明的作品中,虽然也有种种对于山河地理、征途起居、战争胜负的描述,审美重心却落在对“思乡-怀人”情感的抒发上,从而奠定了“征夫-思妇”文学母题的雄厚基础。随后历朝历代的征戍抒情,从“捣衣诗”意象中“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的牵挂与期盼,到“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的小女儿情态,再到“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的凄苦无望,直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生死哀叹,更大大地丰富、拓展与深化了“征夫-思妇”母题的审美路径和价值蕴涵。
中国文学征戍抒情传统中的“征夫-思妇”母题之所以底蕴深厚、韵味绵长,是因为在传统中国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极为稳定和强大”,虽然“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却很少变动”,已经“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22]284,聚族而居、夫妻子女、田园生活、安土重迁则是其基本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文明史背景下,从认同“战争经常是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因素”,到“哀伤、感叹和反对战争带来的痛苦、牺牲”[22]8,皆可以家庭结构为审美视野、以“征夫-思妇”为意义格局。在《诗经》所反映的从周初到春秋中叶的历史生活中,原始宗法制逐渐解体,走向大一统的社会政治局面尚未形成,“屈民而伸君”[23]的家国一体思想体系尚未周密地建构起来,家庭结构视野和“征夫-思妇”格局的审美地位就显得尤其突出。在随后“君国一体”的王朝历史格局中,虽然出现了战争灾难、江山残缺、建功立业、征戍苦寒等诸多征戍抒情母题,但家庭这一社会结构基本单位在战乱之世的共同命运模式并未改变,以夫妻关系为中心的“核心家庭”的心理情感定式也未改变,“征夫-思妇”审美格局成为征戍抒情传统的重要一脉也就事所必然了。
孙犁抗战小说所反映的历史时代虽属现代中国,但强敌压境时“国民党放弃了这一带国土,仓皇南逃”[18]55,冀中人民“苦于没有领导,他们终于找到共产党的领导”[5],于是“在抗日的旗帜下,男女老少都动员起来了”[18]56。这种严密的家国体系瓦解与重构的社会史状态,同样异常突出地显示了个体家庭的地位,从而为个体征战感知的嵌入、为战士与家属角度的战争生活理解,提供了深厚的心理和情感基础。孙犁抗战小说聚焦思乡、思亲之情来“真实记录”特定时代的现实生活,也就客观上构成了对传统中国百姓生活样式及其审美感知路径的深层次艺术皈依,从而显示出一种现代中国版的“征夫-思妇”抒情格局。
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毕竟处于“同构”而“异质”的历史状态,从根本上看“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对孙犁来说只是一种审美文化的“积淀”,在创作中也是作为深层艺术资源、以“潜结构”“潜叙事”“深层思维导向”的方式具体表现出来的。在革命文学研究领域中,“隐形结构”“潜结构”“潜叙事”等概念是陈思和、张清华等学者所倡导的一种理论思路。陈思和认为,某些革命文学作品在显性叙事背后蕴藏着“民间隐形结构”,显性叙事往往存在时代的局限性,民间文化形态却“依托了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显形形式,隐晦地表达出来”[24]218,“畸形地展施出自身的艺术魅力”[24]221。张清华将思想视野由“民间”拓展到了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认为革命文学叙事建构的深层“有着大量来自传统的旧的叙事结构与故事元素”,成为作品的“传统潜结构”,“暗中支持了红色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的文学性魅力”[25]。这种理论思路以对文本内涵及其审美资源的拆解性辨析为基础,深层次拓展了探索革命文学审美魅力的学术路径。与大量其他革命文学作品一样,孙犁的抗战小说也存在显性话语和潜结构并存的审美路径特征,而且正因为文本意义建构的深层包含着“征夫-思妇”的审美潜结构,他的作品才显得底蕴深厚、韵味悠长,“风格”的艺术精灵才在他那现实主义作家的“灵魂里醒来”。
三、“抗属家务事”叙述中的“征夫-思妇”母题意涵
孙犁小说以“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为题材,实际上是以“家务事”和“儿女情”叙述来抒发对“悲欢离合”的感慨。他的“家务事”叙述主要聚焦出征战士与其妻子的离别、思念和团聚,由此构成了一种“抗属家务事”的叙事形态,这种形态典型地体现了“征夫-思妇”母题的古今意涵及其相互关系特征。
中国文学征戍抒情传统的“征夫-思妇”潜结构及其传统审美意涵,在孙犁小说的“抗属家务事”叙述中表现得丰富而鲜明。
首先,这些作品的整体审美格局表现出鲜明的“征夫-思妇”叙事逻辑。孙犁创作于1941年的《子弟兵之家》以少妇对出征丈夫的思念与期待为核心,步步推进地描述了李小翠从送丈夫入伍到大年夜逗弄孩子时的一次次“想起心思”来。《丈夫》(1942年)、《山里的春天》(1944年)也都以“思妇”的幽怨情绪及其向开朗、快乐的转变为叙事线索。《荷花淀》(1945年)与《嘱咐》(1946年)更是典范性地描述了“送郎上战场”和“久征回故乡”两种生活样式与情感境界,从而成为孙犁抗战小说的代表作。《光荣》(1948年)总结性探讨“战士出征、抗属留守”的“光荣”伦理,情节演变几乎涵盖了从送别、等待、变故到团聚的“征夫-思妇”叙事所有相关环节,甚至在叙事时间节点的选择上,孙犁也颇有讲究。《子弟兵之家》中的春节,《丈夫》中的中秋,《山里的春天》中的春耕时节,《荷花淀》的“小别离”之际,《嘱咐》和《光荣》中的荣归故里之时,都属于传统文化心理的“倍思亲”时分。这就以契合中国民俗文化心理的时间点,不动声色地唤醒了读者对“征夫-思妇”相思之情的心灵感应。
其次,这些作品在具体的叙事抒情过程中,丰富而深切地展开了“征夫-思妇”母题的传统审美意涵。《诗经》相关作品堪称是“征夫-思妇”文学母题的源头,我们就以孙犁小说与《诗经》作品的审美共同性为切入口来进行分析。《荷花淀》《嘱咐》的基本情节框架“送郎上战场”和“久征回故乡”,恰与《诗经》作品的抒情出发点“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和“我东曰归”“今我来思”相呼应。《荷花淀》以水生嫂为叙事视角,颇具《伯兮》《君子于役》等作品的“思妇怀人”色彩,甚至水生嫂“你总是很积极的”与《伯兮》中的“伯兮朅兮,邦之桀兮”,年青媳妇们“藕断丝连”地结伴“探夫”与“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都有明显的精神与心理相似性。《嘱咐》的叙事视角转到了“征夫怀乡”方面,水生有着常常想家的“苦恼”和希望到家看看的“热望”,《诗经》的《东山》中也有“我徂东山,慆慆不归”的想望;水生在“日之夕矣”靠近村庄时产生“家对他不是吸引,却是一阵心烦意乱”的感受,显然是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理;他担忧父亲“是不是还活着”、妻子“正在青春,一别八年”“房子烧了吗”,更与《东山》中征夫“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的战乱思亲具有明显的心理共同性。在更宽广的文学史视野中,这种种基于“征夫-思妇”审美格局而相类似的情形同样特征鲜明地存在。《子弟兵之家》中的小媳妇“思夫”情态,颇有唐代思妇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之趣。《光荣》中的坚贞守候、立功回乡、庆功大会等情节,则明显存在着“苦守寒窑”“荣归故里”“夫贵妻荣”等中国古典征战小说的“潜叙事”。所以,孙犁抗战小说的“抗属家务事”叙述文本确实触角深广地展开了“征夫-思妇”母题的传统审美意涵。
但孙犁的“抗属家务事”叙述又是从抗战时代的现实生活出发形成的审美建构,对“征夫-思妇”审美文化底蕴的感悟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所以,基于对时代问题、民众心理的体察而拓展、深化和更新“征夫-思妇”母题的意涵,又构成了孙犁抗战小说审美建构不容忽视的另一侧面。
其一,孙犁揭示了“抗属家务事”中隐含的家庭现实问题及其演变趋势,大大增强了“征夫-思妇”抒情的时代色彩和政治意蕴。《子弟兵之家》以春节期间小兰送窗花小纸人、村里优待白面和猪肉等细节描写,既表现了根据地优待抗属的政策与风尚,又揭示了抗属小翠期待丈夫“多打好仗”的心理愿望。《丈夫》以两连襟“好玩”和“好念书”、当伪军和当八路的对比性情节结构,表现了“她”对丈夫抗日从幽怨“为什么你出去受罪”到“觉得很荣耀”的精神转变。《山里的春天》中的留守妇女因为生产艰难而对“当兵的”生起气来,后来却发现刚吵完架的八路军兄弟同样远离妻女,而且正在她地里进行代耕劳动,进而明白了八路军是“天南地北的大家庭”,就不禁“眉开眼笑了”。《光荣》聚焦留守妇女凭啥忠诚等候抗日战士归来的人生问题,正面确立了抗战时代“光荣”伦理的历史合法性。对这种种社会史问题的审美反映,有力地强化了文本意义建构的时代生活骨力。
其二,孙犁抗战小说着力发掘和营造“思妇”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彻底扭转了传统“征夫-思妇”征戍抒情的哀怨、凄苦情调。孙犁在家乡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刻发现,中国农民“是献身给神圣的抗日战争的”,“机智、乐观的”,“充满胜利的信心的”[4]359-360;特别是“那些青年妇女……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18]57。于是,他鲜活、真切而满怀热情地讴歌了这“民族觉醒和奋起”时代的民众心理现实。《丈夫》中的女人中秋时分觉得“日子过着没心思”,但回娘家时又一次体会到“抗日光荣”,丈夫还托县游击大队长带回了家信,就“快活了一晚上,竟连那圆圆的月亮也忘了看”。《嘱咐》中的水生嫂听说丈夫回家住一晚就要走,不由得“无力地仄在炕上”,却仍然连夜撑着冰床子送丈夫上前线。《光荣》中的秀梅宣示不结婚,精神信心和心理意志兼有地“等着胜利”,原生荣归故里的事实则表明“我们求什么,就有什么”,乐观主义精神确有其道理。甚至在对《钟》充满了犹豫和矛盾的修改过程中,孙犁也最终决定“删除了一些伤感,剔除了一些‘怨女征夫’的味道”[26]。
在孙犁抗战小说的“抗属家务事”叙述中,时代特色鲜明的思想倾向与传统意味深长的情感心理并呈,显性主题与潜结构内涵有机统一,充分体现出“征夫-思妇”母题意涵的诸多深层次古今相通之处。这种相互映衬、相得益彰的关系特征,在孙犁对“光荣”伦理的审美建构中有着更凝练集中、具体而微的表现。
孙犁将“光荣”伦理作为叙述“抗属家务事”的价值基点,几乎贯穿于所有作品的审美建构之中。《山里的春天》中留守妇女心理转变的关节点,是“你抗日有了成绩,我和孩子在家里也光荣”。《丈夫》中两姐妹对比的分界线,是抗日“荣耀”“光荣”的精神享受足以超越一时的物质功利和世俗快乐。《荷花淀》中父亲临别时对水生说的,同样是“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
孙犁建构“光荣”伦理的核心艺术手段,却是营构“骑大马、挎长枪”这种洋溢着古典战争诗意的审美意象。《子弟兵之家》中的小翠自编曲儿,以“骑大马,背洋枪”来想象丈夫打胜仗后的光荣和威风。《嘱咐》中的水生嫂“向着那不懂事的孩子”诉说的,也是“他拿着大枪骑着大马”,等回来了“把宝贝放在马上”。《光荣》更对“光荣”伦理进行了民俗仪式化的艺术表现。从骑枣红马、背大草帽的“狂跑”返乡姿态,到开全区大会表彰,再到打马游行大庆祝、爹娘坐大骡车跟随,直到“修下这样的好儿子,多光荣呀!”的街头议论,孙犁酣畅淋漓地表现了原生作为特等功臣衣锦还乡的人生荣耀。这种高头大马、抬匾执仗、锣鼓喧天地大游行的仪式,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彰显光彩与威仪的典型形态。所以,“光荣”伦理所包含的精神与情感享受,孙犁是借助民族传统方式才充分渲染出来的。
四、“战地儿女情”叙述中的“拟征夫-思妇”思维路向
与古代将士戍守边塞的苦寒寂寥、“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相比较,八路军战士既有《嘱咐》所描述的“走过各式各样的山路”、十年八年难归家的相似性,又有人民子弟兵在“天南地北的大家庭”处处感受到人情温暖的差异性。孙犁抗战小说从这样的时代特征出发,又聚焦远离家乡的八路军士兵与出征所在地“女孩子”的互助性交往,发掘“那些妇女内心的柔情”[27]及其在战士心中的“激荡”,从而形成了一种以“战地儿女情”为中心的叙事形态,并以“拟亲属”[28]的人物关系建构和“征夫怀人”的叙事抒情意味,显示出“拟征夫-思妇”的审美思维路向。
在1940年代初期建构“抗属家务事”叙述模式的同时,孙犁也开始了在军民互助故事中添加“战地儿女情”元素的尝试,并表现出向“拟亲属”伦理关系转换的审美路径特征。《芦苇》(1941年)尚是单纯地讲述躲在芦苇丛中反“扫荡”的军民之间如何互换衣服。《红棉袄》(1941年)中的姑娘脱下红棉袄盖在初次见面的八路军病号身上,作者就描述到了那衣服“满留着姑娘的体温”,但又解释为那动作属于“服侍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过的”,单纯的军民互助故事中于是兼有了男女身体的体感和“拟亲属”关系的意味。在《老胡的事》(1942年)中,“已经是三十岁开外”的老胡觉得小梅“相貌俊”“处处好”“可喜欢”,对她的劳动、衣着、身体发育“全看在眼里”,连小梅上山拾秋末的风落枣子也跟着去帮忙,一腔“儿女情”在作者的细细描述中呼之欲出。孙犁却又宕开一笔,转而描写老胡当兵的亲妹妹前来探望,随即将“热爱劳动的小梅和热爱战斗的妹妹”并列起来,建构起一种自我抑制、归“情妹妹”心理情感于家庭兄妹关系的“拟亲属”伦理规约。
在随后长时间的创作中,孙犁将这种“战地儿女情”性的叙事建构隐匿、搁置了起来,其中种种耐人寻味的原因,如规避在八路军战时婚姻制度层面“犯禁”、关注思亲更甚于品味儿女柔情等等,笔者在此不拟深究。到1940年代末,在以《光荣》系统性探讨了“征夫-思妇”征战母题的意涵之后,孙犁又重归“战地儿女情”的审美路径,连续创作了《浇园》《吴召儿》《山地回忆》《小胜儿》等一系列作品。《浇园》和《小胜儿》讲述根据地女孩护理八路军伤员的故事,《吴召儿》讲述识字班女生为八路军当向导反“扫荡”,《山地回忆》以根据地女孩用家里仅有的布为八路军战士做了双袜子为线索。这些作品都存在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内涵,但孙犁的审美重心并不是根据地司空见惯的军民互助故事本身,而是那些隐藏于其中的私密性“战地儿女情”及其向“拟亲属”伦理关系的转换。
《吴召儿》和《山地回忆》两部作品,都着力强化了八路军战士和根据地女孩子的“战地儿女情”及其“拟亲属”意味。《吴召儿》中的吴召儿在当向导的过程中,从告诉八路军“到处是吃喝”,到在姑姑家熬倭瓜吃,再到送给每人一根山桃木拐杖,所显示的皆为根据地青年女性的自信、乐观与能干。但她与“我”在山路上解开口袋交换炒面与红枣,“走亲戚”到姑姑家亲昵地介绍“炕上就是我的老师”,以及两人放哨时于狂风暴雨中“紧挤着躺在”大平石下“软软的白草”上面,“战地儿女情”就有了越来越浓郁的表现。《山地回忆》中的女孩子与“我”不打不相识,给“我”做袜子也属正常的军民互助。但从“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的新家”开始,“我”与女孩子父亲爬山越岭去贩卖红枣,女孩子要求买架织布机而“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就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我”作为“家庭特殊成员”的意味。
《浇园》和《小胜儿》也超越了对根据地女性如何照顾八路军伤员的常规性讲述。《浇园》的前半部分尚属军民鱼水情“常规叙事”,但在伤号李丹能拄着拐走动之后,孙犁细细铺叙了一个香菊浇园、李丹陪伴的劳动过程,真正的艺术用心就充分显示出来。李丹最初只是想帮忙,后来开始“喜爱”这地方、“心疼”这人,再后来对香菊的劳动“无比地尊敬起来”,显示出香菊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香菊从不让他带伤帮忙,到商谈劳累、天气与收成,再到天晚双双回家时在棒子地“拔了一颗,咬了咬,回头交给李丹”,直到“慢慢在前面走”却又注意听拐响“不把他落得远了”,心理情感显然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整个浇园的过程,则不啻是一幅“夫妇相随”、耕作劳动的传统田园生活经典图景。《小胜儿》中的小金子与小胜儿本就是从小称兄道妹、“过得很亲密”的邻舍,小金子当骑兵时还收到过小胜儿的小马鞭。小金子进地洞将养伤病期间,小胜儿既为他的营养卖了“陪送袄”买挂面和鸡蛋,又筹划着何时“就该给你饺底子做鞋了”,俨然家庭主妇的气派。小胜儿母亲叮嘱小金子“你可别忘了你妹子”,更将小金子的“准女婿”身份鲜明地表露出来。
孙犁小说对“战地儿女情”的描述蕴蓄着浓浓的人性、人情意味,实际上已走到了政策、政治和文化多层面“越界”和“犯禁”的边缘,但在关于孙犁小说“小资情调”的批评与指责中,这类作品始终未曾作为个案和例证来分析。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孙犁对“战地儿女情”进行了“拟亲属”伦理关系的审美转换。这种“拟亲属”关系所形成的审美意味,既可解释为对“战地儿女情”发展成美满夫妻关系的期待和暗示,又可阐发为“军民一家亲”“人民子弟兵”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在此基础之上,孙犁又运用“得胜回头”的叙事策略,来表达“激荡着我对那女孩子的纪念”“不知她现在怎样了”,其意味也是既可解释为“征夫”对战地儿女情往事的亲切怀恋,又可阐发为胜利不忘根据地人民的集体共情话语。于是,作品就以一种可进行双向解读的文本意义建构,既表现了征战环境中的人情渴望、人性本原而别具探索气息,又因“拟亲属”的伦理关系转换、“得胜回头”的时空疏离,淡化和深藏了个体生命本位的人性、人情色彩,强化和彰显了契合意识形态话语和民族心理定势的抒情方向,从而成功地规避了政治伦理文化的风险。
如果剥离意识形态话语的表层逻辑,我们即可发现,“战地儿女情”叙述的“拟亲属”伦理关系转换和“得胜回头”式跨时空怀想,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种“拟征夫-思妇”的深层思维路向。
五、文明连续性:孙犁抗战小说的审美经典性之“源”
孙犁的抗战小说长期受到高度关注,但审美潜结构的研究思路并未用于对他这些作品的阐释之中。当我们将孙犁小说与其他革命文学作品纳入同一视野、都从审美潜结构角度来解读时,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反而浮现出来:既然这些作品都以潜结构来支持“文学性魅力”,为什么唯独孙犁的小说出类拔萃、更胜一筹呢? 对这个问题的圆满解答,需要从不同作品审美潜结构的差异性说起。
审美潜结构“作为集体无意识的美感嗜好”[25],具体来源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陈思和的“民间隐形结构”是指“民间(特别是农村)流行的通俗文化传统”[24]202,这种传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但也“构成了独特的藏垢纳污的形态”[24]207-208。张清华的“传统潜结构”则是既包括“原型”“母题”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艺术塑形,又包括“叙事功能与类型的意义上”的成规和俗套、“类似曹雪芹从明清小说中所总结的诸种弊端与特质”[25],其中既可能凝聚民族审美文化的精华,又有可能收纳人心的庸俗、低俗之气乃至人性的阴暗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潜结构”介入革命文学创作就不可能必然地保证文本艺术品质的纯正与优良,而是既有可能与显性结构相辅相成、和合共生,从而增强作品的“文学性”;也有可能添加庸俗、低俗的质素,以致“拉低”显性结构的艺术品位。陈思和所分析的《沙家浜》“一女三男”角色模式,就既可以“精致化”,从沪剧到京剧“转喻为各种意识形态”[24]216的人物关系表征;也可能低俗化,形成着重渲染“一女三男”性关系、酿成“亵渎红色经典”轩然大波的2003年中篇小说《沙家浜》。某些革命历史小说在影视剧改编中衍生出“多角恋爱”“抗战神剧”等媚俗情节,也因为原著中本来就潜藏着“青春言情”“江湖传奇”之类的叙事俗套。
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潜结构还有一种未曾被充分关注和认识的来源,就是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代表的传统雅文化。这种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耀千秋的经典和高峰的雅文化,同样能生成后世文学的创作母题、审美潜结构,并具备高雅的审美文化品位和旺盛的艺术生命力。“征夫-思妇”格局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孙犁正是以卓越的文学素养、审美眼光和艺术才情,深切感受到了抗战时代现实生活中所积淀的“征夫-思妇”母题意涵,并给予了诗化抒情色彩浓郁的艺术表现,从而于风趣横生中显出一种情思高远、韵味深长的审美风范。
孙犁抗战小说审美经典性的更根本基础则在于,“征夫-思妇”这一文学母题不仅具有深厚、高雅的审美文化积淀,还是中华文明家庭结构形态及其特性与规律的艺术反映和转化。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人民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9],“征夫-思妇”文学母题就具有文明规律之“源”和文学传统之“流”有机融汇、合而为一的优势,从而彻底超越了通俗文化内蕴芜杂、良莠并存的审美境界。具体说来,孙犁抗战小说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对中华文明新型“离乱之世”的认识与概括。他的作品大主题和小题材的关系,奠基于传统农业文明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形态;其抒情性、诗意美和浪漫色彩的艺术魅力基本构件,生成于中华文明的夫妻人情之“美”与家国伦理之“正”;他所表现的“真善美的极致”,则是中国现代农民热土难离却抛妻别子御外敌、青年妇女缱绻情深却识大体顾大局的对于“光荣”伦理的追求。所以,孙犁的抗战小说既契合乡土中国心系家庭关系结构和人性人情之美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又彰显出中华文明战胜野蛮战争的强大伦理力量和深刻乐观主义精神,作品也就具有了进行多层次艺术品味和感悟的可能性。
传统中国家庭生活样式之所以具有深厚的审美生命力,则源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30],具有生息繁衍规律、社会结构形态的历史恒常性和古今异质同构性。正是中华文明的这种突出特性,决定了新时代的社会风尚、精神走势往往潜藏着文明传统的深厚内质,决定了作家对时代生活及其内在文明特性的审美自觉和真切反映有可能生成审美的经典性。孙犁认为文艺的根基同时存在于“现实生活”“民族性格”和“民族传统”三个方面,就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及其艺术反映传统的一种深刻把握。正是以此为基础,孙犁描述冀中平原“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讴歌出征战士和留守家属的精神情怀,就自然地构成了对中国文学“征夫-思妇”征戍抒情传统和中华文明连续性规律的精神皈依,从而在历史、文化与文明相结合的深广背景中打通了抵达审美经典性的艺术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