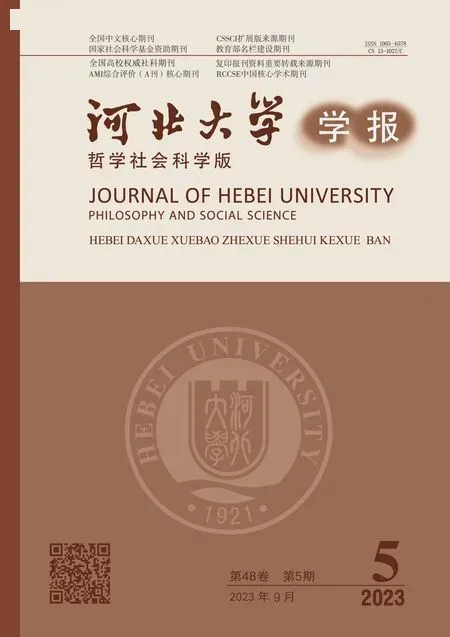孙犁的文学“风景”与晋察冀抗战经验
熊 权,刘振琛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引言: “风景”的转移与连续
孙犁的抗战文学以描绘白洋淀水乡的优美风景而独具特色,也造成了相关研究中的“定见”。例如,有的研究者将孙犁放置在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脉络中,认为他的写作追求一种单纯的美学效果,《白洋淀纪事》将抒情小说“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有的研究者认为孙犁描写白洋淀水乡的人性美、人情美是自觉疏离主流革命文学,体现了一种“文人的情调”[2]。这些解读契合“新时期”以来学界重视文学审美、个人化的研究范式,自有其合理性。然而文学审美并不仅仅是艺术形式问题,还与作家的思想及生活实践、历史语境等构成有机联系。孙犁自己就曾说:“关于苇塘,就不只是一种风景,它充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冀中的名胜。”[3]在探究孙犁文学“风景”的复杂性方面,有的研究者考察孙犁小说的诗意风景描写与抗战时期晋察冀乡村建设的紧密关系[4];有的解读孙犁在田园风光中讲述抗战传奇,强调作家笔下的“风景”不仅具有审美功能而且“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5],对突破孙犁研究领域的“纯文学”范式进行了富有启发的尝试。
综观孙犁抗战题材作品,不仅描绘优美的白洋淀水乡也多写阜平山地的险峻壮美,已有研究对后一种“风景”关注不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风景”既反映地理、时势也关涉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包含晋察冀抗战局势的历史变化以及文学观念的建构过程。文学聚焦“风景”,通过描绘自然风光表现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叙述策略等;再进一步,“还要时时创造出风景,要使此前作为事实存在着的但谁也没有看到的风景得以存在”[6]。从白洋淀水乡到阜平山地的自然风光虽然发生变化,但孙犁认识风景的“装置”一以贯之,始终赞美故乡人民积极、乐观的抗战精神。本文剖析两种“风景”的转移与连续,发掘其中转化乡土家庭观念、因地制宜凝聚军民共同体等抗战经验,进而强调孙犁以个性抒情呼应时代主潮、把文学书写作为抗战行动,构成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不可忽视的精神资源。
一、白洋淀:家/国同构田园诗
描写清新优美的白洋淀风光、刻画冀中人民积极乐观的抗战情绪是孙犁成名的关键[7]。然而“白洋淀纪事”发生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局势中,战争造成的破坏客观存在,而且冀中民众未必一开始就具备积极主动的救亡意识。在家/国同构视野下激发乡土社会内在的家园意识进而调动民众抗战卫国的积极性,是孙犁描绘白洋淀田园诗所蕴含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内容。
众所周知,在孙犁的《荷花淀》等小说中,美好的人情、人性与地域风景互相辉映,呈现优美和谐的田园诗风格。不可忽视的是,白洋淀田园诗之下时有暗流或裂隙。小说里眺望茂盛的荷塘:“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来,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俯瞰丰收季节的芦苇:“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荷花、芦苇作为自然景物显得柔美甚至柔弱,在孙犁笔下却自有一种刚强。荷叶是哨兵林立的“铜墙铁壁”,荷花苞如直指天空的“利箭”,金黄色的芦苇堆积,筑起一条守卫的“长城”……字里行间透露了攻战进退的紧张严酷,可见一种全民皆兵的警备与激昂。
白洋淀田园诗并非与世隔绝,而是镶嵌在战火硝烟的时局当中。水生嫂月下织席构成一副令人难忘的织席风景画卷,也成为白洋淀人民安居乐业的典型镜像: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8]
然而水生的推门而入,带来即将离家征战的消息,打破了悠游自在的织席意境。不止《荷花淀》突然切换场景,战争阴影下的白洋淀水乡笼罩着无处不在的威胁。在《织席记》中,日寇的炮楼雄踞村庄,乡民日夜处于监控之下。由于日伪政府统制苇席销售,低价强收,常常发生一天饿死数条人命的惨事。《采蒲台》里的小红和母亲为招待远道而来的“我”,带着质量上乘的渔网、苇席去集市换取粮食,却因市场被破坏不得不低价贱卖。在《渔民的生活》中,渔民们遭受侵略者和商贩们的双重剥削,他们经常饿着肚皮劳作……越是塑造家园故土的安宁静好,就越是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丰饶的白洋淀从鱼米之乡变成了饿殍世界[9],鲜明反差之中,体现孙犁动员民众抵抗敌寇、保卫家园的文学策略。
《嘱咐》作为《荷花淀》续编,仍然以水生夫妇作为主人公,讲述战争中的“离家-还家”故事。在《嘱咐》中,水生参加抗战游击队已经七八年,因为部队偶然驻扎家乡附近,才终于有探亲的机会。在他归家途中,小说以大量笔墨展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风景。一种是想象中的家,黄昏时刻袅袅炊烟构成的田园风光。另一种是触目所及的现实景象:许多高房,大的祠堂,全拆毁修了炮楼,幼时记忆的几块大坟地,高大的杨树和柏树,也砍伐光了,坟墓露出来,显得特别荒凉。水生踏进家门,才得知老父亲早已在战乱中去世,数年中只有水生嫂艰难持家。目睹家园残破,他与妻儿短暂相聚甚至来不及给父亲上坟烧纸就急迫归队。水生嫂一大早起身,驾着冰床子(白洋淀冬天冰面出行的一种交通工具,状似小艇)送丈夫匆匆离家。这些“反人性”的情节设定,因为夫妻同心、坚信有一天能打败敌人凯旋还家,显得分外动人。水生嫂临别嘱托水生:“我为什么撑得这么快? 为什么着急把你送到战场上去? 我是想,你快快去,快快打走了进攻我们的敌人,你才能再快快地回来,和我见面。”[10]
水生夫妇遭遇的家园破毁、至亲分离,是抗战历史中无数家庭的一个缩影。孙犁讲述他们的故事,寄予了从个人经验、从乡土家庭观念动员爱国救亡意识的思考。在以“家”为生产单位、为血缘伦理共同体的乡土中国,如何调动农民参军是抗战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成为晋察冀边区政治工作以及文艺工作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父母在,不远游”等口口相传的传统观念成为征兵工作的掣肘。此外,青壮年离家当兵造成农业生产缺乏劳动力,也造成婚姻关系不稳定等现实问题。孙犁出生于华北农村,当然知道农民固守家庭、轻易不肯离开自己世代栖居的地方。“七七事变”发生后,他经同学介绍准备投奔河北自卫军政府,但家里人商量来去不能答应。孙犁从小身体孱弱,兄姐先后不幸夭折。在重子孙繁衍、血脉接续的乡土中国,家里独子冒险征战违背风俗人情。最后还是孙犁父亲下了决心并说服众人:如果不去打仗,家里的这些田地以及所有人的性命,将来恐怕都保不住。老人只有朴实的生活经验,却越出切身利益而触及国家救亡问题。中国自古认为家国一体,在家庭结构的基础上延伸、建构为宏大的国家体制。覆巢之下无完卵,国之不存何以为家? 在举家犹豫之际,孙犁的父亲顾虑远忧所以支持儿子的选择。孙犁亲身经历这样的情理冲突,非常理解水生恋家却又离家的心情,也说出自己的心声:“他们当兵打仗,正是为了保卫他们。暂时的分别,正是为了将来的团聚。”[7]56在民族国家遭受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卫国即保家,为人也是为己。
即使家/国同构已积淀为民间文化心理,抗战动员还是需要有政治政策组织及推动。在老百姓那里,“家国虽然并列,但较起真来,家的份量无疑还是要大些”[11]。水生夫妇甘心情愿分离,边区政策提供了补偿和保障。在中共抗战时期的政治工作中,充分重视“家”作为生产单位、作为血缘伦理共同体的重要性,强调兼顾“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一方面调动农民参军奔赴前线,另一方面重视安定军心、扶助后方家庭[12]。动员民众爱国救亡,必须考虑他们的具体诉求,征兵工作“只有顺应乡村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人情——才有可能取得成功”[13]。为此,晋察冀边区政府先后颁布《晋察冀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办法》等文件,通过“助耕”“代耕”等补偿劳动力的办法缓解抗日军属的生产压力。水生临别劝慰水生嫂:“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所谓“自然有别人照顾”,指的就是关于抗属的保护政策。有了合情合理的制度,水生这样的青壮年才能自觉自愿地放下家庭去参军征战。
水生嫂等与游击队利用白洋淀地形、合力伏击日寇的大船,起因是思念丈夫、探亲不遇。水生趁队伍驻留匆匆还家,则是遏制不住思乡之情。一方面,眷念家庭的情感与爱国救亡的责任构成直接冲突;另一方面,如果因势利导则可以促使家/国情感互相激发、相辅相成。边区政府尊重民众的家庭情感,鼓励士兵与家人保持通信联系,还批准他们在不耽误作战任务的情况下回乡探亲、帮助生产[14]。孙犁也经常涉笔战士与家人的通信。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得到亲人报送平安的信息无疑是战争乱世莫大的宽慰欣喜。在《山里的春天》中,“我”长期在山里游击战,接到家信正是春天好季节,心里也感觉如春意融融:“我们八路军的弟兄,比亲弟兄还亲,他们在那里驻防,打敌人,知道我不在家,就会替我去种上地,照顾我的大人孩子,和我在家一样。”[15]《纪念》也是关于家信的故事,“我”与战友在定县打击还乡队,暂住村民小鸭家,恰好收到她父亲的来信。“我”字字句句地读信,“这是八九年来一家人最快乐的一个夜晚”。父亲在信上告知家里,自己正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作战,现在已经升为营长,而且胜利在望、即将归来。小鸭父亲的行迹令“我”发生共鸣:“这生命经过长期的苦难,正接近幸福的边缘”,也意识到自身的责任重大:“有这么些母亲和孩子,把他们的信心,放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当作了保护人。”[16]
借人物的经历和语言,孙犁反复强调保家与卫国的一致性:“为国家打仗,那是本分应当的”,“把这打仗看成是自家的事”[17]。在家/国同构的视野下,孙犁书写战争避开现实主义的血泪控诉而重视抒发乐观和生机。在他笔下,那些征战的男人、守家的女人虽有感伤却极少悲凄,他们坚定地相信终有一天能赶走侵略者、合家团圆。所以茅盾评价孙犁小说的好处,在于“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18]。正如《嘱咐》末尾淡化离别之际难舍、担忧的感伤,借水生的视角描画水生嫂送别途中驾驶娴熟、风姿秀美:
她轻轻地跳上冰床子后尾,像一只雨后的蜻蜓爬上草叶。轻轻用竿子向后一点,冰床子前进了。大雾笼罩着水淀,只有眼前几丈远的冰道可以望见。河两岸残留的芦苇上的霜花飒飒飘落,人的衣服上立时变成银白色。她用一块长的黑布紧紧把头发包住,冰床像飞一样前进,好像离开了冰面行走。她的围巾的两头飘到后面去,风正从她的前面吹来。她连撑几竿,然后直起身子向水生一笑。[10]217
对侵略者的愤恨、对家园安稳的期盼定格在这嫣然一笑。即使前途未卜、生死难测,只要还有盼归的家,还有等待的家人,战士就有永不泯灭的热情,爱国救亡的事业就扎下了牢固深刻的根基。
二、阜平:患难相济山地情
孙犁以书写白洋淀水乡著称,同时也多写阜平山地。这种从水乡到山地的“风景”版图拓展,与华北抗战局势相关。1942年以来,晋察冀的抗战队伍因日寇步步紧逼无法在平原地区容身,主要转入河北西南部的太行山区一带,孙犁作为文职工作人员也随军辗转。阜平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是河北与山西两省四市九县交汇处。这里群山起伏,被誉为“冀晋咽喉”“畿西屏障”。在险峻且贫瘠的自然环境中,游击战士与当地民众患难相济、凝聚为同仇敌忾的抗战共同体。虽然山水风光迥异,但孙犁的“认识装置”不变,还是重在从日常生活发掘乐观精神、以鼓励抗敌斗志。
自1939年开始,日本调整侵华战略,对已经控制的华北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五一大扫荡”堪称冀中抗战的标志事件,“冀中人民经受历史上空前灾难,经历人类最残酷最伟大的考验”[19]。这次“大扫荡”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持续近两个月,造成巨大破坏。到6月,日寇基本控制了冀中平原,施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到1942年止,(日军)共计建筑了1753个据点与碉堡,平均每四个半村庄或者2.8平方公里就有一个据点或碉堡,并将各点碉中间妨碍展望和射击的树木、房屋及丘陵一律削平。”[20]在野蛮扫荡的逼迫之下,共产党军队的活动空间和机动能力遭大大缩减,连老红军都忍不住感叹比长征时期更残酷[21]。晋察冀政府指挥主要部队撤退到狼牙山以南,孙犁写《山地回忆》《吴召儿》《蒿儿梁》《看护》《在阜平》等关于山区游击战的名作,都是记录、纪念这段随军辗转的生活。
相对于白洋淀水乡的丰饶,阜平地势崎岖、土壤贫瘠,孙犁描写风景从优美一变而为壮美。他见过当地最高最险的神仙山:“它黑得怕人,高得怕人,危险得怕人,像一间房子那样大的石头……一个顶一个,一个压一个……一步蹬错,一个石头滚下来,整个山就会天崩地裂房倒屋塌。”[22]267他驻扎过蒿儿梁、三将台、石桥以及无数不知名的乡村,知晓那里的农民与自然斗争,生活充满艰辛:“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植物却萌发着顽强活力。高山上的庄稼长得青翠坚实:“在这样高的黑山石上……在这样少见阳光,阴湿寒冷的地方,庄稼长得那样青翠,那样坚实。玉蜀黍很高,扁豆角又厚又大,绿得发黑,像说梅花调用的铁响板。”[22]270山梁、沟畔的树木生意葱茏:“无边的杉树,同年同月从这山坡长出,受着同等的滋润和营养,它们都是一般茂盛,一般粗细,一般在这刺骨的寒风里,茁壮生长。”[23]113
孙犁“看”阜平山地,饱含人的能动性与抗战意识形态内容。孙犁文学凝视风景让读者获得现场感,也对之注入强烈的主观意向:穷山恶水加上侵略者的威压,无论当地老百姓还是撤退至此的游击队只有因地制宜,才能艰险求存、开辟新生路。他写农民土里刨食也颇有诗意:“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的坡上,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在描绘山坡风景之后,孙犁接着带出一笔:“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24]11。
阜平民众生活物质匮乏,常年吃糠咽菜,甚至靠吃各种树叶度日,却给外来的游击队员慷慨救助。孙犁怀着深切的感恩、怀念之情,把军民间的患难相济写得细致动人。《山地回忆》围绕关于一双袜子的往事。1941年冬,“我”随军打游击驻扎在阜平小村庄,偶遇一个在河边洗菜的小姑娘妞儿。她看到“我”光脚冻得发黑,就拿家里节省的布料做了一双袜子送给我。当地山高谷深,缺乏阳光无法种植棉花,一般以麻代线,因此妞儿织成的袜子底、面都相当坚实。“我”整整穿了三年多,直至抗战胜利。《吴召儿》讲述为躲避日寇追击,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吴召儿带着游击队员夜登神仙山。在山顶吴召儿的姑家里,饥寒交迫的众人躺在主人让出的热炕,吃上了他家地里长得最大的一个倭瓜,“吃过了香的、甜的、热的倭瓜,我们都有了精神,热炕一直热到我们的心里”。《在阜平》的年三十除夕,“我”随军采访,就地过年。东望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我”有家不能回,内心难免沉重。借宿的房东是一个沉默拙言的老光棍汉,他端来一碗豆腐、一个窝头,“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他的馈送。孙犁作品历数的饭食,还有雁门关外的辣椒面、蒿儿梁的搓窝窝、石桥村的红烧肉……它们简单乃至粗粝,却是当地老百姓倾尽所有的分享、赠与。孙犁在辗转山地的行军生活中,深刻体会到他们受困于物资贫瘠,同时又感动于他们改造、利用有限条件的韧性与智慧,尤其感念他们的慷慨无私:“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22]273
在战乱分离、家园破毁的悲惨境遇中,游击队员与民众结成了“类家属”的抗战共同体,这种非血缘共同体在物质上、精神上都构成有效支撑力。一衣一饭体现日常生活、人情交往的积淀。“我”接受妞儿纺织的袜子,也经常帮助她家挑水、搬运,“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25]250。小胜儿母女收留骑兵团受伤的战士小金子,为了让他尽快恢复伤势,她们变卖家里唯一值钱的花丝葛袄,换来挂面和鸡蛋做伤员饭[26]241。香菊家收留伤号李丹,悉心给他疗伤。李丹拄拐能起身了,给纺织的妇女做加速轮、帮助拉风箱烧火、汲井水浇园……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像一家人一样,越混越亲热了”[27]193。赶走侵略者,恢复家园平安静好,则是凝聚军民共同体的强大驱动力。在河边洗菜的妞儿尖牙利齿,指责“我”洗脸弄脏了她洗菜的河水。“我”本想回敬几句,看到她淘洗作为早餐的树叶、穿着单薄的衣服,还有河滩远处被敌人烧毁过几次的村庄,怒火立刻转化为怜惜。妞儿送给我那双厚如鞋底的袜子,关切地问:“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我”答以持之以恒的决心:“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25]247蒿儿梁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全力接纳游击队的伤员病号。“整个小村庄在热情地支援帮助这个小小的队伍”,小孩子要去送信砍柴,妇女们拆洗伤员的药布衣服,分班做饭。在共同御敌的目标之下,村民与战士之间结下牢固情谊。村民感谢战士们打倒地主,也盼望他们彻底赶走日本鬼子,完全把他们视为“自己人”。村主任说出全村人的心声:“老百姓帮助你们,情愿把心掏给你们,为什么? 这为的是你们把我们救了出来!”军医杨纯则看到其中互助共存之道:“这就叫鱼帮水,水帮鱼。”[23]117面对自然暴虐与侵略者的威压,孙犁着力刻画出患难相济的人性“真善美的极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孙犁虽然居住于天津的都市环境,却常常想念乡野生活。他时时回想阜平的山路、流水,更加忘不了艰苦岁月里与当地民众结下的深厚情谊:“时常想念阜平山地,不只在那里相处过的农民,时时再现眼前,引起怀念,就是那里险峻的山路,激越的流水,也经常出现在梦境之中”[28]462。孙犁称阜平为“晋察冀边区立业起家的基地”,是难以忘记的“第二故乡”[29]430。那里的风景入梦、入心,与眷恋家园的情感、爱国救亡的事业融为一体。
三、植根晋察冀抗战语境的“革命人”
孙犁凝视自然风景既融入个人性情,也看见华北地理、乡土众生,生成了独特的文学主体性。他擅长从日常生活阐扬战斗的乐观、韧性精神,拓展了“五四”以来的个性主义文学观念。在走出知识分子的书斋、案头,把文学作为呼应抗战政治、积极介入现实的一项行动的意义上,孙犁是植根晋察冀抗战语境、与时代主潮共鸣互动的“革命人”。实践性与行动性,堪称孙犁抗战书写的突出特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孙犁是“诞生”于抗战的文艺工作者,与“五四”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了大批的文人作家。他们绝大多数在都市从事与教育、编辑出版相关的职业,属于书斋知识分子。又因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接触欧风美雨,深受西方“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话语影响。孙犁从中学时代开始,也很有兴趣地阅读新文学作品,尤其好读鲁迅、茅盾、叶圣陶等的小说。但他后来抗战投军,并不局限于学院、案头,而是积累了多年游击战还有深入乡土社会的经验。他回顾自己的创作起点,强调对生活、对时代的实感:“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24]12
在抗战的历史情势中,文艺既是宣传动员的方法也是边区政府求生存、求发展的重要途径,力求面向更大多数的社会民众。孙犁亲历其中,形成了不同于“五四”的文学观念及评价标准。在《“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一文中,他明确提出文学以人民为中心,也明确反思五四新文学的不足: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倒是多接受了一些西洋的东西……它使文学局限在少数知识青年圈子里,和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五四”文学运动以来,无论在小说戏剧、诗歌翻译,我们都可以整理出一定的成果。从这些成果中,自然可以看到文学与人民的结合,还有很大距离。[30]
在孙犁看来,“五四”运动虽然促使文学冲破贵族、山林走向民众,然而未能将通俗化、平民化进行到底。作为一个富有才华的作家,孙犁当然认为文学有抒发个性情感、展现个人天才的功能,但在民族国家的危亡关头,文学的更重要的是成为救亡事业的一部分,是“中国人民的事业”:“今天应该把文学看作一种事业,中国人民的事业。过去,有人嚷着文学无用论。把文学书叫作闲书,把作家看作狂生。我们觉得这个时期已经老远过去了。”[31]他重新为文学定位:“在今天,文学工作便是整个抗战工作的一部分。而写作者本身,便是革命行动里的人们中间的一个。”[32]
孙犁1933年才中学毕业,他继承五四文学传统是从鲁迅等作家那里“隔代遗传”,晋察冀文艺运动才是他成长为作家的历史情境。在1938—1941年之间,晋察冀边区文艺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期。在这一时间,边区的“文协”分会、文联相继成立,县、区、村级的文建会也陆续建立起来。即使出版、宣传受到客观条件限制,但各种油印、石印的文学刊物纷纷出版。边区政府考虑到农民对演剧、唱歌、图画等喜闻乐见,又组织成立了多个话剧团、村剧团。另外,街头诗、秧歌剧、歌咏、木刻画、壁报等通俗文艺形式层出不穷。如果说文学是抗战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晋察冀文艺运动“有效地发挥了文化的‘黏合剂’效应,整合了边区各阶层的利益,将一盘散沙般的大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战,为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心理基础”[33]。
在晋察冀文艺面向大众、重视行动等风气的熏陶之下,孙犁逐渐崭露头角。综观孙犁晋察冀的行伍时期,属于文学创作的尝试与积累阶段,仅写作小说《爹娘留下琴和箫》、叙事诗《白洋淀之曲》等十余篇。他这一阶段主要充当一个配合抗日的宣传工作者,有大量文艺理论与批评问世。为促进边区的鲁迅宣传,他先后写过《论鲁迅》《鲁迅、鲁迅的故事》《少年鲁迅读本》;为了指导晋察冀通讯社的通讯员们写稿,他写下《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编辑“冀中一日”群众写作运动的专门资料之后,他写下心得文字《文艺学习》[34]。孙犁回顾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把“战士”身份摆在先于“作家”的地位:“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始,我经历了我们国家不同寻常的时代……我有幸当一名不太出色的战士和作家。”
在晋察冀文艺运动中,孙犁参与的“冀中一日”活动尤其值得一提。这次活动旨在发动尽可能多的群众拿起笔来,讲述抗战军民的日常生活。具体是聚焦1941年5月27日“平凡的一天”,以文字书写反映当天的边区的人与事。当地民众积极参与,连一些老秀才、识字班的妇女以及目不识丁的老太太也被动员起来。他们有的自己动笔,有的口述请人代写,场面非常热闹。孙犁在这次活动中担任选稿和编辑工作,他与王林、李英儒等人合作,最后从五万余篇来稿中选出两百多篇分辑出版。在“冀中一日”的集体写作活动中,孙犁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组织者执行者,也属于“被教育”“被塑造”的一员。他由此深刻认识文学不仅是艺术的、美学的,在抗战语境下更是实践的:“从前不知道笔墨为何物,文章为何物的人,今天能够执笔写一二万字,或千把字的文章了”,“使上层文学工作者更去深入体验生活,扩大生活圈子重新较量自己”。
晋察冀的抗战经历为孙犁创作打下根基,由于亲身参战、体验广阔多样的社会生活,他的文字带着山野田间气息。孙犁在晋察冀边区生活的多年,所见所写都是“小人物”。如《邢兰》中喜好“管闲事”的邢兰、《老胡的事》中活泼善良的房东女儿、《出走以后》勇于摆脱婆家控制、到部队里当看护的王振中……这些人物没有耀眼的光芒,在后代研究者、评论家那里也不怎么受关注。但孙犁后来塑造的一些典型形象,如水生、水生嫂、吴召儿等,都由此脱胎而来。经历晋察冀时期的深入生活,孙犁成长为新一代的作家、知识分子。晚年丁玲评价孙犁以及其他晋察冀边区作家群体,也相当侧重其实践特性、与民众结合的特性:“(他们)与人民一道滚过几身泥,吞过几次烈火浓烟,学过使枪,学过使锄,比较熟悉劳动人民,生活底子厚……他们有接近劳动人民的本领。劳动人民亲热地把他们看成自己人。”[35]
结 语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抗日战争既是中国人民遭遇的巨大灾难也是追求现代独立国家道路上一个令人瞩目的里程碑。这场艰巨考验留下重要精神文化资源,孙犁的抗战书写即是其中一页。从白洋淀水乡的和谐优美到阜平山地的险峻壮美,一直贯穿着孙犁对家园的眷恋、对故乡人民乐观积极抗战精神的赞美。孙犁从个人、从乡土家庭观念出发召唤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亲历游击战、战地文艺工作,阐扬因地制宜的抗敌策略、患难相济的军民情谊。以“风景”抒情,从日常生活发现乐观、韧性的战争美学,是孙犁书写晋察冀抗战经验的方法。
虽然孙犁晚年创作发生“衰年变法”,转向批判丑恶,但他始终不悔少作。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我不轻视早期的作品。我常常以为,早年的作品,青春的力量火炽,晚年是写不出来的。”[36]如果抽离孙犁文学所植根的晋察冀抗战语境,一味强调他创作的个性主义、文人的“审美风格”“趣味”等,并不切合孙犁本身。在孙犁看来,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互为成就:“对于参加抗日战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也不后悔。我总觉得,这是给了我一个机会,至少是在文学上给了我一个机会。”[37]孙犁其人其文与华北乡土、与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救亡运动紧密结合,在复兴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力的当下时代仍然可以提供丰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