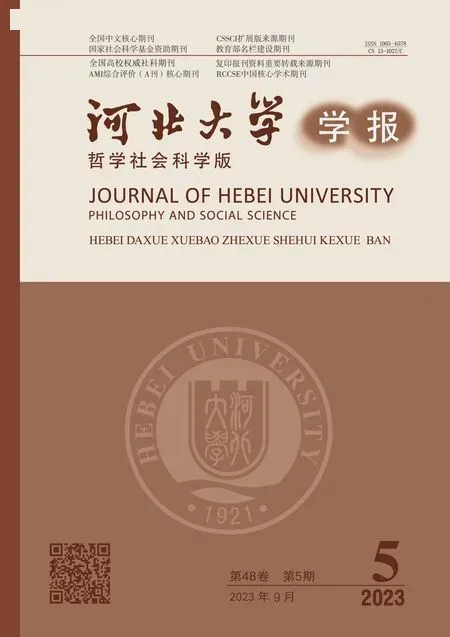冷与热,直与谅
——孙犁晚年忆旧文章片论
杨联芬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读书、忆旧,是孙犁晚年生活和写作的主要内容。愈到晚期,其怀旧和自省的情绪愈浓,文章也愈加沉郁、洗练。他的“童年漫忆”“乡里旧闻”,以及对父母和亡妻的纪念,展现了比其前期小说更加丰富的乡土世相、人情物理,乡愁中隐含一丝忏悔,文字百读不厌。同时,他还有一些写友朋故旧的文章,背景主要在“进城”以后,与其精神生活、职业生涯关系更大。这类作品所写内容,往往直接体现社会现实,笔下人物的行止和命运,也构成孙犁人生的一部分,这类是回忆,也是写现实。本文所论,主要是后面这一类。
孙犁晚年总结写作经验时说,一,“不要涉及人事方面的重大问题,或犯忌讳之事”;二,“不写伟人”,“不写小人”[1]55。第一方面,与他“远离政治”的一贯心态有关。他说:“我的一生,曾提出过两次‘离得远些’。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有人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论点。但我的作品,赖此,得存活至今。这一次是说离文坛远一点。”[2]104不写伟人,盖因“伟人近于神,圣人不语”;不写小人,则是遵循“宁过于君子,勿过于小人”①管子言。孙犁原文是“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的古训。孙犁这些带有传统中庸色彩的经验之谈,个人语境重,不宜做字面的机械理解,但“不写小人”,却昭示了一个事实:孙犁刻画的人物,即便不能称做君子,也绝非小人,无论孙犁对其好恶褒贬如何,这些人都是值得写的。
一、君子之交
孙犁曾自责,“余于友朋,情分甚薄”[3]401。但实际上,他只是性情疏淡,不好结交而已,加上晚年孤独,体弱迟惰,使人以为其冷。只要稍微观察,便可得知,孙犁是一个重感情、讲义气的人。其散文作品中有大量书信,便是明证。
《芸斋书简》中,孙犁晚年通信最多的,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叫邢海潮的人。从1989年3月开始,到1995年6月,孙犁致邢海潮信达83封①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芸斋书简》中,孙犁致邢海潮的信有83封。但有文章披露,孙犁致邢海潮信84封,邢海潮致孙犁信90余封。参见赵长青《同窗佳话:孙犁与邢海潮》,《当代人》2013年第7期。。1988年春夏之交或1989年初②这两个时间,分别据“芸斋小说”《老同学》和《芸斋书简》中孙犁第一封信推测。,孙犁接到失联五十多年的高中同学邢海潮来信,二人遂开始了书信往还。他俩曾于1931至1933年在保定私立学校育德高中同班两年。孙犁在文章《老同学》中回忆道:“当时,他是从外地中学考入,我是从本校初中毕业后,直接升入的。他的字写得工整,古文底子很好,为人和善。高中二年同窗,我们感情不错。”[4]73邢海潮是河北赵县人,读书时家境较好,故高中毕业便直接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而孙犁家境虽在当地算小康,但育德中学六年的昂贵学费,已使其父不堪重负,故高中毕业后,没再考大学,而是按父亲的希望去考邮政局,但在英语口语环节失利,没有取得铁饭碗。孙犁在北平市政局职位上失业后,邢海潮曾陪他找过中学国文老师孙念希想办法,还借给他五元钱。但这五元钱孙犁一直还不起,有一次海潮写信给已回家的孙犁,说二胡弦断了,手头没钱买新的,委婉暗示老同学还钱,而孙犁那时实在没钱——《报纸的故事》中曾写道,他那时想订份《大公报》,都得鼓起勇气向父亲请求——回信叫海潮去北京图书馆查报纸,看看有没有他新近的投稿发表。为此,邢海潮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北京图书馆翻看近一个月的京津报纸,结果没有孙犁的东西,孙犁这五元钱也就欠了下来。忆及三十年代初这段往事,孙犁有点忍俊不禁说,“我们那时都是青年人,有热情,但不经事,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和做法”[4]74。邢海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复旦大学新闻系副教授[5]74-76,但因曾在“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政权下做事”[4]74,后来处境不好,晚年妻、儿离世,他孤身一人回到河北乡下投靠弟弟,帮助编县志,但生活拮据,意气消沉。孙犁曾叫家人给邢寄去二百元钱,既是接济,也有还债的意思[4]73-75。自此,他设身处地关心这位落魄的老同学,为他介绍审稿差事,又建议和敦促他写文章向报纸投稿。1989年6月23日致海潮信说:“弟冒然询兄,如精力有余,是否愿从事一些业余工作,如代出版社看一些古籍文稿……”7月26日信说:“关于兄业余做些事的问题,弟已与百花文艺出版社谈过,该社社长郑法清同志说,最近想去石家庄,顺便到赵县和兄面谈一切……”9月23日信:“目前,出版社事多,郑君恐未能去石家庄。因之亦未到兄所。”1990年1月23日信:“郑法清出国刚回来,最近他会写信给你的。”4月12日信:“前与郑法清见面,彼谓俟书稿到后,即与兄联系……”[6]524-528彼时,百花文艺出版社正计划出版一套“古代散文丛书”,孙犁认为审校古籍书稿,既是邢海潮专业所长,又能有笔不错的薪酬,故频繁联系郑法清。但这套书迟迟未能上马,其间,邢海潮多次致信孙犁询问,孙犁则每信必复。郑法清回忆道,“那时我工作确实很忙,整体东奔西跑。孙犁同志一时找不到我,于是信中不无‘郑法清是个忙人’,‘办事拖拉也无准则’之类的话。后来,这些信件在《长城》发表出来,孙犁同志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法清啊,最近我在《长城》发表了一批信件。其中多次提到你郑法清。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听后哈哈大笑:‘那有什么,你不就是找不着我着急嘛!’”[7]277另一方面,孙犁鼓励邢海潮投稿给报纸,他一方面向报社推荐邢的稿子,另一方面又以编辑的视角,给海潮提建议。“报社传话,兄之大作,他们可能选用数节。以弟所知,近年颇有些人,写这种文章,兄所记,有些已谈过。他们一定是选用新内容的。”最初邢的文章多谈戏曲,报纸采纳不多,孙犁建议道,“您还可以写些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文章,知识性的或趣味性的。可否写一篇回忆钱穆的短文?”[6]524-532“兄撰论赵高一文,金池转给(《天津日报》)《百科之窗》版刊出,弟已拜读,写得很好。金池编的版,不大登此类文章。今后比较深奥的历史短文,可寄给《今晚报》的达生同志。”[6]541在孙犁悉心关怀下,海潮撰写历史和文学掌故方面的文章,终受欢迎,他也成为《今晚报》的经常撰稿人。
在孙犁致邢海潮的八十多封信中,最多的内容是他为老同学出点子、联系出版社和报刊编辑、寄书寄文、敦促打气,即便自己病体孱弱时也如此。1993年他大病初愈,就给《天津日报》编辑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写信,继续为邢海潮介绍投稿或校稿工作,还想办法将自己给邢海潮的通信寄到《长城》杂志发表,稿酬则分了一半给海潮。1993年4月25日邢海潮致孙犁信说:最近因事外出十五天,4月23日返回邢村,其弟江潮告诉天津孙犁汇来人民币一百六十元,“从汇款单附言中知悉乃孙兄在《长城》杂志发表书简稿费之半数。弟深感兄之惠受,但却有‘踧踖不安’的心情。”[8]161当邢海潮终于逐渐走出生活困境,老有所为,精神有所寄托而身体亦转好时,孙犁满心高兴。与邢通信中数年如一日的日常关切,嘘寒问暖,呈现了孙犁重情仗义,以及过去不太为人所知的细心关照他人的一面。孙犁自小因父母溺爱,又自恃“家有一点恒产”“不愁衣食”而对生活琐事几乎一窍不通,母亲称其为“大松心”[9]3-14,后来又长期养病,对家事和亲人有所忽略,《亡人逸事》和不少回忆亲人的随笔,透过平淡的语言,能感觉到其内心的隐痛。然而从晚年他与邢海潮的通信看,孙犁对需要帮助的人,竟能如此细心周到、体贴入微。1994年10月10日,他给邢海潮信说,“收到来信,知兄冬季取暖,已准备就绪,甚慰”[6]568,而那时,他自己刚刚经历大病,做了胃部切除手术后不久。邢海潮对孙犁“数年以来不以庸樗见弃”,“多方诱掖慰勉,奖饰荐拔,并惠寄书册现金,抬爱优渥”,十分感激,多次在信中发自肺腑说:“兄实乃弟晚年之最大支柱也。”[8]159对于赵县有关人士托邢向孙犁求书求字,孙犁总是毫不犹豫慷慨满足,给这位晚景凄凉的老同学以切实的帮助。他对邢始终很尊重,写信一直称“海潮学兄”,落款则署“弟犁”,字里行间,热忱和仗义可掬。看到邢海潮信纸粗劣,孙犁还时常给他寄一些好稿纸。邢那些“来自一个县城粗糙简易的信封信纸”,孙犁都“将所有来信平平整整按时间顺序捆扎有序仔细保存”,与之对照的是,“许多名气甚大的作家、编辑约稿信,他并不保存。冬天点炉火用了,一捆捆的”[8]159。孙犁常说,他只愿雪中送炭,不喜锦上添花。与邢海潮书信交往,体现了孙犁这一性情。
二、友直友谅
孙犁经常感喟,“少年时的同学,在感情上,真有点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的味道”[10]67。《小同窗》就写他与初中同窗、终身好友李之琏之间几十年的手足情:他们十四岁时在保定育德中学同班,“后来我休学一年,关系还是很好……李长得漂亮,性格温和,我好和这样的人交朋友”[10]66。后来,李之琏上了北平的法商学院,孙犁升了高中;再后来,李入狱,孙犁正在北平谋生,他“胆小,没有到过这些地方,约了一位姓黄的同学,一同去看他”。隔着一个小小的窗口,孙犁“和他谈了几句话。我看到他的衣服很脏。他平日是很讲究穿着的。我心里很难过,他也几乎流下了泪”。抗战开始,李之琏任吕正操人民自卫军民运部长,孙犁被他动员参加了部队,“因为有他,我出来抗日,父亲的疑虑就减少了。我是独生子”[10]6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李由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升任中宣部秘书长,1958年,“因为替一个作家(按:指丁玲),说了几句话,一下就成了右派。先是下放劳动,后来就流放到新疆石河子去了”。
临行前,他到天津来了一趟。我给他一些钱作为路费,另外送他两本书:一是《纪氏五种》,其中有关于新疆的笔记。一是《聊斋志异》,为想叫他读来解闷儿的。他说,“聊斋,你留着看吧。”[10]68
平反后李之琏当了中纪委常委,照片和国家领导人排在一起,孙犁自豪地说:“这在过去,就是左都御史!”可李仍然保持朴素作风,一次到天津公干,不乘专车,带着天津当地司机去看孙犁,“那一顿饭,我只是应酬司机,也没有很好照顾他”。孙犁跟李抱怨社会风气,李之琏并不反驳他,只笑了笑说:“哪里都一样。”[10]681956年孙犁大病,住医院、到各地疗养,都是李之琏安排的。他“私下里询问天津的熟人,问我的病是怎样得的。被询问的人说,是夫妻不和,他就说,那样就不必叫他的爱人来看他了。后来又听人说,我和妻子感情很好,他又笑着说,那就叫她常常来看看他吧”[10]69。孙犁淡笔白描,人物性情跃然纸上。
孙犁晚年随笔,好用“君子”一词。他念兹在兹、保持终身友谊的旧友,都有君子人格。曾与孙犁在晋察冀通讯社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老战友陈肇,后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家徒四壁”,“从不伸手,更不邀功。知命知足,与世无争。身处繁华,如一老农。辛勤从政,默默一生”,他“就连公家的信纸、信封都不用,每次来信,都是自己用旧纸糊的信封”。陈肇多才多艺,诗文、书画、音乐兼通,却“从不自炫,不大为人知道”。“有一次,我想托他在故宫裱张画,又有一次,想摘故宫一个石榴做种子。一想到他的为人,是一尘不染,都未敢张口。”[11]13-16
孔子曾告诫,交友应“友直,友谅,友多闻”,孙犁认为其中“直”最可贵,而“谅”则不易。他记述一件事,由此可看到陈肇这位谦谦君子的“谅”:
1962年夏天,我去北京,住在椎把胡同的河北办事处。一天下午,我与一个原在青岛工作、当时在北京的女同志,约好去逛景山公园。我先到景山前街的公共汽车站去等她。在那里,正好碰上从故宫博物院徒步出来的陈肇。他说:
“我来看你,你怎么站在这里?”
我说等一个人。他就站在路边和我说话。我看见他的衬衣领子破了,已经补上。
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注意停下来的公共汽车,下来的乘客。他忽然问:
“你等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是女的。他停一下说:
“那我就改日再到你那里去吧!”
说完,他告别走了。我一回头,我等待的那位女同志,正在不远的地方站着。
这戏剧性的一幕,在极简的语言中跃然纸上,陈肇的宽厚体谅,可触可感。孙犁自省道:“在对待朋友上,我一直自认,远不能和陈肇相比。在能体谅人、原谅人方面,我和他的差距就更大了。”[11]14
1978年,孙犁在《吃粥的故事》中写过他和诗人曼晴在晋察冀时期的艰苦生活。1989年,曼晴因病去世,孙犁写《悼曼晴》,再次忆及1940年冬季反扫荡时二人的结伴辗转——在荒凉而恐怖的山沟里,“我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游而不击,‘流窜’在这一带的山头、山谷”,在危险的饥饿和寒冷中,两人竟写了两篇通讯,和一些“浪漫蒂克情调的诗和小说”[12]31。曼晴性情像农民,“文革”后在石家庄文联,埋头兢兢业业编一份“土里土气的刊物《滹沱河畔》”,孙犁把一些诗作寄给他,他不喜欢,给《孙犁诗选》作序时,也直言不讳批评。他作诗也一直没有走红,“晚年才出版了一本诗集,约几个老朋友座谈了一下,他已经很是兴奋”。退休时他的头衔只是地区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比起显赫的战友,是显得寒酸了一些。但人们都知道,曼晴是从来不计较这些的。他为之奋斗的是诗,不是官位”[12]32。孙犁交友,“向如萍水相逢,自然相结”;“对显贵者,有意稍逊避之,对失意者,亦不轻易加惠于人。遵淡如水之义,以求两无伤损”[12]34。
孙犁在晚年,来了客人,就送人两本书:一本是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一本是虚构之名的纪实小品《芸斋小说》。他说,“我的生活,全在这两本书里,从中你可以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包括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兴衰、成败,及其因果。”[13]68这一微言大义,是我们理解孙犁精神世界的关键。而李之琏、陈肇和曼晴等,正构成了《风云初记》的底色。
三、和而不同
孙犁忆旧散文中还有一类人物,共事久、彼此非常熟悉,一同经历坎坷、见证历史,孙犁对其性格和命运有深刻印象,因此,对他们的书写,也成为孙犁反省历史、回味人生的一种方式。《记邹明》《记老邵》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进城”以后,孙犁一直在《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任编辑,级别为副科,手下只有一个兵,就是邹明。1956年孙犁外出养病,不久邹明被送农村劳改,这对搭档,在“文革”结束后,才又重新一起工作。邹明是福建人,与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因为爱好文艺,从而走上了革命征途”,“为此,不少人曾付出各式各样的代价,有些人也因此在不同程度上误了自身。幸运者少,悲剧者多”[14]43。孙犁认为邹明属于后者。在单位,孙犁和邹明是一对奇特的组合。他们性情本不相同,邹明喜欢洋玩意,爱看毁禁书,脾气不好,对孙犁倒尊重。他们也有一些相通之处,如处事淡泊,尊重作者,敬业,无野心,不投机等,因此一生“官运也不亨通”[14]42。但在他们的开垦下,《文艺周刊》在五六十年代成为青年作家成长的摇篮,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都从这里起步和成名。邹明被人们视为孙犁的“嫡系”,其实二人很少交心,关系也淡淡的。但孙犁信任邹明,其私人印章、样稿等,都交邹明保管[15]86。孙犁写了东西也爱拿给邹明看,而邹明“总是说好,没有提过反对的意见”。孙犁晚年自省:“他对文、对事、对人,意见并不和我完全相同。他所以不提反对意见,是在他的印象里,我可能是个听不进批评的人。这怨自己道德修养不够,不能怪他。”[14]39-401958年,当孙犁在外地疗养时,邹明被打成反党分子,罪状是《文艺周刊》发表右派分子从维熙、刘绍棠及胡风分子鲁藜等的作品[15]86-87。有一次,孙犁妻子看见邹明拿着刨子从工作间出来(劳动改造),心疼得要流泪。“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孙妻在公共汽车上遇到邹明,像遇见亲人似的“流着泪向他诉说家里的遭遇,邹明却大笑起来,她回来向我表示不理解”。
我向她解释说,你这是古时所谓妇人之恩,浅薄之见。你在汽车上,向他谈论这些事,他不笑,还能跟着你哭吗? 我也有这个经验。1953年,我去安国下乡,看望了胡家干娘。她向我诉说了土改以后的生活,我当时也是大笑。后来觉得在老人面前,这样笑不好,可当时也没有别的方式来表示[14]37。
1989年秋当邹明被诊断出癌症后,孙犁心情沉重,十分挂念。10月14日,他在《史记》包书皮上记下:“邹明脑中取出肿瘤二,手术顺利良好,系脑系科王主任所做,老鲁所托也。手术时,老于一直在场,照顾周到。现邹明语言清晰,可慰也。”随后又补一行:“疾病无常,邹明发病前一日,尚在和面做饭。”[16]236他与邹明之间,在平淡如水的交往中,实际有了一种生命的联系,对方已构成自己历史的一部分。“回顾四十年的交往,虽说不上深交,也算是互相了解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我们之间,初交以淡,后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他不顺利时,我不在家。‘文革’期间,他已不在报社。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进行批判。也没有发现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对我进行侮辱攻击。这就是很不容易,值得纪念的了。”[14]41
孙犁自言其年轻时写作,顾虑较多,比较谨慎。到晚年,则率性直言。《记老邵》写报社总编辑老邵,颇有《史记》风韵。
老邵是孙犁进城后的同事,直率而有些刚愎,“想做官,能做官,会做官”,既有行政能力和业务能力,同时也享受官威。
老邵在任上,是很威风的,人们都怕他。据说,他当通讯部长的时候,如果和两个科长商量稿件,就从来不是拿着稿子,走到他们那里去;而是坐在办公桌前,呼唤他们的名字,叫他们过来。升任总编以后,那派头就更大了。报社新盖了五层大楼,宿舍距大楼,步行不过五分钟,他上下班,总是坐卧车……老邵的办公室,铺着大红地毯,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编辑记者的骨干,都是他这些年亲手训练出来的那批学生。据说,一听到走廊里老邵的脚步声,都极速各归本位,屏息肃然起来。[17]61
寥寥几笔,就把老邵的性格勾勒出来。在孙犁看来,老邵人生的沉浮,并非关乎其能力,而与“上面”人事关系更大。五十年代中后期,老邵被革职下放,“文革”中惨遭批斗。这次批斗,显露了老邵刚强正直的一面。“有一天晚上,报社又开批斗会,我和一些人,低头弯腰在前面站着,忽然听到了老邵回答问题的声音。那声音,还是那么响亮、干脆,并带有一些上海滩的韵味。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回答,完全不像批斗会上的那种单方认输的样子,而是像在自由讲坛上,那么理直气壮。”这个态度,招来拳打脚踢,“会场烟尘腾起,噼啪之声不断”,“老邵一直紧闭着嘴,一言不发”。“文革”后,老邵曾患半身不遂,康复不久,想再回报社做点事情,并责备孙犁软弱,写文章不敢批评社会现实。1990年老邵去世,留下的遗嘱是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孙犁在文末点评道:“老邵为人,心直口快,恃才傲物,一生人缘不太好。但工作负责严谨,在新闻界颇有名望,其所培养,不少报界英才。我谈不上对他有所了解。但近年他多次罔顾,相对以坦诚。他的逝世,使我黯然神伤,并愿意写点印象云。”[17]59-64这些随笔,无论内涵还是细节,都不输于任何小说,堪称当代文学精品。
四、秉笔直书
被孙犁冠以虚构之名的“芸斋小说”,实是纪实,这一点他在不少场合都提到。1989 年写的《罗汉松》,主人公老张,实是其老同事王林。王林的革命资历和创作生涯都比孙犁老,1933年孙犁向《大公报》投稿时,王林已在包括该报在内的报刊发表短篇小说数篇,193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幽辟的陈庄》。“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王林都是见证人和参与者,还创作了表现西安事变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和《火山口上》。1938年孙犁加入人民自卫军时,王林已任火线剧社社长和冀中文建会副主任,孙犁《〈善闇室纪年〉摘抄》记载,他1937年“识王林于子文街头,王曾发表作品于《大公报文艺》,正在子文街上张贴广告,招募剧团团员”[9]5。自此,二人一直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和领域,王林主持《冀中一日》征文,请孙犁来帮助编选。土改时王林任组长,曾对孙犁“搬石头”。新中国成立后王林和孙犁同住天津,交往颇多,王林日记中有关孙犁的记载,有二百七十余处共十万余字[18],而孙犁不同时期的文章中,也经常见到王林的名字。
小说描述老张,“以他的资历,本来有许多机会去做大官,他都没有去做……终于以作家身份,了其一生”[19]2。王林不同于陈肇、曼晴,他带匪气,有些油滑,故小说写道:“他不愿到山里去,那里生活太苦……他打游击,不避阶级嫌疑,常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这些人家,都有子女在外抗日。他到一家,大伯、大娘叫得很亲热,既保险,又能吃到好饭食。他有时住在我家,我父亲总要到集上去买肉。”“老张的口福,是有名的。抗日期间,我从路西回来,帮他编书(按:指《冀中一日》)。他们一天的菜金是五分,我是客人,三角,他就提出跟我合伙。……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父亲给我炖了一个肘子,刚刚炖烂,他就从外村赶来了,进屋大笑着说:‘我在八里以外,就闻到香味了。’”“进城以后,他是市长的老朋友,经常赴宴。打听哪里有宴会,只要主客一方是熟人,他就跑去。”[19]3孙犁对这类生活细节不厌其烦地描写,有其原因。孙犁父亲非常节俭,原做掌柜,抗战爆发被辞回家,“带着一家人东奔西跑,饭食也跟不上……舍不得吃些好的,身体就不行了”[20]108。而王林大大咧咧,缺乏体谅。“有一次,他(按:指老张)到路西去,父亲托他带给我一些零用钱,还叫妻子把钱缝在他的夹袄腋下。他到了路西,我已去了延安,他把钱也买了书。”[19]3近年披露的王林日记,可印证《罗汉松》的纪实性;而“老张”的到处蹭宴会,与“三年自然灾害”饥饿有关,而那时孙犁正在各地疗养。《罗汉松》对生活小事的斤斤计较,可理解为小说细节描写的需要;孙犁对王林最大的不满,是处世态度上。“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以老运动员,或称老油条的功夫,顺利通过。土改时,他是组长,当然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机立断,以‘左’派姿态,批评了市文教委书记。在那样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他一改平日的邋邋遢遢的形象,穿上一件时兴的浅色的确良的衬衣,举止活泼,充满朝气,以自别于那些忧心忡忡垂头丧气的人物。”[19]4孙与王,个性迥异,处事风格南辕北辙。孙犁另一篇文章说,“西安事变时,我有一位朋友,写了一个剧本,演出后,自己又用化名写了长篇通讯,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对剧本和演出大加吹捧。抗战时,我们闲谈,有人问他:你怎么自吹自擂呢? 他很自然地回答:因为没有别人给宣传!”[21]56这位自吹自擂的朋友,应是王林。孙犁拘谨、自律、敏感,王林不拘小节、左右逢源,孙犁对其“不仅游戏人生,亦且游戏政治”[19]5的做法,无法接受。小说写老张对于权势者,“他可以当着很多人的面,去拍他们的马匹,插科打诨,旁若无人”[19]4。资历和见识比这些新贵高、而并不追求官位的“老张”,确实是以喜剧的姿态游戏人生。其“老油条”状有几分像王蒙笔下的“刘世吾”。“当不少同行家破人亡之际,他的家庭,竟能保持钟篪不移、庙貌未改的状态,这在全国也恐怕是少见的。”[19]5如何评价王林,孙犁也感到不好拿捏,故文末 “芸斋主人曰:相交过久,印象丛脞,不易下笔”[19]3。这篇小说或许有偏见,但所提供的生动细节,却揭示了王林性格和行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于认识革命队伍中另一种知识分子,颇有意义。孙犁对其政治漩涡中“善泳”的感受,对理解王林几十年修改《腹地》过程中为迎合政治而逐渐丧失自我、丧失文学创造能力的悲剧性命运,也提供了参照。
孙犁有道德洁癖。他承认,“我有洁癖,真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意写进我的作品。……一些人进入我的作品,虽然我批评或讽刺了他的一些方面,但我对他们仍然是有感情的,有时还是很依恋的……”[22]78因此,他的尖锐讽刺,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历史体验与感情的。看王林在“文革”时期对孙犁的“揭发”,并未罗织,基本忠于事实——
孙犁也不喜欢广交,以前感情好的,一直保持友情。以前谈不到一起的,永远格格不入。不以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用超阶级的友谊挂帅……
我觉得孙犁对工作,不论是通过组织,或是为工作需要临时拉夫,孙犁都是勤勤恳恳,尽力而为之的。可是总是“同路人”的心情,也就是“四旧”中的“为朋友谋而不忠乎?”的帮忙态度,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向来不高……
孙犁跟周扬、林默涵等文艺黑线头子们的关系如何呢? 据我所见到的,他们来到天津倒是主动找孙犁见见面、谈谈。可是孙犁对这种事能推就推。即便去了,也感到是一种痛苦,还不如到水上公园去钓鱼愉快。[23]131-132
那些充满时代特色的“帽子”,多属性质并不严重的“四旧”,且在涉及与周扬、林默涵的关系时,王用揭发的口吻为孙犁撇清,其“老油条”外形内的真诚正直,可见一斑。
1991年1月15日,与孙犁相识半个世纪、曾经十分亲密的老友康濯在北京病逝。
从感情上说,康濯一度与孙犁“情同手足”,“从1939年春季和康濯认识,到1944年春季,我离开晋察冀边区,五年时间,我们差不多是朝夕相处的”。二人切磋写作,有许多共同语言。康濯对孙犁的作品非常珍惜,孙犁回忆说,“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晋察冀文艺》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给了我,我却不拿着值重,又都糟蹋了”[24]18。1956年,孙犁晕倒,病情一度严重,康濯怕他从此不起,特意将其作品编选为《白洋淀纪事》付梓。二人的通信,孙犁写给康濯的,都被康濯完好保存;而康濯给孙犁的,却在“文革”抄家时被孙家为避祸而烧毁,孙犁“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他”[24]18。
1950年代初,康濯政治地位擢升,1954年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1955年8月,作协党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孙犁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大家都很紧张。小组会上确定谁去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最后,孙犁称病推辞,中宣部一位负责人(林默涵)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25]62孙犁如蒙大赦。而彼时,康濯正处于“两条路线斗争”的抉择中,他曾在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担任副秘书长。会前,他审时度势做了检讨,会上,他表现也较积极。“大跃进”期间,他写紧跟形势的“放卫星”的作品。孙犁虽一直珍视与康濯的友情,但自康濯当官以后,他便与之疏远起来。“我们来往少了,也很少通信,有时康濯对天津去的人说:回去告诉孙犁给我写信,明信片也好。但我很少给他写信,总觉得没话可说,乏善可述。”《芸斋书简》中孙犁1946至1954年间致康濯信有七十多封,1954年后戛然而止。晚年孙犁文集中偶见致康濯的零星短简,也属礼节性答问。对孙犁而言,他和康濯之间的“相濡相忘”,皆“时势使然”[24]19。他自言“自幼腼腆,怕见官长。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见了官长,总是躲着。如果是在会场里,就离得远些,散会就赶紧走开”[26]57,这与王林交代材料所说相符,据说是受其父亲影响[23]132。不过,康濯逝世的消息传来后,孙犁尘封心底的感情汹涌起来,很少流泪的他,眼里含满了泪水,当即写下《悼康濯》一文。康濯腾达时他疏远,康濯倒霉后他不投石。在这篇悼念文章中,他客观写道:“康濯很聪明,很活跃,有办事能力,也能团结人,那时就受到沙可夫、田间同志等领导人的重视,他在组织工作上的才能,以后也为周扬、丁玲等同志所赏识。”[24]17“他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那时的创作,现在,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像李延寿说的: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是不寻常的。它是当国家危亡之际,一代青年志士的献身之作,将与民族解放斗争史光辉永存。”[24]18没有通常悼文的虚矫和夸张,且不回避谈康濯后来的过失:
至于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24]19
在几十年来“齐声”歌颂或声讨的文坛,孙犁这一姿态,实在难能可贵。
孙犁晚期写作,虽皆短文随笔、寻常人物,但那些熔铸了作者生命和情感的沧桑历史,回味弥久,滋味愈浓。他秉笔直书,徐徐道来,展现的就是一幅鲜活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