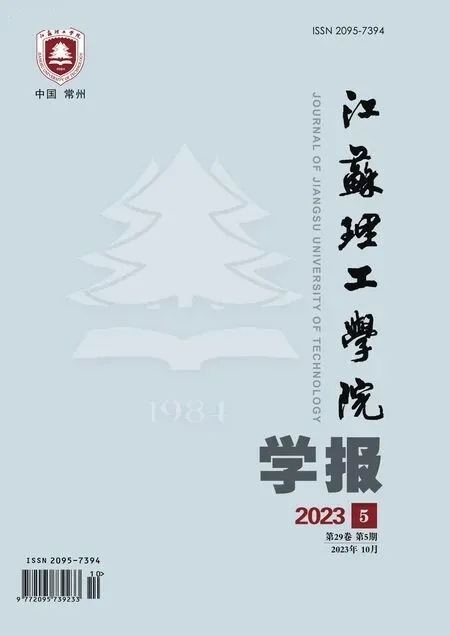《恶棍来访》中的隐喻叙事
杨艳
(江苏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
美国女作家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1962—)从1995年发表第一部小说《看不见的马戏团》(The Invisible Circus)至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共出版过6 部长篇小说,其中《恶棍来访》(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2010)获得了包括普利策长篇小说奖、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在内的美国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伊根本人也一跃成为美国文坛最炙手可热的作家之一。《恶棍来访》以唱片制作人本尼及其女助手萨莎为核心人物,讲述了一群摇滚音乐人近50年的人生历程。普利策奖评委会评曰:“这部小说对数字时代人们的成长与衰老进行了极具创造力的探究,展现了人们对文化急剧变迁的强烈好奇心。”[1]
珍妮弗·伊根这个名字并不为国内读者所熟知,国内学界对其作品《恶棍来访》的研究也相对较少,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为小说获奖后的推介,以作者生平以及小说情节和创作手法介绍为主;其二为小说中的创伤叙事研究,如薛玉凤[2]以小说中患有偷窃癖的萨莎为例,分析其偷窃行为背后的童年创伤,并从“接纳与承诺疗法”三重自我理论入手把握萨莎对自我的追寻;其三为小说中的后现代叙事策略研究,如陈艳红[3]从非线性叙事、不确定性、元小说和黑色幽默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后现代叙事策略在小说中的运用,强调小说的叙事形式对主题思想表达的助益。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虽注意到了小说对隐喻的使用,如小说标题中的“恶棍”,“在书中隐喻为摧残人性、毁灭人生的无形外力,比如时间”[4]142,但尚未有研究该小说中隐喻叙事的篇什。
一、隐喻的内涵
隐喻是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隐喻研究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隐喻是指用一个词替代另一个词,以达到修饰语言、增强语言效果的目的。之后学界对隐喻的研究基本都在语词层面上进行。直到20 世纪30 年代理查兹的《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Rhetoric,1936)面世,隐喻的研究才开始转向语义层面。在当代,隐喻研究的重点在认知层面。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1980)开篇就明确了隐喻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上,日常生活中隐喻无处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体系本身就是以隐喻为基础的”[5]1。莱考夫等强调隐喻是人类的思维方式,将隐喻划分为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三种[5],并用“始域源”(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替代传统隐喻研究的喻体和本体,将由始域源向目标域的互动称为“映射”(mapping)[6]。
既然隐喻是人类的思维方式,那么隐喻思维当然也贯穿了小说创作的全过程,但“隐喻的微观研究不足以展示隐喻化思维与话语叙事的全貌,只有跳出语词的樊篱,才能更清楚地了解隐喻的语篇功能,从而更好地理解隐喻与叙事的关系”[7]17。小说中的隐喻叙事,“一般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把作者的写作思路、写作意图渗透在叙事安排和展开过程中”[8]103。因此,本文拟从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和小说结构三方面分析隐喻与小说叙事的关系,探讨隐喻叙事对小说文本意义构建的作用。
二、本体隐喻:表达小说主题
莱考夫等人认为,所谓本体隐喻是以自然物体(特别是我们的身体)的经验为基础,“把事件、活动、情感、想法等看成实体和物质的方式”[5]23,如“大脑是机器”[5]27。《恶棍来访》正是基于本体隐喻提出并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相关研究大多认为,该小说体现了作者对时间和人生主题的思考[4][9-10]。本体隐喻“时间是恶棍”[11]141,356在小说中直接出现过两次,小说的标题“恶棍来了”也是“时间是恶棍”的延伸。时间被实体化,始源域“恶棍”身上凶恶、蛮横、胡作非为的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时间”上,强调时间如恶棍般夺走生命里的一切:青春、爱情、友情、梦想……,任何企图对抗时间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故事里的每位人物都被时间这个恶棍所“造访”。在小说核心人物之一萨莎以及以她为中心辐射出的多个人物,如舅舅泰德、大学时的男友、现在的丈夫德鲁、相亲对象阿历克斯等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对个体的影响,时间于他们来说意味着挑战和希望,他们无所顾忌地释放着自己的渴望,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挫折。另一个核心人物本尼是美国70年代摇滚音乐人的代表,小说以他为中心辐射出更多命运迥异的音乐人:当年叱咤乐坛的卢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一起组建乐队的主唱斯科蒂早已放弃音乐,一起创办唱片公司发掘摇滚乐人的前妻斯蒂芬妮也成了家庭主妇……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变迁中摇滚音乐产业的兴衰以及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焦虑境况[12]。
生命本是一种无形的状态,但在《恶棍来访》中被隐喻为不同的实体,它们的形态和变化隐喻了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态。小说第一章《寻回之物》曾作为短篇小说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三十五岁的萨莎向心理医生倾诉自己的偷窃癖,她总是控制不住偷窃的欲望,公寓的桌子上堆满了她偷来的小物件。萨莎清晰地记得每一件偷窃来的物品的来历,它们浓缩了她过去数年的生活,承载着她的人生,她一方面为自己这种行为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需要改变和救赎。她将偷窃来的东西与自己的物品分开存放,设想有一天将它们一一归还,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然而第一章的最后,萨莎仍旧处在一种割裂的状态:渴望救赎却又安于现状,唯有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第二章《金箔疗法》中,人到中年的本尼靠所谓的金箔疗法来为自己的身心注入活力。他在咖啡里加入金箔,看着金箔在水中快速旋转,坚信“这是金箔——咖啡发生化学反应的明证”[11]24。这里,小小的金箔被认为包含着生命的活力,是当下本尼精力的来源,寄托着他的全部希望,时间带走了他的青春、梦想、爱情、家庭,他只能依靠金箔做着无效抗争。
容器隐喻是本体隐喻的一种。莱考夫等人认为,容器隐喻的经验基础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就是一个以皮肤为界限,有里外之分的实体容器[5]27。容器隐喻以容器这一空间性实体为始源域,映射其他非空间性的目标域。在小说第七章中,老迈多病的吉他手博斯克明知自己病入膏肓,仍然想举行全国巡回演出,哪怕是一次自杀式巡演。他说:“过二十年,你再也不会神采奕奕,尤其是身体里的许多东西都被拿走了后。时间是恶棍。”[11]141这里身体被隐喻为容器,“身体里的许多东西都被拿走”,鲜明地呈现出容器图式的基本框架,即里——外——边界,博斯克生命的活力被时间从身体(容器)中夺走,他的人生也即将走到尽头。在小说第十三章中,斯科蒂因怯场不敢登台,在阿历克斯看来,斯科蒂“就是徒有人形的一个字壳:外壳的精华已消失殆尽”[11]]356。同样,这里人的身体被视为一个容器,斯科蒂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精气神,只剩下一个人形的外壳,一个空洞的容器。
三、路径隐喻:塑造人物形象
路径图式是人类最重要的意象图式之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目的是终点”是人类最重要的基本隐喻之一。目的地是目标,方式是路径。实现了某个目的,就是到达了路径的终点。此隐喻帮助我们将很多抽象的目的都视为一段路程的终点,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基本隐喻,如“生命是旅程”“职业是道路”等。《恶棍来访》故事始于20世纪70年代,结束于2020年左右,时间跨度约50年。生命于小说人物来说就是一段旅程,从旧金山到纽约,一群怀揣梦想的摇滚青年经历梦想的破灭、爱情的消失、事业的挫败,最终来到孤独平庸的中年,直面身体的衰老以及最终的死亡——每个人的人生终点。
路径隐喻实际上既有方向维度又有时间维度,但特纳曾强调,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一个物理的空间里,对空间十分熟悉,所以人们常以可具体化的空间概念去理解其他模糊抽象的非空间概念,如时间[13]51。因此,我们可以基于人物所处的物理空间(方向维度)来把握时间维度,进而梳理出人物不同的人生轨迹和迥异的内心状态。比如萨莎,少年时曾与一位乐队成员私奔去过东京、香港;被抛弃后,独自一人去了中国大陆、摩洛哥,最后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靠偷窃、帮人打扫卫生,甚至出卖身体谋生;被舅舅找到之后,她返回美国读大学;毕业后在纽约为音乐制作人本尼工作,直至因偷窃被解雇;之后萨莎与大学男友恢复联系,与他结婚,最后在加州靠近沙漠地带定居。从亚洲到欧洲再回到美国,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萨莎的前半生,“生命是旅程”,物理空间的每一次变动都指向她人生旅程中的一个新的“站点”,同时“状态是地点”。“站点”(地点)又意味着她心态性格的变化:年少时的随心所欲,放荡不羁;成年后的回归常态,改过自新;再经历消极无为,安于现状;最后终于找回自我,积极生活。再如本尼,少年时转学到旧金山的高中,与斯科蒂等人一起组建了“燃烧的迪豆”乐队,四处寻求演出的机会;成年后混迹于纽约下东区,在曼哈顿成立猪耳唱片公司,成功与多个摇滚乐队合作;婚后全家搬到富人区克兰黛儿,想方设法融入当地的俱乐部;出轨邻居,与妻子离婚,搬离克兰黛儿,事业一落千丈,制作的音乐也渐渐无人问津……从旧金山到纽约,本尼的生命旅程里,他曾努力爬上巅峰,后又跌落至谷底,成功时志得意满,失败时颓废郁闷,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西班牙裔美国人的美国梦的实现与幻灭。
此外,小说人物也直接借助路径隐喻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形成了人物的性格差异。如第一章《寻回之物》中,萨莎认为:“整间公寓六年前看上去只是通往某个好去处的小驿站,结果却在萨莎的周围变得愈益坚不可摧,块头变大,体重大增,终于使她觉得既身陷其间又很庆幸自己还有这个房子——好像她不仅没法继续前行,甚至还想都不愿去想了。”[11]15此时萨莎正为自己的偷窃癖所扰,虽已向心理医生求助,但病情似乎并无进展。纽约这间小公寓本是她人生路上短暂的逗留之所,如今变成了一种桎梏,萨莎深陷其中,无法也不愿继续向前,她开始安于现状,甚至庆幸人生中有这样的一处所在。又如第七章中,本尼搬到富人区克兰黛儿后,格外重视居所中的一切,一点点打造房间里的装饰细节。对于本尼来说,房子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家是生活的必需品,可以遮风挡雨,所以“他每次取出钥匙打开房门时都会满怀敬畏之感”[11]37;另一方面,家是埋葬人们生命和精神的坟墓,所以他坚持,“想死在这里”[11]130。将“家”与“坟墓”并置并非作者的原创,而是人们惯常的认知习惯,房子是人生前的居所,坟墓是人死后的居所。坟墓又指向死亡,隐喻人生旅程的终点。此时的本尼事业成功,家庭幸福,摆脱了之前贫困糜烂的“往昔岁月”[11]146,在高档社区安了家,他想永远保有这样的生活,直至生命最后的终结,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但也可看到,“往昔岁月”里“如果他们不喜欢结果,那么他们就会跑回去,从头再来”[11]146的勇气已然被功成名就后的生活消磨殆尽。
四、循环图式隐喻:构架小说结构
约翰逊认为,循环主要有两种形态:第一,类似于一个圆的循环状态,意味着对最初状态的回归;第二,是一个正弦波的循环状态,有周期性的升高或降低,最终又回到水平线。循环图式是人类关于经验和理解世界的最基本图式之一,提供了一种在大范围内理解事件顺序的方式[14]119。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将四季的循环引入对叙事结构的论述中,充分肯定了循环在作品思想表达上的意义[15]。
伊根在接受采访时,曾声称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HBO上演的《黑道家族》。在小说的扉页上,作者引用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三部《盖尔芒特家那边》中的句子:“诗人们声称,当我们回到年轻时生活过的一幢房子、一座花园,可以暂时找回曾经的自己。这种故地重游全凭运气,成功与失望参半。时过境迁,那些不变的地方,最好到我们内心去寻找。”[11]1这里的“找回曾经的自己”和“故地重游”暗示了循环,作者以这段引语开篇,意味着小说从开头就确立起“回归”之意,为循环图式提供了文本依据。
小说共十三章,分为A、B两个部分,A部分由六章组成,B部分由七章组成。十三个章节中的故事情节相对独立,故事时间的顺序也被打破,构建了一个碎片化的文本世界。有研究把小说的非线性叙述归因于现代媒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16],或认为是后现代叙事的表征[3]。然而从隐喻视角出发,可以发现整部小说的布局在很大程度是基于约翰逊循环图式的第一种形态——圆形状态。
首先,小说章节标题的设计颇具巧思,A 部分六章的标题分别为:《寻回之物》《金箔疗法》《我才不管呢》《野游》《你们(复数)》和《X’s 和O’s》;B部分七章的标题分别为:《A 到B》《把将军销售出去》《四十分钟午餐:吉蒂·杰克逊对爱情、名誉和尼克松侃侃而谈》《身外之物》《再见,我的爱》《了不起的摇滚乐休止符》《纯粹的语言》。A 和B 两个部分犹如“黑胶唱片的两面”[17]79,A 部分结束,B部分开始的第一章(即小说第七章)被直接被命名为《A 到B》,仿若播放时唱片被翻面,暗示新乐章的开启。
其次,循环图式隐喻帮助构架了小说结构,投射了作者开篇引文中的立意,以达到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小说各章节故事相对独立,前章节的人物在后章节中会再次出现,以小说A部分为例,第一章中的主要人物萨莎在第二章中年本尼的故事中再次出场;第三章故事时间跳转到本尼的中学时期,瑞娅用第一人称讲述自己和乔瑟琳对摇滚音乐人卢的痴迷;第四章则转到卢带着女友和儿女一起去非洲旅行;第五章时间又推进到20 年后,乔瑟琳和瑞娅去探望弥留之际的卢;第六章中早已放弃音乐的斯科蒂去拜访彼时正意气风发的青年本尼。这类似于读者在网页浏览时遇到的超链接,只需点击这个超链接,就进入相关的新页面,依次类推层层打开。小说的最后一章《纯粹的语言》中,第一章曾出现过的阿历克斯第二次出现,他无意间与本尼聊起了萨莎,阿利克斯提到了两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本尼也说到萨莎手脚不干净并因此解雇了她,这里“点击”萨莎又可以回到第一章继续阅读关于萨莎与阿利克斯的会面以及萨莎的偷窃癖,从而完成了从B 又回到A 的循环。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结构安排会打破从头至尾单向式的阅读顺序,读者可随意挑选阅读的起始章节,在提供一种新的阅读体验的同时,也吻合了约翰逊循环图式的圆形状态中每一阶段地位相同这一基本特征。
五、结语
《恶棍来访》赋予了隐喻重要的地位,隐喻叙事成为其表达主题意义、塑造人物形象和构建叙事结构的重要手段。小说借助包括容器隐喻在内的本体隐喻表达时间的残酷以及人物反抗的徒劳等方面的主题;借助路径隐喻塑造了不同人生轨迹、内心状态和性格的人物形象;借助循环图式隐喻构建起小说圆形叙事结构,为读者提供新的阅读体验。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言,隐喻无处不在,隐喻是人类的思维方式。从隐喻视角审视小说《恶棍来访》,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作者在主题、人物和结构中体现的隐喻思维,也有助于我们把握隐喻叙事对小说文本意义构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