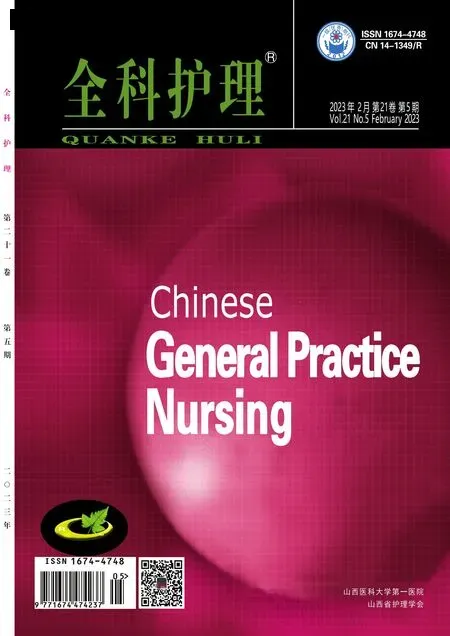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研究进展
李雅慧,金瑞华
头颈癌(neck and head cancer,NHC)临床上以喉癌与鼻咽癌常见。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头颈癌病人生存率越来越高。头颈癌病人以手术治疗为主,而头颈部是身体暴露在外较多的部位,疾病的治疗不仅使病人的容貌发生改变,还会进一步影响病人的各方面健康和生活质量[1],这些负面影响可能导致病人身体、心理和社会受损[2]。然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消极事件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一些积极作用。1983年Taylor[3]提出了益处发现的概念,在他们看来,益处发现是指个体应对重大变故或消极生活事件时所产生的积极变化,表现为一种认知及行为上的积极应对。自此,国外学者研究发现,癌症等创伤性事件可使病人产生一定积极正向的改变,如创伤后成长(post traumatic growth,PTG)、益处发现(benefit finding,BF)等[3]。我国已有学者对乳腺癌[4]、结直肠癌[5]、食管癌[6]等疾病病人进行了这方面的相关研究,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对头颈癌病人的益处发现进行探讨,因此本文对国内外关于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头颈癌病人的心理护理提供参考。
1 益处发现
1.1 益处发现的概念 Taylor等[3]认为益处发现是指个体在面对消极生活事件时所产生的积极应对。2004年Tedeschi等[7]指出,益处发现是指当处在消极事件中时,人们把寻找其中的益处作为应对痛苦的措施,用以促进适应消极情景。虽然各位学者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其中的共性是消极事件可以对人有积极的作用。
1.2 国内外益处发现研究现状 国内外大多数关于益处发现的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乳腺癌病人,通常来讲,乳腺癌病人相较于其他癌症病人而言有更高的生存率[8],且乳腺癌病人益处发现发生率为53%~83%[9]。同样,在前列腺癌[10]、良性脑膜瘤[11]、患有癌症的青少年[12]中也发现了中到高水平的益处发现。对于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的研究不多,但国外一项研究表示,从诊断开始到治疗后6个月[13]头颈癌病人的益处发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可能发生得相对较晚。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和社会关系、癌症的分期和所接受的治疗方式等。
2 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的测量工具
2.1 益处发现量表 最初由Antoni等[14]于2001年针对乳腺癌病人编制,该量表共17个条目,内容效度评价表采用Likert 4级评分。不相关计1分;需进一步修改方可确定计2分;相关,但需要稍作修改计3分;非常相关计4分。经国外研究者验证,该量表信效度良好。
刘谆谆等[15]对益处发现量表进行汉化,汉化后的益处发现量表包括22个条目,每个条目都以“患癌症(从诊断至今这段经历)……”对病人提出设问,汉化后的量表由6个维度组成,各维度及相关条目分别为接受维度(条目1~条目3)、家庭关系维度(条目4、条目5)、世界观维度(条目6~条目9)、个人成长维度(条目10~条目16)、社会关系维度(条目17~条目19)及健康行为维度(条目20~条目22)。采用5级评分法,由完全没有(1分)到非常多(5分)。得分越高的病人益处发现水平就越高。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3。
国外一项研究中将益处发现量表更名为“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量表”,并应用于头颈癌病人中,病人采用1~5分评分,“一点也不”计1分,“非常正确”计5分。得分超过3分表明益处发现处于中等水平。该量表已被验证在头颈癌病人中应用是有效、可靠的[16]。
2.2 第4版华盛顿大学头颈癌生活质量量表(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Quality of Life instrument,UW-QOL)[17]UW-QOL在针对研究头颈癌方面有12个领域,包括疼痛、外貌、活动、娱乐、吞咽、言语和焦虑等。其综合得分是10个独立领域得分的算术平均值,最高分数为100分,最低分数为0分。其中疼痛领域包括以下选项:完全没有痛苦为100分;轻度疼痛,无需服药为75分;有中度疼痛,需要定期服药(可待因或非麻醉性药物)为50分;剧痛,只能靠麻醉剂来控制为25分;有严重的疼痛,无法抑制为0分。国外学者已证明UW-QOL的内部一致性,该量表可有效、准确地应用于比较头部和颈部癌症病人的治疗效果[18]。将该量表应用于500多例病人后,研究结果指出UW-QOL符合以下由Spilker提出的理想特点:①完成时间短、速度快;②在头颈部肿瘤病人中具有可重复性、可靠性和有效性;③不需要过多培训即可实施;④易于解释,结果客观。
2.3 “担心癌症”量表[19]被用来评估病人对癌症复发的恐惧程度,从而间接反映病人有无益处发现。该量表主要包括以下3个项目:①“你担心癌症发生(复发)的频率是多久?”回答结果用数字代替,没有时间为“0”,很少为“1”,偶尔为“2”,经常为“3”,一直为“4”。②“对癌症的担忧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其他想法和活动?”得分为0~10分,没有影响为0分,最大程度为10分。③“你对癌症带来的可能性有多沮丧或苦恼?”使用与第2项相同的0~10分评分。该量表已被证明可以用于检测头颈癌病人对复发的恐惧[20]。
2.4 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 国外PTGI对于创伤后成长[21]所带来积极影响的一种解释是,这种创伤经历的性质可能是一个“警钟”,提醒幸存者生命可以在瞬间终止。这样的“警钟”可能会让人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多地寻求亲朋好友的支持,并激发人们对意义和目标的探索。PTGI包含病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7个条目)、发现未来的希望(5个条目)、增加自我的力量(4个条目)、改变自身的精神状况(2个条目)和充满对生活的希望和喜欢(3个条目)5个维度,共21个条目。PTGI已被用于评估病人身心健康、药物滥用、人格特征、保护性心理社会特征、社会联系、利他主义、精神和生活方式等方面。
我国香港Ho等[22]将PTGI汉化修订为繁体中文版,并应用于癌症病人。汪际等[23]也于2011年翻译了PTGI,汉化后的中文版PTGI与原版PTGI基本保持一致,也包含21个条目,包括与他人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精神变化和对生活的欣赏5个维度。该量表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从“创伤后完全没有体验到这种改变”到“创伤后这种改变非常多”计0~5分,总分0~105分,得分越高表示创伤后成长越多。汉化后的PTGI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74,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611~0.796。
3 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的影响因素
3.1 疾病因素
3.1.1 吞咽和言语障碍 头颈癌及其治疗造成的损害可能会导致病人对身体形象、认知和行为的不满。吞咽和言语障碍是头颈癌幸存者治疗后的常见症状,其强度各不相同。在放疗后的第1年内,约有一半的头颈癌幸存者出现吞咽困难和语言障碍[24]。而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等)是造成病人慢性吞咽困难(发病490 d)的主要原因。在头颈癌病人中,病前抑郁是一致、有力的抑郁预测因子[25]。与头颈癌相关的心理社会压力源包括人际关系担忧、不确定性、活动干扰、沟通、对复发的恐惧、耻辱感、对痛苦的担忧、对疾病和治疗的担忧、存在的压力源、财务问题、信息缺乏以及手术后的负面预期(如外貌和身体形象改变等)。
3.1.2 癌症分期 Ho等[26]发现,晚期癌症(Ⅲ期和Ⅳ期)病人的积极心理变化(positive psychological change,PPC)水平较低。在治疗后3~12个月,早期癌症(Ⅰ期)病人的PPC报告水平高于Ⅱ期和Ⅲ期癌症病人,且明显高于Ⅳ期癌症病人。Ⅰ~Ⅲ期癌症病人的PPC水平高于Ⅳ期癌症病人。对于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为癌症分期越低,治愈率越高,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越有可能去发现癌症给自己带来的积极作用,但是被诊断为Ⅳ期的癌症病人经历严重的痛苦或面对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使得他们在治疗后至少1年内无法发现任何积极变化[27]。
3.1.3 治疗方案 在同一时间段内仅接受手术治疗的受试者所报告的积极变化比接受手术加放疗的受试者要多,也比未接受手术治疗但接受放疗加或不加化疗的受试者多。
3.1.4 疼痛 疼痛在头颈癌病人中是一个重要表现。研究发现,48%的头颈癌病人在诊断时有疼痛,在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时分别为25%和26%。此外,研究显示疼痛对病人治疗后1年和2年的生活满意度有不利影响[28]。
3.2 社会人口学因素
3.2.1 性别 癌症病人益处发现相关研究显示,女性病人益处发现发生率高于男性[29]。女性病人往往更多地报告人际关系方面的积极变化。但Cavell等[18]的研究显示,头颈癌病人的性别对于其益处发现水平没有相关影响。其中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索。
3.2.2 年龄 在之前的研究报告中发现,年轻癌症病人的益处发现水平往往更高[8],但Cavell等[18]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这可能是因为头颈癌病人往往年龄偏大,不同研究中年轻癌症病人的例数不同,代表性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同,因此需要更高质量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3.2.3 性格特征 Harrington等[30]发现,在患有头颈癌的病人中,性格乐观和积极的重构可以解释PPC中23%的变异,拥有乐观性格的人更容易去发现生活中积极的一面,包括疾病给自己带来的各种正面的反思,而那些性格悲观、沉闷的病人,更容易陷入疾病带来的抑郁情绪中,很难拥有积极的情绪去应对困难和发现癌症及其治疗带给自己的正向引导。Llewellyn等[31]也通过自己的研究再次支持了Harrington等[30]关于积极的性格和重构的研究结果,并发现情绪支持的增加和自责的减少对PPC有积极影响。
3.2.4 婚姻状况 已婚病人与单身病人相比有更高水平的PPC。在Threader等[2]的研究中发现,病人会有“如果我一个人在这里,而我的妻子不在这里,我自然会躲藏起来”的想法。Ruf等[32]的研究也发现,得到健康伴侣的理解和支持的病人可以更好地适应疾病及手术带给他们的痛苦,大多数配偶的支持给病人带来了积极的变化。Schorn等[33]得出同样的观点,当病人有配偶陪伴或处于恋爱关系中时,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单身病人,对疾病复发的恐惧显著低于单身病人,情感支持显著高于单身病人。
3.2.5 社会支持 Threader[2]指出,当病人收到复查预约信息而害怕疾病复发时,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能够给他们提供安慰。面对疾病及手术治疗带来的痛苦,病人需要家人、朋友和社会的支持。Schorn等[33]也认为当病人缺乏可靠的友谊时,抑郁和焦虑会显著增加。病人抑郁、焦虑的发生也与大量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与更多人相处的需求显著相关。
3.3 心理因素
3.3.1 羞耻感 羞耻感是指将自己的癌症发病归因于过去行为的参与者,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后悔,并对其后果感到痛苦。在研究中,病人常会有“这是我自己愚蠢的过错造成的”这样的想法。比如患有头颈癌的抽烟病人会将自己的癌症归咎于自己的抽烟行为,认为吸烟是导致其患病的主要原因,从而使他们感觉到了一种与应受谴责的癌症有关的耻辱感。尤其是在术后的病人中,他们无法掩盖面部的变化导致了明显的耻辱感。正如一位参与者所说:“这种癌症,你无法隐藏它,你无法戴上一顶大帽子或遮住半张脸。”病人治疗后面部的变化加重了病人内心的羞耻感[2]。
3.3.2 自尊感降低 癌症治疗的其他不良副作用,如说话不清晰和流口水,可能会导致病人的尴尬,不仅不利于社会和家庭互动,还会对病人更内化的低自尊感产生重大影响[28]。
4 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的干预措施
4.1 心理社会干预
4.1.1 认知行为疗法 在Fiegenbaum[34]的研究中,试验组病人接受了10次为期2 h的培训,内容包括与毁容有关的问题以及言语和饮食问题。结果显示其社交焦虑显著减少,自信心显著增强,这些改善在2年的随访期内保持不变。Robinson等[35]设计了一个类似的社交技能研讨会,在干预前、干预后6周和干预后6个月随访中使用标准化量表对76项心理健康进行了测量。社交回避和痛苦的平均得分显著低于接受干预前的水平,并在6个月的随访中该结果进一步降低。
4.1.2 团体心理疗法 Aaronson等[36]组成了心理治疗团队,由一名心理学家作为领导者对新确诊癌症病人1年的生活质量(包括精神病发病率)进行纵向测量,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其中有13例病人进行了团体心理治疗干预,8例病人完成了干预和评估过程。在1年的随访中,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病人在益处发现等心理方面有显著改善。Mayo等[37]同样也进行了针对头颈癌病人及其家属的团体心理教育干预,在病人治疗后约2个月为病人和家属提供2次心理教育团体干预。要求所有参与者在干预结束时完成相关项目评估测量,包括人口信息(即性别、年龄)、课堂满意度、课堂参与在其恢复中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所有病人和家属都应该参加课程等。每个项目都使用Likert式评分,评分等级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4.2 基于夫妻的支持性沟通(couple-based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CSC) 有研究在病人接受化疗期间与夫妇面对面进行了4次75 min的治疗,治疗师的职责是保持夫妻关系正常,鼓励他们进行情感的反映,并通过阻止过早解决问题或消极行为(如无效或改变话题和/或说话者/听众角色)将谈话转移到更深的情感层面。CSC干预加强了夫妻关系和亲密关系。与6个月前的随访相比,病人和伴侣在测试后亲密度更高,病人的益处发现水平也更高。
5 小结
益处发现对头颈癌病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认知方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国内对于头颈癌病人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头颈癌病人益处发现相关研究,构建适合于我国头颈癌病人的测量工具,从而提高我国头颈癌病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