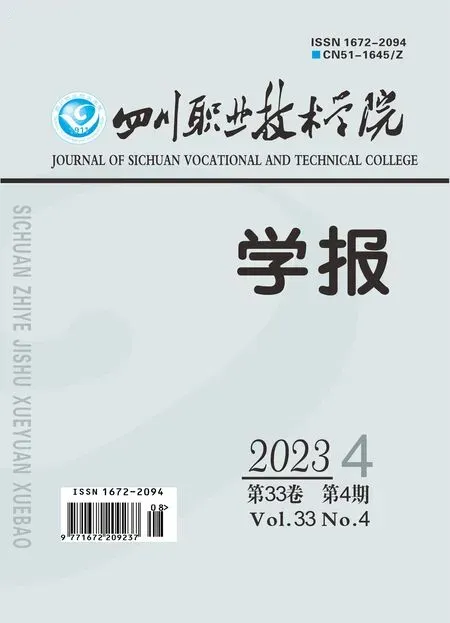羌族神话《燃比娃取火》的神话原型解读
吴 纯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神话原型批评作为一种广为使用的文艺理论,发轫于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卡西尔的象征主义哲学,集成于文艺理论家诺斯莱普·弗莱之手。我国学者叶舒宪率先将其理论予以总结、引入和运用。简言之,弗莱的原型理论中的“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其特征在于反复出现于文学作品中,具有约定性的联想;其次,原型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能将原本孤立的作品所联结,使文学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殊形态。而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它将文学与生活沟通,成为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该理论注重以宏观性的视角,结合整个人类文化创造中的各组成部分,以远观之法来解读作品,使之系统而全面地展现文本背后所隐含的深层表达。
分布于岷山山脉深处的羌族,其历史源远流长而波澜壮阔,无数次迁徙与征战孕育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由于缺少本民族文字,其文学和历史仅以口传心授而绵延至今。文学作为一种杂糅着主体观念的社会现象,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因此在阅读和分析羌族文学时,需注意其背后所蕴含的族群历史、道德和宗教观念等深层表达。羌族神话《燃比娃取火》(异文《燃比娃盗火》《热比娃取火》《取火种》《蒙格西送火》等)是一则文化起源神话,该神话既流传于民间民众口中,也运用于羌族释比的祭祀中,最早由罗世泽在1982年采集,现以羌族释比周润清解读和翻译的、收录于四川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主编的《羌族释比经典》中的版本为分析对象,简述其内容大致为:
在万物美好的远古时代,女首领阿勿巴吉带领族人生产生活,立规约俗。诸神嫌人类愚钝、人间聒噪,要对世间凡人予以教训,恶神霍都主动领命,从此人间寒冷。天神蒙格西心疼人间,又见阿勿巴吉人美心善,便予其神果。阿勿巴吉腹中怀下天神之子,生孩后取名燃比娃,令其寻父取火。燃比娃历经多次磨难,终取神火,从此人间复得温暖。[1]
该神话内容丰富,囊括了诸多的文化元素和神话原型,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相关理论来解读该取火神话,得以窥见其背后所蕴藏的,具有神话原型价值的神人结合意象、英雄原型、祖先信仰,成人仪礼,以及原始思维对于人类历史的抽象讲述,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等内容。
一、神人结合的原始意象
羌族神话《燃比娃取火》流传于民间,版本众多。在诸多版本中,取火者燃比娃的父亲均为天神蒙格西,母亲为羌族的族群首领阿勿巴吉。天神蒙格西怜惜人间,又钟情于阿勿巴吉,便予其神果,阿勿巴吉因此十月怀胎,产下天神之子。这一情节属于典型的神人结合意象,天神蒙格西与人类阿勿巴吉结合,交合与受孕的过程被表述为“吞下神果”。而神人之子“燃比娃”,出生后便展现出非同凡人的一面,“浑身长得毛茸茸,又长一根长尾巴,还未落地就说话。”[1]266“一岁能将兔逮住,九岁杀虎又捉豹,十六成人体如山,越岭跨涧本领高,一步能将山跨过,一跃能渡一条河,空中雄鹰也能擒,飞禽走兽语能通。”[1]267拥有如此神力的燃比娃,在取火过程中更展现出历尽磨难而百折不挠的意志力,当其取火归来后,众人围火而舞,燃比娃也由此成为族群内的取火英雄。
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协调人际关系、不断完善社会结构、不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在原始社会初期,先民们仅掌握着初级的工具制造方法,从事着简单的采集和渔猎活动,当其面临无法预测和驾驭的自然现象时,仅能臣服和顺从于自然,崇拜和依赖于自然的外化物,即主观建构出的各种“神”。在这一过程中,将自身无法认识和把握的力量予以神化,故而神源于自然,是自然力的人格化后的产物。从该角度出发,神与人的接触和结合,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映。此外,虽然神人之间存在着对立斗争与统一和谐的两种关系,但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工具尚未发达的原始先民而言,自然力常是令人生畏和恐惧的。因而神人关系,或言人与自然之关系,更多时候均表现为对立相争。神人结合的原始意象大量存在于各民族的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中,代表着广大原始先民们对于自身和自然的思考。正如《燃比娃取火》中众天神嫌人类愚钝便降下寒冷,天神霍都阻挠燃比娃取火等情节,不仅体现出神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也暗含着自然条件对于人类的束缚和压制。不仅如此,在诸多书面文本和口承表达中,神与人的结合,实质上是人对于神的崇拜行为,人通过与神的接触、交合、生子,同神产生关系,进而“借”到神力。这种“借神力”的行为,根本上仍是先民对于自然的崇敬,对于无法预测和驾驭的自然力量的臣服与顺从,试图通过神人之交,来提升自我族群的内在能力,也暗示了人类对于掌控自然力的内在渴望,企图与神所匹敌。在《燃比娃取火》中,父系为神,母系为人,通过二者的神人结合,其子燃比娃具有了神与人的共同血液。换言之,既有神的能力,即前文所提及的落地能言、跨山渡河、通鸟兽语等;也有人的品格,即勇担族群使命、历万难而不摧、意志坚定等。因此,融合了神人血液的燃比娃,凭借着自身的顽强意志力,以及父系天神的帮助,在取得神火后,被族人敬为英雄。
在羌族的神话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异文《木姐珠与燃比娃》)中,也存在类似的神人结合原型。木姐珠身为天神木比塔的女儿,与凡人斗安珠相遇后相爱,斗安珠在木姐珠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天神木比塔所设下的种种测试,进而成功迎娶天神木姐珠。在该故事情节中,凡人斗安珠先后展现出自己的体魄、智慧、勇气、力量和品德,天神木比塔所设下的一系列考验,正是原始农耕社会对于一位青年待婚男子的全面要求。神人的结合,凡人男子迎娶天神女性,在迎娶的过程中展现出凡人的诸多美好品行,这一情节所蕴藏的内在文化因子,即是神人间的斗争关系。人在斗争中凭借自身智慧和外在帮助,处于优势而赢得斗争,展现出人对于自然的认知和态度,从畏惧到顺从,再发展到企图匹敌,甚至于渴望战胜。该过程中人的力量被逐渐放大,主观能动性也逐步突显,这是同人类的相关历史发展所同步演化的。另外,羌族民间文学中“迎娶天神”的凡人男性,“嫁与天神”的凡人女性,以及“神人所生”的后代,此类与神产生关系的人物,大都被族群内部奉为英雄,或指定为祖先神,其相关故事更是为羌族释比在祭祀时所唱诵,成为具有整体性和持久性的族群记忆。此类的神人结合原型,不仅体现在羌民族的远古神话中,更广泛分布于华夏各民族的神圣叙事里,深刻反映出早期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具有表层特殊性和深层普遍性的典型原始意象。由此观之,神人结合的原始意象,在本质上是原始先民对于自身和自然之关系的思考,通过神人二者的结合,达到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目的,并以此同神产生关系,进而“借”得神力,建构起族群内的英雄形象,隐含着原始先民渴望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内在情感,达到增进族群精神力量,维系族群内部团结的潜在作用。
二、历尽磨难的英雄原型
在羌族神话《燃比娃取火》中,产生取火的背景为人类世界正经受着漫长的寒冷,其前提为燃比娃之父乃天神蒙格西,且自身拥有神力,在这样的背景和前提之下,燃比娃一出生虽经受严寒,但却潜藏机遇与使命。在取火的过程中,燃比娃翻山越岭,经受遥远的路程而来到天门外,其后三次取火,途中经历神火烧身和洪水漫卷,燃比娃数次昏迷,毛发尽褪又失去尾巴,在其父蒙格西的帮助下,将神火藏于白石中,最终把温暖重新带回人间。何以成为英雄?“一是他做了别人不愿或不能做的事,二是他是为自己也是为一切人而做的。”[2]365由此观之,该情节中燃比娃三次取火,三遭磨难,屡战霍都,不仅成功克服了路途中的艰难险阻,更承受住水与火的身体考验。羌族先民尊燃比娃为取火英雄,不仅是纪念其卓越的取火功绩和不凡的意志品格,更希望借此精神来团结族人,鼓舞士气,增强自身民族的内部凝聚力。
在羌族的族群历史中,燃比娃的英雄精神具有着深刻的普遍性,是深植于羌民族灵魂深处的精神表现。现代羌族主要分布于岷山山脉的高山深谷间,具体为四川省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以及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但依据考古发掘、文献资料和口承表达的多重证明可知,其背后具有深远的民族发展史和迁徙史。羌民族原本驰骋于广袤的西北原野,甘青地区的河湟一带为古羌的祖居地。在漫长的历史中,古羌民族或东进中原,成为华夏民族之组成血液;或沿横断山脉向南迁徙,与当地其他部族产生交流与融合。因此当我们研究今日之藏、彝、白、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普米、景颇等民族的历史时,均须探讨其与古羌之间的族源关系。费孝通先生将羌族称为“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而这种“输血”行为的发生,则源自于古羌先民们千百年来不断地远离家园和迁徙他方。一个民族的迁徙史,注定充满着征战与困苦,注定是历尽磨难和考验的族群记忆。羌族史诗《羌戈大战》记录着古羌人因战争而迁徙至岷山地区的故事,该史诗以浪漫雄奇的语言,讲述着羌人与魔兵、戈人之间的战争,史诗开篇便提及“诉说着祖先的英勇,诉说着祖先的坚强,他们从旷野的戈壁滩迁徙而来,他们从莽莽的草原上迁徙而来,他们与狡诈的魔兵刀光血溅,他们与凶残的戈基人斗智斗勇”[1]4,族群间因生存资源而交战,其中所承载的民族记忆和民族精神,一直为羌族释比所演述至今。无论是《羌戈大战》,抑或《燃比娃取火》,英雄形象的背后,所蕴藏的历经磨难而愈发坚韧的品格,正是古羌先民们的迁徙历史的真实讲述。
历经磨难的英雄原型,并非羌民族所独有。于整体人类的历史进程而言,此类英雄原型代表着远古先民们同自然抗争的永恒记忆。当自身力量无法同外界自然抗衡时,必然产生富有理想化和超越性质的个体角色,此角色高度凝炼起族群整体的共同希冀,是具有整体代表性的“超人”形象。历览古今中外,以及华夏各民族的书面文本和口承表达,均可发现此类受磨难的英雄原型的存在。射日英雄、取火英雄、治水英雄、创世英雄、文化英雄,抗争英雄,英雄原型存在于神话的各个题材领域。此类原型代表了整体利益,他们承担使命而历尽磨难,是熔铸了特定族群、特定背景、特定记忆、特定精神的文化综合体,象征和表达着族群精神,鼓舞并引领着族群的发展方向。
三、“成人礼仪”的神话原型
纵览人类文学的发展史可知,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深植于原始文化。而神话作为原初的文学模式,其研究必定要追溯至远古的宗教礼仪,以及形而上的哲学和思维层面。因此对于神话原型的探讨,本质上是一种文学层面的人类学研究。叶舒宪在《神话—原型批评》一书中论及“原型批评以人类学的理论及视野为基础,其核心方法,按照弗莱的倡导,叫作‘远观’(Stand back),可以说是一种宏观的全景式文学眼光”[2]。在此处理下,文学已不再作为单独且孤立的文本,而是同人类整体的文化创造相结合,换言之,文学同宗教信仰、民间风俗、文化礼仪都紧密联系。因而,以神话原型批评的相关理论来解读羌族神话《燃比娃取火》,势必要与相关的人生礼仪和宗教信仰相结合,以“远观”之法来审视该神话文本。
《燃比娃取火》讲述着神人之子“燃比娃”,历经磨难而前往天界盗取神火的故事。神话中提及“待你长大成了人,去上天庭把火取”[1]268。可见燃比娃取火之事发生在其成年之时或之后。其次,燃比娃承受住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考验而取得神火,并在取火途中完成了由猴到人的身体形貌转变,失去原有的猴形的外在表征,而成为“焦黑皮毛全脱尽,健美身形映水中”[1]278的人的基本样貌。因此取火行为不仅使燃比娃获得“人型”,成为一个拥有具体人类外在形象的“人”,更让他经受了精神层面的磨砺,使其品性坚韧而愈加成熟,具有了抽象层面的“人”之品格。取火归来后,燃比娃被族群内部尊为英雄,更使其完成了具有社会性的“身份转变”。因此从这三个层面出发,燃比娃取火一事,完成了自身的“成人礼仪”。另外,火的使用对于人类历史具有深远意义,可用于照明、取暖、防卫和烹饪等诸多领域,极大地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就整体层面的族群言之,从无火至有火,“火的使用”使得族群迈入新的历史阶段,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由此观之,燃比娃取火一事,不仅是其个体生命的“成人礼仪”,更是族群整体的“成人礼仪”,两个层面上的“主体”均在取火中获得了超越原本的自身突破,因而更加完整和成熟。
位于岷江上游的羌民族,恪守着祖辈流传至今的诸多人生礼仪,例如出生礼仪、成人礼仪、婚姻礼仪、丧葬礼仪等。并以此类礼仪来程序化地界定出人生的各个阶段,赋予族人在不同人生阶段以不同的社会角色,进而形成一整套既定且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模式。将该神话与羌族传统的成人礼仪相观照,可以获得超越文本层面的独特理解。羌族男子的成人礼仪在其人生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是青年人进入社会交往、寻求配偶、获取社会认同的关键步骤。该礼仪多于年满十五至十八周岁之际举行,具体过程又分为屋内屋外两种冠礼。屋内冠礼筹备于农历八月,举行于十至十二月之间,届时释比唱经并祭祀家中诸神,族长详谈祖先历史,为其灌注本民族的内在情感和精神力量。屋外冠礼举行于祭山大典之后,释比唱诵族群历史,为其祈祷祝福。成人礼仪的举行,标志着羌族青年从此被接纳为社会的一员,获得群体的社会性承认。虽然此类仪礼已随物质生活的提高而逐渐衰弱,但其背后所呈现的,则是羌人对于自身和外物关系的思考,即企图通过主观行为和外在形式达到强化自身生命力的深层目的,并以步骤化的程序来标志其具有社会身份。结合前文对于神话《燃比娃取火》中“成人礼仪”的相关分析,可见羌人在人生礼仪和文学文本中所共同呈现出的人生观和生命观,以及对于个体同群体之关系的思考。或言“把他从一个自然人在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具体的文化背景中,通过周围人的联系形成相互作用的合力,使他逐渐认识自我,成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3]。得益于成人礼仪的存在和施行,燃比娃一类的羌族青年,通过克服挑战和提升能力,完成身份标签的转变,进而融入社会,达到“成人”之目的。
四、原始思维的历史讲述
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与自然的矛盾关系是神话产生的基础,而神话的内容与表达,则与人类思维的发展密切关联,即“是以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原始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神话思维为其背景的。”[4]思维结构是指由思维主客体和思维媒介所共同构成的结构,以及在思维过程中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在原始的蒙昧时代,思维的主客体之间常以一种含混不清的关系相伴而生,先民们运用“观察、类比、摹写”等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其思维结构主要表现为类比思维和简单的抽象思维。多种原始思维的含混杂糅,共同构成原始先民对于外部世界的基本表达,即远古神话中常见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神话作为一种口头文学,产生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其文本内容是结合了创作者主观的夸张和想象,以及外在环境的客观实在的综合表达。因此,从某一程度而言,神话来源于模仿活动,即赵忠牧先生所言的摹写—洞察的经验知识。远古先民观察周围环境,将日常所见之物、所触之感都予以记录,通过直接感官来获取对于外部世界的基础认知,诸多客观认知在脑海中形成了简单的抽象表达,此般内容便成为神话创作的基本元素。它们或关于生产生活,记录日常;或解释某种未知,表达关怀与敬畏;或讲述自身历史,谋求族群团结和内生力。诸如此类,神话亦可理解为远古先民对于外物世界的整体感知和群体记忆,其深层次所蕴含的内在表达,可通过还原思维模式,以类比思维和简单的抽象思维切入,来解读神话内部的历史讲述。
羌族神话《燃比娃取火》,蕴含着古羌先民对于历史的讲述和思考。概言之,该神话中体现出父系氏族对于母系氏族的承接和转变,生物进化视角下的人猴关系,以及火的使用与人类历史阶段之关系。羌人运用简单的抽象思维和类比思维,在神话中讲述社会发展和人类演变的历史,反映出古羌先民对于“我是谁”“从哪来”等哲学问题的基本思考。聚焦于神话中的具体情节可知,部落首领阿勿巴吉为人类女性,其子燃比娃从母居,燃比娃出生后便问道“我的阿爸他是谁”[1]266。在远古的母系社会,“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亦不懂得两性之间交媾和怀孕生产的道理,因而《燃比娃取火》中所涉及到的“阿勿巴吉食用天神蒙格西所予的神果后怀孕”“燃比娃不知其父,从母居”等情节,均是对远古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讲述。其次,阿勿巴吉作为人类部落的首领,带领族人寻找食物和组织生产,是该神话前半部分的主角。而取火成功的燃比娃被族人敬为英雄,羌人将获得火、运载火、使用火的伟大功绩都附着于燃比娃一人,使其成为该神话最终的歌颂对象。主角的转变,也透露出人类社会已悄然从母系向父系开始过渡。而该神话《燃比娃取火》中所记录的人类社会由无火、被动用火、主动取火,再到两石相击而“造火”的相关过程,即是对火的使用与人类历史阶段之关系的抽象讲述。在无火时代,天寒地冻,人类刨开积雪食草根,而燃比娃第一次取火时用“油竹火把”,但狂风使神火引燃自身的毛发,这一阶段的人类仅能被动用火,且极大地受制于自然火种的偶然性。第二次取火利用“瓦盆”盛火,暗示人类已进入主动保存自然火种的历史阶段。第三次取火,利用两块白石相碰撞,产生火星而引燃火把,此时人类已学会“造火”。燃比娃的取火历程正是原始人类对于火的利用过程,而取火的成功也标志着人类迈进新的历史阶段。
另一方面,出生后的燃比娃,是浑身长满长毛且有尾巴的“猴毛人”。在取火的过程中,大火将浑身毛发引燃,大水将焦黑的皮毛脱尽,关闭的天门将尾巴夹断。三次磨难让燃比娃“由猴变人”,失去原本属于“猴”的外在表征,从形象上进化为“人”。而羌族的另一神话叙事长诗《木姐珠与斗安珠》也记载斗安珠为“猴毛人”,神话《猴人变人》记载祖先由“猴人”所变。可见在羌族的诸多民间文学作品中,均以猴为人类始祖,暗含“由猴变人”的生物进化过程,此论与现代科学之观点不谋而合,是羌人对于生物演化和人猴关系的历史讲述。不独于此,同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傈僳族、拉祜族、哈尼族、珞巴族和门巴族也有着与羌族《燃比娃取火》所类似的“猴人取火”神话。在珞巴族神话《人和猴子为什么不一样》中,珞巴族先民“把猴子变人和火联系了起来,反映了古代珞巴族在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火对人类生存的作用”[5]。门巴族神话认为猴子在食用了烧熟的果子后,毛发脱落,逐渐有了人的模样。傈僳族神话则认为天神用泥土捏成的猕猴演化成了人。因此,学者王小盾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目前所见的45例猴组神话进行了分类描述,并依托神话学和语言学的相关资料梳理了汉藏语系民族的猴组神话谱系,认为此类神话“反映了汉藏文化共同体的某种嬗变”[6]。可见,人猴之变和火种的使用是普遍存在于汉藏语系民族间的共同记忆,是具有图腾信仰性质的神话母题,更是分析原始思维、探讨民族间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论证。
神话《燃比娃取火》中的历史讲述,融合并反映着古羌先民的原始思维,而此类思维又以简单的抽象思维和类比思维为主。将周围的生存环境进行抽象化的表达,将自身文化和历史进行类比化和象征化的讲述,以燃比娃的取火历程来暗示人类对火种的利用进程,以神话细节和神话主角的变化来象征母系父系氏族的悄然转变,以燃比娃自身的体征变化来暗示整体人类的生物进化。由此可见,羌族先民运用原始思维,将外在事物和自我族群作为演绎对象,结合浪漫瑰奇的艺术语言,在其神话中蕴藏了大量的历史表述。
五、结语
神话《燃比娃取火》广泛流传于羌族民众口中,唱诵于释比祭祀的具体仪礼中,讲述着羌族先民同自然抗争、取火以谋求生存的永恒记忆。该神话中所体现的文化基因,如今依然存在于羌族群众的生活中,外化为“火塘文化”“白石崇拜”“猕猴崇拜”等文化事象。因此,以神话原型批评的相关理论解读该取火神话,注重以远观之法进行审视,联系羌族的民间风俗和宗教信仰,以该神话为切口,窥见燃比娃这一形象所代表的历尽磨难的英雄原型,取火行为的背后所蕴藏的“成人仪礼”,原始思维对于自身文化和人类历史的抽象讲述,以及羌族先民对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哲学思考。
神话作为人类文学的最原初形态,产生于原始人类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之中,是蕴藏着特殊时代下集体记忆、族群历史、思维逻辑的综合性表达。随着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思维模式的不断发展,文学的体裁和样式也与之同步更新迭代,其内容和形式也愈加丰富。因此,在文学不断发展的态势中回望和反观文学的源头,重新审视神话文本背后所隐含的丰富的深度表达,以及不同族群在原始思维表达上所具有的普遍共性,则有助于当下“以古审今”地反思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之关系,更有助于从文学层面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所共通的原始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