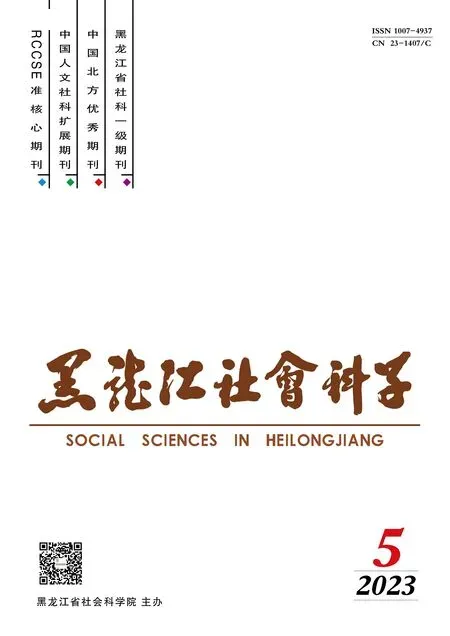王国维序跋古文字研究述要
叶 玉 纯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王国维是近现代著名学者,著述宏富,在哲学、美学、教育学、戏曲、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领域成就卓越、贡献突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精深的学术遗产。其治学特点之一,是正式开展研究之前对研究材料详细梳理,建立汇编或索引。如研究金文,先做《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研究宋元戏曲,先做《曲录》;研究元史,则先做《元朝秘史地名索引》。其治学特点之二,是为各类研究撰写序跋,介绍相关背景,厘清前人研究成果。序跋是王国维学术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纵观王国维一生论著,两百余篇序跋贯穿始终。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专治“古文字之学”,在古文字材料尚未大量发现、古文字研究尚处起步的当时,除借助专著及论文,还借助序跋,阐发了一系列关于战国文字、古文字考释及古文字学的极具前瞻性的重要观点,对古文字学的建立有创始之功。
一、王国维的序跋概述
王国维的序跋文,主要收录于《观堂集林》的《艺林》《史林》卷和赵万里所编《观堂别集》中,而《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中失收的一些题跋,在2009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第14卷得以专门补充收录,《上海博物馆藏王国维跋雪堂藏器拓本》则集中收录了35篇题跋,与《观堂集林》多有重复。这些序跋有序、叙、序录、总论、后序、跋等多种名目,内容涵盖考古、历史、文学、文献、翻译等多门学科。而其中多篇关涉文字学,从详细内容又可分为:考订出土器物序跋,如《殷墟书契考释序》《魏石经残石考序》《商三句兵跋》《北伯鼎跋》《敦煌汗简跋》;重辑字书序跋,如《史籀篇疏证序》《重辑仓颉篇自序》《校松江本急就篇序》;著录汇编序跋,如《齐鲁封泥集存序》《宋代金文著录表序》《国朝金文著录表序》;古史研究序跋,如《古史新证总论》等。多数为自作序跋,也有为他人而作,如《殷墟文字类编序》《金文编序》《桐乡徐氏印谱序》等。
李学勤的《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充分肯定了王国维的《说文》古文及壁中古文实为战国东方流行文字这一观点在文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唐友波的《〈王国维跋《雪堂藏器拓本》〉读后》指出题跋虽有起因于应酬者,但一定是学者学问和识见的表现,与其学术思想有所关联。张志亮的《王国维题跋〈齐侯罍精拓本〉》认为跋文对齐侯罍文字内容中“大司命”的考证可谓至深。王国维序跋已引起学界关注,但相关研究与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且意义重要的序跋远不匹配。许多文字学相关序跋从学术角度出发,有的集多年研究心得于一长文,有的则是短小精悍的学术札记,无论长短,其中蕴含的古文字思想均值得深入探讨。
二、王国维的序跋对古文字学的意义
王国维序跋中的古文字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利用各类传世文献与新发现古文字对照,实现出土文献文本释读、补正《说文》等字书;二是在古文字材料的整理及研究过程中,总结摸索释读古文字的方法,从古文字学命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注意原则等方面初步构建古文字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
(一)手定“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是20世纪建立的。它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字学,同时又与金石学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字学萌芽于先秦,曾是“小学”的一部分,为阅读典籍服务。直到1906年,章太炎才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首次提出“语言文字学”这一名称,并提倡用“语言文字之学”代替传统小学。文字学自此才向近代的独立学科发展。金石学产生于宋代,“金石学建立之始,就孕育着古文字学分立的因素,这是由这个传统学科的不纯粹性和兼容性决定的。从一开始,金石学就包含考器与考文两项任务。考文的发展结果,必然是古文字学的分立。如果追溯考释古文字的历史,可以上推到东汉的许慎、张敞,但是,古文字学的分立直到清季才见端倪”[1]。
20世纪初,古文字学继承了传统文字学的考据实证之风,又继承了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孙诒让等人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同时突破了《说文》学的藩篱,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古文字”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汉书》“张敞好古文字”,而“古文字学”这一名称是何时产生的?是谁首先提出来的?徐中舒《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记:“不过到了最近二三十年,龟甲兽骨文字出土,钟鼎的范围,固然包括不了,而古籀二字也不妥当。静安先生根据了新旧的材料,考定古文只是战国时东土——六国——的文字,籀文只是春秋战国之间西土——秦——的文字,所以先生就将古籀二字弃去不用,而迳称为古文字学。先生在《国朝金文著录表》里说:‘古文字之学一盛于宋而衰于元明’;又说‘国维东渡后,从参事(罗振玉先生)问古文字之学’;罗振玉先生为先生做《观堂集林》序也说‘辛亥之变,君(指先生)复与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尽弃前学,专治经史,日尽《注疏》数卷,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照此看来,古文字学这个名词,也可以说是先生所手定的。”
从徐中舒先生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古文字学”,是王国维亲自命名的。而他的序跋中,多次提到“古文之学”“古文字学”“古文字之学”,恰与徐中舒先生的记载互相印证。
赵宋以后,古器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欧阳永叔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宋代金文著录表序》)(1)引自王国维序跋的内容,出自《王国维全集》(2009),均在正文标明篇名,不再另外标注。
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一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国朝金文著录表序》)
今古文日出,古文字之学亦日进……(《金文编序》)
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余所见得四人焉:曰嘉兴唐立庵友兰,曰东莞容希白庚,曰胶州柯纯卿昌济,曰番禺商锡永承祚。(《殷虚文字类编序》)
由此可知,“古文字学”这一名称当是王国维最先提出和使用的。
(二)界定古文字学研究对象
1913年,王国维在《齐鲁封泥集存序》说:“自宋人始为金石之学,欧、赵、黄、洪各据古代遗文以证经考史,咸有创获。然涂术虽启,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于是三古遗物应世而出。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者,既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
何为“三古”?《汉书·艺文志》:“《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易·系辞下》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在王国维看来,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春秋战国,所有出土的文字都是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且随着出土材料的逐渐增多,文字载体的种类也丰富起来,“金石”之名不足以概括全部出土文献。
王国维没有明确指出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范围,但我们可以从他对出土文献的重视和论述中,看出他的研究涉及所能见到的所有古文字。而他也确实在研究中覆盖了所能见到的所有古文字。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为证明壁中古文与六国古文字相似,列举了大量含有文字的材料——货币、玺印、陶器、兵器、石经——与壁中古文对照,并总结归纳了汉代之前能见到的文字材料载体:
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诸国并有彝器传世,独战国以后,彝器传世者唯有田齐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诸鼎,寥寥不过数器。幸而任器之流传,乃比殷周为富。今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
《王国维年谱长编》有对此所做评价,“王德毅说,先生对古文字学的研究,除治甲骨文外,其他古钟鼎、彝器、兵器、陶器、玺印、货币等实物上的铭文,都用以与《说文》比证”[2]。也能从侧面反映出王国维古文字研究所涉及的范围。
(三)阐发古文字考释方法
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认为古器文字有许多不能完全释读,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古文字年代久远。从周初到20世纪初近三千年,即便从周初到秦汉也有一千年。文字经历了很多变化,而后人并不能清晰了解文字变化的脉络。其二,假借的广泛应用。古书中大量使用假借字,而从周初至汉代,语音变化也很大。因此,无法确定每个假借字的本字。其三,古书和彝器上的文字都是当时的通行文字,当代人读不懂古文,在于对古代生活的了解不够。因此若要释读更多的古文字,就需要运用科学合理的文字释读方法,王国维概括地阐述了考释古文字的方法:
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 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以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然后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则庶乎其近之矣(《毛公鼎考释序》)。
即当从四方面进行古文字考释:一是考察古史、制度、文物,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二是参照传世文献,如《诗经》《尚书》的辞例,释读文义;三是因声求义,利用古音,分析假借用法;四是参照相关出土材料,在文字系统内部验证文字的变化、字形和应用情况。用上述方法进行文字考释,对仍旧不可释读的文字则可标注阙疑,留待以后研究。
王国维对所提倡的考释方法身体力行,如在研究封泥时,与官印古玺对照,辅以当时官制制度。《齐鲁封泥集存序》所记如下:
癸丑之岁,上虞罗叔言参事既印行敦煌古佚书及所藏洹阴甲骨文字,复以所藏古封泥拓本,足补潍县陈氏、海丰吴氏《封泥考略》之阙者甚多。因属国维就《考略》所无者,据《汉书》表志为之编次,得四百余种,付诸精印,以行于世。窃谓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尤夥。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
又如释读铭文时,王国维或运用一种方法,或几种方法综合运用,给出土古文字考释及文意释读指出了方向,带来了新的研究气象:
所云大祖、大父、大兄,皆谓祖、父、兄行之最长者。大父即《礼·丧服经》及《尔雅·释亲》之世父,古世、大同字,如世子称大子,世室称大室,则世父当称大父,非后世所谓王父也(《商三句兵跋》)。
历代金石学家、文字学家都在不断总结释读古文字的方法,宋代吕大临作《考古图释文》,这是古文字学里的第一本书,有人认为这本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书中认为从小篆考古文,只能得三四,并提出若干辨识古文字的原则,如笔画多寡、偏旁位置左右上下不一等。清代刘心源《古文审》中写道:“讲古篆,必绝四弊……不谙篆法,一弊也……不明假借,二弊也……不识古义,三弊也……不达古音,四弊也。”[3]王国维之后的学者也重视归纳古文字考释方法,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归纳出对照法、推刊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四种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强调考释古文字要结合原始氏族社会的生活习惯,考释甲骨文和金文,必须追寻其形、音、义的源流,既要寻出横面的同一时期的相互关系,又要寻出纵面的先后时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还要注意古文字和典籍互证。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不仅是宋代、清代学者古文字考释方法的集大成者,同时又为其后学者开创了研究框架。
(四)提示古文字研究的注意原则
王国维始终秉承着批判的精神关注古文字研究,其序跋中多次指出一些治学方法的不当之处:
自来释古器者,欲求无一字之不识,无一义之不通,而穿凿附会之说以生。穿凿附会者非也,谓其字之不可识、义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毛公鼎考释序》)。
自王楚、王俅、薛尚功之书出,每器必有释文,虽字之绝不可释者,亦必附会穿凿以释之,甚失古人阙疑之旨(《金文编序》)。
利用穿凿附会实现器铭的全部识别、完全读通,是不正确的。而若因字不可识、义不可通,就完全置之不顾,也是不可取的。王国维提倡的解决之法即“阙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并于《金文编序》中详细阐述了“阙疑待问”的观点。
孔子曰“多闻阙疑”,又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许叔重撰《说文解字》,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至晋荀勖等写定《穆天子传》,于古文之不可识者,但如其字以隶写之,犹此志也。宋刘原父、杨南仲辈释古彝器,亦用此法(《金文编序》)。
“阙疑”之法古已有之,汉代许慎、魏晋荀勖及宋代金石学家,都有所运用和发挥。到了清代,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将未识之字列于附录;罗振玉考释甲骨文,特撰《殷墟书契待问编》;王国维也在《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中,多列阙释之字。皆因“古器文字有不可尽识者势也”,“古器文义有不可强通者亦势也”。以现有的知识水平,遇到难释难解之字实属必然,不应为追求通篇释读、尽善尽美而用穿凿附会的说法来解释,而应标注“阙疑”,留待后学解决。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推进,阙疑的问题终将得到妥善解答。
“阙疑待问”是否可以随意应用?《毛公鼎考释序》有详细的原则,“于前人之是者证之,未备者补之,其有所疑则姑阙焉”。即在考释文字基础上,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仍有未解之疑,才可标注“阙疑”。
面对复杂难通的古文字,清代一些学者凭私臆曲解文字,无所忌惮,给古文字研究带来极坏的影响。王国维同样指出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提议清代的古文字之学不能与训诂学、《说文》学、音韵学并驾齐驱。
而俗儒鄙夫,不通字例。未习旧艺者,辄以古文所托者高,知之者鲜,利荆棘之未开,谓鬼魅之易画,遂乃肆其私臆,无所忌惮。至庄葆琛、龚定庵、陈颂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极矣(《殷虚书契后序》)。
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复兴,辄鄙薄宋人之书,以为不屑道。窃谓《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亦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吴诸家不能岀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之所不能免也(《宋代金文著录表序》)。
综上所述,王国维倡导的古文字研究需注意的原则可概括为以下五种:不穿凿附会;不过度阙疑;不置之不理;不肆意曲解;不鄙薄前人。
在他的影响下,商承祚《殷墟文字待问编》、孙海波《甲骨文编·附录》记录了未能释读的文字;《金文编》则将图形文字之不可识者列为“附录上”,形声之不可释者及考释犹待商榷者为“附录下”。《古玺文字征》《汉印文字征》以及《甲骨文编》(1965)等书正编之后亦均附录不识或待商榷之字,以供进一步研究。
(五)古文字学研究的具体成果
王国维通过序跋形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为,提出“古文”为战国东方六国文字。《说文·叙》云:“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4]按许慎认为的文字演变顺序来说,“古文”主要指自仓颉造字至周宣王太史籀之前的古文字,“古文”是早于籀文的。这也是汉代古文经学家的普遍认知,并一直延续至清代。如段玉裁仍言:“凡言古文,皆仓颉所作古文。”[5]清代吴大澂和陈介祺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许慎所说的古文,疑为周末文字。
1916年春,王国维作《史籀篇疏证序》,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
《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岀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
1926年又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通过大量的文字材料,如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详细论证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六国的文字,其特点是“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
“古文”是战国时的六国文字的观点最初也受到质疑,但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增加,通过不断研究验证,这一观点已为不刊之论。当时六国文字材料较少,而王国维凭借敏锐独到的学术眼光,“一语道破了壁中书来源,可谓发千载之覆,是古文研究的奠基之作”[6]。同时这一科学的“古文”观,开辟了新学术方向——战国文字研究,何琳仪先生指出:“近代战国文字研究,是建立在出土文字数据和对传世‘古文’研究基础上而兴起的新学科,王国维则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人。”[7]
三、余论
《汉语文字学史》将民国以来的科学古文字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20世纪30年代,为科学古文字学的草创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为奠基阶段。1978年以后为古文字学的全面发展阶段。学界一般认为唐兰、于省吾奠定了科学古文字学的基础,特别是1935年唐兰出版《古文字学导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古文字学的各个方面,是第一部古文字学理论专书。而王国维处在草创阶段,以往在谈到王国维古文字研究贡献时,常突出他利用古文字来证经考史所取得的成就,而忽略其对古文字研究及古文字学这一学科本身的贡献。通过对序跋的研究我们发现,实则王国维在古文字学科的创立上进行过很有意义的探讨,其贡献也远大于我们之前的认识,创始之功,实至名归。序跋在王国维古文字研究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时一些序跋也体现出王国维古文字考释的成就。正如朱芳圃先生所言:“先师古文字学及其造诣之深,发明之多,海内学者多能道之。余谓其最大之成绩,在探出文字进化之程序与建设文字学之新系统是也。”[8]望本文研究能使王国维先生在古文字研究及古文字学史上的贡献和卓越成就被学界所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