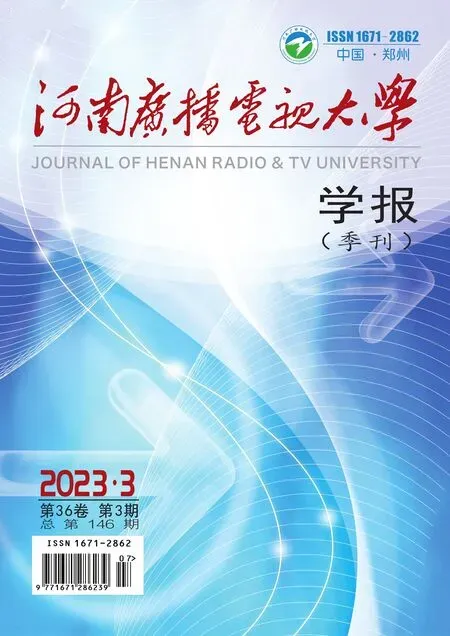新世纪国产青春电影疾病叙事的审美价值
魏 玲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疾病,就医学层面而言,指的是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受病因损害后因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包括生理疾病与心理疾病。这异常的生命活动一旦作为一种叙事策略与电影发生勾连,其深层意义便指向了对社会文化的镜像表征。而“青春”最早出自《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其意指蓬勃生命的至阳,不啻于那升于扶桑的太阳,是春神句芒播撒在大地上的力量。于是,疾病/青春即对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两形。“一盛一衰,文武论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1]这“一清”为阳,阳为青春;这“一浊”为阴,阴为疾病。如果说阳为乾,阴为坤,阴阳相合方能生出乾坤大“美”的话,那电影无疑就是最适于调和阴/阳(疾病/青春)两极的艺术器皿了。
在新世纪以来的青春电影中,疾病叙事能够以其至阴的一面唤起观影者对死亡的恐惧,迫使其认清无休止的物质主义带来的虚无;亦能够通过患病主体青春至阳的一面,来抵御疾病带来的发肤之痛与生存绝望。如果说青春带来生命的美,疾病带来疼痛的美,那么电影则带来撞见“死亡”时刻的美,使每一位观影者都于心间凝成一把抽象的尖头铣刀,“雕刻”出与自身浑然一体的和谐之美。这“美”或是内在生命力的焕活,或是迷醉狂欢的朝圣,或是“绝圣弃智”的疯癫,抑或是权力与话语的寓言。
一、绵延生命的触点
新世纪以来的青春电影中,疾病作为叙事元素,其审美旨归绝然不会仅仅囿于表现疾病本身,而是以疾病做引,通过干扰主人公正常健康的生命进程,将主人公置于极端情境中,逼迫其冲破理性秩序的牢笼,焕活内层无意识中对绵延生命的感知,以达到无所为而为的“自为”状态。而观影者亦可在审美过程中,通过与银幕内角色的交感同情而孕化出创生的生命体验,从而进入一种纯意识的绵延状态。正如美学家桑塔耶纳所说:“爱情使我们成为诗人,死亡的临近使我们成为哲学家。”[2]在当代工业“巨兽”的重压下,“同质化的恐怖”摧毁了青年人对生命的认知,使其沉迷于物质的虚无与精神的空洞。唯有高悬的死亡恐惧,才会迫使青年人迈出虚无的荒漠,回归母题安宁的本源,海德格尔称其为“向死而生”。
在电影《送我上青云》中,疾病所暗含的象外之旨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中的“好风”。正是在疾病这阵风的吹拂下,盛男才开始触摸到潜意识中的爱欲生门,并在寻求疗愈的旅程中,窥得了生命的闳意妙指。自小被冠以男性特征的盛男,在患病前是一位去欲望化的“花木兰式”女性形象,其欲望的形态是拘禁的、陌生的、游离于身体与灵魂之外的。“我好久没有性生活了,我的卵巢怎么可能癌变呢?”这既传达出盛男一直以来都在斜视女性对生理欲望的正当淫求,又生猛地暴露了她潜意识里对女性欲望污名化的倾向。显然,高级知识分子和现代独立女性的双重身份并不能使其懂得女性也享有身体快乐的权利——“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3]。通过盛男对女性意识的误读,也可诊断出现代社会中一类中产阶级女性的症候——放弃对女性身体快感的欲求。概言之,此时的盛男还处于“自在”生命的阶段,她内心欲望的诉求仍被拘禁在那个传统规范化的“铁皮屋子”中。当疾病猝不及防降临时,死亡及永失快感的恐惧则迫使她重返精神的圣地,踏上崭新的生命之旅。在这段旅程中,疾病恰如一缕刺骨的寒风,刺破了“铁皮屋子”的窗口,也刺破了盛男潜意识里被禁锢的欲求。于是,这欲求便开始裂变、创生出新的生命体验。影片收尾处,盛男再次登上山顶,这与片头的登顶情节形成出发—回归的循环对照,只是这场看似回到原点式的旅程中,盛男终是逃离了“自在生命”的禁锢,步入了“自为生命”的全新阶段。
如果说,在《送我上青云》中,盛男借疾病得以在精神领地御风而行、扶摇直上,直达生命之巅的话,那么在电影《送我一朵小红花》《再见吧!少年》中,疾病这缕借力的清风便凝为万家灯火中的每一盏灯芯,既点燃了患者对生命的渴求与热爱,也照亮了家属在病患逝去后那痛不堪忍的岁月。在《送你一朵小红花》《再见吧!少年》中,影片不仅呈现了青春年少的主人公在死亡临近前那循梦而行、向阳而生的美好特质,而且也通过对患病家庭日常细节的侧写,传达出病患家属在陪伴患者对抗死亡的过程中,自身所经历的“痛苦—挣扎—无力—坚韧—创生”的心路历程。这里,疾病作为绵延生命的触点,让观者窥得了中国式家庭中最动人心魂的温情脉脉,爱将身体的落败升华为绵延生命中最永恒的美丽。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尾声处,父母用拍摄小视频的方式为韦一航预演了未来时空中可能发生的死亡,韦一航以在场的方式参与了自己未来的缺席。《再见吧!少年》中病故后的王新阳在演唱会大屏幕上对家人的温情告白也以同样的方式阐释了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病危的马小远,同样也在日薄虞渊之际,用影像的方式延展了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透过银幕的镜像投射,影像中包孕的“生命—疾病—死亡—影像—永生”之间的关联,也在电影文本的召唤结构中,被有着不同“前见”的观众嵌入脑中,并经由“知性”的过滤,而获得异质性的审美体验。
二、酒神精神的载体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用日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来象征艺术的两种形态。日神精神在艺术中体现为恬静睡梦般对现实的美化,以“梦”为表征;酒神精神在艺术中则体现为纵情沉醉般投入生命的狂澜,以“醉”为境界。这与“一阴一阳谓之道”的中国哲学观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骏马秋风冀北”的阳刚,后者是“杏花春雨江南”的阴柔。在青春电影《芳华》中,刘峰的病症是他那残缺的右手,而导致他悲剧的根源却是文工团那次错误的拥抱。在那段场景中,冯小刚用朦胧的色彩和曼妙的歌声滋润与催化了“活雷锋”潜意识里暗潮涌动的“力比多”,使其处于酒神的狂欢醉境之中。于是,平日里以“超我”占据身体话语权的“雷锋标兵”终是在那一瞬间让久经压抑的“伊德”夺得先机,成为后日里疾病的根源。酒神精神中的狂欢意味着人们释放“超我”的禁锢从而进入“本我”的无意识状态,其目的就是让主体解放本真的状态,故而造成刘峰残疾的起源正是酒神精神的介入。只是在遭遇了爱情受挫、战友背叛、人性鞭挞、身体残缺等一系列悲惨境遇之后,刘峰不仅没有失去本真状态,反而以磨而不磷的人生态度笑对生活的种种苦悲。这正是尼采所极力推崇的超人哲学,即身体的落败无碍于意志的永恒。
如果说酒神精神的迷醉是刘峰疾病的根源,那对于患有精神病的何小萍来说,便是治愈疾病的良药。在《沂蒙颂》舞台剧那场戏中,患有精神病的何小萍,在听到旧曲《沂蒙颂》的袅袅之音时,不自觉地进入了迷醉的境界,以超然卓绝的身姿在草地里月下独舞。在这1分27秒的独舞中,无论是银幕内的何小萍还是银幕外的观众霎时间都体悟到了庄周那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美。而这大美也正是“酒神精神”的东方式表达。在这“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的迷醉之境中,曾经的折辱也好,扭曲也罢,一切都被此时的狂欢与醇美疗愈了。何小萍曲终舞毕的那一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更是将酒神的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醉”是一种体验,一种自我和万物和解的愉悦和满足,更是何小萍在遍尝人间酸苦后所大觉的自由之道。
这在《山楂树之恋》中亦有类似的呈现。影片中,正是因为“白血病”的介入,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在那个禁忌年代才得以短暂性地获得了酒神的迷醉与狂欢。因为只有在高悬的死亡阴影下,人的爱欲才会突破禁忌到达自然之境。白血病纯洁的“白”象征着老三和静秋之间至纯至真的爱恋,白血病猩红色的“血”则既是他们情欲的诱发剂,又是指引老三和静秋进入酒神之境的道法之门。而白血病玄黑色的“病”,则成了悲天悯人的法器,在剥夺老三生命的同时,也为他们的爱情赋上一曲激慨壮美的悲歌。这正如酒神颂歌在悲叹狄奥尼索斯尘世受苦的同时却赞美他的新生一般。人们在个体生命的消亡中体验到一种万物归一的沉醉,以此产生酒神式的悲剧快感。伴随老三肉体的湮灭,极致的美与极致的悲在影片中合二为一,孕育出崇高的种子,撒播在观众的心中,开出一朵朵绚烂的山里红花。而在张扬的电影《昨天》中,酒神的疯癫之气,更是将贾宏声置入一种朝圣般的迷狂之中,以一种神灵附体的状态,使其无限趋近艺术与真理的云端。
三、惩罚与规训的青春寓言
智障、抑郁等患有精神类疾病的角色,在青春电影中常作为某种隐喻的形象出现。创作者们将自身无意识的呐喊、控诉凝缩成这一类患有灵魂病的角色符号,并借由他们的癫狂和失语来抵抗、规避话语机制的规训与惩罚,以实现内在欲望与现实梦想之间的暂时性缝合。他们或是作为艺术家对自我被规训的反思与无意识抵抗,用“傻子”的形象换喻为自身少时的镜像,并曲笔绘出“自我”是如何从个体被询换为主体的过程:天才—疯子—驯化—失语—主体。又或是借由“傻子”这个符号来消解主流话语所定义的崇高与伟大。这一点,早在1994年的青春片《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就已有所体现。片中只会喃喃念叨“古伦木、伦巴”的傻子,却在片尾听到“我们”这群自诩聪明的人朝北京呐喊“古伦木、伦巴”时,说了一句“傻逼”,颇具讽刺意味,暗喻着青春岁月里的我们都是“傻子”。
新世纪以来,在多部青春影片中也都能窥见“傻子哲学”的身影。电影《孔雀》中,大哥高卫国就是以患有脑疾的傻子形象出现的。借由“脑疾”这一层外衣,他遵循了乱世之中“虚己”以“保身”的混世原则,“遵从”“无争”“妥协”“避让”这些在现代观影者看来“前现代”的特质在他的身上毫不违和,既不让人生厌,也不叫人乏味,没有人会追问他有没有自我,更没有人会要求他去承应“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这一切只因他的身上有一个预设的前提——脑疾。因此,他可以在母亲因丢钱痛哭而全家沉默时,避过伦理的规训置身事外,也可以略过自古以来长兄如父的责任,心安理得地享受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福利。在“脑疾”的躯壳下,他想怎么活都理所应当。所以,高卫国真的“傻”么?这里可化用雪莱那一句“浅水喧闹,深潭无波”作解。诚然,他是以脑疾的形象登场的,但回看兄妹三人的青春岁月,却只他一人做到了且以喜乐、且以永日的达观,也只他一人能够在木槿昔年的岁月里,体会到沂水弦歌的逍遥自在。《道德经》第45章载入:“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4]大抵可以用来形容高卫国的为人处世,只是在此番“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4]的处世哲学之下,疾病倒成了最好的掩护外衣。这难说不是导演顾长卫在借“脑疾”这一灵魂残缺的意象,传达出在时代的裹挟中,我们若想“保身”“全生”“养亲”“尽年”,就必须“虚己以游世”“混世于江湖”的哲学寓言。
与之相对,在王小帅的电影《青红》中,疾病叙事的审美价值则趋向于对父权的无力呐喊。青红的精神病一方面是作为女性的她在遭遇父权压制和男性性暴力的双重围猎后,无奈选择的控诉方式;而另一方面,精神病也象征着青红开始放弃抵抗,并对自我的青春进行阉割,以达到对父权规训机制的完全服从。这也正是女性沦为“他者”的根源。关于这一点,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已经做了理性的阐释。波伏娃认为,女性对男性的附庸是伴随私有制的诞生被确立的,“她”首先是她父亲的财产,然后是丈夫的财产。在父亲还未通过婚姻把权力转交给“她”未来的丈夫之前,父亲拥有对女儿贞操的规训与监禁权。是的,电影中青红的青春仿佛一直被监禁在一座全景敞视监狱中,父亲无时无刻不在那象征权力的瞭望塔上,以爱之名监视着她成长中的一举一动。于是,在父亲这个“他者”反反复复的惩罚与规训中,她将作为人类个体的自我建构成了合乎标准的第二性。此外,她还遭遇了来自爱恋对象小根的性暴力,前者是象征着父权的亲情,后者是隐喻着“夫权”的爱情,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青红都遭到了来自男权的压迫。所以她先是以自杀的方式试图毁灭肉体带来的枷锁与不堪,在毁灭失败后她又谋得了另一种戕杀自身的方式——精神病。于是,她的青春便同她那坏了的精神一般,随着那段岁月的逝去被阉割。
四、权力与话语的隐喻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提到:“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5]的确,疾病本身就是一种驳杂的隐喻。“先天性心脏病”意味着主体对自身健康话语权的天然丧失,患者自身既毫无过错也别无选择,这种病症成了物竞天择的命运悲剧。而在电影《奇迹笨小孩》中,这种疾病的天然属性也隐喻着“景浩们”迁出故乡,来到深圳这座“异托邦”时所处的困窘境遇:对于这座造梦的城市而言,不隶属于精英分子的异邦人是城市的“他者”,也是对自身健康丧失话语权的“先天心脏病患者”。于是,导演利用“先天性心脏病”这个隐喻符号及触发机制,将景浩妹妹迫在眉睫的手术期限同深圳于1981年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形成镜像互文。没有30万,景浩妹妹的心脏病就无法疗愈,隐喻着没有金钱,景浩就丧失了保护家人生命的话语权。从表层看,这是一个在深圳创业的青春励志故事,景浩成了尼采强力意志的践行者。但面罩之下,我们似乎窥得一个悖论: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生命的权利。
诚然,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摆脱普遍的贫困,“景浩们”对那句口号的响应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当下青年人来说,生命的意义远非金钱和效率可以涵盖的,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生存权利的励志事迹更是颇具剖腹藏珠的意味。况且,影片中代表着精英话语的“赵总”又何尝不是上一代的“景浩”,而处于话语边缘的“景浩”又何尝不是“年轻赵总”的镜像对照?曾经,他们都是这座城市的“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被排异、驱逐。最后,也都成长为新一代的强权文化的守护者,排异、驱逐新的“先天心脏病患者”。于是,围绕着疾病展开的故事,其内核既隐喻了异乡“他者”对城市主体话语的争夺,也指涉了当代青年人为接近权力中心而作出的病态拼搏。此外,电影中还出现了“耳疾”的隐喻。“耳疾”意味着寂静和失语,它既隐喻着在男性强健的生理构造面前,作为“第二性”的汪春梅面对暴力时的失语与无力反抗,又隐喻着资本家对工人权利的剥削和暴力的围堵。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阶级统治将永远消亡,而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也随之告终”。作为无产阶级女工的汪春梅,疾病点燃了她潜意识中“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火苗,使其在挣脱女性枷锁的同时,也在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领地中,点起了一盏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与《奇迹笨小孩》的励志青春不同,电影《推拿》是一部关于盲人的“残酷青春物语”。如果按福柯对权力与话语运作模式的读解,整个主流社会是一个全景敞式监狱,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各自的牢房中接受自我与他者的双重凝视的话,那么“沙宗琪推拿中心”这个特定的场域则可以定义为“支流”社会。在主流社会中,瞭望塔的顶端是权力的监督者。而对于盲人来说,有眼睛的正常人就都是权力的化身。在看与被看间,他们永远都只能处于被看的亚姿态。相较于主流社会的层级监视,微观权力对他们的压抑则更深。加之视觉功能的剥离,身体的触碰便成为他们话语交流的主要方式,这便形成了一个悖论:视觉快感的剥离使盲人所产生的“力比多”压抑较常人更甚,而永无止境的黑暗又将他们钉在了全景敞视监狱中最为外显的位置上,这使得身体的诉求与愉悦的权利始终以两极的状态在他们的意识中不断博弈。然而,出于对后代遗传基因的保护,疾病作为权力的隐喻,将他们的肉体规训在了那个只属于盲人的、割裂的空间之中。故而无论沙复明多么的优秀博学,都很难得到“主流社会”女性的认可。
而关于盲人的情欲书写这一点,在小马的身上体现更为明显。因车祸而失明的小马同先天性盲障有所不同,他是经历了生殖器期(产生“恋母情结”的时期)之后、生殖期之前失明的。这也意味着性心理年龄停留在第三阶段的小马,对有着“成熟”气味嫂子产生爱恋是有迹可循的。这种爱恋是“性本能”层面的,是对幼时占有“母亲”话语权的蔓延,也是其心理上对性愉悦权利失控所作出的扭曲反应。而后,按摩女郎小蛮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暂时性弥合了小马因性压抑而产生的心理裂隙。在小马看来,“小蛮”作为正常女性的符号,她对自己的接纳,意味着主流群体对自身可以拥有合理性话语权的认可。在与小蛮朦胧的性体验中,他开始尝试“垄断”对小蛮身体的话语权。但他未意识到小蛮同样属于丧失性支配权的边缘群体。作为权力与话语的隐喻,小蛮的“疾病”是一种将自身“物化”而不自知的“现代病”——她将自己身体和性的支配权以商品的形式售卖给了所有购买此商品的人。于是,想象性地以为自己拥有了对小蛮身体话语权的小马被小蛮的“商品购买者”暴力捶打。这种暴力象征着主流男性对小马越过交易秩序、不守“等级尊卑”的规训与惩罚。小马的失明,隐喻着作为男性的他拥有完整爱情的权利被阉割。电影结尾,小马的复明也隐喻着权利的修复与重获,他跨越了与小蛮正常两性之间的话语鸿沟。对于小蛮,也逃脱了“按摩店”那个场域中被“异化”的话语体系,从而获得自醒的认知。
五、结语
新世纪以来的青春电影中,疾病既可作为一种叙事元素为电影“拄起叙事的拐杖”,又可刺破叙事的表层,直击其蕴藉的美学要义。它既可化身为酒神精神的载体,让患者超然物外,领悟生死齐一的境界;亦可化作一则抵抗规训与惩罚的青春寓言,成为大智如愚的隐匿外衣;还能作为权力与话语的隐喻,释放出那些藏于疾病表征之下的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压制。在当下以“功绩”为主流价值的社会里,青年人需要一些“美”的启发来消解现实的疼痛与压力,只是这种消解不是麻痹,而是自醒,一种在疾病与灾难面前尽管罹难重重,却依旧保持生之热爱的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