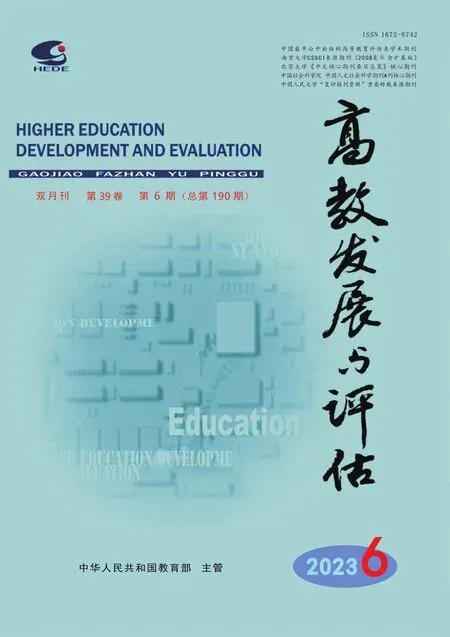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德育困局
朱鲜峰
(1.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2. 湖南师范大学乡村教育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081)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节点,对此后中国高等教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因此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就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一方面,不少研究着重探讨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成就,淡化其在办学过程中面临的困难,甚至通过纪念蔡元培的贡献来表达自身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蔡元培神话”[1];另一方面,对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学界也多有关注,但其教育思想如何转化为教育实践,其间又有何种调整,相关研究仍不够充分。蔡元培在北大的德育探索及其面临的困局即处于这一理想与现实、思想与实践交织的地带。对上述困局进行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我们返回历史现场,重新思考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与办学语境。
一、德育地位的确立与动摇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借助德国古典大学理念,将北大改造为研究高深学问的现代学府,学界对此多有关注和研究。与此相对应,德育在德国古典大学观中占有何种地位,蔡元培在实际办学中如何处理德育问题,似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就理念层面而言,德国古典大学并非不强调德育。研究者指出,德国古典大学的“修养”(Bildung)观念即具有道德、宗教、精神等多方面的内涵,但在德国大学的实际办学中,往往强调通过心智训练获得通识性的修养[2],此种“修养”偏重理性而非道德。以德国教育家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蔡元培曾译介该书的总论部分)所介绍的情况为例,该书仅有极少数篇幅谈及道德,而其所论述的道德为“自由”和“荣誉”,即学术的自由与追求真理的荣誉,二者与理性有密切联系。[3]由此可见,在当时的德国大学中,通常意义上的德育并未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一位对中外道德传统有深入认识、人品堪为楷模的教育家,蔡元培对于德育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在其为人所熟知的“五育并举”思想中,公民道德教育即处于中坚地位。因此,在大学德育层面,蔡元培并未对德国古典大学观亦步亦趋,而是将其作了本土性转化。例如,在论述“修养”时,蔡元培主要是从道德层面着眼,“修养道德”“修养德性”等表述在其著述中并不鲜见。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演说中,针对此前北大存在的问题,蔡元培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大主张[4]8-10,其中第一点指向“学术”,后两点则指向“道德”。蔡元培在其他演讲中明确指出:“大学目的有二:一为研究学问,二为培养人格。”[5]可见他对大学的学术使命与道德使命均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尽管蔡元培在演讲中往往将“学术”与“道德”并举,但在实际办学中必然会有所偏重。就客观情况来看,应当说,蔡元培更为看重的是学术研究。担任北大校长一年之后,蔡元培试图加强学校的德育,并对此作了解释:“会一年来鞅掌于大体之改革,未遑及此。”[6]3可见德育的改革并非蔡元培心目中最急迫之事。在著名的《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蔡元培坦言个别教员德行有亏,又进而指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7]为求得学术人才而不惜降低道德标准,固然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不得已之举,但这同时也成为影响北大德育工作开展的一个隐忧。
从这一时期北大的课程设置来看,课表中与道德较为密切的是伦理学课程,并未开设修身课程。[8]对于伦理学与修身书的区别,蔡元培曾作过如下分析:“修身书,示人以实行道德之规范者也……伦理学则不然,以研究学理为的……其于一时之利害,多数人之向背,皆不必顾。盖伦理学者,知识之径途;而修身书者,则行为之标准也。持修身书之见解以治伦理学,常足为学识进步之障碍。”[9]蔡元培清楚地指出,伦理学研究不必考虑社会的道德观念,若试图通过研究伦理学来为社会树立道德标准,反而不利于学术的进步。可见,北大开设伦理学课程并非从德育的角度着眼,而是偏重学理分析。这也意味着,就课程层面而言,德育的地位并未凸显。
在实际教学中,“道德”也受到“学术”的挤压,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例如,章太炎弟子、著名史学家朱希祖上课时,常有学生起身质问或指摘讲义中的纰漏,甚至一度发展为写匿名信进行人身攻击。[10]燕树棠、王世杰在行政法、国际法课程上一改传统的“纯粹讲义制”,采用“简单讲义方法”,部分学生并不赞同,通过写匿名信甚至张贴匿名揭帖的形式表达不满,极大伤害了师生感情,以致燕树棠与王世杰一度以辞去北大教职相抗争。[11]在上述事例中,学生为争学术之是非与教学方法之优劣,忘却了对教师的尊敬,也从侧面反映出德育的地位在教学中并不明确。
由上可知,蔡元培在借鉴德国古典大学重视理性修养这一传统的同时,进一步强调道德的修养。然而,求“善”与求“真”二者存在内在冲突,在北大的办学实践中,德育的地位受到学术的冲击。在师资层面,蔡元培为求取学术人才而放宽了道德标准;在课程层面,北大并未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在教学层面,学术上的平等观念消解了传统的师道尊严,尊敬师长这一基本的道德准则也因此受到动摇。在此情形下如何重新树立德育的地位,采用何种方式开展德育,成为蔡元培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私德的培育及其困境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知识界对中国传统过于重视私德的倾向多有批判。蔡元培并不赞同这一观点,明确指出:“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曾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6]2在北大的德育实践中,蔡元培始终将培育私德作为重要的一环。
上文谈到,蔡元培强调研究高深学问的理念决定了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中心,并未正式开设修身课或类似的德育课程。蔡元培在演讲中也曾谈及科学对于修养的助益,以及以美育促进道德修养的提升,然而上述方式只能作为辅助手段。经过斟酌,蔡元培决定通过创立进德会来培育私德。
1918年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蔡元培的《北京大学之进德会》一文,标志着该会初步成立。文章将进德会会员分为三个等级: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6]4(后略有调整,规定前三条为基本戒约,其他五条戒约可自由选择。)入会时由本人注明愿为某种会员。
从形式来看,蔡元培之所以选择社团性质的进德会,其直接渊源为李石曾、吴稚晖等人191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的进德会。蔡元培此前曾加入该会,对其组织结构较为熟悉。对比北京大学进德会的戒约与上海进德会的会约,两会所定的条目相同,只是等级划分稍有差异[12],可见二者的承袭关系。在北大内部,1917年4月,学生朱一鹗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同学俭学会”,该会简章曾呈给蔡元培,得到其首肯。俭学会规约中亦有“勿赌博”“勿狎妓”“勿吃烟”“勿吃酒”等条目。[13]该会在当时北大的众多社团中虽不显眼,但由此可见,学生层面也有涵养私德的呼声,这无疑为蔡元培在北大创立进德会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若将视野进一步放宽,进德会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中国士人的结社传统与西方大学的社团传统,进德的取向及师生共同参与的特点又使其区别于以兴趣为导向的学生社团,为当时的大学德育开拓了新的途径。
就内容而言,进德会的上述要求存在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强调个人的修养与习惯,不涉及私人交往中的道德准则。通常来说,私德既包含前者,也包含后者,特别是亲人朋友间的道德关系。尽管蔡元培本人是著名的孝子[14],但北大进德会回避了在当时引起激烈争论的孝道等传统伦理道德,客观上搁置了相关争议。其二,突破了“内圣外王”的儒学传统。蔡元培提出“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与“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传统截然相反,意味着其切断了“内圣”与“外王”之间的联系。而在当时官场腐败、风气污浊的背景下,不做官吏与议员显然超出了职业选择的范畴,实质上是洁身自好的体现。其三,标准较低,且均为否定性的道德。蔡元培本人对此作了解释:“进德之名,非谓能守会规即为有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即孟子‘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之义也。”[15]较之相对抽象的肯定性的道德,否定性的戒约更具有操作性,这也表明了蔡元培务实的姿态。今日看来,其中几条戒约似属于道德底线,由此亦可见当时私德普遍受到轻视的严峻现实。
1918年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进德会首批会员,包括甲种会员19人,乙种会员9人,丙种会员2人,其中蔡元培本人为乙种会员。[16]此后会员人数不断增加,截至1918年5月18日,校内会员人数已达469人,其中包括职员92人,教员76人,学生301人。[17]据统计,这一时期北大教员总数为217人,学生总数为1 980人[18],按照比例计算,加入进德会的人数已十分可观。1918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又不断收到入会申请。1919年3月18日,进德会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启事,公布新入会会员,其中包括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1918 年9 月开学后收到的申请至此已达436份。[19]按照常理,进德会的会员人数达到新高,影响也逐步扩大,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然而,该会的工作竟戛然而止,此后未再发布公告。
北大进德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革命烈士王复生(原名王濡廷)1918年秋考入北大,入校前已听说蔡元培发起成立了进德会。在给父亲的家书中,他提出入学后拟尽早加入进德会,“入会后各方面监视綦严,己有所慑。他人虽欲强之冶游取乐,亦易谢绝”[20]。王复生在1918年10月递交了入会申请,除三条基本戒约之外,还选择了“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吸烟,不饮酒”四条戒约,体现出严于律己的态度。[21]教员钱玄同加入进德会后,基本能够遵守戒约,1919 年2 月4日,因天气太冷,到西车站吃了一顿西餐,并喝了一杯白兰地酒。为减少内心的不安,他在日记中为自己辩解:“为驱寒而喝酒,或可以说是喝药酒,不算犯进德会会规罢!”[22]可见进德会戒约对其仍有所约束。
与此同时,进德会也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其中包括如何切实帮助会员“进德”,如何进行监督,对违反戒约者如何惩罚,等等。总体来看,进德会在上述几方面均无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一个方面,有会员提议通过时常开会来促进会员的交流[23]3-4,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一建议并未被采纳。第二个方面,按照蔡元培最初的计划,进德会设评议员与纠察员,前者负责审议,后者负责监督。在1918年6月29日召开的评议员纠察员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纠察员的李大钊指出,纠察员的职责不易履行,建议取消这一名目,会议表决将已选出的纠察员全部改为评议员,这也就意味着由会员进行相互监督。第三个方面,在取消纠察员之后,进德会规定,如有违反戒约的情况,由其他会员签名报告,书记收到报告后通信劝告该会员,若此后仍违反戒约,经会员十人以上签名报告,由评议员展开调查,如果属实,开评议会宣告除名。[24]可见,上述规定较为繁琐,不易执行。
由于进德会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在实践中也出现诸多问题。首先,进德会戒约的执行基本上依靠会员的自觉,而个人的自觉是不可靠的。自蔡元培发起成立进德会后,学校内外对于部分会员不守戒约的责难之声就未停止过。1918 年10 月17日,学生梁绍文上书蔡元培:“我常常听见别人说,进德会的人,亦有叉麻雀的,赞成进德会的人,亦有逛窑子的,这样子看来,进德会的条文,不过一种欺人之具罢了。”[23]3其次,会员之间相互检举的约戒既不现实,也不利于组织内部的团结。事实上并未有人因受到检举而被除名。此外,也有人认为,道德是个人的事情,不应通过社团来标榜,因此不屑于入进德会。[25]面对外界的质疑,蔡元培最初尚能以进德会会员众多,难免有人不守戒约作解释。然而,随着攻击北大文科学长、进德会评议员陈独秀私德不修的报道闹得沸沸扬扬[26],蔡元培不得不作出回应。1919 年3 月26 日,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等连夜开会商讨,最终决定免去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务。但此次风波对进德会还是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此之后,进德会再未发布消息。
总体而言,蔡元培通过进德会培育私德的尝试不乏新意,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从进德会的会员数量来看,蔡元培对私德的重视得到大量师生的认可,表明进德会在观念层面并未遭遇大的阻碍。然而,北大进德会的戒约系从他处借鉴而来,并未根据自身的环境和特点作大的调整,相关规章制度也不够完善,加之此时北大正处在从“官僚养成所”向现代大学转化的时期,旧习仍有一定惯性,难免出现泥沙俱下的情形,进德会也因此遭受严重挫折,难以为继。
三、公德的培养及其问题
作为一位具有宏阔视野的现代教育家,在私德之外,蔡元培亦十分重视公德的培养。他指出,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举动“往往就一人一家着想,而乏团体社会之观念”[4]102,亦即缺乏公德。在蔡元培看来,“公尔忘私之心,于道德最为高尚,而社会之进步,实由于是……使人人持自利主义,而漠然于社会之利害,则其社会必日趋腐败,而人民必日就零落……”[27]116。蔡元培在论述公德时,强调的是对社会利益的关心,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中的规范与准则。对当时的北大学生而言,国家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则是微型的社会,“爱国”与“爱校”是公德中较为显著的两个方面,以下即围绕这两个方面作重点讨论。
对于“爱国”与“爱校”,蔡元培均有独立的见解。蔡元培的道德观念含有某种世界主义的立场。他曾指出:“故为国家计,亦当以有利于国,而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为标准。而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4]531可见,爱国是蔡元培非常重视的一种道德品质。但另一方面,鉴于“一战”当中极端的国家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爱国主义之上,蔡元培又强调人道主义,力求实现二者的统一。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认为,学生理应对学校有认同感。他强调“团体的荣誉,就是个人的荣誉”[28]140,在给学生的复信中也指出,作为北大学子“宜爱护母校”[29],要求学生自觉维护学校的名誉。
就这一时期的北大而言,学生“爱国”与“爱校”最集中的体现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蔡元培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本身即怀着一种深挚的爱国情怀。在各种场合的演讲中,他多次提醒学生关心国家与社会。另一方面,蔡元培在1919年5月3日向学生透露了巴黎和会的消息[30],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一页,五四运动充分展现了学生的爱国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在1919年5月4日的游行示威结束之后,学生们积极营救被拘捕的同学,并在蔡元培辞职出京后以罢课要求“挽蔡”,充分彰显出爱校的热忱。从上述角度来说,蔡元培对公德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既不容许学生的“爱国”行为,也不容许蔡元培大力提倡“爱国”。1919年5月4日当天下午,32名参与游行的学生被军警拘捕,其中有北大学生20人。[31]据传北洋政府已决定将蔡元培免职,由马其昶接任北大校长,甚至更有传言称有人要焚毁北京大学,暗杀蔡元培。[4]629-630显然,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严重缺乏开展公德教育的空间。
就蔡元培而言,从现实的角度考量,欲维持学校、保护学生,势必要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有所约束。在观念层面,蔡元培对五四运动亦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他在内心认可学生对国事的关心,但他同时也认为,因罢课而影响学业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对于这一问题,学界已有所探讨,此处拟从德育的角度对蔡元培的立场作进一步的分析。1920年5月,蔡元培在《新教育》杂志发表文章,对一年前的五四运动作了回顾与反思。他指出,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学生的“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28]140。所谓虚荣心,指的是学生将运动视为出风头、邀名誉的机会,而倚赖心指的是学生对群众运动的依赖,把其当作解决问题的一个便捷途径。
针对上述情况,蔡元培尝试在德育方面采取相关措施对学生进行引导,一个重要做法是将学生的爱国之心引导到爱民的途径上。这种引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开展平民教育,其二是关心民间疾苦。
前一方面,在1919 年9 月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着重指出:“傥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情,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望诸君特别注意。”[4]701对于五四运动,蔡元培断言:“五四后的惟一好结果,是平民教育。乘我们用功的余暇办些学校,教育那些失学的人,就是牺牲光阴,也是值得的。”[28]210可见蔡元培希望学生将目光从抽象的国家转向切实的平民教育问题。
后一方面,蔡元培则是以身作则,做出表率。1920年,中国北方地区遭遇大旱,蔡元培联合学校部分教职员工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赈灾会,倡议师生踊跃捐款。部分学生到灾区调查灾情,用文字或照片发表出来,以求引发更为广泛的关注,蔡元培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28]3371922年,浙江遭受特大水灾,蔡元培两次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启事,号召学校师生特别是浙籍师生施以援手。[28]822
上述言论和举措表明,蔡元培试图将爱国主义教育与以“自由、平等、亲爱”[27]10为核心的公民道德教育相结合。这能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德育作用,但其成效亦不能过分高估。五四运动三周年之际,蔡元培曾发表文章感慨:“听讲以外,听听戏,打打扑克,把时间消遣去了,不肯在公益上尽点义务,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人了么?怕不但不是没有,而且还是很多。”[28]616可见虽有蔡元培的极力倡导,仍有部分学生对公共利益并不关心。
就“爱校”这一层面而言,当学校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之时,学生往往不能体谅校方的难处,甚至出现过激举动。发生于1922 年10 月的“讲义费风潮”即集中反映出蔡元培面临的德育困境。由于办学经费拮据,北京大学决定在1922年秋季学期对免费发放讲义的制度进行调整,向学生收取讲义费。部分学生得知消息后,感到自身权利受到侵犯,遂于10月17日下午群拥至学校会计课,谩骂乃至恫吓相关职员。10月18日一早,又有数十名学生涌到校长室,蔡元培与教职员多方解释,学生依然激愤异常,一向温文尔雅的蔡元培也不禁说出“我给你们决斗”[32]的愤怒之语。第二天蔡元培即递交辞呈,最终在学生的挽留下复职。此次风潮经报章披露后,一时舆论哗然,对学校的声誉和办学秩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蔡元培之所以将此事看得极重,主要是在道德层面对北大学生失望。在辞呈中,蔡元培不无沉痛地写道:“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28]784-785在复职后召开的全校大会上,蔡元培再次谈及此次风潮,并着重指出三点:第一,此种有损人格的举动竟然出自于大学学生,使人失望;第二,讲义费问题本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不应诉诸暴力;第三,此次风潮竟有不少学生盲从,更有不少学生隔岸观火,令人心寒。[28]788上述几点均指向道德层面的批评。
对于如何避免类似的风潮再次发生,蔡元培并未止于强调遵守校纪校规,而是更进一层,一方面是动之以情,唤起学生的道德情感:“本校现正在最困难的地位,不是全校同人齐心协力来维持他,怕的终不免有破坏的一日呵!”[28]789另一方面则晓之以理,指出应敬爱师长,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我们若是为维持本校……总要大家保持一种良好的感情,不要多所猜疑。”[28]789在他看来,“爱校”应从外在的要求转化为学生内在的自觉。
不过,就在“讲义费风潮”发生三个月后,蔡元培因“罗文干案”辞职(有论者指出,此次辞职与“讲义费风潮”亦有关联)。[33]1923年6月,北大学生会派代表赴上海请蔡元培返校复职,蔡元培在给学生会的信中说明了无法返校的缘由,同时特别指出:“培以为电报政策,群众运动,在今日之中国,均成弩末。诸君爱国爱校,均当表示实力(指共同筹措学校经费——笔者注),请于维持母校一试之。”[34]其对运动式的“爱国爱校”的态度显而易见。蔡元培此后数年只在名义上担任北大校长,德育方面的改革和探索自然也就此中断。
由上可知,五四运动凸显了北大学生爱国爱校的情怀,但学生运动这一形式有其弊端,“讲义费风潮”则暴露出部分学生爱校意识的欠缺。蔡元培试图对此作出引导,力求将抽象的“爱国”落实为具体的“爱民”,并在“情”与“理”两方面增强学生爱校的自觉。然而,一方面,政治的黑暗令学生不能满足于埋头读书与从事成效较缓的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运动的胜利也助长了部分学生心态的膨胀,不再安于听从师长的教导。在恶劣的政治生态之下,蔡元培亦不免屡次辞职,其培养公德的举措和成效也随之受到影响。
结语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正值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的变革与动荡之际,加之德育本身的复杂性,使得蔡元培在北大开展德育之时面临诸多困难。
首先,从理念层面来看,蔡元培对德国古典大学观作了本土转化,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同时,将德育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学术的求真取向与道德的求善取向之间存在内在冲突,蔡元培未能充分调和二者的矛盾。就德育观而言,面对“中西”与“公私”之争,蔡元培持相对稳健的立场,试图融通中西,兼重公德与私德,但同时也为不同道德观念的冲突留下了空间。此外,“公”“私”截然二分的方式实质上延续了梁启超《新民说》中的思路[35],有其历史局限性。
其次,就制度层面而论,由于德国古典大学制度强调通过系统的学术训练培养学生的理性,蔡元培将这一制度移植到中国时,在德育方面并无充足的制度资源可供借鉴。另一方面,蔡元培对古代书院重视德育的传统有所体认[36],但在实际办学中,受制于“教授治校”“选科制”等北大整体的治理原则和制度设计,并未充分利用书院在德育方面的相关经验和举措。进德会作为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培育私德的主要方式,融合了中国的结社传统与西方大学的社团传统,在德育形式上有所创新,但其构想与规章并非来自教育领域,总体而言组织较为松散,规章制度亦不够完善。对于公德的培养,蔡元培则主要借助个人的演讲及校役夜班、平民讲演等相对灵活的形式。总之,这一时期北大在德育方面并未形成固定而成熟的制度,因而缺乏约束力。
最后,在实践层面来看,蔡元培在开展德育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北大的师资、课程与教学均以学术为中心,德育的地位发生动摇。蔡元培试图在私德与公德两方面加强德育,然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通过进德会培育私德的努力受旧习的制约而遭受挫折;另一方面,蔡元培尝试引导学生将“爱国”落实为“爱民”,而非罢课与游行,并注重增强学生爱校的自觉,但这一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公德教育的开展受到政治现实的掣肘,加之北大学生的自主意识空前高涨,不安于听从师长的道德说教,使得蔡元培培养公德的相关举措不易收到成效。
更进一层而言,蔡元培与北大的德育困局并非近代中国特定大学所面临的个别性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现代大学德育面临的普遍困境。在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大学同样出现了“知识”与“道德”的分离,以及随之而来的德育的削弱。[37]就这一层面来说,重温蔡元培对大学德育的探索与尝试对于当前的大学教育依然有其重要意义。